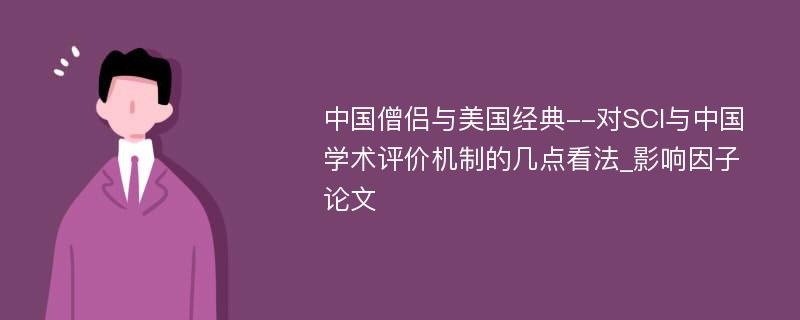
中国的和尚与美国的经——关于SCI与中国学术评价机制的几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几点论文,美国论文,和尚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14)06-0011-04 近期出版的《中国科学报》报道,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韦恩·谢克曼于诺贝尔奖颁奖前夜在英国《卫报》发表了署名文章“《自然》、《细胞》和《科学》这类顶级期刊正如何损害科学”,呼吁科学界应该推翻顶级期刊的暴政[1]。这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谢克曼教授的身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这则报道在医学界引发的反响尤为强烈。长期以来,对于学术评价、人才评价、课题评审等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被反思,反思的范畴也从三大科学杂志扩展到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 1 SCI与中国 SCI于1961年根据现代情报学家尤金·加菲尔德1953年提出的引文思想而创立,和与其类似并同为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科技会议录索引》(Index to Scientific Technical Proceedings,ISTP)、《科学评论索引》(Index to Scientific Reviews,ISR)以及由美国工程信息公司出版的《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EI),并称为当今世界的四大检索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将SCI引入教师的职称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开启了中国科研评价的定量化时代,SCI这本美国的经开始被摆在了中国研究者的庙堂之上。20余年来,中国国际论文发表的数量迅速增长,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统计,2003年~2013年(截至2013年9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14.30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仅2012年,我国作者以第一作者发表的SCI论文就达到16.47万篇[2]。然而,对SCI的质疑从未停止过,有时甚至是“骂声一片”。游苏宁将SCI称为“Stupid Chinese Index”,而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更是戏谑地评价“SCI成了Stupid Chinese Idea”[3]。 2 SCI与学术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几乎与SCI进入中国同时开始的这场旷日持久且波及甚广的论战,其核心问题实质是在讨论中国的学术评价问题,要不要SCI来评价我们的学术水平,这首先应当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2.1 需求度的问题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SCI?这是我们面对SCI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常识,没有需求则供给就会丧失意义,因此需求度问题是讨论SCI与学术评价的首要问题。SCI通过引文数据分析和同行评估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估期刊的学术价值,其收录的万余种期刊覆盖了国际上大多数有重要影响的刊物,是国际公认的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准的代表性工具,SCI论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及其科技实力。这也是将SCI引入学术评价的重要原因,正如原南京大学校长、我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曲钦岳教授[4]在谈到为何要将SCI引入南京大学的学术评价时所指出的:“对于科技研究成果的质量问题基本上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评价标准。在成果鉴定或教授职称评审时,很多人都说自己的学术论文、研究成果是‘国内第一’、‘国际先进’的。但究竟是否先进、是否一流并不清楚。”这个简单的初衷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992年~1999年,南京大学在各大学SCI论文评估中实现了“八连冠”;1995年12月7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科学的文章,其中将南京大学的经验概括成一篇题为“南京大学:努力追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的短文[5]。上述种种使南京大学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除了这种个体的收获以外,就群体而言,收益更为明显。SCI的索引功能拓宽了获取最需要文献信息的途径,科研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本领域或即将探索领域的研究数据,从而减少重复研究或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SCI还可以高效地展示某学科的发展过程,获取包括研究评论、理论证实、工作扩展、方法改善、假说验证以及概念创新等内容在内的最新科技发展信息。我国的科学研究在SCI引入中国后获得了空前的国际认可,一方面获得了国际上先进的科学研究资讯,另一方面也为全球的科技进步贡献着中国力量,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国内与国际的双赢。科学研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从客观上推动了国内外的科技合作,很多国内的专家学者纷纷走出国门,在将中国的学术观点带出国门的同时,也将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带回国内,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我国的科技进步。随着我国科技进步步伐的加快,我们对于SCI的需求程度与SCI对我们的需求程度必将不断增高。 2.2 契合度的问题 SCI与中国科研是否能够契合是其能否被用于学术评价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SCI能够与我国科学研究契合则能用于科学评价,反之,无论其多好也不能用于学术评价。SCI与中国科研的契合度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要看我国科技人员对于SCI的适应程度,如果我国科技人员无法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则说明契合度不好,我们将SCI引入中国可能有些操之过急,甚至是揠苗助长,反之则说明契合度良好;另一方面要看SCI在中国的推广普及程度,如果只有“985”高校等研究型大学和中科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认可SCI,则说明其契合度差,反之如果国内的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接纳SCI,则说明其契合度好。最新出版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的数据显示,仅2011年,SCI就收录了我国作者发表的论文136 445篇,是1995年的17倍。从2005年至今,每年都以1万余篇的速度递增,在这13万余篇论文中,有83.2%的论文发表于国外杂志[6]。这表明,我国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并没有如SCI被引进中国时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受到地域和语言的影响,我国科研人员对SCI展现了良好的适应性。与此同时,SCI在我国的接受度也在逐步扩大,适用主体从最初只有几所重点高校采纳逐步推广到国内大部分高校认可,再到当前很多省级职称评定标准中也将SCI作为学术成果的一项重要要求纳入其中;适用范围从原本的教授、副教授的晋升逐步扩展到博士研究生毕业。这说明SCI在我国的普及程度和接受程度在逐步加大、加深。从以上两点不难看出,SCI与中国的科学研究展现出了良好的契合度,初步具备了成为一种学术评价标准的基础。 2.3 质与量的问题 质与量的问题是SCI与学术评价讨论的另一焦点。客观地讲,我国科研论文的总体水平不高,根据一项以引用频次为标准的研究表明,我国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6.92次,而世界的平均值为10.69次,我国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虽与世界平均值差距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论文的发表数量过大且引用频次不高造成的[2]。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主要应该看我们的论文“量”是否有所提高,并且这种提高是否带来了“质”的改善,而不是单纯地看质与量之间的比例关系。从图书情报学的角度看,论文的质一般依靠“表现不俗”的论文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热点论文数量、世界名刊的论文数量以及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表现不俗”的论文是指统计年度内被引用次数超过某个学科领域世界均值的论文,这说明该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超过其所在学科的一般水平,2012年我国此类论文数为4.35万篇,占论文总数的26.4%。高被引论文是指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论文,2003年~2013年,我国此类论文总数为9 524篇,占全球总数的8.6%,位居世界第4位[2]。热点论文是指发表后2年内就得到大量引用的论文,这些论文往往就是被引用次数排在各学科前1‰的论文,并且在未来的更长时间内会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截至2013年9月,我国的热点论文数为349篇,占世界热点论文总数的14.3%[2]。世界名刊的论文是指发表于Cell、Nature和Science三个享有国际公认的最高学术声誉的科技期刊的论文,这些论文往往经过全球知名专家层层审读、反复修改而成,论文的质量、水平较高。2012年以上三种期刊共刊登论文5 983篇。其中,中国论文为187篇,排在世界第9位。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是指各学科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在此暂不考虑影响因子的科学性,仅以其同一性作为参考标准。2012年176个学科领域中高影响力期刊共有150种,共发表论文47 651篇,其中,中国发表4 020篇,占世界的8.4%,排在世界第2位。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尽管无法得出我国论文的水平很高的结论,但肯定可以驳斥我国论文水平很低的论调,而站在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论文水平在SCI进入中国后应该还是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在SCI“量”上的积累推动了当前部分“质”的提升。 2.4 代用品的问题 在关于SCI与学术评价问题的论战中,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SCI不是一个合适的评价标准,那什么才是?所谓“不破不立”,从逻辑上看,我们往往更注重“破”是“立”的前提,但却忽视了“立”是“破”的必然结果,无“立”之“破”不如不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标准来取代SCI,那么还不如不要取消SCI。就学术评价而言,可资利用的标准并不多,其中比较常见的除了论文外,主要还包括图书以及同行评价——课题与奖励的评审主要也是通过同行专家来完成。同行专家评价的路子我们走过,伴之而来的是对于评价的客观性的质疑,很多学者不把精力放存研究上而是放到了拉人情、搞关系上,而且随着学科分工的细化和学科交叉的增多,很多前沿领域很难在国内找到合适的同行专家,学科相近的专家又很难界定相关成果的学术价值,同行评价恐怕会带来比SCI更多的问题。以图书为标准面临的问题同样不少,仅对图书的学术评价一点就已然十分困难,从概率上讲,图书的出版水平会跟出版社的级别、规模呈正相关,但如果硬性圈定某些出版社,其效果与SCI何异?最后再来看论文,国内当前评价论文首先是通过评价杂志的方式,认定理工科杂志的除了SCI之外,还有EI、CSCI等,认定人文社科杂志的有SSCI、CSSCI、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等。除了杂志外,认定论文实际水平的还包括其他内容,就人文社科论文而言,还包括:是否有国家或省级的立项课题支持,是否被他人引用,是否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是否被某级政府采用以及是否被某级别领导批示等多个方面,其复杂程度远超SCI。如果我们认为SCI不是学术评价的适当标准,那么上述提到的内容哪个才是?而这个新成立的标准会不会也像SCI一样被打倒?很明显,没有人认可回到那个用人脉评价学术的年代。 2.5 和尚与经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关于SCI与学术评价争论的本质是学术评价机制的问题,SCI只是一个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哪种标准都会引发这些争论。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关于评价机制的讨论,那么我们可能找错了对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观念的关键不在于外来的经而存于念经的和尚。SCI仅是一本美国的经,中国学术评价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和尚,从这个角度上说,李国杰院士的评价一语中的,愚蠢的是和尚的idea,而不是远来的SCI。SCI是学术评价的一把尺子,这没有问题,全球范围的经验都表明,这是一把客观、有效的尺子,问题是我们把它变成了唯一的一把尺子,而这把尺子从测量学术的某一个方面变成了全方位评价,职称晋升、课题申报、成果评审等都用这一把尺子,这把尺子还被影响因子标上了精确的刻度。于是,现实变成了无论是从事尖端研究的医学家,还是行走于基层的普通医生,无论从事的是以研究为主的基础工作,还是从事以治疗为主的临床工作,都要唯SCI马首是瞻,都要受制于论文的影响因子。事实上这才是我们批判和改变的真正靶点。 3 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 改变唯SCI论应从改变我国的学术评价机制做起,要把SCI的定量与多元化学术分工的定性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的质和量的建设。 3.1 定性与多元化 任何评价性研究都是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一般情况下,定性会发生在定量之前作为定量研究的基础。我国当前学术评价最大的弊端就是在缺少定性的情况下单纯、盲目地进行定量。当前我国科研工作最大的现实在于复杂与发展不均衡,所谓复杂是指科研工作不仅包括实验室的研究,也包括科技应用和推广,其人员构成上不仅包括研究人员,也包括教育和实践人员。就医务工作者而言,往往会集这三种身份于一体。但就实践中的情况而言,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三种相关却又扮演不同身份的人屈指可数,这些人大多成为了裘法祖、吴孟超这类的医学大家,承担着更多基础性医疗工作的一线人员对于这三种身份只能是疲于应付甚至应接不暇。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构建多元化的学术评价机制以适应这种不均衡。当前,我国医疗系统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医务人员由于其工作岗位、服务对象等不同,工作性质差异较大。可以考虑根据医务人员执业场所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定性要求。服务于大型医疗机构特别是地区级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由于承担着复杂疾病的诊断治疗工作,有必要紧跟国际医学科学进步的趋势,从而不断提高我国的医疗水平,因此SCI的评价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对于服务于中型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是我国医疗保健工作的中间力量,其应当可以完成一定数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对这类医务人员,CSCI等要求足以,SCI则大可不必;而对于那些服务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其主要任务是从事基础医疗保健工作,科学研究则不应成为其主要任务,而且由于服务范围的有限性和服务对象的相对固定性,论文等研究性要求也可免则免,这样才可以有效体现出倾斜基层的政策导向。 3.2 相同性质的定量 在定性之后,对于同类性质人员,应当以定量考核作为学术评价的依据。“量”的评价可以限制评价人员的主观性,从而保证整个评价活动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量的评价中,要特别注意对量的标准把握。以SCI为例,其最主要的定量依据就是影响因子,而影响因子并不是期刊水平的完全体现,很多世界名刊的影响因子甚至不到高影响因子杂志的1/4,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文由于理论太过超前,以至于发表数十年后才被学界广泛关注,而此时早已过了影响因子的计算周期。因此,定量考核的“量”不宜定得过细,更不可唯影响因子是从,可以参考体育比赛,对影响因子进行分段评价,在一定影响因子之上设立无差别级。对于不用SCI评价的人员可以以论文发表数量、患者诊疗数量、医疗质量等多个方面进行量的评价。 3.3 质与量并举 医学学术水平的进步有赖于我国论文发表质与量的共同进步。客观上看,SCI“量”的增加推动了“质”的提高,逻辑上的直接原因是重点高校和知名专家为了体现学术上的优势,一般不会选择在普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论文“质”的提升与飞跃需要“量”的积累,这点在医学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很多发表于知名杂志的论文是基于若干个发表于普通杂志的论文的基础。从现实的角度,如果只能获得某一个地区的数据资料,可能会发表一个影响因子不足10分的论文;如果能获得一个国家或一个州的数据资料,可能会发表一篇影响因子10分~20分的论文;如果能够获得全球的数据,就可能发表一篇影响因子在20分以上的论文。由此可见,“质”的提升需要“量”的积累。但在科学研究领域,“量”的增加又不会必然带来“质”的提升,因此,我们必须在科研活动中积极促成“质”的提高,不断增加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世界医学科学的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收稿日期:2014-04-15 修回日期:2014-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