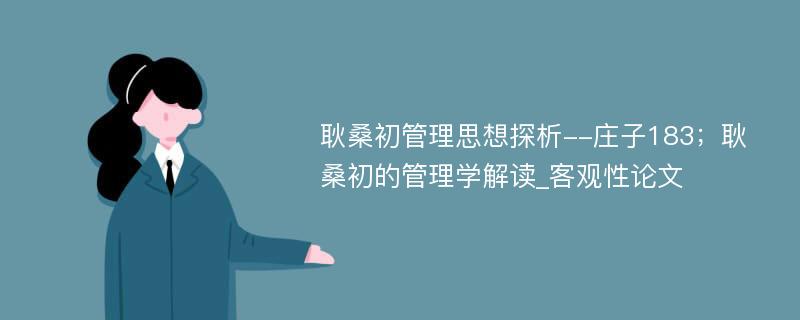
庚桑楚管理思想探赜——对《庄子#183;庚桑楚》的管理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管理学论文,管理思想论文,庚桑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67[2008]12-0189-02
庚桑楚亦称亢仓子、亢桑子,春秋时期楚国人,老子的得意弟子。据《庄子·庚桑楚》记载:“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1]据《列子·仲尼》记载:“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2]庚桑楚跟从老子学道成功后,不仅在鲁国广收门徒传授道学,而且在畏垒山运用道家思想进行无为管理,使道家学说深入民心,使其本人亦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爱戴。由此,庚桑楚的管理思想值得研究。而要研究庚桑楚的管理思想,就必须依据能够反映其原始思想的著述。从庚桑楚的著述看,《汉书·艺文志》就已经没有了庚桑楚或其弟子著作的记录。在唐代搜寻御封真人的真经时,出现了一部题名为《亢仓子》的书。但当时已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该书是时人襄阳处士王士元杂取诸子文义、杂烩而成的伪作。至此,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对庚桑楚的原始思想进行探讨,就不能依据《亢仓子》一书的内容,而只能依据《庄子·庚桑楚》这章内容(以下引文无标注者,均源自本章)。
一、不得已而为的管理理念
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庚桑楚追随道家的基本管理思想,也主张无为管理。有所区别的是,庚桑楚把这种无为管理阐释为“不得已而为”的管理。
先就不得已而为来看,它表面上是一种有所为,但究其实质,由于这种为乃是出于不得已,所以只能算作是无为之举。如其所赞同:“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一切人在世都免不了要有所为,因为性动就是有所为了。如果就此来看,世界上就没有无为之存在。因此,界定为和无为必须要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就庚桑楚来看,为与无为的分野在于有心而为还是无心而为。有心而为添加了修饰,必然使本性得以丧失,所以这种为可以说是有为,即真正的“为”;无心而为则顺性而动,它出于无心且不受人之内心驱使,虽有“为”之表象而无“为”之实质,所以这种为非真“为”,而是“无为”。不得已而为实质上是这种无心而为的无为,所谓“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也就是说,有所作为但不是有心作为,那么作为也就出于无心作为,无心作为便是无为。
继之,对管理行为进行分析可知,管理也有其有为管理和无为管理之分。总体上看,管理本身必然要有所为,这是其本性使然。如上所述,此“为”蕴涵了管理的有为和无为两种行为方式。有为管理意味着管理是一个处心积虑、鞠躬尽瘁的过程,它要求管理者一定程度或巨大的身心付出。无为管理则意味着管理是一个无心而为的过程,它不需要管理者带有任何成见或偏见进行管理。对此,庚桑楚认为:“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如果管理者不能够做到诚于中,而是直接将主观看法表露在管理之中,那么,管理就不能做到恰到好处。进一步,如果管理者一直不能放弃这种先入之见,那么,管理的每一步都有可能会产生错误。也正是如此,庚桑楚强调管理者应当做到“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意即管理者应当事事顺应于不得已,顺应于事物之客观,才有可能处置适宜,取得管理成效。而“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缘于不得已进行管理,才是真正的管理之道。
二、虚己以待物的管理途径
庚桑楚认为,为了进行不得已而为的管理,管理者首先应当去除自身的主观意识而达到空虚无己,即做到:
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为了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效果,管理者必须要虚己以待物。这就要消除其意志的错乱,解开其心灵的束缚,去掉其德性的拖累,打通其大道的障碍。引发意志错乱的因素主要有尊贵、富有、显赫、尊严、声名、利禄等,束缚心灵的因素主要有容貌、举动、美色、道理、神气、情意等,拖累德性的因素主要有憎恶、欲望、欢喜、愤怒、悲哀、快乐等,堵塞大道的因素主要有舍去、附就、摄取、施予、智慧、才能等。管理者只有敢于消除这些影响事物客观性认知的主观意识,才能公正无私,宁静清明,从而在无所思虑、无牵无挂中顺物之性进行无为管理,取得无不为的管理效果。
很明显,庚桑楚在面对管理中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时,其解决方案无非就是要抹去主观性的一面,突出客观性的一面,凭借物之客观性压抑人之主观性,以彰显人之无为之举。这种无为管理在压抑人之主观性的同时,必然会强调要去贤弃智。老子一定程度上就存在着“绝圣弃智”的管理理念,他曾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三章),[3]“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十九章),[3]认为去除人主观上的智巧、欲望,可以制止争斗,更加有利于管理。庚桑楚吸收了老子的绝圣弃智思想,更加反对举贤,否定任智,认为“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由于举荐贤才会使被管理者相互伤害,而任用智能会使人民相互欺诈,都将危害到组织发展,所以管理者一定要去贤弃智,以免人们在追求“贤”、“智”的过程中,产生“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等严重危及到组织安全和发展的后果。而从“智”而言,庚桑楚认为“至知不谋”,即最高的智慧是不去思虑,不用谋略,所以管理的最高境界亦应当是:不仅管理者本身要去除各种思虑才智,而且在管理过程中也要去贤人、弃智术。虽然从道的观点看,这不失为一条使管理返归道本的重要途径,但是,从现实的观点看,当庚桑楚把管理行为推展到这一步时,就已经使管理本身变得毫无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庚桑楚极度的去贤弃智思想可以说消融了人之主观性,张扬了物之客观性。
为了进一步彰显物之客观性,庚桑楚认为管理者在去除人之主观臆想的同时,应当凭借物之客观性进行无为管理。他说:
一雀过羿,羿必得之,或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是故,汤以庖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而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
这就是说,管理者凭借主观意识进行管理,就如羿射雀,虽然箭术高明,也只不过是或许能够取得管理的成功,而不是必然能够取得管理的成功。但换一种思路,如果管理者能够凭借物之客观性进行管理,即尊重和借用物之客观性进行管理,管理就不可能不成功。这是因为,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物都必有其本性,有其客观性,顺应其本性,遵循其客观性,投其所好,理所当然地能够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实现管理高效。而这必然要求管理者去除自身之主观臆测,以免反事物之本性及其所好。可见,按庚桑楚的认识,无为管理依靠的是物之客观性的认知,而非人之主观性的臆想。而只要时时处处都能够以物之客观性为管理准绳,则管理必然成功无疑。
三、下知有之的管理态度
老子早就提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作为管理者,庚桑楚对此可谓心领神会。基于其“不得已而为”的管理行为,他追求下知有之的管理态度。这从其实际行动中可以看出。在他“居三年,畏垒大壤”之后,老百姓开始对其赞赏不已,称其为“圣人”,甚至要对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这引得庚桑楚颇不高兴。因为就庚桑楚看来,畏垒管理的成功,只不过是自己遵循天道,在管理中顺应了自然运行规律而已,所谓“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这种循天道而进行的管理本是“不得已而为”的管理,自己作为管理者,也本应当是“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的圣人。至人实际上就是老子所讲的“太上”即最好的管理者。对至人而言,应当是老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就行了,没有必要对他亲近赞誉。一旦老百姓对他亲近赞誉,也就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下知有之”的管理者,而只是一个如尧舜般躬行仁义的有为管理者而已。当庚桑楚潜在地把自己看作至人,而百姓以及弟子都将他等而下之,把他和尧舜相提并论时,他当然就不高兴了,以至于马上就对弟子进行训话。
从庚桑楚的不高兴就可以看出,庚桑楚非常注重管理者下知有之的管理态度。实际上,庚桑楚谨遵老子教诲,也往往把管理者分成多种,而每一种管理者都代表着一种典型的管理行为,如“下知有之”的管理者代表着无为管理的实施,“亲而誉之”的管理者则代表着仁政等有为管理的实施。由此,庚桑楚就把“下知有之”的管理者看作是道的化身,他在管理中遵天道,行无为,使被管理者也可以率性自然,自由发展。
标签:客观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