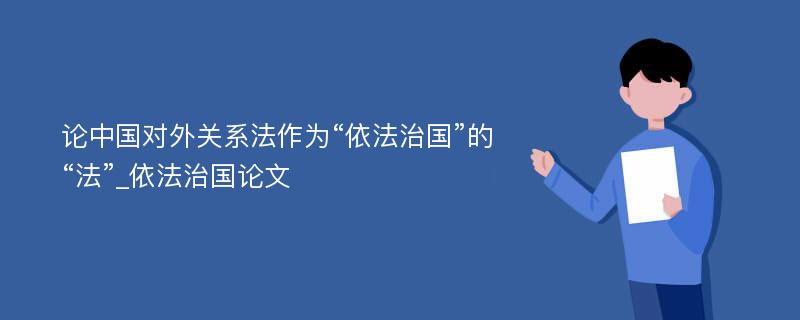
论作为“依法治国”之“法”的中国对外关系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依法治国论文,中国对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依法治国”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成效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及分类上,学界虽然有所谓“五分法”②、“八分法”③等主张,但将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完整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却寥寥无几。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目标,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健全并实施好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同样应该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内涵。中国对外关系法同样应该是“依法治国”之“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拟尝试界定“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含义及构成,阐述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中国“依法治国”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应然性及其作用,提出健全和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应注意的若干关键问题。 一、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含义及构成 (一)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含义 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间的各类跨国关系,构成丰富多样、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从国家的角度看,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组成部分的一国对外关系,通常可大体划分为对外政治关系和对外经济(包括对外民商事)关系。这些关系相互间的影响力及其地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势下往往有不同表现。⑤对国际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而言,在对外交往中产生或客观存在的关系,是需要相应的规则或法律予以规制的。这些规则或法律,既包括人类社会所共同遵循的习惯和一般法则,也包括国际社会经由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国际习惯,还包括反映国际社会成员协调意志的各类条约法,以及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各国专门用于规范其对外关系的各类法律法规。与一国对外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包括民商事)关系相对应,一国的对外关系法也分别由规范对外关系的公法性法律和私法性法律构成。如果再作进一步的分类,又可将这类法律分别归类到我们通常所称谓的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范畴。这类法律要么渊源于一国国内立法,要么渊源于一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要么渊源于为一国所认可或接受的国际习惯。而其中的国内立法,既包括一国相关对外关系的单行法,也包括与对外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国内部门法中的相关规定。一国的对外关系法就是由上述法律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法律体系。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主要由调整纯粹国内关系的法律体系即国内法体系和调整对外关系的法律体系即对外关系法体系构成。因此,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调整我国对外关系的各类法律法规所构成的法律体系,是指专门调整同我国有关的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体系。具体而言,中国对外关系法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在内涵上,中国对外关系法处于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之中。一国的对外关系法是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和需要逐步形成的有机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对外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内容不断丰富,体系亦日渐完备。中国对外关系法的范围已涵盖政治、经济(包括民商事)等对外交流的方方面面,并将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充实。 第二,在外延上,中国对外关系法既包括国内法中专门用以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对中国具有拘束力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一个国家对于与其有关联的各类对外关系的调整,既依赖于该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也有赖于国内法中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专门立法。中国对外关系法是由国际法规则和部分国内法规则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第三,中国对外关系法与相关概念具有显著区别。(1)中国对外关系法不同于中国外交关系法。中国外交关系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我国在实施外交政策过程中,由外交机关在国际访问、谈判、签订条约、外交文书往来、派出常驻外交代表机关、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中所产生的关系。本质上来说,外交关系法只是对外关系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相比中国的外交关系法,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对象更为广泛,既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包括国民)、国际组织之间产生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包括中国的自然人和法人及相关组织(或者在中国境内有经常居所的自然人、在中国境内有营业所的法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自然人、法人及相关组织之间的民商事关系。(2)中国对外关系法也有别于某些国家如美国法学会颁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中的“对外关系法”。《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所称的对外关系法,是指对美国对外关系具有实质影响或存在其他重要关联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其中,关联的国内法规则是否属于美国对外关系法的范畴,往往有赖于法官在个案中的阐释。而且,美国对外关系法的国内法渊源既包括联邦法,也包括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州法。⑥在外延上,美国对外关系法几乎包括国际法的所有原则和规则,但多强调的是国家的对外关系法。现已出版的《美国第三次对外关系法重述》实际上是在以美国观点说明国际法的大部分原则和规则。⑦ (二)中国对外关系法的构成 中国对外关系法,主要由涉及调整对外关系的宪法性法律、依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转化而来的国内立法以及专门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构成。 1.有关对外关系的宪法性法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宪法中有关对外关系的规定,既是我国处理各类对外关系的最高法律依据,也是我国关于对外关系立法的最高依据。中国对外关系法的构建也必须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权限及框架内进行。我国现行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宪法性法律主要包括: 第一,调整对外政治关系的规定。这类规定包括:(1)关于分配外交事务权力的规定。对包括战争权、核战略的发展、秘密行动和条约缔结权在内的各项外交权,《宪法》第67条第14项、第81条、第81条第9项均有明确规定。⑧(2)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规定。国家安全政策又被称为防务问题,既是一国主要的政治问题,也是一国重要的军事问题,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分别在序言和总纲中规定了外交政策与国防政策,第62条第14项、第67条第18-19项、第80条对战争权及其行使作了明确规定;(3)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为保护个人依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⑨我国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33条第3款中明确了对人权的保护,将人权保护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直接转化为宪法条款。 第二,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规定。这主要包括以下两类规定:(1)关于经济体制的规定。例如,《宪法》第7条有关国家经济所有制问题的规定、第15条有关国家经济体制问题的规定以及第16条有关国有企业自主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规定。(2)调整对外民商事关系的规定。明确外国人、外国法人和外国组织在内国的法律地位,是一国对外交流的前提。为此,《宪法》第18条和第32条明确规定,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可以依法同中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中国法律保护其在中国的合法权益。 2.有关对外关系的专门法律法规 对外关系的专门法,即一国专门适用对外交流中某类或某领域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在我国,这类法律法规既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各类涉外法律,也包括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还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涉外行政法规。 第一,涉外法律。⑩这些法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规范各类对外关系的单行涉外法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单行的涉外法律,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以下简称《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以下简称《缔结条约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以下简称《引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既反映了我国维护主权以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意志,也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表现。从制定依据来看,这些涉外法律大致可分为三种:(1)根据我国自身利益需要,将较为笼统、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国际法规则细化衍生为专门性国内法律,如《国籍法》、《缔结条约程序法》;(2)将国际习惯规则“立法转化”为专门性国内法律,如《引渡法》;(3)依据《宪法》制定的专门调整特定领域内对外关系的法律,如《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另一类是分散于相关部门法中的涉外法律。以1983年以来我国颁布的涉及国际私法的立法为例,在多个部门立法中有调整对外关系的规定。这些法律大体有两种渊源形式:(1)专篇专章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14章“涉外海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4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等。(2)分散规定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6条等。这些分散于相关部门法中的涉外法律,是对外关系的专门立法之重要补充,也是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必要构成部分。 第二,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缔结的双边条约主要涉及如下方面:双边友好政治条约、(11)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12)划界(包括海域划界及渔业问题)条约、(13)领事条约、(14)经贸合作条约与投资保护协定、(15)关于教科文卫方面的条约、(16)有关航海、航空等交通条约、(17)关于能源、矿藏领域合作条约。(18)1875年到2015年,我国参加的多边条约共计388项,(19)主要包括一般国际法方面的条约、具体国际法领域的条约、国际经济(包括国际民商事)条约及其他方面的条约等。我国参加或缔结的上述各类双边和多边条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纳入我国国内法:(1)通过立法接纳条约为本国法的一部分,条约因此可以自动在国内适用,即“直接适用”。这类条约主要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民商事条约,相关国内立法及实践也赋予了这类条约直接适用的效力。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6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2)通过制定实施性立法,使条约得以在国内适用,即“间接适用”或“转化适用”。这类条约主要为我国缔结或参加的非民商事条约。例如,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国制定了《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使公约的相关规定得以在我国生效。 第三,行政机关制定的涉外行政法规。为了更好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在保障国内经济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对外交往的行政法规来规范各项行为。例如,2001年11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相继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性文件虽然不是专门调整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却是对外政策实施的保障和依据。例如,为更好促进进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国发[2014]13号)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三个方面总体规划,实施支持重点、加大财税支持、强化金融服务和完善服务保障等政策,要求各部门依此规定来落实责任,制定相应方案,以确保对外文化贸易的持续发展,保障内外国法人和经济组织的权益。 (三)中国对外关系法的构成依据 提出并认识中国对外关系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内关系与对外关系联系日益紧密的认可,也是对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客观存在的大量对外关系法律法规在部门法层面的确认,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1.理论依据 中国对外关系法的上述构成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国际关系的广泛性要求中国对外关系法必须涵盖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这也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法体系构成的广泛性。一般而言,国际关系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1)国家间关系。包括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及本国政府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2)民商事主体间关系。民商事主体在跨国活动中产生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和市民社会组织活动范围不断扩展、交流方式日益更新的背景下,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20)与规范国内政治、经济(包括民商事)关系的国内法相对应,中国对外关系法亦应由调整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包括民商事)关系的法律法规构成,这既是我国全面参与国际交流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对外关系广泛性的内在要求。 第二,国际关系的法治化要求中国对外关系法应包括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为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治理的法治化,各国在国际关系中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制度来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正因如此,各国通过参加和缔结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方式明确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尊重和遵循国际习惯。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我国一直坚持以法治反对霸权和强权、以规则维护公平和正义。在国际法解释、适用和发展的重大领域,我国先后缔结或加入了27000多项双边和多边条约,(21)将我国对外交往实践全面纳入法治框架。因此,中国对外关系法包含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以及由之转化的国内立法,既是对当今国际关系法治化要求的顺应,也是对我国践行国际法治的证明。 第三,国家对外交往的法治化要求中国对外关系法必须包括有关对外关系的宪法性法律和国内专门调整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我国宪法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所参与的各类对外交流活动同样也应纳入法治轨道。为确保我国对外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我国应秉持法治理念,一方面要求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必须维护宪法权威,严格遵循依据宪法所制定的专门调整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应根据为国际社会成员所接受的、通行的制度和规则来处理和应对各类对外关系。 2.实践依据 无论是从国内实践还是域外实践来看,中国对外关系法的上述构成都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 第一,作为以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的法治国家,我国的对外关系法既应包括相关国际法,也应包括相关国内法,这是对外开放实践本身的需要。我国对外交往法治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在对外开放、参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客观上需要一个涵盖国际法和相关国内涉外法律法规的制度体系来发挥保障作用。而且,我国对外交往的实践已经证明国际法与相关国内法之间的紧密联系。在立法实践上,我国参加和缔结的国际条约及国际习惯可转化为国内立法,而国内立法实践也可被国际条约采纳或作为国际习惯存在的证据。 第二,一国对外关系法的上述构成,已为相关国家的实践所印证。(22)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对外关系法在实践中也得以不断丰富。例如,《美国第三次对外关系法重述》既包括国际经济法、海洋法、外交法、国际争议解决与合作法等国际法,也包括国际法的渊源及其在美国法律中的地位、国际法上的救济以及外国主权豁免方面的国内立法。显然,美国对外关系法既包括国际法,也包括相关的国内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学会已启动《美国第四次对外关系法重述》的编制工作,其任务包括管辖权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约、国家豁免等问题,邀请了涉及对外关系领域和国际法领域方方面面的学者,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美国第四次对外关系法重述》依旧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方面的内容。(23)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看,中国对外关系法既包括规范中国对外关系的相关国内法,也包括与中国对外交流相关的应予遵守的国际法规则。在国际法规则部分,不仅包括适用于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经济等关系的国际公法规则和国际经济法规则,还包括规范与我国有关的对外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规则。 二、中国对外关系法是中国“依法治国”之“法” 中国对外关系法本身的具体构成已表明,中国对外关系法无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依法治国”之“法”,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一)应然性问题 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我国维护各类对外关系主体利益的重要保障,作为中国“依法治国”之“法”,主要有如下理由: 第一,主权国家治国理政的对象既包括国内事务,也包括与国家主权及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依法治国,宗旨在于治国要依法。这就要求中国“依法治国”的“法”中必须包括调整对外关系的对外关系法。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内政和外部事务,国内法(规范纯国内关系的法律法规)在支配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和事方面具有优先权,这是由国家主权原则得出的必然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内外事务的处理,可以随意而为。相反,国家不仅要依据国际法规则处理与外国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外国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特定内部事务的处理也要遵循相关国际法规则,这不仅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明确的宗旨。我国近年来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如在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大陆架划界与岛屿归属、国际投资与贸易、国际司法协助与合作等问题过程中,我国都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在构建公民权利保障的国内法规则与制度的过程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修订也充分考虑到我国所承担的国际人权条约义务。 第二,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的交互影响更为明显,这也要求中国“依法治国”中的“法”中必须包括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经济体,中国已融入国际交流体系之中,并强调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公平正义。(24)中国国内法律体系与国际法体系的交互影响,是一种必然趋势:一方面,中国国内法体系直接受到国际法体系的影响。例如,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领域,为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我国按照世贸组织法的要求;对大量法律、行政法规、部门和地方性规章进行系统清理,以满足世贸组织法规则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法体系也对国际法体系的构建提出新要求。例如,在国际民商事领域,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新近重启的“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项目谈判工作中,我国基于国内涉外民事管辖权的一贯理论和实践,对美国力推的“一般经济活动管辖权”持谨慎态度,而坚持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倡议得到巴西、印度等国的积极响应。(25) 第三,将中国对外关系法纳入中国治理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使之成为“依法治国”之“法”,不仅是理论架构和实践的必要安排,也是对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客观事实的承认和尊重,更直接关系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和维护。尽管《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缔结和批准国际条约的职权问题,但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及国际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并无原则性规定。对于《民法通则》第142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66条这类规定的合理解释应该是,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是中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并可以直接适用。(26)此外,我国相当一部分国内立法将我国已经或将要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纳入其中,实现对国际法的国内法转化,使相关国际条约得以在国内间接适用。(27)我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公平秩序的建立及承载这些价值的相关国际法的创立做出过贡献。这些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在被国际社会广为接纳的同时,也已纳入中国对外关系法中。因此,在相关国际法规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部分已是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中国对外关系法必须予以认可和尊重。积极、正确地适用中国对外关系法,不仅充分证明我国接受国际法规则的开放态度和构建良好的涉外法治环境的努力,也可清晰表明我国尊重和维护国际法治的坚定立场。将中国对外关系法纳入中国治理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直接关系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和维护,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司法公信力。 第四,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之宗旨出发,作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立法活动的结果,也应将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中国“依法治国”之“法”。客观而言,当前国际秩序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在维护自身重大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规则多为反映欧美国家核心利益的意志所主导。但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革,尤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相关对外关系上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而又必须予以协调的客观现实中,不同国家立足于不同立场并极力输出对自身有利的法律理念、规则和制度已成为常态。积极参与国际立法活动,既是我国主动参与构建公平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途径,也是有效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作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我国需要借助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政府间国际组织表达自身立场和诉求,以达到在对外交往中充分维护国家利益之目的。在此过程中,总结和提炼中国对外关系法中现有的成熟实践和经验,无疑是提高我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和依托。因此,基于我国在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中能充分表达我国立场、反映我国利益和价值观之考量,也必须将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中国“依法治国”之“法”。 (二)作用问题 中国对外关系法既是国家对外关系的行为准则,也是国内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处理各类涉外争议的依据。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深入贯彻和实施,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中国对外关系法所发挥的作用都将日益彰显。 1.在国内层面的作用 中国对外关系法在国内层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保障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及国家安全。确保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安全,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前提。国家主权独立和安全无疑是中国对外关系法的首要关注点。中国对外关系法涉及的国家主权、领土、外交、军事、国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就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第二,保障和促进民主、法治及人权。对民主、法治及人权的保护,既反映一国的法治水平,也关涉一国的国际形象。《宪法》将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和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作为重要目标,缔结了一系列关于人权保护的国际条约,这都是中国对外关系法强化人权保护的表现。此外,根据《宪法》和我国作为缔约方的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也特别就国际民商事交流中的人权保护问题在一系列国内立法中作出规定。对外关系法作为涉外法治环境的重要保障,往往也是通过保障和促进民主、法治及人权而发挥重要作用的。 第三,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践行科学发展观,我国坚持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缔结的关于环境与渔业的条约、经贸合作条约和投资保护协定、教科文卫方面的条约、能源与矿藏领域合作条约、劳工方面的条约等已成为我国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保障。例如,我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为履行公约义务、规范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和开发活动、保护海洋环境并促进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新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实施,对于促进深海海底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意义重大。 第四,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既然已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纳入我国民商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调整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包括“三资”企业关系之外的其他对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是否也应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呢?从涉外民商事交流在各国对外交流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国际民商事关系在各类对外关系中的构成看,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因此,为完善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不仅要将这类法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且还应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的方向:一是要在宪法上明确调整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的地位;二是要强化和协调相关国内和国际立法活动。 第五,提升依法治国的水平。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就是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来处理国事。将各类对外交流事务纳入法治轨道,既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部分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之体现。因此,健全和完善我国规范各类对外关系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对外关系法,是提升中国依法治国水平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实践也表明,中国对外关系法在提高我国司法、行政工作的透明度方面意义尤为深远。 2.在国际层面的作用 中国对外关系法在国际层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推进多边合作机制,维护国际和平。作为当今世界多边合作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和构建者,我国积极推动以多边合作和全球共同发展与进步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建立。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我国在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冲突和增强国际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8)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推动者和创建者,我国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并批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为提高打击恐怖主义的协调能力和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对外关系法必然契合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建造性角色,不断促进国际关系的多边主义和合作主义。而且,作为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对外交往的依据,中国对外关系法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我国在维护世界安全与和平方面的决心和态度。 第二,促进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处理包括国际政治、经济等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时,我国一贯主张坚持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我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和维护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完善,一方面可以为我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时所提出的主张提供更充分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加速推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实质性地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在扩展国际贸易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等方面做出诸多贡献。(29)《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签订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不仅有助于继续推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而且有助于我国在外交战略中发挥本国资本在国际金融中的力量,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制度保障。而这些实践和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有赖于我国在恪守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同时清理国内相关立法,另一方面也亟须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这也正是我国在强化涉外经济法治建设方面的着力点。 第三,促进和便利国际民商事交往。国际民商事关系作为当今各国间交流的基础性法律关系,对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前提,我国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在中国对外关系法领域内的作用当然不可忽视。在双边机制下,依据已签订38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我国2015年办理的国际司法协助案件达2210件,区际司法协助案件达1.1万件,涵盖贸易纠纷、海事运输、产品质量责任、保险、侵权、离婚等诸多领域;(30)在多边机制下,作为《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的成员国,我国年均处理涉外送达请求超过2000件。(31)由此可见,中国对外关系法对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高效解决、确保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内外国当事人权利的平等保护、推动和便利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流转,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30多年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公平合理地处理好各类国际民商事纠纷,是国际民商事交流稳定发展、构建安全和有效的国际民商事交流环境尤其是国际投资环境的条件和保障。 三、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健全和完善 将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中国“依法治国”之“法”,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是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工作重心 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中,以中国对外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对外关系法无疑将发挥关键作用。为此,我们不仅要改变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忽视中国对外关系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应有作用和地位之现状,而且还应将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工作重心。这主要是基于如下考量: 第一,将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要组成部分的认识,还尚未树立。如前所述,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中国“依法治国”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当然组成部分,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我国并未得到应有重视。(32) 第二,中国对外关系法亟待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还存在一系列问题:(1)体系性问题。除有关对外关系的专门性立法外,中国对外关系法律法规分散在宪法和其他部门法有关对外关系的规定中,尚未形成体系。(2)逻辑性问题。若干对外关系法规则如关于国家主权原则的规定存在重复规定的情况。(3)立法空缺或立法层级问题。对外投资、对外援助、口岸、开发区、领事保护等领域无法可依或法规层级较低的现象仍然存在。(4)可适用性问题。对外贸易、国籍、在华外国人管理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比较原则笼统。(5)透明度问题。一些政策性涉外法律法规缺乏透明度。(33) 第三,健全和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意义重大。健全和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不仅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基础,也是中国坚持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输出反映中国特色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先行举措。在中国对外关系法的既有实践中,我国一贯遵循主权平等、互利互惠、沟通合作的原则,促进不同文明的相互借鉴、兼容并蓄和取长补短,进而为构建和谐世界服务。 在将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完善作为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工作重心的前提下,下述事务尤需严格遵循中国对外关系法: 第一,涉外立法事务。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加强涉外领域的国内立法及参与国际立法成为中国依法处理涉外事务、增强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中国利益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领土争端、气候变化、国际航运、网络安全、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救援、贸易与投资、金融与货币、知识产权等议题,已成为中国无法回避和必须参与解决的问题,而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构建则必须在中国对外关系法框架内进行。 第二,涉外司法事务。涉外司法事务既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法治文明形象,也关系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高涉外司法工作水平,其重要意义无须赘言。在涉外司法实践中,对于审判方式、证人出庭作证、送达和取证、司法救济和律师服务在内的涉外司法事务,当然应严格依照中国对外关系法的规定,这也对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涉外执法事务。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各国执法事务跨国性的增强,加强涉外执法事务的国际合作,就成为一种必然要求。目前,在打击跨国贩毒、走私、洗钱、电信诈骗、拐卖人口以及跨国渔业、公共卫生、资产追回等问题上,国际执法合作的迫切性已日益显现。中国参与上述问题的国际合作,自然应在中国对外关系法的框架内进行。 (二)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域内效力及其适用问题 条约的域内效力问题涉及条约与宪法及相关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各国实践表明,不同国家给予条约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34)但我国宪法尚未明确条约的效力问题,其原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我国宪法的制定深受前苏联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1)将宪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章程,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宪法本身作为法律应具有的可诉性;(35)(2)在条约与宪法的关系问题上,保持缄默。(36)其二,成文宪法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对于国内法(包括宪法)与条约的关系问题,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均未予规定;在对此作出规定的少部分国家中,部分国家规定,若条约与宪法规定不同时,该条约或协定仍然有效;部分国家则规定,二者抵触时,条约无效。(37)这主要因这些国家的历史与政治制度所致,与社会制度的性质往往关系不大。尽管如此,对中国具有拘束力的条约,作为中国对外关系法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例如,作为国际合同法领域“三大支柱”之一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中国已生效实施多年,该公约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的“一元论”观点所蕴含的合理性成分。基于中国对外关系法实施的需要,我国宪法应该明确条约在我国的效力问题。(38) 此外,还需明确条约在我国适用所产生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条约的分类适用问题。对于不同类型条约的适用问题,一般有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两种情形:(1)属于民商事性质且涉及私人权益的条约,在我国是直接适用的。具体表现为:在国内法中明确规定,国际条约调整的事项不再适用国内法;(39)或在国内法中规定,国际条约与我国法律冲突时优先适用国际条约。(40)(2)对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人权、经济贸易等民商事以外的条约,在我国是间接适用的。例如,《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世贸组织各项协定等,均需先由我国立法机关予以转化后才能适用。因此,对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根据其目的和宗旨以及条约本身的性质,明确其分类适用问题,无疑是必要的。二是条约的解释问题。条约的解释直接关系条约的适用,正确合理地解释条约是正确适用条约的前提。条约的解释一般涉及解释主体和解释方法两方面的问题。在条约的解释主体上,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尤其是对于依据《缔结条约程序法》由国务院核定的相关国际条约的解释,如何确定解释主体这一问题,我国立法也未作明确规定;在条约的解释方法上,依据一般国际法规则,除条约本身另有特别规定之外,一般应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进行解释。但条约的国内解释与国际解释之间的关系如何,我国立法上也并未明确。(41)而这些问题,都直接关涉条约在我国的适当适用。 (三)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域内效力问题 尽管对于“作为通例之证明而接受为法律”的“国际习惯”有不同认识,但国际习惯作为不同于条约的国际法之重要构成部分,是基本得到认可的。(42) 在我国,已经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应包括国际习惯的共识。我国一贯倡导遵守并根据国际法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表明我国已经将国际习惯作为中国对外关系法的组成部分。但国际习惯法原则和规则是否直接适用于国内,在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其效力如何,对这类问题,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尽管《民法通则》确立了国际惯例补缺原则,但对于国际习惯的界定以及国际习惯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仍有待立法予以明确。(43)目前我国有学者主张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对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作出原则规定。(44)这种主张有助于从根本上明确中国对外关系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地位问题。 (四)国际法学在建设中国涉外法律人才队伍中的作用 通过国际条约确定各国权利义务,已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应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并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人才队伍。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国际法学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现状,与我国解决涉外民商事争议及参与国际事务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第一,在解决涉外民商事争议方面,就审判机构的设置来看,截至2014年10月底,全国共有203个中级法院、204个基层法院具有一审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这些法院大部分位于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2015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涉外商事案件6079件,海事商事案件1.6万件,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2210件,审结涉港澳台、涉侨案件1.7万件,区际司法协助案件1.1万件。(45)享有涉外民商事(包括海事)案件一审管辖权的法院面临繁重的司法审判任务。涉外法律专业审判人才的缺乏,也制约着涉外民商事争议的高效解决。针对涉外民商事审判的特殊性,如何培养能够正确理解和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熟悉中外法律和国际通行规则、掌握国际司法发展动态的涉外法律专业人才,就成为国际法学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中心工作。 第二,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我国一直恪守联合国、世贸组织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国际组织的制度和规则。利用国际组织这一平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是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表达主张和诉求的主要通道。但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相关法律活动的影响仍然有限。迄今为止,在世贸组织常设上诉机构中仅有一位中国籍人士任职。我国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中派出的本国实习人员数量仍然较少。(46)要在现行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框架内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努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必然需要我国国际法学界教育培养出更多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高端法律人才。(47)此外,在我国参与国际及地区事务中的角色及作用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也急需大量涉外法律专业人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预示我国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面临着新的艰巨任务。例如,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我国预计启动重点项目900余个,涵盖基础设施、贸易、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生态环保、人文以及海洋等方面。(48)这就要求我国在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能源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环境法、国际文化法、国际海洋法等方面培养和储备相应的法律人才。同时,为解决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上述领域的国际经济(包括民商事)争议,不仅需要具有涉外法律素养的法官和司法行政队伍,而且需要有能够为中外当事人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律师群体。这种涉外法律工作队伍的建设,要求我国国际法学界不仅要重视国际法理论人才的储备,更要重视涉外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培养。 (五)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国际法学是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实践中,国际公法发展出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国际行政法、国际刑法、国际空间与航空法、国际海洋法、国际环境法、国际能源法等分支部门法;国际私法发展出国际民事诉讼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法等分支,在部分存在多法域的国家,国际私法还包括区际私法(或区际冲突法);国际经济法也发展出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国际税法等分支。晚近以来,伴随着我国参与国际事务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对于我国在对外关系中产生的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国国际法学界充分关注,开展了较为深入并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学术研究,对我国对外交流的发展贡献显著。(49)实践证明,中国国际法学必须是中国法学体系中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相对应,一个完整的中国法学体系应包括中国国内法学和中国对外关系法学。在中国对外关系法学体系之下,至少有三个独立的法学部门——中国国际公法学、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及中国国际私法学。(50) 四、结语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乃法治之重要内涵。在中国对外关系法作为中国规范对外交流中各类对外关系的法律法规体系,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组成部分的客观情势下,中国各类对外交流活动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中国政府、司法机关以及参与各类对外交流活动的主体,都必须严格遵守中国对外关系法。一方面,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对外关系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主要地位,也要认识到中国对外关系法同样也是中国“依法治国”之“法”;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发展,中国对外关系法也将不断丰富和完善,为此,我们必须解决一系列先决性理论及实践问题。 注释: ①参见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二○一一年三月十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1年3月11日。 ②参见孙国华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171页。 ③参见何勤华主编:《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④国内学者一般将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的法律规范排除在中国法律体系之外,只有少数学者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参见何勤华主编:《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415页。 ⑤国际关系学学者也指出,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内政与外交的互动更加广泛和深入,普通公众、经济行为体、军贸公司和知识界等国内社会因素也会对一国对外关系产生影响。参见张清敏:《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内外统筹——国内因素与中国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 ⑥在美国对外关系法的国内法渊源部分,除联邦法外,对于实质上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州法是否属于美国对外关系法,尚存争议。See Emily Chiang,Think Locally,Act Globally?,Dormant Federal Common Law Preemption of State and Local Activities Affecting Foreign Affairs,53 Syracuse Law Review 923(2003). ⑦参见王铁崖主编:《中国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⑧参见韩大元等:《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⑨参见王家福、刘海年主编:《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⑩在我国,由于司法解释几乎发挥着与法律同等的作用,故中国对外关系法也应该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中国对外关系法所作的司法解释。 (11)例如,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12)截至2016年1月,我国已与67个国家缔结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和打击“三股势力”协定共121项(105项已生效)。其中,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19项(17项生效)、民(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项(全部生效)、刑事司法协助条约35项(31项生效)、引渡条约41项(32项生效)、打击“三股势力”协定7项(6项生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我国对外缔结司法协助及引渡条约情况》,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wgdwdjdsfhzty_674917/t1215630.shtml,2016-05-02。 (13)例如,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 (14)截至2015年2月27日,我国先后与46个国家陆续签订了领事条约。参见一帆:《中国已与46个国家签订领事条约》,《法制日报》2015年4月14日。 (15)例如,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捷克共和国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和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16)例如,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耳他共和国政府2009-2012年文化交流计划》。 (17)例如,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航空运输协定》。 (18)例如,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关于石油、天然气、矿产领域开展合作的议定书的补充谅解备忘录》。 (19)据外交部已公布的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参加的多边条约共计388项。其中,1875年到2003年273项,2004年10项,2005年12项,2006年14项,2007年18项,2009年13项,2010年13项,2011年2项,2012年9项,2013年5项,2014年6项,2015年13项。参见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2016-05-02。 (20)See John Gerard Ruggie,Reconstituting the Global Public Domain:Issues,Actors and Practices,1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99(2004). (21)参见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4日。 (22)前文虽对美国的“对外关系法”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法”的不同概念进行了区分,指出二者在范围上存在差异;但从整体内容来看,二者都包含了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即均囊括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相关内容。 (23)See M.Traynor,The Future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17 SW.J.Int'l L.5(2011). (24)例如,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6月29日。外交部长王毅在2014年10月24日的“联合国日”发表文章,提出“坚持推进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4日。 (25)See Peter Gottwald,Jurisdiction Based on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Hague Draft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Foreign Judge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4 Eur.J.L.Reform 199-218(2002). (26)中国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后,司法实践中就直接适用该条约处理相关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转发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8年第1期。 (27)参见刘楠来:《国际法:依法治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学习时报》2007年10月11日。 (28)例如,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外国干预叙利亚内部事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三次否决向叙利亚政府施压的决议草案,有力地维护了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 (29)参见余敏友、刘衡:《评中国在WTO近十年的表现——兼评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变化及其影响》,载孙琬钟主编:《WTO法与中国论丛》(2011年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0)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21日。 (31)参见傅铸:《中国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三十余年》,《法制日报》2013年4月23日。 (32)对于中国对外关系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如前述未能得到学界认可,而且现有官方文件也认为,中国法律体系大体由在宪法统领下的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部门构成。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8日。 (33)参见汪洋:《加强涉外法律工作》,《人民日报》2014年11月6日。 (34)对于宪法与条约的关系,《法国宪法》第55条、《德国宪法》第25条、《希腊宪法》第28条、《日本宪法》98条第2款等都规定条约在宪法之下但高于一般国内法;《荷兰宪法》第91条第3款、《奥地利宪法》第50条第3款规定条约高于宪法;《美国宪法》第6条则规定条约与宪法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对于条约与法律的关系,日本学者一般主张条约地位高于法律,而法国学者一般认为条约的地位与法律相当。See T.Alexander Aleinikoff,International Law,Sovereignty,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Reflections on the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Debate,98 Am.J.Int'l L.91(2004). (35)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政治局委员写信时,开列了必读参考资料清单,包括1936年《苏联宪法》、《斯大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1924年《苏联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和东欧民主国家宪法等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我国制宪者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在价值取向上,已受到1936年《苏联宪法》影响。宪法在当时更多是起到一种象征作用和宣示作用,从形式上更像一项纲领。参见肖明辉:《苏联宪法与我国宪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6)不论是1918年《苏俄宪法》还是1936年《苏联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条约的国内法律效力及其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周恩来总理就宣布要对西方列强过去强加给我国旧政府的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进行审查,分别加以承认、废除、修订或重订。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基本上是如此规定的。但问题是,哪些条约是平等的,哪些是不平等的,哪些应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最后并无结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也不适宜于对条约的效力与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 (37)国外学者对成文宪法国家相关立法进行的统计表明,在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83.1%的宪法包括了国际性立法的规定(主要指在宪法中对缔约权的规定),但关于国际法的其他事项则常常很少涉及。大多数宪法没有规定国内法(包括宪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该比例达到69%,没有规定宪法与国际法的关系的达到74.6%。即使是在有相关规定的国家中,也仅有4.9%的国家规定,如果条约或协定与宪法规定不同时,该条约或协定仍然有效;9.2%的国家则规定,二者抵触时,条约无效。参见[荷]亨克·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165页。 (38)学界亦有人主张,国际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具有低于宪法而高于法律的效力地位。参见赵建文:《国际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 (39)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6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8条之规定。 (40)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2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第1款之规定。 (41)例如,在世贸组织争端中,成员既可对争议的世贸组织协定条款进行国内解释,也可寻求国际解释。参见冯寿波:《论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完善——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9期。 (42)See Hiram E.Chodosh,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eaty and Customary Law,28 Vand.J.Transnat'l L.973(2001). (43)参见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44)参见戴瑞君:《谈依法治国不应忽视依国际法治国》,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 id=3680,2016-03-18。 (45)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21日。 (46)例如,2011年联合国总部实习项目需要200多位实习生,但从中国国内直接申请的仅6人。参见韩大元:《国际型法律人才,如何培养》,《光明日报》2011年5月5日。 (47)参见刘仁山:《全球化背景下法律人才的培养问题》,《法律科学》2011年第2期。 (48)参见祝建华:《起底“一带一路”项目清单》,《上海证券报》2015年5月29日。 (49)例如,《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作为一项学术成果,对实务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颁布产生了重大影响。又如,在国家讨论是否加入某公约时,中国国际法学会为中央决策提供大量、有影响的参考意见。 (50)国内有学者曾提出“宏观国际法学”这一概念,并认为国际法学体系应当由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诉讼法学和国际行政法学等构成。参见黄进:《宏观国际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从法学体系的构成及分类而言,“宏观国际法学”这一概念是有其正当性的。中国国际法学会近年来的学术活动已经证明这一点。笔者基于本文研究目的,从我国法律体系的构成与分类以及与此对应的学科体系之建构出发,采用中国对外关系法学来概称包括中国国际公法学、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和中国国际私法学在内的以中国对外关系的各个部门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标签:依法治国论文; 法律论文; 国际法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中国法律体系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社会法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