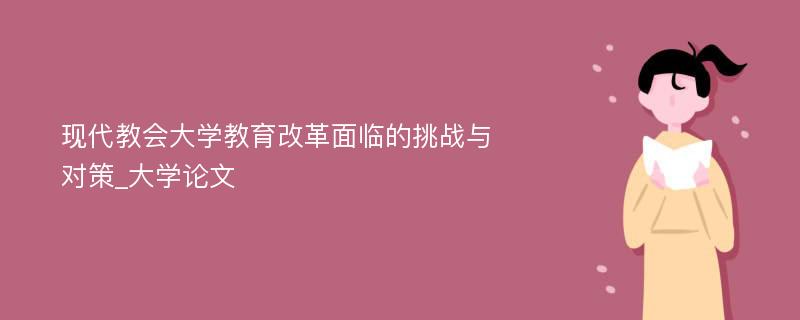
挑战与应对:近代教会大学的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近代论文,教会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6)03-0097-05
一、改革动因:中国本土大学崛起的挑战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基督教教会势力逐步侵入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些知名的教会大学纷纷于此期设立、成型。教会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涉足与发展,缘于培养教会领袖人物,旨在实现所谓“中华归主”的宗教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垄断中国高等教育”,进而建立起完整的教会教育体系,借以达到与中国本土世俗教育分庭抗礼的需要。因此,自教会大学建立以来,其一直是传教士们所关注的热点和办学的重心。传教士无时不在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变化,研究最有效的对策,竭力维持着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在20世纪以前,中国本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教会大学不仅在数量上遥遥领先于中国本土高等教育,而且作为“移植到中国来的西式学校”,其所特有的西式管理、西式课程和西式教法,无疑在与中国本土旧式高等教育的竞争中占据着质量上的优势。因此,教会大学在其时的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可谓是一枝独秀。然而,教会大学在晚清最后十来年间充分发展之时,也孕育着自身存在的危机。这一危机在教育上的表现就是,随着中国社会自身新式教育正式跨入现代化进程,中国本土大学的日益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中国古代并不乏培养高等人才的教育机构,如汉代的太学、西晋的国子学以及宋代以来的书院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具有某种大学的特征,开展了适应于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1]。但是,近代意义的中国大学却不是传统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与发展,而主要是学习、借鉴西方的产物。诚如芳威廉(William B.Fenn)博士所言:“早期由于(中国)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2]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大学,肇始于19世纪末期。它是伴随着晚清统治危机、教育危机的出现而萌生的。甲午战后,借鉴西方模式相继建立的天津中西学堂(1895)、南洋公学(1896)和京师大学堂(1898),“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形”。在清末的最后十几年间,由于受封建传统观念、办学经费以及师资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一直步履蹒跚,发展得十分缓慢。据统计:截至清朝灭亡时,全国仅有大学4所,教职员229人,本专科学生481人[3] (P14-15)。教会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为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同时,由于政权更替,百废待兴,社会对各种高级人才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中华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发展大学教育的有利时机,适时地颁发了《大学令》、《大学规程》等一系列法令,对清末的大学教育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初步改造。与此同时,针对当时政府财政困难、经费紧张的实际情况,民国政府还放开了大学教育的办学权限,积极提倡私人参与大学的创办。有基于此,民初大学教育较之清末有了较大的进步。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数目逐年递增,至1915年,全国公、私立大学数已达10所[3] (P14-15),教职员与本专科学生数也有了较大的增长。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近代中国则更是如此。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以及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民初改革的许多设想并没有在实际中得到贯彻。因此,尽管民初大学教育较之清末有较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只是体现在大学规模的拓展之上,而诸如学术研究、教学质量等一些反映近代大学特质的方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以北大为代表的老校,依旧继承了清末“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具体表现为校政腐败、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教学质量低下、封建文化泛滥等。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延续多久,1917年蔡元培对北大改革后,逐渐得到了改善。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7开始,在短短的几年间,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过蔡元培的改革,北大在学术水平、教学质量等许多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一改昔日的“著名腐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中国最有影响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4],在全国大学改革与发展中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在北大改革的影响与推动下,其他不少大学也纷纷效仿,实行了改革,一批高质量的学府相继涌现,中国本土大学的整体水平,也随之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质量逐渐提升的同时,此期中国本土大学的数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截至1922年,全国公、私立大学已增至20所[3] (P22-23),与同期的教会大学数基本持平,在校学生数也超过了教会大学。此外,还有一些大学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筹创之中。
中国本土大学的“复兴”,引起了在华传教士们的警觉和不安。如果说,清末教会大学是在毫无竞争的局面下得到发展,他们还可以高枕无忧的话,那么,随着中国本土大学的崛起,传教士们深切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挑战。尽管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复兴的过程”[5],并竭力维持着教会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教会大学不可能成为建立全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样板,而且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根本无法控制住中国改革的进程。”[6] (P75)教会大学不仅在数量上逐渐被中国本土大学赶上,更为重要的是,在质量上也开始失去优势地位。摆在教会大学面前的出路是:“要么成为一所综合大学,由一流人才有效地管理,拥有优秀的教员和学者”;“要么成为一所五流的有名无实的大学,只有一些往日的荣誉,而被日益增长的竞争远远地甩在后面”[7]。
二、“更加有效率”:“巴敦调查团”的改革建议
如何应对中国本土高等教育日益崛起所带来的严峻挑战,继续保持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新时期教会大学发展的走向,成为了传教士们共同关注的中心话题。
1920年2月,在“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和“中国续行委办会”的多次申请下,纽约“北美差会顾问委员会”决定向中国派遣专家考察在华教会高等教育,并委派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巴敦担任调查团团长。1921年1月,在美国各差会举行联席会议时,巴敦调查团正式宣告成立,调查团由巴敦、司徒雷登等18名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并在教育界或宗教界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外人士组成。同时,会议决定“扩张考查[察]范围,除高等教育外,兼及基督教所办一切教育事业”[8] (P2)。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巴敦调查团分南北两路对中国基督教教育进行了实地考察。
调查团在实地考察中看到,“有大群中国高尚人士决志在国中建设一坚固之教育制度。彼等任事勇敢,有爱国心,办事诚实,明达而富于牺牲精神”。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国新式学校不仅在数量上已超过教会学校,而且在校学生也“倍蓰于在教会学校中者矣”,“一个新的中国教育制度正兴起”[8] (P2)。这些事实让调查团认识到,教会学校已处于“完全不同于几年以前所占有的地位,以前几乎只有教会学校在中国是采用新式方法教学的。现在意味着,要从数量的基础上进行成功的竞争已是不再有任何可能了”[9] (P349)。然而,就在数量失去优势的同时,调查团在考察中还发现,教会教育的质量也差强人意。长期以来,为了加强福音宣传及与中国本土教育相抗衡,教会不顾人力、财力的局限,建立了许多学校,但“关于学校的三个因素——校舍、设备和教职员——在三要素方面符合正常标准的学校为数甚少”[10]。“摊子铺得太大了”,教育质量下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难怪巴敦在向胡适征求其对教会教育的意见时,胡适反诘他道:“教会教育能不能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的真正超等出色的学校,而不去办那许多中等下等的学校?”[11]
或许是受胡适的提示,更主要的是时势使然,调查团认识到,既然已失去了作为中国惟一提供新式教育的机构的地位,那么,“今后教会学校必须把基础惟一地放在质量上”[9] (P12-15)。为此,他们主张对教会教育进行必要的改革,其口号“就是要使教会学校更加有效率”。所谓“更加有效率”,就是要提高教会教育的质量。调查团认为,只有提高质量,使每一所教会学校都成为“模范学校”、“样板学校”,才能“在中国建立牢固的立足之地”。调查团尤其重视教会大学,“要求一定要把在华教会大学办得永远保持领先地位”[12]。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认为教会大学“非有整顿不可耳”。
调查团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教会大学质量的意见与建议。他们充分肯定了各差会合作办学和教会大学合并的趋势,认为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最佳途径”,并主张进一步“缩减规模,各个学校作出牺牲,联合起来以求得更好的整体效果。”[13] 为此,他们具体建议将中国分为六个大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华西、福建),每区集中力量办好一所大学,其他学生不足100人的有名无实的教会大学,应并入其他大学或者降为专科学校。在强调学校合作、合并的同时,调查团还要求教会大学狠抓教学质量,并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学生入学与毕业标准、课程设置标准等一系列旨在提高教会大学教学质量与专业化水平的建议。另外,调查团对教会大学的学术研究也非常重视,主张加强对任职教师的学术水平的要求,并提出了在教会大学设立研究所、研究生奖学金的建议。
三、由重“量”到重“质”:教会大学的教育改革
“巴敦调查团”考察结束后不久,中国本土大学教育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私立大学数日益剧增。截止到1927年,全国大学数已达到52所[3] (P22-23),比调查团来华时的13所增加了整整3倍。“年来大学之兴,大有蓬蓬勃勃之象”[4]。而与中国本土大学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会大学并没有在数量上继续跟进。相反,在“更加有效率”方针的指导下,教会大学逐渐把办学重心转移到教育质量的提高之上。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既然在数量上已无法再与中国本土大学抗衡,那就于实质上争胜。
1.控制整体规模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教会大学内部就曾经出现过一股合并的热潮。许多在华的西方差会通过相互协商,将一些由本差会单独办理、规模较小的教会大学或具有准大学性质的学院联合起来,组建成为规模较大的教会大学。例如,1915年,苏州的东吴大学与上海的中国比较法律学院合并为新的东吴大学;1916年,北京地区的华北协和大学、汇文大学、华北协和神学院合并为新的汇文大学(后更名为燕京大学)等。“更加有效率”的方针提出之后,各教会大学本此精神,结合调查团“缩减规模”的具体建议,就相互之间的合并事宜,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然而,由于合并,尤其是异地合并,受资金、管理及交通等因素的限制很大,因此,尽管不少教会大学之间达成了合并的初步意向,但最终只有“三起”同处一个城市或相邻地区的教会大学合并成功。这“三起”分别是:1924年,武汉地区的文华大学、博文书院(大学部)、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为华中大学;同年,济南地区的山东基督教大学与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合并为新的山东基督教大学(后更名为齐鲁大学);1929年,华中大学又与岳阳的湖滨大学、长沙的雅礼大学合并为新的华中大学。虽然合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但是教会大学的整体规模还是得到了显著的控制。在此后数十年里,教会大学的数量一直稳定在13所左右,“没有建立任何新大学,现有的大学则着眼于巩固工作”[6] (P113)。因此可以说,调查团所提出的通过“限制其事业,以求效率之增进”的目的基本得以实现。
2.开展校际合作
“数年之前,教会大学颇有互相妒忌和猜疑之事”,彼此之间缺乏“明确的统一计划和有效的合作”[15]。“更加有效率”的方针提出后,各教会大学逐渐加强校际之间合作的力度,为此,他们先后联合建立了“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协进会”(1925)、“中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1928)以及“中国教会大学校董联合会”(1932)等校际合作机构。在这些机构里,“各校皆以团体之一份子自居,而勉尽其份内之义务”[15]。遇到重大问题时,他们就“召集在一起协商、采取共同行动”,俨然一紧密的整体,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学校的办学效率。抗战爆发后,教会大学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许多因战事西迁至成都华西坝或撤退到上海外国租界里的教会大学,纷纷联合起来,采取松散结盟的形式,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校舍以及设备等资源,进行协作办学。正是因为如此,尽管这些教会大学在战乱中经济损失惨重,但却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教育教学水准。除了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外,20世纪20年代以后,许多教会大学还利用自身的优势,与差会所在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校际合作关系,如金陵大学农林学院与康乃尔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与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公共关系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宾西法尼亚大学以及华中大学与耶鲁大学等,在教学、科研和师资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交往与协作。这种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同样也极大地促进了教会大学整体质量的提高。
3.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是衡量大学整体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巴敦调查团”着重强调的一个内容。20世纪20年代之后,各教会大学逐渐加强了对教学质量的重视程度,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其一,提高对教师任职资格的要求。师资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意欲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则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各教会大学改变了前期“所有教师由差会委派的旧例”[16],纷纷按照严格标准自行选聘教师,并且还根据教师的水平确定不同的职称。如燕京大学将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襄教授、讲师、助教、助理六个等级,每一等级都有相应的资历和学历的要求。其中,晋升教授的条件是:必须“具备五年以上教学工作经验,在拿到最后一个学位后有专著出版”。在当时,这个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其二,严格考试制度。考试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督促学生勤奋学习,借以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教会大学十分重视考试在提高教学质量中的作用,学生从入学到毕业,要经过无数次考试的层层选拔。虽然各校采取的考试方式不尽相同,但“严选择”、“高淘汰”则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沪江大学1925年的统计表明,该校仅41%的一年级学生能读到四年级;华中大学每年也有很多学生因未能通过“中期考试”而被迫留级。其三,改善教学设备条件。图书、教具、器材等教学设备,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重要物质条件。教会大学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教学设备的建设,在经济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改善教学设备的条件。如燕京大学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将从“洛克菲勒基金会”争取来的捐助,大量用于购置珍、善本书籍,从20年代末开始,在短短八九年间,使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从原来的几万册增加到30多万册,图书馆藏书量居中国各大学之魁首。在各教会大学的不懈努力下,教会大学的教学设备条件大为改观。截止到1938年,“基督教大学总数占全国大学总数约为百分之十二,学生亦为全国大学学生百分之十二;而在基督教大学设备、经费、图书等之百分比皆远过此数,可知基督教大学在设备经费图书上皆占优势”[17]。通过上述措施,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正是由于具有较高的教学质量,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不仅吸引了中国多数最优秀的青年;并有许多毕业生已在社会事业上成为各种领袖”[18]。
4.加强学术研究
“教学与研究是大学教育的两翼”。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教会大学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得到了加强。1924年,为了推动教会大学努力提高学术水平,“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开始规定最低的学术水平标准,并按照学术水平对教会大学进行分级。此项举措大大激发了教会大学对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各校因此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强化学术研究的措施:首先,积极鼓励在职教师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如金陵大学规定,讲师以上的教师工作满5年且成绩卓著者,就可以带薪出国深造,时间为1-3年;华中大学为此也专门建立了“青年教师基金”,用于每年资助一名优秀青年教师赴国外大学进修,等等。其次,建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在贯彻这条由调查团所提出的建议方面,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动手最早。1922年底,燕京大学就在教会大学中率先成立了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开始了学术研究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1934年,该校正式成立研究生院,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学系已达到了12个[19]。在燕京大学的带动下,各教会大学纷纷效仿,先后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如东吴大学的淡水生物研究所、福建协和大学的植物病虫害研究所、华西协和大学的农业研究所以及金陵大学的农业经济研究所和农艺学研究所等。通过这些机构,教会大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研究生,而且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再次,创办学术性刊物。学术刊物反映了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也是进行对外学术交流的窗口。各教会大学纷纷改变了前期校刊与学刊合而为一的做法,另行创办了一大批及时反映学术研究动态、具有较高学术性的刊物,如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半年刊,1927-1951)、金陵大学的《金陵学报》(半年刊,1931-1941)以及东吴大学的《法学季刊》(1922-1941)等。这些学术刊物以研究、交流学术为宗旨,多由本校教师担任撰述,间以发表学生和校外学者的论文。它们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教会大学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此外,教会大学还采取了诸如组织学生创立学术社团、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学等旨在提高学术水平的相应措施。随着这些措施的贯彻与落实,教会大学的学术水平显著提升,“在抗战前的中国整体学术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20]。尤其是在医学、农林、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商学以及图书馆学等学科领域,与中国本土大学相比,他们“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21] (P1)。
在“更加有效率”方针的指导下,教会大学从内外两方面着手,通过前述种种措施,使自身的整体质量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专业化水平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乃至于国际社会享有较高的声誉。“他们与非洲的教会学校相比,显然处于较高的层次;与印度的教会大学相比,为数虽较少而质量则较高;与日本的教会大学相比,则具有较强的与公立大学竞争的实力。”[21] (P1-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还“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示范与导向的作用”[22]。毋庸置疑,在“更加有效率”方针指导下的教会大学教育改革,其初始动力乃是传教士保持教会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进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华归主”的宗教目的。但其客观上,却将竞争机制引入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本土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果从立案注册后,教会大学“已在实际上认同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23] 角度而言,20世纪20年代后教会大学的专业化改革,则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在诸多方面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