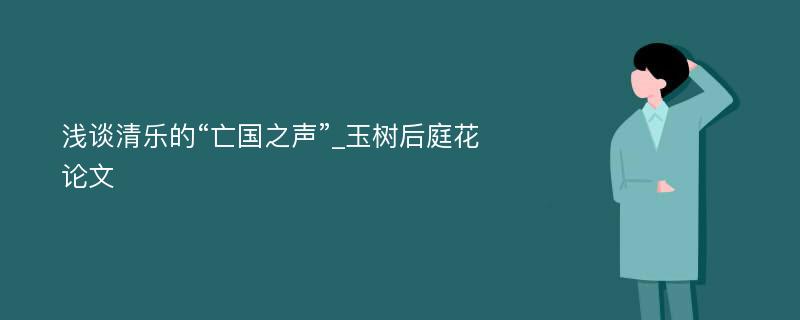
清乐“亡国之音”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亡国之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12)02-016-05
清商乐又名清乐,是中古最为流行的音乐之一,其曲辞也是中古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乐当中,产生过很多美妙动听、感人至深的乐曲和诗歌。然而,有些清商乐曲虽然辞、曲双美,却颇为人所诟病,蒙上了不好的名声,比如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所录《杂曲歌辞》的“解题”有云:
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寖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昔晋平公说新声,而师旷知公室之将卑。李延年善为新声变曲,而闻者莫不感动。其后元帝自度曲,被声歌,而汉业遂衰。曹妙达等改易新声,而隋文不能救。呜呼,新声之感人如此,是以为世所贵。虽沿情之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迫,少复近古。故萧齐之将亡也,有《伴侣》;高齐之将亡也,有《无愁》;陈之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隋之将亡也,有《泛龙舟》。所谓烦手淫声,争新怨哀,此又新声之弊也。[1](P884-885)
郭氏提到的《玉树后庭花》、《泛龙舟》二曲分别是南陈和隋朝时创作的“清商新声”,①而《无愁》、《伴侣》二曲的产生也与清商新声有密切的关系。不幸的是,这几首“感人如此”、“为世所贵”的乐诗,却被编录者视为萧齐、南陈和隋朝几代灭“亡”的原因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亡国之音”。这样的看法有什么依据呢?值得进一步讨论。另若再作稽考,史上蒙有如此“恶名”且又与清乐关系密切之乐曲尚有不少,俨然形成了历史背景和艺术特点相近的一个小类。如把它们集中在一起略加考释,并分析其共同特点所在,不但对回答前述的问题颇有帮助,似亦有补于以往的音乐史和诗歌史研究。
一
前引《乐府诗集》中提到:“故萧齐之将亡也,有《伴侣》;高齐之将亡也,有《无愁》。”其实《伴侣》和《无愁》二曲都出于北齐,与南朝的萧齐并无关系。先看《伴侣》,据《北史·阳俊之传》记载:
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2](p1728)
可见,北齐文襄帝高澄(521-549年)时已有阳俊之者曾作过《阳五伴侣》曲辞。阳五应指阳俊之,卖书者误以为古之贤人,所以俊之窃喜也。另据《文献通考·乐十五》称:
(北齐)后主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倚弦而歌,另采新声为《无愁》、《伴侣》曲。[3](P1253)
可见,到了北齐后主(565-576年)时,复在“淫荡而拙”之《阳五伴侣》的基础上创编出《伴侣》,所谓“采新声”当指采用了《阳五伴侣》的曲调形式。因此,无论齐襄帝时的《阳五伴侣》抑或齐后主时的《伴侣》,均产生于北朝,《乐府诗集》说“萧齐之将亡,也有《伴侣》”,实误。
接下来再看《无愁》曲,其产生的过程,与《伴侣》一曲颇为相似,而且也和北齐后主有关,据《隋书·音乐中》记载:
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4](P331)
可见,《无愁》也是齐后主“别采新声”而编制的乐曲,其名目在《乐府诗集》卷七十五《杂曲歌辞》中收录,又名《无愁果有愁曲》,曲前“解题”补充《隋书·音乐志》称:“李商隐曰:‘《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也。’《唐会要》:‘天宝十三载,改《无愁》为《长欢》。’”[1](P1064)其后录有李商隐所作一首,七言十四句古体,但唐以前的曲辞则已不传。
以上是《伴侣》、《无愁》二曲的基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此二曲虽产于北齐,但均与南朝的清商新声有关。首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王运熙先生,他在《论六朝清商中之和送声》一文指出:
清商乐曲的变曲,恐怕也是基于和送声的变调。最显著的便是《莫愁乐》,它是从《石城乐》的和声产生出来的。……当时清乐既流行于北朝,后主的新声很可能受到它的影响。我疑心《无愁曲》即是利用《莫愁乐》的和声制成,因无、莫两字可以相通的。……《通考》一四二:“北齐后主,别采新声为《无愁》、《伴侣》。”是后主于《无愁曲》外,又有《伴侣曲》。《伴侣》与《无愁》合叙,二者性质必甚相近。我疑《伴侣》是西曲《杨叛儿》的变曲,叛、伴同音,儿、侣同声,伴侣即叛儿的音变。[5](P115)
王氏提到的《杨叛儿》,或名《杨叛》,或名《杨伴》,列于“西曲”,故属南朝清商新声的范畴。除王氏所述的理由,尚有证据说明《伴侣》与西曲《杨叛儿》有关,据《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
《杨伴儿》,本童谣歌也。齐隆昌(494年)时,女巫之子曰杨旻,旻随母入内,及长,为后所宠。童谣云:“杨婆儿,共戏来。”而歌语讹,遂成杨伴儿。[6](P1066)
由此可见,西曲《杨伴儿》“本”于“童谣歌”而作,为三言的句式,但两个三言句如不断开则成为六言,正好与《阳五伴侣》“多作六言歌辞”的句式相合,而且在时间上确实也早于《阳五伴侣》的出现,有可能影响及之。至于《莫愁曲》,也属西曲,《乐府诗集》卷四十八《清商曲辞五》录之。前引王运熙先生文中指出《无愁》曲的“和声”乃“利用《莫愁乐》的和声制成”,所以清乐对《无愁》有很大影响。这也有道理,因据《隋书·音乐志》记载,《无愁》曲曾被胡儿阉官辈“齐唱和之”,颇合于清商新声演唱的惯例。
此外,《伴侣》和《无愁》二曲都是北齐后主“别采新声”而创编的,是哪种“新声”能令“唯赏胡戎乐”的后主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呢?窃以为亦非南方传入北朝的清商曲莫属。据《魏书·乐志》记载:
初,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其圆丘、方泽、上辛、地祇、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7](P2843)
可见早在北魏后期,南朝的清商新声已因战争等原因大量传入北朝,以至于“殿庭飨宴”皆广为演奏。到北齐时,这种音乐理应更为流行,所以朝廷才专门设立了“清商署”和“伶官清商部直长”以管理之。②有鉴于此,《伴侣》和《无愁》这两种“亡国之音”受南朝清商新声影响而创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二
与北齐相比,南陈的“亡国之音”似乎要多得多,除了商女“隔江犹唱”的《玉树后庭花》外,与之一起产生而又性质相近的还有《黄鹂留》、《金钗两臂垂》、《临春阁》、《春江花月夜》、《堂堂》等曲,以下略为申述。据《隋书·音乐志》记载:
及(陈)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簿。男女唱和,其音甚哀。[4](P309)
可见,《玉树后庭花》、《黄鹂留》、《金钗两臂垂》等皆为“清乐”,而且由南陈后主新“造”,自属清商新声无疑。其中《玉树》一曲在《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辞四》见录,其“解题”称:
《隋书·乐志》曰:“陈后主于清乐中造《黄骊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五行志》曰:“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辞甚哀怨,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谶,此其不久兆也。”《南史》曰:“后主张贵妃名丽华,与龚孔二贵嫔、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并有宠,又以宫人袁大捨等为女学士。每引宾客游宴,则使诸贵人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千数歌之。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1](P680)
郭氏“解题”后录有陈后主所作《玉树后庭花》原辞一首,七言六句:“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1](P680)至于《黄鹂留》及《金钗两臂垂》二曲,则《乐府诗集》不载,大抵亦陈后主或诸贵人、女学士等所作。词既艳丽,又由宫女歌之,则称为“宫体”也无不妥。
另外,上引郭氏“解题”中又提到《临春乐》,此曲当与后主所建“临春阁”有关。据《陈书》卷七《张贵妃传》记载:
至德二年(584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春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沈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8](P132)
据此,则《临春乐》亦为清商新声无疑,但《乐府诗集》中也不录。除上述诸曲外,《春江花月夜》、《堂堂》二曲,亦与《玉树后庭花》等大约同时产生。《春江》一曲在《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辞四》见录,其“解题”云:
《唐书·乐志》曰:“《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后主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1](P678)
可知其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均与前述南陈诸曲相近。其后录有隋炀帝《春江花月夜》曲辞二首,俱五言四句: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1](P678)
此曲当是隋平陈后,陈朝清乐为隋人所得,故杨广据旧曲填上新辞。另一首《堂堂》亦为清乐,据《通典·乐六》“清乐”条称:
清乐者,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氏以来旧曲。……及隋平陈后获之。……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先遭梁、陈亡乱,而所存盖鲜。隋室以来,日益沦缺。大唐武太后之时,犹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投壶》……《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共三十二曲。[9](P3716-3717)
可见,直到中唐杜佑时清乐《堂堂》的曲辞尚“存”。但《乐府诗集》中已无陈人原作,而仅录温庭筠所作《堂堂》诗一首,七言八句:“钱塘岸上春如织,淼淼寒潮带晴色。淮南游客马连嘶,碧草迷人归不得。风飘客意如吹烟,织指殷勤伤雁弦。一曲堂堂红烛筵,金鲸泻酒如飞泉。”[1](P681)此诗前四句入声作韵,后四句又换韵,乃属古体,虽晚唐人作,犹有六朝旧曲声辞之韵味。
总之,《玉树后庭花》、《黄鹂留》、《金钗两臂垂》、《临春乐》、《春江花月夜》、《堂堂》等五曲皆为南朝陈代的清商新声,多创作并施用于宫廷宴会之中,其曲辞皆可视为梁、陈之宫体。而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它们多和陈后主的荒淫游宴有关,所以亦负上了不雅之名。
三
至隋炀帝时期,也产生了几首和清乐有关的“亡国之音”,包括《泛龙舟》、《投壶乐》、《万岁乐》、《斗百草》等。前引《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之“解题”就提到“隋之将亡也,有《泛龙舟》”,据《隋书·音乐志》记载: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4](P378-379)
可见,隋炀帝时创编了一大批“新声”,其中《泛龙舟》在前引《通典·乐六》中已列入“清乐三十二曲”的范围。《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四》收录炀帝《泛龙舟》曲辞一首,七言八句:
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1](P682)
而在敦煌遗书中也有《泛龙舟》曲辞一首,七言八句,并有送声:
春风细雨沾衣湿,何时恍忽忆扬州。南至柳城新造口,北对兰陵孤驿楼。回望东西二湖水,复见长江万里流。白鹭双飞出溪壑,无数江鸥水上游。泛龙舟,游江乐。[10](P379)
上引曲辞的字数、句数与隋炀帝所作相同,表明唐代尚有此乐的流传。最后两句作“泛龙舟,游江乐”,此六字即所谓的“送声”。如前所述,清乐曲调的命名往往取曲中的“和送声”为之,《泛龙舟》与此符合,由此也可证明它为“清乐”。另据《旧唐书·音乐志二》称:“《泛龙舟》,隋炀帝江都宫作。”[6](P1067)故此曲当为炀帝南游时由白明达新造,其本于南方的清商乐实可信。
除了《泛龙舟》,炀帝乐正白明达所造的新声还有十余曲,其中《投壶乐》一曲也属清商乐范畴。据《旧唐书·音乐志二》称:
《骁壶》,疑是投壶乐也。投壶者谓壶中跃矢为骁壶,今谓之骁壶者是也。[6](P1066)
而《新唐书·礼乐志》更直接认为:“《骁壶》,投壶乐也。”[11](P474)据此,《投壶乐》应就是《骁壶》。由于《骁壶》在前引《通典·乐六》中列入曲辞尚“存”的“清乐三十二曲”,可证白明达所造的《投壶乐》也是清乐。它与《泛龙舟》在《隋书·音乐志》中之所以被放入《龟兹》部乐内叙述,当是因为白明达造二曲时融入了龟兹乐的成分,详后。
此外,炀帝时诸新声中的《万岁乐》、《斗百草》二曲也与清乐颇有关系,据《唐会要》卷三十三《诸乐》记载的“太常梨园别教院”所“教法曲乐章”中,有法曲“十二章”,其中四章的名目如下:
《玉树后庭花乐》一章;《泛龙舟乐》一章;《万岁长生乐》一章;《斗百草乐》一章。[12](P614)
由于《玉树后庭花》及《泛龙舟》原本皆为清乐,至唐被改为法曲;而《万岁乐》、《斗百草》二曲则与之并列,有理由相信《万》、《斗》二曲原本也为清乐,唐时始改为法曲。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法曲这一乐种直接源于清乐,这在宋代就被陈旸指出过,③所以《万岁乐》和《斗百草》即使不是纯粹的清乐,也必与清商乐有密切关系。
换言之,隋炀帝乐正白明达所造的“新声”十余曲中,有《泛龙舟》、《投壶乐》二曲可属清乐范畴,《万岁乐》和《斗百草》至唐代被称为法曲,故其起源亦必与清乐有关。这四首乐曲同样负有艳丽淫绮的不雅名声。
四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北齐的《伴侣》、《无愁》二曲,南陈的《玉树后庭花》、《黄鹂留》、《金钗两臂垂》、《临春乐》、《春江花月夜》、《堂堂》五曲,隋朝的《泛龙舟》、《投壶乐》、《万岁乐》、《斗百草》四曲,或本身即为清商新声,或和清乐存在渊源关系,并且与北齐、陈、隋三代的灭亡都产生了联系,成为后人眼中的“亡国之音”。在清乐中出现这种带有共性的现象,其原因和意义都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
笔者认为,这十余首乐曲被称作“亡国之音”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分别产生于北齐后主、南陈后主、隋炀帝三位“亡国之君”手中,甚至有数曲更是亡国之君所亲手创作;古人受“乐与政通”观念的影响,认为政治的不清明与朝廷、社会上流行的音乐有必然的联系,于是这批乐曲竟不幸成了亡国的替罪羊。类似情况在先秦时期就出现过,据《韩非子·十过》称:
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13](P62-64)
自上引可见,师涓所奏的“清商”之曲,曾被晋国乐官师旷认为是导致商纣灭亡的“靡靡之乐”。先秦时的“清商”曲和南北朝及隋的“清商新声”当然不可混为一谈,但它们被视为“亡国之音”的原因却大体相似。当然,若从政治的角度讲,齐后主、陈后主、隋炀帝三位国君对这些清商乐过分沉溺、“悦玩无倦”的态度确不可取,也难免增加了它们蒙上恶名的可能性。
抛开历史和政治的因素,其他的原因似乎应从清商新声本身的艺术、文学、表演诸方面特点中找寻。总的来讲,南北朝及隋的清商乐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特点,尤其是它们怨哀靡曼、感人至深的风格,与古人崇尚的典正平和之雅乐有明显差别,这是它们成为“亡国之音”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据梁元帝《金楼子》卷二《箴戒篇》记载:
齐武帝有宠姬何美人死,帝深凄怆。后因登岩石以望其坟,乃命布席奏伎。呼工歌陈尚歌之,为吴声鄙曲。帝掩叹久之,赐钱三万,绢二十匹。[14](P899)
这是南齐武帝时事。如所周知,南朝清商新声是魏晋清商旧乐与吴歌、西曲相结合的产物,引文提到的“吴声鄙曲”正是指吴歌。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哀怨凄怆”是清商新声的一种主要风格,所以前文引述的典籍中也一再出现过“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掩抑摧藏、哀音断绝”等形容词。这种令人“掩叹久之”的新声,当然也具备了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不过,古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亡国之音哀以思”(《礼记·乐记》),清商新声的主要艺术风格不幸又与“亡国”一词对上号了。
第三个原因则与这批乐曲在艺术上的过度求“新”有关,部分乐曲乃至于和西域新传的胡乐相结合,以致“繁手淫声”、“流而忘反”,其中尤以北齐、隋朝诸曲为甚。王运熙先生在《清乐考略》一文中就曾指出:
自北朝起,清乐与胡乐渐有合流的倾向。……我在《论六进清商曲中的和送声》一文中曾经考证(齐)后主的《无愁曲》是南朝清乐《莫愁乐》的变曲。然则《无愁曲》当系清乐与胡乐的混合产品。隋代许多典章制度,直接承袭北朝,音乐亦然。炀帝所制的《泛龙舟》,很可能跟《无愁曲》一样,是清乐与胡乐的混合产品。日人林谦三氏在《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中说:“白明达当是龟兹人,龟兹王白姓,见《魏书·西域传》、《隋书·龟兹传》、《唐书·西域传》、《悟空入竺记》等书。”又说:“《泛龙舟》本来是清乐,它是白明达所造,恐与龟兹乐有关系。”其说颇可信。[5](P219-220)
白明达为龟兹后裔,近世向达、丘琼荪诸先生均持此说,所以上引的观点颇为可靠。复因此,南北两大乐种遂能冶为一炉,其音调新异、令人叹赏沉溺就不足称奇了。另外,陈朝的《玉树》等曲可能也有南乐和北乐合流的因素,因为前引《隋书·音乐志》曾提到陈后主“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而《玉树》诸曲又多为宫中女学士所作,融入北方箫鼓的特点也极有可能。但古人尚古,过分创新甚至融入异族之乐,都被视为是不可取的。
这批乐曲成为“亡国之音”的第四个原因则与其曲辞特点有关,恰如历史记载所说的“绮艳相高,极于轻簿”,这批清乐曲的遣辞造句均极为藻艳,除了前文已引的例子外,不妨再看看唐人所写的《春江花月夜》曲辞:
春江湖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深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首诗是初唐“吴中四杰”之一的张若虚所写,曾被誉为“孤篇压全唐”之作,闻一多先生对其评价尤高。④然而,就其文辞来看,依然脱不开六朝新声那种“艳丽”、“淫绮”的风格。唐人之作尚且如此,六朝人作清乐新声曲辞之艳绮如何,自不烦多说。由绮艳而至于“轻薄、淫荡”,从传统的角度看,确非帝王所宜,宜乎其遭人诟病也。
第五个原因则与乐曲的实际表演情况有关。作为清商乐,这批乐曲不但是音乐,也是文学,而且还须应用于表演。《陈书·张贵妃传》说南陈诸曲表演时要动用宫女有容色者千百数,其靡费可知。另据《大日本史》卷三四七《礼乐志》记载:
堀河帝尝闻元兴寺藏有《玉树》装束,遣左大办大江匡房检之。柜上题曰:“《玉树》、《金钗两臂垂》装束二具。”其装束美丽无比,金冠贯以五色玉,饰以各色丝,似神女装束。[15](P189)
说的正是《玉树后庭花》和《金钗两臂垂》二曲表演时乐人的装束。从“金冠”、“五色玉”等词看,此二舞所费不知凡几。在生产力尚非十分发达的古代,国家兴亡往往与上层的奢华靡费有重要的联系,这批新声曲在表演时装束奢侈、劳民伤财的特点难免会成为众矢之的。
总而言之,北齐、南陈、隋朝三代都出现过与清商乐有关的“亡国之音”,不妨将它们作为一个小类加以研究,这种尝试本身带有一定的创新性。探讨过程中还可以发现,这批乐曲在艺术、文学、表演诸方面有着不少相同之处,它们被称为“亡国之音”亦有大致相同的历史、政治原因。这些特点和原因的揭示,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古诗歌史和音乐史发展似亦有一定的帮助。所述不当之处,敬祈教正。
注释:
①根据音乐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习惯,把流行于魏晋时期的清商乐称为“清商旧乐”;东晋以后,魏晋清商旧乐流传到南方,和吴歌、西曲结合产生了新的清商乐,则谓之“清商新声”。
②详拙作《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所述,兹不赘。
③陈旸《乐书》卷188称:“法曲兴自于唐,其声始出清商部,比正律差四,郑卫之间。有铙、钹、钟、磬之音。”(《文渊阁四库全书》211册84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④闻一多先生《宫体诗的自赎》一文曾评价此诗云:“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庭所遗下了那分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收入《唐诗杂论》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