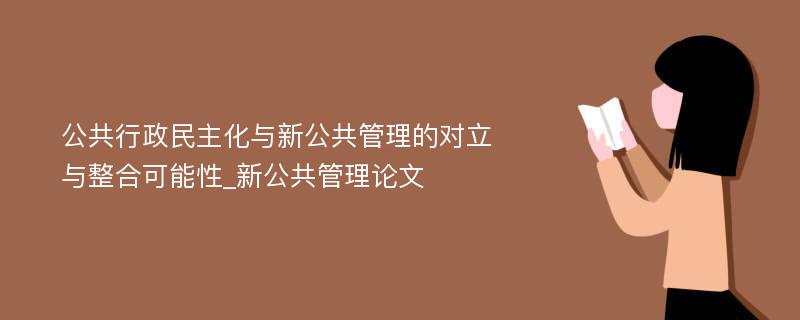
公共行政民主化与新公共管理的对立及融合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化与论文,公共管理论文,可能性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1-0087-06
自从新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流行以来,阐释者与批判者围绕公共行政是什么的问题,形成了一场新的交锋,其中民主制行政学派是批判的强音符。分析民主制公共行政的理路可显现新公共管理侵犯了什么和遭遇批判的原因。但新公共管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与民主制公共行政有融合的方面。
一、民主化公共行政的七条路径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美国公共行政针对威尔逊—韦伯范式的“古典理论”或“正统理论”的质疑而发生的学科分化运动,民主制行政理论出场。这是解构官僚制化行政的第一波民主化思潮,它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昙花一现”,而是持续化的。当新公共管理出场后,民主化思潮之锋芒所向又指向了它,它们的对立将是持久性的。但民主化公共行政也并没有统一的纲领,有些方面甚至是冲突的,又有家族的相似性。从有关的文献中,可以厘析出民主化公共行政的七条路径。
1.新公共行政的民主化第一波
新公共行政的基础理论奠基者是民主理论家达尔和公共行政学家沃尔多。达尔批判了公共行政的泰勒主义和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强调了公共行政必须要有文化的、伦理的、历史的视野。沃尔多从重释公共行政是什么的视角,诠释了“行政”是关于人类实践的“理性合作”的一种,而更主要的是如何“获得”理性合作。而“公共”不仅仅是“事务”的“结构—功能”之解释,它应当与“文化”取得一致性,而且“文化”更为根本。[1]190-196追随沃尔多的一批青年学者在这条道路上进行耕犁。如弗雷德里克森从公民公共精神的本体论视角,以“乐善好施”[2]175作为公民精神的规范,重塑官僚人格——代表性公民,构建了高公民精神与高行政管理相一致的社区民主自治的民主化公共行政之路径。
2.复合政体与交叠管辖的民主制公共行政
此学派几乎与新公共行政于20世纪同期出场。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是领军人。他批判了美国宪法的解释的模糊性。认为宪法包含了官僚制行政和民主制行政的双重可能性。而官僚制作为选择取向是因为联邦党人中的国家主义的党派政治强势使然,丧失了美国精神的根本——民主自治。“民主自治”才是联邦民主的基础,他借用列宁的话批评代议制民主是政党派别的“清谈馆”和“俱乐部”。在重释宪法民主之根基的基础上,重构社区公民自治与州政府、联邦的分权与复合的政体。在公共事物上交叠作用、服务于社区的民主自治。以“公共企业家精神”,亦即以公共利益为行动指向的公民性之精神[4]174-175,形塑“公民性”的官僚人格,构建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公民参与、选举、监督、共同合作实现公共利益的民主制公共行政模型。他也规范了公共行政学者所要做的事情:提供“结社”学问的新政治学。
3.后现代公共行政
后现代主义是欧洲大陆的产儿、北美的养子,这也是后现代公共行政在美国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之缘由。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学者们虽然没有统一的纲领,但在批判、解构官僚制,实现公共行政的民主化上是一致的。他们基本上借用现象学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诠释学”、梅洛-庞蒂的“身体政治”、德里达的“解构”、福科的“话语实践”、哈贝马斯的“公共性”和“交往实践”等概念,组合成基于社区自治的“话语实践”民主理论,作为公共行政之取向。
4.新公共服务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代表学者罗伯特·登哈特、珍妮特·登哈特认为,新公共管理在实务的领域大行其道,其市场主义之取向及其作为理论基础的公共选择理论悖逆了公民权、公共利益、公共性等公共行政之价值;“掌舵”而不“划桨”之主张,是“主人”政府,而不是服务于公众并以公众为主人的政府。他(她)们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已包含了公共服务的内容,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仍然要发挥主要的作用,但其局限性在于片面地强化了“国家主义”,而忽视人之存在的社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公民权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为思想资源,视民主是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构建官僚、公民团体、民选代表以及司法救济机构在内的民主治理系统[4]79,官僚的角色是促进“话语实践”与公共利益的联结及其实现。
5.黑堡宣言学派的民主制公共行政理论
此学派以古德塞尔的《为官僚制辩护》为蓝本,发表了挑战新公共管理的《公共行政与政治过程:转变美国的政治对话》(简称“黑堡宣言”)而确立。黑堡学派反驳新公共管理视官僚制的无效率与才智低下,但也并不是一味坚持所谓韦伯理想类型的官僚制之合理性。认为官僚制这种精细化的行政组织错置于循环民主论的政党斗争中;应重释宪法的民主价值,使官僚机构和官僚效忠于宪法,这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回应获胜的民选官员。宪法激活了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团结的“契约”,它是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官僚机构生于斯、服务于斯,代表人民效忠宪法,扮演“贤明的少数”,使社会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保持动态的平衡。公民的参与与官僚机构的回应,激活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治理路径。
6.治理的民主化途径
治理(governance)并不是新的,传统意义上与管理、统治互替。因此“治理”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殊异的指谓。但治理的民主化途径,强调了与新公共管理等同的治理之不同,“是在众多不同利益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以便实施某项计划”[5]16。“善治”是指治理的“应然”取向,强调的是互动性的网络组织,政府和官员是核心,但并不是主宰,是组织、动员的领导者。以平等、认同、透明、回应、道德、责任等范畴构成善治的行动过程,实现公共利益。
7.社会建构主义的民主化公共行政
此学派被西方有的学者视为“新公共行政”的传人,但社会建构主义的公共行政具有其独特性,整合了现象学的诠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实践、新公共行政的理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资源。认为人类实践是各个人都置身其中的互动、沟通、对话的理解境域,采取一致行动的组织不是一个固定化的“科层”制的精英组织外于公众,而是公众成员主体间性的话语实践创造了组织的现实。公共行政的一致行动就是官员与民众共同学习和持续性的参与、协商的话语实践。
二、民主制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的差异
民主制公共行政与官僚制化的公共行政是对立的,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做出的判定。在一个民主制的国家,大众参与和共同管理的行政必然陷入价值冲突、混乱不堪的境域。因此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度,价值与事实相分离的两个领域,以代议民主的议会斗争框定“价值冲突”、平衡政党政治;而公共行政所框定的是“事实”的、理性的领域,理性官僚制作为合理性的根基在于法律合理性,科层化的权力资源配置和官僚对法律的效忠、价值中立、对大众不偏不倚、无情无义的机器般运行是效率的、无矛盾的,与社会公平的大众意识相一致。韦伯所得出的结论是:民主诉求催生了理性官僚制,但官僚制一旦发展起来,就让大众走开。但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只是“理想类型”的理论预设,而在现实中是难以存在的。从经验上,美国随着“新政”的大政府兴起和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官僚政客化、政客官僚化的双向驱动,行政官僚在法律、规制、政策、执行等方面的能动性,官僚并不是无情无义的非人格化的机器,也不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工程师心态。因此西蒙关于“有限理性决策”之模型的提出,并非是纯理论的预设,而是经验的,将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引入“行政人”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民主制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以瓦解官僚制为己任,但二者在以下两个方面显明其差异性:
1.关于出场路径
民主制公共行政建基于人类实践的合作理性的假设之上,是在伦理的文化、人性之传统之中的。以此理解的行政即是“试图获得合作理性”,而非理性既不可能排除,也不可忽视。交往实践的主体间性的差异、认同、协商是合作理性生成于“生活世界”之本体的“集体行动”的合法性源泉。以“好公民”,即“乐善好施”为公民的规范性假设,形塑官僚的公民性人格。“公民性”是官僚的人格规范,它指谓了以公共利益维护、实现的公共精神的价值向度和具有平等、博爱的职业精神、专业技能的统一,在公民、利益相关者、各种机构的大系统中成为领导者和服务者,但并不是主宰。在上述的民主化公共行政七条路径中,这些是基本的。
新公共管理的出场路径较为复杂。在实践的路径上,是指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里根—撒切尔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政府改革运动。1991年,英国学者胡德所撰写的对这场运动的评估报告中予以“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标签,并描述为七个方面的特征。其核心的理念是“各级政府为实现经济、效率、和效能的‘3Es’作出决定性的努力”[6]2。因此它又被称为“管理主义的”、“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在学术领域,学者们对新公共管理无论是轻视、赞誉还是批判都在反思诠释的语境中探寻新公共管理“新”在何处?美国学者罗森布鲁姆认为,威尔逊所开辟的道路就是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同义。“新”是相对于其而言说的。澳大利亚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公共管理是作为技术层面的功能分支,新公共管理就是把“管理”提升到行政之上,使行政作为其“执行”的分支领域。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亨利在厘析公共行政学科从政治学、普通管理学和工商管理学科分离运动中,后者称公共行政为公共管理。美国学者费斯勒和凯特尔判定,将公共行政包含于一般管理之中的是社会学家、组织研究专家和商学院的管理学者。[7]8因此,公共管理在西方有四种不同的路径:(1)作为公共行政同义的公共管理;(2)来自政策学派的公共管理;(3)来自普通管理学和工商管理学科的公共管理;(4)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5)重塑政府学派的公共管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与这几种公共管理的关系存在着辩难。休斯等人证明公共管理不同于公共行政的焦点是行政(Administration)与管理(Management)的差别问题,这只是语义学上的。古德诺也说明了英语的“行政”之模糊性,人们往往误解为执行,他所强调的是管理之意[8]11;另一方面威尔逊又指出了政治是行政的方向,但不因此而是政治,行政是法律的执行,但不因此仅仅是执行法律,这显然也是强调的管理之义。因此在语义学的语境中厘析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差别收获甚微,只是强调了词义的哪一方面为重音符的问题。新公共管理的命名者胡德称它是“新泰勒主义”的“新瓶装旧酒”,主要指涉它试图复兴科学管理的路径。但新公共管理还是有“新”之处的。在西方的学者中,传统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无实质的差别,关键在于它是基于政治学途径的。奥斯特罗姆指认,它是属于进步政治运动的“政治科学”之途径。而新公共管理正是基于管理学的学科基础,这也是新公共管理试图被学科化而寻找新的理论资源的努力取向。来自政策学派的公共管理、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重塑政府学派的公共管理都与新公共管理有着差别,虽然有的学派申明对新公共管理的纠偏,但与新公共管理也有一定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所采取的“理性人”假设与民主制行政学派的人性假设不同。尽管新自由主义不再以“人是自私的”作为立论的根据,转而采取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人既不是自私的也不是利他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一假设产生三个问题:(1)公共利益不存在,所谓公共利益就是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机构宣称代表公共利益,是欺骗,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是典范;(2)集体行动不可能,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理论典范;(3)官僚机构和官僚都是以预算最大化为行动指向,与政党形成“双边控制”,生产的公共产品大多是无效的,尼斯卡宁的官僚的批判理论是典范。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新公共管理的锋芒所向是对官僚制公共行政的批判,所选取的道路是获胜的政党“掌舵”。而民主制公共行政所批判的就是政党对公共行政的掌控。从民主化公共行政所追求的实质民主和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的态度来看,它就是反民主的。
2.关于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中轴问题,学术上的争论及对实务取向上的反思、诠释、批判都与这对范畴有关。常识性的问题是:威尔逊—韦伯范式的理性官僚制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它是由哲学家休谟关于价值与事实二者之间不可相互推论之命题转换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态中。代议制民主是价值的领域,而公共行政即是关于“事物”的“事务”领域,正如“民主党与共和党修路有什么不同”一样,它是“事实”的问题,或是工具理性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断定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难以和解,因此政党在政治斗争中的冲突与平衡必然导致理性官僚制这种合理合法型的统治形式,它的工具理性和价值中立排除了公共行政的冲突与矛盾,达到无矛盾性的运行。但是,这一常识性的问题却往往忽视这些学者所说的政治指谓的什么?
韦伯有明确的论断,政治是关于谋取、获得、经营国家权力的行动,而“权力”与“权威”又有差别,前者在民主社会依据法律所具有的支配力,而后者是基于人们的自愿认同、服从所形成的。但在威尔逊的文献中对政治的界定是模糊的。他在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中讨论“政治”概念,并没有明确区分广义与狭义,而在言说行政并非政治之时,又没有明确他所说的此政治是“政党政治”。这种模棱两可性,到古德诺已经澄清了。“‘政治’一词在这里的含义,不是大多数政治著述家所认为的那种含义……‘从狭义和较常的意义上说,政治是公民中的政党组织指导或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或职业’……它就经常不顾伦理道德的区别而特别包括那些左右公共舆论,吸引和引导选民,以及获取和分配公职位职权的艺术。”[8]10-11显然,威尔逊所说的“政治”也是狭义的“政党政治”。但不仅如此,威尔逊、韦伯、古德诺所说的政治还包括大众政治,也就是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政治。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家登哈特认为,威尔逊所强调的政治与行政分离只是限于高层或国家层面,这似乎为社会事务层面的民主制追求留下了遗产。的确,威尔逊在说完政治不是行政之后,紧接着就说:“这是高层权力的区别界限。”[1]4但威尔逊在论说人民在公共行政中的角色时,只限定于舆论评判上,而且他指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全部行政机关与人民、人民领袖以及其普通工作人员的共同政治生活隔离的时候,官僚制组织才能生存,官僚制组织的动机、目标、政策和标准必然是官僚性的。”[1]21这如同韦伯所说的官僚制行政会让大众走开是一致的。
民主制公共行政的核心理念:公共行政是政治的。这里所说的政治更主要是指大众参与共同治理的政治,而非政党政治。这种政治概念,是吉登斯划分解放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两种政治形态中的后者。因为前者是一部分人解放另一部分人,或为部分人解放、管理大多数人的政治,它主要是由政党代表的议会制民主的形式民主;而生活政治即是公民直接参与、共同治理的自治,而不是“他治”。新公共行政的奠基人沃尔多关于公共行政是关于历史的、文化的、伦理的人类实践之“试图获得合作理性”的智慧之论断,鼓舞了民主制公共行政探寻者们从古希腊雅典的公民民主,古罗马的共和制民主,托克维尔对美国新英格兰乡镇民主自治的评价中挖掘理论资源。尽管奥斯特罗姆重视了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官僚批判理论,也提出公共企业家精神作为代表性公民的假设,但他在统合托克维尔的社区自治的民主理论、杜威的社群共同体的“道德民主”而非“利益民主”的理论中,排斥市场主义和政府独揽公共事物之“大政府”,强调的是“联合生产公共产品”之取向。民主制公共行政主要是在重建规范政治学并以其为途径,“公共”的结构是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共同参与、共治、共享和责任分担,即民有、民治、民享。
新公共管理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这是一个焦点问题。新公共管理的赞赏者、辩护和旨在学科化的学者,声称它是非政治的。但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是:新公共管理的主张都是淡化法律和程序,结果是强化政党对公共行政的控制。
三、民主制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融合的可能性
民主制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都是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中所出现的现象,根源于西方民主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生活形态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对立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可以断定,在学术流派、学科化的取向中,可能是永久性的,但二者可融合的时空不仅仅是学术流派的,在实务领域融合的可能性会更强势。
来自于民主制公共行政以外的学者往往对其评价是规范有余,应用不足或实证性不强。对来自新公共管理之外的批判更为苛刻,英国学者胡德对新自由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改革予以“新公共管理”的命名,本身就有贬意。传统公共行政学派是高级公务员和有成就的学者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对新公共管理表现出“只闻其名,不知其意”之轻视。“‘新公共管理’的标签只能是一种大杂烩的描述而不能成为自成系统的理论,这一提法没有前提、立论、思辨、论证的过程,有时甚至前后矛盾。”[1]157这一批评符合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出发地,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它本身的不足之处。民主制公共行政的学者们,虽然没有共同认可的民主制公共行政的学科体系,但在基于人类实践的“合作理性”的规范性假设上是一致的,这也是批判管理主义、新泰勒主义的出发地。但是新公共管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所强调的“3Es”精神也是民主制所应借鉴的。可以断定,民主制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之融合的可能性具有较强的时空域。
1.关于学术流派、学科的问题
美国百余年公共行政学史不缺乏理论,但并没有一致认可的理论,这与美国的总体学术生态相一致。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公共行政一直在学科分化和杂化中发展。传统公共行政学派、公共政策学派、公共管理(管理学途径的公共管理),以不同的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学术取向而形成差别,就公共政策学派来说,又区分为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个派别,后者关于执行的网络化模型又与管理学派有相近似性。美国学者斯蒂尔曼教授分析“二战”后,公共行政理论每隔20年就出现新的理论焦点和学术流派。20世纪的后十年出现了六大派别:重塑学派、社区学派、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重构学派(黑堡学派)、阐释学派、方法论建构学派、新官僚分析学派。[9]36-38这些学派的志趣都在试图创新。另然这些学术流派往往被称之为不合主流、不科学的学术玩家。[9]40但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家的工具,在公共行政实践需要上会有相融性的组合。
2.关于官僚制的问题
民主制公共行政并没有把理性官僚制作为其主要的敌手,它是把代议民主制或环式民主制条件下,作为政府工具的官僚制作为敌手。试图以社会生活的“共同网络”为基础,以代表性公民的假设重塑官僚这一特定的职业角色,使其置身于民主治理公共事务的场域之中。这一努力主要集中在解构作为政府工具的官僚制,而重构作为公民工具和公民“掌舵”的新的组织形态,或者说,是把政府工具的或统治所需要的官僚制,重塑为受“公民性”伦理规范约束的“代表性官僚制”。古德塞尔和弗雷德里克森为“官僚说好话”之辩护正是这种努力的典范。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敌视以至辱骂,可以与巴尔扎克的《公务员》文学作品中的视官僚为“侏儒”“白痞”相媲美。但是新公共管理在葬送官僚制的喧嚣中,摒弃它了吗?不仅没丢弃,反而在对其文官制的价值中立性之丧失(政党政治的)中,走向了政党化的工具理性的官僚制,实质上是“经济人”和“经理人”的官僚制。这是新公共管理被诟病的症候之一。但是,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对结果负责的责任机制也有其价值,这也是民主制公共行政理论所缺环的。
3.关于政治与价值的问题
民主制公共行政秉承了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观点,视政府(广义的)为工具,而基于社会“生活世界”的价值与政治(生活的政治)的一致性,重构民主制行政理论。但是,它并不是消灭代议民主制的国家,而是使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分界及功能性的设置保持分属,代议民主制或环式民主是需要的,但其功能要设定在一定的限度内,官僚这一特殊的职业角色是需要的,但要效忠于公民,而不是政治党派。新公共管理的要害在于:以“与政治无关的”障眼法,推行了政党的意识形态。传统的公共行政在政治(政党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中,对选举获胜的政党具有重要的牵制作用。这一功能之丧失,服务、服从于选举政治和官员任命的亲党派性的“分肥制”之死灰复燃,必然受到民主理论的批判。因此,新公共管理被学科化也要走出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也必须在民主之根基上构建学科体系。
政治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公共行政难以处理的问题。从政党政治来说,与价值的一致性没有什么问题,选举政治受约于人民的价值期待,但反政党政治的视角又批评地指认,人民是受政党意识形态所形塑或建构的。所以视公共行政为科学,公共行政的官僚机构和官僚就应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这在西方竞争性选举政治的生态中,公务员的价值中立是有意义的,适应其政治生态更具有现实性。理解价值可以从预设性或形而上的和工具的两个层次,从基于人类的实践理性“合作”的应然之“好”出发,必定是在“人作为人”或“人成为人”的内在性的预设开始,它是内在价值;而以“客体满足主体之需要”之理解的价值,只能是在结果的预测中或实质的结果评价中获得,它是工具性的价值。民主制公共行政从基于人类实践理性之“合作”的内在价值出发,但不可忽视工具性的价值;相反,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不能过分强调工具价值,而无视内在价值。
收稿日期:2010-06-29
标签:新公共管理论文; 公共行政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行政管理学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