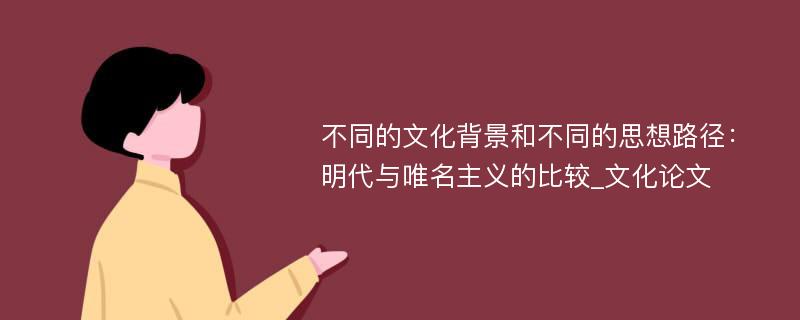
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不同的思想路数——因明与名辩学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明论文,路数论文,文化背景论文,思想论文,名辩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059(2007)02-0042-05
一
作为“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的创始人”的张东荪曾经指出,不同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思想模式,而之所以造成不同特质的思想模式,全在于其产生的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范畴等所致。将这种方法用于逻辑学的研究,张东荪认为“逻辑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1]383,从而得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存在有四种逻辑系统,即: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其特性在于整理语言,是因社会对于辩论术不仅注重于修辞,而且还须注重于条理所“逼迫”出来的;数理逻辑,其特性在于表明数理思想,是表示人类文化中的数理思想的一方面;形而上学的逻辑,其特性在于满足人们的神秘经验,是由于人类文化中宗教的神秘经验所“逼迫”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逻辑,是专用以说明社会政治现象,是为了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的实际需要所“逼迫”出来的。[1]388-397总之,在张东荪看来,不同的逻辑系统是由不同的社会文化需要所造就的。
尽管张东荪并没有提出古印度因明是什么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凭借这种思路,探讨古印度因明和中国古代的名辩学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得以产生,它们的思想路数是什么,其相同、相似、相异的地方是什么。
应该说,任何思维工具系统的产生,都是人类思维活动发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作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中两支的古印度因明与中国古代名辩学,从它们的发生、发展过程看,论辩的需要,是它们得以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因。
因明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其时,诸教派兴起,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各教派在论战中竭力张扬自己的观点,完善自己的体系,相互之间就各种哲学问题、知识论问题进行论辩。这样的论辩不但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同时也促使各派开始研究论辩本身的方法和技巧问题。在对关于知识论、思维工具系统和辩论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提炼出充满“立破正邪”、“咸称轨式”推理论证规则的逻辑体系。《政事论》的最后一章,《正确的论辩体系》就论及议题、准备、类推、举例、取舍选择等32种论辩方法;《正理经》十六句义中则有“论议”(按逻辑规则反复推究两种对立观点何者正确)、诡论议(以混淆是非为论辩出发点)、“曲解”、“倒难”(含有错误的貌似对方的而实非对方的论式)、“堕负”(论辩中沦为失败的种种情形)等内容。
从这些论著的内容来看,“古印度的哲学家们十分重视论辩的方式方法,并且已经从研究论辩的程式进而研究思维的形式和推论的规则”[2]了,其目的就是为了论辩中如何寻求“正理”。具有明显的逻辑意识。
什么是“正理”?“正理是依据知觉和圣言而进行的推理”[3]3,是对某种理论进行理论解释和缜密论证的学说,其“论证式……无非是论证圣言的过程而已”[3]3。其所形成的学说,必定是要寻找一种正确论辩的准则,以期明确论辩的“真似”。因此它的“目的论和神学性质”,“不仅从外部规定了正理学,而且给予正理学派逻辑学本身以根本不同于西方逻辑学的某些性质”。[3]2
而中国古代的名辩学产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的时代。兴盛了数百年的周朝典章制度,由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关系的诞生,已无法挽回,出现了“名实是非相淆”、“名实相怨”、刑罚不清的混乱局面。如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赵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风闻此事后,一生汲汲,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痛心疾首: “晋其亡乎!失其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揰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后人对此时的评价是:“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实是非之未辩,公私爱恶之未明。其极至于君子小人之分犹未定也……名实是非当日以淆,而公私爱恶未知所定,何望夫风俗之正而刑法之清哉?”(《陈亮集·策·廷对》)
当此时,如何平定天下,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有效管理与控制,始终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的需要,决定了这个时代也是一个需要论辩、产生论辩的时代。诸子们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的需要,均“思以其道易天下”,都在通过自己的谈说论辩来播其声(主张)、扬其道(理想)、释其理(理由)。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产生在这个时代,是具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的。
但是,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不能不要求论辩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素质、知识素质、艺术素质。这种知识素质和艺术素质,就是指他们都在探讨论辩的准则、方法与技巧,从而在论辩中总结出正确的论辩原则和方法,使人们的正常辩说能有一个规范化的思维工具,从而促进了思维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但名辩学始终具有一种极强的政治伦理性,有着鲜明的求真、求治的时代烙印和时代精神,这体现在它的鲜明的论辩目的、论辩原则、论辩方法与技巧、论辩的各种逻辑要求和伦理道德要求上。“求真”的逻辑意识较“求治”、“求善”的伦理意识淡薄。如作为论辩之风开创者的邓析,其关于“辩”的目的很明确:“谈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意通志,非务相乖。”(《邓析子·无厚》)从求真的角度讲,“殊类”、“异端”是一事物按之类同、类异,依不同的性质各属不同的类,从而以实定名,形成不同的名,以保持思维对事物事实的类同、类异。但从求治的角度讲,如果在思维的过程中,保持了名与实的同一性规则,就可以“治世,位不可越,职不可乱,百官有司,各务其形,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 (同上)。这样,正确的定名、使用名就有了极强的政治伦理目的,从而将如何使用“名”的思维认识目的和政治伦理目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论辩的求真精神与求治精神熔铸在一起了。又如孔子的“正名”学说,以“正名以正政”的“名分大义”,规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被辜鸿铭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中认为是“中国人的精神”。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上》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而公孙龙的“正名”学说,以“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求真”精神和“正名实而化天下”的求治精神,延续了孔子的“正名以正政”。至于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集大成的《墨经》,也以其“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墨经·小取》)的六大论辩目的,使论辩在求真的过程中也无时无刻地打上了政治伦理性极强的时代烙印。而主张“君子必辩”的荀子,在其批驳“三惑”时,也是将论辩本身的逻辑问题同政治伦理问题纠缠在一起,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礼者,人道之极”(《荀子·礼论》),将“礼”作为一个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乱也。”(《荀子·天论》)
胡适曾经说过:“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4]从中国古代名辩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古代的论辩,须臾离不开政治伦理这个大课题,诸子们对论辩原则、方法的探讨、研究,仍然是通过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论证时事、人事、世事,即西汉司马谈所说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均“务为治”。(《论六家要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论辩原则、方法,始终是“求真”、“求治”二而一、一而二的。强调名辩学的认识目的和政治伦理目的,是中国古代名辩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首要方面,有其实实在在的时代精神。
总之,现实的论辩需要,促进了因明和名辩学的产生与发展,但因明的产生与发展有浓重的宗教意味,其论辩内容多围绕宗教理论展开,如世界的有常无常、世界的有限无限等等,哲学味浓;其论辩目的是寻求自家宗教教义的正确,是求“真”;名辩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政治的需要,论辩内容是如何有效地管理社会,论辩目的是在求真的过程中寻求如何求治、求善,并以其调整社会秩序。作为当时人们逻辑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们均成为日后思维工具体系的前奏。
二
尽管因明和名辩学产生的过程相同而目的不同,但希冀创立一种思维工具系统的要求却是一样的。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其相异的地方是这种工具系统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相同、相异点在思维方法上均有所体现。
因明注重推理研究。论辩主要是围绕各派宗教教义而展开,是为了论证自己宗教教义的正确性,所以他们的论辩,不能不一开始就围绕宗教命题或哲学命题而展开,做有效的逻辑推理论证。因此因明对论题的分析详细,如论题“宗”的结构有宗依、宗体的区别;宗依又有前陈(主词)、后陈(宾词)的区别;前陈和后陈又有种种不同的关系;论辩形式的规则,如宗必须由前陈和后陈组成,宗依必须是立论者所主张而论敌所反对(违他顺自)等。这就使得因明一开始就注重论辩的方式、方法、原则,以证明本派本宗的论题,并破斥对方的论题。虽然这也使得因明“忽视了对概念的分析”[5]85,但这样做的结果是:
一是论证本宗本派思想观点的需要,能够使它专注于对命题理论的探讨,如因明对宗(命题)的分类、结构的分析却比较全面,在语言形式上分命题为“表诠”、“遮诠”:“遮谓遣其所非,表谓显其所是。”(《宗镜录》卷三十四)表诠相当于肯定命题,遮诠相当于否定命题[5]88。从实质内容上又分命题为“有体”、“无体”,“有体”为“共许极成”,是论辩双方共同认可的;“无体”又分为双方都不认可的“两具无体”和只有一方不认可的“随一无体”。如因明对宗、因的分类。[6]
二是在这个基础上,为了能够据“因”而立“宗”,充分展现本宗本派思想观点何以成立,因明能够展开对推理论式的探讨,并使之成为因明的主要内容。从《正理经》的五支论式到经陈那改革为三支论式,“格式化”①始终是它的论式的特点。如五支式与三支式的格式。
这种论式的演变,增加了逻辑论证的有效性。如早期正理学派五支论式:宗:此山有火;因:因有烟故;喻:如灶,于灶见是有烟与有火;合:此山如是(有烟);结:故此山有火。这是从特殊推至特殊。而陈那改革的新因明的三支论式为:宗:此山有火;因:因有烟故;喻:(同喻)有烟处必有火,如灶,(异喻)无火处就无烟,如湖。宗:声是无常;因:所作性故;喻:(同喻)若是所作,见彼无常。(喻体)如瓶。(喻依),(异喻)若是其常,见非所作。(喻体)如虚空。(喻依)
同喻和异喻的喻体揭示了一种因果关系,并且同喻和异喻的喻体之间,还有一种类似穆勒求因果关系五法中的“求异法”的痕迹。②于是,尽管仍然是从特殊到特殊,但由于有了“有因有果”,“无因无果”的正反论证,展现了原因与结果的“不变伴随”关系,就使得结论的有效性大大增加了。
自20世纪初印度因明研究的重新兴起,曾有学者将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形式比附于因明的三支论、五支论式。这是求同意义上的重构。如清代孙诒让就已经提出过三大逻辑体系之间有相通之处,但他并没有展开具体的研究,明确进行研究的是梁启超、章太炎等。章太炎即说:“辩说之道,先见其旨(先提出论题),次明其柢(列出论据),取譬相成(取譬设喻),物故可形(加强其立论)。因明所谓宗、因、喻也。印度之辩(指因明的三支论式):初宗,次因,次喻;大秦之辩(指逻辑的三段论式):初喻体,次因,次宗。其为三支比量一矣。《墨经》以因为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大秦与墨子者,其量皆先喻体,后宗。先喻体者,无所容喻依,斯其短于因明立量者,常则也。”[7]通过这种比较研究,章太炎还认为因明三支论式是推理的理想论式。
但是,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的产生,是“疾形名之散乱”,而欲“正名以正政”、 “正名实以化天下”。所以名辩学一开始就由“名”而辩,注重概念分析,并以此开始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道路。先秦逻辑思想史中成篇的逻辑思想论著多是探讨“名”(概念)的问题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在思维方法上名辩学不同于因明的第一个方面。
名辩学不同于因明的第二个方面是,由注重概念分析而至推理方法的分析,使名辩学的推论方法主要是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上的援类而推的思维方法,即“推类”。它是按照两种不同事物、现象在“类”事理上具有某种同一性或相似性,以“假物取譬”、引喻察类的过程,通过论说者的由“所然”进到“未然”的认知形式,描述、说明、论证或反驳了一个思想的是非曲直。它寻求的是一种可以进行说明的“范例”。这种“推类”方法的产生,有一个从“类”概念到“法式”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古代整体思维与意象思维的表现。整体思维的结果是将“类”的“族类”之名延伸、扩展至“种类”之名;而意象思维的结果则是将“类”的概念发展成为“类”的法式。这种思维法式有“类”事物和“类”事理的相似或同一的依据,其“类”法式的取法标准分别有伦理的标准和逻辑的标准,其“类”法式有通过比照事例而分类,进而援类而推的思维进程,从而可以在“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的论辩中,论证政治伦理的是非。因此,虽然中国古代的“推类”思维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思维的必然性。[8]但由于“推类”的思维方法所寻求的可以对论点进行说明的“范例”过程,它所关注的只在于两个思维对象之间有“举相似”的同一性,从而断定对于它们的思维取舍也相同。并以此表明现世应该怎样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伦理精神,从而以这种思维方法最好地表达了它那个时代的理想诉求,熔铸了它那个时代的求真的态度与精神,以及求善、求治的振世精神和人文关怀。但这种思维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就是它对于论证方法“格式化”的要求并不迫切,因此也就难以走向形式化的道路。
从因明与名辩学的推理方法上看,在保证论证有效性上,两者都是论辩工具;其从特殊到特殊的共相都可以使表达思想、进行论证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在推理论证过程中,均以“悟他”为用,如因明“为欲简持能立能破义中真实故造斯论”,“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因明正理门论》卷首一偈),而名辩学的“推类”也强调“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因明不单靠论式的必然性从前提推出结论,还要靠次序井然的心理过程,而名辩学的“推类”在如何选择“譬”的事物时,其为什么“相似”也有一定的心理尺度,故而两者均有一定的心理因素影响。这是它们在思维工具系统内的共性。
但二者又是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里产生的,因此又各具特点,表现出它们的差异。因明是对已知事物的事理之是非的说明,其结论是“事实如此”的实然命题;不具有道义性;且“格式化”的特征,使之论证过程清晰有效,更接近于西方传统逻辑;因明重视对无效证明的研究,早期因明学曾经列出了数百种过失。至商羯罗主时,还列有三十三过(似宗九、似因十四、似喻十。[9]但由于因明作为工具系统,本应具有普遍意义,却又局限在佛教宗派的圈子内,没有发展成为大众的思维工具,因此它也不如西方传统逻辑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普遍化意义。而中国古代的推类方法是对已知事物的事理之正误的说明,其结论是“应该如此”的价值命题,具有道义性;其思维方法与语言特点,也难以形式化,其论证过程有心理认定的因素,具有或然性、模糊性;对于推理谬误的系统分析,名辩学则少,仅《墨经》等列出几条(“流而失本”、“类不可必推”等)。但由于这种思维方法适应了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法和意象思维方法,因此至今这种“譬”的思维方法仍然鲜活。这也就是因明不能在中国发展的原因所在。目的不同:因明是求自家宗教教义的正确,主要是求“真”的工具系统;名辩学则在求“真”的逻辑要求之外,还兼有求治、求善的伦理要求。论证方法不同:中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推类理论,因明的形式化方法也不适合中国传统的语言特点和意象性的论辩方法。③
之所以会有这些差异,是因为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并因此而有了不同的思想模式。古印度因明其特性在于整理语言,是因社会对于辩论术不仅注重于修辞,而且还须注重于条理所“逼迫”出来的;而中国古代名辩学是专用以说明社会政治现象,是为了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的实际需要所“逼迫”出来的。因此,作为思维工具系统,没有普遍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不同的逻辑系统是由不同的社会文化需要所造就的。
但是,任何文化都是各个民族不同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们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保留下来,显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是具有价值的和实用的。又由于“每个文化集团都有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10]。因此,在思维科学的比较研究中,美国现代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所提出的“历史特性主义”(historic particularism),可以作为站在“文化相对主义”基点上观察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原则。即因明与名辩学都是根据自身的需要与环境的影响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它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价值与功能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从文化具有不同价值的本身来讲,“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因明与名辩学之间的差异,只能用“不同”来解释,不能按照一种逻辑的标准划分为“简单”或“复杂”。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研究中,根据所研究对象的标准来对其做出评判,有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探讨古印度因明与中国古代名辩学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从而充分认识它们内在的、独有的特质,是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自以其特有的方式,适应着不同的历史需要,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历史作用,从而展现了具有不同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通过这种研究,在了解和分析不同文化群体的历史生活状态中,体会不同思维工具系统的相通性和差异性是辩证的统一。即相通性不等于同质性,只是表明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同质人类在认识事物时相同的或类似的反应。这是人类不同文化能够沟通的重要条件之一。
收稿日期:2006-12-25
注释:
①之所以不用“形式化”的概念,是因为因明的论式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化。
②如果是严格的求异法论证,应该是:同喻:有烟处必有火,譬如厨房;异喻:无烟处就无火,譬如湖。这样的推导才能真正使因果关系的论证清晰而有效,归纳确证的强度才高,逻辑性才强。
③关于因明不能在中国传播的其他原因,还可参见周山《因明与名辩》,载《因明新探》,第 109~120页;孙中原《印度逻辑与中国、希腊逻辑的比较研究》,载《因明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第53~69页。
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墨经论文; 古印度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