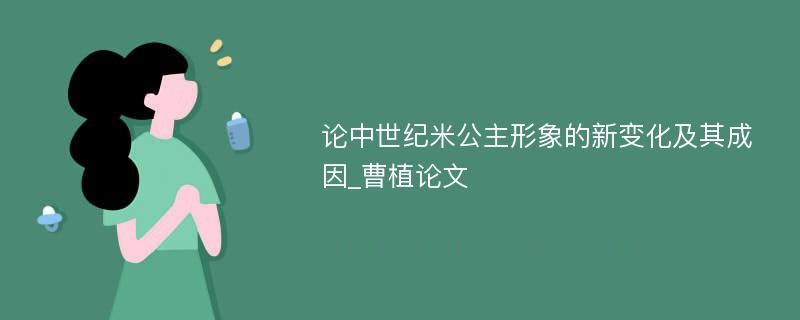
论宓妃形象在中古时期的新变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成因论文,时期论文,形象论文,论宓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3)02-055-060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批帝女形象,即天帝、传说中的古帝的女儿,如宓妃、女娃、湘妃、瑶姬(巫山神女)、女桑(织女)、嫦娥等,其中宓妃作为洛水女神,因曹植作《洛神赋》、顾恺之作《洛神赋图》而备受世人关注。
近年来,关于宓妃的研究,既有探讨其文学史意义的论作,如吴冠文《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复旦学报》2011年第1期);更多的是对曹植《洛神赋》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洛神赋》创作背景“感甄说”的辨析:如刘跃进《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范子烨《惊鸿瞥过游龙去,虚恼陈王一事无——“感甄故事”与“感甄说”证伪》(《文艺研究》2012年第3期)等。这些探讨确实深化了宓妃(洛神)研究。然而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宓妃形象的丰富、发展主要是在中古时期,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是曹植的《洛神赋》,此外,还有哪些作品中描写到宓妃,宓妃形象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这其中既有先秦两汉以来宓妃形象塑造的传统,又与当时时代风气、社会现实状况密不可分。在此,立足于文学文本,从宓妃形象继承与发展的视角,试图绎出中古时期宓妃形象的新特点,并探讨其发生新变的原因。
《楚辞》开创了以文学形式描写宓妃的传统。然而,屈原《天问》、《离骚》所出现的宓妃形象,却有着不同的身份与特点。
(一)配偶神。在文学史上,宓妃形象产生之初只是一位个性苍白而没有独立意志的配偶神。其源于屈原《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东汉王逸注曰:
帝,天帝也。夷羿,诸侯,弑夏侯相者也,革,更也。孽,忧也。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猎,变更夏道,为万民忧患。胡,何也。洛嫔,水神,谓宓妃也。传曰: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故其宜也。羿何罪欤?深,一作保。羿又梦与洛水神宓妃交接也。[1]99
屈原所问,意是“天帝降下夷羿,祸害夏民。为何又射河伯,娶洛水女神为妻?”显然,在屈原笔下,宓妃本为河伯之妻,却被羿所霸占。关于羿射何伯而霸占其妻宓妃的本事,王逸注释叙述得非常清楚,故事也相对完整。然而,古代羿有二人,一是尧时的后羿,见《淮南子·本经》;一是夏代有穷氏国君,见《尚书·五子之歌》。宋代洪兴祖认为是前者,其《楚辞补注》曰:“此言射河伯、妻洛嫔者,何人乎?乃尧时羿,非有穷羿也。”[1]99并引《淮南子》为证。然此说颇受学人责难,朱熹《楚辞集注》就赞成王逸所注,认为杀夏相的是有穷氏国君。今之学者多取王逸之说,并不明言羿所处时代。然而王逸注“羿又梦与洛水神宓妃交接”,似乎并未明确羿娶宓妃为妻。后人理解也见仁见智,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看法则遵从王逸的解释:“以射为实,以妻为梦。”[2]卷二十五一种是用历史化的眼光批评这则神话,如朱熹斥之“此妄言也”,而同时之史绳祖批评更为激烈:“若以怪证怪,则羿妻乃宓妃岂常娥耶?学者不观正史及经注字义,而惟怪诞之说是信。是盖吾夫子所云,未见好德如好色也,可不悲夫,故为之辨。”[3]卷三与之相类的,还有清代屈复亦云:“问天帝,既降羿,除后相之荒淫。革夏民之忧矣。而又射河伯妻洛嫔,荒淫尤甚何也。”[4]卷三据笔者看,理解这则神话,应该以屈原原意为准,屈原所问,恰恰说明在屈原时代,羿射河伯而娶其妻,流传是由来已久。而王逸所注,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羿梦中与宓妃交接,或是交代羿娶宓妃的原因,惟因见宓妃而难以忘怀,至于梦中交接,才使羿娶宓妃。二是在神女系列的文学中有不少都是感梦而衍生出故事,如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以及后来曹植的《洛神赋》等。
(二)信美而无礼的独立女神。如果说,在《天问》中,宓妃只是一个神话的构成元素,尚缺少鲜明个性的话,那么在《离骚》中诗人已经赋予宓妃鲜明的个性。前者以配偶神的身份出现,后者则是诗人所追求的神女身份出现。其诗曰:“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盤。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1]31关于宓妃的身份,王逸注曰“神女”,洪兴祖补注曰:宓妃,伏牺氏女,溺洛水而死,遂为河神。[1]31
此则注释实际上是抄自唐代司马贞《史记索引》所录的汉人如淳的说法,如淳注《史记·司马相如传》中《上林赋》曰:“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这两则注释交待了宓妃故事的缘起。而屈原诗中所谓“吾令蹇修以为理”,洪兴祖又补注曰:“宓妃伏牺氏之女,故使其臣以为理也。”[1]31这也将诗中人物的逻辑关系也梳理得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在屈原此诗中,宓妃乖戾、骄傲,美而无礼,淫乐无度,具有比较具体的性格个性。
至于宓妃形象之象征意义,历来有两种看法:一是以王逸为代表。其《离骚经序》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悯其志焉。”[1]3王逸将神女宓妃喻为隐士,认为屈原为求得隐士清洁若宓妃者,解佩带之玉以结言语,使古贤蹇修而为媒理,然宓妃用志高远,保守美德,骄傲侮慢,日自娱乐以游戏,无事君之意。总言之宓妃虽有美德却骄傲无礼,不可与共事君,来去相弃,而更求贤也。李善注《文选》中也沿用这一看法[5]卷三十二,1500。另一种是以何焯为代表,将宓妃喻为贵臣,“求女如宓妃者,而不可得,相与骄傲滛游而已。上下相习,大小成风,乱国之朝,其势固然。……此宓妃贵女以喻贵臣,佚女以喻遗佚之贤,少康以喻嗣君,二姚以喻嗣君左右之臣也。”[6]卷四十八,943这两种解释都能够解释得通,宓妃的形象确实可被视作隐士,也可看作是贵臣。总之,屈原笔下的宓妃形象,一种是仅作为配偶神的女神,另一种是作为诗人所追求的具有象征内涵的女神形象。这可视作是宓妃形象的初始内涵,在后世文人笔下,宓妃形象中的这些内涵得以衍生、发展。
两汉文学特别是辞赋继承《离骚》的手法,以刘向等人之笔触,逐渐使宓妃形象描绘得丰满而逼真,并且将《离骚》所表达的对宓妃行为的不满,转变为带有道德评判意味的寄托,因此也逐步产生了比较浓的世俗化倾向。两汉文学对宓妃形象的塑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理想的女神形象。这一形象又有两层不同的内涵:第一,沿袭《离骚》而来,宓妃发展为诗人理想的女神。《楚辞·远游》:“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王逸注曰:“屈原得祝融止己,即时还车,将即中土,乃使仁贤若鸾凤之人,因迎贞女,如洛水之神,使达己于圣君。”[1]172《离骚》中的宓妃美丽傲慢、淫乐无度,所以诗人违弃而改求。而这里的宓妃则是诗人理想的女神,亲密的伴侣,是一个已经完全富有诗意的女神形象。然而这一形象究竟出现于何时,则牵涉到《远游》是否为屈原创作的问题。学界多持《远游》非屈原作的观点,如清代学者胡濬源、吴汝纶及现代郭沫若、陆侃如等。近年,吴冠文又补充考证了《远游》非屈原作,认为当在东方朔之前已经以屈原的名义流传于世。这一论断大体能够成立,因此我们可以说,赋予宓妃形象新的内涵是在西汉初期。第二,沿袭《天问》而来,发展成为贤德的皇妃。刘向《九叹·忧苦》:“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诚愿藏而不可迁。逐下袟于后堂兮,迎宓妃于伊洛。”王逸注曰:“言己愿令君推逐妾御出之,勿令乱政,迎宓妃贤女子伊洛之水,以配于君,则化行也。”[1]302辞中的“宓妃”是诗人理想中的足以匹配君王美德的贤淑王妃。其身份虽然还是配偶神,其内涵则已完全不同。显然刘向又接受了《远游》的影响。此外,杨雄《羽猎赋》:“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饷屈原与彭胥。”[7]106《六臣注文选》曰:“屈原彭蠡、伍子胥皆贤臣。沉于水,故饷之。宓妃,邪神,故鞭之也。”[8]卷八夸饰宓妃邪恶的一面,或当别有寄托。其意义仅是将《离骚》所表达的情绪推向极致而已。
(二)狐媚的神女形象。张衡所创作宓妃形象特别具有丰满的美学意义。其《思玄赋》:“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妙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袿徽。离朱唇而微笑兮,顏的砾以遗光。献环琨与璵縭兮,申厥好以玄黄。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双材悲于不纳兮,并咏诗而清歌。”[9]226宓妃与玉女妖娆魅惑,娥眉媚眼,纤腰曼妙,衣裾轻扬,朱唇开而笑溢,眉眼动其耀光。于是男子难以自持,献上佩玉,申述爱慕之情,然而女神情志逸荡,弃之不顾。其描写手法与形象内涵,显然受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深刻影响。在这里,女神已作为情欲的化身,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魅力。而男性只有在砥砺自我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才能经受住女性美色的诱惑,“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他们主要依靠的是自身以礼自持,从而彰显自身的道德素养。颇具魅惑力的宓妃成为检验作者道德修养的女性形象。
此外,杨雄《甘泉赋》:“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李善曰:“言既臻西极,故想西王母而上寿,乃悟好色之败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微谏也。”[7]62《汉书·杨雄传》亦载:“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齐肃之事。”[10]2623汉成帝时宠幸后宫赵昭仪,作者以屏却神女宓妃微谏之,是神女狐媚形象的自然延伸。
(三)现实的美女形象。在汉赋中,宓妃还用来作为现实中美女的代称。一是指代如花似玉的美女。司马相如《上林赋》:“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娴都,靓妆刻饰,便嬛绰约,柔桡嬛嬛,妩媚姌嫋,曳独茧之褕袘,眇阎易以戌削,媥姺微屑,与世殊服,芬香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礫;长眉连娟,微睇緜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11]76-77从中可以见出,司马相如采用铺陈的手法,描写上林苑中美女的气质、妆容、服饰、笑容、香气、神态的艳姿丰貌,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言:“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12]卷二,147繁富的内容、艳丽的语言,让这些上林苑的美女可谓堪与宓妃、青琴媲美。其实这一神女形象实际上也就是人间美女形象。二是指代清声曼妙的舞女。杨雄《太玄赋》:“听素女之清声兮,观宓妃之妙曲。”[7]142王褒《九怀·危俊》:“闻素女兮微歌,听王后兮吹竽。”王逸注:“宓妃作乐,百虫至也。”[1]273所描述的都是善于清歌曼舞的女子。
除文人辞赋外,宓妃形象还出现在《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中,“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洛浦即洛水之岸,故代指洛水之神宓妃,此指男子艳遇的美人。同袍,指代“同衾共枕”的夫君。思妇悬想丈夫未归,乃是另有新欢。而《淮南子》中的宓妃,虽也是一位配偶神,然所嫁之对象则是“真人”。其《俶真训》曰:“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13]61而其地位似乎由嫡妻下降为妾了。
东汉张衡笔下的宓妃形象与西汉前期楚辞《远游》、《九叹》中的宓妃形象有着明显不同,她是理性思维之下,道德自律的参照。而司马相如《上林赋》、杨雄《太玄赋》中的宓妃则是现实中色艺出众的美女。宓妃形象的不断世俗化是汉代文学作品中宓妃形象的基本特点。
中古时期描写宓妃形象,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当首推曹植的《洛神赋》。《洛神赋》在宓妃形象的塑造上,既汲取了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影响,又是对司马相如、张衡所创造的宓妃形象的发展,因此所塑造的宓妃形象立体感特别强,审美意蕴也特别丰富,从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也因为其浓郁的世俗化,引起后人对曹植所描写的宓妃形象本事的种种揣测。
(一)其宓妃之美集人间美女之大成。作者从外貌、举止、心灵、个性等方面多层次地刻画了洛神的形象,创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描写外貌,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若“轻云之蔽月”、“流风之回雪”的形态之美,“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皎若太阳”,“灼若芙蕖”的神采之美,“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的体形肤质之美,还有“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的气质仪态之美,等等。描写举止,有攘腕采芝的天真,将飞未翔的灵动,戏流拾翠的活泼,扬衣翳袖的妩媚,含辞未吐的娇羞,凌波微步的轻盈,若往若还的的风情等等。而且洛神形象仙性与人性结合。一方面,洛神女具有“惊鸿游龙”的外在形态,“体迅飞凫”的迅捷举止,“凌波微步”的轻盈步履,众神簇拥的尊贵地位,“潜子太阴”的神秘住所,有浓烈的仙人的色彩;另一方面,洛神艳逸的容貌,闲雅的气质,天真活泼的性格,习礼明诗的淑美,特别是多愁善感的心灵世界,一往情深的爱情追求,徘徊不定的惆怅痛苦,使具有人间美女的普遍性特征。神性与人性的有机交融,曹植创造出一位个性色彩十分浓郁的洛神女形象。
(二)其人神之恋尽曲折跌宕之能事。形象的动人还缘于情感的细腻刻画。作者细腻地刻画了“我”与“神女”的情感在刹那之间细微的变化。从“我”的角度说,悦其淑美而心旌摇荡,托秋波、解玉佩以传情,又惧其欺我而以礼克制自己;然而无法抵御洛神真挚情感的感染,动人容貌的诱惑,优美举止的迷恋,终至于“令我忘餐”——陷入情感的泥淖而难以自持;最后,洛神鸣玉鸾偕逝,并不知其所舍,自己怅然若失,神魂颠倒。动情——约情——悲悼之情,是“我”情感三次变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从神女的角度说,举玉佩,指潜渊而为期,表明洛神已动之以情;在对方以礼自持,情感冷漠之时,徙倚彷徨,“若将飞而未翔”,联想到匏瓜无匹、牵牛独处,又“若往若还,转眄流精”,欲离而不忍;但是人神道殊,在陈言袒情之后,欲留不能,只能在悲悼中离去。动情——伤情——悲悼之情,是神女情感发展的基本线索,均以动情为始,以悼情为终。在细腻表现了双方情感波澜的同时,揭示了一幕人神异途的爱情悲剧。
无论是洛神形象的描述,还是人神恋曲的展开,都使洛神的形象真切感人,染有浓郁的世俗化倾向,这也引起了后人对《洛神赋》本事的种种揣测,成为了文学史上一桩难以缕析的公案。尤刻本李善注《文选》,在题目下注引《记》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未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5]卷十九,896。
这段文字是被后人视为“感甄说”的源头。李善所引之《记》已不详所指,然必然产生于李善注《文选》之前,而李善注《文选》在武则天显庆年间(656-661)。据此,曹植与甄妃的传说流传于中唐说,或认为产生于唐代传奇作家之手,都还值得商榷。东晋顾恺之据曹植之作所创作的《洛神赋》图。据周汛、高春明《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考证:顾恺之《洛神赋图》,洛神梳灵蛇髻。据民间传说,灵蛇髻为甄后发明,故顾恺之所画洛神,即据甄后为原型。南齐袁彖《游仙诗》:“羽客宴瑶宫,旌盖乍舒设。王子洛浦来,湘娥洞庭发。”亦描写王子携洛神赴瑶池宴会,此处之“王子”显然是指曹植。这说明“感甄说”确实产生很早。而且大多文人宁肯信其真实性。后世的画家、诗人、小说家的创作中,多以此为题材进行二度创作,如李白、李商隐、裴铡、蒲松龄、曹雪芹等文学作品都可以找到“感甄说”的影子。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如胡克家、刘克庄、张溥、丁晏、潘德舆、朱乾等。其中驳斥最力,又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何焯对《文选》李善注《记》中内容进行的批驳:
注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按魏志。(甄)后三岁失父。后袁绍纳为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安有子建尝求为妻之事。小说家不过因赋中愿诚素之先达二句而附会之。注又曰。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按。示枕赉枕,里老之所不为。况帝又方猜忌诸弟。留宴从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赋。其为不恭。[6]卷四十五,883-884
何焯依据史实《魏志》分析甄后的身世经历,否定曹植曾求之为妻。又从事情内在的逻辑关系入手,分析甄后“示枕赉枕”之举有悖常理。他指出此赋应为曹植讽托之词,“《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6]883即曹植通过宓妃,委婉表达的是对文帝曹丕的忠心。
何焯的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曹植通过塑造宓妃这一女神形象来寄寓政治理想,与中古时期文人普遍的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的追求有关。《洛神赋》创作于黄初四年(223)曹植由京城回封地的途中。这一年朝廷举行“会节气”大典,曹植希望得到文帝曹丕的召见,能够当面申说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不久任城王曹彰暴薨于京城,灌均等监国使者恶意中伤,曹植等被驱遣回封国。在回封地的途中,曹植怀着对京城的不舍之情,对继嗣立业的理想的怀念之情,身陷抑郁难平的境地。当他在洛水边,听说宋玉对楚王所说神女之事,通过对洛神(宓妃)的追求及人神殊途的结局的抒写,寄寓自身曾经憧憬的政治理想及理想破灭。由此可见,曹植《洛神赋》中,无论对洛神形象的塑造,还是在洛神形象中所寄托的寓意,都表现出一种浓郁的世俗化倾向。
西晋以降,宓妃的形象在文学作品发生了一些孽变,一方面,在内涵上宓妃不仅成为神仙的一员,突出其神性;而且也是现实美人的指代,突出其人性。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宓妃的称谓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在游仙类的诗歌中,宓妃是以神仙的面貌出现的,所寄托的有是诗人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之情。陆机《前缓声歌》:“游仙聚灵族,高会层城阿。长风万里举,庆云郁嵯峨。宓妃兴洛浦,王韩起太华。北征瑶台女,南要湘川娥。”[14]572诗人在游仙昆仑之时,层城上有神仙正饮酒高会,有生于洛水的宓妃、起于华山的王韩、还有瑶台之女和湘川之娥。郭璞《游仙诗》(清溪千余仞):“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15]297《文选》李善注:“灵妃,宓妃也。”[5]卷二十一,1020诗中对宓妃有爱慕之心,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蹇修这样合适的媒人,不知该派遣谁去说媒。所写内容虽然延用《离骚》中追求宓妃一事,但作者只是借求爱无缘来表现现实中求仙不成,寻道无路的苦恼,与《离骚》又有本质差别。游仙诗所表达的对神仙宓妃的企慕之情,与当时文人在进退维谷的人生窘境中企慕神仙的逍遥和追求精神的自由有着密切关系。
南朝诗人喜用“洛妃”来指代“宓妃”,显然受汉前传说与《洛神赋》的双重影响。而在具有宫体风格的诗歌中,洛妃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她美丽的外表,或以高髻示人,“妾闻洛妃高髻,不资于芳泽。玄妻长发,无藉于金钿。”[16]卷五十七,1038(梁,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其一);或以含情脉脉的表情动人,“博山登高用邺锦,含情动靥比洛妃”[17]卷十九,1884(梁,刘孝威《赋得香出衣诗》)。这类诗歌中的宓妃除了美貌,并无内在的气质、心理活动等的描写,因此无法将她与其他的美人区分开来,宓妃也就成为美人的代称。宓妃指代现实中的美人的写法,既有前代文学因子的继承,也与南朝以来世俗享乐之风的盛行有关。诗人在声色享乐过程中,把身边的歌伎舞女、倡家宠姬写入诗歌当中。这些现实中的美女因其多以色艺示人,其性格特征并不明显。因此神女宓妃成为诗人对现实中美人的褒扬之词,无法拥有更深的生命内涵。
在南北朝时期,洛神(宓妃)活动的洛浦(伊洛)也由原本的地理范畴化为文学意象,其涵义有三个方面:第一,洛浦是宓妃神话的诞生地,因此洛浦成为美丽的诗歌意象。如温子升《常山公主碑》:“奄辞身世,从宓妃于伊洛,遽捐馆舍,追帝子于潇湘。”[18]卷五十一,500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诗》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云。倾城今始见,倾国昔曾闻。”[17]梁诗卷十五,1807江总《新入姬人应令诗》曰:“洛浦流风漾淇水,秦楼初日度阳台,玉轶轻轮五香散,金灯夜火百光开。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来。”[17]陈诗卷八,2595或指长山公主仙逝,乃是随从洛神游于伊洛;或指美人倾城倾国之美;或指与美人相会于洛浦。第二,洛浦是恋人分别或遗赠佩珰的地点,因此洛浦又成为浪漫激情的诗歌意象。如王筠《五日望采拾》:“献珰依洛浦,怀佩似江滨。”[17]梁诗卷二十四,2016刘孝绰《为人赠美人诗》曰:“巫山荐枕日,洛浦献珠时,一遇便如此,宁关先有期。”[17]梁诗卷十六,1837不仅将洛浦作为情人欢会之地,而且洛浦的故事与巫山神女的故事又融为一体。第三,洛浦之女神擅长歌舞,因此洛浦指代现实中歌姬表演演奏之地。阴铿《侯司空宅咏妓》:“楼似阳台上,池如洛水边。”[17]陈诗卷一,2457庾信《奉和夏日应令诗》:“愿陪仙鹤举,洛浦听笙簧。”[17]北周诗卷二,2381洛浦又成为了美人歌舞的神仙境界。
此外,宓妃还作为男性寄托情感的对象,成为文学典故,出现在南北朝文学当中。最早使用此典的作品是曹植《妾薄命行》:“想彼宓妃洛河。退咏汉女湘娥。”诗人先描写男女携手又同车,再写比肩而上,亲密恩爱,先抑后扬,这就乐极生悲,更大程度上烘托出红颜不常、欢乐难久,从而心羡神女——宓妃、汉女、湘娥的情思。此外如鲍照《采桑》:“灵愿悲渡湘,宓妃笑瀍洛。”[19]卷三,137萧衍《戏作诗》:“宓妃生洛浦。游女出汉阳。”[17]梁诗卷.1535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诗》:“洛阳远如日。何由见宓妃。”[17]梁诗卷二十七,2085魏收《美女篇》:“仍令赋神女,俄闻要宓妃。”[17]北齐诗卷一,2268等都是以宓妃为典故,寄托对神女宓妃的向往之情。在徐悱夫妇的赠答诗中,也有以宓妃作典故的例子。徐悱《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忽有当轩树,兼含映日花。方鲜类红粉,比索若铅华。”[17]梁诗卷十二,1771以桃花喻妻子。其妻刘令娴《答外诗》其二:“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还看镜中色,比艳自知非。”[17]梁诗卷二十八,2130则谦言自身的外貌无法与宓妃相比,以回应丈夫的过度赞美。
综上所述,在中古时期宓妃形象得以丰富和发展,延续楚辞传统,在人神相恋主题下寄托政治理想;在游仙诗中成为世人钦慕的神仙形象;在宫体诗中变身世俗的美人形象。宓妃及其所在的洛浦都具有文学生成意义,成为文学典故和文学意象。当然宓妃的形象也正是在不断演变发展中日趋丰满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