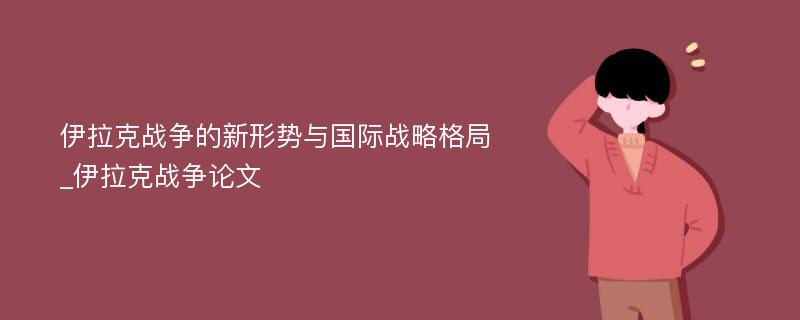
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战略格局的新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势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格局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美国总统布什2003年5月2日在“林肯号”航母上发表演说,宣布美英联军在伊拉 克“主要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注:Transcript:President George W.Bush's Remark
in the Desk of Aircraft Carrier Lincoln on May 1,2003,The Washington File,May 3,2003.),伊拉克问题已经进入了“国家重建”的新阶段。然而,这场战争究竟对 世界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是目前国内外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无论从哪个角 度来看,伊拉克战争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战争的结果正在孕育着世界格 局自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又一次显著变革。
以“极”为分析方法的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
有关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到底是多极还是单极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普遍使用的世界局势的“多极化趋势”算是一种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比较稳妥的提法。但国内学术界很少真正对当前国际体系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进行过深入和细致的理论论述。其实这样的争论非常正常,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之外,即便在美国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究竟应该朝着多极还是单极、或是两极发展也有着相当尖锐的争论。(注:在美国,主张美国的“单极霸权”可以得到维护和持续的相当极端的观点,请参见Charles Krauthei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1,pp.23—33;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 4,No.1,1999,pp.5—41;而对多极化、包括恢复两极结构的观点,请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18,No.2,1993,pp.45—73;Robert Jervis,“International Primacy:Is the Game Worth the Candl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1993,pp.52—67;Charles
Kegley and Gregory A.Raymond,A Multipolar Peace?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St.Matin's 1994;而介于这两者之间、认为未来世 界可能会重新回到不稳定的多极世界的“悲观主义”观点,请参见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1990,pp.5—56;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但美国学术界的争论和中国的争论 有着相当的不同。中国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实判定”的争论,即争论今天的国 际体系究竟是多极还是单极,而美国的争论则是一种“政策需要”的争论,即究竟是多 极还是单极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与现实世界的需要。(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主张维持“单极霸权”更符合美国利益的主张成为了多数。美国新保守主义防务政策理 念强烈追求“单极霸权”目标。参见Robert D.Kaplan,The Coming Anarchy: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Cold War,New York:Random House,2000。)
伊拉克战争使得这样的争论再度尖锐起来。国内学术界和政策领域内的相当一部分同志认为,伊拉克战争并没有造成世界格局的变化,因为从总体上来看,国际力量对比没 有发生根本变化。(注:蔡文中、葛瑞明:《伊拉克战争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载《 和平与发展》季刊,2003年第2期。)也有的同志认为,伊拉克战争有利于多极化的发展 ,甚至将加速多极化进程。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多极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趋 势,但伊拉克战争却典型地说明了今天国际体系的“单极”特征。由于“不同的体系给 大国和小国提供了不同的菜单”,(注:[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著,王玉 珍译:《世界政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是我们认识世界、把 握国际局势、制定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因此,在伊拉克战争之后 ,联系战争的事实来澄清今天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体系特征”问题,已是一个十分严肃 而又紧迫的学术课题。
传统的“一超多强”的论述是支持多极化认识的基础,但应以力量对比作为判断和分析世界格局的基本标准,不是简单地分析国际关系中大国的数量。以力量对比的分析来判断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取决于两个标准:一是国家间权力的能力(capabilities)的分配;(注: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4.)二是在能力分配的基本体系结构中寻找是否存在着有效的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和权力的能力是两个有着紧密联系、但又相当不同的概念。如果说权力主要是指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其具体的构成可以由经济、科技、军事、领土、资源以及价值观、制度的效率、社会生活的成熟度、凝聚力和士气等“硬”和“软”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权力指标来衡量的话,那么,权力的能力则包括权力的威望、使用与追求权力的方式以及权力的构成要素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注:沃尔兹教授并没有对权力能力做出非常明确的定义,只是强调应该具有“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31.另一位现实主义的理论 大师罗伯特·吉尔平对此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述,参见Robert T.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h 1。)通常来说,权力构成了能力的基础,但权力的能力 却是一国权力的具体实施和发展,并对权力的分配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国际关系 史上,虽然拥有权力,但却并不注意如何去形成强大的权力能力的例子并不少见。因此 ,单纯意义上的大国的数量并不是我们得出国际体系是多极、两极还是单极的依据。
国家间权力的能力分配的基本结构,构成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特征,(注: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26—127.)也使得国际体系可以分为“ 单极”、“两极”和“多极”。体系中的“极”(Polarity)的概念是普遍界定国际体系 权力分配特点的分析工具,“极”的数量也是说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的依据。这不仅 可以了解我们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国际体系”中,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了解现有国 际秩序以及个体国家政策选择的关键。因为“国家间权力的分配构成了各种国际体系的 主要控制形式”,(注:Robert T.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52.)是在国际体系的“环境因素”制 约条件下了解国家间实力差距最有说服力的方式。
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极”的资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构成“极”的国家是否在经济规模、人口、劳动生产率等综合国力上具有优势,特别是其军事实力上能够比国际系统中另外一个军事大国的军事实力还要强大。具体来说,一个可以在军事力量上至少占到其他任何一个军事大国的军事实力51%的国家,可以构成一个“极”。(注:Randall L.Schweller,Deadly Imbalances: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17.)现实主义者之所以更看 重军事力量是“极”的定位的重要标准,是因为安全是国家间关系中根本性的内容,也 是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早在20世纪70年代,沃尔兹就认为美国具有比较其他大国而言 在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地拥有领先优势,(注: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201.)但仍然与只是在军事实力和战略争夺能力上旗鼓相当 的苏联形成了“两极体系”。“一超多强”只是一种简单的描述性方法,并不是国家间 权力能力分配的解释性方法,因为它忽视了权力的构成常常影响权力的性质以及运用权 力本身要比单纯的权力存在更为重要这两个基本事实。今天美国的军费支出超过世界上 军费开支在美国之后的15个国家的总和,是对国际体系单极特征的生动说明。在新现实 主义理论看来,经济实力固然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济实力并不能自动等同 于国际关系中国家的行为能力,也不如军事力量那样可以对国家的国际行为和国际体系 的权力格局发挥更为实质性的影响。(注:虽然当代世界政治强调经济发展与经济竞争 力在权力认识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在理论与实践中这常常是一种“误解”。无论是进攻 性现实主义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有关国家权力追求、安全目标、均势的建立与破坏以 及国家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的关键策略等问题的论述中,审视和拥有相对还是绝对优 势的军事力量都占有中心位置,而简单的经济实力的增加可以构成制衡能力的基础,但 难以对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发生实质性影响。在“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理论中 ,军事力量更是经济与政治实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挑战或者维持秩序的决定性要素。 请参见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
单极体系下的权力制衡
国家的能力优势是定义“极”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能力优势还必须同占有这样的能力优势的国家数量有关,这是“极”的定义的真正核心。如何区分“一极”、“两极”或者“多极”体系的基本标准,是看一个国际系统中综合实力占有第二位的大国是否能够对最强大的国家构成有效制衡;如果第二位的大国无法构成有效的制衡,甚至若干大国间的联合都无法构成有效的制衡,一极体系就已经形成了。(注:这一观点,由沃尔兹首先提出,随后得到了许多现实主义理论学者的支持。请参见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p.5—41;John M.Owen,IV,“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S.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3,2001/2002,pp.117—152; Randall L.Schweller,Deadly Imbalances: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能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很难被制衡( counterbalance)”,那么,这意味着体系中国家间的能力分配出现了向某个国家的重 大倾斜,该体系也出现了“单极体系”的具体特征。(注:明确地以此来作为“单极体 系”定义的,是威廉·C.沃尔弗斯,参见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p.10。)
“权力制衡”或者说“均势”之所以是解释以“极”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特征的关键,是因为“极”的分析简化了国际权力对比关系,是更好地认识“均势”的钥匙。(注:就现实主义理论而言,“极”的概念引入可以更为直接地解释国家间均势状态,因为这让国家间权力关系“简单化”了。Jack Donnell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00,p.106。)具有 相互制衡能力的一定是“两极”体系或者是多极体系。如果缺乏有效的权力间的相互制 衡,这样,才会出现“单极”的格局。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并不缺乏制衡性的政策诉求, 美国的许多单边主义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指责;也不缺乏对特定政策行为的制衡行动 ,例如伊拉克战争之前,法、俄都曾威胁动用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通过授权动武的协议 。但之所以仍是一个“单极体系”,就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均势”——涵盖所有权力 主体的体系性均势——已经崩溃,美国正处在一种“非均势”(imbalance of power)的 、几乎不受实质性挑战的权力关系之中。
体系性的均势,至少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基本原则:第一,当某一个大国准备发动可能破坏其他大国利益的军事行动时,其他的大国可能将单方面或者联合通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方式进行遏止。(注:有关军事手段在均势中的首要作用,参见John M.Owen,IV,“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S.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 6,No.3,2001/2002,p.119;约翰·米尔斯海默把“均势”更是直接解释为国家间“军事能力的分配”。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Ch.1 endnote 36。)面对威胁,军事结盟通常是稳定权力关系和恢复均势最重要的途径。(注 :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 7;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Ch.1.)第二,违背其他大国利益的单边行动应该受到惩罚。不顾其他大国反应的 行为应该让风险远远大于收益。第三,将会导致力量变更迅速、因而破坏稳定的国际战 略平衡的行动无法得逞。已有的国际战略秩序可以产生一种有压制力的稳定效应。没有 国家可以依靠单方面的力量谋求改变秩序。第四,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建立制度化的 大国一致。或者说,在国际制度内部,大国自觉的行为克制是可以指望的,而且,通过 大国协商,既维护多边主义,又保障在国际制度内部制度化合作的发展。(注:有关实 现制衡的手段,笔者在这里的归纳糅合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在新现 实主义看来,制衡的有效方法是“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即通过“威胁— 惩罚”来执行;而新自由主义更强调国际制度中通过自律的合作而能产生的“奖赏—惩 罚”效应来进行。当然,新自由主义从不把国际合作理论视为“均势”。但在自由制度 主义看来,国际制度的约束力具有制衡权力、特别是单边行为的重要作用。)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见证了美国单边主义的兴起,目睹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的不断扩大,却没有发生任何直接针对美国的军事结盟关系。虽然在和平与发展的前提下,区域与次区域的合作进程有了新的发展,但在军事领域除了北约东扩之外,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同盟条约以及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都只是区域意义的安全安排。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成为大国安全与战略努力的重要方向。这一方面有助于大国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生动地体现了今天国际力量对比的事实。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之所以没有出现针对美国的结盟关系的发展以求实质性地制衡美国的“单极霸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美国的优势是综合性的,几乎涵盖了国家权力发展的所有领域,具有在政治、 经济、科技、军事、资源、信息与地缘政治等方面诸多的主导性力量,结果形成了对其 他国家多方面的战略性牵制,并使其他大国难以形成对美国充分的军事、经济、技术和 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等领域内的挑战。(注:有关美国作为“单极”霸权所具有的综 合性优势及其影响,请参见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pp.277—290;Robert J.Lieber,ed.,Eagle Rules?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Hall,2001。)
第二,“跨国自由主义”的全球发展,对美国的霸权性质产生了更大的“容忍力”。美国一直有人声称“美国式”的单极霸权是一个“良性霸权”或者“柔性霸权”,并从这种“霸权”的政治、文化、价值与制度特征来论证美国霸权在世界政治中的稳定作用。(注:对美国“良性霸权”的定义与分析,请参见Charles A.Kupchan,“After Pax Americana,:Benign Power,Regional Integration,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2,1998,pp.40—79。)此外,美 国权力构成中的非特质性要素的优势——“软权力”——让美国真正具有“世界领袖” 的特质,成为美国显示和追求权力的重要手段;(注:Joseph 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对美国 政治经济制度的认同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制衡美国“单极”力量的动机和决心,甚至出 现了心甘情愿“服从”美国单极霸权的倾向,也同样加强了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 (注:John M.Owen,IV,“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S.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3,2001/2002,pp.117—152.)
第三,美国的经济、安全与国际市场的主导能力,产生了深刻的区域影响,成为当代区域政治和区域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其结果,往往使得许多中、小国家缺乏紧随其他大国制衡美国的愿望和热情,制衡美国的国家常常不具备在所在区域内的足够号召力。(注:Stephen M.Walt,“Two Cheers for Clinton's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79,No.2,2000,pp.63—79.)甚至当它们决定在战略上挑战美国时 ,可能成为区域政治环境中首先被制衡的对象。这种区域事务中不可替代的美国角色, 又进一步促进美国来推行“俾斯麦式”的强权政治。尽管在某些地区政治中,例如在亚 洲,美国还无法完全建立某种“单极霸权”,但美国的威望政策以及随时准备显示实力 以进行干预的意志,决定了美国仍可以建立起“多极—单极”相结合的地区政治体系。 (注:Aaron L.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1993/1994,pp.5—33;and
Josef Joffe,“Bismarck or Britain?Toward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Bipolarity,”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9,No.4,1995,pp.94—117.)
第四,美国的“单极霸权”由于美国所主导的联盟体系的发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而“极”的背后所具有的组织和主导国际网络的能力、或者以“极”为首的国际阵营的紧密程度,往往是衡量“极”的质量和权力能力的又一重要标准。(注:G.John Ikenber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Persi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1998/1999,pp.43—78.)美国 是今天世界上最广泛地建立和利用各种国际制度来形成有利的权力优势的国家。在2002 年5月,北约开始接纳7个中东欧的新成员国加入北约之后,美国与世界上60个国家签署 了双边或者多边的军事同盟条约,与7个国家签署了利用军事基地或者派兵的协议。这 样一个最为广泛的军事同盟体系,大大增强了美国“单极霸权”的行动能力,也进一步 削弱了世界力量对美国的制衡实力。因为从一个单一国家所具有的这种与其他国家关系 的紧密程度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超过美国。而美国作为今天世界上惟一的“极”与其他 国家所具有的这种影响力,是美国能够建立“单极霸权”的又一重要基础。(注:有关 一个具有国际体系中“极”的地位的国家应该具有的“集合”(amass)国际支持的能力 对“极”的地位的作用以及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请参见Edward Mansfield,Power,Trade,and Wa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21—44。)
第五,当代国际关系中各种制衡性因素都面临着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内在问题和困难,从而制约了它们发挥对美国的制衡能力。在中短期内,国际社会中还难以出现在权力能力上与美国能够接近、从而能有效制衡美国的新的综合性强国或者国家集团。因此,对美国的挑战或者制衡很大程度是以特定的利益为导向的,而不是传统均势中的那种体系性的、全局性的制衡关系。
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强调,由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对国际体系的变迁具有重要作用,每个国家都将有选择地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单纯以国家的能力分配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的特征似乎并不能说明国际关系中的各国政策选择的主观作用,“不同体系的特征在于不同的国家行为模式”。(注:[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95页。)不仅是单一国家,国家间的联盟、特别是像欧盟这样紧密型的国家集团同样可以构成国际体系中的“极”。(注:Jack S.Levy,“The Polarity of the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An Empirical Analysis,”in Alan Ned Sabrosky,ed. ,Polarity and War: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Boulder,Colo.:Westview,1985.)但就国际体系的整体而言,构成体系性的制衡力量最重要的是 依靠权力的能力,而不是制衡的愿望或者非全面性的、不彻底的制衡政策。20世纪90年 代以来,欧盟力量的发展,特别是欧盟内部正在推行的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建立6万 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对美国一系列单边政策的批评等等,都展示了欧盟扩大的自主意 识。但欧盟的问题是:有制衡美国的众多手段,但“缺乏使用这些手段的组织能力和集 体意志”。(注: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2000,p.31.)
伊拉克战争为什么无法阻止?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经历了主战与主和势力从2002年9月开始讨论1441号决议到2003年4月这半年多的外交角逐。在这期间,反战国家阵营与主战国家阵营的尖锐对立,经历了安理会辩论中伊拉克问题上的彻底决裂,也经历了2003年4月15日提克里特被占领之后大国关系开始修补的过程。2003年6月3日埃维昂峰会所发表的伊拉克问题8国首脑声明,强调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民主的伊拉克”,(注:Keith B.Richburg,“Chirac's Show,Bush's Agenda-Statement by G-8 at French Summit Reflects U.S .Aim,”Washington Post,June 4,2003.)标志着大国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进行了9个月 的“外交战”告一段落。
主和势力阻止了美国获得安理会授权而对伊拉克动武合法化,从表面上看,是国际社会主张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正义力量的胜利。但战争还是爆发的事实、美国在43天的 伊拉克军事行动中依靠高科技军事手段所获得的决定性胜利以及目前美国排斥联合国单 方面军事占领伊拉克、主导伊战后进程的客观状况,说明了美国“单极霸权”没有得到 有效制衡的当前单极体系的基本特征。伊拉克战争之所以无法得到阻止,说到底,体现 了单极体系下国际权力运作的“体系特征”。
第一,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的能力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
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迄今为止的最高代表。发动伊拉克战争所需投入的权力资源要比布什政府不参加《京都议定书》、废弃《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做出部 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要大得多。由于战争涉及众多的大国利益,战争本身更是美国所 具有的“权力空间”的试验场。在国际关系中,对单边主义的约束力不是取决于国际法 或者国际道义,而是一个国家权力大小。(注:Steven E.Miller,“The End of Unilateralism?Or Unilateralism Reduc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5,No.1 ,2001/2002.)“两极”或者“多极”体系中之所以缺乏单边主义政策行为,就是因为“ 两极”或“多极”体系中的国家间力量分配使得即便享有“极”的地位的国家也无法享 有足够的权力资源而追求单边行动。因此,能否具有单边主义的政策倾向,是一个国家 权力的国际空间所决定的。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不仅反映了美国的实力地 位,更是因为美国享有一般国家所远远无法企及的权力空间。当美国的权力追求不需要 顾及更多的消极后果、不需要支付难以承受的成本代价或者利益损失时,单边主义就会 成为一种权力追求的可靠方式,并进而成为基本的政策模式。单边主义客观上反映了一 个国家行使和追求权力时所享有的“自由度”。(注:Chalmers Johnson,Blow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New York:Henry Holt,2000.)伊拉克 战争之所以没有被阻止,就是因为美国占有了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权力自由”,使它 能够绕开联合国、绕开国际社会普遍的反对浪潮。
第二,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制度、多边主义等地位不断提高的国际权力要素虽然重要,但在依然以权力政治为基础的当代国际关系中,短期内还难以成为强大的“单元力量”,替代或者超越国家形式的权力主体而变成制衡“单极霸权”的决定性角色。
在伊拉克是战是和问题上的大国竞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反战力量主要是 在利用安理会表决机制、利用联合国这一多边外交场合,反对美国全力冲向战争。为什 么反战力量没有尝试通过其他的国际斗争手段,例如,显示武力、削减和美国的贸易关 系或者降低对美国的投资等制裁手段以及发展新的军事同盟让美国去体会一意孤行的战 略代价,就是因为美国之后的其他大国,包括中、法、德、俄等国,或者在军事力量、 或者在经济需要、或者在政治利益等方面,都存在着对美国完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注:用数字来表示军事实力,如果美国为100,那么英国为50,法国为40,其他北约国 家在10~30之间。参见[日]江佃谦介:《信息革命巩固了美国控制性的地位》,载[日] 《中央公论》,2003年第2期。)这一关系制约了“反战轴心”制衡美国的能力。从2003 年3月20日开战之日起,反战阵营的主要国家纷纷开始调整政策、转而寻求修补对美关 系,(注:Elaine Sciolino,“European Leaders Struggle to Mend Rift with U.S., ”New York Times,March 20,2003.)开始避免美国“秋后算账”的务实外交,更是典型 地说明了联合国等国际制度的局限性,多边主义能够牵制美国的霸权行动,但并非是规 范和能够决定性制衡霸权国家的工具。
伊拉克战争及目前美国主导的重建进程生动地说明了国际制度与单极体系中非霸权国家之间的两难关系。在军事战略力量上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的俄罗斯,在经历了从叶利 钦时代的经济痛苦、战略收缩到普京时代的全力争取美俄新战略伙伴关系、利用西方资 金重振经济到同意北约新一轮东扩、基本放弃与美国即便在欧洲的战略竞争,俄罗斯的 变化加剧了美国与其他大国在权力领域的不对称发展。法国与德国虽然在政治上体现了 平衡美国主导作用的政策选择,但法德两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难以对美国构成 有效的制衡。(注:有关美欧之间的实力的差距、特别是军事力量与防务预算之间的差 距,请参见Charles A.Kupchan,“Rethinking Europe,”International Interests,No .56,1999;Robert Kagan,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vs.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New York:Knopf,2003。)中国选择了埋头发展国内经济的道路,也面对着 台湾问题这样的“战略瓶颈”的掣肘。为此,希望制衡美国的大国外交都纷纷将重点放 在维护联合国这一多边国际组织在世界事务中的核心地位上,国际制度、多边主义以及 已有的国际规则等,成为非霸权国家平衡美国霸权影响、反对单极化的重要手段。维护 多边主义、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不断倾斜的实力对比,各大 国被美国“挤压”出来的外交选择。然而,伊拉克战争使得联合国的国际制度权威受到 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不过,这也算澄清了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长期的争论: 国际制度不仅不能取代权力制衡,相反,没有权力制衡支撑的国际秩序中国际制度的作 用是非常有限的。(注: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说明在安全这样的“高位政治”中自由制度 主义理论的失败。诚如沃尔兹教授所指出的,国际组织的制度性作用的发挥,首先是建 立在可靠的权力互动的基础上,国际制度的约束力并不比权力制衡更大。参见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pp.18—27。)
第三,当美国这样的单极霸权缺乏体系性的制衡力量时,权力的逻辑必然支配美国转向赤裸裸的权力意愿、追求最大的权力利益,而不会真正顾及非体系性制衡行为的挑战。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除了政治上的反对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对美国单边行动宣布惩罚或者制裁行动。相反,却是美国在占领巴格达、眼见伊拉克军事行动胜利在即之际,宣布要对反战的国家进行惩罚。围绕着由谁来主导伊拉克战后重建、是否应该尽快恢复联合国监核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的核查工作、在联合国安理会未就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得出结论之前是否应该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以及伊拉克石油利益的重新分配究竟由谁说了算等一系列问题上,战前就已出现的主战与主和势力的较量继续进行了较量。2003年5月22日通过的1483号决议却最终显示,美国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几乎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设想,美国的霸权意志并没有受到根本挑战,甚至是布什“一个人的演出”。( 注:“U.N.Expert Say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on Iraq Creates a' One-Man
Show'”,Interview to William J.Durch on May 28,2003,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t www.cfr.org/publication print.php?id = 6002&content.)反战力量赢 得了“和平信念”的胜利,但却输掉了“权力政治”的“游戏”。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 输掉了国际道义和法理,但却赢得了“权力政治”的胜利。在简单的“一超多强”的描 述性力量对比背后,“多强”受制于美国的程度要远远高于“一超”可以受制于“多强 ”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一超多强”的传统世界战略格局的描述性语言,或许换为 “一强众弱”更为恰当。
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战略格局的新态势
伊拉克战争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单极特征,但并不意味着多极化进程从此暗淡。国际格局中一系列新的战略性动向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世界政治中的均势格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传统的涵盖所有权力角色在内的制衡机制“休克”了,但对美国的权力制衡仍将继续。国际制衡的特点将从传统意义上“制衡美国”转向“制衡美国的行动”或者是“挑战美国的政策”。
国际关系中结构性的制衡力量依然存在,但目前的均势格局似乎只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发挥作用,而美国成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游离于现有的均势格局之外、并正在对均势格局的形成可以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在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中的“超越”现象,是我们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历史上所找不到的,也最直接地论证了单极体系的主体特征。因为,我们可以在两极体系中看到的那种稳定的“恐怖均势”、或者在多极体系中可以看到的哪怕是不稳定的“多元制衡”都已经不再是权力行为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当传统的大国均势不对美国的权力追求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力时,传统大国均势基础上的“多元制衡”失效了。均势成为位于美国的世界主导之下的国际权力结构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权力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其结果,一直被中小国家所反对的“权力等级制度”(hierarchy of powers)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将大大提升;(注:日本前外交官伊藤宪一提出,当今世界正处在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近代国际体系要向可称为是“第二次中世纪”的后近代世界体系的转变过程中。这倒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参见[日]伊藤宪一:《向“正统的”认识国际政治的“前提”提出质疑》,载[日]《中央公论》,2003年1月号。)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在“回归传统”,即权力的支配性作用将超越以往历史中所形成的国际制度、国际道义和国际法规则,或者说强调“权力来定位规则”,而不是让“规则来规范权力”。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受到来自美国单极霸权的体系性限制。
第二,美国式的单边主义说明了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所无法达到的权力空间。但美国到底能在扩张性的“单极霸权”的位置上呆多久,仍是个疑问。只要美国继续追求单边主义政策,美国与世界其他力量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就不可能结束,而只可能继续发展。这样的冲突和斗争将有利于缩小国家间权力能力分配的已有差距,一是因为各国内外政策发展的新的紧迫感,二是因为美国“四处伸手”、由于负担过重而自身受到削弱。(注:Chalmers Johnson,Blow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New York:Henry Holt,2000.)从长远来看,美国单极霸权主导国际事务的格局必然会被打破,多极化仍然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未来和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在国际关系中建立自上而下、权力垂直控制的单极霸权体系。美国的政策行为持续受到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制衡美国的外交、政治、社会和战略行为不会少见,甚至会在新的形势下发展。“权力制衡”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中国家对权力的基本需要,当权力过分向一个国家倾斜时,其他国家必然要采取行动以便恢复并维护均势。(注:在沃尔兹看来,均势是一种“系统结果”(systemic outcome),这是 由国际系统的结构特点决定的,因为国家和政治家的行为是“非决定性的”。Kenneth
N.Waltz,“Evaluating Theor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 4,1997,pp.915—916。)亨廷顿(Samuel E.Huntington)认为,国际体系将可能一直保持 在“单极—多极”的竞争状态之下;(注:Samuel E.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No.2,1999,pp.24—49.)而主张美国应获取绝 对安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则干脆否认当前国际体 系是“单极”,因为美国不可能不受到挑战和制衡。(注:John Mera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s,Ch.10.)
伊拉克战争生动地说明:“不受制衡的权力,不管谁来行使它,对其他国家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注:Kenneth N.Waltz,“Evaluating Theories,”p.915.)美国《新闻 周刊》杂志刊文指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强硬举动已经令世界感到“惊骇”。 (注:Fareed Zakaria,“The Arrogant Empire,”Newsweek,March 17,2003.)伊拉克战 争将迫使有关国家不得不面对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寻找尽可能缩短这些差距的 途径,而不会坐视差距的存在甚至扩大。2003年4月初,德国和法国政府都表示将增加 军费;6月初,欧盟首次决定绕开北约向刚果派遣维和部队,欧盟的共同外交与防御政 策也将有更快的发展趋势。这种寻求军事力量发展的努力,虽不是为了如何“对抗”美 国,但势必产生以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反映大西洋两岸关系的积极效应。伊拉克战 争是美欧关系出现决定性变化的转折点,尽管这一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寻求对美国 霸权新的制衡性约束,将是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注:Simon Serfaty,“Renewing the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CSIS Publication,2003,pp.28—29.)
第三,实力差距难以迅速缩短将导致单极体系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单极体系”的现实出发,将会进一步按照自己的实力地位加强全球的力量配置和霸权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正在成为当前国际秩序最大的“挑战者”,而不是最大的“维护者”。
美国将会加速全球战略的调整过程,以便让今天的国际秩序与美国新的霸权地位和利益要求相匹配,并继续享受单极霸权所带来的“权力自由”。布什总统2003年5月21日宣称,“世界未来的和平与自由依靠美国的行动”,预示着美国将会全力推进2002年9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注:“Transcript:Bush Outline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Agenda,”Washington File,May 23,2003,p.3.)这在布什政府目前宣 布的全球军事部署的调整,继续冷落德、法等“老欧洲”,将大西洋两岸的联盟关系明 显向中东欧国家倾斜,对重建“失败国家”具有热情以及全力干预中东和平进程等行动 中,都有具体的体现,显示了美国想要重新塑造新的国际战略秩序以便顺应“单极体系 ”的战略性企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非霸权国家现在倒反而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而美国却在全力营造“单极体系”下新的国际秩序。这种新、旧秩序观的对峙和冲 突,将使世界局势在短期内难以稳定,并成为后伊拉克战争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变 数。
与此同时,非霸权国家将不得不重新寻求提升对美国霸权行为制衡能力的新外交行动。这一过程可能同样是漫长的、渐进的,但却同样代表了世界外交格局发展的一个新的 方向。对此,我们应该有期待和乐观的情绪。最近,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印关系的 实质性改善以及法国国防部长2003年6月末访华时所提出的呼吁欧盟国家解除对中国的 军事出口限制等动向,都或多或少地展示着国际关系朝着这一方面的艰难努力。而美国 的战略调整,是否应该更多地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欢迎,美国内部的反思也会不断进行 。总之,对未来世界政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我们无法把握住“体系变迁”的高度,恐 怕将难以有准确的洞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