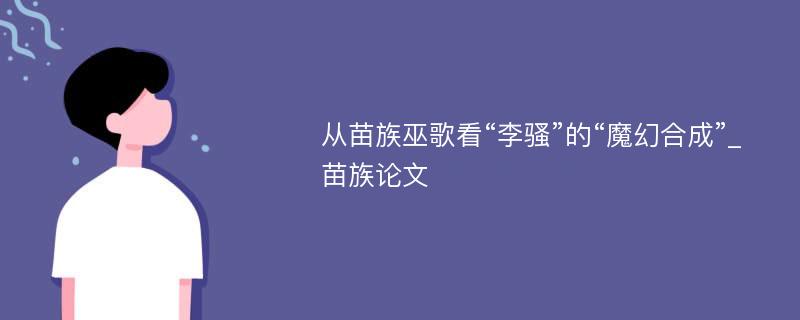
从苗族巫歌看《离骚》的“魔法综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族论文,离骚论文,魔法论文,巫歌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幻交混”是深层心理躁动的结果
毕加索曾把自行车的一只车座和一个车把组合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一件艺术品——牛头造型。自行车的车座、车把的形状无人不熟悉,但只有毕加索看出了它们之间巧妙的默契,他把两种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统一体。很早就有人指出这是一种“魔法的综合”,可惜这种综合是许多人想不出来的,它涉及到创造的重要方式——非关联思维。
非关联思维粗看是无逻辑的,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逻辑。
在一个秩序化的世界里,旧的符号体系半强制性地建立起人们与事物的习惯性联系,车座与车把的关联仅限于自行车的实用结构,而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用实用的眼光看待它们的价值。新的符号行为则要有意地打破日常语言的符号性,发现在旧符号体系的系统性之外的潜在联系。正像卡西尔说的那样:“我们可能会一千次地遇见一个普通感觉经验的对象而却从未‘看见’它的形式;如果要求我们描述的不是它的物理性质和效果,而是它的纯粹形象化的形态和结构,我们就仍然会不知所措。正是艺术弥补了这个缺陷。”创造性的思维往往最初表现为非关联思维,即把两种或几种本来不相容的事物放在一起,考察它们的统一性,艺术思维无疑首先具有这种品格。在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中,我们看到非关联思维几乎占据了主要地位。狗布拉托被甩出去,像泥巴一样粘在墙上;汽车像野兽一样喘气,从河里上岸时还抖落身上的水珠。文学也一样,古希腊文学中半神半人的英雄,中国文学中种种富于变化的妖魔鬼怪皆出于此。
所谓非关联思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思维,否则便无迹可寻。非关联思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思维线索,其中也包括部分“相似同一”的联系。非关联思维一般可以划分成两种基本形态:一是非关联物的结合;一是非关联物的化合。
因为非关联物的结合与苗族巫歌和《离骚》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对“非关联物的化合”问题,我们暂时不讨论,而重点讨论非关联物的结合问题。
在非关联物的结合中,被结合体各自保持了部分的特征。通过“结合”可以揭示双方关系中的特殊意味,造成双重联想。当两种似乎不相容的事物构成新的统一体时,双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又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比较、映衬、抗衡,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两极中往返、游移,在双重观的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
常见的类型很多,“真幻交混”就是其中一种。
有些创作将梦境、现实、科学、想象、神话、幻觉等对立因素熔于一炉,造成一种似真似幻,既荒诞又神秘的情境,比如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让死尸、亡魂和活人同时登场,通过老人享梅尔和木乃伊的一场戏,把登场人物几十年间的恩仇纠葛一一展示出来,把人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虎视眈眈的世相刻划得淋漓尽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则打破了幻与真、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小说人物可以进入幽冥世界,与鬼魂和妖魔打交道;后者也可以随意进入现实世界,同活人一起生活。
产生这种类型的“魔幻综合”得有一定的前提,拉美的土著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神话、传说、图腾、巫术、宗教等等,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土壤。拉美有极其多样的神奇的现实,除了密林、草莽、荒原、绝谷、虎豹、鳄鱼、蟒蛇、食肉植物等可怖生物外,还有白人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巨大反差,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生活土壤。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构思了十五年,才忽然想到应该像外祖母讲故事那样叙述现实,外祖母曾不动声色地给他讲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沉着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起来像真的一样。马尔克斯的灵感里显然也产生了非关联思维的“魔幻综合”。
屈原是楚国的大巫。《离骚》是祈神的祷词。它在使用非关联思维方面,与《百年孤独》等纯文学作品不同。《百年孤独》的“巫幻意识”是创作主体的想象,而《离骚》的“巫幻意识”却是创作主体的意识与无意识的交混。
这种意识与无意识的交混,实际上是创作主体深层心理躁动的结果。这可以通过散存于民间的苗族巫术活动来予以说明。
贵州苗族存在着一种做神的活动,有的叫做“七姑娘”,有的叫做“苗家稻”,有的叫做“菜花神”……,黔东南苗族叫做“七姑娘”(也有叫做“苗家稻”的),时间在农历七月初至七月半。在月光的朗照下,人们集中在村边的空旷处,由一人或几人扮“七姑娘”神游天界。用布蒙脸,以手指塞耳,向前点燃香火,他人从田中摘下稻叶插在他(她)的头上,并给他(她)扇风。引导者用话和歌来给予引导。做神者慢慢昏迷,两脚抖动,便进入“阴间”,去会亡灵,去到“最美丽的地方”后,开始返回,如遇到死去的亲人的亡灵就痛苦不已,如果遇到青年男女,就同他们对歌。平时不大会唱歌的人,也变得特别能唱,据说这是神(“七姑娘”等)授的结果。
为什么进入迷狂状态后会具有特异的歌才——一种在清醒时不可能具有的特异的灵感?这种歌才是不是“神授”的呢?笔者认为这种特异的灵感不是神授,而是他(她)自己深层心理的激活与躁动。
荣格运用无意识理论研究原始意识,原始人类的深层心理,这对我们研究迷狂心理有直接的参考价值。他说,研究无意识,“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疯子的幻想以及所谓的降神会。只要自主心灵成分被投射出来,无形人便随时随地会出现”。“如果一个人被某种重要的心灵内涵投射到,他就算是着魔了。”①这说明迷狂、幻象,是原始人的“心灵投射”,像精神病人心中的幻影一样。它不是客观存在的“神灵”,而是人的深层心理无意识的投影和幻象。
心灵的投影和幻象如何产生呢?人在清醒时,感官接受外来剌激,引起表层的心理活动。表层心理的内容是对现实的反映。深层心理的内容是本能的,是世代相传的集体表象。中层心理内容是被遗忘的概念和意象。梦的景象和精神病人的幻象,都有三个层次的心理内容。人入睡后,大脑皮层广大区域被抑制了,但个别兴奋点尚未抑制。个别兴奋点的兴奋或某一兴奋点引起其他兴奋点的兴奋,形成幻象系列,是非逻辑的。这种梦,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梦,是表层意识的余波。中层心理活动的梦是过去遗留的表象而近日遗忘的内容。深层心理的梦,是非个人经验的“种族记忆”、“集体表象”,它是一种形象符号,它不表达固定的生活内容。巫师“过阴”(做鬼)和一般人“做神”(“七姑娘”等)的心理活动也和梦相似。他在清醒时主要是表层心理活动。如果他需要迷狂进入神界时,就得采用蒙面、塞耳等手段,促使大脑皮层抑制,或使用咒语和灵物,使其发挥巫术作用。这样,做神者大脑皮层慢慢抑制而逐渐昏迷,犹如进入梦乡。他只听到引导者的声音,其他毫无所知。平时人的表层心理活跃;深层心理似乎沉睡着,深层的无意识以其感情欲望影响人的意识,而不直接表现为意识,所以不易觉察;迷狂时,表层心理抑制了,中层和深层心理被激活起来、释放出来,从而获得灵感和异乎寻常的歌才。
特异歌才——迷狂心理激发的灵感,这只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而所唱的内容则决定于他的深层和中层心理结构所储存的信息。迷狂时的心理幻象,即是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或是维列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
一般人做神(“七姑娘”等)进入“阴间”后所走的路线也是一种原始意象,是一种“种族记忆”的“集体表象”。黔东南苗族做神,要沿着祖先迁徙路线走到东方祖先发祥地,所经过的地方,今天的人们不太了解,但做神的人却能一一唱出来。②
由此可知苗族“真幻交混”的巫术迷狂,正是柏拉图所说的“迷狂说”、“神授灵感”。创作需要表层心理激活,也需要深层心理的激活,需要理智,也需要迷狂。创作的最佳心态是理智与迷狂结合的半迷狂状态,是进入角色,旁若无人,如醒如痴,情绪激越的状态,是思想、感情、想象、理智充分激活的状态。
在屈原时代,一切都笼罩在神话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之中。人们确信被我们称之为虚幻的神话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我们视之为奇异、荒诞,然而在那种社会的集体表象中却不作如是观,在他们的集体意识、集体表象中,我们称之为神话的一切内容本身就等于存在、等于真实,因而屈原很容易从现实进入巫幻的情景,达到真幻的巫术境界。
苗族巫歌与《离骚》都是真幻交混的“魔法综合”的产物
苗族巫歌与《离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理智与迷狂相结合的产物。它们身上都打上了真幻交混的“魔法综合”的印记。
苗族无论接龙、椎牛还是敬神、招魂,都能同已逝的祖先或鬼魂进行交流。比如苗族招生魂,巫师找到灵魂囚禁的地方后,先同守洞的鬼进行周旋:给它好吃的,说它喜欢听的,若守门的鬼执意不放生魂,便进行强攻。苗族驱鬼也是一样,若鬼老是赶不走,巫师则把油锅烧得烫烫的进行强攻。苗族巫歌叙述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但也沉着冷静、绘声绘色、真幻交混、真真假假,粘合得天衣无缝。
《离骚》中的“真幻交混”一般人都能理解。它是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现实的不幸命运与辉煌巫风世界经过“魔法综合”甚至撞击之后形成的一种不可遏制、狂烈奔涌的灵感状态,从而在人—神共祀的世界中熔铸出千古不朽的抒情篇章。
这本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对《离骚》进行具体研究时往往就忽视了这“真幻交混”的特点。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叙》提出讽谏说,指出写作的动因是讽谏,对象是直指楚王。“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塑,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记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隋书·经籍志》亦说《离骚》“用以讽谏”。班固《离骚赞·序》认为《离骚》乃抒忧之作。指出创作的心灵动因是“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罹)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这两种解释比较有代表性,说明《离骚》的创作心理动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政治讽谏,一是心灵的宣泄,双重对象是楚怀王和社会。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动因与对象的四个因素尽管互相关联,却不能涵盖整个作品,换句话说,即在“真幻交混”中只反映了“真”,未反映出“幻”的奇异与辉煌。
然而,《离骚》并非一种以倾诉内心情感表达心灵世界为动因的纯粹文学创作,而讽谏之说不但失去了“幻”,而且难以涵盖《离骚》博大浩渺的宇宙意象。从《离骚》抒情主人公多次占卜、多次神游,以及直面神祗的祈祷形式,我们都可以发现《离骚》较之纯文学或一般讽谏君王之作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抒情动因和倾诉对象。直接地说就是在两种动因和两重对象之上,还具备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动因和倾诉对象,这是属于“巫幻”方面的“神灵对象”以及“巫风通神”的动因。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离骚》是“巫祝之作”是令人信服的。林河先生认为:“《离骚》是屈原深感楚王不听巫言,自愧不能属尽神职,只好祈祷皇天,求神允许他离开人间,皈依天界,以彭咸之所居的祷词。”这一说法从“巫幻”方面去理解是极有见地的,若从整首诗去看,又未免失之偏颇,因为《离骚》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巫祝之作,而是根植于生活的沃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作品;应用真幻交混“魔法综合”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不能只抓住一个字去做文章,否则就大谬了。
苗族巫歌与《离骚》的相同审美特征
由于苗族巫歌与《离骚》都是真幻交混的“魔法综合”的产物,因而它们都具有“飘忽美”、“矛盾美”与“升华美”的审美特征。这些审美特征归根结底是主体至上的哲学思想与意念万能的巫术心理相结合的产物。
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对苗族巫歌与《离骚》进行比较分析。
先说“飘忽美”。
苗族巫歌与《离骚》都具有一种飘忽美,这是受“巫幻”性质所决定的。飘忽美,即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主人公可以时而天上,时而地上的穿行,甚至当代的人可以和古代的“魂”对话,有形的人可以与无形的鬼交谈。
这种飘忽美一半属于形式,一半属于内容。从形式上讲,这是一种活动过程,它以梦幻般的自叙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主体的情感,而且创造了一连串变换莫测的意境群。这些意境群神秘、辽阔、宏蒙、幽远,让人感到优美而神秘。但这种飘忽美又是以内容作为基础的。飘忽往来是抒情主体的神思自由飞越,是一种不为生活逻辑所制约,不受时空阻挡而任主体独往独来的巫幻意象,这个心理流程表现了主体生命力的张扬和主体至上的本我观念。
苗族巫歌运用巫幻的方式创造的意境是离散的、迷蒙的,但主体的情绪可以在意境群中自由穿行,并且可以把这些迷蒙的意象变得很清晰。
黔东南苗族做“七姑娘”回老家的路线一般是:上马——天地交接处——生死桥——桑那岭——扬州城。巫师和所有做“七姑娘”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些地方,但这些地方是什么模样,距离有多远,都一概不知,但神游者可以倏然而至,而且什么地方有沟,什么地方有坎,什么地方有狗,什么地方有人,都说得清清楚楚。苗族巫歌的审美取向与儒、佛、道迥然不同,它表达了一种对生命本体意识的追求,它的审美特征不是静态的体验,而是内心自由奔放的游动;审美境界不追求虚无与色空,而强调斑驳陆离、朦朦胧胧的荒诞美;审美的愉悦不是人性消失后的超然自行,而是人性得到充分展露后的舒展与快乐。
《离骚》的飘忽美,是诗人借助巫幻方式,模拟太阳的行程游弋到天界地极,给人一种巫术无所不及、无所不能及的感受。“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这里“高丘”指阆风山。“春宫”指东方青帝所居之宫。此二境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抒情主人公却能用巫幻意识将其紧紧地串联在一起。他忽而“登昆仑兮食玉英”;忽而又“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忽而“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忽而又从九天看见了自己的故乡:“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整个过程离散、跳跃,飘飘忽忽如同梦幻一般,色彩的多变,感受的纷乱与朦胧,展露了诗人的内心体验与审美态度,让人感受到抒情主体的人性、情欲获得抒发后的快感。英国学者霍克恩先生在《求宓妃之所在》一文中,将这种飘忽美的运用方式称为“宇宙式”,也有的学者将其称为“梦幻式”。不管是“宇宙式”还是“梦幻式”,都是巫幻思维对这些意境群的宏蒙与离散的飘忽美的概括。
在“飘忽美”这个审美特色上,《离骚》与苗族巫歌有极其深刻的内在联系。《离骚》中,抒情主人公神游天界,意识里不但存在着厚实的意念万能的巫术心理基础,而且“就重华而陈词”、“求宓妃之所在”……要寻求贤才和故世先祖的神灵来服务现实,拯救祖国。这种真幻交混的“魔法综合”紧紧地把“人的本质永恒”同“意念万能”维系在一起,具有一种飘忽而又有程序,朦胧而又不失清晰的审美效果。
次谈矛盾美。
苗族巫歌与《离骚》都是若干对矛盾的统一体,这些矛盾本身是无法解除的。它们都通过这一对一对的矛盾来挖掘主体内心的苦闷与哀愁,离乱与困惑,从而显示出主体在矛盾中的崇高与伟大。
矛盾美在苗族巫歌中,特别是在丧葬歌和送魂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黔东南苗族的《焚巾曲》就是其中的一首。唱《焚巾曲》的目的,是送亡人的灵魂沿着祖先迁徙过来的道路,一步步回到远古祖先居住的老家,再从老家送到月亮上去。亡人的灵魂上了天堂,“阴安阳乐”,才能赐福给后代儿孙。苗族《焚巾曲》的矛盾表现在:既希望亲人长寿,为亲人的去世而婉惜:“爸央来主宰/定妈的寿数/逃也逃不脱/推也推不掉。”但又怕去世的亲人留恋人生,魂魄回来作祟,而说亲人是自愿离开人世。“年高妈衰老/人老容貌衰/衰老实难看/不愿留人间/要往天上还。”整首长歌一千三百余行,内容十分庞杂。包括民族的来源、迁徙、战争;包括死者的出生、成长、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等。《焚巾曲》饱含着深沉的感情和韵味。我在拙著《中国苗族巫术透视》③中曾作过论述。比如描绘老人年轻时的情爱生活是这样唱的:“哥吹木叶叫/妹把头巾招/哥从高山下/妹从高山下/相会坝子边/坐在枫树下/枫树枝叶茂/枫枝把哥遮/枫树把妹妮/……情歌声悠扬/情话软绵绵/……歌声太动听/飞鸟飞拢来/……鹡宇说妹妹/成双趁青春/不成双青春过/过了青春时期/嫩叶变成老黄叶……”这段巫歌极具诗情画意,他们年轻时的美丽、风采及他们快乐的神态都得到了生动的表现。这里的“枫树”、“鹡宇鸟”④像吉祥的光环笼罩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想起亭亭如盖的枫树,想起天空的一轮皎月,想起如凤凰般美丽的鹡宇女神的保佑,加上情歌对答,此乐何极!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巫歌么?一点不假,这确实是巫歌。它主要是通过这美好的回忆来表现人们对生的渴望,对生命的礼赞。但《焚巾曲》毕竟是以送魂为目的,希望亡灵离开家乡到月亮上去享福。因此,《焚巾曲》描述亡灵告别家乡、告别家人、告别物事的情节亦很精彩:“妈妈走到水井边,/妈辞别水井:/‘请坐了水井!/留给姑娘来挑水,/挑给她的情人喝。’/妈妈走到菜园地,/妈辞别菜园:/‘请坐了菜园,/留下种青菜,/给妈的儿孙吃。’”这几句巫歌情感十分强烈,其意思有这样几层:1.表现母亲对生的留恋;2.表现了母亲美好的心灵;3.表明晚辈、寨邻对母亲一往情深。但除了这几层意思而外,更深层的意思是相信语言的巫术魔力,亡灵告别水井,不会回来作祟,使水井永远都是满满的;告别菜园,亡灵不会回来作祟使儿孙有菜吃。
苗族巫歌竟把生与死、留与走的矛盾描绘得是这样地具体、生动、形象,又通过刻意的内心体验,使这种矛盾美中包含了人性美和人格美。
与苗族巫歌相比,《离骚》的矛盾要表现得直接些、外露些。
楚顷襄王立,闻屈原在非难朝政,东山再起之心不死,便怒而将他放逐到江南。屈原窜伏沅汀,深感政治无望,他打算离开祖国,求合于他国。可是深固难徙的思想使他下不了决心。走与留的矛盾,长时间困扰着他。“灵氛为余占之”,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再请巫咸指示前程,巫咸叫他留下求合,别在远游中错过了君臣遇合的机会。灵氛劝他走,巫咸叫他留,反映他在去留问题上举棋不定。可是当他环顾楚国的现实,还是决心离开楚国去“周流上下”。于是在虚构的幻境里开始了远游。最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因看到了故乡,“远逝自疏”的幻境又被击得粉碎。
《离骚》围绕诗人政治斗争经历中的思想发展变化而展开情节。他的思想变化主要围绕独善其身、与世推移、去国远游三大思想矛盾的产生、斗争与解决来展开。诗人在描述、展开思想矛盾时,采用真幻交混的“魔法综合”构建了一个个幻境,暂离丑恶的现实生活在巫幻情景中展开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在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时又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了。因此,全诗的意境若真若幻,深刻地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不可调和。
由于《离骚》的这种矛盾美熔铸了人生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内容,因此,它除了闪耀着人性美、人格美的光辉外,还包含着一种悲壮美与崇高美。
再说升华美。
升华美实际上是对矛盾美的一种补偿。苗族巫歌追求的升华美不是超功利的,不是把主体超越苦难然后化仙成佛,作为审美取向;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把不可能实现的生活内容,通过巫幻意念来予以实现。黔东南苗族做“七姑娘”,表面上看,是通过唱歌送阳人“上天”旅游,领略天国风光的一个荒诞的过程。通过真幻交混,使人从巫幻情景中获得超越苦难的慰藉。苗族巫师招魂,按“魂”的要求一一给予满足,具体表现为,“魂”渴望什么,便祭献什么,使“魂”的缺憾不复存在,最后把“魂”送到最快乐的地方去,与祖先们一起享受极乐世界。
实际上苗族的每一种巫祭活动都表现了超越苦难的隐性意图。
《离骚》中的升华美也是很明显的。诗的抒情主人公多次占卜、多次神游,以及为神祗的祈祷,灵魂的独往独来,都是为了超脱政治上的不得志。特别是在诗的末尾,在走不能,留无益的情况之下,诗人只能选择巫幻的理想来解脱现实的苦闷,从而强烈地表现了一种爱国主义精神。
《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的爱国主义形象全无忠君不二的伦常羁绊,表现出鲜明的叛逆精神。辞中表现了自己对楚王朝整个贵族统治集团的决绝之意,这是“真幻交混”的“真”的方面的内容;它的“幻”表现在“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要以彭咸大巫为榜样,到另一世界去,永远同他们在一起。因此,我们说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是通过“巫言”来实现的(后来,屈原以自沉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那是另外一回事)。诗人正是这样,通过真幻交混的“魔法综合”消除了思想上的种种矛盾的对峙与缠绕,获得了最大的快慰和美的享受。
张中一先生在《屈原新传》中认为:屈原自沉“没有悲伤,只有信仰”。“他的生是巫的降临,他的死是巫的升华”。这些观点都是极有见地的,亦可以此来证明《离骚》的升华美的确是它的一个显著的审美特征。
注释:
①引自《探索心灵奥秘的现状》。
②以上材料引自潘定智《深层的心理躁动》/《苗岭风谣》总第六期/贵州民族学院民研所编(内)。
③拙著《中国苗族巫术透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④苗族神话认为:枫树生蝴蝶妈妈,蝴蝶妈妈和水泡“游方”生下十二个蛋,请鹡宇鸟孵,孵出了人类始祖姜央及雷公、龙、虎等。苗族巫歌中“枫树”与“鹡宇鸟”是吉祥幸福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