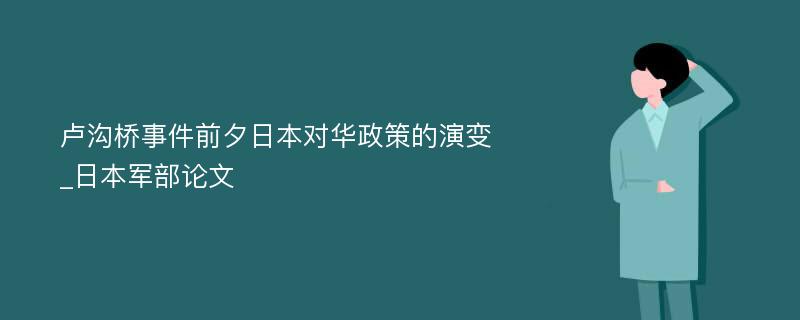
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沟桥论文,日本论文,事变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两国学者在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研究中,其最大分歧或争论的最终焦点是有无计划及预谋的问题。〔1 〕这除了对于事件本身的研究之外,在近代中日关系的过程中,如何认识与研究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乃是重要环节或关键所在。鉴于国内有关学者的成果〔2〕, 本文选取1936—1937年上半年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主要运用日方资料,立足于最高军政决策当局,论述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之“确立——调整、失败——再调整、再失败——再确立”的演变过程,以论证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一 1936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确立、调整及其失败
30年代初,日本三赌“国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对华政策就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乃至左右了国内政局。在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对华政策多与广田弘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为作为外相乃至首相(1933—1938年间的广田,只在1937年2—5月间未入林内阁),“广田至少从1933年起就参加了实行侵略战争的共同计划和阴谋”,“他对于军部及历届内阁所采用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人,有时是支持者”。〔3〕广田于1933年9月14日就任外相不久,斋藤内阁连续5 次召开五相会议,最后决定了外交方针(10月21日), 其中首先是对华方针〔4〕;初登政坛的广田联络高桥藏相,在五相会议上暂时成功地抑制了陆军的主张〔5〕,而以“和协外交”登场。 为将上述对华方针进一步具体化,外务省与陆、海军省的有关课长之间进行了半年多的协商,在冈田内阁成立后的1934年12月7日决定了三省之间的《对华政策》, 其中较为详细且具体地规定了对华政策的本义与实行方针、策略与行动纲要。〔6〕1935年,当华北事变日趋高潮时,外、陆、 海三省有关当局继续就对华政策进行了近半年的协议,10月4日阁议通过了《外、陆、 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7〕,此即所谓“广田三原则”。 在该谅解案的《附属文书》中还有一项规定:“1934年12月7日外务、 陆海军主管当局一致同意之备忘录,应与1935年10月4 日各有关大臣之间达成的谅解案相并行且继续有效,直到研究出可替代该备忘录的决定时为止。”〔8〕至此,“广田三原则”及“1934年12月7日备忘录”,就构成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部内容,同时它又把进一步研究与确立对华政策的任务留待以后。
1935年下半年日本策动的“华北事变”,使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先已发表“八一宣言”的中国共产党之主力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领导了华北民众的反日运动。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遭到打击,蒋介石在11月的国民党“五大”上发表“最后关头”的演说,成为“一九三六年中国对日政策的根本方针”。〔9〕1935年底的中国正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 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的结局也并不完全如日本之初衷。这些情况迫使日本统治集团迅速拟定“广田三原则”的实施策略,并正式厘定华北政策。而一贯充当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于12月间就华北问题提出对策,并特别指出:“华北分离的实质,就在于使国民党政权沦为长江一带的地方政权或趋于崩溃的命运,以利于促进日满对全中国的提携。”〔10〕它的主张,与上年底日本在华陆军武官的上海秘密会议所决定的“打倒国民政府、扩大亲日区域之国策”〔11〕,如出一辙。
1936年1月8日,广田外相召集外务省有关官员及驻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在外相官邸举行“对华方针研讨会”,与会者对当前日中关系的重要问题达成共识。9日, 东亚局第一课长守岛据此拟成《对华外交方案》,又称“守岛私案”。〔12〕该方案提出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以全面调整日中关系的方针,并准备了当南京政府提到华北问题时的对策。与此同时,参谋本部(9日)发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 对去年的运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帝国今后……要使华北明朗化变成现实”。〔13〕这个意图,很快就表现于13日陆军省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的《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之中。〔14〕该纲要规定以“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作为处理华北的主要目标,并由中国驻屯军实施华北五省自治。15日,陆军省派影佐到外务省向守岛课长出示了上述纲要,并说己向海军方面出示。守岛向外相及次官报告后,该两上司均认为此件大体可行。〔15〕20日,参谋本部派喜多等人到外务省,表示军部对于“守岛私案”基本无异议。〔16〕经过上述协调,21日,广田外相在第68次议会上公布了对华三原则,并谎称中国政府已表示赞同。〔17〕陆军省的上述指示,即(第一次)《华北处理纲要》,同样亦作为政府决定,从而由军部政策上升为国策,实现了陆军一年来的夙愿〔18〕,而且,由于该纲要把军部的分离华北政策正式确认为国策,它的出笼,“是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19〕
针对中国方面的外交调整(张群继汪精卫任外交部长,许世英继蒋作宾为驻日大使),为更好地贯彻广田三原则,2月8日,日本任命前次官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此前(6日), 参谋本部已向外务省表达了对于日中南京会谈的意见。〔20〕当有田赴华前(19日),外务省也在给他的关于南京谈判的指示中说:关于华北工作,须参照陆军中央部致天津军司令官的指示。〔21〕新任驻华大使就是身负军部与政府的双重使命、准备来华开展谈判以调整日中国交的。但是, 当有田到沪上任的2月26日,日本国内政局却发生剧变,暂时中止了日中谈判的进程。
“二·二六”事件后产生的广田内阁(3月9日),随着军部支配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的恢复,军部对于政治的发言权进一步强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从此要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策大纲以及外交方针上”。〔22〕日本的对外政策及其核心对华政策,也就在这种形势下最终确立下来。
3月28日, 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在与有田大使会谈时声称:“现在已到了改变我对华政策的根本观念、确立作为国策的对华新政策之时了。”〔23〕1936年春夏之交,日本侵华活动迈出重大步骤。4月17日, 广田内阁决定加强中国驻屯军:大幅度增兵并改为永驻制,司令官由少将级晋升为天皇亲授的中将级,其目的在于“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增加在华北公开行使我国武力之机会”。〔24〕随着对华北经济掠夺的加剧,军方庇护下的冀东走私于5—6月间达到高潮。有田八郎回国接任外相后,5月16日任命前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 川越被视为著名的“中国通”,并且是与军部极为接近的人物;而外务省另一名素称稳健的“中国通”,长期居于次官地位且被广田首相作为驻华大使之首选的重光葵〔25〕,被免去次官一职后,由于军部不愿把在中国的权力由陆军省交给外务省,故绝对不会通过让重光任驻华大使的提案,重光只好改任驻苏大使。〔26〕重光与川越之争,反映了军部继续操纵对华外交的意图。由于日本在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到6月间, 就连蒋介石也感到:“除非日本改变其对华政策”,否则中日间“冲突已不可避,且为时不远了”。〔27〕日本非但不加改变,反而在军部支配下,加紧确立新的对华政策。
早就叫嚷“1935、1936危机”的日本军部,在“危机”到来时,陆海军却围绕国防国策问题发生分歧。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参谋本部提出以对苏为主的“先北后南论”,并拟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但借口“无条约时代”到来的海军则强烈反对之,主张“北守南进”。4月16 日海军中央部在其调查会第一委员会研究的基础上,发出《关于对外国策的通知》〔28〕,再次确认海军的上述主张并提出对华政策的基调。为解决陆海军间的分歧,参谋本部决定先与军令部就《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的修订问题进行协商,并于5月间完成修订,6月3日经天皇批准。 其中规定了未来战争对象是“以美、苏两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英国”,并提出了以中国为对手时的作战纲领。〔29〕随后,参谋本部在第一部内增设以石原为课长的主管战争指导的第二课,经该课与海军进一步协调,6月30日确定了陆军的《国防国策大纲》, 同时产生了陆海军间共同的《国策大纲》,至此,陆海军终于在“南北并进”这个战略目标上达成一致。同日,永野海相向首相、外相、陆相、藏相出示了《国策大纲》,陆海外三相间对此已基本无异议。〔30〕陆海军在进行内部协调时,与外务省的协调也在进行。6月19日, 外务省接受陆军省的建议,经两省多次协商,并征得海军、大藏两省同意,决定设立“时局委员会”,它是隶属外相(外务次官为委员长)的秘密决策机构,任务是对于日本对华北的各种政策与措施进行研究、审议、立案、上报,外、藏、陆、海四省有关局长各一人参加委员会,有关课长各一人参加干事会(东亚局长为干事长);同时外务与陆军当局间还达成谅解:把对华北的内部指导权,由外交移与陆军。〔31〕时局委员会的设置,便于日本各方对华北政策的统一,但也使军部在华北攫取更大权力。
按照军部国防方针产生的《国策大纲》的确定,7月初开始, 陆海军又向外务省提出确立《帝国外交方针》的希望,此后三省有关当局开始协商。外务省在次官指导下,先后于7月13日、15日起草了两案, 17日形成三省协议的基础案,30日,三省最终形成定稿。〔32〕这个《外交方针》把当前外交重点置于打败苏联在东亚的“侵略企图”,因而接近于陆军主张〔33〕;而在审议过程中,陆军亦以对苏为由,要求迅速实现华北特殊化并使全中国反苏附日,从而又使对华政策发生变化。〔34〕与此同时,7月以来, 陆海与外务当局关于对华政策的具体实行策略不断进行研究,其方案经过时局委员会的审议后,分别形成了《对华实施的策略》与《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及其《附录》。〔35〕
在主要由陆海与外务三省一个多月的不断协调,并基本定案的基础上,8月7日,广田内阁召开五相会议(首、外、陆、海、藏),决定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是外交与国防相配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36〕这是将陆、海主张兼收并蓄的“南北并进论”,并确立了外交从属于国防的方针。同日,广田内阁又召集除藏相外的四相会议,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37〕,确定日本外交的核心是“培育满洲国”,同时“主动调整与苏、中两国的关系,并设法向南洋方面进行和平扩张”。11日,广田内阁有关各省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及其《附录》。〔38〕这是上述国策与外交方针在对华政策上的具体化,是以“华北分治”为重点的对华策略,主要内容有:1.华北五省分治,“建立亲日满的特殊地带”;攫取该地区的国防资源、扩充其交通设施。在《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附录》“第一号”中,规定了当前对冀察政权(含冀东)应采取的经济措施;在“第二号”中规定了在华北国防资源中应迅速开发的项目及建设有关交通设施。这两项长期被忽略的附录文件〔39〕,将华北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它实际上是按照参谋本部此前的《华北重要国防产业开发要领》〔40〕而制定的。2.对于南京政权,要采取具体措施引导其“反苏附日”;特别应促其“实际上承认华北联省分治”,以作为处理华北的最上策;对南京工作与华北工作,不一定同时实施,力求分别予以解决。但不久(13日),参谋本部即对《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实施提出希望:“如今,对华北工作而言,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进入实施的时代了”,故“应使中国驻屯军的现地工作与大使及武官进行的对南京政权的工作互相配合”。〔41〕
上述一系列决定通过后,15日,广田首相将8月7日的《外交方针》及11日的阁议决定,上奏天皇。〔42〕鉴于政府一系列决定的重要性,为使政策更好地贯彻于在华文武官员,8 月底外务省派东亚局第一课太田事务官到长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向外交官员进行传达;同时,陆、海军分派影佐、中村两中佐赴华,召开武官会议进行贯彻。〔43〕至此,以军部为主导而形成的广田内阁一整套对外国策与方针、对华政策与措施,最终全部确立下来,在日本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具体表明了除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外,还想侵略南方以至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侵略计划”〔44〕,此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决策即以此为据。
日本对华政策全面确立后,它就取代了此前并行有效的广田三原则与1934年12月7日的三省备忘录,随后就是伺机付诸实施的问题。 恰在此时,8月24日的“成都事件”及9月3日的“北海事件”, 为日本贯彻政策提供了借口。于是继1936年初提出的南京谈判的方案,日本以该两事件的解决为契机,开始进行调整日中国交的谈判。9月5日,有田外相发出对川越大使的“第一次训令”,要他“以此次成都事件,引导国民政府转向调整日中国交的方向”,交涉的重点在于“根本解决”的项目上。〔45〕8日、10 日须磨在与张群的会谈中又将日中“根本解决”的项目具体化为七项要求。〔46〕这七项要求成为川越与张群谈判的焦点,它基本上与成都事件不相干系,乃是上月决定的对华政策的具体与深化。“北海事件”后不久,军部的反应更为强烈。9日, 海军省指示:“将本事件与成都事件一起,引导中央政府负责全面取缔排日及根本调整国交。”〔47〕15日,军令部决定《北海事件处理方针》,再次重申上述方针〔48〕;同日,参谋本部也决定了《对华时局对策》,指出“万一华北发生关系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时,中国驻屯军应断然加以严惩”,并要关东军派兵增援华北。〔49〕以发生于中国境内的两个事件为借口,日本军部与外交相配合,以武力为后盾,开始了贯彻既定政策的调整国交谈判,实即一次对华高压下的全盘勒索,其要求甚至超出“二十一条”。〔50〕
在川越与张群会谈破裂后,26日,海军省与军令部再次决定了《时局处理方针》,提出促使蒋介石回南京,与其直接谈判〔51〕;同时在《备忘录》中表示要“促使陆军与海军采取同一步调的行动”。〔52〕蒋介石回南京后,10月2日,广田内阁召开四相会议, 决定了三易其稿的《川越与蒋介石谈判方案》,并由有田外相密电训令川越,是为“第二次训令”。〔53〕在“第二次训令”中,日本准备了一揽子方案与蒋介石谈判,但在8日川越与蒋介石会谈中, 由于蒋表示仍由张群与其谈判,且“张部长之意见即系政府之意见”〔54〕,川越只好再次与张群会谈。在此期间,按照军部指示并与南京工作相配合,日军加紧在华北行动。9月30日,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与宋哲元达成了《田代—宋哲元协定》,规定了关于“华北开发”的具体项目〔55〕,以实现《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中的要求。关东军司令部也于9 月间批准了田中隆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决定由日本特务组织所谓“谋略部队”进攻绥远,伪蒙军随后进攻。〔56〕
但在南京谈判期间,日本操纵的绥远战争于11月中旬迅告失败,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乘胜收复百灵庙。在此情况下,12月3日, 张群约见川越,指出因绥远问题发生,调整国交问题发生阻碍,并拒绝了川越送来的日方起草的《七次会谈备忘录》。〔57〕7日, 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绥远事件发生,致障碍外交进行”〔58〕,实际表明中方结束调整邦交。至此,日本精心策划的、以成都、北海事件为借口的所谓调整国交的谈判遭到失败,被迫回到问题的出发点上来。30日中日解决了上述具体事件,而日方也认为这是按其要求而获之成果。〔59〕这样,“一九三六年之中日交涉,遂以成都及北海两事件之解决而告一结束”〔60〕,日本除了获此成果外,分别由外交方面进行的南京工作与由军部主持的华北工作均遭失败,按既定方针调整对华政策的计划宣告破产。
这时中国突然发生了西安事变,日本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14日,陆军省制定《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声称对此“没有必要改变以前的方针”,须视情况变化,依照既定的外交方针和对华实施策略继续推进,对华北则“决心实现《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61〕15日,陆、海、外三省有关局、课长聚会于外务省,讨论陆军省的上述对策,三省官员一致同意陆军省的“沿袭并促进”的对华政策。陆军省军务局长矶谷声明,关东军不取“积极”表现。〔62〕但关东军随后表示:如中国方面侵犯《察哈尔协定》(按:即《秦土协定》),则坚决以武力排除之。〔63〕17日,有田外相会晤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时称:“本事件结局如何,与日本影响至大,故帝国政府予以重大关心并关注其发展”(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并希望中方对张学良“采取严重适当的措施”。〔64〕上述表明,日本军政当局不希望西安事变出现“容共抗日”的结局,企图借机再贯彻其既定对华政策。但西安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及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又大大出乎日本的意料。
二 1937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政策的再调整、再失败与再确立
1936年底发生于中国的绥远事件与西安事变,被日本视之为“决定命运”的两事件。〔65〕它不但宣告了日本既定对华政策的失败,也促进了中国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以此为契机,日本统治集团被迫继1936年初之后,自1937年初开始,进行“对华再认识”,并考虑再次调整对华政策。受此影响,日本国内政局出现了九一八以来的第二次大动荡。在对华政策上走投无路的广田内阁于1月28日总辞职, 此次“倒阁的主力,正是有力支配广田内阁的军部”。〔66〕而且正由于军部的反对,特别使用了拒绝推荐陆相入阁这一手段,使宇垣一成的组阁梦迅速破灭。2月2日,由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组成“更加坚定的法西斯化”新内阁。〔67〕
实际上,在广田内阁尚未垮台前,军部即已开始“对华再认识”,并考虑相应调整政策。1月6日,参谋本部第二课提出《〈帝国外交方针〉及〈对华实施策略〉的改正意见》〔68〕,8日, 军令部第二课也提出了《对华时局处理方针》〔69〕,均表示应以西安事变为契机,重新认识中国、调整对华政策。25日当宇垣刚拜受组阁“大命”时,参谋本部就匆匆将上述意见的核心内容作为“意志”,表示于未来的陆相,并特别指出:如果改变了对华政策,而日中关系仍未调整、更加恶化,“至不得已时,应准备在万分忍耐之后,予以彻底之痛击”。〔70〕军令部也根据正在国内汇报情况的须磨驻南京总领事的意见,认为“此时应对既定的对华政策加以再检讨,准备和、战两手,以期万无一失”。〔71〕这样,在林内阁成立前,军部已就对华政策的再调整达成共识。
在林兼外相的1月间,外务省在与陆海军协调的基础上, 分别拟定了1936年8月11 日《对中国实施策略》和《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修正方案。先是,2月7日,陆军省军务局的园田中佐拟制了《对中国实施策略》和《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修正案的初案,是为“园田方案”。〔72〕20日,外务省东亚局的太田事务官仅将陆军的“园田方案”作了少许文字改正,即形成外务省关于调整《对中国实施策略》与《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第一次修正案,又称“太田方案”。〔73〕与1936年8月11日的定案相较, 此次将“对南京政权的施策”放在“对华施策”的首位,而放在第二位的“对华北的施策”则体现于《第三次华北处理纲要》中,提出“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之成为坚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区”,当前应“首先致力于进行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经济工作”,对冀东走私和华北自由飞行问题加快解决。在此基础上,经与陆海军的协商,3月3日,太田拟制了外务省的“第二次方案”,同时还草就了《关于废除冀东走私》及《关于调整华北自由飞行问题》的“第一次方案”。〔74〕外务省“第二次方案”变化较大之处,是根据海军省的意见,在对南京政权的施策中规定要“再开谈判以解决日中间各悬案”,内容则是上年底调整国交时诸要求的重复。对废除冀东走私及解决华北自由飞行问题,第一次方案规定了“有条件”废除与解决的方针,即:国民政府以月额100万元现金换取冀东走私之废止,以日本保留惠通公司、 上海—福冈间通航换取华北自由飞行之解决。这样,至3月3日,林首相主持下的外务省已与军部协议后拟定了一整套调整对华政策的方案。同日,原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就任外相。4日就将外务省3日拟定的上述“太田方案”改为东亚局方案,并予以通过。
“佐藤外交的任务,是改善目前完全陷入僵局的对华关系”〔75〕,而五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政府确立了对日本抗战的方针后,在对日外交上也进行了相应调整,3 日任命王宠惠为外长(前外长张群改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8日, 在佐藤外相于贵族院会议上提出要以“新的出发点”来检讨对华外交后不久,王宠惠也就中国外交政策声明:要以国家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平等、互利为基础,建立国际关系。〔76〕在日中两国政府推动下,12日—22日,以儿玉谦次为首的日本经济使节访华团,访问了南京、上海,会见了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等要人。儿玉归国后向佐藤外相进言:中国目前正上下一致努力于统一与国家建设,日本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现状,以决定今后的对华政策。〔77〕儿玉访华团的活动,政治意义突出,反映了佐藤外相的新的对华外交思路,并迷惑了一些中国人。〔78〕
但是,日本军部却对“佐藤外交”持有异议。3月上旬, 参谋本部将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召回东京,听取他们对中国形势的看法。喜多等认为:当前日中关系已非一般手段可以调整,应采取应急方针,即(1 )从对苏作战出发,调整对华国交;(2)在上述调整不可能时,“在对苏行动前, 要首先对华加以一击,摧毁蒋政权的基础”;(3 )不论上述两种情况如何,目前应调整对华关系,充实战备。〔79〕15日,海军省又拟定出《对中国实施策略》的第二案。〔80〕19日,陆军省提出了对于外务省关于废除冀东走私及对华航空问题方针案的意见,海军方面对此则表示“全然同意”。〔81〕
在军部推动下,3月22日, 外务省拟定了《对中国实施策略》的第三次方案,并根据海军意见,将《第三次华北处理纲要》改名为《华北指导方针》,并相应拟定该纲要的第三次方案。〔82〕4月5日,佐藤外相就“调整对华政策”向阁议说明时指出:此前关于对华政策的再检讨问题,经与陆、海军事务当局的协商,已形成共同意向;而关于对华政策之具体处理方式,三省当局业已达成一致。〔83〕在三省一致的基础上,又就“华北经济开发”问题征求了大藏省的意见后,4月16日, 林内阁的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省大臣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及《指导华北的方针》〔84〕,这标志着1937年初以来对华政策再调整的定案完成。
与上年8月11日决定的对华政策相比, 此次改正的重点在于:“废止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政治工作,而主要依靠文化、经济工作来指导帝国的对华策略。”〔85〕但在《指导华北的方针》中,却提出了与《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相同的目的与几乎相同的指导方针:除了对华北政权进行内部指导外,要使南京政权实质上确认华北的特殊地位〔86〕;与此不同的是提出了迅速解决冀东走私与华北自由飞行问题。5月7日,陆军省在外务省意见的基础上,将其3月4日初案的内容扩大为“对华航空问题”,并相应决定了“促进解决”的方针,要求迅速解决“日、德两国飞机在中国领空内起飞、着陆以及设置安西飞机场问题”〔87〕;8日,又表示对外务省关于废除冀东走私方案无异议。〔88〕10日, 佐藤外相通过川越大使,将与军部交涉的上述两问题通知在华主要领馆。〔89〕至此,佐藤终于完成了他上任前即由军部与外务间达成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方案。上述方案的过程与内容也同时证明了:“佐藤的中国外交,只能说是作为增添军部的新气象而登台,并继续加以发展的。”〔90〕也就是说,“佐藤外交”不过是军部推行对华政策的一个招牌而已,它是以“和”的一手,掩盖了日本的大战准备。
但“佐藤外交”的对华政策尚未及实施,针对当年初以来的“对华再认识论”,5月开始,日本又掀起“对华再认识论的再认识”。 月初,川越回国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为此提供了依据,而中国税警部队进驻青岛一事又提供了借口。10日,军令部提出针对“税警团事件”的《山东问题对策意见》〔91〕,要求当此之际“即使冒全面战争之危险,也要断然派遣讨伐之师”。15日,佐藤外相主持召开外、陆、海三省会议,听取川越报告后,就对华北政策进行“再检讨”,提出要从“新的出发点”重开日中谈判。〔92〕20日,担负华北警备的海军下村司令官致电次长:“如今调整国交、经济侵入的策略不可能成功,莫如以开战来整顿一切战备和指导适合国际形势的外交,乃为良策。”〔93〕陆军方面则于14日设立综合国策机关“企划厅”,并于29日向政府提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以待有事之日,可以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94〕此外,5月中下旬,陆军还派遣教育总监香月清司、 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参谋本部第七课长永津佐比重等要员,陆续到华北视察,以根据实情制定新的对策。在军部“对华再认识”的影响下,“佐藤外交”这个被视为软弱外交的招牌,于5月31 日随着林内阁的总辞职而迅速宣告失败。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观察因佐藤外交而出现的日本侵华周期性退潮时,曾感到如坐火山,且“不知火山将在何时爆发”。〔95〕佐藤外相在辞职时也曾忧叹:“如今日中两国的形势已处于这样一种危急状态,即如果就此发展下去,不知何时就会飞起战火。”〔96〕他们的预言在继任的近卫内阁初期很快就实现了。
6月4日宣告成立的近卫内阁,仍保留军部的重要人物即杉山陆相与米内海相,而以广田弘毅再任外相。同日,近卫在就职演说中声称,日本“对外不能仅以维持现状为是”〔97〕,表明“举国一致”的该届“青年内阁”将在对外政策上有所作为。而面对已陷入僵局的日中关系,近卫内阁的使命就是在对外政策上当务之急在于解决日中两国多年的悬案,调整两国国交〔98〕,这个使命则历史地赋予再次出场的“广田外交”。5日,广田外相声称:以前的广田三原则,今日已不适当, “因中日关系已经由抽象之原则,从企图实现提携之时代,进至实际问题,应加以解决之阶段”。〔99〕7日,广田在会见外国驻日使节团时, 会晤了中国驻日代理大使杨云竹,再次表示:中日间一切悬案应予解决。〔100〕在近卫内阁企图在对华关系上打破现状、 实际解决问题的主旨下,继上月以来“对华再认识”之趋势,6月初开始, 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纷纷以新内阁成立为契机,迅速表达其关于对华政策的见解与对策。
被军部派往华北视察的要人们首先汇报了实地的状况和对策。6 月5日,香月清司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危急, 必须增强中国驻屯军的兵力〔101〕;8日,永津佐比重报告说:不知何时就会在华北发生什么事件,需要对青岛一带严加戒备〔102〕;9日,柴山兼四郎报告说:蒋介石政权所进行的中国统一运动,实则仍未超出封建军阀的范围,而日本对此评价却甚高。〔103〕与此同时, 驻中国当地的官员们也向东京中央表达了他们的见解。6日, 驻青岛的陆海外官员就“税警团事件”向中央建议:要求中国税警团返回原驻地,向日本国内及欧美各国彻底宣传中国在山东的挑战态度〔104〕;7日,驻上海大使馆武官致电次官、次长,说:鉴于中国目前状况,无需马上改变对华政策,专守沉默、持静观态度乃是明举〔105〕;但驻南京武官则对该电表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与前年相比,南京的对日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日本现在若以妥协态度在华北问题上让步,调整国交则近乎不可能。 〔106〕但对调整对华政策最为关注的还是关东军。对前内阁政策强烈不满的关东军,于6月初便派东条英机参谋长到东京,表达其意见。 东条先是严厉批判了林内阁的对华方针,指出:不伴随政治工作的经济工作实行起来相当困难,这只要想到满洲事变前满洲的状况即可明了;而日本要求与南京亲善,反而会助长其排日、侮日的态度。〔107〕东条于9日提出关东军的对华政策是:“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108 〕关东军的“对华一击论”,与1937年初以来军部的主张一脉相承,成为此时日本对华政策的代表和强音,左右了近卫内阁初期的对华政策之基调。18日,视察了华北各要地的井本参谋向参谋本部报告说:中国的排日、抗日、侮日气氛已达于沸点,驻华军部官员对此看法大致相同,在对策上,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对于中国不加以一击,则不能打开局面”〔109〕, 这证明关东军的观点已获华北驻军的认同。与此同时,被石原莞尔派去视察卢沟桥现地情况的冈木参谋也报告说:必须预先准备强有力的应急措施。〔110〕
在军部及现地官员的影响和推动下,外务省的对华方针亦趋积极与强硬。6月初,东条英机在东京期间,外务省次官堀内及欧亚、 东亚两局长曾与之会谈,对于关东军的上述见解获得谅解。〔111 〕广田外相也认为,前内阁的“中国再认识论”过高地估价了中国,这反而会使中国更加傲慢。他在进行对华再认识之后,提出了对华的强硬方针与积极态度。〔112〕外务省的上述宗旨,表现于20 日对川越驻华大使的归任训令中,该训令特别提出要“侧重对华自主积极的推进,对佐藤外交之后退色彩予以修正”。〔113〕川越赴华返任的前日(24日), 曾与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陆军省军务局长后宫及海军省军务局长丰田举行会议,彼此交换了对华政策的意见后,他于同晚发表谈话,要求中国认清日本生存与发展之权利,以及伪“满洲国”之生存与华北间之必然联系。〔114〕川越的谈话表明了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方针, 中日两国间的问题已难有和平解决之望。
为了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在川越归任前,外务省派人来华与当地日本官员协商。6月21日,东亚局上村课长在青岛召集驻济南、 青岛总领事及武官,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以及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铃木少佐等人,说明政府的新政策并商讨华北政情及策略问题,与会者均表示要避免与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而以各地当局及民众为对象,分别利诱威胁实行经济文化上之侵略。〔115〕与此相呼应,30日, 广田外相在枢密院就对华关系作说明时,也声称外务省今后应体会前内阁对华政策之本意,寻机与中国当局开始;为此有关各省已派员赴中国及满洲说明上述新政策,以求贯彻。〔116〕但是, 当外务省东亚局上村课长来到驻华大使馆说明前内阁废止冀东走私之方针时,大使馆的陆、海、外官员一致认为:日本想让南京政府交付月额百万元的现金作为补偿,要待百年河清之时,莫不如仍继续对冀察方面进行内部工作。〔117 〕这说明再次登场的广田外交已不可能故技重演,只有寻求对华政策的新出路。
这时的中国政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在进行各种抗战准备的同时,采取了联合英美、对日强硬的外交立场,中日关系已形成互不退让的僵局。如何打开这一僵局?川越驻华大使在会晤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及王宠惠外长后,7月5日提出日本当前最适当的办法是:“实行满洲事变以来我一贯坚持之对华根本方针的急转弯。”〔118〕6日,在近卫内阁确立施政方针的阁议上,广田外相也表示:虽然对华方针与以往并无改变,但如今即使实现了日中亲善,也难望有成效;对于不能不说不满的日本而言,“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全体阁僚的一致同意。〔119〕至此,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近卫内阁初期的外交政策终于走到与军部主张相同的“正确政策”,亦即以“首先对华一击”来打开僵局的政策,剩下的问题,只是选择一个发生于什么时间和地点的“事件”为借口来加以实施了。于是,历史又回到了“九一八”以前,作为“第二次柳条湖事件”的卢沟桥事变已呼之欲出了。
注释:
〔1〕 曲家源著:《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 兼与日本有关历史学家商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156页;荣维木:《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
〔2〕 关于“从九一八到七七”、 或“七七”以前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国内所见有10余篇论文,但上述论著对“七七”前夕的日本对华政策之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其实,迫近“七七”的这一年多的日本对华政策最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意义。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 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77页。
〔4〕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5年版,第275—277页,(以下简称《主要文书》(下))。
〔5〕 [日]上村伸一著:《日本外交史》第19卷, 《日华事变》(上),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145页。
〔6〕 [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一)》,东京三铃书房1964年版,第22—24页。
〔7〕 《主要文书》(下),第303—304页。
〔8〕 《现代史资料》(8),第108页。
〔9〕 周开庆编著:《一九三六年之中日关系》, 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29页。
〔10〕 《主要文书》(下),第320—322页。笔者按:[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 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64—365页所载,由该书作者摘要的部分, 却并非该文件的核心内容。
〔11〕 日本驻华各地陆军武官曾于1934年11月12日起于青岛、16日起于上海举行秘密会议,见有吉致广田电(11月27日)、若杉致广田电(12月12日),载《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PVM30, 第238—246、250—255页。
〔12〕 《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2,第446—456页。
〔13〕 《现代史资料》(8),第128—134页。
〔14〕 《主要文书》(下),第322—323页。
〔15〕 《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2,第486—491页。
〔16〕 《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2,第477—479页。
〔17〕 《主要文书》(下),第324—326页。
〔18〕 [日]《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 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66页。
〔19〕 [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5页。
〔20〕 《日本外务省档案》,SP201,第34—35页。
〔21〕 《日本外务省档案》,SP201,第36—46页。
〔22〕 信夫清三郎,前揭书,第609页。
〔23〕 《主要文书》(下),第330—334页。
〔24〕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75—76页。
〔25〕 [日]《重光葵外交回想录》,第日新闻社1978年版,第166页。
〔26〕 美驻日大使格鲁致国务卿电(8月7日),载[日]《东京审判辩护方资料》第3卷,国书刊行会1996年版,第16页。
〔27〕 《蒋介石与李滋罗斯谈话录》(6月28日), 《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
〔28〕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84—386页。
〔29〕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95—397页。
〔30〕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88—389页; 《战史丛书·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第297—298页。
〔31〕 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3—3,第1328—1339页。笔者按:《现代史资料》(8)第372—373页所载内容出入较大, 应以前件档案为准。
〔32〕 以上各案,均载《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14 —34、45—54页。
〔33〕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931页。
〔34〕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87页。
〔35〕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88—89页。
〔36〕 《主要文书》(下),第344—345页。
〔37〕 《主要文书》(下),第345—346页。
〔38〕 上述文件,载《现代史资料》(8),第366—371页。
〔39〕 如,《主要文书》(下)载《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时,并未收录此件。
〔40〕 《日本外务省档案》,UD79,第55—59页。
〔41〕 《日本外务省档案》,UD79,第87—88页。
〔42〕 《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
〔43〕 《日本外务省档案》,UD79,第83—85页。
〔44〕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87页。
〔45〕 《现代史资料》(8),第287—289页。
〔46〕 《现代史资料》(8),第294页。
〔47〕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193—194 页。
〔48〕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199页。
〔49〕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18—419页。
〔50〕 如当时在日内瓦出席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曾致电外交部,指出:“川越提出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果然坚持包括中国全部,其范围超越二十一条之要求,真是日本亡朝鲜故技”。张群著:《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73年版,第68页。
〔51〕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203—204 页。
〔52〕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19—420页。
〔53〕 《现代史资料》(8),第297—298页。
〔5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1981年版,第675页。
〔55〕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69页。
〔56〕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12—113页。
〔57〕 《张群、川越会谈记录》(12 月3 日), 《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5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8—690页。
〔59〕 《现代史资料》(8),第310—312页。
〔60〕 周开庆前揭书,第105页。
〔61〕 《现代史资料》(8),第608页。
〔62〕 《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28,第9—18页。
〔63〕 《现代史资料》(8),第612—613页。
〔64〕 《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28,第80—84页。
〔65〕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13页。
〔66〕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30,第9—10页。
〔67〕 李凡夫著:《从广田内阁到林内阁》,黑白丛书社(上海)1937年版,第47页。
〔68〕 《现代史资料》(8),第378—381页。
〔69〕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213页。
〔70〕 《现代史资料》(8),第384页。
〔71〕 《现代史资料》(8),第420页。
〔72〕 《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95—100、55—64页。
〔73〕 《现代史资料》(8),第394—396页。 经笔者详细核照,此件与“园田方案”差别甚微。
〔74〕 上述方案见《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78—94、156—172页。
〔75〕 信夫清三郎,前揭书,第616页。
〔7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1至6月份),台北1985年版,第250页。
〔77〕 转引自[日]臼井胜美:《佐藤外交与日中关系》,入江昭等编《战间期的日本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第257页。
〔78〕 据《国闻周报》第14卷第10期载,当时某些中国政府官员认为:佐藤外交“颇似空谷足音……确较广田与有田为进步。”
〔79〕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26—127页。
〔80〕 《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78—94页。第一案为3月5日拟定,载《现代史料资料》(8),第397—399页。
〔81〕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122—123页、131—132页。
〔82〕 《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65—74页。
〔83〕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页。
〔84〕 《主要文书》(下),第360—362页。
〔85〕 《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4页。
〔86〕 参见佐藤外相关于该政策向驻华使领的说明(5月6日),内有对“实质上与特殊性”的解释。载《日本外务省档案》,IMT402,第12—20页。
〔87〕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133—134页。
〔88〕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124页。
〔89〕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112—115页。但《主要文书》(下)(第362—365页)一书中只收录该件甲号、C号, 缺少乙、丙号及A、B号。
〔90〕 臼井胜美,前揭书,第253页。
〔91〕 《现代史资料》(8),第433—435页。
〔92〕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30—31页。
〔93〕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27页。
〔94〕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27页。
〔95〕 (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1页。
〔96〕 [日]佐藤尚武著:《回顾八十年》,时事通信社1970年版,第376页。
〔97〕 《国闻周报》第14卷第23期。
〔98〕 [日]风见章著:《近卫内阁》,日本出版协同公司1951年版,第27页。笔者按,该书作者当时为第一届近卫内阁的书记官长。
〔9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1至6月份),第545页。
〔100〕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04页。
〔101〕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33页。
〔102〕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33—135页。
〔103〕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28页。
〔104〕 驻青岛总领事大鹰致广田电第165号,《现代史资料》(8),第436—437页。
〔105〕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402,第26—29页。
〔106〕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402,第30—35页。
〔107〕
转引自[日]三宅正树编集代表:《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2),第一法规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6页。
〔108〕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61 年版,资料附录,第333页。
〔109〕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35页。
〔110〕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28—429页。
〔111〕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21—226页。
〔112〕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31页。
〔113〕 东京驻日大使馆致南京外交部电(6月25日),载《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台北,1967年版,第128页。
〔114〕 《申报》1937年6月26日第一版第三张。
〔115〕 青岛市长沈鸿烈致南京外交部电(6月22日),转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1至6月份),第616—617页。
〔116〕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58—259页。
〔117〕 上海大使馆武官致次官、次长电(7月2日),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76—279页。
〔118〕
转引自[日]臼井胜美:《“支那事变”前的日中交涉》,载臼井胜美著:《围绕中国的近代日本外交》,筑摩书房,1983年9月版,第121页。
〔119〕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