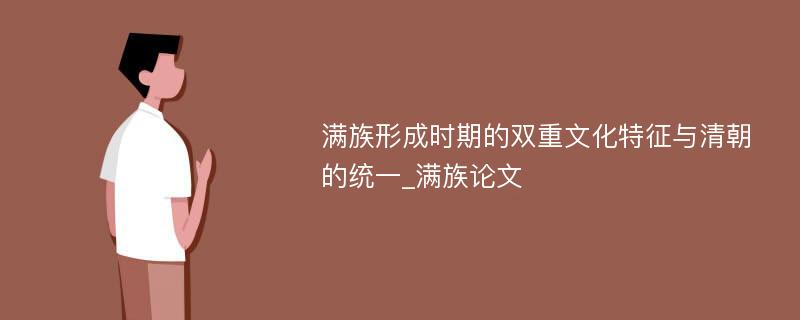
满族形成时期的二元文化特质与清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特质论文,时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满族共同体形成时期,具有鲜明的二元文化特质:既有崇尚骑射的游牧文化,又有筑室而居的农耕文化,这两种带有排斥性的异质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却有机地统一在满族共同体内,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相互吸纳、作用。满族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对清朝的统一,以及入关后对广袤疆域的长期有效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英国文化学家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又具有流动变异性的特征。前者使一种文化与他种文化相区别,后者又使文化之间有沟通性。〔1〕满族形成时期的二元文化特质及其演变, 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满族早期发展史上,游牧文化的特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游牧文化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二是精骑善射,崇尚武勇。这两个特征在明代以前的满族先民身上,表现得都很充分。《元史·地理志》记载:“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真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廓,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元朝政府曾对女真居住区严弓矢之禁,造成女真人失业,产生“怨望”情绪。〔2〕达达指蒙古族鞑靼部,这里将女真与达达并称,可见元代时女真族仍无定居生活,而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另一特征,《满洲源流考》的作者在叙述满族“国俗”时讲得更为清楚,文中说道:“自肃慎氏矢石,著于周初,征于孔子,厥后夫余、挹娄、靺鞨、女真诸部,国名虽殊,而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莫能或先焉。良由禀质厚,而习俗醇,骑射之外,他无所慕,故阅数千百年,异史同辞。”〔3〕这就是说,满族的先民们在历经二千余年的治乱沧桑里,作为游牧文化基本特征之一的崇尚骑射的风俗依然不改。
然而,到了明代,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满族的先民——女真族的游牧文化特征开始发生变化。这主要是他们“逐水草而居”的特征逐渐消失,已逐渐走向定居时代。而游牧文化的另一特征——精骑善射的勇武精神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却得到强化。因此,以后满族(及其先世)的游牧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骑射文化的发展上。换言之,骑射文化归属于游牧文化中,骑射文化的发展及存在使满族仍具有游牧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由于女真族的生存环境各不相同,各部族的文化特征也不尽一样,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满族及其直接先世的一般状况。
早在明朝初年,建州、海西女真已对狩猎(骑射)生活表现出厌倦心理。洪武二十八年(1395),辽东卫镇抚张能说:“三万卫所属女真归附者,常假出猎为患”。〔4〕以“出猎为患”, 这说明女真人传统的“逐水草为居”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动摇。其中,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变化更多,只有野人女真“惟以捕猎为生”。〔5〕女真人在村落里营造了很多“庐室”。“自汤站(汤山城)抵开原,曰建州、毛怜、海西、野人、兀者(赫哲),皆有庐室,而建州为最。开原北松花江者曰山寨夷(哈达),亦海西种类。又北抵黑龙江,曰江夷,但有室庐,而江夷为最”。〔6〕定居生活在女真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此后女真族已与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区别开来,而具有农耕文化的一些特点了。
尽管如此,骑射以及狩猎仍在女真族生活中占重要地位。正统十一年(1446),朝鲜平安道节制使朴以宁说:建州卫的婆猪江人每年于二月到五月,又从七月到十月“率以二十余人为群,皆于郁密处结幕,每一幕三四人共处,昼者游猎,夜则困睡”。〔7〕半个世纪后, 当朝鲜国王问建州三卫达生等三人“计活何如?所事何事”时,他们答说:“多储匹段布物,一人所有貂鼠皮可至三百余张”。〔8〕建州定国政以后,狩猎进而组织在牛录的形式中进行。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努尔哈赤鉴于过去围猎“每一牛录的人在同一个地方走,有的牛录的人直到回家也不能行到围底”,实行“十牛录合在一起,给一令箭行走,这样以来,每次围猎各牛录的人都能进入到围底二三次”。努尔哈赤还对围猎“制立禁约”,以此规范女真人的狩猎行为。〔9〕制定规章进行围猎,可见狩猎在女真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骑射也是如此。入关前皇太极曾指出骑射之于满族的重要性。他说:“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州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10〕衣冠服饰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皇太极强调骑射对满族的影响,也是基于这一认识。
清初,骑射成为八旗官兵考核的重要科目之一,它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命兵部尚书于春二月,角射而赏罚之。前期,都统、副都统率其属及部卒,习射于国郊,日一往。数日,兵部尚书监视,而第其上下:一卒步射十矢,马射五矢,步射中的七,马射中的三,为上等,赏以弓一矢十,白金、布帛各七;步射中五,马射中二,为中等,赏白金、布帛各五,无弓矢;步射中三,马射中一,为下等,无所赏;马步射或一不中,或两俱不中,则笞之。一佐领受笞之卒过十八,则佐领有不教练之罚,至夺俸。一旗满六百人则都统、副都统之罚亦如之。护军、先锋营阅射亦如马军之制。”〔11〕清朝统治者对八旗成员的最起码要求是:自幼即开始学习“骑射”,直至六十岁以上方能免试。
由于骑射在满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于形成了独特的骑射文化,表现在方方面面。如满族人若是生个男孩,便在门口挂一枝箭,祝福孩子长大成为一名好射手。孩子长到六七岁,就开始习武练箭。用榆柳的枝条做成弯弓,以荆杆的茎杆为箭头,用鸡翎做成箭羽。如果生个女孩子,就挂一根小红布条,表示吉祥,也象征着古代满族妇女骑马射箭的需要。因为女孩子从生下后,在她的胳膊肘、膝盖、脚脖子三处,要用四五寸宽的布带捆绑起来,以使她在长大时拉弓箭能保持胳膊平直,骑在马上腿的位置能保持端正。在婚丧嫁娶中也表现了浓重的射猎文化印迹。婚嫁的聘礼主要也是用于骑射的盔、甲、鞍革和弓箭。人死后,用弓箭陪葬。满族的一些舞蹈也再现了射猎生活,如早期的“庆隆舞”和后来进入宫廷的“杨烈舞”等都反映了这种情况。〔12〕
跃马弯弓,崇尚骑射是草原民族的一大特征,但在满族共同体内却完好地承继下来。天命五年(1620)十月十五日,一位朝鲜人李民宾在回朝鲜经婆猪江和万遮岭之间时,亲眼看到“六七十里之地,放牧马群,漫山遍野者,不知其几万匹”。〔13〕而男女老幼,个个精骑善射,更令李民宾大吃一惊,他记载道:“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少有暇日,则互率妻妾畎猎为事”。〔14〕再现了“马背上的民族”的奇异风彩。
二
满族及其先民不仅有精骑善射的一面,还具有农耕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如前所述,至迟到明代中叶,女真族的大部分已走向定居生活。而农耕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定居生活。可以说,定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
满族的先民很早就有了农业生产。北魏时的勿吉人“有粟及麦、菜则有葵”,“佃则偶耕”,〔15〕说明已从事种植。到了金代,女真人“皆自耕,岁用亦足”。〔16〕明初,女真人已是“半耕半牧”。永乐三年(1405)女真人十四户男女,并一百余人,由辽东迁入朝鲜国的吉州“务农”,因“节晚失农,每户一二人欲往旧居处,捕鱼资生”。〔17〕几十年后,女真人的农耕生活已相当发展。正统二年(1437)朝鲜金将等五人潜渡婆猪江,至兀刺山北隅吾弥府,“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而马则不见。”另有宋世雨等五人至兀刺山麓婆猪之东,也看见两户人家,男女十六人,“或耕或耘,放养牛马”。〔18〕一个世纪后,明朝监察御史卢琼在《东戍见闻录》中记载说:“建州、毛怜……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他还记载海西女真“俗尚耕稼”的情况。万历二十三年(1595),申忠一前往弗阿拉,沿途所见土地皆已开垦。从今新开河支流,经新开河中下游,浑河支流,富尔江支流,富尔江上游,苏子河上游到苏子河支流索里科河,“无墅(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19〕“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者仅得一石”,“秋收后不即输入,埋置于田头,至冰冻后输入”。〔20〕
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使女真族首领逐渐认识到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早在万历十二年四月,努尔哈赤就明确提出“粮石被掠,部属乏食”,必然导致部属“叛散”的危险后果。〔21〕天聪六年(1623年)后金因为分田不均,地薄民贫,粮用不足,认识到“积金不如积谷”的道理。〔22〕第二年,皇太极指出“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要求所有闲散官员,各往本牛录庄屯“劝垦耕”。他还批评抢掠成风,不注重农业生产的旧习,指出“以有土有人为立国之本”,民众“厚生之道,全在勤治农桑耳”。〔23〕同年,皇太极明确提出农业为“国之大经”的思想。他在阐述这一思想时说:“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24〕把发展农业与骑射习武列为同等重要地位,并为贯彻这一思想采取种种措施。
早在太祖时期,为使田土有足够的肥力,每年秋收后令各官“将千匹马牧于田谷”中,指令必须“耕月耕之”,“耕田勿迟”,不可仿照蒙古“耕田之月”。努尔哈赤还要求耕田要因地制宜,不要完全效法汉族“耕田二次”的做法,要按女真“旧习”,“拨草培之”。努尔哈赤还设“田谷通制”,以求遵守。〔25〕皇太极时期,为“专事南亩,以重本务”,下令城廓边墙,“有颓坏者,止令修补,不复兴筑”,并严禁滥役民夫。〔26〕他亲自观察民间耕种。他还提出“地尽其力,人尽其财”的思想,在女真地区推广代耕、助耕的耕作方法,充分利用了土地和劳力。〔27〕
对于耕作役使的牲畜,后金禁止买卖、宰杀。天聪二年皇太极告谕臣下说:“马骡以备驰驱,牛驴以资负载,羊豕牲畜,以供食用,各有宜,非可任情宰杀也。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买,所用牛马骡驴,永行禁止。如有违法禁用者,被家人及属员举首,将首人离主,仍照所用之数,追给首人,牛录额真及章京失察者,罚锾入官”,“至于诸贝勒大臣有牧牛多者,亦须节用,毋得妄杀。自宫中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止许用羊豕及鸡鹅鸭等物。明国及朝鲜蒙古之人,善于孳牧,以至繁盛。我国人民,既不善于孳牧,复不知樽节,过于宰杀,牲畜何由得蕃。今后务须加意牧养,以期蕃息。”〔28〕
后金对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也极为重视。天聪七年皇太极在阐明农业“为国之大经”的同时,着重指出加强农业技术的重要性。他说:“至于树艺之法,洼地当种梁稗,高地随地之所宜种之,地瘠须培壅,耕牛得善饲养”,“至所居有卑湿者,宜令迁移”。〔29〕崇德元年他又详细论述重视农业技术的重要性。他说:“至树艺所宜,各因地利,卑湿者可种稗稻高梁,高阜者可种杂粮。勤力培雍,乘地滋润,及时耕种,则秋成必获,户庆充盈;如失时不耕,粮从何而得耶。”〔30〕这些农业技术是行之有效的经验之得,对发展满族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为积累粮食,努尔哈赤还创设“谷库之制”。后金于万历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命每牛录出十男四牛,于空旷之地耕田,生产谷物,储入公仓,一时“谷库充盈”。〔31〕都城赫图阿拉东门外,“则有仑廒一区,共计十八照,各七八间,乃是贮谷之所”。〔32〕这是公库。至于各家则“五谷满囤”,甚至有“日暖便有腐臭”的情况发生。〔33〕
经过多年的努力,入关前满族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基本上达到了自给。一入其境,“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之属”,凡“禽兽、鱼、鳖之类;蔬菜、瓜、茄之属皆有”,〔34〕全然一派农家景象。
三
满族形成时期,兼具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两种特征,这种现象早已引起当时及后代学者的注意。明人瞿九思在所著《万历武功录》中,说女真人“颇有室屋耕田之业,绝不与匈奴逐水草相类”。〔35〕他的话是针对当时人将女真、蒙古混为一谈而发的。表面看来,女真人也以狩猎为业,驰骋草原,跃马弯弓与“匈奴”(即当时的蒙古族)无大区别。但瞿九思察微思巨,揭示出两者并不相同,因为女真人有定居生活,并有耕田农作,而蒙古族却没有这些。所以他还加了一个“绝”字,以揭示满、蒙两个民族之不同。
到了清代,满族人福格进而论述满族的生活习俗说:“满族之俗,同于蒙古者衣冠骑射,异于蒙古语言文字。满州有稼墙,有城堡世居之民;蒙古则逐水草为行国,专射猎而无耕种也。”〔36〕福格的这段话,进一步揭示了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其骑射、服饰与蒙古相同,但蒙古逐水草为居,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满族则定居生活,且实行耕种田地,这又和中原汉族无异,属农耕文化范畴。
满族文化兼具游牧、农耕两种文化特质,这种表面看来奇特的历史现象,却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既具有相排性,又具有亲缘性。前者是指两者在语言、社会结构、家庭关系、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风俗习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具有相互排斥的属性。但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亲缘性:游牧民族的生存发展条件,或者说其财富的获得主要依靠两个方面——游动的牲畜群和固定的牧场和水源,他们必须把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业生产者两者的适应性潜力结合在一起。像狩猎采集者那样,他们必须了解自己领土的潜力,以确保牧草和水的不断供给。同时,他们又像早期农业生产者那样,牲畜群把一片草地啃光后,必须让土地休闲,直到牧草自己又长出来为止。换言之,游牧民族的“游动性”或“逐水草为居”是有规律、有目的、有限度的。从根本上讲,各种文化类型的民族,都是依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有效利用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这也是世界各不同种族、部族能和平相处,互相吸纳最终使人类走向大同的“自然”依据。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主要差异之一,即“游动”与“定居”的区别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前者的“游动”是有范围、有目的的,这如同农业生产者在耕种时要考虑尽地力是一样的道理。游牧民族的“游动性”说到底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
文化除具有亲缘性的特点外,还具有变异性,即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变异、演化。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环境因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文化的变异和演化主要是人类生活对物质状况适应的结果。劳动力的分工、地域群的大小、稳定性及其空间分布、居处规则等生态适应问题会敏感地作用于文化;而气候的季节性、水源的便利性、土地的肥沃程度等这些生态压力因素的调适又可以决定群体(民族)的大小、群体(民族)的持久性、群体(民族)分布的情形以及群体(民族)人口如何组织生产活动等社会结构。这些社会结构上的影响由文化加以分化,促成那些与生态系统并无直接关系的领域的变异,如世界观、政治继承模式和宗教艺术等。西方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类似的环境中使用类似的技术应产生类似的生产劳动力安排和分配形态……接着又产生类似的社会群体,并经由类似的价值和信仰体系来支持、协调其行为。”〔37〕这里,至少描述了生态系统和社会结构与文化变异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
满族在其形成过程中,正是遇到了比他们更为成熟、发达的农耕文化,这促使满族文化迅速发生演化。明朝初年开始,至嘉靖中叶止,历时一个半世纪,这是满族先民——女真人的迁徙阶段。这一阶段的迁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大部落集团形式,较大规模地迁徙;另一种是各种女真零散南迁。这种迁徙固然有受到其他部落攻击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其“游动性”的游牧文化因素在起关键作用。同时,尽管迁徙时间、规模、方式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方向一致,尽皆南向,接近或进入农耕文化圈。
嘉靖中叶以后,女真族大多数走向了定居生活,迁徙活动基本停止,它们沿着辽东东北边分散聚居,建州三卫分布在抚顺关以东,海西四部散居在开原以北。建州和海西南迁后,吸取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农耕文化的特质在女真族中越来越浓重。由于广大汉族人进入女真地区传播农耕技术,由于互市贸易,以及明政府的民族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女真族的农业生产向前迈了一大步。
万历到崇祯时期,即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是满族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女真族及后金政权在政治、军事上很明显是与明政权相对抗的,但在经济、文化上前者更向后者靠近了。从地缘上看,后金、清已完全进入农耕文化的氛围,对汉族先进文化及生产方式的吸纳变得更为迫切及直接了。满族形成时期的文化演变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环境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四
一般而言,单一文化特质的民族从比较优势上看总是有缺陷的。游牧文化的勇武精神虽值得称道,但缺乏稳定性,内部组织结构不严密,对部落(民族)的约束力差等不能不说是缺陷。同样,农耕文化的田园诗般的稳定性,人们安居乐业,社会成员的控制性强等方面都是优势,但过于脆弱,缺乏活力,也是不完美的。
满族形成时期兼具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二者的长处,共同溶铸于满族共同体内,这就使它能够应付来自这两种文化的挑战。笔者不能对中国整体文化进行分类,但就满族而言,它在入关前后主要遇到的是这两种文化类型及其民族。
就客观条件而言,无论与南明政权比,还是与李自成的农民军比,满族的力量欲统一中国是很困难的。其人口少,生存环境差,粮食很难自给,这些困难是南明政权及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没有的。但以后的历史结局是:后金、清政权统一了中国。这一历史结局促使我们从多视野去分析其“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满族及其政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一个很小的部族发展起来并建立自己的政权,进而统一中国,文化的因素实在不容忽略。
清入关前的两位最高统治者,其浸透在强烈的民族意识中的文化意识是很浓重的。
女真人口很少,所谓“女真遗种,本自无多”〔38〕,根本不适应大规模对外战争的需要。因此,努尔哈赤在起兵初期,就采取“树羽翼”政策。即“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州部落人一”。为什么?史称:“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廓土著、射猎、习俗同”,〔39〕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同根。
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统一东北的事业中,俩人皆以种族相号召。在统一黑龙江流域时,皇太极多次劝谕那里的人民“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40〕使统一局面不刃而得。
在统一东北的战争中,蒙古是天平中最关键的法码。为争取蒙古族的同情、支持,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竭力在满蒙两族间寻找共同点。天命四年(1613)六月,努尔哈赤致书五部喀尔喀诸贝勒时,一再申明汉族与朝鲜族“语言虽异,而衣着相同”;满族与蒙古族“语言虽异,而衣着皆同”,试图说服喀尔喀五部站在后金一边。不久,在复察哈尔林丹汗书中,再次重申满蒙“服发亦相类”的意见。〔41〕天聪五年(1631),为招服大凌河蒙古归降,皇太极令属下射入城中的招牌书,竟称满族、蒙古“原系一国”。〔42〕
从历史上看,满蒙地域相近,族众相杂,长期通婚,确有“族种相近”之处。史称海西叶赫首领的“始祖蒙古人,姓土墨特”,南迁时改称纳喇氏。〔43〕乌拉满泰、布占泰的族属亦来自蒙古,是“蒙古苗裔。〔44〕哈达部王忠、王台的族属与乌拉部同系。建州女真亦不“纯”是女真,首领李满住有三妻,而蒙古女居其二。〔45〕。万历三十五年(1607),努尔哈赤派“麾胡”三名至朝鲜,“说称我是蒙古遗种”的话,〔46〕当时并无讨蒙古欢喜之意,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满蒙两族间非同一般的关系。历朝政治家、军事家也认为,中原王朝得辽地,即可控制东北各族,而东北各族得辽地,即可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结论是辽地“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47〕同样,蒙古族之强弱,亦“系中国之盛衰”,〔48〕因此,后金戎马兵锋四十载, 直到天聪八年(1634)察哈尔林丹汗死后,统治者才大吁一口气,从此大书攻城掠地的情况。
由此可见,满族统治者巧妙地利用满族与蒙族在衣冠、服发、饮食、骑射等习俗文化上的同根性,顺利地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统一,从而为统一中国奠定基础。
其次,满族文化中的骑射文化特质是加速完成统一中国的重要因素。骑射文化崇尚勇武精神,这是满族由弱小部落逐渐发展壮大的文化因素。努尔哈赤、皇太极皆身经百战,冲锋陷阵在前,对鼓舞士气有很大作用。而且,满族在其兴起史上,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役,这也得成于其骑射文化的勇武精神。对此,《满洲源流考》曾有一段论述:“我国家肇造大东,敦庞之俗,弧矢之威,自古已然。恭考《实录》我太祖高皇帝以十三甲始申天讨,父问宏昭。乙酉年,哲陈之役,太祖率近侍三人,败诸部八百人。丙午年,斐优之役,我兵二百,败乌拉兵万人。至天命四年,萨尔浒之战,以我众数千,歼明兵四十万。明之宿将锐师,一举而尽。我太宗文皇帝服朝鲜,降蒙古,松山、杏山之捷,破明兵十三万,咸用少击众,一以当千。固由神武之姿出于天授,贤臣猛将,协力同心。亦我貔虎熊罴之士,有勇知方,骑射之精,自其夙习,而争先敌忾,气倍奋焉故也。”〔49〕如果抛开这段话的夸张成份,大体是可信的。
再次,骑射文化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有积极作用。自唐代以来,中央政权在加强集权、贯彻“重内轻外”治国方策的同时,冗兵积弱的弊端越来越严重,有明一代在边防上一直处于守势。清朝建立后,中央对地方尤其是边远地区实行有效治理的同时,中央的辐射能力更强了,疆域更加巩固。清前期的几个皇帝,如康熙、雍正、乾隆,不仅个人武功高强,而且每遇边疆叛乱,皆“御驾亲征”,尤其是乾隆帝,以“十全老人”自诩,平生陶醉在“十全武功”中。西方的船坚炮利东来前夕,近代思想家魏源在他所著的《圣武记》一书中,还十分赞赏清朝历代所取得的“武功”。
同时,由骑射文化衍生出来的“肄武绥藩”的木兰行围,更具有意义。据统计,从康熙二十年(1681)开设围场起,直到道光元年(1821)停止行围,大约140余年间(雍正帝未举行木兰行围),很少间断过。康熙年间行围48次,乾隆年间28次,嘉庆年间15次,总计91次,平均一年半举行一次〔50〕。行围制度对维系满蒙关系起的作用,乾隆帝曾这样评价:“蒙古向重武事,予昔年在木兰围中,驰射发,武艺精熟,众蒙古随围数十年,无不知之。但今年既不行围,蒙古王公等不几谓予怠于肄武,因乘暇于山庄内,即鹿以试精力,而近日所中之鹿,皆系一发即中。及颁赐蒙古王公等,无不欢喜钦服。”〔51〕很显然,木兰行围绝不是例行“公事”,摆摆样子,它是满蒙两个民族在“重武事”上寻找共同点,也是两个民族的最高领袖在骑射文化上的交流,对巩固和加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纵观中国大势,周边少数民族林立,强大者也不乏其族。但只有北方少数民族屡次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一道长城,绵延万里,它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也证明了骑射文化的威力所在。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毫无疑问,它的天下是马背上打出来的。令人惊奇的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存在不足百年(指对全国的统治),而且其存在的这些岁月里,外族反抗,内部斗争从未间断过。与此相比,与蒙古族在文化上有更多亲缘关系的满族所建立的清王朝却维持了267年之久, 称得上是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之一。并且,晚清统治者所面临的“国际大气候”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不曾遇到的,即“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然而,它的统治仍延续了80年之久。这本身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笔者认为,如果从满族文化的另一特质——农耕文化这方面进行探讨,就会得到很多启示。
治清史者都为这样一种现象所困惑:明初承元末丧乱,仅用了10余年时间即完成了社会经济的恢复;清承明末战乱,却用了40余年时间恢复社会经济。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用满族文化二元特质来解释,似更恰当。自后金政权建立起,直到康熙初年止,后金、清的政策始终在摇摆、矛盾中实行。这种摇摆、矛盾的政策与其说是社会性质不同使然,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造成的。有的时候,农耕文化的特点突出,后金、清政权的矛盾、危机就小一些;反之,当骑射文化的特点突出时,会造成更多汉族的反抗。清初实行圈地,雉发所遇到的情况是明显的例证。笔者认为,随着全国统一政权的确立和巩固,满族的骑射文化特质逐渐淡化,其农耕文化的色彩反而越加明显,突出的标志是蠲免田赋。康熙自幼受汉族文化影响至深,懂得攻守异势、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守之的道理。亲政以后多次大规模蠲免田赋,除水旱灾害照例“全免”外,几乎“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康熙五十年(1711)开始,又实行“轮蠲”,即将全国各省分为三批,每三年轮免一次。据户部统计,康熙元年(1662)起,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止,不到五十年中,全部蠲免,“已逾万万”〔52〕乾隆帝继承乃祖的做法,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次全免南方漕粮,累计免赋银二万万两。康乾时期,多次大规模蠲免田赋,其原因正如乾隆所说:“朕思海宇父安,民气和乐,持盈保康,莫先于足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53〕这就是“藏富于民”的道理。史书上说清朝对亿万百姓“深仁厚泽”,并非是掠美之词,一个显见的道理是:多次蠲免钱粮,尤其是“轮蠲”,使全国不能同时处于一个贫困线上,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许多地区实现温饱。这就是清朝前期为什么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而这些,正是一个发达的农业社会才会出现的。
自康熙朝开始,最高统治者多次强调要振饬“国语骑射”,强化其民族意识及文化特征。但是,满族的生存环境已全然改观,骑射文化已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所谓“振饬”正是衰落的象征。从发展的角度看,骑射文化的衰落无论对于满族自身,还是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而言,都是一种进步。因为在当时这个小农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国度里,唯有农耕文化才具有更广泛、长期的适应性。
以上从大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满族发展、壮大、清朝统一以及对全国长期行之有效的统治等问题,有些认识不成熟,甚至可能是错误的。诚恳希望方家、读者指正。
注释:
〔1〕《文化论》,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2—13页。
〔2〕《元史·斡赤斤传》。
〔3〕《满洲源流考》卷16。
〔4〕《明太祖实录》卷239。
〔5〕魏焕:《皇明九边考》卷2《辽东镇边夷志》。
〔6〕卢琼:《东戍见闻录》,载《辽海丛书》第一册,第456页。
〔7〕《李朝实录》卷113《世宗实录》。
〔8〕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第11卷。
〔9〕《满文老档·太祖》卷4。
〔10〕《清太宗实录》卷32。
〔11〕金德纯:《旗军志》,《辽海丛书》本第2页。
〔12〕参见拙著《清代满族风情》第34~37页。
〔13〕李民宾:《栅中日录》。
〔14〕李民宾:《建州闻见录》。
〔15〕《魏书》卷100《勿吉传》。
〔16〕《金史》卷45—50《食货志》。
〔17〕《李朝实录》卷10《太宗实录》。
〔18〕《李朝实录》卷77《世宗实录》。
〔19〕申忠一:《建州图录》,载《旧老城》第16页。
〔20〕申忠一:《建州图录》,载《旧老城》第103页。
〔21〕《满州实录》卷1,第22页。
〔22〕《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45页,见《史料丛刊初编》。
〔23〕《清太宗实录》卷15,第8页。
〔24〕《清太宗实录》卷13。
〔25〕《满文老档·太祖》卷5,卷61,卷52,卷18。
〔26〕《清太宗实录》卷1。
〔27〕《皇清开国方略》卷24。
〔28〕《清太宗实录》卷3。
〔29〕《清太宗实录》卷13。
〔30〕《清太宗实录》卷31。
〔31〕《满文老档·太祖》卷3。
〔32〕《东夷奴儿哈赤考》页2上,参见《筹辽硕画》卷首。
〔33〕《建州闻见录》。
〔34〕《李朝实录》卷71《宣祖实录》。
〔3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1《王台列传》。
〔36〕福格:《听雨丛谈》卷1。
〔37〕[美]恩柏:《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38〕《李朝实录》卷33《仁祖实录》。
〔39〕《圣武记》卷1,第12页。
〔40〕《清太宗实录》卷21。
〔41〕《满文老档·太祖》卷10。
〔42〕《东华录》页6上《天聪六》。
〔43〕《清太祖实录》卷1。
〔44〕《清太宗实录》卷15。
〔45〕《李朝实录》卷57《成宗实录》。
〔46〕《李朝实录》卷208《宣祖实录》。
〔47〕《全辽志·叙》第1页。
〔48〕《蒙古游牧记·序》第1页。
〔49〕《满州源流考》卷16。
〔50〕李秀春:《木兰围场三百年大事年表》。
〔51〕李秀春:《木兰围场三百年大事年表》。
〔52〕《清圣祖实录》卷25。
〔53〕《清高宗实录》卷242。
标签:满族论文; 努尔哈赤论文; 满族文化论文; 满族服饰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满族风俗论文; 明朝论文; 女真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