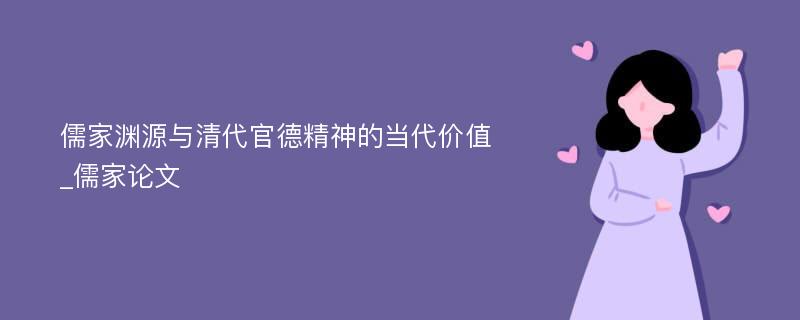
清官精神的儒学渊源与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官论文,儒学论文,渊源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提出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将这一方略正式写进宪法,法治成了法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在关于法治的讨论渐达高潮时,适逢最受中国普通百姓崇敬的古代清官包拯(公元999年~1062年)诞辰1000周年。 对包拯的纪念不能不让人在古代清官和现代法治之间产生某种联想。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问题最多、最不能让人满意的是执法,而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清官享有执法如山的盛誉;司法腐败遭受的批评越来越多,而历史上清官恰恰专门惩治贪官污吏;我们设计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蓝图(其中有借鉴西方法治观念、模式的成份),而在中国普通百姓中,清官文化的影响力却远大于由学者们从西方引进的法治观念,我们能否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等等。这诸多的联想促使我们探讨清官精神,探讨清官精神的文化渊源及其在当代的价值。以下的讨论或许是肤浅的,但所提出的问题却显然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一、清官特点与清官精神
清官的光辉形象主要不是由包拯、海瑞等历史人物自己造就修炼的,而是由宋、元以来历代中国百姓通过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塑造出来的。清官人物的特点主要不是记载在有关历史人物的本传里(虽然许多清官形象是以有关历史人物的个人事迹为基础演义出来的),而是表现在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形式中。由社会加工出来的清官具有以下特点:
1.不贪恋官职和富贵。海瑞就是为了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的好官,曾被下狱治罪,被革职罢官,闲居十几年。(注:《明史·海瑞传》)要做清官就得能舍弃功名利禄,就得随时准备丢弃官职和朝廷俸禄。那些为了保住官位,为了爬上更高的职位而不惜出卖良心、唯上司之命是听、专看皇帝或上司的脸色行事的人,绝不可能成为清官,他们只能是孟子笔下的“妾妇”。(注:《孟子·滕文公下》)
2.爱护百姓,为民请命。狄仁杰为宁州刺使期间,宰相张光辅率兵讨伐反叛者,军中士卒恃功危害百姓及投降的兵士,而宰相不仅不阻止,反纵其杀戮。狄仁杰不顾一切地前去阻止,斥责宰相“纵邀赏之人,杀降以为功”,使“无辜之人咸坠涂炭”。(注:《新唐书·狄仁杰列传》。又,清官本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但在清官出现之后,人们又把清官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段。在今人的心目中,狄仁杰与海瑞、包公等一样都是清官。清官本为社会所创造,故从俗。)包拯任开封知府时,因开封权贵争相在惠民河岸边修建楼台亭阁,致使汛期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危及百姓生计,包拯为了全城百姓的利益,下令拆除河道内的所有建筑,派人疏浚河道。对私改地契以河道内土地为自己所有为由而妨碍排洪者,他便毫不留情地上奏弹劾。
3.不畏权贵。法律制定易,实施难,而实施之难不在百姓,而在权贵。(注:商鞅“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之论对后世人有广泛影响,也许更为清官们所熟悉。)权贵者有权在手,别人违法深究,自己犯法不问;权贵者有钱,在权力鞭长莫及时便可用那能使鬼推磨的钱买通“现管”之官,逍遥法外。权贵者或有权或有钱或既有权又有钱。他们相互间既可进行权钱交易,也可进行权权交易,还可权权、权钱一起交易。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要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就必须追究权贵的违法,就必须敢于对违法的权贵用法。包拯七弹国戚张尧佐就是清官不畏权贵的显例。
4.明察。他们既敬业,又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包公案》、《施公案》等小说中的许多故事虽有些离奇,但作者们编出这许多故事无非是要赋予他们理想的清官更神奇的办案能力。海瑞初任淳安知县,就是因为其查验尸体、识破诬告假案才名声大振。人们绝不会爱戴总办错案、在公堂之上总是颠倒黑白的官吏。这种官吏也有一个称谓——昏官。
许多昏官之所以常常错判错杀人犯,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自己不具备办案的专门知识,而具体的审判活动和定罪量型又受刀笔小吏左右。杨乃武案一开始如能弄清葛品连不是中毒身亡,便不会出现后来的一错再错,不会出现会审大员明知有错而故意掩盖原判错误等情况。明、清时期官场腐败,司法不公,刀笔吏的舞文弄墨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作用。
5.无私。对清官最确切的评价是铁面无私。包公在法律面前不徇私亲,能够对自己的亲属依法论罪。清官不是别的什么显赫的头衔,而是在法律与个人的或家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舍私而为公的人,能够抛弃私利而守法的人。
对由社会所塑造的清官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提炼出清官的精神。我们认为清官精神有如下三点:守道、爱民、无私。
其一,守道。清官的不贪恋官职和与官职连在一起的富贵,并不是因为他们已修就了视富贵如浮云的仙风道骨,甚至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他们都是常人,他们也接受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把做官作为自己谋生的基本手段,也都希望能通过为朝廷出力为自己换来光宗耀祖的好名声。他们之所以能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舍官职的选择,或者在明知会丢掉官职的危险时刻仍痴心不改,是因为他们内心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有一个对他们更具有规范意义的尺度。有些清官直接面对皇帝或者皇亲国戚,不惜触及龙鳞,惹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发怒,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视死如归,希望早日踏进彼岸世界去享受极乐的生活,而是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高于自己命运和自身幸福的价值目标。清官心目中的那个更高的原则和价值目标就是孟子所说的道。(注:《孟子·尽心上》)
守道高于守法,守道比守法更难。对于执法者来说,对法律的忠诚具体表现为对职业和岗位的忠诚。官员的守法精神表现为依法处理自己权限范围内的各种事务,绝不贪赃枉法,决不纵容坏人、冤枉好人。守道者不仅要尽到职业上的义务,不仅要按照法律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且追求对违法行为的真实制裁和对合法利益的切实保护,不论其是否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不管自己是否有那么大的能力管。当案件交给上司之后,当上司已依据其权力对案件作出处理之后,这个下级官员的守法任务已经完成,但其守道的任务却没有完成。当一定的法律事务已上报给皇帝之后,尤其在皇帝已经有了自己的处理意见之后,守法者已无事可做,但守道者却要继续对案件的最后处理结果负责。守法者和守道者都维护法律,但前者用的是职务,而后者用的是生命;前者的工作做在职权之内,而后者的工作常常做在其职权之外;前者依靠的是权力,是国家给予的公权力;而后者依据的是公理、是正义,是广义上的责任。守法者做的都是应当做的,不那样做,他们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守道者做的不是职务上要求必须做的,如果只是为了领薪水,他们完全可以不那样做。守法者更为重视的是程序上的责任和正义,而守道者更关心的是实质正义的实现。
其二,爱民。清官是官,但清官形象是百姓塑造的,不是官员们塑造的。在我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国家管理活动中官与民之间关系中的官强民弱现象十分明显,而这种状况决定了在非管理领域中也存在官强于民的状况。有些官把在管理领域中的优势运用到非管理领域,用国家赋予的管理权来支持自己的私人权利,运用这种得于国家的优势地位与百姓相对抗,这样便形成在管理领域之外的官压迫民的局面。比如,在诉讼领域内,有官身份的人和无官的百姓之间本应是平等的,但一些有官身份的人把自己受之于国家的公权力用作争取胜诉的筹码,造成“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或“有理无权莫进来”的局面。在官和民、权与理的矛盾面前,清官站在民和理这个方面。他们始终以爱民为己任,不是千方百计地找百姓的毛病,倒是对做官为宦者在鸡蛋里头挑骨头;他们不是蓄意偏袒有权之家,而是或多或少地照顾细民、弱者的利益。他们为民请命,替百姓伸张正义。
在一个官僚统治的社会,官强民弱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总体的社会关系失去了必要的平衡。官吏对权力的滥用和公权力对私人利益的侵夺与对正常法律关系的破坏,不断造成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官民之间的冲突。清官实际上是民间创造的一种平衡官民关系的角色。如果说监察官是皇帝、朝廷创造的平衡官民关系的调节器,那么清官则是百姓们希望的并以小说、戏剧等方式创作出来的官民关系的调节器。如果说监察官系统是皇帝设置的具有制度意义的调节器,那么百姓没有能力改变国家的制度,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设置制度性的调节器,他们只能在文学作品中、在舞台上创作、描绘他们所希望的没有制度意义的调节器,并希望所有官员、所有有望担当公职的知识分子或其他人在担任官职时都能像清官那样为民、爱民。社会所设计的这种调节器不是以制度的力量实现对官民关系失衡的矫正,因为清官不是一个新的制度系统,而是社会加给国家设置的官员的一种品格。这种品格与任何具体的人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与任何具体的机关系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这种调节设计并不必然有效。虽然百姓无法创造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具有制度意义的调节系统,但清官这种调节器却使百姓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百姓创造的清官,其使命就是扬民而抑官。这种清官产生于官僚社会,清官的爱民精神也产生于官僚社会的土壤中。
其三,无私。站在清官对面的是贪官。贪官的突出特征是自私,是私欲膨胀。清官的精神是无私。他们在职务活动中不为金钱、官位、美色等所动,这是无私。他们为了公正执法不贪恋官职和富贵也是无私。他们为了百姓的利益不惜与自己的上司甚至与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拗着劲干更是无私。没有无私的精神就没有清官。
无私不等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清官的无私首先是一种职务的无私。他们并不拒绝接受他们的职务所应获得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待遇甚至特权。这种无私就是在履行职务所当得的利益之外绝不谋求非分的利益。这种职务上的无私或许只能算是对守法者的要求。清官的无私还是守道的无私。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自己心目中的道联系在一起,在道需要的时刻或者按道的要求已无法履行职务时,他们便勇敢地抛弃职务上属于他们的私利,也包括职务本身,甚至自己的生命。
二、清官精神与儒学传统
我们可以在儒家学说中找到清官精神的主要思想渊源。
1.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注:《孟子·滕文公下》)这是孟子从政的原则,也是一切仕进者的龟鉴。士大夫应当有自己矢志不移的政治信念,应当有做人为官的原则,应当有为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做人原则而献身的精神。作为儿子,即使无米下锅,讨来剩饭也不忘先敬父母;作为将领,即使身陷敌营,只要一息尚存,也不应忘记报效祖国。同样,抚民受职的官员在执行职务时,即使遇到上司甚至皇帝阻挠的情形,也应坚守职务自身的要求,为一定职务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社会利益而献身。
为官者坚守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气概,就一定做清官。清官的守道精神就来自于孟子的这种大丈夫气概。中国的百姓熟悉这样的气概,他们希望政府的官员在面对贪赃枉法的上司和昏庸无道的皇帝时能够有这样的气概,他们希望在他们遭受来自官宦权贵的非法侵害时能遇到有这种气概的好官。清官的守道精神就产生在“亚圣”的大丈夫气概中,就产生在百姓对这种主要应当表现在官员身上的大丈夫气概的需求中。
2.孟子主张,(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注:《孟子·万章下》)他所阐扬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注: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的观点等,也都赋予臣以政治上的独立性。)他讨厌的是逆来顺受、惟命是听的“妾妇”之道。孟子的谏诤之论及其他儒家思想家的谏诤论给清官的刚直不阿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官员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精神,就只能唯君命或上司之命是听。唯他人之命是听的人其内心没有自己的道,这种人缺乏成为清官的起码条件。在政治实践中,只会服从、迎合的官员不可能担当矫正政治偏失的重任,他们只能维护、加强封建社会中官强民弱的格局,使基本政治关系的失衡更加明朗化。这种没有独立精神,以迎合上司为能事的官员也不可能是私的清官。因为他们的迎合就是对国家、百姓没有责任心,就是自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是清官最基本的观念支撑。古代言吏治者强调出于正途的士大夫与刀笔吏的区别,那是因为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大夫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他们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非正途出身的官吏没有接受过儒家学说的正规教育,他们没有品行,其行政选择的原则往往是“有奶便是娘”、“无利不起早”,其行为的特点是善于察(上之)言观(上之)色,随时准备逢迎拍马。
3.孟子学说服务的对象是天下,他在政治上关心的主要是作为基本社会成员的民,因为他认为天下的根本是民。不管是他的民贵君轻论,还是他的暴君放伐论都集中体现了民本主义的要求。(注:参见拙作:《“民贵君轻”论辨析——兼论孟子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 )这种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现在政治实践中就是爱民、利民。在孟子的政治学说中服从(上司和皇帝)不是第一位的,保民、爱民才是第一位的。按孟子的学说,一切投身政治的人要守的道首先就表现为对民的爱护。并且一切投身政治的人的无私也首先表现为不能以己之利害及百姓,在百姓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上级的利益甚至君王个人或家庭的利益的矛盾面前,应当先照顾民的利益。清官的爱民精神就来自于孟子的天下观和爱民观。
儒家的守道精神、爱民精神都可以导出无私的结论,但清官的铁面无私却难以在儒家学说中找到没有争议的来源。孔子所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注:《论语·子路》)虽指案件当事人,但毕竟明确了伦理重于政治的基本态度。孟子让身为天子的舜背负犯罪的父亲而逃,弃天下不问,遵海滨而处,(注:《孟子·尽心上》)虽然尊重了国家司法权,但仍然把个人之私置于国家之公之上。儒家学说揭示并进一步强化了伦理与政治的矛盾,而儒学的广泛传播和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又将儒学中伦理高于政治的思想倾向带给全社会,并由此而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这种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与为政者的亲戚无关的事务没有多少影响,所以,在一般的政治实践中,官员们可以是无私的,他们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纠正上级或皇帝的过错,他们可以不惜丢官,甚至可以无私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当政治实践中出现了自己的亲属,尤其是血缘亲属的利益与国家或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时,这种思想和价值观念便成为政治运行的障碍,由于它们的影响,无私的官员就会变成有私的孝子贤孙。
如果说清官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优秀的执法官,那么儒家文化传统实际上难以培养出这样的清官。虽然守道和爱民的清官精神有深厚的文化土壤,但铁面无私的清官却缺乏文化的有力支持。这便决定了儒家文化可以培养出最好的谏官、行政官,可以培养出君王的忠臣,但却难以培养出清官这样的执法官;决定了清官可以是违抗君命、抗拒上司的百姓救星,但却不是大义灭亲、在是非功罪面前对亲疏都一视同仁的公正裁判者。可以说“亲亲”的儒家传统是产生清官的文化障碍。
三、清官精神评价与其当代价值
当代学者就历史上的清官做过反复的讨论,评价清官的著述也屡见于报刊,(注:如:王思治先生有《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光明日报》1964年6月3日)、《关于“清官”、“好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64年7月9日)、《再论“清官”》(《光明日报》1978年8月15日)等文, 吴晗先生有《〈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光明日报》1964年6月17日), 潘仁山先生有《为清官昭雪》(《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冯佐哲等先生有《论“清官”的历史作用》(《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范明辛先生有《从海瑞看封建“清官”的本来面目》(《政法研究》1966年第1期)等。 )而这些载于报刊的著述对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清官及其历史作用等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今天,新的时代要求我们用法治的眼光重新审视清官精神。
1.清官的守道精神对维护国家的或社会的利益具有实质性的优点,因为国家不论设计怎样的制度,其最后的目的都在于寻求有关权益的实现、发达或对有关利益的实质上的保护。但在确定的制度下,守道不如守法更有利于维护法制所确定的秩序,更符合法治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在守道的题目之下,法律实施只是保护其他利益的手段,不是一定官员所要追求的目标。在清官的头脑中,最有价值的不是法律,而是法律后面的甚至与法律的某些具体规定相背的利益。清官是为国家、为百姓而奋斗的官员,不是为法律而献身的法律战士。这种清官精神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难以承认法律的至上性。其二,守道可能成为违反既定的秩序的理由。在为国家、为人民的旗帜下,守道者可以不顾由法律确定的秩序。既然最高的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人民的或国家的个别的、暂时的利益,那么为了这些利益而违背在根本上是服务于这些利益的法律,就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应当的。
道与法有时是矛盾的,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道自身因时因地而演进或生长出来的有时可能只是短时的要求与法律的稳定和规范的严格相冲突。在这种矛盾面前,政治家和法官应当取不同的态度——政治家从道,法官从法。政治家的从道不应表现为对既定法律秩序的任意否定,而应表现为按照法定的或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程序,让产生于过去的法律适应道提出的新的要求。法官的从法表现为以既定的法的实现为自己的目的,法不改,法官的选择也不改。
清官的守道精神不是法官应有的精神。法官如果不以守法为己任,而以守道为选择,那便意味着对法律秩序的破坏。曾几何时,警官、检察官、法官三家在一张桌子上搞“一条龙”作业,就是这种从道而不从法的典型事例。
守道精神不仅在实践中有可能导致对既定法律秩序的破坏,而且无助于法官群体形成不同于政治家的职业信念。
2.爱民精神对维护弱者的利益,遏制豪强权贵对普通百姓的非法侵害有其积极意义。但爱民精神在司法领域也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因为法治在司法领域中的要求是诉讼主体的平等,而不是差别对待。程序正义是与对任何人或任何群体的偏袒不相容的。正义对处分当事人实体权益的要求也是一视同仁的。在法律之外增加或减少任何一方的义务都是不符合正义要求的。
爱民精神的思想来源是民本主义,而民本主义显然与现代法治的精神不相容。按照法治的要求,法官不需考虑什么人民利益(指作为人民组成分子的个人的利益,下同),甚至不应考虑保护人民的或其他什么特殊群体的利益。他们所应考虑的只有合乎法律规定的利益。他们不是为某种特殊利益而存在或工作,而是为一切合法利益而存在和工作。他们既不是专门为政府或有权力的个人服务的,也不是专门为下层百姓或没有权力的人鸣不平的。他们要保护和实际保护的只能是法律要求保护的,他们要惩罚和实际惩罚的也只能是法律要求惩罚的。可以说为阶级、集团以及其他社会群体服务的法官不是法治下应有的法官。那些宣布为保护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工作的法官,终将成为法治的破坏者。
3.无私的精神与法治的要求相一致。作为法官,其在司法活动中的行为选择的唯一根据只能是法律,而不应是其他什么。他们在审判实践中既不能因上司的意思而确定用法的轻重,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而出入人罪。他们不仅不能用审判权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而且不能因自己亲属与案件有关或与案件一方当事人有某种特殊关系而上下其手。我们可以说清官的无私精神符合法治要求,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为了实行法治应当弘扬清官的无私精神。
无私的精神符合法治的要求,但这种宝贵的清官精神却又缺乏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传统的有力支持。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中国百姓所歌颂的历史人物中大义灭亲的清官极其少见。而这告诉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征途上,我们实际上要面临同“亲亲”观念作斗争的艰巨任务。如果人们相信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注意到,亲疏有别的传统观念是不易克服的法治障碍。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的人情案、关系案就是这种传统在新时代的变种,我们常看到的拉关系、托人情、批条子以及认同乡、攀校友、结拜兄弟、追踪战友等,实际上是延续这种传统的与时代发展方向相背的一种努力。
尽管清官精神的某些方面与法治的要求是矛盾的,但它对推进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也有其积极作用,我们不应忽视其当代价值。
第一,守道精神虽可能导致对既定法律秩序的违背,但守道者完全可以同时也是守法者,也就是说,守道者可以在守法的前提下谋求对道的维护。反过来说,法官可以对既定的法律不满意,积极谋求对既定法律的更改,但同时又坚决依据现行法办事。如果我们的法官都能严格依法办事,同时又都有守道的精神,那将有力地促进法制的完善,因为这些守道的法官们会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同时,积极促进对现行法的完善,以促使现行法更符合他们的道的要求。法官更需要的是守法精神,但对于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守法的法官们多一点守道的精神,似乎并不多余。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培养官员的守法精神而牺牲他们的守法精神,因为守道精神并不必然是恶,并不必然导致守法精神的丧失。只要我们的法官在执法时严守法律工作者的本分,那么他们在执法活动之外的政治家情怀对法治就是无害的。
第二,爱民精神中渗透着保民思想的成份,在爱民的概念中的民缺乏权利的能动性,这似乎是消极的。但是,官员们放弃爱民的口号并不意味着民的权利意识的自然提高。我们的公民缺乏权利意识,不能在法治建设中担当主角,不是清官文化拖累的结果,相反,清官文化是公民或臣民不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主宰自己的命运的结果。要想让公民们自己站起来,成为自己命运和国家的主宰,靠枪毙清官文化、消灭清官精神并不能实现。如果我们把清官作为一种文化来对待,那么,在当代它依然是一种既存的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在当代还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只要在社会生活中官强民弱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变,只要百姓事实上尚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清官精神就会活在百姓心中。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努力消除清官意识和清官精神,而是对清官精神做合乎时代的转换。如果我们的每一位法官或其他法律工作者,都能在工作中用爱民的精神帮助普通百姓树立权利观念和主人意识,鼓励公民主动地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用自己正确的执法行为让百姓品味依法保护自身权利获得成功的喜悦,那将极大地促进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
百姓的清官意识对法治没有积极作用,但这不等于官员们的清官意识也无助于法治的发展。百姓消极地等待“清天大老爷”的拯救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但这不等于官员们公正地对待弱者的司法活动也违反法治精神。我们完全可以把清官对百姓的爱变成造就法治下的合格公民的行动,就像我们为了让老百姓学会使用法律武器而开展普法活动那样。
第三,清官的无私精神无疑是有利于实行法治的。我国法制实践中出现的许多不良现象都与法官的自私自利有关,有些则是直接由法官的私心太重、私欲膨胀引起的。无私的法官不会是司法中的腐败分子。在讨论法制建设,尤其是在讨论克服司法腐败的对策时,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学界和国家也在制度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应当说搞制度建设是正确的,但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仅仅进行制度建设又是不够的。司法和执法的实践告诉我们,任何良好的制度都需要由具有相应意识的人来执行才能真正是良好的。只有良好的制度,如我们从西方引进的许多宪政制度,没有具有相应观念、素养的人,这些制度便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它们在实践中就会走样。如果我们注意到制度和意识之间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我们承认在我们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先进的制度与落后的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我们应较多地关心意识培养,尤其是法官的意识培养问题。
清官的无私精神可以成为法官的法治意识的文化支持,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把它作为我国法官这个特殊的职业群体的群体意识基础。
标签:儒家论文; 法官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法律论文; 光明日报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