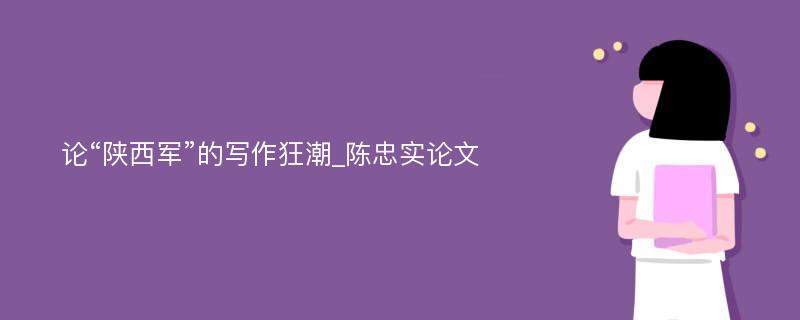
评“陕军”笔底性狂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狂潮论文,陕军论文,笔底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性是人的一种最自然的生命行为。“陕军”笔底性狂潮冲破禁欲主义的禁区,是文学的进步;但性描写应该有一个度,这就是:为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写,为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性格服务,尽量写得含蓄、侧重于性心理的、理性的、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面,使性描写趋于艺术化。
【关键词】 陕军 性狂潮 性描写原则
80年代中期,当一批又一批小说带着引人注目的性描写扑面而来的时候,人们惊呼那是一股强劲的“性冲击波”。惊呼之余,人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作为那“性冲击波”的最强波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它特有的哲学思辨的穿透力和对人性的不同凡响的探求,刺激了不同层面的读者的接受意识,引起了评论界的极为广泛的注意。从1985年10月到1986年9月,竟有四、五十家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0月,编印《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书,入选的文章就多达44篇。现在,九年过去了,当年那股“性冲击波”的势头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在“陕军东进”的几部小说里,竟然愈演愈烈,演化成了一股“性狂潮”。
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我们不能不对这几部小说涉性的问题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和研究。
一
在人类文明社会中,性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本能,也是一种最自然的生命行为。《白鹿原》、《热爱命运》、《最后一个匈奴》的涉性描写中,有着属于人的原欲的性冲动。白嘉轩连续七娶的新婚之夜,白赵氏精心设计的白孝义媳妇与兔娃的交媾,南彧和蓝桂桂舅妈在滂沱大雨里的短暂和谐,以及一直守着空房的灯草儿强要外出归来的丈夫杨作新交欢的神秘境界,等等,无疑都是性的本能冲动。本来,人的本性中,对异性的倾慕,性爱的渴求,情欲的冲动,无论从生理学还是心理学说,都是一种正常的生命现象。从人类得以蕃衍的角度看,恩格斯甚至还断言,性行为更是一种与劳动同样神圣的“再生产”。正因为如此,他曾经热诚地赞扬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说维尔特在作品里“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与肉欲”,正是他的长处。恩格斯在谴责了假道学的虚伪之后,还曾满怀热望地预言:“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羞怯心……最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①当代中国作家突破“性神秘论”的束缚,不顾封建式的禁欲主义设置的禁区,大胆涉性,应当说是我们的文学的一大进步。正如陈忠实所说,在《白鹿原》中,他“把性撕开来写”,这“不单是一个勇气的问题”,而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②我很同意这种见解。
问题在于,能不能因为性是人类生命的根源,就把性说成是人类社会的原动力,又是“艺术激情的根源”③?
我们看《废都》。《废都》里的庄之蝶空虚、无聊、消极、颓废,以至于濒临精神绝望的境界,作品让人觉得,似乎庄之蝶只有从女人那里可以找到出路,可以寻找到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小说里,唐宛儿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看得出来,我也感觉到了,你和一般人不一样,你是作家,你
需要不停止寻找什么刺激,来激活你的艺术灵感。而一般人,也包括牛月清在内,她们可以管你吃好穿好,却难以不停地调整自己给你新鲜。你是个认真的人,这我一见到你就这么认为,但你为什么阴郁,即使笑着那阴郁我也看得出来,以至于又为什么能和我走到这一步呢?我猜想这其中有许多原因,但起码暴露了一点,就是你平日的一种性的压抑。……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天性,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
……我知道,我也会来调整了我来适应你,使你常看常新。适应了你也并不是没有了我,却反倒使我也活得有滋有味了,你也常看常新不会厌烦。女人的作用是来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也便使你更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
这样一个唐宛儿,这样一番陈词,庄之蝶感动了,他于是告诉唐宛儿:
我觉得你好,你身上有一股我说不清的魅力,这就像声之有韵一样,就像火之有焰一样,你是真正有女人味的女人。更令我感激的是,你接受了我的爱,我们在一起,我重新感觉到我又是个男人了,心里有了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
事实相反,随着故事往前发展,我们看到,唐宛儿非但没有给庄之蝶带来艺术创作的常新力量,相反,以此为开端,庄之蝶除了替人写情书外,他那“好文章”实际上是玩了唐宛儿,又玩柳月,玩了柳月,再玩阿灿,终于成了一个肆无忌惮的纵欲者而不能自拔。庄之蝶走向了堕落。
这三个女人,并不像唐宛儿美化的那样,她们向庄之蝶“贡献”的不是什么“美”,而是自己的肉体,为的是去换取庄之蝶的“名声”,以满足她们浅薄的虚荣或获取个人的出路。而庄之蝶呢,他以自己的“名声”换回了女人们的肉体,以满足自己放荡的性欲。虽然不用金钱,这实际上也是在做交易,哪里有一丝一毫真挚的爱?!又哪里有一点一滴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呢?!有人说,庄之蝶和唐宛儿的结合,是灵肉的和谐。这不真实。如果他们两个人作爱是建筑在真挚的情爱基础上的,那么唐宛儿又怎么能教唆庄之蝶去占有柳月,而且还能容忍庄之蝶当着自己的面和柳月发生性行为呢?!性爱是排他的,性爱也常常都是要隐秘地进行的。庄之蝶似乎全都不顾了。当着唐宛儿的面,按倒了柳月,他哪里说得上对唐宛儿有和谐的爱?又有人说,庄之蝶和唐宛儿拉柳月下水,和《金瓶梅》里的情景酷似的这种群交,是为了堵住柳月的嘴,遮掩他们偷情的行径。好,要是这样的辩解也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庄之蝶在这之前和柳月动手动脚,百般勾引,在这之后见了阿灿就上床,又作何解释呢?庄之蝶私筑安乐窝“求缺屋”算是不打自招了!“求缺屋”,“求缺屋”,他求的什么“缺”?庄之蝶“求”的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和工具,那三个女人就是这样的对象和工具,这三个女人在那“求缺屋”里又“求”的是什么“缺”呢?她们求的是庄之蝶的“名声”,还有这“名声”带来的种种好处。要是说唐宛儿和庄之蝶的私通还有“灵”的一面,那唐宛儿的“灵”,就是不择一切手段去成为“庄之蝶的人”,使自己和名人挂上钩,荫庇在“名人”之下。
其实,《废都》,还有《骚土》,企图表现的这种性为艺术之源的见解,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只不过是弗洛伊德学说的翻版而已。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④换句括说,性欲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原动力,它可以决定一切。弗洛伊德显然极度夸大了性本能和性冲动的作用。
人类的社会活动,表现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三个领域,因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这三种生产的发展,缺一不可。人的性本能、性冲动是人的再生产的源泉和驱动力,但是,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再生产是其他两类生产的前提。当然,人类要是只有“性本能”、“性行为”,人类也就不能成其为文明的人,成其为文明的人类社会。要是只有“性本能”、“性行为”,和其他的动物群体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所以,我们不能用“性本能”、“性冲动”的作用来代替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所谓“性欲决定论”,完全排除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基因。弗洛伊德学说的这种偏颇,在当时就遭到了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反对。阿德勒认为,“决定个人思想、感觉和行为的不是性冲动,而是权力欲。”荣格以“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因素,修正了弗洛伊德夸大性欲和意识中的个人因素。杭妮也深信,“社会因素在决定心理症的性质上比性因素更具重要性。”⑤阿德勒、荣格、杭妮等先后脱离了弗洛伊德学派,而自立门户。在这里不想对阿德勒、荣格、杭妮的言谈行为说三道四,我只是想,阿德勒这些人在弗洛伊德面前都会独立思考,而不去盲目地跟着弗洛伊德误入理论歧途,为什么《废都》、《骚土》的作者反而不如人家呢?
弗洛伊德学说的根本错误,是排除了人的社会属性,只承认人的自然属性,即动物属性。当然,人的性本能,性行为,正是人最贴近动物性的一面。自从人类以自己自觉的社会劳动和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使自身发生质变,成为文明人而和动物区分开来之后,人类就开始了崇高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中,“性行为”能给人以惬意的快感,但并不占有唯一的或全部的超常地位。这是人类区别动物的一种质的标志,也正是人类发展史上超越动物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勿庸讳言,在我们的社会里,确实存在着那种无所事事而又有余力用“性行为”来填补空虚无聊生活的人,确实存在着那种悲观颓废又想以“性行为”安妥破碎灵魂的人。《废都》里的庄之蝶就是这样的人。《骚土》里的庞二臭、水花、针针等等,也是这样的人。然而,这样的人的性行为代表不了人类的基本面貌。唐宛儿治好了庄之蝶的生理性的“阳萎”,使之成为一个性功能健全的男人了,但她没有治好而且永远不可能治好庄之蝶精神上的“阳萎”。
有人问我:你说贾平凹等人是受了弗洛伊德的“性欲决定论”的影响,让庄之蝶去女人那里找创作的激情,而《废都》的实际内容又否定了贾平凹的初衷,这又怎么解释?
这很简单。因为,弗洛伊德的学说本身就是有毛病的。贾平凹按着这种学说写庄之蝶,根本就不可能把庄之蝶写成一个有创作灵气的作家,一味地沉湎于声色,专注地追逐于淫乱,他庄之蝶哪里有精力和才华去写出好小说来?贾平凹想要包装庄之蝶,或者想要包装自己的《废都》,结果,这“包装”不能不成了童话世界里的“皇帝的新衣”了!这该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说起来,想要按弗洛伊德的学说写性小说,老村的《骚土》更为张狂。《骚土》扉页题辞说到“性,不仅是生命激情的根源,也是艺术激情的根源。最好的艺术无不是性的最艺术的表现。”
结果,《骚土》写那“文革”的悲剧时代,就成了男女老少都沉湎于声色的时代,写那渭北黄土高原小村的风俗,就成了粗人细人都专事于淫乱的风俗,而且,一味追求“画云儿雨儿”,加之趣味、格调卑俗,手法、文字下流,他所谓“性文化”云云,就成了货真价实的春宫画了。
二
我在前面对《废都》和《骚土》作如是观,并不是说小说不能写性。性,既然是人生的一种现象,尽管它包含着生理的和心理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甚至非理性的和理性的两个侧面,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人生现象,无论如何,文学艺术都是可以去描述、去表现的。问题是在于,文艺作品对性怎么描述?怎么表现?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古往今来,严肃的而非色情诲淫的文学作品涉性描写,一直都有雅俗之分,高低之别。你说《金瓶梅》文字不洁,涉嫌诲淫,自然是事实,但那《红楼梦》又怎么说?贾宝玉神遊太虚幻景归来,不忘秦可卿一番缱绻情意,拉着袭人初试云雨之情,他曹雪芹就写得那么干净?但对《红楼梦》,除了封建卫道士斥之为“淫书”,人们对那性描写,又并无微词。又比如,鲁迅写《伤逝》,写到涓生、子君那一对冲破封建樊篱的男女,终于赁屋住进了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家庭,实现了他们的梦想。而同居生活的性爱,鲁迅只有一句“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这该是相当简约,相当含蓄的了。可是,茅盾的《子夜》写吴荪甫在书房对于女佣人,或者写赵伯韬在饭店对于交际花,文字那么直露,那么放开手脚,又该怎样评价呢?还有郁达夫写《沉论》,郭沫若写《咯尔美萝姑娘》,文字都不怎么含蓄。按陈忠实所说,要“把握住一个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⑥。那么,这个“分寸”应该怎么把握?
其一,要揭示出人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在他的《性心理学》一书中有一个论断:“要知性冲动有一个特点,和饮食冲动不大相同,就是,它的正常的满足一定要有另一个人帮忙,讲到另一个人,我们就进到社会的领域,进到道德的领域了。”应该说,选取“性”这一个特殊的侧面来揭示人和人之间复杂关系,作家是在努力揭开人性的另一层面纱。
《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与黑娃相知相爱,是从郭举人吃田小娥下身泡的枣儿写起的。作家在这里是在自觉地表现田小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她对现存秩序的反叛。在郭举人家,田小娥已然丧失了她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地位、权利和尊严。她充其量也只是郭举人用来强筋壮骨的一种工具,只是郭举人发泄性欲的一种工具。正如她自己说的,“连只狗都不如”!和黑娃相知相爱,进而偷偷作爱,都集中地强烈地表现了田小娥的人的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对于受苦受难的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然而,在中国,人的解放还没有完全彻底地实现之前,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此而言,陈忠实的《白鹿原》写田小娥和黑娃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就富有了文化的深层蕴含,即,蕴含着古老而又新鲜的反封建的意义。
既然性爱必须是要两个人共同去实现的,这种作为“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的“男女之间的关系”⑦,当然就是和人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了。这就必然要规范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这种规范就是道德。费尔巴哈就说:“性关系可以直接地看为是基本的道德关系,看为是道德的基础。”⑧一般说来,野蛮人追求的是感官的快乐,带有强烈的生物性、动物性、兽性;文明人追求的是灵与肉相融合的快乐,是人的自然属性升华为社会属性时对异性精神的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如此这般地写黑娃和田小娥相爱,大胆地描述他们之间的性心理、性行为,是具有现代意识的。
正因为如此,《白鹿原》里的芸芸众生,对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鹿兆鹏等人,由衷地佩服黑娃的勇气与果断,相比之下,还自愧不如,为父母包办婚姻中自己的软弱、动摇而后悔不已。白嘉轩、鹿三等人则恨之入骨,不仅把他们两人扫地出门,还下毒手杀害了田小娥,甚至人死了还不放过,还要置塔以镇之。《白鹿原》用长长的篇幅表现了这种道德观的对立,陈忠实留给读者的就是极为深刻的文化思考了。
应该说,这样的涉性描写,是在力图涵容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社会历史内容之外所表现的从生理到道德的审美追求。这样的写法是应该肯定的。
其二,为推动情节发展,为刻画人物性格及其发展而服务。
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逼真地、大胆地写了鹿子霖乘人之危,协迫田小娥就范时的性心理性行为,既刻画了鹿子霖的贪婪狡诈,又表现了田小娥的纯真以及为营救黑娃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允许的。相反,《废都》离开了以周敏等人的笔墨官司为线索的故事情节,写了作为人大代表的庄之蝶在会议空隙时间,和唐宛儿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床、交媾,绝不是什么“出于人物的需要”,而是通过这种挑逗性的、诱惑性的场面,达到某种商业目的。其后果,只能让人感到作者审美趣味的低下,小说文化品格的低下。
所以,离开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的需要,为写性而写性,或为其他什么目的而写性,都是不可取的,应该加以反对的。
其三,要写得含蓄。
古往今来,文学作品涉性描写,一般地说,总以含蓄、婉转为上乘,总要避免直露、粗鄙才好。问题是,含蓄到什么程度才合适呢?又如何去把握这个“度”呢?
前已说明,人的性行为具有二重性,它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既是非理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有人的自然属性一面,又有人的社会属性一面。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文化现象就包含着这一个又一个二重性内容。恩格斯早就说过:“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欲望,因此,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或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⑨
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不能是人的种种生活的自然主义的抄录,所以在描写人的性行为的时候,作家应该更多地,或者主要地写性心理的、理性的、人的社会属性一面。我们的文学创作不应过分地突出和夸大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动物本能那一面,更不能孤立地写人的那种性本能、性冲动。事实上,那是在写兽性,而没有写出文明人的真正的人性来。所以,有人说,“性”在文学中只是绘声绘色的性的展览,那就不是人性的高扬,而是把人性降为兽性了。
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写康妮和梅勒斯的性爱,着重写的是他们的情爱,写的是梅勒斯叹服于康妮的女性的体态美。有一个细节是,梅勒斯从大雨中把康妮抱回屋里,让康妮静静地躺在床上,他用芳香沁人的鲜花一朵一朵地放在康妃裸呈的身体上。那情景给予人的是美的享受:花美,康妮更美!
《白鹿原》里的鹿兆鹏和白灵特别的新婚之夜,写得情深意切,爱意绵绵。作家把这一对青年男女交欢的情景,升华为人类最真挚的一种情爱美了。
这样看来,所谓“深度”说也就站不住脚了。
有人受到弗洛伊德“深层心理学”的某些影响,误认为只有表现人的潜意识、性本能才最显示出作品中人物的深度。其实不然!人类的精神发展的进程,总是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的。人类意识层次中的原始的、混沌的潜意识,所具有的理性因素,文化蕴含是最淡薄稀少的了,它永远也不可能是人的深层的本质。如上所说,专门描写人的动物属性,挖掘所谓的性本能、潜意识,其结果只能是一批毫无意义的充满生物性的作品。
其四,是使性描写不断趋于艺术化,美化。
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对生活的超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离不开“真”。只是,在“真”的基础上更要升华为“美”。对于文学艺术,如果只有真而无美,那就要失去文学艺术的生命。所以,“性爱一旦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它就应该成为艺术美的一种形象体现,给人以美感。即使描写淫邪之徒丑恶的性心理、性生活,也要成为一种艺术美的形象体现。”⑩
在这方面,《热爱命运》的性描写算得上是比较美的。《热爱命运》的性描写或者说性欲形态艺术化,有三种情况,即:一种是为性欲、性冲动蒙上一层艺术的轻纱;一种是着重描写性的心理体验,富有文化蕴含;另一种是直观地再现男女性特征的美。
应该说,从生命繁衍的意义来看,人的自然属性表现为两性的交媾乃是根本的、终极的行为。等到社会进化,人已成为文明人的时候,人类的思维发展到达相当高的水平,这时人才有了对异性性特征形象的审美欣赏。所以,“描绘性特征实际上是更高一级的文化层次。以性行为内容的动态艺术倒是便于人们理解,而以性特征为内容的凝态形象则更有利于人们审美心灵的体验,审美理想的驰骋,启迪读者的丰富相像,净化人们性的审美的情趣。”(11)
这,并不是每一位作家、每一部作品都能做得到的。在“东进”的“陕军”里,就显得如此良莠不齐,我们期待着作家的努力。
注释:
①恩格斯:《维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1883年5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②⑥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③老村:《骚土》,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④见《精神分析引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⑤见《精神分析入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
⑦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务馆1984年版,第52页。
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页。
⑨陈丹晨:《文学与性刍议》,《文艺报》1986年11月27日。
(11)曾庆瑞:《揭开人性的另一层面纱》,见《竹林小说论》,台北智燕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