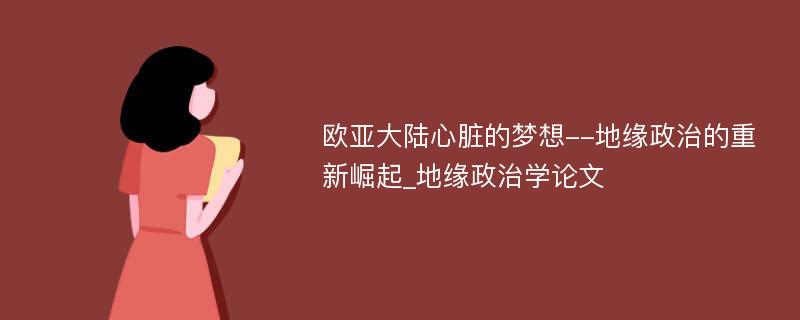
欧亚心脏地带的各种梦想——地缘政治学重新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论文,地缘政治学论文,心脏论文,地带论文,梦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乎没有哪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像“地缘政治学”理论那样,奇思怪想以致无所不容,罗曼蒂克以致晦涩难懂,聪明耍尽以致粗疏难免,并且可能引发一场第三次世界战争。
地缘政治学,因一位行为怪癖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 ( H.Mackinder )爵士而于20世纪之初流行起来;它假定,全球将永远被分为两个天然敌对的领域:陆地和海洋。在此模型中,全球陆权的天然储库是欧亚“心脏地带”——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麦金德描写道:“无论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将永远寻求控制欧亚大陆并且最终控制世界。”
令人毫不惊讶的是,这一地缘政治学理论在心脏地带自身也一直备受关注。今天,受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地缘政治理论拥有了一班趋之若鹜的热心人。众多俄罗斯英才,他们曾经认为其祖国对世界的胜利应是历史的不可避免的结局,现在将俄罗斯回归伟大殊荣的希望寄托于一种理论,即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的学说。现在,胜利将发现于地理学,而不是历史学;于空间,而不是时间。
当今,俄罗斯经济危机使举国久受其苦的人们变得激进起来时,一种被唤做“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已成为俄罗斯“红—褐”联合阵线——极左派和极右派政治家联盟,他们控制了近半数的杜马(俄议会下院),而且日见壮大——的共同焦点。
欧亚主义以较温和的面目出现时,强调俄罗斯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俄罗斯不需要西化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但在其强硬路线的看法中,这场运动把欧亚心脏地带视为发动一场全球反西方运动——其目标就是从欧亚把“大西洋”(读作“美利坚”)的影响最终驱逐出去——的地理发射平台。
这条强硬路线一系列的追随者包括共产党的领袖们,共产党今天在俄罗斯是最大的政治组织。它的主席久加诺夫,刚出版了一本地缘政治学宣言《决胜地理学》,其中他放弃了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学说。久加诺夫写道,“我们生活于一个时代,这里地缘政治正在敲响其大门,对此毫无所知,将不仅仅是一场错误,而是一场犯罪。”在这本书里,马克思的名字唯一的一次是出现在有关引述中,其意在揭示,他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
其他的激进政治党派,诸如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也已经登上了地缘政治家的宣传车。他们的喧嚣不能忽视。自由民主党控制着杜马中的地缘政治学委员会,并且与自由得多的国际事务委员会(它代表有关俄外交政策的听众的声音)一争高低。
在立法机关之外,俄国防部以及军界精英也得了欧亚主义感冒。一些评论家甚至在俄罗斯令人神秘的新总理普里马科夫的政策中,也发现了对地缘政治的认同。他的政策与欧亚主义学说合拍是这样的天衣无缝,以致很难不把普里马科夫视为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之一——尽管他从未公开过对此理论的个人看法。
与恶魔同枕共眠
欧亚主义的广泛成功,部分归功于它的无所不容的杂交性格。在其小心翼翼的空想家们娴熟的掌玩之下,欧亚主义在调和共产主义、宗教正统的信仰以及民族主义性质的原教旨主义之间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学说方面,已取得成功。因而,欧亚主义尽力表现得堂而皇之而不是民族主义,表现为救世主义而不是公开的沙文主义。它已成为掩人耳目的一套哲理;后苏维埃政治思维,犹如大而深的敞口锅里纷纭的泡沫,对其中活跃的成份都兼收并蓄。欧亚主义或许是俄罗斯传说中的“第三条道路”,一种左翼和右翼极端间的折中,然而,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不偏不倚。
如果欧亚主义似曾相识,绝不是巧合。这一理论直接继承于19世纪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现为了20世纪之计而重新粉墨登场。它剽窃于麦金德,而且因历史学家萨维德斯基(P.Savitsky )的《往东大出奔》(Exodus To The East)的出版而于1921年出笼。它寻求建立俄罗斯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身份。欧亚主义不再强调所有斯拉夫人的文化联盟(就像泛斯拉夫主义曾经所为的那样),它转向南方和东方,并且梦想着把欧亚学说与伊斯兰民众溶为一体。
欧亚主义通过数页反对派新闻报纸《今天》——创刊于1990年,并在1993年易名为《明天》——而进入后苏维埃世界。8年以来, 其编辑普列汉诺夫(A.Prokhanov)以及他的前任副手杜金(A.Dugin),已经把欧亚主义演变成了俄右翼和左翼意图反叛者们重振雄风的观点。杜金在正对着莫斯科诺夫迪维奇修道院的办公室里说道,“除了欧亚主义者,无人会提出如此一项工程。它起自本世纪20年代,但在本世纪90年代仍一样奏效。其他倾向——泛斯拉夫主义者、西化者、左翼和右翼、红派和白派(极端保守派)——这些皆已偃旗息鼓,他们对于怀旧派来说,就像集邮或收集老爷车一样。”
自从离开《明天》报,杜金已成了名为《大纲:欧亚纵览》杂志的编辑,并作为俄杜马共产党发言人谢列兹尼奥夫(G.Seleznev)的智囊人物。他以其1991年的著作(《地缘政治学基础: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未来》,借助于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会而著就)表明,在欧亚主义运动中持中间立场。《地缘政治学基础》一书持麦金德的观念:陆权派与海权派在地缘政治上是对立的,并更进了一步;它假定,两个世界并不仅仅由一争高低的战略性使命所统辖,它们在文化意义上是互为敌对的。对杜金来说,陆地和海洋间的敌对状态与东西方的分野相似。他说道,陆基社会着迷于绝对价值体系和固守传统,而海基社会则天生自由。
从战略交锋线来说,杜金建议,俄罗斯、日本、德国和伊朗,基于他们对西方同持拒斥态度,结成反西方的联盟,将有能力把美国的影响从大陆上排挤出去。尽管事实是,这样的一个联盟,对西方读者来说似乎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就像与事实不符地声称,德国和日本是非“西方”国家一样——杜金建议的一些内容看上去已经梦想成真地获得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例如,他建议把有争议的千岛群岛交还给日本,作为建立联盟的一个步骤。结果是,1998年秋季正是这样的观念被提交与日本人讨论。杜金的这些观点也是叶利钦建立莫斯科—柏林—巴黎轴心的号召及普里马科夫针对两伊的行动(起始于他还是外交部长之际)的预兆,杜金和俄罗斯官方机构的观念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贴近,以致不能被忽视。
洋溢着共产主义
就在杜金和普里马科夫作为欧亚主义主要的空想家抛头露面之际,这场运动的最大实践者是久加诺夫。久加诺夫已经运用欧亚主义去重建共产党,并且令人惊奇并成功地把它诉诸于实践。通过把民族主义、宗教正统的信仰以及马克思主义掺和起来,他已经成功地包括了民族主义者们,在广泛的政治领域内左右逢源,赢得了赞成根本改革的选票。并且其在杜马内的共产主义力量有可能在余下的选举中成长壮大,因为大众厌恶主流政治学,导致投票者趋向极端:由于久加诺夫的战略,它们现在都把票投回给共产主义者。
久加诺夫已经在俄社会白派和红派间的鸿沟上架上了桥梁。首先,通过把俄罗斯的“民族观念”与广泛的传统以及俄东正教连结起来;然后,把它们捆扎进共产主义。在他1995年的著作《超越地平线》中,久加诺夫认为,传统的俄罗斯公社观念以及社团主义的正统学说——两者皆认同集体财产所有权以及公共决策——显示出,在历史长河中,共产主义实际上早已是俄社会中的主题。
久加诺夫是欧亚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名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也把其自身模仿为一个巴什基尔民族主义者,一个鞑靼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卡尔梅克佛教捍卫者。久加诺夫的总观点是,所有的传统型社会从深层次上说都是“社会主义的”。他已熟练地把种族民族主义和不同国籍间共产主义友谊概念联结起来,以便把所有欧亚种族群体一起缝合进一个恪守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反自由、反西方的混合物中去。
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活动中,久加诺夫的这一战略已有所回报。在非俄罗斯族人地区,他唾手可得地就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对自决运动的深得人心的支持令人景仰;他坚持反对诸如列别德这类候选人——更具排斥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如果《超越地平线》正是久加诺夫企图把共产主义和俄罗斯欧亚传统联结起来,那么,他的最新著作《决胜地理学》的企图则更具雄心:把阶级斗争与东西方冲突相类比。在该书中,久加诺夫费力而傲慢地解释了西方文化和俄罗斯之间的不共戴天。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将不再是中产阶级的”。他继续声称,俄罗斯相对于西方已处于下风,并且已成为单纯意义上的原材料基地——一种令人不快的困境,他认为其类似于后殖民地东方的命运。
对久加诺夫来说,这场冲突的根源在于西方文化的独特的特点。他承认,西方的政治哲学奠基于雅典的民主理念,但认为雅典社会分化为平民和奴隶,这种情况隐藏于这一历史传统之中——一种西方民主很少认可的理念。这种分化,在久加诺夫看来,是西方世界观的基本信条:生活于西方世界的居民中的“亿万富翁”对其他的人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其他人卓有成效、也是公平地扮演其角色:资源供给的附属物、有害废弃物的仓库以及存放生物学意义上有害产品的空间。
一切着眼于东方
久加诺夫警告,为了进行全球阶级斗争,俄罗斯首先必须把东正教世界巩固为一个单一的集团,并与激进伊斯兰运动铸就密切联系。“在接近20世纪尾声之际,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伊斯兰道路正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真正替换物”。他写道,“原教旨主义作为向若干世纪古老民族精神传统的复归而被理解,并且可能导致非常积极的结果。它是向人际关系道德规范的复归……保持社会道德的完整无缺。”
俄罗斯与东方关系的这种调整,对于欧亚主义者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他们是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是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事实上,通过提倡与亚洲邻居、尤其是伊斯兰邻居结盟,众多欧亚主义者把其自身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了。就如普里马科夫说的那样,“欧亚观念是一个整合性概念。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欧亚主义的对立物,两种意识形态是完全不相容的。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俄罗斯)概念不会把鞑靼斯坦或高加索考虑进去。”
对东方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使人回想起普里马科夫,已做了总理的俄罗斯著名的阿拉伯专家和亚洲问题里手。当然,东方主义——普氏专长——是一门西方的科学,自从19世纪以来对东方的研究、分类、具体化,以及正是其在俄罗斯的存在,已帮助许多俄罗斯人相信其本质上的西方定位。但是东方主义在俄罗斯,像诉诸实践的那样,总是暴露出对其实践对象矛盾的关系以及与西方的天生对峙性。普里马科夫众多政策都是这种模棱两可状态的典型,并干脆地迎合了欧亚主义计划。自从90年代早期以来,普里马科夫在幕后加深与中东无赖国家——众人皆知的两伊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主导力量。事实上,久加诺夫《决胜地理学》的大部分篇幅,或许可能是从普里马科夫1983年的著作《殖民体系崩溃后的东方》中逐字逐句抄来的。其中,普里马科夫描写了帝国主义西方如何通过“不对称的独立”来尽力控制后殖民地时代的东方,并且他肯定了作为东方卫士的苏联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在该书出版后的16年中,许多俄罗斯人明白无误地把其国家看作是受压迫东方的一名荣誉成员。
杜金写道,“今天,欧亚主义正轻轻地走来。”“普里马科夫的政策就是欧亚主义政策,在内部,这是左翼经济政策;在海外,向东方定位,帮助阿拉伯国家,帮助像塞尔维亚这样传统的盟友,加强前苏联的整合。这是欧亚主义心脏地带的政策。”这是第三条道路,或许代表着俄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3—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