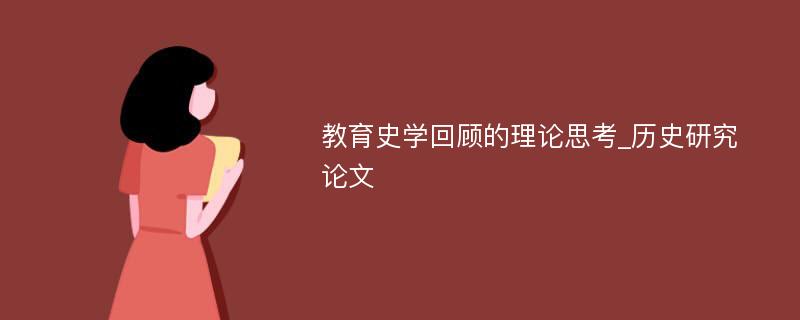
关于教育史学评论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1-0065-9
教育史学评论是依据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对教育史研究的活动和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过程。作为对教育史学科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教育史学评论是教育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史研究和教育史论著的编纂起着直接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一、教育史学评论的意义
教育史学评论以教育史研究自身的实践活动为对象,与一般的教育史研究有着根本的区别,教育史评能够从总体上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1.教育史学评论是对教育史学科自身的认识
作为中国教育史学大家庭中的特殊成员,教育史评是教育史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教育史研究的派生物。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史研究,以客观的教育历史过程(教育史Ⅰ)为对象,以记录、描述、分析和总结客观的教育历史过程为内容,属于教育史Ⅱ与教育史Ⅲ的范畴。教育史评的对象是教育史研究活动及其成果本身,属于教育史Ⅳ的范畴。(1)作为对客观的教育历史过程的记录、描述、分析和总结,教育史的研究和编撰,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活动,但在教育史评面前,它又成为教育史家的客观研究对象。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里曾将哲学史视为对哲学自身的认识,即各个时代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哲学思考,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在哲学史家那里却成了客观的研究对象。教育史评与教育史研究的关系也大致如是。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思维的研究,不仅对它的实际过程进行心理学上的分析,而且对它为自己所树立的理想进行分析。历史思维是人们思考客观世界时所采取的许多态度中的一种态度;……历史哲学应当是对这种态度、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是为发现历史思维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它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及其有效性所作的一种尝试。”[1](P.158-159)如果说黑格尔的哲学史是对哲学自身的认识、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思维自身的研究,那么教育史评也是对教育史研究自身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教育史评除了须回首以往教育史研究的实践活动和研究成果外,还须密切关注和追踪当前的研究实践。
虽然教育史评与一般教育史研究有别,但又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派生物,教育史评是随着教育史研究的产生而产生的,“总是先有了史学实践活动,然后才有对史学实践活动和史学著作的分析和评价,从而派生出史学评论。”[2](P.282)教育史研究的实践,教育史著的编撰,是教育史评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如无教育史研究,教育史评以何为评?反之,如无教育史评,教育史研究对其置身何处将会知之甚少。教育史评以认识教育史研究的自身状况为目的,帮助后者认清自我,明瞭未来,这也正说明教育史评是对教育史学科自身的认识。
2.教育史学评论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教育史评通常有两种形式,即对他人的教育史研究和史著的评论与史家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促使着史家治教育史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成为群体性的活动,同一学科的研究者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成为学科发展的动力,而教育史评是沟通同行、促进研究的重要途径。论著、目录索引、论文摘要、研究动向、相关学科的进展,固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信息,然而,更有价值的信息则来自于教育史评。因为,教育史评通过评论得失,总结过往,指向未来,反映了学科内外对研究者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有助于研究者认清自我,据以改进和推进自己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明瞭同行的研究意图、方向和水平,适时调整研究计划,寻找新的突破点;有助于编者和出版者了解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动向与水平,选择和发掘新的有价值的选题;有助于学术领导者和管理决策部门全面把握学科发展状况,确定学术导向。尤其是那些议论中肯,能够提出问题的教育史评,更以其富于启迪性的见解,提升着人们的学术眼界和学科意识。章学诚在评价其所著《文史通义》对上下古今的史著所作的“议论”时,自信是在“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其中的篇章“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认为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随着科学研究的日益社会化,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研究不是个体行为,越来越重视同行与社会对其研究的评价,越来越注意对自己研究活动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大凡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的史家,总是能够从他人对自己的研究及其成果的评论中得到启发。当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通过史学界内外对影射史学的评论对自己的史学实践作出过自我反思:“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特别是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现实已经起了本质上的变革,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现代化使之符合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4](P.7-8)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的创立者、参与者和见证人,翦伯赞的自我剖析是对自己史学实践的评价,也是对新中国史学历程的批判,更是对史学一般问题的深刻反思,这样的评论已成为新时期以来史学界(包括教育史学界)的一般共识,成为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原动力。
因此,教育史评作为对教育史学科的自我反思,不断增强和深化着学科意识,提升着教育史研究的实践水平。
3.教育史学评论是联系历史研究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纽带
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想真正为社会所接受,对社会产生作用,“一是要满足于社会对它所提出的要求,一是要使它为社会所了解、所认识”,[5](P.34)否则,它的社会价值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并未取得实际意义,其自身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要使教育史研究有“用”,首先必须要使它为社会所了解、所认识。一项新材料的整理与发现,一种新见解的提出,一部(篇)新论著的问世,都是研究者劳动的成果,如何使之成为整个教育史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固然,成果的发表本已表示研究者个体的劳动成果已具有了社会属性,然而,如果适时地写出史评著作,将成果向同行与社会读者推荐和介绍,必将加快研究成果的社会化过程,从而促进教育史研究与现实的教育实践乃至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使之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显示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其次,教育史研究及其成果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在社会发展中,生产与经济的发展总是最为活跃和先行的;在教育的发展中,教育实践的发展也总是最为活跃和先行的。相对而言,作为观念和理论形态的教育史研究,总是滞后的,况且,教育史研究自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教育史研究就有可能落后于教育实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而社会经济和教育实践的发展,要求教育史研究共同参与现实的社会和教育问题的解决。例如,随着我国社会现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如何发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吸取全人类道德遗产中的合理成分,重建中国的道德规范体系,就是时代对中国教育史学科提出的要求与课题,而以往的教育史研究对这一时代的大课题就没能作出很好的回应。不过,教育史研究与教育实践及社会需要之间从不相适应到基本适应的转变,往往不是自发实现的,教育历史与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距离,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更缺乏直接联系,这就需要某种中介来联接和调节,而充当中介的就是教育史评。教育史评是现时代的人、以现时代的眼光、按照现时代的需要,对教育史研究作出的评价,它能够调节历史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使两者从不协调走向协调。社会在发展,社会的发展将不断向意识形态领域提出新的需要与课题,教育史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又会产生新的不适应,教育史评对此不断作出反应,提供教育史学科自身状况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反馈信息,以使其作出新的调整。如此循环往复,教育史学科的社会价值不断得到体现,自身也不断取得进步。正如历史上无数学者所反复指出过的:历史研究从来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刘知几撰《史通》,评点历代史著,“虽以中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在万殊,包吞千有”。[6]教育史评丰富了,它与教育实践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密切,历史研究的意义会越来越为人们所首肯。所以,史评兴则史学兴。
二、教育史学评论的客观标准
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教育史研究的客观对象,也是教育史评的客观基础,这是由于客观的教育历史过程是教育史研究的直接反映对象,而评论教育史研究及其论著,无非是评点它们对客观教育历史过程的反映是否接近了史实本身,进而是否把握了教育演进的线索与规律;是否充分发掘了应有的史料,进而是否得当地剪裁、编排了这些史料,并作了恰如其分的表述和阐发。因此,教育史评并非仅仅评论了史著的文字,而是进一步评论了客观的教育历史过程。“无论是剖析错误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还是证明正确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总要联系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客观历史过程总是史学评论的最后落脚点”。[2](P.399-400)
史评家如果不是从客观历史过程出发,就难以对史著作出正确的认识和中肯的评价。近年来,教育史学界重视以流派和思潮的形式展现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流变,意在充分反映某一时代教育的流派与流派之间、思潮与思潮之间、教育思想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充分反映教育思想的全貌及其演变,这种史著表现形式表达了史家对教育思想史的理解,其客观基础就是历史上教育思想的现实状况。史评家固然应留意史家的治史意图和表现教育思想史过程的水平与境界,但尤应注重教育思想史的客观过程,如此方能公允地评说流派和思潮,展现思想史实际的是非得失。如果对客观历史知之甚少,史评家何以敢对史著置一辞?因此,高水平的教育史学评论,要求史评家不仅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良好的教育理论素养,还要熟悉教育史学评论对象的对象,即熟悉客观的教育历史过程。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堪为史评家的楷模。马克思、恩格斯评判和批评当时法国史学界在拿破仑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英雄史观和其他错误史观,凭借的就是他们对法国历史的深入理解,他们甚至还著有多种有关法国史的论著。正如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所说的,马克思“深知法国的历史”,“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7](P.601-602)1897年,列宁曾写过一篇评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的著名教育书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次年,又发表《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一文。正因为列宁对教育实践问题的深刻理解,在后一篇书评中,很在行地从“教者”与“学者”两个方面,对教科书的形式与内容作了评论,留给后人一份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史的珍贵书评。
因此,史学评论只有也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才能不仅帮助人们认识某部史著、某位史家的研究,也帮助读者和史家正确认识客观历史的过程。客观教育历史过程是教育史学评论的起点,也是它的根本目的,还是确定评论标准的依据之一。
1.教育史著内容的真实性
教育历史研究应有两方面任务,即一,阐明教育史实,展示客观的教育历史的发展过程;二,探求教育历史的本质,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是展示历史过程,还是揭示历史规律,都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础。尊重教育历史事实,包含有三层含义。
其一,教育历史研究的对象,“应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事件、人物或现象,而不是虚构出来的东西”。[8](P.242)为了探求客观的教育史(即教育史Ⅰ),应该尽可能去搜寻足以反映教育史Ⅰ的教育史料(即教育Ⅱ),从而撰写出一部接近教育史Ⅰ的教育史著作(即教育史Ⅲ)。
其次,史家所搜集的史料(即教育史Ⅱ)要能够“近真”地反映存在过的客观历史事物,必须是尽可能“直观的记录和复制”,[2](P.309)对教育事件、教育活动和教育人物的记录,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有严格的规定,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的揉合、捏造、渲染和杜撰。试想,如果依据伪《古文尚书》去展现商周教育的历史,如果依据《孔子家语》去描绘孔子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这样的中国教育史又能有几多价值可言?
其三,教育史Ⅲ必须能够反映教育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即对教育史Ⅱ作出接近教育史Ⅰ的说明。因为,“历史现象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本质的真实性”,[2](P.310)客观的教育史、史料中所反映的教育史和史家思想中的教育史,是同一教育历史事实的三种不同形态,三者可以是三回事,也可以取得本质上的统一。
因此,教育史学内容的真实性,要求教育历史研究对象的真实、史料记载的真实和史家主观展现的真实,三者达到本质上的、合乎规律的统一。“文革”期间“四人帮”作崇,御用文人炮制“儒法斗争”的教育史,就不仅虚构了一个中国教育历史过程,而且“发现”了如此之多的“事实”材料,更造作出一部令人瞠目的教育史!正因为在撰写历史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远离了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以“儒法斗争”的线索所再造的教育史就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中国史学评论的传统一向重视史学内容的真实性要求。孔子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理由就是他“书法不隐”,真实地记录了晋国的历史,[9]北周史学家柳虬也评论董狐精神,“是知直笔于朝”。[10]唐代刘知几撰《史通》还专辟《直书》与《曲笔》两篇,具体阐述了史学评论的真实性标准。把“书法不隐”、“直笔”、“实录”作为评判史书优劣的尺度这一史评传统,理当为当今的教育史评所继承。
三、教育史学评论的社会标准
任何评论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作出的,而任何评论标准又总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和时代的要求。史评标准可以分为社会的和学术的两大方面。所谓教育史评的社会标准,就是考察和评价教育史著和研究活动时,着眼于它们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即从政治的和道德的角度评价其社会价值。
1.确定教育史评社会标准的依据
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就是“资治”。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后,在其《进书表》中曾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对其撰史目的加以概括。不独司马光,中国古往今来的史家著史、评史,也无不以此为追求。宋人孙甫在其《唐史记》中评论司马迁《史记》时曾说过:“夫《史记》纪事,莫大乎治乱。”[11]清人王夫之更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12]因此,“资治”也就成为史家撰史的出发点、追求目标和史家评史的依据。这一目标的确立又是基于人们对历史学性质和功用的认识。“因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13](P.12)于是,今天的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人类以往所经历的经验教训能够指导自己的行动,“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的眼中显得的不那么完美。”[13](P.12)正是依据了对史学性质和功用的这种认识,才使人们明确提出以“资治”为史学追求的目标,能否做到记古今、明治乱,就成为评论史著的重要标准。
一般的史评是如此,教育史评同样如此。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方面,教育的主体和对象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人。一方面,任何时代和社会的教育都是在前代基础上延续的,但这种延续又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常常显示出全新的意义,这就使人们的教育实践总是面对新的问题,需作新的尝试,新的尝试别无参照,唯有借助过往的经验。“任何对当代的思考,任何分析当前教育形势的尝试,都暗示着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思考或尝试使我们求助于或是被体验……,或是被想象……的过去的某种状况。”[14](P.126)这样,教育史研究就成为从“历史研究中抽象出来的有某种倾向的规律性”,从而“引起对新问题的注意”的“行动的指南”。[14](P.128)显然,人们对教育史研究的性质和功用的理解,同样在于“资治”,只不过所“资”者在于“治”教育而已。能否使教育史成为“分析形势的工具”,[14](P.126)就成为教育史评社会标准确立的依据。
2.教育史评的社会标准
正是因为认识到教育历史“传统在政治家的计划或决策中至关重要,所以,与过去的关系使辨别所设想的改革真正包括新的东西成为可能。”[14](P.126)因此,人们总是为了总结以往社会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教训,去研究历史,了解历史发展过程。而在阶级社会中,人们了解历史,探寻历史经验,又必然服从一定的阶级要求,受着一定的政治观念的制约,人们评价史著的社会效果,往往就带着深深的阶级的和政治的烙印。教育史评的社会标准,就集中体现为一定的阶级、政治标准。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自然要求教育史著在反映客观教育历史过程时,必须符合或起码无害于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需要和道德规范,凡符合或无害于这些标准的史著就被认可或提倡,反之,就将受到批评或抛弃。孔子所修的《春秋》以“彰善贬恶,不避强御”[15]而备受中国古代史家推崇,被奉为“春秋之教”,这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评史标准。然而,包括《春秋》在内的正统史籍,在中国近代史评家笔下,却被斥为“相斫书”、“蜡人院”,而二十四史更被批评为“二十四姓帝王家史”,其中无“公史”、无“民史”,自然更无教育史,这又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评史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公开宣称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恩格斯在批评资产阶级史学时曾尖锐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6](P.573)恩格斯在批评资产阶级史学的阶级本性时,也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应坚持的著史、评史标准。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开展整风时,郭沫若写出了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成败得失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致郭沫若信时评论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17]这是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去评论史著。
就教育史评而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杨贤江著成《教育史ABC》,指出教育史研究的任务尤应说明教育性质的变迁、变迁的根据和“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段”在此过程中关系的变化,主张教育史研究应向人揭示出:统治阶级占有教育,以之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却标榜为代表社会全体是欺人之谈,而且劳动群众的教育活动是全社会教育史不可轻视的部分。这虽是为了表明杨贤江自己的教育史观,但也提出了崭新的教育史评标准,即教育史研究应以人民利益为上。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教育史学界指导地位的确立,古代王充、李贽等一些反传统、具有人民性的教育家思想家,近现代李大钊、鲁迅等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思想家,被研究和发掘出来。这同样是以人民利益的标准著史、评史的结果。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史评标准的具体社会内容会有所不同,但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则是始终应当坚持不渝的。
应当指出的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切忌简单化、公式化的方法,如果从抽象的理论和原则出发,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现阶段国家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作为教条去生搬硬套,孤立地、片面地去看待教育史著中的局部、个别和具体问题,就会妨碍我们对教育史著作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建国以后曾一度出现的混淆学术研究和政治原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乃至戴帽子、打棍子的偏向已经给过我们深刻的教训。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固然应当服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然而弘扬“主旋律”不可牵强比附。教育史著作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效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作为历史研究,教育史著必须符合客观的教育历史过程,“要讲究史德,实事求是”,[13](P.11)这是教育史著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基础。因此,教育史研究断不可简单成为现实政治的诠释和证明。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研究,教育史著显然无法提供解求现实教育问题燃眉之急的锦囊妙计,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的魅力在于“首先触发人的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13](P.10)何况,教育历史的传统究竟哪些是应当为我们所汲取的精华,而那些又是应当为我们所剔除的糟粕,还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总之,坚持教育史评的社会标准,尚须尊重教育历史的客观事实,遵循教育史学自身的客观规律,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反而会背离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教训。
四、教育史学评论的学术标准
所谓教育史评的学术标准,就是从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角度考察和评价教育史著和研究活动的优劣成败。中国传统史评理论中的注重褒贬,是对史学社会标准的强调;而注重事实与文采,则是对史学学术标准的诉求。因此教育史评的学术标准,无外乎史学内容的真实性和史学表现形式的完美性。
孔子在评论“君子”的人格要求时曾说过一句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8]孔子要求,“君子”的人格应当是形式与内容即外部表现与内在气质的完美统一。孔子评价“君子”的标准,也完全适用于教育史评。
在解决了史著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后,史著表现形式的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内容与形式是一部教育史著作显示自己生命力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孟轲评价孔子作《春秋》时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9]概括出评论史书的“事”、“文”、“义”三个范畴。“事”与“义”属于对《春秋》记述史实的真实和对史实本质把握的真实的肯定,“文”则属于对《春秋》表述形式完美的肯定。人们肯定《史记》、《汉书》的极高造诣,除了因其记述历史事实真实可信外,还因其编纂体例和文字叙述的出色。
中国传统史评理论向来注重史书的体裁和文字表述。从孔子作《春秋》注重“文”与“例”,使“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到刘勰《文心雕龙》提出“详实”、“准当”、“文质辨洽”,到刘知几的“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再到章学诚强调“文字之佳胜”,均讲究史著表现形式的完美。西方亦然,古希腊唯物论思想家琉善(又译卢奇安,约125—约192)曾撰有《论撰史》一文,提出一些史学审美原则,其中论及史著之美主要有“真实的美”、“秩序之美”和文字表述的美。中外史评理论关于史著表现形式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两方面,即体系结构的完美和文字表述的完美。
其一,体系结构的完美。
体系结构的完美指史著须有恰当的体裁,有严密的逻辑性。由于历史事实的千头万绪且错综复杂,史家的视角也会各各不同,这就使史著的表现形式有了大量的选择余地。中国传统史著向重体裁、体例和谋篇布局,在漫长的史著实践中,创造了多种表现形式,如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等。编年体史著首创于《春秋》,刘知几评价说:“系明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理尽一言,语无重出”。[20]表现出以时序为中心的形式美。纪传体史书肇基于《史记》,刘知几评价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20]表现出综合复杂史事各部其类的形式美。典制体创始于杜佑《通典》,杜佑解释其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为篇第的理由时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堕然而用刑罚焉……”[21]表现出合乎社会生活制度逻辑的形式美。纪事本末体创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未》,杨万里评价说:“太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22]表现出以事件为中心的形式美。以上几种体裁以各自的逻辑,编排了纵向的历史时序和横向的社会生活面,各适其当,一定程度体现了历史地考察、逻辑地再现相结合的研究、表述方法,堪为讲究史著编排形式的楷模。
由于近代学科分类观念的发展,以上史著表现形式未必完全适合于现代教育史著,但内容编排的合乎逻辑、结构的和谐,同样应当引以为重。
其次,文字表述的完美。
中国传统史评理论向以“善叙事”为“史之良才”的一项重要素质。“善叙事”当也包括善于选材取材、善于谋篇布局,而文字表述的造诣则是其中的主要方面。人们于二十四史中尤重“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文字表述的优美。“前四史”会有那么多篇什被选入《古文观止》一类范文读物,当是其文字优美的一个明证。
著史而须讲究文字表述,固然是因为精当的史实内容需有相应的表达形式,同时也“因为历史本身并不单调”。[2](P.317)教育活动场面,或生动活泼,或严肃认真;教育历史人物,或刚毅高洁,或温文敦厚;教育思想流程,或高深玄奥,或浅显直白;教育制度沿革,或井然有序,或错综曲折。无不各具特性,风韵别致。因此,如此丰富多彩的历史场面、历史人物、历史过程,自然需要文字记述的准确、鲜明和生动。另一方面,史家要将已汹涌流动在脑中的教育历史付诸笔端,引发他人产生共鸣,尚须有一个读者的接受过程;而欲使人接受,就须使文字表述具备最大限度的易解性、感染性和可接受性,这需要文字表述的传神、洗练和流畅。
史著文字表述的完美实须注重以下诸端。
文字的真实之美。乃是指史著的文字表述可深入反映教育历史的本质。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史学就变成了文学,史著的文字追求即成为华而不实乃至无本之木。班固评论《史记》“其文直,其事核”,即肯定了史著文字须尽力表现历史真实。
文字的质朴之美。乃是指史著的文字表述朴实、平易。故作高深,“佶屈聱牙”,读之令人云罩雾障,史著仅为史著者独赏,何以醒世人?刘知几评论先秦史书说:“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23]“素以为绚兮”,朴素的语言亦足以描绘绚烂的史事。
文字的简洁之美。乃是指史著的文字表述省要、不枝蔓。文字简练并非仅仅是修辞问题,更是能否准确反映历史过程的本质问题。宋儒批评汉儒注经“一字说至数万言”,终致离题万里。历代史评家大多“尚简”,刘知几更以为史著“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如能做到“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述史应从“省句”、“省字”做起。[24]
文字的含蓄之美。乃是指史著的文字表述不皮相,意蕴深远。《左传》评论《春秋》之文“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25]即肯定了《春秋》行文的隐喻、深沉、婉约。我们固然无须效法孔子的“微言大义”,然而,如刘知几所说:“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24]是应当追求的。
文字表述的完美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历史文学”之所以能得以成“学”,实得益于历代史家著史的良苦用心。只是迄今所见的中国教育史著,文字表述可称完美者,还为数不多见,足可见教育史家们尚须致力于文字功夫的提高。
教育史著的表现形式并无规定的样式,表现形式的选择取决于能最大限度地展现教育历史的客观过程。但万变不离其宗,评价任何表现形式均须注意结构与文字这两大要素。“如果说,严密而科学的逻辑结构是史学著作的筋骨,那么,在忠实于史实基础上对具体场景的生动描绘,就是史学著作的血肉,它们一起构筑成史学作品的具体形式。”[2](P.318)评价教育史著的学术性,史著表现形式的完美是一项具体而重要的标准。
标签:历史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