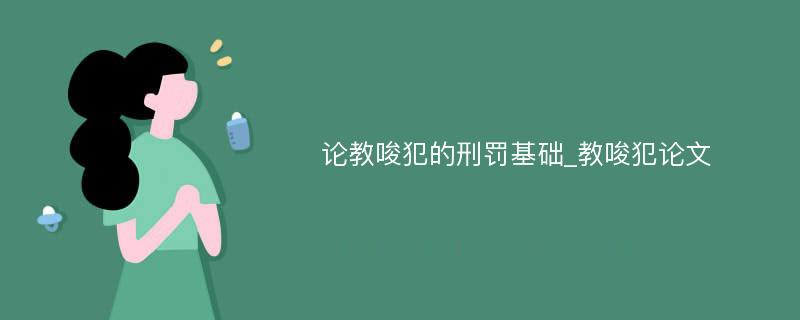
教唆犯处罚根据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唆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9)05-0057-04
作为犯罪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教唆犯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在事关教唆犯体系建构的本源性问题即对教唆犯的处罚根据方面的研究,却略嫌薄弱。教唆者缘何承担刑责,不仅是对立法的正当性考问,也是对人权保护机能的回应。加强对教唆犯处罚根据的研究,是完善教唆犯体系的必要之举。
一、教唆犯处罚根据研究范式概介
教唆犯以制造他人的犯意为核心特征,意在使被教唆之人实施所教唆之罪。对教唆犯的处罚,历来有之。据史记,关于处罚教唆犯的规定,始于奴隶制时期①,并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及至近现代,教唆犯已被刑法明文规定为一种犯罪形态。而对教唆犯处罚根据的追问,则始于晚近,并形成了侧重于从教唆者自身寻求处罚根据的积极研究范式、从被教唆者方面寻求处罚根据的消极研究范式及介之于其中的折中式研究范式三大立场。
积极的研究范式以对教唆者的分析为切入点,寻求教唆犯的处罚根据,主要包括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其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因为,“教唆与帮助等行为,虽然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实行行为,但它们在共同犯罪中对于犯罪结果的发生起着大小不等的作用。因此,教唆与帮助等行为也是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这就是共犯应受刑罚处罚的根本原因之所在”[1](P285)。其二,认为教唆犯本身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和法益侵害性是对其进行处罚的主要根据。因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应当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寻求。共犯在客观上教唆或者帮助正犯,共同引起正犯的犯罪事实或犯罪结果,具有法益侵害性;同时共犯有主观上希望或放任自己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促成或便于正犯的犯罪事实或犯罪结果发生,具有人身危险性”[2](P706)。其三,纯粹的惹起说。该说“以共犯固有犯说为前提,主张共犯之处罚根据在于共犯者本身独自侵害刑法分则上所保护之法益,而共犯之违法性(不法)完全从正犯之违法性而独立,系由共犯行为本身而产生,并将从属性视为处罚之条件,仅具有事实从属之性质”[3](P325)。
消极的研究范式以被教唆者为视角,认为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在于使被教唆者陷入某种否定性境遇,教唆者因被教唆者的不法而承担刑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其一,不法共犯说,即社会完整性侵害说与行为无价值惹起说。前者认为,教唆犯之所以受处罚,不仅是因为惹起犯罪行为,而且也是因为陷国民于不法,使之处于和法敌对的事实状态中,从而侵害该社会成员的社会完整性[4](P94)。后者则以认为共犯是因为惹起他人的行为无价值而受处罚作为理论基础,其主张者威尔兹尔认为,处罚共犯者的内在根据并非在于将正犯者引入责任和刑罚,而在于唤起正犯者实行社会难以容忍的违法行为决意或对该事实予以援助。其二,修正的惹起说。该说以完全的共犯从属性说为前提,主张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犯参与了正犯对法益的侵害,因而正犯的违法性直接导致了共犯的违法性。
折中的研究范式并重于从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两方面去寻求解答之策,主要包括责任共犯说和折中的惹起说。前者认为,教唆者一方面对法益加以侵害,另一方面则对正犯者加以侵害,是双重形态的犯罪;只不过对于将犯罪本质理解为对伦理秩序的侵害而非外在损害的见解者而言,这个诱惑因素原则上比起客观的法益侵害更为重要。后者认为,共犯的不法是由其本身侵害法益所形成的独立、固有的要素与正犯行为的不法所导出的从属性要素构成的。简言之,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其通过正犯间接地侵害了构成要件上所保护的法益。
二、法理介评
无论是积极的研究范式、消极的研究范式还是折中的研究范式,都以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构成共同犯罪为立论基础。其中不法共犯说、责任共犯说、折中的惹起说坚持了教唆犯从属性说,认为教唆行为只是从属于正犯行为的共犯行为;积极范式中我国学者所认为的两种处罚根据论坚持了教唆犯的二重性说,认为教唆犯既有从属性,也有独立性;纯粹的惹起说虽然坚持了教唆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犯是正犯的一种形态,教唆行为是教唆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把成为规范的障碍的某种意义上违法的他人行为当作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了犯罪构成要件[5](P395),但同样以共犯说为基础而展开。
通说认为,构成共同犯罪,必得各共犯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故意且彼此之间具有犯意沟通、客观上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然而,教唆者与被教唆者并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求:从主观方面看,教唆者意在教唆他人以使其产生犯罪决意,而被教唆者在主观方面则表现为决意实施所教唆犯罪;从客观方面来看,教唆者的实行行为表现为教唆行为,而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则是其实施所教唆犯罪的行为。承认教唆犯的共犯性,还存在以下问题:在独立教唆犯的场合,存在定罪及量刑上的困惑②,在教唆他人自杀的场合,对教唆者如何定罪,以及如何解释《刑法》总则在第29条承认教唆行为为共犯行为的情况下,分则关于教唆行为独立成罪的规定③所承认的教唆行为实行行为性之间的矛盾等,涉及处罚教唆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不利于明确犯罪构成和犯罪概念的辩证统一关系、违背了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客观说、对被教唆人的处罚会产生理论上的悖论,以及造成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6](P89)等实际问题的出现。以教唆犯共犯性说为立论基础探讨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存在根本性缺陷。
不能否认的是,积极的研究范式与消极的研究范式虽然都只注重了共同犯罪人中的一方而忽视了对另一方应负罪责的关注而失之片面,但从教唆者本身出发探求教唆犯处罚根据、从直接结果出发寻求行为的不法性,以及折中的研究范式兼顾具有继属关系的教唆者与被教唆者双方而寻求教唆犯的处罚根据的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教唆犯处罚根据论的基本立场
教唆犯的处罚根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教唆犯的地位认定:承认教唆犯的共犯地位,就必须承认作为正犯的被教唆者在教唆犯处罚中的作用,采用消极的研究范式或折中的研究范式;承认教唆犯的正犯地位,就必须采用积极的研究范式,承认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在于教唆者本身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与教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而教唆犯地位的认定问题,是研究教唆犯处罚根据论的基本立场问题。
承认教唆犯的独立构成地位,是近年来学界在质疑教唆行为共犯性的妥当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说。该说认为,教唆行为是犯罪的实行行为而非共犯行为,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能构成共同犯罪,理由在于:教唆行为不具有所教唆之罪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的该当性,教唆行为与所教唆犯罪造成的危害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教唆犯与被教唆犯罪人没有共同故意[7](P6)。应当说,教唆行为实行性的提倡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开创了教唆犯研究的新气象。第一,有助于弥合现行刑法规制不足的缺陷,有效避免共犯性语境下教唆行为判断必须依赖于所教唆犯罪的判断标准而引发的一系列弊端④。第二,有利于现行刑法中共同犯罪论体系的完善,能消除以作用分类法为主并辅之以分工分类法的双重分类标准划分出来的共犯体系所引起的质疑⑤。第三,有利于我国现行刑法总则与分则体系的协调。
对教唆犯为具有独立犯罪构成的观点提出的批评是:它没有客观、全面、科学地揭示出教唆犯的本质特征;对教唆犯的演进历史认识表面化、绝对化,没有准确把握教唆犯立法发展和理论发展的趋向;对现有的共犯理论——主要是二重性说理论的责难与批判欠缺说服力;对教唆犯被规定为独立犯罪的理论论证不足[8](P92)。
针对关于教唆行为实行行为性的批评,本文认为,界定教唆行为为共犯行为抑或实行行为的关键,在于教唆者是否具有“支配事态的核心形象”[9],这也是犯罪支配论关于共犯行为与正犯行为区别的关键所在。教唆者意在制造被教唆者犯罪决意⑥的特征说明,教唆者具有支配整个犯罪进行的主观构成要素。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教唆犯“必须至少带有间接故意地容忍了引起正犯作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决定”[10],本文不敢苟同。教唆犯意在使无犯罪意图者产生犯罪决意或犯罪意志不坚定者坚定其犯意,认为教唆者希望通过被教唆者实施所教唆犯罪而完成犯罪,是对教唆犯罪所作的事实性评价而非规范性界定。另外,从客观方面看,教唆行为本身具有能够独立担当实行行为功能的行为品质,我国《刑法》分则第353条第1款所规定的欺骗他人吸毒罪即是例证。作为犯罪的创案者(Urbeher)[11],教唆者所实施的教唆行为即“创案”的操作性行为。对教唆行为所导致结果的发生与否以及教唆行为与被教唆行为之间关系的评定,属于广义教唆犯罪内部结构的逻辑分析而非本质特征界定。此为其一。其二,对于认为“如果教唆行为就是实行行为,那么教唆犯与间接正犯就不能区别”的观点[13](P323),本文认为,被教唆者具有相应的刑事主体资格,其实施所教唆犯罪的行为完全充足某一犯罪构成,而在间接正犯的场合,间接正犯者缺少犯罪的某一构成要件要素。换言之,间接正犯是利用了不构成规范障碍的他人行为意图达成犯罪,而被教唆者的行为则构成规范性障碍。
四、教唆犯处罚根据体系的建立:以教唆者为本位的扩展性思考
在教唆行为为实行行为的场合,教唆犯被认为具备了完备的犯罪构成。对教唆行为的处罚,在于教唆者主观上所具有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以及客观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的法益侵害性。但是,区别于一般的独立犯罪,教唆犯在充足自身犯罪构成的同时,也是构成另一犯罪的直接诱因,作为教唆犯罪的再生性犯罪,所教唆犯罪的实施与既遂,直接影响到教唆犯的刑罚裁量,是教唆犯罪客观法益侵害性的重要表现。因而对教唆犯处罚根据的研究,既要关注并侧重于对教唆者本身因素的研究,也要涉及被教唆者方面的因素。
(一)教唆者所具有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是对教唆犯予以刑罚处罚的主观根据
对于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界定,学界观点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人身危险性最基本的概念应当是指再犯可能性,初犯可能性,严格而言,是属于已然的法益侵害性的范畴,而主观恶性则是人身危险性的征表之一,不是人身危险性本身[13]。也有学者认为,“所谓人身危险性,指的是犯罪人的存在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即其再犯罪的可能性”[14](P259),由此将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区分开来。本文的观点是,就广义而言,人身危险性是一种内在于行为人本身的、实施犯罪的初犯可能性及再犯可能性,因而是以未然的、不确定状态存在的;狭义的人身危险性则是指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因行为人实施已然的犯罪而得以被发现。主观恶性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具体犯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反社会性,这种反社会性潜在于行为人本身而彰显于具体犯罪的实施过程中,因而就一定层面而言,主观恶性是人身危险性的征表。
以纯粹的教唆犯独立性说为立场,教唆者以胁迫、利诱等各种方式教唆被教唆者实施犯罪,其主观恶性表现为明知自己所实施的教唆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但仍坚持完成,力图使被教唆者接受并实施所教唆犯罪。作为能够进行理性判断并作出选择的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者,教唆者应当对其所造成的教唆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刑罚的必然要求,也是教唆者对其错误选择所应付出的代价。教唆者的人身危险性表现为潜在于其本身的社会威胁性,这种对社会造成某种危害的可能性是近代学派力主对行为人予以处罚的根据,也是在具体犯罪中主观恶性得以表现的根源所在。教唆者实施教唆行为,是一时判断所致,也是其长期积存的人身危险性的凸显。对教唆犯予以处罚,是减弱或遏制其人身危险性的必然之举。.
(二)教唆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严重的法益侵害性是对教唆犯予以刑罚处罚的客观根据
一般认为,“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则是刑法上的法益”[15](P167)。教唆犯的客观处罚根据,即表现为教唆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的侵犯。
在独立构成说语境下,教唆犯是被作为行为犯予以界定的,只要教唆者实施了教唆行为,无论被教唆者是否接受教唆、是否实施所教唆犯罪、也无论所教唆犯罪是否既遂,教唆行为都已具有客观的法益侵害性。其一,教唆行为以教唆者利用利诱、胁迫、劝说等形式,意图制造他人的犯罪决意为特征,这种使本无犯意之人产生犯罪决意的客观属性,是教唆者作为理性自由人直接侵犯社会共同体利益的直接表现。教唆者违背其应当遵守共同生活规则并为所处共同体创造利益的基本原则、以具有破坏性的反向行为作用于该社会共同体的行为,是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的,在达到道德及行政性谴责已无法表达这种否定性评价的严重程度的情况下,刑罚作为社会防御的底线,无疑是最恰当的选择。其二,教唆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还表现为它作为一种诱因性犯罪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再生犯罪能力,简言之,教唆行为不仅制造了犯罪决意,在被教唆者实施了所教唆犯罪的情况下,还制造了犯罪人。教唆行为的双重法益侵害性,还表现为在教唆行为本身已对法益造成侵害的情况下,作为其行为结果的被教唆者实施因所教唆犯罪而对法益造成的再次侵害。在独立构成说语境下,被教唆者实施所教唆犯罪虽然不能作为教唆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作为一种非构成的结果性要素,教唆犯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刑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虽然不能成为教唆犯的处罚根据,但因教唆行为而产生这一法律事实决定了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成为教唆犯处罚根据构成要素所具有的应然性与必然性。
收稿日期:2009-05-20
注释:
①如《尚书·费誓》中记载:“盗牛马,诱臣妾,汝则有常刑”,即规定了以引诱的方式教唆他人(臣妾)实施非法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参见周密:《中国刑法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②独立教唆犯是指被教唆者未实施所教唆犯罪或者实施的是非所教唆犯罪的情况。按照教唆犯共犯说,在被教唆者实施的是非所教唆犯罪的情况下,存在罪名认定上的困惑,在所教唆之罪存在多种量刑幅度时存在量刑上的困惑。
③如《刑法》分则第353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他人吸毒罪等。
④如在被教唆者未实施所教唆犯罪、实施的是非所教唆犯罪等情况下教唆犯认定上的争讼。
⑤“承认作用分类法的合理性、科学性,但又不恰当地引入分工分类法。……其实,这两种分类方法是互相排斥的,不能混合调和……”(杨兴培:《论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依据与立法完善》,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5期)
⑥事实上,除认为教唆者的主观方面只能表现为故意外,也有学者认为,教唆者在主观方面可以表现为过失。如大场茂马就指出:“所应研究者,即过失犯有共犯与否?是也。共同正犯,教唆犯,从犯,以过失而成立者,固罕,然不能谓其绝无,过失犯之共犯,在于共同行为者,有为行为之意思,当行为之际,并认识该行为,而于行为之客体,手段,时,地等性质,可以认识,因不注意致未能知之而构成。”(参见[日]大场茂马:《刑法总论》(下卷),日文版,第1013页)论题及篇幅所限,本文无意于对教唆者的罪过形式进行探讨,故采通说即故意说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