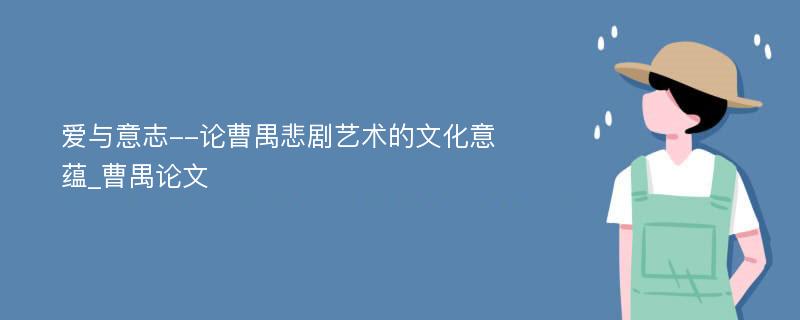
爱与意志——论曹禺悲剧艺术的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爱与论文,意志论文,悲剧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与文化、人与历史、人与自身三方面对曹禺的悲剧艺术进行考察。文章认为,曹禺的悲剧艺术提出了“人样地生活”这一最高的理想。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曹禺力图达到人对文化理性与历史理性的超越: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中谱写生命之诗;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中谱写道德之诗。但是这种人生终极的追求在现实中常常落空,从而导致了曹禺悲剧艺术的产生。
曹禺悲剧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是从“人样生活”理想失败和破灭展开的。“人样生活”是作者先验预设的人性完满状态,是浪漫主义的自由乌托邦,人道德地生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圣洁的乐土,即人自由地审美地存在。在这种先验的人性自足完满的自然状态中,人挣脱了现实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一切羁绊束缚,同时也割断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因而上述终极理想既是对人的精神本质的最高肯定,又是对人的现实本质的最高否定。“人样生活”理想本身便包含了人的自我悖论,即人的超验追求与经验存在的矛盾,人的理性本质的不确定性与人的感性存在的现实给定性的矛盾,这种悖论使得人的精神追求最终必然悲剧性地走向无解的空洞。简单地说,曹禺“人样生活”是指人对文化理性和历史理性的超越,是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中谱写情欲之诗(生命之诗),在人与历史的关系中谱写道德之诗。但这种高贵的企求落空了,悲剧不可避免地诞生在文化的迷失处、历史的迷失处和自我的迷失处,重建人与文化、人与历史、人与自我自由关系的愿望化为泡影。
一、文化的迷失与悲剧的诞生
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是精神与肉体的双向建构。但在人的历史进程中,两者并不总是均衡地发展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互相敌对的,从而造成蓬勃的感性生命与僵死的理性文明的尖锐冲突。生命是个人本位的,是彻底为我的。在尼采看来,那些“毕生未为他们的‘自我’工作过的人是真正白活了一生。”〔1〕因为他们没有高扬生命的大纛,是些精神上的中等货。“理性的最大原罪”就是压制生命本能,生命本能的衰竭导致社会的颓废和人类的退化。“一步步走向颓废——这就是我对近代‘进步’的定义。”〔2〕文化理性是社会本位的,生命的道德辩护将在它那里败诉。当人以社会公民步入文明世界,其“精神”本质不断成长壮大,它的日益丰富化和精致化压制和扼灭了许多人所固有的本质和情性。这样,人作为社会动物,其文化本质日益强化,其生物本质日益受到损害和剥夺,人愈来愈远离他的自然状态,外在于人的东西不断强加给人并使人相信这是他固有和应有的本质。于是,人变得虚伪了,戴上文明的面具,不敢袒露自己的真性情,丧失了“童心”,遗忘了“真心”。行动的意志被磨钝了,粗糙有力的情感日趋精致柔靡,生命的本能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而日益式微……文明的缺陷使人在野蛮中呼吸到一种质朴刚健的空气,感受到那未经雕凿、提纯的天性,敏悟那奔放无羁的火一样的情感。因为生命总是粗率的,不规范的,而文化则是一种教化,总是趋于精致、规范,总是在对人的原初形态的损害中发展自我的。
《雷雨》作为曹禺的第一个剧本以“乱伦”为题材绝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作者鲜明的反社会倾向,向理性文明,向人类的道德秩序发出凄壮的挑战。“乱伦是反社会的,文明包含着对它们的不断否定”〔 3〕。曹禺将人与文明置于尖锐对立的两极,对乱伦的双方寄予赞美和同情,表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深切关注。《雷雨》通过两个乱伦故事的展开,揭示了生命意志与伦理意识的冲突,作者对生命意志的张扬是肯定和赞美的,但同时,对伦理意识的认同也是肯定和同情的,最后的悲剧性结局便是:生命的疏离和伦理的认同。《原野》悲剧的本质在于,它热情讴歌人的感性生命力,赞美冲决一切束缚的原始野性,同时又意识到理性文明的自身合理性,意识到它对于社会和秩序的进步意义和重要性,于是又否定了野性的反抗。虽然在理性文明“欺人太甚”的极限处只有以人的原始野性反抗之才能获致暂时的胜利,但这种反抗本身最终亦将遭到反抗者自身的否定,因而它的胜利不仅是暂时的,而且其暂时的胜利亦是其永恒的失败。所以,《原野》既是对野性的激情礼赞,也是对野性的深刻悲悯;它既是文明(文化)的挽歌,也是野蛮(反文化)的挽歌。
高傲的女性与阉鸡似的男人的冲突,是感性生命与文化理性对抗在曹禺悲剧艺术中的一种具体呈现。曹禺是写情大家,几乎他的每一部剧作都要写到性爱,许多作品就是以男女性爱关系描写为主体内容和主视角的,事实上,男女性爱关系的描写常常是其作品最精彩、最深刻、最撼人心魄的部分。作者把畏琐萎靡的男人与高傲深厚的女性联系在一起,让他们组成最紧密的关系,通过男人在这种情感关系中对待女性的态度,暴露其生命的颓废和退化。那些爱不敢爱,恨不敢恨的男人,都是为理性文明教化、精致、提纯的病态婴儿,倒是那些美丽真挚的女性生机勃勃,光芒四射。
男女性爱是人间最自然最深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最能映照人性的真纯、生命的力度。但这种情感关系随着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而日益丧失它的“情感”性,日益变得虚伪、软弱、贫乏、苍白。现代社会的文明性爱大大增加了它理性的内容并具有了理性的“形式”(文雅的语言,高尚的态度,精神的旨趣,适度的距离等),却永远丧失了原始性爱纯真的情性、刻骨的欲念、粗犷的力量。
在曹禺剧作中,那些心性高傲、秉性高洁的女性,都有着美丽真挚的情感,爱成为其生活的第一主题和生命的第一事情,在无情的世界里如饥似渴地执着追求着爱,一往情深,锲而不舍。即如黑格尔所说,爱情于女性最是相宜,她们整个身心生活在爱中,或把一切推广为爱情。“女性的爱,最具意义的,通常在本质上是激情的——母性的。女性把自己奉献给她所爱的人,因为她感觉到他的欲望使他受苦。”女性的爱“更可爱,而且比男性更纯净,更勇敢也更持久”。〔4〕曹禺剧作爱情关系被设置在个体情欲与理性文明的尖锐对立中,她们的爱情要求都是有悖社会公理并将遭到社会公理彻底否定的。正是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女性表现了她们的美丽心灵、人格力量、崇高意志,男人则暴露了自身的苍白柔弱,颓废胆怯,暴露了他们可悲性格的喜剧性,暴露了他们不敢爱身处逆境的女人,事实上是不敢爱自己,暴露了他们不敢坚决勇敢地、坚持到底地反抗理性文明的神圣秩序,本质上是不敢真正地热爱自己的生命……
曹禺剧作女性形象的“诗”性来自她们的“爱”的生命本质,她们都在爱中或通过爱确证自己。“爱情里确实有种高尚的品质……显示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在爱情里最高的原则是主体把自己抛舍给另一个性别不同的个体,把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和个别孤立的自为存在放弃掉,感到自己只有在对方的意识里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5〕无论是“恶之花”蘩漪、金子、陈白露,还是“善之花”的愫芳、瑞珏等都是焦渴着爱又受到无爱现实的严酷规定的。“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心却偏天样的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而为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6〕但她们(特别是那些“恶之花”)为了爱,可以置家庭、婚姻、名誉等这些居于女性情感世界中心位置的东西于不顾,只需要爱人,只需要人爱。所以,作者说,“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蘩漪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7〕女性的天性就是情感,天生地具有反理性文明的倾向,因为理性就本质而言就是男性的。就“善之花”而言,她们深深地爱着,苦苦地等着,但未采取极端的行动,而是在自我牺牲中默默地奉献着爱。她们深挚地爱着却得不到回报的痛苦存在,再次证明了男性生命的堕落!
阉鸡似的男人作为“情感与矛盾的奴隶”,没有“铁的手腕、厚的胃口、岩似的心”,缺乏反抗理性文明的坚强意志和充沛的生命蛮力,必然使爱的渴望落空或得而复失。周萍虽曾一度救活了蘩漪这个爱的干渴者,但很快出于害怕,出于对理性文明神圣正义的敬畏,又用决绝的态度把蘩漪送回无爱的沙漠经受永恒的放逐。周萍的处境和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但其自愿主动向理性文明俯首称臣的行为本身证明了他是个失去感性生命力度的懦夫。他认识到自己性格的喜剧性,看到文明教化剥夺了自己身上冲决一切的蛮力,于是才佩服父亲,甚至佩服鲁贵,于是才喜欢作为青春和健康女神的鲁四凤,喜欢她身上的粗,她身上的活。焦大星还是母亲怀里的孩子,缺乏火一样的情欲,缺乏带有“恶”的感性生命冲动,不配享有金子这样的媳妇。曾文清亦复如此,只能在心灵最深处咀嚼与愫芳的爱情,本来,他有较之周萍与蘩漪容易得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实现与愫芳的爱情结合,但他“像老坟里的棺材,慢慢地朽,慢慢地烂,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烦,懒,懒,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多少年前他就发现了一个了解他的女人。但是他就因为胆小,而不敢找她,找到了她,又不敢要她。他就让这个女人由小孩而少女,由少女而老女,像一朵花似的把她枯死,闷死。”觉新铭心刻骨地爱着梅表姐,可家长一句话便葬送了他的爱情,他却连声也不吱,虽在心里不停地呼喊着痛苦,却在现实中不断妥协。同时正像曹禺所说,觉新也可能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时时苦恼着自己。方达生是以上帝的姿态企图拯救陈白露的,他只爱的是回忆中的少女竹君,——天真纯洁,白璧无瑕;他不喜欢现实中的陈白露,看不惯她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换言之,他并不打算接受现实中活生生的整个的完全的陈白露,也没有能力和胆魄接受她。方达生只是一个对社会没有多少清醒深刻认识的书呆子。这类男人缺乏粗硬的外观,气质女性化,是被阉割的匮乏存在。“谦卑”、“谨慎”、“穷酸”、“迟疑”,犹豫、沉滞、懒怠、脸色苍白、忧郁、眼睛深凹,这类人物悲剧的文化实质在于,他们不是作为独立的自足实体而存在,不是为自我生命丰富而斗争,其追求表现为一种本位追求。在男人世界中,周朴园、潘月亭、李石清算是具有理性力量的人物,但他们是外在于“情感关系”的,他们只是社会关系中的强者,在与女人的关系中都是冷血动物,都是情感的空壳。曹禺剧作检验人性真度、深度、力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物对待情感的态度,因此,唯一不像阉鸡似的男人只有仇虎。故而曹禺呼唤野性,希望以野蛮充实那些生命的空壳,希望能写出富有强劲生命力的人物。
二、历史的迷失与悲剧的诞生
人是历史的主体,但人作为历史的人又是把自己交付给历史了的,换言之,社会的人处在人的社会中,在其变革自然,推动社会发展时,必然把自身确立为客体,作为自己认识和实践的对象,这就是人作为主体自身的双重规定。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并不是以个体为“本位”的,它直接地表现为人的“类”的发展,而“类”的发展又是以个体的片面化、不发展、完满性的牺牲为代价的。在谈到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地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如果亚洲的社会善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的话,“那末英国不管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8〕这就是冷酷无情的历史理性,它以“恶”的情欲开拓着历史运动的方向,以历史的尺度否定个体自我发展的呼声。在黑格尔看来,人人都是理性目的的工具,即使是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躲避这种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但是,人毕竟是感性的个体存在,他并不因为看到了“类”对个体的剥夺的合理性而放弃对这种剥夺的反抗;人毕竟是道德的存在物,有着“心灵性”的高级本质,他并不因为看到了历史运动的非道德化的合理性而放弃对非道德的历史的抗议;人毕竟是具有主体精神和多种需要并追求自我实现的能动个体,他并不因为看到历史对人的拨弄的正当性而放弃对这种正当性的质疑、放弃自身真正地走向自我、超越历史的正当追求……人类必然(也是应该的)地以价值的尺度抗议历史的尺度,以个体的人的人性、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为正义原则来看待历史理性、怀疑历史理性、否定历史理性。面对无法超越的客观历史理性,人希图保持心灵的高贵完满性,要求历史照顾(个体)人的具体特殊性,实现生活的主观道德性……一方面,我们感到了主观的先验的目的与客观的经验的手段的分离,看到了道德的目的不能以道德的手段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又认识到“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9〕这便构成道德情感与历史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人作为历史的人质,便充当了悲剧的主角。
曹禺的意识倾向是十分复杂的,他人性理想的核心是爱与意志的有机组成和辩证统一。缺乏爱的意志将走向冷漠(如周朴园、李石清、潘月亭等)导致暴力、走向对社会的操纵和对强权的膜拜,人沦为“情感的空壳”;缺乏意志的爱则成为无谓的感伤(如周萍、焦大星、曾文清、高觉新等),矛盾的奴隶,面对生活的困境不能进行有效的抗击,造成对他人和自我的伤害,人沦为“生命的空壳”。理想的人性应是情感的充实(深度)和生命的充实(力度),既能从生命充实角度抗议文化理性的压抑,又能从情感充实角度控诉历史理性的罪恶。曹禺对“意志”与“爱”在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充满了辩证精神。
在曹禺剧作中,我们看到一些沦丧了自我的主体性的喜剧角色,他们永远在场,却又永远缺席。在客观规定性面前,他们还没有张开自己正义的反抗旗帜时便俯首称臣,缴械投降了。黄省三是绝对善良无辜的,只想按照合乎社会规范的行为求得自己的生存,而社会并未为之提供这样的生命空间,并不给其“循规蹈矩”以善意的报答。当其明明知道这个社会并不是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时候,他仍然不愿也不能以违背理性文明准则的方式反抗这个非人的社会理性文明。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哀怜、乞求,不会发怒,不会抗争。李石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不是替黄省三这样的人预备的,入木三分地指出黄省三是如何为理性文明奴化、压扁,成为历史理性可怜的牺牲品的。就此而言,李石清和鲁贵、王福升等社会“油子”却自有其清醒过人处,其毫无持操的行为亦有其现实合理性。他们认识到了所谓理性文明神圣正义的无根性,认识到了理性文明不过是强者招摇的旗帜和遮羞的破布,认识到公正的理性文明对善良无辜者的播弄和不公,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游戏的态度播弄调戏理性文明,以“历史理性”反抗历史理性。但由于他们不具有蘩漪、仇虎的神圣的目的,追求公正的动机,因而他们只是历史理性养出的不肖之子、孽子、浪子,而不是反抗历史理性的悲剧英雄。只要历史理性能给他们点滴的好处,他们就会对其俯首贴耳、卑恭屈膝、无所不为。他们既无高尚的使命,亦无坚贞的信念,他们表面是与历史理性捣蛋,实质是利用历史理性以满足一己私欲。
曹禺一方面要肯定人感性生命力,张扬人的生命意志,必然以历史主义眼光写出富有强劲生命力的人物;另一方面,又有道德回归倾向,对丁大夫、愫芳、瑞珏的传统美德赞不绝口,偏爱至深。一方面肯定历史情欲的正义性,一方面又怀恋道德主义温情。一方面他爱人,写出其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也恨人,恨那些卑微、琐碎的小人。〔10〕另一方面,他又恨只讲强权的人。“我恨这不平等的社会,我恨只讲强权的人。”可见,埋藏于曹禺心灵世界深处的仍然是承继于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哲学,洋溢着对“穷”的诗意向往和赞美,流露出道德至上、精神本位的价值取向,并没有站在历史主义高度,从社会进步角度肯定“恶”的历史作用,而有的只是对它的恐惧和否定。因为曹禺关心的是人的命运,人的灵魂痛苦,人的精神追求。上述二元矛盾分离的实质在于:在情感关系中,肯定那些敢于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可喜的英雄;在社会关系中,对只讲强权的人充满峻切的道德的愤怒。这有其生活经验作基础。1927年,其父投资破产,于是曹禺对现代资本竞争中的胜利者(他们必然采取不仁的手段获取成功)充满切齿的憎恶和潜在的心理拒斥。愈是到后来,其道德的诗化倾向愈是明显而突出。“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为什么允许金八他们这么一群禽兽活着?”方达生的困惑表达了作者的道德主义倾向。《日出》以“天之道”否定“人之道”,实际上暗含了作者潜在的大同世界理想,人人均等地合乎道德地生活,没有争斗,没有冲突,只有和谐。《北京人》在描写曾家与杜家的对抗关系中作者的全部同情都放在了曾家。袁任敢博士那段话充分、完全地道出了曹禺思想的实质和理想本质:(1)从文化批判视角看,在人的精神天地中,人自由地生活,一切文明的束缚烟消云散,克服了理性对感性的压抑,消灭了道德对生命的吞吃,人自由地美学地存在;(2)从社会批判视角看,在人的现实世界中, 人合乎道德地生活,没有利害冲突,各行仁义之事。这两者的连接在其“精神”性上。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大同观念本能地仇视对物质的巨大热情和不竭贪欲,建构了物质与精神的虚假关系。在这个倒错的关系中,精神被置于本位的地位,具有“本体论”价值,是人的存在之根和生活目标,“安贫乐道”成为理想的人格范型,物质情欲的“恶”被贬到无底的黑谷。曹禺的世界观根本上仍是传统的道德哲学;对物质情欲的恶性膨胀持否定态度。在他那些洋溢着悲剧精神风采的动人篇章中,作为具有“恶”的情欲的英雄好汉无一不是因其表现了“人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反抗”而受到肯定和赞美。蘩漪表面是追求肉的满足,实质是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贯彻自己作为人的生命意志,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亦即只有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中,曹禺才肯定反抗理性文明的“恶”的精神情欲或精神情欲的“恶”,这是从生命本位、生命正义立场出发的。因为生命意识的觉醒须以个性主义为前提,生命意志本身必不可免地包含有“恶”的因素。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对物质情欲的“恶”则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表现出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
曹禺创作从整体上讲,其审美视角有从文化批判向社会批判转化的倾向(虽然这两种批判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因而诗化道德的态度日趋明显。体现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是对丁大夫、愫芳、瑞珏这些道德美化身的“善之花”的赞美。——从对高傲女性的赞美到对善良女性的赞美,因而对不具有善良美德的曾思懿持偏憎态度,而无视她真实的痛苦和存在合理性。他肯定愫芳、瑞珏自我忍耐、自我牺牲、自我完善的道德哲学,赋予她们沉静深挚的灵魂而不是张狂野性的情欲。所以,在《北京人》和《家》中,他埋葬了旧的制度,却同情其中的人的命运;他批判了旧的文化,却赞美那种文化培育的情感。同时,对与“善之花”构成情感关系的懦弱的男人的同情和爱护增加了,嘲讽和批判减弱了(与“恶之花”构成情感关系的这类男人遭受了作者无情的揶揄)。
三、自我的迷失与悲剧的诞生
“现代文学的最高峰,往往采取最终的两重性形式,这是诚实的天才对世界所能作的最好的描绘——即二元论没有得到解决而产生的诗境。”〔11〕曹禺即是这样的诚实的天才,他看到了人的悖论,看到人的自我迷失,艺术地表现人的双重否定性悲剧宿命。
人的自我悖论主要是指人的本质的不确定性(虚无)与人的存在的具体可感性(实有)的矛盾,主体肯定自我与肯定自我的对象(自我对象的存在是确定自我的前提)的矛盾,人的自由本质与人的本质不自由的矛盾。
人的悖论即是人的宿命、人的悲剧性。生存就是痛苦,自我就是地狱。即如前述,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中,人是文化的人质;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是历史的人质;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人是自我的人质,是自己命运的人质。人的悖论使人的追求都具有自我否定性。因此,不是别的什么存在,正是人自身的存在否定了人自身,把人送进深渊;人既是合理的,又是片面的;既是无辜的,又是有罪的。
曹禺悲剧艺术的深刻性正在于其揭示了上述人的悖论,表现了人的双重否定。首先,他展示了双重世界,即真实的世界与虚幻的世界,通过人物在上述世界中的感觉颠倒达到对人物自身的否定。这些人物在虚幻的世界中反而感到真实、自在、幸福,在真实的世界中反倒感到虚幻、造作、痛苦。周冲生活在自筑的对四凤、对母亲、对世界的爱的梦幻中,“他藏在思想的堡垒里,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他不能了解他自己,他更不能了解他的周围。一重一重的幻念茧似地缚住了他。他看不清社会,他也看不清他所爱的人们。他犯着年轻人Quixotic病,有着一切青春发动期的青年对现实那样的隔离。他要现实的铁锤来一次一次地敲醒他的梦。”〔12〕对这个不断探寻着自己的梦幻者来说,当他看清了周遭现实,当他的梦被敲醒之时,他的真实生命也就终止了,最后,他否定了自己对四凤的爱的真实性——“大概是胡闹”。方达生也是个生活在幻觉中的人物,他并没有感受到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真实性,而是构想了心中世界的真实性;他并不真正地了解这个社会、他的爱人、他自己,在剧的末尾发出“我们要做一点事,要同金八拚一拚”的呐喊也只是个自我讽刺。作者之所以没有把这个唐·吉诃德似的先生夸张得比较可笑些,只是于心不忍。可见方达生这个“好心人”对他置身的世界仍是隔膜的,他只能在虚幻的世界中按照自己的思想路线行动,当其按自己主观想象在真实的现实世界中行动时只能表现为迂阔可笑,只能遭致失败,因而,可以说,他与生活是脱节的。愫芳苦苦地忍耐,默默地期待,在幻想中咀嚼着与文清的爱之诗,并幻想(更确切地说,是自己强迫自己不能怀疑)曾文清这只病态的鸽子(生命的空壳)能振翅高飞。不过,她的梦幻愈来愈被严酷的现实剥去其玫瑰的彩色,或者说她终于有一丁点勇气正视自我,稍稍降低了一点自欺的程度,自觉松动了与自己爱情寄托对象之间的价值联系,所以,当瑞贞问她想不想见到文清时,愫芳说出了一句富于生命觉醒意味的话:“见到了就快乐吗?”在此,我们不是能深切地感受到愫芳的悲凉心境,感受到她悲剧性的人生吗?
其次,曹禺表现了反抗对象的双重本质即片面性与合理性。历史理性,文化理性的片面性对人压抑和剥夺造成了人的悲剧,但人对历史理性、文化理性的反抗势必损害其合理性(因为它们不是绝对片面的,而是合理片面的),而这种合理性又得到(也应该得到)了反抗者的认同和敬畏,因此对它的干犯必然成为对自己的干犯,这种干犯导致自我否定,造成了反抗者的悲剧命运。《雷雨》最后的结局是现代家族伦理意识的胜利,《原野》表现了对理性文明秩序悲壮反抗的失败,悲剧主人公低下头颅,自觉向“宇宙正义”认罪。
再次,曹禺表现了悲剧主人公的双重属性,这种双重性可分两种情况。其一,曾文清、高觉新、焦大星、周萍等人物生活命运的悲剧性和文化品格的喜剧性,他们有着充盈的情感,却缺乏坚强的意志,他们情感的真挚性无辜性使其生命带有悲剧色彩,而他们意志的稀薄和软弱使他们缺乏“恶”的情欲,缺乏反抗命运的悲剧精神。其二,蘩漪、仇虎、金子等人物的无辜性与有罪性。他们受到生活的不公平对待,本是无辜的,为了自己的权利起而反抗也是正义的。但他们反抗的并不是绝对片面的东西,而是具有能得到自身认同的合理性的东西,对它的反抗,必然干犯世界的统一,破坏它的秩序,因而这种反抗又是有罪的。他们有着对痛苦的清醒意识和对前途的绝望态度,明了自己即使在二难窘境面前也应该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不是完全的自由,也不是命定的不自由,而是矛盾的自由,因而他们是自相矛盾的,既感到自己是无罪的(遭遇的不幸不公)又是有罪的(如果自己选择“不反抗”或不选择“反抗”,那么自己将是绝对无辜绝对无罪的)。因此,他们最后都以纯粹的善和绝对的合理要求自身,认识到自己的片面性,否定了自己的合理追求;从反抗理性到皈依理性,从“情感的憧憬”到“无名的恐惧”。最后是感性冲动向理性冲动屈服,情欲在宣泄了它不可一世的威力后,宁静地皈依于“永恒正义”的旗帜下,宇宙在经过一阵喧哗骚乱后复归和谐统一。
注释:
〔1〕尼采:《朝霞》105节。
〔2〕尼采:《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的远征》第 44节。
〔3〕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陷》(中译本)第2页。
〔4〕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第89—90页。
〔5〕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323、326页。
〔6〕〔7〕曹禺:《〈雷雨〉序》,《曹禺研究专集》上册第1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59页。
〔10〕《曹禺论创作·序》
〔11〕R·W·B·路易斯:《〈熊〉:超越美国》, 见《福克纳评论集》第207页。
〔12〕曹禺:《〈雷雨〉序》。
标签:曹禺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理性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文学论文; 雷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