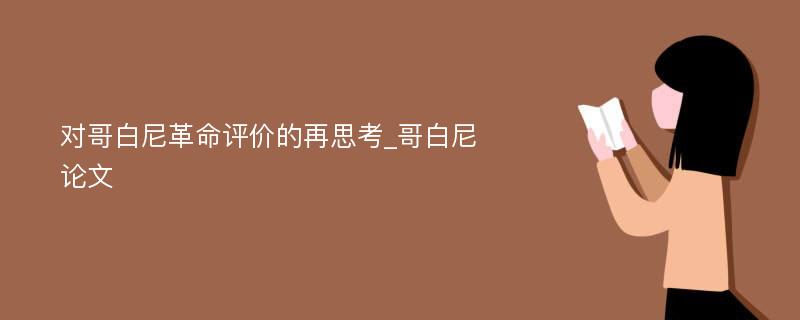
对哥白尼革命评价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白尼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概要评价了哥白尼革命的历史意义。重点对这次革命进行反思:认为“日心说”并非尽善尽美,“地心说”也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前者取代后者是一种科学史上的必然和进步。作者还认为经院哲学不能全盘抹煞,新航路的开辟及新教改革对《天体运行论》并无促进作用。
关键词 哥白尼革命 日心说 地心说 再评价
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十六世纪波兰天文学家,他的天文学上的巨著《天体运行论》(以下简称《运行》)点燃了近代自然科学向欧洲中世纪神学宣告起义的火炬。从那时开始,这人类智慧的火炬象奥林匹克圣火一样代代相传至今,照亮了人们从物质到精神、从宏观到微观的每一领域。本文简述并评价这次革命,且试图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视角来理解这次革命并作些哲学思考。
一、哥白尼革命的多重历史意义
哥白尼之前在天文学上占统治地位的天体模型是“地心说”。这还是公元二世纪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的理论〔1〕。 这个不合事实的理论在当时已沿用一千多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显得越来越不精确和繁琐。可由于人们被表观现象所欺骗,特别是天主教会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后把它定为宗教信条,以致在御用天文学家甚至整个西方社会中奉若神明。因此,“地心说”也就和人们由日常所见而积淀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教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连在一起。科学在当时是神学的婢女,教会对新科学总是尽力压制,人们稍有科学探索的越轨行为,便会招来教会以异端名义的迫害,所以新科学的微光很难闪亮。
那时,文艺复兴运动正蓬勃发展,哥白尼追逐着这个运动的潮流,刻苦攻读,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还接受了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他大胆怀疑“地心说”中的结论,指出它的不准确性,青年时代就立志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取代它;他以超出时代的科学精神,在古希腊罗马著作的启发下,历尽三十年的艰辛观察、演算,终于完成了天文学巨著《运行》〔2〕, 提出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日心说”天体模型。
“日心说”多重的历史意义很值得我们探讨。
⒈新科学的起点。根据现在一种“最小质能空时参考系”,日心坐标要比地心坐标优越五个数量级,即其简单与精确度要高出上十万倍。那么即使仅从天文学角度看,“日心说”也具有巨大的现实科学意义。它潜在的科学意义更是难以估量,它在革新天文学的同时也作为了整个科学体系的突破口,致使刻卜勒、伽利略、牛顿的卓越成果接踵而来。“对于刻卜勒来说,它(指日心说)是他发现行星运动定律的必要前提,而对牛顿来说,它打开了一条合理解释这些定律的道路”〔3〕。 从科学发展线索上可看出“日心说”是近代科学内在的原始逻辑生长点,是所有新科学的起点。
⒉刷新了人们的世界观。“日心说”“地动”的观点要求人们以全新的甚至是头脚倒置的眼光来观察和感受世界。爱因斯坦认为“哥白尼的这个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也帮助了人们在宇宙观上引起了决定性的变革”〔4〕。库恩也看到“哥白尼以后, 天文学家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同时,正如科技史家丹皮尔所说的,“哥白尼的天文学不但把经院哲学派纳入自己体系内的托勒密的学说摧毁了,而且还在更重要的方面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与信仰”〔5〕。它摇动了教会一千多年来的精神权威。从这以后,科学中的神学色彩逐渐消弱。这一点,恩格斯有精到的论述:“在科学的猛攻之下……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6〕。
⒊在哲学史上带来了新的活力。人们根据简单常识、直观经验得出的理论不可信了,势必认为理论应当以实测数据为基础,并由实践来检验,应象哥白尼一样根据事实,看透隐藏在“日出日落”的表现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这样,开创了科学理论与直观经验之间非直接同一的辩证结合的新传统,在哲学领域引入了理性思维,近代唯物主义的很多万分也初见端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为哲学史提供了包含人类认识三个阶段的一个典型的科学事例:对于日出日落、行星运行的观测属于感性认识;从观测中总结出的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是知性认识;而通过对观测资料进行了起直观经验的总结概括的哥白尼学说则是理性认识。“日心”对“地心”的超越正好对应于康德学说中从知性到理性的飞跃〔7〕。
哥白尼革命其理论内容是天文学上的一次飞跃,在科学的范畴里便是一次开天辟地的科学革命,历史时代背景决定了哥白尼理论的诞生、传播至取得胜利无比艰难,而正是这种因素又决定了它成为人类历史很多方面影响巨大的一次革命。歌德曾热情地称颂它“自古无一种创见,无一种发明可与之相比”。可以说,只要人类存在,哥白尼革命就会在历史上空闪亮!
二、“日心说”革命给科学史的反思
哥白尼,因其巨大的历史影响而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通常把对传统的否定或超越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不少人把它看得过分简单,就认为是勇敢的哥白尼战胜了残酷腐朽的教会,抛弃了可恶的“地心说”,创立了先进的“日心说”。明眼人一定会问:“日心说”就那么完美得滴水不漏吗?“地心说”就那么该全盘否定抛弃吗?哥白尼革命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发展的科学及人类的智慧启示我们该去思考这些及其它更多的问题。
⒈“日心说”并非尽善尽美。应该说,“日心说”本身有缺陷。“太阳中心说——顾名思义,以现代宇宙观来看,就是错误的。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宇宙是没有中心的。哥白尼认为行星轨道是正圆形,且是匀速运动,这在刻卜勒即已总结出是椭圆〔8〕且变速运动。 “日心说”体系还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其理论依据源出“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宇宙先定简单和谐论。贝尔纳曾指出:“对于这项革命性的改变,他所操的理由基本上是哲学的,是审美性的”。“兼有两点,一是重返到对宇宙最古而确然玄幻的见解,一是推崇中央王制,‘太阳王’”〔9〕。而相对“地心说”在当时其准确度的提高很有限,就当时来说,库恩认为“即使是哥白尼更为精致的学说,比托勒密系统既不更简单,也不更精确”。“没有导致日历上的任何改进”。直到刻卜勒,哥白尼的理论几乎没有改进由托勒密做出的行星位置的预言”〔10〕。以上种种不足,致使象丹麦的第谷等这样著名的天文学家也不愿意接受它,造成在天文学家中传播的困难。刻卜勒、伽利略等人接受“日心说”主要是看上了它潜在的简单性。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在理论的深广性方面,从较长远的观点来看,“日心说”提高了天文理论的简单性、准确性和抽象性,但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说,缺少了亚里斯多德学说的那种宏伟的广阔性和严密的完整性。
哥白尼革命和其他科学革命,也和一切形式的革命一样,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它产生和完成的过程。这次革命有它的历史条件:欧洲经济日积月累的发展,东西文化的交流,文艺复兴的兴起,航海业的发达,都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天文学、数学的进步。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也是从罗吉尔·培根到达·芬奇的近代科学的若隐若现则使之在文艺复兴后期的发生成为必然。这次革命也要依赖传统:经院哲学给了科学以积极的张力,古希腊的智慧给了哥白尼以指引,当时天文学在意大利及其它国家初步的发展则充当了先导。维尔纳大学的天文学教授普尔巴赫和约翰·缪勒、瓦尔特等的天文观察记录和著述为哥白尼的伟大发现奠定了基础,意大利的诺法拉则直接启发和鼓励了他。再者,我们还可注意到这次革命的促成与别的科学革命不同,科学本身以外的因素在发挥着重要影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库恩在评论导致这次革命的成因时曾说:“更全面的说明还要考虑中世纪亚里斯多德派的批评,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以及其它一些重大的历史因素”〔11〕。进一步看,革命要历经一段过程。卡约里曾经说过,哥白尼作出的反对托勒密的论点不是结论性的,完全推翻“地心说”需要刻卜勒。就这次革命抢救出自然科学的意义来说,哥白尼只是革命的点火者,向神学下了挑战书,“是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旗手”〔12〕,而不是阵前搏斗的士兵,真正与神学作战、与世俗的愚昧作战的是伽利略,“一直到伽利略把他的新发明的望远镜指向天空,发现木星及其卫星,好象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的时候,哥白尼的理论才声名大著”,“哥白尼的体系的胜利是姗姗来迟的”〔13〕——只是在牛顿时代才获胜。一般认为科学形成系统理论结构则是始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就是说,这次革命至最后胜利经历了一个多世纪。
⒉“地心说”也有可取之处。“地心说”也并非一无是处。是古希腊(当时属罗马帝国)托勒密高超地运用欧几里德几何学,对亚里斯多德、阿波罗尼和希帕克等前人的学说进行系统的整理,吸收东方天文学成果而总结出来的,对古时观测的天文现象可以解释,并能较准确地预测行星未来某时刻的位置,以及日蚀、月蚀的时间,“那时这个体系在预言恒星和行星的位置变化方面取得了值得赞美的成功。任何一种其他古代理论都做不到这么好”〔14〕。“地心说”有它适应的范围,“在当时的观察所要求的精确度范围内,用来解释事实是相当成功的”〔15〕,相对于那种面对上天茫然无知是一种莫大的进步,比中国张衡的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这种较为浅陋的模型也科学多了,它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有一定地位的,“在推动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中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16〕。哥白尼也曾承认他利益于“地心说”不浅。那么我们对“地心说”就不能一棒子打死。凯德洛夫指出,科学上的革命从一种世界图象到另一种世界图象的过渡非谬误——真理,而是从比较不完备的相对真理——另一比较完备的相对真理。这也正是“地心说”与“日心说”的关系。
而今,我们可轻易指出“地心说”中的错误,并因此而更多地注重对它的贬斥。这也可类比于我们嫌弃哥白尼“日心说”中的种种不足或追究古希腊那些凭空想象的唯心主义体系诸如此类对前人错误的不满。这种态度是否有真正的理由呢?科学史家G·萨顿曾说过, 错误在科学史上特别有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价真理,而且还能帮助我们避免将来发生类似的错误。“从错误比从混乱中更易于发现真理”〔17〕。今天的真理明天或许要被重新考虑,而谁又知道昨天的错误明天会不会变成近似的真理呢?以前被唾弃的东西往往在新的领域里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复活。爱因斯坦正是往休谟的怀疑论回摆才发现了相对论。“过时的理论不能因为遭到摒弃就一定不科学”〔18〕。看来,我们对科学上类似地心之论的错误是不能连根拔起地扔掉的。
我们再从天文学上宇宙观的进化轨迹:原始零碎的天文观察——亚里斯多德、希帕克等人的地心理论——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无限宇宙观——大爆炸理论——暴胀宇宙学来看,“地心说”“日心说”两者都是天文理论发展的一环,都是人类智慧与实践结合的产物。虽然从外在影响来说,后者相对于前者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科学理论的内在结构与层次发展来看,却并无实质性进展。两者都一样,未曾在描述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深层理论结构(这一点直到牛顿才完满做到),只能算是浅层描述性的进步。卡约里、爱因斯坦、罗素等人都持这个观点。据人们所说的库恩的范式概念的六个层次〔19〕,“日心说”相对“地心说”主要是在“理论”和“世界观”层次上的进步。
由上分析可见,“地心说”是有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很多方面与“日心说”相比并不逊色。
⒊证明科学克服自身的阻力而发展。把这次革命放入自然科学发展的大河,可以更透彻地理解它,也可加深对科学的了解。
首先,这次革命验证了库恩的“危机——革命”〔20〕的科学革命结构的理论。在新旧理论转换之际,旧的理论及传统会困兽犹斗,而新的事实又向旧的框架频频攻击使之危机。正是哥白尼及同时代天文学家们新的观测使“地心说”解释不了而造成它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使天文学家们趋向哥白尼的因素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了危机。首先是由于危机,才有了新的创造”〔21〕。于是导致“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革命。科学史上,是光电效应、黑体辐射、原子光谱等实验事实中连续向牛顿创立的经典物理学发难而造成危机,从而使“相对论——量子力学”体系应运而生。再看道尔顿的原子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科学理论都是从它们产生前夕的危机阵痛中诞生的。“危机——革命”克服自身阻力而进步是一个普遍的革命模式。这也是彭加勒、爱因斯坦等所主张的。
其次,通过对这次革命及科学史上其它革命的观察,可正确看待科学自身的阻力。这是非常遗憾的:科学经常遭受本身的阻力,原有的科学结构的思维方式对新的观点、理论总是排斥和压抑,如同生物体内的“排异”现象。“日心说”不为第谷等天文学家所接受,同样,光的波动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玻尔的互补理论在诞生之初,遭受的阻力倒主要不是来自社会而是出自科学本身。是否这种本身的阻力与生俱来并朝夕相伴呢?科学史给与人们的是一个肯定的回答。科学家是人,人的一切他都具有,他永远也无法超越自身。人们会恼怒地斥责坚持“地心说”的天文学家,可连爱因斯坦也难免陷入他曾经深切厌恶且发誓避免的不先验自明的结论中。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经常以骂态度对待的阻力进行反思。科学自身这种阻力应该可以比作如自然界中的摩擦阻力。摩擦阻力阻碍有摩擦的物体运动,降低了物理效率。但一旦没有这种阻力才更可悲:那样人只要迈出一脚就再也停不下来,地球上的物体也统统无法维系。可见摩擦阻力少不得。科学自身的阻力正是这样一种必要的张力,是科学不可缺的,它可“保护规范不太容易遭到抛弃,……可以保证科学家也不会轻易受到迷惑。”这种阻力“并不违背科学的标准,而是科学研究本身的一种标志”〔22〕。
再次,通过思考与反思,更会发现这次革命势不可挡。我们考察这次革命时,第一眼看出的是“地心”“地静”等观点不是太荒唐了吗?肯定会被主张太阳才是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运动轨道的中心的观点所代替;可不,再深入一下:“日心说”并非完美无缺,“地心说”也有可取之处,于是似乎又可冲淡革命的意义;但再反思一下,又会发现“日心说”代替“地心说”毕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也是科学发展、人类进步的要求。
从哥白尼开端的新科学,至今已经历了四个多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可以震惊历史上任何一位无论怎么大智大慧的科学家。会喝斥亚里斯多德,会瞧不起托勒密,可以指教哥白尼,可以嘲笑牛顿,也会使麦克斯韦谦虚,甚至令爱因斯坦难堪。前人的成果总会被后来的成就覆盖,没有哪一个真理永恒绝对。纵观科学史,只有发展的观点和开放的体系才真正明智。“终极”——这是谁也不敢也不可能抱住的一个概念。
⒋经院哲学不可一笔抹煞。在这里,我要说中世纪经院哲学也不是有百害而无一益。人们总是看到它是教会文化的代表,崇尚以信仰的权威代替理性的思考,禁锢人的思想,因而通常尽情地痛骂它的昏昏无为、把人的精神往僵死胡同里带。这种观点是欠全面的。经院哲学是当时的传统文化,任何进步和革命都不可能是突变的,无法同传统决裂。经院哲学给新科学两种社会张力:唯实论把科学作为神学婢女引入了社会舞台,客观上推动了古希腊已有一定基础的科学的复兴而给与了一种肯定性社会张力;正统经院哲学花大力气去否定唯名论的科学倾向,又在客观上强化了科学的社会影响。与东方文化对科学的超脱和漠然态度不同,经院哲学不是对科学不闻不问,而毕竟把科学当作一个婢女引入了神学领域。自然,这个“婢女”在天主教这个老巫婆面前更显得美丽动人而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科技史家丹皮尔曾在这一方面肯定过经院哲学:“毫无疑问,经院哲学由于告诉人们宇宙是可以了解的,的确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23〕。因此,经院哲学对新科学也有某种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不能一笔抹煞。
⒌新航路的开辟及新教改革对哥白尼革命并非促进作用。人们有时把哥伦布及麦哲伦开辟新航路与十六世纪初期的新教改革放入促进哥白尼革命的时代背景中,当作是革命产生的推动因素。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哥伦布首开新航路是1492年,到它对社会产生影响肯定晚于此年,是以后的事了;麦哲伦及其同伴的环球航行更是到了1519—1521年。而哥白尼《运行》的出版尽管是在1543年,但他1491—1494年在波兰克拉科夫大学求学时即有了“日心说”的萌芽。故不能朦朦胧胧地把新航路的开辟当作革命前提。当然,在此之前航海技术的进步对人们提出了重视天文学的要求,促进了哥白尼的老师及天文学前辈们的成果,因而应该是这次革命的前提。所以要把这两者:新航路的开辟与在此之前的发达的航海业区别开来。
也许新教改革在其孕育期,它的某些先进思想对哥白尼革命有过间接的推动作用,但马丁·路德在1517年及随后加尔文的新教改革都在“日心说”萌芽之后,谈不上对哥白尼能有什么帮助。这里有必要澄清新教与《运行》的关系:新教对《运行》是毫无促进作用可言的。一方面,两者是文艺复兴在不同领域的产物,也是在不同领域的反映,是一种并列关系。促进新航路与新教改革的时代背景实际上也正是《运行》产生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新教是仇视新科学的。“日心说”是对人类信仰的动摇,是对《圣经》权威的否定,也是对人类传统观念的冲击。在这一点上与新教的关系本质上是与宗教的对立:宗教要求信仰服从,可不必追问信条的来历,而科学讲求事实,追求真理。更甚的是,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比罗马教廷更专制,对教徒管理更严,对异端的打击更厉害,因此对被看作是异端的科学的迫害更残酷。路德和加尔文对《运行》的出版气急败坏,竭尽嘲笑谩骂之能事。加尔文曾把塞尔维特活活烤了两个钟头才烧死,大大超过了罗马天主教处死布鲁诺的血腥程度。恩格斯断言过:“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所以, 我们不能因为科学与新教同是天主教的敌人而误把两者当朋友。
我的上述思考,是对哥白尼的“日心说”及其引起的革命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考察,从不同的背景来理解,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观察,尽量使我们对这次革命的了解更全面、更深刻、更丰富一些。
收稿日期:1995—10—15
注释:
〔1〕参见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144页,115页。
〔2〕《天体运行论》是一部巨著,共六卷。包括宇宙概观,天体运行基本规律,地球、月球、内行星和外行星的基本规律及数学论证。对本文来说,主要注重其中的“日心说”这个理论。
〔3〕亚·沃尔夫:《十六、 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0页。
〔4〕《爱因斯坦文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601页。
〔5〕〔10〕〔11〕〔14〕〔17〕〔18〕〔21〕〔22〕分别引自:T、S、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63页,127页,127页,58页,57页,15页,2页,63页,12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29页。
〔7〕参见朱亚宗著:《近代科学思想史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3页。
〔8〕爱因斯坦已明显看出非真椭圆——作者注。
〔9〕贝尔纳[英]、著:《历史上的科学》, 伍况甫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1页。
〔12〕黄顺基, 刘大椿著:《科学的哲学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6〕童鹰著:《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19〕参见李醒民著《科学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第70页。
〔20〕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完整地表述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