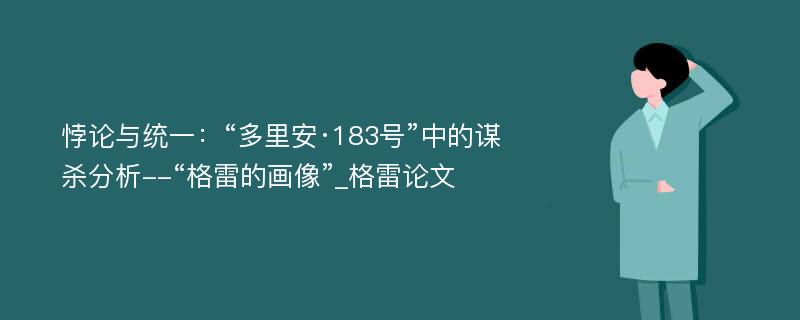
悖论与统一:《道连#183;格雷的画像》中的谋杀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谋杀案论文,悖论论文,画像论文,格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英国文学史上,王尔德(Oscar Wilde)是继佩特之后最有影响的唯美主义理论家,他在艺术创作上亦有很高的造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王尔德研究一直是国内国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九十年代后,王尔德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新的一轮‘世纪之末’似乎使得王尔德再次成为英美等地的热门话题”(张介明30)。而在我国,“90年代的王尔德研究在深度、广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吴学平156)。从这两篇重要的研究综述来看,国内外对王尔德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译介领域都有丰硕的成果,然而不足之处在于,对于王尔德所身躬力行的“为艺术为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确实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学者们往往过多地关注其“艺术至上”的统一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悖论的一面。在《道连·格雷的画像》①中,小说的情节简洁而清晰,其高潮部分集中体现在两桩谋杀案上:一是谋杀画家贝泽尔(Basil Hallward),一是谋杀画像而造成了自杀。这两桩具有哥特式风格的命案,蕴涵了王尔德美学思想悖论与统一的复杂性、深刻性。
一、自由的享乐:谋杀画家贝泽尔
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贝泽尔与道连·格雷(Dorian Gray)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首先,贝泽尔与道连·格雷是画家与模特儿的关系。道连·格雷本身娇美的外貌、高贵的出身、优雅的气质是贝泽尔遇到的最好的艺术模本,也使得贝泽尔的艺术造诣达到了顶峰;其次,贝泽尔与道连·格雷是朋友关系。在生活上,贝泽尔企图引导道连·格雷向善的方向发展,从而维护其纯真、道德高尚的生活与艺术的完美复合体,这与亨利(Lord Henry)所代表的维多利亚时期享受青春、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形成截然鲜明的对比。从情节的一开始,贝泽尔与亨利展开了对道连·格雷何处何从的争夺,显示了对道连·格雷友情崇高的一面。再次,由于贝泽尔“不愿展出这幅像,是因为我担心它会泄漏我自己灵魂的秘密”(9)。因此,道连·格雷作为画像艺术成品的偶然因素,与画家的情感、灵魂结合奠定了画像的艺术内涵,而又因为道连·格雷的一个为青春之美而祈祷的祷告的实现,画像又成了道连·格雷经受岁月摧残的替代者、灵魂真实面貌的展示品、道连·格雷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物和见证人。这时,画家与道连·格雷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贝泽尔为了追逐艺术的更高境界,对道连·格雷的本身之美进行着呵护,力图使其免于社会生活的浸染、腐化,乃至堕落;另一方面,由于道连·格雷为了青春而把灵魂出卖给了画像,画像和人物交换了位置,这时贝泽尔出于艺术和友情的目的对道连·格雷进行劝导,就在无形中对其追求享乐形成了一种暗中的监控,也使得道连·格雷不会越过生活的本真情况而遁入到一种毫无约束的完全自由境界。这种不自觉而形成的监控人身份使道连·格雷的灵魂袒露和社会制约紧密的联结在一起,对其无节制的享乐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也是铸成画家被谋杀的原因之一。
而道连·格雷一出场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贝泽尔的向善劝导和亨利的享乐观是摆在他面前通往崇高与罪恶的两条道路,只不过在亨利的诱导下,道连·格雷不仅认识到了自身的美和灵魂深处的种种欲望,并且身体之美和出身的高贵是他实现自己欲望的得天独厚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亨利为代表的社会文化赢得了对道连·格雷的胜利。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向一个更具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自由主义转变”(佩里176)。但自由主义和资本结合的文化状况却导致了艺术处境的艰难和堕落享乐的盛行,“我说这一切都是那种蹂躏艺术并把商业敬奉为神圣宗教的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制度以极端的愚蠢为其主要特征”(莫里斯278)。王尔德让道连·格雷追随亨利的步伐一方面是对社会文化的回应,而更深的层次是“reaction against a utilitarian culture”(对一种功利主义文化的反对)(Brown 28),也是王尔德本人追求快乐原则的体现,“我一点也不悔恨自己曾经为快乐而生活,……但只继续着同样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它是有限的,我不得不转换一种方式,……当然,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艺术中预示过、预想过了”(孙宜学218)。王尔德的快乐哲学不光蕴涵着身体与灵魂的享乐,还包含着其追求方式的多样性,所以,这部小说的自传性质锻造了道连·格雷离弃贝泽尔、投怀于享乐观的必然性,这又使得双方处于一种矛盾的对立之中,隐伏了贝泽尔被谋杀的必然因素。
道连·格雷追求快乐是以一系列的作恶行为来实现的,其中最显著的事例就是为了一桩虚假的爱情而导致了戏剧演员西碧儿·韦恩(Sibyl Vane)的死。首先,道连·格雷与其相识是出于猎奇与冒险的动机;其次,对其抛弃的原因在于西碧儿·韦恩不能完全的活在她所出演的艺术世界里,这违背了道连·格雷追求爱情—艺术—体的初衷;再次,对其服毒自杀,道连·格雷视为是为了艺术而殉身,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不仅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体现,更显示了道连·格雷内心的冷漠与自私。从以上可以看出,道连·格雷这次荒唐的爱情活动不是源自内心的相亲相爱,而是一种贵族似的猎艳游戏,这在画像上深深地留下了为享乐而堕落的痕迹。之后,道连·格雷的享乐活动都使得他离原始的纯真自我越来越远,也使得画像对其罪恶的记录越来越多,这不仅使其自身处于灵魂与肉体分裂的焦虑之中,也加深了贝泽尔与道连·格雷的矛盾冲突,为了解除这种焦虑的苦痛,同时把自身从贝泽尔的监控之中解放出来,谋杀画家已经是势在必行。
道连·格雷谋杀贝泽尔的理由是充分的:第一,道连·格雷认为享乐是自由的,而贝泽尔的艺术、道德操守以及对他的劝导是一种无形的制约和障碍;第二,道连·格雷认为享乐之后灵魂痛苦的根源在于贝泽尔,是贝泽尔的画像让他看到了灵魂的另一面,这对其自由的享乐是一种控诉和指责,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人性的分裂和焦虑;第三,贝泽尔在发现事实的真相后,依然劝告道连·格雷用祷告的方式来获得灵魂的救赎,对于道连·格雷来说,这种说教的形式只不过是世人蒙骗自己和社会的虚伪做法,其力量不能够完成灵魂的救赎,也不足以战胜其心中日渐膨胀的享乐欲望。而对于王尔德来说,这是让社会流俗的观点左右艺术的创造,将小说艺术逼入单一化的工具论,是艺术对生活和大众的屈服、创造性的抹杀和独立自主地位的丧失。因此,谋杀贝泽尔不仅是享乐的需要,更是自由主义力量的展示。
二、个人主义的突显:谋杀画像
道连·格雷谋杀了贝泽尔之后,画像出现了令他胆战心惊的变化,“肖像的一只手上出现了湿漉漉、亮闪闪的红色露珠。那是什么讨厌的东西?难道画布会冒汗沁血?多可怕啊!”(185)这表明了谋杀贝泽尔虽然扫清了自由享乐的障碍,但也制造了新的个人危机,画像成了谋杀画家的唯一目击者,是随时可以把道连·格雷送上绞刑架上的实在威胁,道连·格雷与贝泽尔的矛盾转变成了与画像的冲突,并且矛盾处于不断升级的趋势中,逐渐演变成了生存与死亡的尖锐对立,这使得道连·格雷对画像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首先,画像不仅显示了道连·格雷灵魂最深处的、最不为人知的罪恶秘密,还是其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的最高评判者;其次,画像是道连·格雷犯罪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把握其生死的玄关,同时,道连·格雷以后的何去何从都处在它无形的监控之下,这比贝泽尔和亨利的影响更具有广度、深度和力度,在立场上更加具有稳定性与恒久性;再次,道连·格雷的一切行为在画像面前都无法遁形,他对画像的情感态度也由单纯的厌恶转变成了敬畏与恐惧。因此,道连·格雷灵魂与肉体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就转移到了画像的身上,这对道连·格雷身败名裂始终是一个可以随时爆发的危险因素,反过来也就为画像的被毁设置了情节上的必然性。
之后,道连·格雷用威逼的手段让艾伦·坎贝尔(Alan Campbell)销毁了画家的尸体,同时,因为画家个人性格的孤僻古怪使得公众对他的无故消失不予关注,而道连·格雷也用对仆人撒谎的手段掩盖了自己作案的嫌疑。随着情节的发展,坎贝尔也因为不堪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了,这对道连·格雷来说,这桩谋杀案获得了预想的圆满结果。随后,西碧儿·韦恩的弟弟詹姆士·韦恩(James Vane)为了姐姐的惨死而向道连·格雷寻仇,但却被当作猎物意外地被枪杀了。这两个命案对道连·格雷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也加剧了他与画像的矛盾:首先,这两个命案连同贝泽尔被谋杀将道连·格雷过去的罪行彻底掩盖了,他的享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他的青春之美在现实的意义上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获得永恒,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意味着艺术行为的实践对象而不再有利害关系的任何牵连;其次,从画像这个角度来讲,它记录着这罪恶发生的一切,在逻辑上起着道连·格雷与生活发生关系的勾连作用,画像成了剖析道连·格雷灵魂的唯一线索、指控其犯罪的仅存证据,所有的矛盾冲突在此时都汇聚到了画像这里而具有了唯一性与集中性。因此,几个命案的相继发生,并不是表明了身体之美与灵魂之恶之间的媾和,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与自我的较量的开始。
道连·格雷又经历了一场与乡下女孩海蒂(Hetty)的新恋爱,这件事情不仅意味着道连·格雷与画像关系的又一转变,也暗含了王尔德艺术指向的变化。首先,道连·格雷与海蒂的爱情刚开始就被他匆匆结束了,从行为动机来说,道连·格雷是不想伤害海蒂而与其分手,而画像却真实的反映了这只不过是伪君子行径、是贵族公子的一种新形式的爱情游戏,这就从根本上把整件事情否定了,是对道连·格雷企图向善的一种嘲笑和否定;其次,从结果上来说,道连·格雷妄图通过这一次事件来达到恢复画像之美的目的,而画像由于洞穿了事情的本质真相后愈加丑陋不堪,这就意味着道连·格雷想通过欺骗自己和画像来实现灵魂与肉体的和谐、解决身体之美和画像之丑尖锐对立的失败,也是道连·格雷对画像表示妥协的破产;第三,由于道连·格雷的身体之美、不断地追求享乐而作恶和画像都具有超脱生命界限的永恒性,而在画像面前,道连·格雷所有的对其罪行的掩盖都是一种虚伪的徒劳,这样,不是人物控制画像的呈现而是画像制约人物的灵魂,二者在力量上的不对等使得画像凌驾于人物之上,道连·格雷在与画像的矛盾、灵魂与肉体的冲突、丑与美的对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谋杀画像是道连·格雷唯一的选择。
比较这两桩谋杀案,后者的艺术蕴涵更加复杂丰富:第一,从创作原则上讲,王尔德在“W·H·先生的画像”②中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切艺术都是一种行为方式,它试图在某种想像的平面上实现自我人格,这一平面超越了限制性的偶发事件和现实生活的束缚”(赵武平191)。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道连·格雷复现了王尔德的自我人格,同时,王尔德把道连·格雷从社会关系网中孤立、隔离出来,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践自己的处世方式和价值原则,是王尔德自身个人主义在艺术文本中的实现。同时,王尔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②中强调:“艺术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一种扰乱性和分裂性的力量。它的巨大价值就在这里。因为它要扰乱的是类型的单一,习俗的奴役,习惯的专制和由人到机器的降级”(赵武平304)。因此,谋杀画像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伦理对享乐作恶进行控诉与处罚,而是人性本身相互冲突而无法解决的必然结果,体现的是王尔德想跳出社会制约的个人主义思想,从艺术效果上讲,王尔德是想依靠个人主义扰乱性和破坏性的力量来打破人格类型的单一性、习俗化和人性异化,从而实现自身形象与艺术形象的双重多元化;第二,从人物塑造的转型来看,道连·格雷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发生了变化,他从贝泽尔和亨利的影响中逐渐摆脱出来,形成了个人的一整套人生观和社会观,并且凭借自身的魅力对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反影响,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随着贝泽尔、艾伦·坎贝尔、詹姆士·韦恩的相继死去,这不仅意味着个人主义对社会约束的不断突破,而谋杀画像也就体现了道连·格雷由单纯的自由享乐者演变成了多元化的个人主义实践者的转型;第三,从艺术表现力的深度来看,第一个谋杀案的发生,道连·格雷是处在贝泽尔和亨利两大对立力量的双重影响和牵制中,反映的是社会文化和人格独立的矛盾冲突,谋杀贝泽尔是对社会伦理的挑战和反叛,是人格独立的开始;而贝泽尔等几个命案发生后,社会对人物的制约逐步削弱,人物性格的发展取向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选择权力,这不仅意味着人格力量的日渐强大,也暗含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完全转移到了个人灵魂之内善恶、美丑的交锋,这是人性本真生存状态的深度展示,也是个人主义思想原则的确立和实现。
三、悖论与统一:谋杀案背后的美学内涵
道连·格雷人物形象的原型就是王尔德本人,“His[Dorian Gray's]clothing,his speech,his decorative choices,and his tendency to 'fling himself' into a chair whenever he enters a room all draw on codes of public behavior widely publicized by Wilde himself”(他[道连·格雷]的衣饰、言谈、富于修饰的物品,以及他进入房间后就‘扑倒’在一张座椅里的行为习惯都近似于王尔德本人所广泛宣扬的公共行为)(Latham 45)。因此,“小说在整体上具有‘解释思想’的象征意义,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也并不指向现实,而往往是对唯美主义思想的象征性解释。”③而王尔德本人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强调:“它[艺术]的美来自于它的作者实现了自我这一事实”(赵武平302)。然而,从《道连·格雷的画像》和王尔德相关的对艺术的论述结合来看,这两桩谋杀案隐喻的美学内涵既有悖论的一面,亦有其统一的一面。
悖论一:艺术对生活的超越与屈服。理查·艾尔曼认为:“他[王尔德]发现艺术具有两个基本活力,两者都是破坏性的。一个坚持它的离开经验的高贵孤立,坚持它的非现实性,无生育力”④。从谋杀贝尔这个故事情节的设置来看,王尔德始终在追求艺术对生活的超越性:第一,道连·格雷从画像中发现了自身的美和正在不断苏醒、膨胀的享乐欲望,然后用一个宗教式的祷告实现了身体的艺术性和画像的生理性,这从故事发生的逻辑起点来说不是来源于生活经验,而是高于生活现实;第二,从情节发展来看,道连·格雷与西碧儿·韦恩爱情破灭的原因在于西碧儿·韦恩离开了自身的艺术生活,爱情走向了生活而不再艺术化,道连·格雷抛弃了这种爱情正是对生活原则的背离;第三,道连·格雷不愿接受贝泽尔的建议救赎自己不断堕落的灵魂,原因在于贝泽尔的建议是一种生活似的宗教方法、是对现实道德伦理的妥协,因此,道连·格雷拒绝了贝泽尔而最终将其杀害是对生活约束的反叛与摆脱。然而,道连·格雷并没有完全超越生活,而是呈现出与生活贴近的趋势:第一,道连·格雷追求自由的享乐本身就是19世纪英国上层生活的真实反映;第二,道连·格雷享乐之后的灵魂痛苦、画像丑化的原因在于社会性的道德的堕落、伦理的丧失;第三,谋杀贝泽尔之后,道连·格雷害怕法律的制裁、画像的泄密也是一种生活理性的体现。因此,从文本的客观呈现来看,王尔德坚持艺术的非现实性是对生活超越与屈服的悖论复合体。
悖论二:艺术对伦理的远离与契合。王尔德在“英国的文艺复兴”中认为:“艺术表现任何道德因素,或是隐隐提到善恶标准,常常是某种程度的想像力不完美的特征,标志着艺术创造中和谐之错乱。一切好的艺术作品都追求纯粹的艺术效果”(赵武平24)。从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目的来看,道连·格雷追求自由的享乐、不顾及社会危害性,这是为了避免艺术表现善恶标准的类型化模式,但从谋杀画像这一案件的整个发生过程来看,其中却蕴涵了更深远的伦理内涵:第一,贝泽尔等命案的相继发生并没有使得道连·格雷走向完全彻底的自由,而是使得灵魂与肉体的分裂进一步加剧,这本身就是伦理意义上的善恶、美丑激烈冲突的表现;第二,道连·格雷放弃与海蒂的爱情是对自己罪恶行径的掩饰,是想用放弃享乐的方式来达到灵魂的救赎,从而恢复画像的原始之美,其不得已采取的虚伪做法也暗示了道德伦理的制约力量;第三,谋杀画像而导致了道连·格雷生命的终结这个细节值得深思,道连·格雷之死意味着王尔德并不赞同生命的存在方式就是单纯的、无止境的追求享乐,他在“佩特先生最近的一卷书”引用了佩特的一段话来阐明自己的道德观点:“要以艺术的精神来对待生活,你就得使生活的方式等同于生活的目的,你就得鼓励自己这样对待生活,这才是艺术和诗歌真正的道德意义”(赵武平285)。因此,道连·格雷之死与画像复原意味着生活方式与生活目的用艺术的精神得以整合,这是对世俗道德的远离与批判,更是对更高层次的纯真、纯善的理想道德的追求与契合。
悖论三:人生艺术化的艰难与可能。王尔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认为:“‘认识你自己’,这几个字写在古代世界的入口处,新世界的大门上将写上‘做你自己’”(赵武平296)。道连·格雷的自由享乐和个人主义处事方式就是对“做你自己的”原则的实践。同时,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中强调:“生活是艺术的最好学生、艺术的唯一学生”(赵武平344)。也就是说,人生首先是个人主义的,而它的实现的唯一途径是向艺术学习、摹仿。从两桩谋杀案来看,个人主义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死亡的发生、灵魂的苦痛、人性生存状态的焦虑,最后,道连·格雷也因为谋杀画像而导致了生命的终结,这表明了人生艺术化在文本中也是一种难以实现的艰难。王尔德后来在狱中所写的书信中认为:“基督的地位实际上是与诗人一致的,他对人性的全部理解都是出于想像,而且只有依靠想像才能实现” (转引自孙宜学221)。因此,人生艺术化只有在虚拟的想像状态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性,由于艺术与生活的特殊关系,这种可能性背后隐藏更多的是无法实现的否定性因素。
从以上这些悖论可以得知,王尔德是想通过超越现实生活的自由享乐、激进的个人主义来获得艺术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揭露现实生活的罪恶、批判虚假的社会道德、展示人性复杂的本真状态,从而建构最为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模式,这使他不得不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只能用美的乌托邦思想来统一他的艺术指向,“进步就是实现乌托邦”(赵武平302)。而这个乌托邦的实质是爱和赞美,王尔德写道:“大多数人都是为爱和赞美而生的,但我们也是应该用爱和赞美来生活的”(转引自孙宜学232)。从道连·格雷的人生发展轨迹来看,正是因为他缺少了爱和赞美才酿成了几个命案的悲剧,因此,王尔德强调由爱而美的乌托邦思想,是为了整合人性本身、人与社会、人与道德、人与艺术之美的矛盾冲突,从而建立他远远超越于时代的唯美主义大厦,这从对后世的影响来说,无论是艺术技巧、艺术理想,还是人文内涵、伦理关怀和社会体制建设等方面都有恒久的价值。
注释:
①Oscar Wilde,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1964)其译文参见荣如德译:《道连·格雷的画像》,《王尔德全集》第1卷,赵武平主编(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②王尔德的“W·H·先生的画像”、“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英国的文艺复兴”、“佩特先生最近的一卷书”等文章均见于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③蒋承勇先生认为《道连·格雷的画像》在整体上是对唯美主义思想的象征性解释,笔者对此深表赞同,然而对其认为道连·格雷是某种人性的象征则持有异议,见蒋承勇等:《英国小说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208。
④参见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