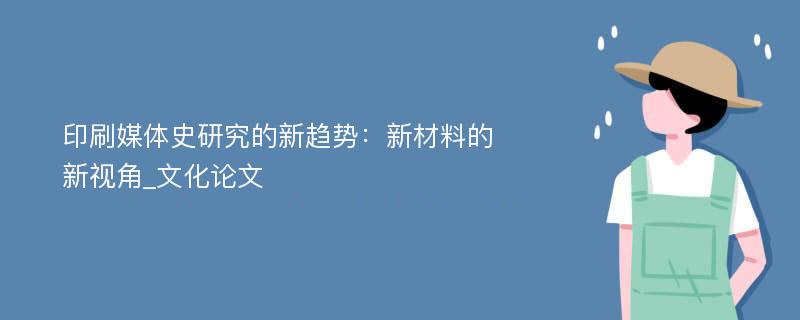
印刷媒介史研究新趋势:新材料 新视角 新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材料论文,媒介论文,新趋势论文,史研究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鉴于印刷媒介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独特作用,自其出现以来便一直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曾对出版自由、人类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书报刊等传播媒介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过精辟的阐述,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出版问题的一系列观点。[1]
进入20世纪,印刷媒介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不同,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遵循传统的印刷史研究方式,主要是以印刷术的演变历程为主线的专业史研究,同时也是考据版本及文献学者的研究领域。但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得益于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倡导的社会史理论,印刷媒介史研究者热衷于通过对原始档案材料的大规模统计,试图重建书籍的流通过程,了解不同群体对书籍的拥有情况,据此对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甚至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和民众精神状态进行探讨。因此,也有学者将其归类为“新心智史学”[2],以费夫贺、马尔坦、孚雷、夏蒂埃与罗歇为代表,这可看作是此项研究的第二阶段。法国学界的研究路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语国家的印刷媒介史研究。美国学术界不管所研究的印刷出版物形态如何,都将这方面的研究统称为“书史研究”(book history),爱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和达恩顿(Robert Darnton)是其代表人物。
印刷媒介史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必定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既有由来已久的印刷技术史、出版史、书目学、图书馆学的传统方法,也有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经济学、传播学、计量史学、文学批评等众多相关学科的积极介入,对印刷媒介的编辑、复制、传播、阅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照。正是由于这些学科的相互影响与不断融合,使得印刷媒介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长期占据引人注目的位置,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不断涌现。20世纪后半期欧美学界对于印刷媒介史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已有数篇文章予以介绍。最近十年来,印刷媒介史研究依然极为活跃,尤其是对印刷术出现后三个多世纪(即15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时间里的社会文化影响给予了较多关注。本文力图勾勒出西方学界关于近代欧洲印刷媒介史研究的最新概貌,以期为国内学术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原始资料的整理
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对于近代早期印刷品原始资料的汇编出版可谓不遗余力,这为学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提供了充分而便利的条件。尤其是早期英文图书在线(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简称EEBO)对近代早期英文印刷品进行了全面整理,旨在勾勒出1473年至1700年间英国及其殖民地所有纸本出版物,以及这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纸本英文出版物的大概,是目前仍留存的早期英语世界227年全部资料的汇总。该项目全部完成以后将收录125 000种著作,包含超过22 500 000页纸的信息。该数据库包括有许多文史资料,如皇家条例及布告、军事、宗教和其他公共文件;年鉴、练习曲、年历、大幅印刷品、经书、单行本、公告等。
除英文资料外,里瑟·舒瓦茨(Lyse Schwarzfuchs)和马文·J·赫勒(Marvin J.Heller)花费大量精力考察了16世纪希伯来文书籍。舒瓦茨的《十六世纪巴黎的希伯来文书籍》(Le livre Hebreu a Paris an Ⅹ Ⅵ siecle:Inventaire chronologique.Paris:Bibli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2004.),旨在列出16世纪在巴黎印刷的希伯来文或使用了希伯来文字母的其他语言书籍的完整书单。赫勒从2 700种版本中挑选出455种进行介绍和描述,这一收集整理工作以翔实的资料表明,许多被后世捧为“经典”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16世纪的印刷活动而显现出其重要性的。这两部作品无疑为从事犹太人研究的其他领域专家开启了16世纪希伯来语书籍和印刷的世界。
另外,杰罗德·弗里克斯(Jerold C.Frakes)主编的《早期意第绪语文本》(Early Yiddish Texts 1100-17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是一本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意第绪语的文本选集,其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一项空白。该书收入了从1100年到1750年间的132个文本,全部按照年代排列,从大约1100年的圣经和塔木德注释开始,以伊萨克·委兹拉的《情书》(1749)作为结束。此外,作者还收入了非文学类作品,如医学书籍、书信,再加上原有的大量宗教和文学文本,使得这一选集包含了大量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内容,这些资料对早期意第绪语相关研究者而言都是极为有用的资料。
同时,近些年来对欧洲各国近代出版企业历史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整理出了很多较为完整的出版目录,如《西班牙朱厄蒂(集团)印刷家族史及其出版书目》(William Pettas.A History & Bibliography of the Giunti(Junta) Printing Family in Spain 1526-1628.New Castle:Oak Knoll Press,2005.)、《十六至十九世纪希腊语印刷书》(T.E.Sklavenitis,K.Sp.Staikos.The Printed Greek Book 16th-19th Century.Athens:Oak Knoll Press,2004.)等成果也同样值得学者注意。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
在研究视角方面,近十年来的印刷媒介史研究突出表现为三大特点。
首先,传统的政治、宗教研究视角依然盛行。基奥德·雷蒙德(Joad Raymond)的著作《近代早期英国的小册子与撰写小册子》(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看到了政治与印刷媒介关系的一个不同侧面,即观念是如何通过16世纪和17世纪的小册子传播的。在他的书里,雷蒙德讨论了从1580年到1700年间小册子发展的复杂性,强调了小册子在社会拥有重要影响的三个特定时期:1588年、1642年和1688年。利用这三个日期作为其叙事的基础,雷蒙德重点描述了内战、复辟和光荣革命期间小册子的利用情况,以及随着小册子出版的衰落而兴起的报纸文化。一般观念认为,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见证了审查制度的崩溃和印刷出版的开放,而这又带来了小册子的空前泛滥。然而,这些基本的假定大部分都难以检验。贾森·皮西(Jason Peacey)的专著《政治家与小册子作者:英国内战和空位时期的宣传》(Politicians and Pamphleteers:Propaganda during the English Civil Wars and Interregnum.Aldershot:Ashgate,2004.),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了内战期间印刷与政治相互连接的世界。基里安·布里南(Gillian Brennan)的研究成果《爱国主义、权力与印刷:都铎时期英格兰的国家意识》(Patriotism,Power and Print: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udor England.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2003.)也关注了印刷与政治情感的联系,该书基于一种语义上的辨析,提炼了“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不同。
宗教是近代欧洲印刷媒介的重要内容,宗教变革离不开印刷媒介的推动,二者关系极为紧密。论文集《加尔文之前的法语福音派书籍》(Jean-Francois Gilmont and William Kemp.Ed.Le Livre Evangelique en francais avant Calvin.Turnhout:Brepols,2004.)覆盖了许多宗教出版问题,所有作者都以一种广阔的视角,在语境中突显了16世纪福音书的重要性。凯特·彼德斯(Kate Peters)的《印刷文化与早期教友派信徒》(Print Culture and the Early Quak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考察了教友派信徒如何利用小册子作为他们建立基督教王国使命的一部分,并且对印刷材料在一个成功的民族运动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估价。在这个后修正主义时代,有必要考察同时代人对印刷材料的接受情况。因此,彼德斯的研究对于17世纪宗教、文学和政治的更广阔领域而言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印刷媒介甫一出现,便受到来自各种权力机构的控制,双方的博弈互动一直是印刷媒介史研究的精彩之处。戴维·克莱西(David Cressy)的《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的书籍焚烧》(Book Burning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Volume ⅩⅩⅩⅥ,No.2,Summer 2005.),论述了16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之间作为近代早期国家传播控制系统的书籍焚烧与审查制度。克里夫·格里芬(Clive Griffin)以其对于16世纪西班牙印刷业的缜密研究而著称,在《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印刷工、异端与宗教裁判所》(Journey-Printer,Heresy,and the Inquisi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中,他对宗教法庭记录予以了全新的使用。格里芬认识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档案文献可以用来重构那些没有记录而又恰巧在那里工作的印刷工人的生活。第三个重要结果是,作者探讨了印刷者与异端之间危险的联合,彰显了印刷技术对政治的影响力。
其次,性别研究逐渐升温,多部成果触及了女性与印刷媒介的关系。《近代早期英格兰的阅读材料:印刷、性别与识字能力》(Heidi Brayman Hackel.Reading Materia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rint,Gender,and Lite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将人们对书籍文本和非文本的各种反应整合到阅读史中,考察那些更多的为愉悦而非行动阅读的人,特别聚焦于女性阅读这一现代学术研究非常薄弱的主题。珍尼·多纳沃兹(Jane Donawerth)的文章《17世纪英格兰妇女的阅读行为:玛格丽特·费尔的〈女性的优雅谈吐〉》(Women's Reading Practic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Margaret Fell's Women's Speaking Justified.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Volume ⅩⅩⅩⅤⅡ,No.4,Winter 2006.),通过对《女性的优雅谈吐》(1666年)一书的考察,发现在该书和其他小册子中,费尔引用了国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圣经版本,但却并不准确。这些错误是由口头传播造成的,书籍作者是靠记忆力记住了圣经的很多内容。这个发现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演讲、手抄本和印刷品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对立的。《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妇女、阅读和文化的政治》(Snook ed.Women,Reading,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arly Modern England.Aldershot:Ashgate,2005.)一书关注的同样是性别领域,该书重点探讨了妇女阅读所体现的政治含义,作者斯努克研究了那一时期女性作者如何在其文本中构筑了性别的、公共的身份。
第三,注重从个人与印刷媒介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约翰·加尔文与印刷书》(Jean-Francois Gilmont.John Calvin and the Printed Book.Trans.Karin Maag.Kirksville,MO: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的作者让-弗朗索瓦·吉尔蒙德强调了加尔文与书籍的相互影响,重在考察印刷文字,而非新教的教理神学。作者特别关注了加尔文如何利用印刷书籍,以及书籍的写作、出版及其分发中出现的复杂关系网络。因此,该书对于我们理解印刷文字的文化大有襄助。
《费迪南德·哥伦布的印刷品收藏:一名塞维利亚的文艺复兴收藏家》(Mark P.McDonald.The Print Collection of Ferdinand Columbus(1488-1539):A Renaissance Collector in Seville..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4.)一书,考察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私生子费迪南德·哥伦布的印刷品收藏。《亨利八世及其妻子们的书籍》(James P.Carley.The Books of King Henry Ⅷ and His Wives.London:British Library,2004.)则并不是关于国王及其妻子们每日阅读的一份简单书单,而更侧重于透过书籍以观察他们的思想兴趣,更广泛的说是一部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书籍史。阿密·格拉尼(Amy Golahny)的《伦勃朗的阅读:艺术家书架上的古代诗歌与历史》(Rembrandt's Reading:The Artist's Bookshelf of Ancient Poetry and History.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3.)试图将艺术史,特别是伦勃朗的生活和作品与书籍史融合起来。《阅读的革命:近代早期英格兰的阅读政治》(Kevin Sharpe.Reading Revolutions:The Politics of Read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以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威廉·德里克爵士的普通藏书为依据,力图找出其阅读方式中隐含的政治因素。
在研究方法上,延续已久的多学科特性依然显著。《英格兰近代早期对过去的图解:印刷书中的历史画像》(James A.Knapp.Illustrating the Past in Early England: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Printed Books.Aldershot:Ashgate,2003.)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尝试,融合了文学理论、艺术史、历史编纂学以及书籍史等众多内容。作者奈普论述了近代早期英语文本的图像与文字的关系,指出伊丽莎白统治的头25年是英国视觉文化的变迁时期,并将这些视觉图像既与文艺复兴诗歌理论做了联系,又与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雷蒙德·威廉斯及其他人的现代理论挂上纽带。
由这本书可以进一步证实,印刷媒介史的成长得益于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印刷媒介史的研究旨趣和学术品格,诸如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中不少著述都有许多涉及书籍、杂志等传播媒介的经典论断,被很多研究者作为理论方法广为应用。例如阿萨·勃里格斯与彼得·伯克合作完成的《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路的时代》中,作者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标杆,分析了从1450年到1790年期间发生的一些在历史上都已为人熟知的传播事件,如宗教改革、宗教战争、英国内战、1688年光荣革命以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旨在强调一个主题:即公共领域的兴起、或政治文化的兴起;亦即在欧洲一些特定社群所共享的政治资讯、政治态度与政治观。在讨论兴起过程时,作者对公共领域进行了进一步区分,将其分为暂时性与永久性的,或说结构性与因缘际会型(conjunctural)的公共领域。[3]伊丽莎白·雷恩·富德尔(Elizabeth Lane Furdell)的《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出版与医学》(Publishing and Medicine in Early England.Rochester,NY and Woodbridge,Suffolk: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2002.),也吸收了关于公共领域与不断增长的出版之间紧密关系的理论。
此外,社会语境问题也是最近西方学术界的热议主题。论文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阅读、社会和政治》(Kevin Sharpe and Steven N.Zwicker.Ed.Reading,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则强调,所处政治语境是解读一部书籍的重要因素。例如,约翰·弥尔顿的作品可以在复辟时期被视为激进的共和主义作品,也可以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被看做是诗歌杰作。在近代早期,一些人已经感到革命是人们阅读和误读印刷作品的结果。然而,适时印制的契约文本则可以避免潜在的暴力冲突,如1688年的光荣革命。总之,一个健全的民主体制需要依赖识字能力与阅读。
三、新观点
爱森斯坦在其代表性著作《近代早期欧洲的印刷革命》(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中,鲜明地提出印刷是一场“未被承认的革命”,指出人们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解释中,低估了印刷所扮演的“变迁的触媒”之角色。其延伸麦克卢汉等人的观点,强调印刷术发明所造成的两个长远影响,即印刷将知识标准化,并得以保存下来;同时,印刷激起人们对权威的批判,让人们更能获得相同事物相互矛盾的观点。
爱森斯坦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对印刷术的传统认识,但在提出之后的数十年中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和反驳,修正主义、后修正主义观点层出不穷,不断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一般说来,人们大都接受“媒体的变革带来了重大的社会与文化影响”这一观点,然而对其结果的本质和所及范围的认识却颇具争议。阿萨·勃里格斯与彼得·伯克重新梳理了所谓印刷革命的脉络,认为爱森斯坦所列出的变迁,从古腾堡的圣经到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发生的时期至少历经了三个世纪,而对新媒介的采用是逐渐发生的。如果革命的速度不快,那么是否仍可视之为革命是值得考虑的;再者是关于触媒动力(Agency)的问题,认为印刷是变迁的触媒的观点太过于强调传播媒介,而忽视了这些为了各自目的使用这项新技术的作者、印刷者和读者;第三,传统观点把印刷视为是相对独立的个体,然而,如果要评估印刷术发明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就必须把媒介视为是一个整体,所有不同的传播工具皆为相互依赖,视它们为一组事物、一个曲目、一个系统。[4]
另一部引人关注的成果是约翰·伯纳德(John Barnard)和D·F·麦克肯兹(D.F.McKenzie)合作主编的《剑桥不列颠图书史》(第四卷,1557-1695)(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Vol.4,1557-169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约翰·伯纳德的引言以广义上的修正主义观点为本卷奠定了基调,既反对目的论的观点,即反对“必胜主义者相信新教文化所主导的本国文化在不断进步”的论调,同时也不认同技术决定主义,不同意将印刷看做是能够创造出思想、宗教联系或文化模式的独特结构。戴维·麦克基特里克(David McKitterick)的《印刷、手稿和对秩序的探求(1450-1830)》(Print,Manuscript and the Search for Order 1450-18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是修正主义观点的又一力作。作者从事的是手动操作印刷机时代的书籍制作研究,通过对近代早期印刷书自身物质证据的关注,说明在这项新技术问世初期,人们对其是犹豫而有保留的接受的。前文提及的《政治家与小册子作者:英国内战和空位时期的宣传》反对那种关于内战带来事实上的出版自由的假设。作者认为只有极少数“政治演员”喜欢出版自由的观念,尽管在1642年出现了相对开放的局面,但议会马上转向控制;到1643年,“越来越多的印刷商被关进了伦敦的监狱”。皮西的论述及时矫正了对这一问题的传统看法。
另外,像凯特·彼德斯的《印刷文化与早期教友派信徒》、马超·陶厄斯(S.Mutchow Towers)的《英格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对宗教印刷的控制》(Control of religious Printing in Early Stuart England.Woodbridge:Boydell,2003.)以及《手稿和印刷品的使用,1300-1700》(Julia Crick and Alexandra Walsham.The Uses of Script and Print,1300-1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也都对传统观点予以有力的驳斥或矫正。总体而言,修正主义,甚至后修正主义观点在如今的西方史学界异常活跃,占据了较为显著的位置。
当然,面对修正派史学者的诸多批评意见,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也并非保持沉默,而是不断通过新的证据为自身观点进行辩护,如爱森斯坦的《近代早期欧洲的印刷革命》(第二版)(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Seco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便是典型一例,从而形成了现今媒介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西方印刷媒介史研究在原始材料的整理上迭出新品;在研究方法视角上,其多学科背景的特点依然显著,并更加注重女性和个人角度;对传统观点不断提出挑战,修正主义占据显要位置。但是,印刷媒介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确定的,但多学科研究路径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现象未有大的改变,学科整合仍是印刷媒介史研究者面临的最大难题。另外,虽然很多学者通过新近发现的资料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有力挑战,但有些结论难免矫枉过正,如对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影响力评价问题上。我们认为,除了研究印刷术出现后各种媒介的关系外,还需要增加对印刷术出现前的手抄本媒介,以及活字印刷术在其他文明地区的运用情况的综合对比;而女性视角的运用在某些方面也有将男女读者群体进行刻意区分之嫌。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全面客观地审视相关材料,以得出更为符合历史逻辑与实际情况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