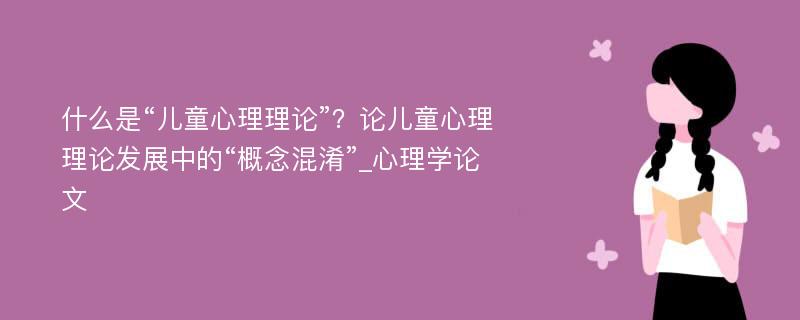
什么是“儿童心理理论”?——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研究中的“概念混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心理论文,理论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5-0128-06
在我们先前的两项研究中,我们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一般的梳理和介绍[1,2]。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研究已成为发展心理学中的一个热门领域(心理学家既发现了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大量观察与实验事实,又对这些发展的事实提供了某些解释),但在我们看来,这一研究从总体上看还是极不成熟的,可以说是进展不大(也许这个领域的专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实验研究范式和方法,研究目的及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怎么明确,心理学史上也没有可供参照的东西,等等。但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概念问题(或用认知科学的术语来说是“概念基础”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洞察的那样,心理学的混乱和贫瘠并不是能由称它为“年轻科学”所解释的,因为在心理学中存在着“概念混淆”。本文试图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进行剖析,特别是致力于澄清当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概念混淆问题,以便从发展心理学理论的层面上推动和深化我国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研究。
一、是“常识”发展,还是“理论”发展?
我们首先要分析的当然是“儿童心理理论”(Children's Theory of Mind)这个概念本身。就一般的意义上说,所谓儿童的“心理理论”,是指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具有一种按“信念”、“愿望”和“意图”等来解释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常识心理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儿童是“常识心理学家”。那么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儿童的这种心理理论并对此作出解释,就可以适当地称之为关于儿童“心理理论的理论”(Theories of Theory of Mind)。
但仔细深究下去,发展心理学家对“心理理论”一词的理解和使用是不同的,甚至是混乱的。这里的关键是怎么样理解常识心理学这个概念。近些年来,常识心理学问题不仅在哲学家那里,而且也在发展心理学家甚至灵长目学家那里都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正如奥斯汀顿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争论的哪一方,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自己的常识心理学理论,我们利用常识心理学的若干原则来思考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无论常识心理学或我们关于心理的常识理解正确与否,在这里其实都不那么重要。姑且不管哲学意义上的争论如何,我们都很清楚,儿童对于心理的常识理解也就是儿童发展中要获得的重要内容。”[3](p15)
这样一来,常识心理学似乎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甚至已成为其合理性用不着辩护的假定前提。以下我们就会看到,由此而引出的问题或混乱是怎样困惑着发展心理学家的。纵观这个领域的大量文献,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心理学家们(当然不是所有的)把“常识心理学”一词所指的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了:(1)按信念、愿望、意图、期待、偏爱、希望和害怕等来解释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常识心理学(Common-Sense Psychology);(2)对这样一种作为常识理论(Folk Theory)的一部分的日常说明(everyday explanations)进行解释——包括利用像信念、愿望等那样的概念的概括化网络——的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这后一种意义上的常识心理学是由哲学家塞拉斯1963年在《经验论与心理哲学》中提出,并由认知科学家莫登1980年在《心理的框架:对心理的常识概念的约束》一书中杜撰为“理论论”(the theory-theory)。很显然,这后一种意义的常识心理学是对第一种意义的哲学说明。
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姑且把这两种意义分别称为“常识心理学(1)”和“常识心理学(2)”。“常识心理学(1)”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说明的一套概念框架。我们可以说,如果常识心理学(1)的说明框架是正确的,那么“因为母亲想要婴儿睡觉”——这里利用了“愿望”的概念——也许就是对母亲关掉电视机这一行为的一种好的说明(尽管这还只是部分的说明)。这里,成人的一套常识心理学框架就出来了:比如说,现在我很饿,我想要(愿望)喝杯咖啡,吃一块蛋糕。我想(信念)冰箱里应该还有蛋糕的。我去打开冰箱,发现一块蛋糕也没有了。令我吃惊(情绪)的是,我的信念竟然错了(即所谓“误信念”)。我很遗撼(情绪)我的愿望没有被满足。所以我想要(愿望)到外面商店买些蛋糕吃。这大概就是常识心理学(1)所具有的涵义。
而“常识心理学(2)”则是关于常识心理学(1)的这套说明框架将怎么样能得到解释。就是说,这套说明框架是有意义的吗?它们能够对人的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吗?如果常识心理学(2)是正确的,那么“因为母亲想要婴儿睡觉”就是这样一个假设:母亲具有想要婴儿睡觉的内部的(脑的)状态,正是这一状态引起了母亲关掉电视这一行动。
虽然“常识心理学”这一表达成为“理论论”即常识心理学(2)的一个支配术语,但现在更普遍地被用于指常识心理学(1)。正是该术语的这种未曾引起注意的广泛的拓展,在文献中出现了混乱。常识心理学(在一种或其他的意义上,或有时在同样的意义上)有如下两种争论的焦点:
第一个是所谓使用问题:当人们按信念、愿望等解释行为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某些哲学家指出,常识心理学——在意义(1)——是一个模拟的事情:使用常识心理学就是训练一种技能;归因一种信念就是把自己投射到该相信者的情境中去。然而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像相信、愿望和意图——常识心理学(1)——那样的概念的使用者,正在利用一种理论——常识心理学(2)。归因一种信念,就是作出关于相信者的内部状态这样一种假设。目前在常识心理学的使用问题上的混乱在于:某些心理学家及哲学家简单地假定理论论是正确的,而另一些人(虽然不是所有的)却没有在常识心理学(1)和(2)之间作出区分。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地位问题:在什么范围内,常识信念—愿望框架是正确的?“地位”问题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在什么范围内,科学(在某种相关的意义上)将辩护常识心理学?当常识心理学被理解为常识心理学(2)时就出现了科学辩护的问题。在一方是像福多那样的意向实在论者。他指出,科学将辩护常识心理学的概念框架。另一方是像邱奇兰德和斯蒂奇那样的“排除式唯物主义”的倡导者,他们指出,作为一种经验理论,常识心理学将不可避免地被具有根本上不同概念来源的更好的理论所取代。正如其他的常识理论(如常识生物学)被科学理论所推翻一样,我们将准备着常识心理学被科学理论——科学心理学或神经科学——所推翻。排除式唯物主义者作出经验的预测:科学将非常可能不辩护常识心理学框架。
这里我们不可能介入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我们必须指出,把常识心理学的两种意义混淆起来,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混淆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当今关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理论论者所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所谓“理论论”,是指关于儿童发展着的心理理论的一种理论解释(或者说是对儿童关于心理生活的认识的一种解释性理论)。应该指出,当今所有理论论者,当他们使用儿童“心理理论”一词时,不是在常识心理学(1)的意义上,就是在常识心理学(2)的意义上理解他们所用的“理论”这一术语。更为严重的是(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两个不同的“论域”中使用理论一词的:一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心理理论中的“理论”,另一个是作为研究者的解释工具的“理论”。下面我们稍加分析:
当他们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使用“理论”或“心理理论”一词时,是指儿童能按他们对信念、愿望和意图等的常识性理解——即儿童的常识心理学,来对他人的行为作出解释。例如,奥斯汀顿在他的《儿童对心理的发现》(1993)一书中,一再声称本书是“讨论儿童对心理的发现(discovery of mind)或是儿童的常识心理学理解”。“正如当弗拉维尔当初使用‘角色扮演’一词并不代表他相信模拟论的观点一样,今天人们大量使用‘心理理论’一词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儿童的确发展出一种关于心理的理论。”[3](p143-144)这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心理理论”的发展,就是儿童对信念、愿望和意图等的常识性理解的发展。
可是,当他们在作为研究者的解释工具的意义上,也就是当他们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作出心理学理论上的解释时,却把这种发展解释为就像科学家的“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样。正像奥斯汀顿所做的那样,当他提到“儿童心理理论”一词时,就用英文小写"t"来区分;当他在解释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时,就用英文大写的"T"即“理论观”(Theory View),以示区别。而“从这样一个理论观出发,愿望、意图、信念和知觉等各种心理状态都可以被视为理论实体。这些心理状态是不可见的抽象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看得见的人类行为。这些理论概念与行为、事件等可见的现象,是在不同层面上的。理论即以其概念之间的一致性和相互依赖为特征。换言之,理论之间是相互联结的,它们相互作用,成为一个系统。”[3](p144-145)这样一来,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就不再是对诸如信念或愿望等的常识性理解的发展,而是地地道道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当理论论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戈普尼克(A.Gopnik)提出“科学家是大儿童”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
戈普尼克在《作为儿童的科学家》(1996)的论文中,当反驳“儿童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这一诘难时写道:“是的,实际上,我的确认为它真的是理论。从出生开始,婴儿已经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推论,这种推论的确超出了他们感觉的直接证据。尤其是,更小的婴儿似乎已经在他人的身体运动与他们自己的内部状态之间作出相当抽象的映射,至少以此为根据作出原始类型的推论和预测。这些推论在婴儿对面部姿态的早期模仿以及他们与他人更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是明显的。婴儿似乎具有天赋的心理知识,这种知识是似理论的,至少在它的确超出直接知觉经验这一意义上。它能产生真正的和富有创造的预测。它依进一步的证据而被修正。(当我们说这种知识是天赋的时,我们不是在哲学意义上指这一点。它是指:既不是该哲学家也不是任何闲荡的家伙能想到一种学习它的方式。我们是指,它在42小时大的婴儿中显示出来。”(4)(p510)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儿童的“理论”与科学家的科学理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则是留给理论论者的一道难题了。
二、是“心理表征”发展,还是“元表征”发展?
我们要分析的第二个“概念混淆”是: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到底是心理表征的发展,还是元表征的发展?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是不怎么清楚的。我们以奥斯汀顿的观点为代表。他指出,儿童对心理要有两个发现:心理是什么;心理是做什么的。心理表征是回答心理是做什么的问题,而“心理”同时也是一系列心理表征的总和——也就是回答了心理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表征这一概念,其一指的是心理活动的状态,如观念、愿望、信念、意图等等。其二指的是心理活动的过程。所以它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既是过程,又是结果。”[3](p22-23)简单说,在他看来,所谓表征,一是指像愿望和信念等心理实体,二是指形成愿望或其他心理状态的心理活动。而“一旦儿童发现了心理,儿童对心理表征就一定有双重意义的理解。心理表征在他们眼里,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结果;换言之,心理表征既可以作名词用,又可以作动词用。如果只有单方面的理解,都是片面的。”[3](p24)如果我们没有误解的话,在奥斯汀顿那里,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就是——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心理表征的发展了。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且以儿童的“假装”游戏为例。莱斯列(A.M.Leslie)认为,当2岁儿童一开始假装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理解他人的假装。这是儿童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第一个明显的标志。但帕勒(J.Perner)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否认2岁儿童会理解像皮亚杰所说的那种“象征性表征”(皮亚杰认为儿童的假装游戏是象征性表征的开端)。他认为,儿童的假装表明他们能设想另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并依照假想世界的方式来行动。但是,能够把一事物想象成另外一事物,比如一块布当成是枕头,这并不意味着儿童就获得了关于一事物象征另一事物的理解。在他看来,至少儿童要到4岁才能有这样的理解。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争论呢?我们认为,正是在这里,心理学家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到底是什么——是心理表征还是元表征——在发展,有不同的理解,并且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同理解往往混淆在一起。我们要着重指出,所谓儿童对他人的愿望、信念和意图等的理解,从我们作为观察者的心理学家的观点看,是元表征的发展,而不是心理表征本身的发展。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元表征”的概念,因为这是所有误解的来源。
我们知道,认知系统是以建构和处理对客体和事态的表征的能力为特征的。心理表征以及(像言语说话那样的)公共表征本身,都可以看作是世界中的“客体”,因而它们是二级表征或“元表征”的可能的对象。从目前的认知科学文献看,在这样的或其他的名称(如“高级表征”)之下,认知科学家对智力的进化论探讨,对常识心理学的哲学和发展的探讨,对交流的语用学探讨,以及在关于意识的理论和推理的研究中,都求助于元表征这一概念。现在看来,元表征不仅仅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而且也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
比较心理学研究表明,多数动物物种的成员不能识别它们自身,或把像信念或愿望那样的心理表征归因于同种。可以说它们完全缺乏元表征的能力。但像灵长目那样的高智力社会动物,被认为已进化了一种通过识别其心理状态来解释和预测他人的能力。丹尼特曾把某些灵长目描述为“二级意向系统”——能具有“关于信念和愿望的信念和愿望”。如二级意向系统能蓄意欺骗。在二级意向系统的群体中,三级意向系统通常处于真正的优势,只是因为它能看穿欺骗。同样,在三级意向系统群体中,四级意向系统更是具有真正的优势——有欺骗他人并且避免自己被欺骗的更大能力。因而被某些人种学证据所支持的假设是:灵长目发展了一种策略性的“马基维利亚式的智力”(Machivellian intelligence)——涉及到更高层次的元表征能力。目前,这些进化的和人种学的论证,与关于灵长目的元表征能力的实验研究——普利马克(D.Premack)等的《黑猩猩有心理理论吗?》(1978)这一先驱论文开始——部分是一致的,部分却是相冲突的。虽然关于其它灵长目元表征能力的水平,仍然有争议,但人类的这种能力是没有争议的。现已基本达成共识的是,人类后裔可能是唯一形成了元表征能力的真正不断上升的人类。
根据我们以上所说的“常识心理学(1)”,人类都是自发的心理学家。他们对像知觉和记忆那样的认知功能有某些理解。他们也彼此归因像信念和愿望那样的“命题态度”,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作出这样的归因。尽管哲学家曾描述过这种常识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并讨论了它的经验适当性,但心理学家却专注于这种认知能力的发展——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心理理论。应该强调,心理学家在这一领域所要研究的是,人类成功地对他人思想和自己的思想加以“元表征”的机制。关于这一元表征机制,有人认为把心理状态归因于他人是通过模拟来进行的(被称为“模拟论”);有人认为是通过从一般原理和证据那里推论而进行的(被称为“理论论”);也有人认为,是天赋“模块”起作用的结果。但不管这一争论的结果如何,我们应该更多地是注意到:在把心理状态归因于他人中所涉及到的不同程度的元表征能力,尤其是归因“误信念”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把误信念的归因看作是基本元表征能力的一个充分的——如果不是必要的话——证据。当然我们不是说,研究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仅仅专注于误信念归因就行了。我们同意梅尔左夫(A.Meltzoff)等的看法:“只专注于儿童何时理解‘误信念’是使人误导的。因为信念仅仅是儿童在他们与人的日常相互作用中理解和使用的许多心理状态之一。儿童可能只是在大约4岁才形成一种对误信念的稳定理解,但他们更早地开始在对人的常识心理学理解的发展道路上。学前儿童在他们对误信念仍然只有不稳定的理解的年龄时,便就已经大量地理解知觉、愿望和意图。”[5](p17)
如果我们把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理解为元表征能力的发展,那么许多无谓的争论便可以得到解释了。就莱斯列的观点来看,他把表征分为初级表征和次级表征,这是有道理的。“初级表征”是儿童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表达,或者是儿童对客观外物的信念(如弯弯的黄色香蕉);“次级表征”则是儿童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念的表征。这是对初级表征的表征即元表征。他认为,儿童天赋的“心理理论机制”(TOMM)可以使他们完成由初级表征到次级表征的转变。一旦初级表征(如“这些樱桃熟了”)转变为次级表征(如“南希认为这些樱桃熟了”),那么它就开始与现实脱离,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但莱斯列断言2岁儿童一开始假装时就能理解假装,却正是把表征与元表征混淆一起了。一个幼儿像他母亲那样拿起香蕉,把一端放在耳朵上,另一端放在嘴上。这是假装打电话。这种假装游戏就体现了元表征——即用一个东西(香蕉)表征另一个东西(电话)。但这是否就意味着2岁幼儿理解了表征——在我们观察者看来就是元表征能力的出现——呢?可以提出两点疑问:(1)早期的假装游戏不一定是元表征,也可能是一种“社会性模仿”。用香蕉打电话可能只是对某个人行为(如母亲的行为)的模仿。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元表征在4岁左右表现得比较明显。(2)假装的出现表明幼儿有丰富的想象能力,但把某物想象成另一物(如把一块布当作是“枕头”),并不意味着幼儿就理解或意识到了他这样做的意义。根据皮亚杰的研究,儿童能成功地做一个动作,与他达到对这个成功动作的意识或理解,中间要隔数年时间(大约是2-5岁)。因此,尽管莱斯列对表征与元表征区分是正确的,但他在从事心理学解释时,却没有意识到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了。
由此可见,将自己的心理状态加以元表征的能力,对儿童的意识能力即意识到他人心理的能力的发展,起关键作用。从理论上说,尤其是在罗森塔尔(D.M.Rosenthal)的意识论看来,一种心理状态是有意识的,如果它在高层次思维中被表征。当一种思想本身是有意识的时候,那么表征它的高层次思想就直接是元表征。这些高层次思想本身可以是更高层次思想的对象:意识的反省特征(即人们能意识到正在意识)于是按元表征的层次得到解释。尽管许多哲学家不接受这种意识的“高层次思想”理论,但至少在意识的性质及其像内省那样的相关现象中,元表征的作用几乎是不用争论的。
三、是“领域特殊”发展,还是“领域普遍”发展?
在研究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许多心理学家中,也许是为了迎合“后皮亚杰时代”(post-Piagetian era)的所谓“领域特殊性”(domain-specificity)的浪潮,也纷纷宣称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是领域特殊的。领域特殊性的基本涵义是:在知识结构、推理样式以及获得知识的机制在跨越不同内容领域方面都是不同的这一范围内,认知能力是领域特殊的。这是与以皮亚杰、维果茨基为代表的“领域普遍”观相对立的。领域普遍观认为,只存在一条单一的发展路线,它决定着儿童认知所有方面(所有内容领域,如逻辑、数、空间、客体等)的发展。而领域特殊观则认为,存在着一些完全不同的发展路线,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每一特殊领域有一个专门的机制支配着)。
就儿童心理理论发展领域来说,许多心理学家相信,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当然是领域特殊的。这首先表现在“模块论”的倡导者那里。例如,莱斯列断言,存在着一系列天赋特化的、预先决定的功能“模块”,它们会在儿童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出现。在一个大模块系统中,一些功能模块专司物理原因问题,另一些功能模块专司心理原因问题。他把这一大模块系统称为“心理理论机制”。这一作为模块的心理理论机制,在儿童大约4岁时——这是儿童时期的一个关键点,这种模块相对地突然打开。也就是说,一个预先设置好了的、用于理解他人心理的功能模块准时启动了。对于莱斯列来说,大约18-24个月早期假装的出现,暗示着在意义与所指物之间作出区分的能力,以便理解作为表征的信念。以这种方式来看,2足岁儿童已出现了元表征能力。根据他对自闭症儿童的大量观察研究,他认为,自闭症的原因就是这一模块受损害所致。
但仔细深究一下莱斯列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他所认为的儿童心理理论的领域特殊的发展,恰恰是——在我们看来——是领域普遍的发展。首先,从现有证据来看,莱斯列的天赋模块假设是建立在对许多自闭症儿童的观察与实验之上的。他拿出大量证据表明,绝大多数自闭症儿童没有心理理论的能力,或者这种能力只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自闭症儿童毕竟是少数,仅仅以此为根据——当然莱斯列认为还有其他根据——就提出一种普遍的天赋“心理理论机制”,断言它适用于所有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反而从其他人的实验中看到,儿童理解他人心理的证据,并没有为所谓存在独立功能模块的观点提供多少支持,相反,正如下面我们将要表明的那样,倒是存在着一种领域普遍化发展的证据。
其次,从莱斯列的论证来看,他的“心理理论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领域普遍的机制。他认为,作为模块起作用的“心理理论机制”,在儿童满1岁时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以后,儿童开始学会扮演游戏,然后逐渐理解为信念、愿望、意图等心理状态。而且,这一模块以一种精确的方式限制了儿童发展的轨迹。儿童的后天经验也许会启动模块的运行,但无论如何不能改变模块本身。如果撇开儿童个体经验的差异性,可以认为全世界的儿童的发展水平都是一样的。这一论证过程不正好是领域普遍式的论证方式吗?
我们再来看看“理论论”的代表人物戈普尼克和梅尔左夫的观点。他们把自己的“理论论”称作关于领域特殊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模式简单说就是科学哲学中的“假设检验”过程:儿童建立了一系列不同的、独立的关于他们心理世界的特殊方面的理论。最初,每个理论都是不完整的,甚至在一些方面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儿童面临着矛盾的证据时,就会不断地修改他们的理论。这样,儿童就像科学家一样,首先提出假设,然后用经验证据检验这个假设,并不断调整假设使之更加完善。正如戈普尼克明确表白的那样:“我的描述的寓意不是说:儿童是小科学家;而是说:科学家是大儿童。科学家和儿童都利用同样特别有力的和灵活的一套认知装置。这些装置能使科学家和儿童发展关于他们周围世界的真正新的知识。”[4](p486)
我们要问,在这样一个普遍的“理论”发展框架下,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是领域特殊的吗?正好相反,我们认为恰恰是领域普遍的。根据戈普尼克等的观点,我们对心理的日常理解与科学理论是类似的。这就是说,儿童对心理的早期理解可以有用地解释为一种理论,其理解的变化可以被当作理论变化。儿童在发展对心理的说明过程中,假定像知觉、信念和愿望那样的心理实体作为说明普通人的行动的手段。而且,在儿童对心理的理解中存在着有意义的、深远的概念变化,并且还有如下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模式:
(1)4岁儿童已有了成熟的“心理生活”。这就是说,4岁儿童对心理的性质有大量惊人的理解。他们对广阔范围的事件——包括完全不同于他们先前所经验过的事件的那些新事件——作出前后一致的并且大部分(虽然不是不变的)正确预测。而且,这些儿童通过提供因果解释来证明他们的预测。这种解释把动作的证据与像信念、愿望、心理实体和心理法那样的潜在认知装置联系起来。
(2)3岁和4岁儿童之间的差别是一种“隐含理论”(implicit theory)的差别。3岁儿童对他人行为和心理的预测、解释和说明完全不同于更大的(如4岁)儿童。当然,3岁甚至2岁半儿童对某些心理状态(尤其是知觉和愿望)作出惊人的广泛而准确的预测。例如,他们准确预测:在屏幕另一边的那个人将不能看到他们自己所看见的东西;具有不同愿望的人将从事不同的行动,被不同的事情弄得愉快或不快。甚至这些非常幼小的儿童也将按知觉和愿望对行动作出联贯的因果说明。
但当我们转向3岁幼儿对“信念”的理解时却看到相当不同的模式。3岁儿童前后一致地预测:在蒙骗场合中的儿童(假想的儿童)将根据真实而不是根据他们的“误信念”(false belief)作出行动。3岁儿童不准确地但前后一致地预测:假想的儿童将认为在糖盒中有铅笔,或者巧克力在蓝碗柜里,或者岩石是海绵。更惊人的是,3岁儿童的说明与这些预测又是前后一致的。例如他们对信念的来源作出不适当的因果说明,他们不能在通过“看”某物而能学得的东西,与通过对某物作出“推论”而能学得的东西之间作出分辨。但根据理论论的观点,这种对信念的来源的丰富因果说明,对于支持关于“误信念”的正确预测则是必要的。2岁儿童按愿望说明行动,随着3岁的进步,他们按真信念但不是按误信念来说明行动。
(3)从早期理论向后期理论过渡或转换的机制。特别是3岁至4岁儿童理论的转换(有称“3-4岁革命”),现已出现某些迹象或暗示。理论论者自信:他们在解释3岁和4岁之间出现的明显的理论转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相信导致这种转换的机制主要是理论建构和反驳),并提供了3种具体的转换机制:对人的动作的模仿和解释;自发的实验活动;证据的整合[6]。
总之,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就理论论者所提供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普遍模式来说,如果这一模式是合理的、有效的(正如他们自己所坚信的那样),那么它们就不是领域特殊的,而是领域普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