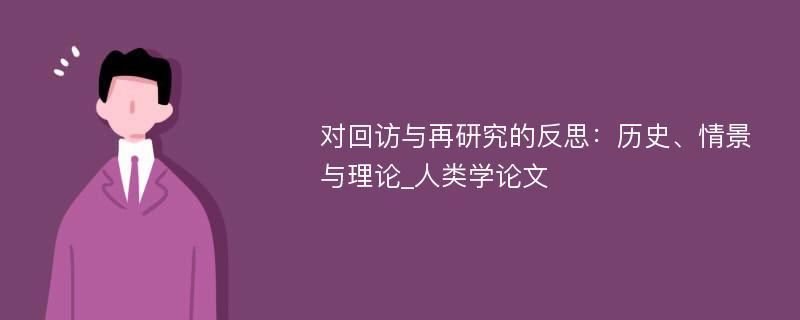
反思回访与再研究:历史、场景与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场景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学田野工作不能不涉及对旧田野工作地点的再次研究,关于这种研究有不同的提法,国内一般称为“跟踪调查”,而海外人类学则称之为“再研究”。[1]再研究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回访和再研究。回访(revisit)是指人类学家对自身做过调查的田野工作点的再次访问,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都曾经回访过先前做过田野调查的地点。再研究(restudies),通常是指到他人做过调查的田野点工作,以期与先行研究进行学术对话。对于中国著名的人类学/社会学田野工作点,如费孝通调查过的江村,林耀华做过调查的金翼黄村和义序,许烺光到过的大理西镇,杨懋春调查过的山东台头村,美国学者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调查过的广东凤凰村等,都已经有人去做再研究。
关于再研究取向对人类学研究的重大意义,有学者概括为:(1)延续田野工作点的学术生命;(2)先行研究留下的民族志文本成为接续研究者的起点;(3)持续研究者与学术名家之间的学术对话;(4)具有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视角。[2]
不同的时间到同一个田野点的研究如何做到前后接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后来到同一个田野点去的人类学家能够接续前人(自己本人或其他人)的研究吗?我们认为,回访与再研究,关键在于看到“异”(不同的研究者去同一个田野点),而不在于“同”(着眼于同一个地点的社会历史变化),舍此难以揭晓人类学的特色和真谛。因为人类学完全不是“研究谁”(study of)的学问,而是“与谁一起研究”(study with)的学问,[3]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参与和互动直接贯穿于调查研究和民族志撰写的过程中,从而影响民族志的表述。本文拟从历史、场景和理论三个方面来辨析回访与再研究,避免将其简单化的倾向。
一、历史:内部过程与外在力量
人类学研究者在不同时间回访同一个地方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田野点发生的变迁。正如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一本关于40年田野工作的回忆录中提到的,“每个人对于可以从生活中获取什么的认识和体会也在变。这种变化比赫拉克利特所设想的还要复杂、还要严重。如果从细微直接到宏大抽象,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对象周围的环境,从研究者到研究者周围的小世界,直至两者所处的更为宽广的世界,一切都在改变,那么,似乎没有任何一处能作为基点,用以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化是如何发生的”。[4]其中反映了回访所面临的挑战:人类学者是他们所研究的世界的一部分,但仅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者无法从自己不断参与同一个世界的活动中摆脱外在世界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布若威(Michael Burawoy)①将关注于田野点变迁的回访归类为现实主义类型的回访,其中又分为两个类型,对于内部过程和外在力量的关注,分别称之为经验主义和结构主义类型的回访。[5]
(一)经验主义的回访
完全的经验主义回访很难找到,但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en Lynd)对于中镇(Middletown)的研究至少可以算一个例子。从1890年开始,林德夫妇通过日记、报纸和口述历史再建构了中镇的35年。为了把握中镇的全貌,他们采用了人类学家里弗斯(Rivers)的计划将社区生活分为六个部分:谋生手段、建立家庭、教育子女、利用闲暇、参加宗教仪式和参与社区活动。他们辩论说这项工作塑造了所有其他领域。工业的扩张带来技能过时、工作枯燥、失业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降低。变迁最快的是经济,导致了其他领域的变化,如娱乐、教育和家庭,而宗教和政府的变迁相对比较慢。[6]
林德夫妇1925年所处的立场是将自己描述为仅仅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并不试图“证明任何理论”。而当他们回访中镇时发现,无法将自己限定在内部过程方面来解释变迁。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1935年率领五个学生的团队重返中镇,他们考察了第一本书中涉及的六个方面。正值大萧条时期,经济的主导作用比以前更强,但林德更关注生活的延续性而不是非延续性,尤其是中镇人重拾旧的价值、习俗和实践以应对外界的变化。林德的经验主义描述将变迁的解释与描述交织在一起。[7]我们可以发现林德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变化:在最初的中镇研究中,变迁通过劳动分工的增长来自内部。而在10年后的回访中,变迁产生自资本主义的动力,如不可避免的竞争逻辑,产量过剩和两极化。中镇正在经历其无法控制和思考的风暴。
理论体系的变化不仅仅来自中镇发生的变化,而是林德夫妇尤其是罗伯特·林德调整了理论框架。他一开始就声称“没有观点的研究”是不可能的。而他的观点与他研究对象的观点是有出入的。从他的《关于什么的知识》中,罗伯特·林德采取了对资本主义更仇视的立场。[8]在十年中,自从在初次中镇研究宣称的经验主义以来他经历了很长一段路程。他的回访受他自己的转变与中镇的转变的影响一样多。
(二)结构主义类型的回访
与林德夫妇回访中镇类似的是弗思(Raymond Firth)对于提科皮亚(Tikopia)的经典回访。这是一个孤立的波利尼西亚小岛,他1928—1929年间第一次研究它,1952年又返回到那里。正如林德回访中镇一样,弗思并不打算解构或再建构其最初的研究,而是作为评估他在两次研究间的24年中所经历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他将提科皮亚建构为一个孤立和自足的实体,社会变迁的动力基本来自外面。其实,弗思正好是在一场罕见的飓风摧毁岛屿之后到达那里的——如果说有外在力量的话这就是外在力量——导致了大面积的饥荒,如同大萧条对中镇的冲击一样,飓风成为弗思对社会秩序迅速恢复能力检验的标志。但是弗思更关注提科皮亚社会秩序如何在面对外部社会变迁(如劳动力向别的岛屿转移,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扩张,西方商品的流入,基督教传教区的扩张,殖民规则的侵入)的时候仍然保持完整。其世系制度削弱但并未消失,礼物交换与物物交换让金钱陷入困境。居住和亲属模式的规则在土地的压力面前还是得以保留。酋长的权力越来越不正式但作为殖民统治的基础同样得到加强。简而言之,一系列无法详细说明、无法探究的外在力量产生影响,但均被整合进一个同质的提科皮亚社会过程中。[9]
更多的近期结构主义重访质疑了弗思的假设。他们考察了外在力量的偶然性及这些力量导致的社会内部的深层分裂。他们更深入地思考了先前的民族志研究者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影响,甚至对重访的世界的影响。[10]而哈钦森(Sharon Hutchinson)将弗思描述的正在经历的现代化的同质社会代之以受传统、竞争与不确定性困扰的社会。
哈钦森的重访是对于苏丹南部努尔人——埃文思-普里查德(Edward E.Evans-Pritchard)1930年代做的经典研究中的那些孤立的、独立的专注于牛的武士[11]的最出色的研究。哈钦森将普里查德对于努尔人的描述作为参考基础,询问60年殖民主义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但她并没有将普里查德的经典研究重新放置在世界历史的场景中进行再建构,而是采用了聪明的方法论工具,比较了两个努尔社区的变迁——一个在西努尔地区,更接近普里查德描述的封闭的世界,另一个在东努尔地区,更强地整合到更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西部由苏丹人民解放军领导成为抵抗北部伊斯兰化的基地。然而即便如此,尽管卷入了战争、市场和国家,努尔人试图保持了他们以牛为基础的社会。牛的交换,尤其作为嫁妆,仍旧增强了努尔人的凝聚力。
当战争加速了努尔人整合进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时候,一个受过教育的努尔人阶层因为拒绝在成年礼上刻上疤印而成为冲突的中心。成年礼是努尔社会的核心,将男人与牛的财富,女人与人类生育联系在一起。同样,当社区变得更贫困,当西药在疾病面前更有效时,以牛为牺牲受到挑战。普遍传播的基督教反对以牛作牺牲。苏丹人民解放军提升基督教的地位以团结不同的南部力量对抗北方,同时在世界剧场作为一种世界宗教以对抗伊斯兰教。最后,石油的发现及琼莱运河的修建(可以从环境上摧毁南苏丹)加速了困境及战争的频繁度。实际上,南苏丹成为全球和地方力量的大漩涡。
哈钦森并未具体化和冻结“外部力量”,而是赋予他们以自身的历史性。不确定性不仅来自外部同时也来自努尔人内部。其中社会过程是开放的——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将未来引向多种可能性。金钱与牛之间有不稳定的妥协。努尔人的宗教与基督教、先知与福音传道者、枪和矛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不稳定结构。[12]因为所有这些不确定性,哈钦森的再研究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她并未解构或再建构普里查德的描述。
在这些个案中内在过程与外在力量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经验主义很容易导向结构主义。只有当我们局限于描述而不是解释变迁的时候,完全的经验主义才是可行的。更多时候重访对于变迁的关注同时考虑内部与外部的动力。同时由于人类学家的田野经历和理论视角的影响,无论是后人重新解释前人的研究,还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回访同一个地点都无法以同样的视角来接续先前的研究,因为他们对于历史变迁的理解和把握不同。
二、场景:部分真实与个人体验
再研究最惹人争议的地方是不同研究者到同一个地方做调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涉及观察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不同关系,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弗里曼(Derek Freeman)对于米德有关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田野工作所作的重访。在其经典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米德将萨摩亚(Samoa)人的青春期描述为轻松、平静的浪漫经历,以宽松和自由的性爱为标志,与美国社会发现的焦虑的、充满压力的、负有内疚和反叛的青春期经历完全不同。[13]弗里曼根据多样的资料——传教士和探险者的记录、文献和他自己在1940—1981年间所作的田野工作——断言米德制造了一个神话。弗里曼笔下的萨摩亚人是一个骄傲的、富有报复心的、惩罚性的和充满竞争意味的人群,他们自大,远非容易相处;经常好斗,远非性情温和;同时他们崇尚贞操,远不是性解放,其中通奸会导致暴怒,强奸很普遍。弗里曼断言,萨摩亚年轻人的违法行为与西方社会一样普遍。
为什么两个人得出的结论相差如此之大呢?弗里曼指出,米德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她将精力集中于其导师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为她指定的主题上,而不是首先去全面了解萨摩亚人;同时米德低估了部落社会的复杂性,萨摩亚的社会文化并不简单;米德不熟悉当地语言,又不住在当地人家中,而是与传教士住在一起。而当地人那时不愿与这些政府代表交往,因此她很难真正了解和与萨摩亚人沟通;米德的受访者多为年轻女子,使得她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更糟的是,不少她的受访者后来声称她们欺骗了米德。弗里曼据此得出结论,米德首先被当地人戏弄,然后以自己的田野经历来误导读者。[14]
这场针对文化人类学经典作品的攻击在学科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纷纷捍卫米德,批评者质疑弗里曼(一个中年白人男子)和妻子如何在调查年轻女性的性生活方面比23岁的米德更成功?他们抱怨弗里曼很少提及他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除了对萨摩亚语言的理解甚于米德。他们怀疑弗里曼宣称自己被作为仪式性的首领是否意味着萨摩亚人更信任他?批评者认为弗里曼的再研究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反驳狂热中,堵塞了理论的再建构以及将历史变迁作为一种策略来协调先行者与后续者之间的研究。
这场学科史上著名的争论对于人类学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促使研究者反思田野调查中的场景性。从人类学者的角度来看,正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述,人类学家自身就是工具。[15-16]研究者的理论背景、个人身份、研究目的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过程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深刻的影响。人类学家的工作只能是尽力靠近一种部分的真实,而不是全部的真实。无论米德还是弗里曼的工作都只是反映了他们田野经历的部分真实。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人类知识存在明确知识与默会知识的划分。明确知识不带个人的成分,以严格的规则作支撑,任何人面对它都没有自由解释的余地,只有遵循已有的研究程序和现存的规则。而默会知识很难用语言表达,带有很强的个人化特点,关联着个人的现实感、实践智慧、想象性理解、洞见、直觉等,它的规则是模糊的,从而给个体的判断力留有很大的空间。如果说明确知识关涉知识的科学性,那么默会知识则体现艺术性的魅力。[17]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田野工作同时兼具明确知识与默会知识的特点,它是由人类学者主动激发的,由被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它必须不同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以往的生活方式。田野工作是与思辨活动不同的一种实践活动,它不是想,而是做,它不是想象,而是生存。[18]所有民族志学者都深陷于求知和求名的网罟之中,并且被研究对象的各种帮助、招待、抵制及有时是故意的欺骗所困扰,同时又被田野经历以外的制度化因素,包括殖民官员、资助机构和评审委员会的种种要求所遮蔽。民族志关系网中的这种流动和过程化的生活,通常意味着研究对象和民族志学者的态度、兴趣和欲求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变动不居。[19]因此田野资料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包含了场景性。
因此,从再研究涉及的场景因素来看,后人去重做前人的田野点,并没有办法证实或者证伪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这种情况,其他人即使在同样的地方或在同样的一群人里做调查,希望至少可以检验一些大致的结论,但是很难否定前人没有明确说出来的事情……无论思考库拉交换性质的状况当时是否存在,这种状况转瞬即逝,《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为所有实用目的而保留的画面无法抹去,无论谁想减轻其影响都必须努力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画面中。”[20]
除此之外,倘若认定民族志是十分注重调查者个人体验的话,那么,同一个人的数度回访与另换一个人对前人田野点的接续调查,至少调查当事者心理感受上是迥然不同的,相同的仅仅是那个“田野点”而已,至少,后辈从来没有进入那个“历史现场”,难以产生前辈触景生情导致的种种联想。用一个差强人意的比喻说就是,跑4×100米接力的选手是难以体验跑400米冲刺时候的身体感觉的。地点虽一样,时过境迁,考虑到场景因素,田野经历给学者带来的感受和直觉是不一样的,加之个人生活和研究经历的变化也会影响人类学家的判断。同一个人可以回到同一个地方做调查,但是不可能回到从前的心境和感情,而这种感受也是别人无法体会到的,所以后来的调查研究是否能与前面的接续恐怕得慎重考虑。
三、理论:理论视角与意义世界
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个田野点进行再研究之所以得出不同结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各自所持的理论视角不同。与弗里曼过分专注于推翻前人的理论而不是再建构不同,韦纳(Annette Weiner)和刘易斯(Oscar Lewis)倾向于用重访来再建构先行者的理论。
韦纳对马林诺夫斯基有关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田野调查的重访发现:男性和女性对于两种物品的交换代表了不同的权力圈子:在男性是对于代际财产转移的控制,在女性则是对祖先认同的控制。因此,死亡仪式相应地分成两种类型:一种通过财产的分配再确立代际的联结,另一种通过分配成捆的香蕉叶恢复一个人的dala认同,或祖先认同。妇女主宰着一个她们自己的权力领域,即宇宙时间的不朽,同时她们与男性在历史时间中分享对于物质世界的控制。[21]
从民族志的角度看,韦纳和马林诺夫斯基二人的调查资料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时空变化后的理论、视角与性别关注不同。马林诺夫斯基虽说注意到妇女在岛上的社会地位较高,但他认为这是由于母系继嗣社会的谱系作用,忽视了当地妇女在政治经济学与交换体系中的作用。[22]而韦纳通过对妇女在当地生产活动与经济交换中的重要作用的分析展示了她们显示出重要的权力,透过物质的实践和精致的仪式而制度化。因此她的再研究通过提供对于男人与妇女之间权力关系的更完整、深入的理解再建构了经典研究。
而刘易斯对于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有关特波茨兰(Tepoztlán)的经典研究再建构了先行者用的历史理论。雷德菲尔德1926年研究了特波茨兰[23],刘易斯在17年后的1943年研究了这个村庄,明显发现了变迁。但他更感兴趣于对雷氏所描绘的整合的、同质的、孤立的和功能平静的村庄所掩饰的“暴力、困扰、残酷、疾病、痛苦和不适”[24]作分析。刘易斯强调了村民的个人主义,他们缺乏合作,有地农民与无地农民之间及这一地区村子之间互相争斗。与雷氏将特波茨兰视为孤立的村庄不同,刘易斯将这一村庄置于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网络中来透视。像韦纳一样,刘易斯并未将雷氏的研究作为评估社会变迁的基础。因为对他而言,雷氏的民族志建立在错误指导的历史理论的基础上,这一理论忽视了历史的“场景依赖”性,而这正是刘易斯试图在自己的研究中加以修正的。
耐人寻味的是,在《小社区》中,雷氏对刘易斯的再研究进行了再分析。他赞同刘易斯:历史变迁并未能解释他们对于特波茨兰描述的分析。但他否认与他所用的乡村—城市连续体理论相关,因为在他写《特波茨兰》时还未发展出此一理论。他将他们的分歧归结为每个人所持的问题不同:“我的书背后的问题是:哪些因素使这些人快乐?而刘易斯的问题是:哪些因素让这些人受苦?”[25]雷氏继续说,情况应该是这样——我们需要对同一地点采用多样化和相互补充的视角,每一视角有其真理。但这忽视了刘易斯的要点问题——问题来自于理论,其中一些比另外一些优越。即使乡村—城镇连续体理论不是完全在《特波茨兰》中形成,它的胚胎在早期研究中也已存在,并作为一种不充分的共时理论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发挥影响。
理论的再建构反映出民族志研究方法面临的一个困境:研究者的理论与被研究群体的意义世界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张力。当研究者过度钟情于既有的理论时,他(她)往往会不自觉地运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田野资料,妨碍了从田野资料中生成理论。由此,研究者的理论无法充分反映被研究群体的意义世界。如果换一种进路,诚然研究者必须深入被研究群体的日常生活、理解他们的意义世界,但是,研究者不能把被研究群体的日常观点看成是对社会结构的直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个别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结构的认知是片段而零碎的,所以研究者关于整体社会结构的科学说明不需要与被研究群体的日常观点保持一致。如果承认好的民族志必须建立在相关的社会科学哲学论述的基础上[26],民族志的再研究有可能前后研究者采取的是不同的进路,研究的哲学基础就相异,后来者站在自己的理论基础上批评前人也就值得质疑了。
四、结语
人类学对于经典民族志研究的回访和再研究是与对于人类学加以反思的意识相伴随的。民族志原本生产关于对象的知识,反思性使关于对象的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权威性受到了限制,却意外地增加了获得关于研究者的背景(他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知识的机会。[27]当今的人类学家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质问某人与他研究的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障碍而是理解和解释的必要条件。作为民族志者我们只是我们研究世界的一部分,而这是通过研究者调用的理论来表现和评价的。
回访和再研究为我们理解民族志的反思性提供了借鉴,启发我们关注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场景与理论,对于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
与国外学者关注不同的思想方法对于同一田野工作地点产生的影响不同,国内的学者倾向于用“追踪调查”来比较过去与现在发生在同一个田野工作地点的事情,以期描写或者阐释社会变迁和发展。但经常只讲现象的“巨变”而忽视了学理性的探讨,妨碍了对前人研究的深化。如在对于许烺光研究过的西镇的追踪调查中,研究者局限于罗列家祭和祠祭仪式今昔对照表,[28]却未对许先生曾提出的“传统模式与新的要求之间怎样共存或是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29]之类的问题做深入的探讨。列维-斯特劳斯说过“积累证据以证明一切社会都处于历史和变化之中是令人厌烦和无益处的,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30]
笔者愚见,“回访”和“再研究”需要区别对待,切忌混为一谈。对于不同学者的民族志撰写而言,本质上并不存在所谓“回访”,而只有“再研究”。这是由民族志这样一种特殊文本的自身属性所决定的。格尔兹就有言道:“所有的民族志只有一部分属于哲学,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研究者的自白。”[16]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提出,民族志是一种理论实践,然而这一实践却是以实践理论为依据的,这一点如同所有的实践一样。普遍而言,理论实践贯穿着实践理论的原则,反映着实践理论的特点。以理论实践为最终诉求的民族志的实践理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实践,因为人类学家的田野实践并不仅仅是同受访者一起工作,而是同受访者协作,共同阐释某一现象。[31]因此,民族志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共识,与其关注它,不如关注民族志作者在生产作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通过文本,我们需要指向的是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关系。[32]前人留下的民族志对后来去做田野的人类学家来说是文本,而如何理解这一文本除了人类学家再进入田野点调查的经历(场景)外,还有人类学者本身的素质(采用的不同理论和对历史的不同把握)。这些都构成民族志理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民族志总是陷入发明文化而非再现文化的境地。[33]
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而言,再研究是否具备理论生产的优势值得深思。从经验研究与理论的关系来看,理论与生产理论的田野有关,在非洲做田野的人类学家发现世系群,在大洋洲发现库拉,在北美发现图腾,在历史文献极大丰富的中国,人们发现“追踪研究”。广泛地说,中国的调查都是有前人做过的。
实际上,从学科史、理论史、变迁研究的角度看,“再研究”并不具备天生的优势。学科史上,百年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民族国家的深刻焦虑中发展起来的,学科史上的断裂甚至学科本身的“挥之即去”,使得学科延续很难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来继承。理论史上,百年人类学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理论的烙印,反思半世纪甚至更早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也未必要通过经验性的再研究才能完成。变迁方面,与世界多数民族不同,中国的几乎任何一处都存在大量的文字记述资料,所以变迁问题不一定非要在出过人类学民族志的地方才能研究。
如果我们将再研究纳入汉语人类学视野,会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实际上很难不是再研究。如果将人类学视为一种以己身关照他者的努力,那么我们会发现,历史上这样的努力很多,并留下不少记述。[34]
因此,人类学作为一门理解“他者”的艺术,其跨越文化的经验实践古已有之,并非今天自认为人类学家的专家特权。使再研究成立的原因,应该在于具体时空场景中的对话与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出新的见解。既与学术先行者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也与同一时空坐落中的当地人进行协商与交流。研究者需要在理解前人(包括前人做调查时所处的历史、场景与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田野工作,明确对话的范围,彰显隐藏的问题。同时对自己所处的历史、场景与理论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回访与再研究的辨析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的人文特色,重视田野调查中的体验和感觉。实际上,在人们的意识活动和社会实践中,知觉与思维、具象与抽象、无意识与意识、身与心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过多地强调科学和理性,就会失掉对于常识的领悟力,难以揭晓人类文化的真谛。
注释:
①布若威的论文将“回访(revisit)”界定为民族志者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一定时空中的对象,将自己的地点与前人(自己本人或其他人)早期在同一地点所作的研究作比较,并未严格区分回访与再研究。布若威从社会学者的眼光来分析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志回访,认为前者倾向于现实主义,而后者倾向于建构主义。并根据观察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内部过程与外在力量四个方面将回访划分为四种类型。本文有关历史、场景与理论的观点及部分案例借鉴了布若威的论文,在对相关资料做翻译的过程中,将回访与再研究区分开来,用“再研究”或“重访”来指研究者对他人的前期同一地点的研究,而用“回访”来指研究者对自己本人早期的同一地点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