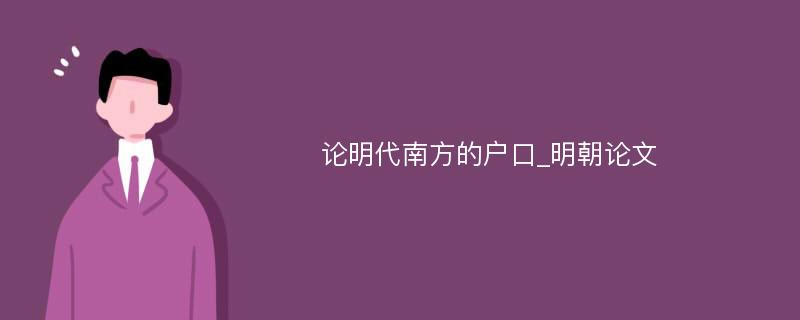
论明代华南的载籍户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论文,明代论文,户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K248
载籍户口是研究明代华南地区人口资源的重要资料。尽管载籍户口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如果撇开这些资料,要想弄清明代华南的人口状况是不可能的。本文拟在全面整理明代华南载籍户口数据的基础上,对明代华南载籍户口的来源、特点及其价值作一分析。
一、载籍户口的来源
载籍户口即文献中记载的户口数据。文献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基本上都来自户籍。所以,在具体探讨明代华南的载籍户口之前,有必要先看一看明王朝的户籍制度。
明朝的户籍制度是由朱元璋一手建立起来的。朱元璋对户口问题十分重视。明朝一建立,即令各地官吏收集元代户籍。洪武二年(1369)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明会典》卷19《户口》洪武三年十一月,诏核民数,给以“户帖。”(《太祖洪武实录》卷58)户帖由各家各户自行填写,内容包括家庭的详细住址、人口的姓名性别年龄大小以及财产状况。为了保证户帖的真实性,朱元璋采取了大军点户的做法,派遣军队逐家逐户“比勘”户帖。规定官吏隐瞒户口,便将该官处斩;百姓弄虚作假,便将百姓充军。(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1)通过这些措施,弄清了各地的人口状况。在此基础上,又于洪武十四年下诏编制“赋役黄册”,规定“以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明史》卷77《地理志》。《太祖洪武实录》卷135略同)从此, “黄册”便成了全国各地管理户口、征发徭役的依据。明代各地的载籍户口都是按照黄册等户籍资料统计的。
按照明朝的户籍制度,各布政司,各府、州、县除每年要审报户口升降情况外,每隔10年还要重造一次黄册。从洪武十五年(1382)算起,到崇祯十七年(1644)共262年,有26个年份需要重造户籍。因此,各地至少应当有26种人口统计数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口统计数据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载籍户口数据是十分有限的。就拿明代华南地区的情况来说,福建、广东、广西三布政司所辖政区达29府,55州,184县,(注:这是万历六年的情况。“州”数中含11 直隶州在内。)留下来完整的户口数据才1200多种。各府的人口数据多寡不一。有的府多至十三四种,有的府只有一二种。各县的情况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些县人口数据至10余种,有些也只有一二种。由于各政区留下的人口数据多寡不一,加之这些数据的年代有一定的差异,因而这些数据不完整,缺乏应有的系统性。比如福建汀州府有洪武二十四年、弘治五年、嘉靖元年的人口数据,漳州府没有这三个年份的数据,而有永乐十年、弘治十五年的数据。这种情况,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过有这些数据总比没有要好。尽管明代华南地区留下的人口数据不完整,不系统,但对研究明代华南人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笔者初步统计,福建布政使司及其所辖各府、州、县现存明代户口数据270多种。其中布政司6种;福州府3种,属县10种; 兴化府属县13种;泉州府3种,属县21种;漳州府4种,属县30种;建宁府3种, 属县23种;邵武府10种,属县40种;延平府9种,属县53种;汀州府3种,属县24种。广东布政使司及其所辖诸府、州、县现存明代户口数据320多种。其中布政司6种;广州府10种,属县50余种;惠州府9种,属县17种;潮州府9种,属县18种;高州府6种,属县6种;雷州府9种, 属县6种;廉州府12种,属县7种;南雄府14种,属县6种;韶州府7种,属县40多种;肇庆府8种,属县20种;琼州府6种,属县60多种。 广西布政使司及其所辖诸府、州、县现存明代户口数据110多种。 其中布政司9种;桂林府6种,属县9种;南宁府8种,属县4种;柳州府7种, 属县12种;平乐府6种;属县6 种;庆远府13种,属县5种;太平府6种;梧州府7种,属县10种; 浔州府6种。属县3种。若据弘治《八闽通志》、康熙《福建通志》、道光《福建通志》、嘉靖《广东通志》、万历《广东通志》、康熙《广东通志》、雍正《广东通志》、嘉靖《广西通志》、万历《广西通志》及明代华南府志、县志对明代华南载籍户口加以整理,以布政司、府、州、县为纲,按照年代顺序将明代华南各地的载籍户数、口数以及户均人数加以排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明代华南户口数据的保存情况和明代华南人口演变的轨迹。
二、载籍户口的特点
明代华南户口变动很大,除某些地方在某个时期有所增长以外,普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以布政司为例:福建在洪武十四年(1381)有户811369,口3840250,(《太祖实录》卷140)这是明初的情况。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户815827,有口3916806,比明初有所增长。 但为时不久,户口即开始下降。弘治四年(1491)有户506039,比明初减少了30多万,下降幅度将近38%;有口2106060,比明初减少了170多万,下降幅度达45%以上。万历六年(1578)有户515307,有口1738793,户数虽然比弘治时略有回升,但口数仍在下降,还不到明初的一半。(《明会典》卷19)广东在洪武十四年有户705632,口3171950。到洪武二十六年即减少5%左右。弘治四年有户467390,比明初减少23万多,下降幅度达43%;有口1817384,比明初减少135万以上,下降幅度达46%以上。万历六年有户530712,口2040655,虽较弘治时有所增长,但户仅及明初的75.21%,口仅及明初的64.33%。广西的情况比较复杂。洪武十四年有户210267,口1463119。洪武二十六年户数增长0.47%, 口数增长1.34%。弘治四年,户数猛增到459640,为明初的218.6%; 口数增至1676274,为明初的114.57%。弘治十五年,户口数又急剧下跌,户凡182422,比十年前减少了27万以上,仅为明初的86.76%;口1005042,比十年前减少67万以上,仅为明初的68.69%。(《图书编》卷90)到万历六年,户数又有所增长,达到218712,超过了明初的户数;口数也有所增长,不过只达到1186179,相当于明初的81.07%。
户口下降是明代普遍存在的现象。(注:张锡纶:《明代户口逃亡与田土荒废举例》,《食货》半月刊3卷2期(1935);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嘉靖八年(1529)六月,霍韬在修《大明会典》前夕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洪武初年,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时甫脱战争,户口凋残,其寡宜也。弘治四年,则承平久矣,户口繁矣。乃户仅九百一十一万,视初年减一百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三十八万,视初年减七百一十六万矣。”(《世宗嘉靖实录》卷102 )但是,各地户口下降的幅度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我们把明代华南各布政司的户口数与当时其它布政司的户口数加以比较,就可发现明代华南户口下降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在明代十三布政使司中,福建、广东、广西三布政司户口下降最为显著。洪武二十六年,十三布政使司平均有户700430,口3988606。 弘治四年,平均有户554392,口3220546。万历六年平均有户625146, 口3532715。若将同年华南各布政司的户口数与这些数字加以比较, 即可看出华南各布政司的户口数低于十三布政使司的平均水平。具体来说,福建洪武二十六年的户数在十三布政使司中仅次于浙江、江西而居于第3位;弘治四年少于山东、山西而居于第5位;万历六年又少于湖广、广东而居于第8位。洪武二十六年口数在十三布政使司中居于第6位;弘治年间降至第9位,万历六年又降至第10位。 广东户数洪武二十六年在十三布政司中居第6位;弘治四年跌至第7位;万历六年户数仍居第7位。口数洪武二十六年居第7位,弘治四年猛跌到第10位,万历六年才升至第9位。广西户数洪武二十六年在十三布政司中居第11位; 弘治四年上升至第8位;万历六年又下降到第11位。 口数所处的位置一直在下降:洪武二十六年居第10位;弘治四年降为第11位;万历六年再降至第12位。
三、载籍户口下降的原因
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的规律,明代华南户口数字应当不断增加。然而,载籍户口所显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这种现象从情理上是讲不通的。因此,早在明代,就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质疑。如万历《福州府志》的作者说:“余常考历代草创,井邑萧条。盖百姓新去汤火故耳。及承平日久,未有不滋殖者也。旧志载正德时户口,视洪武中不能增十之二三,顷视正德又无所增矣。夫国家治平,晏然无事二百年于斯,兹前古所未有也。则休养生息,固宜数倍于国初时,乃民不加多,岂有是理哉!”(万历《福州府志》卷26《食货·户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福建一·福州府户口》同)嘉靖《建宁府志》的作者说:“户口之登耗,系国脉之盛衰,故必培养字育,使之滋息可也。承平既久,生齿宜繁,然稽之版籍,则递减于前,而聚庐顾亦如旧”。(嘉靖《建宁府志》卷12《户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代华南载籍户口的下降?是自然因素还是社会因素?抑或是二者兼有?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我认为明代华南载籍户口的下降与天灾人祸有很大的关系。明代中期以后,华南地区自然灾害相当严重。随着气候由暖到寒的转变,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和生物灾害频繁发生,层出不穷。较大的水灾、旱灾、地震、瘟疫、饥荒都曾导致人员伤亡。如英宗正统七八年间,福州府古田县发生瘟疫,疫死1440余口。(《英宗实录》卷106)宪宗成化十一年至十二年间发生大规模的瘟疫,“疫气蔓延,死者相继”。(《宪宗实录》卷149;《明史》卷28《五行》一)二十一年,广西平乐大水,“漂流民居万余”。广东广州一带风雷大作,飞雹交下,“坏民居万余,死者千计”。武宗正德十六年,福州大疫,府县官员死者四十余员,军民死者极多,无法计算。(《世宗实录》卷3)嘉靖十七年,广东惠州大水, 沿海居民“死者以千计,户口或因之告绝”。神宗万历三十一年,泉州海潮泛滥,淹死万余人。(《神宗实录》卷387)三十七年, 福建建宁等四府大水,淹死人民十余万。(《神宗实录》卷458;道光《福建通志》卷271)四十六年,潮州飓风大作,海水横溢,淹溺12500人,坏民居30000间。(《明史》卷28;《广东通志》卷188)大体与此同时,华南地区的内忧外患也经常发生。明王朝与起义农民和广西、广东等地少数民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在华南地区进行的,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户口损伤。倭寇的破坏也曾损耗过户口。比如兴化府户口的衰减就与倭寇的侵扰破坏有很大关系。16世纪70年代,西斑牙传教士马丁·德·拉达曾出使福建。他在《出使福建记》中写道:几年前,日本人在兴化一带大搞破坏,不仅平毁了郊区的房屋,而且破坏了城中的许多建筑,他到兴化时,“有三万多户的地方仍无人烟”。(注:〔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9页。)类似的事件在明代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如《晋江县志》载:“嘉靖季年,倭夷人寇,兵火疠疫之余,户口十损六七”。 (乾隆《晋江县志》卷3)此外,明代华南重男轻女现象严重,有溺杀女婴的陋习。明代中后期在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弃婴、溺婴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大量女婴被溺,造成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如福建建宁府浦城县正统七年(1442)男35591人,女22243人,男女比例为1.6:1。 成化八年(1472)男42915,女18245,男女之比为2.35:1。万历四十八年(1620)男32966,女11628,男女之比为2.84:1。由于“一邑之中旷鳏十居六七”。(重纂《福建通志》卷56《风俗志》大量无男子无妻,必然会影响到繁殖后代,影响到人口的自然增长。
明代华南载籍户口的下降也与明代中期以后的“隐口”、“逃亡”现象有关。明朝人曾说:“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于土木兵戎”。(《明史》卷77《食货》一)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明代中期以后,政治腐朽,社会黑暗,土地兼并,赋役繁重。这种情况在华南地区也有所反映。据文献记载,当时华南吏治败坏,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无名百出,一纸下征,刻不容缓,加以吏皂抑索其间,里甲动至破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5《福建三》)在这种情况下,“赋役则自少而多,户口则自多而少,纷纭谬乱,不可胜道”。(嘉靖《邵武府志》卷5《户口、赋役》)隐口、逃亡之事便不断发生。隐口有三种情形:一是一般农民不堪赋役剥削而隐口不报。这种情况是各级统治者都不允许的,所以虽然也有,但真正能隐瞒下去的并不多见。二是豪强、官僚、地主与官府勾结或依仗权势隐瞒家庭人口和依附于他们的农民。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三是官府或执掌户籍的官吏利用职务之便,隐瞒户口,从中渔利。这种情况也比较多。此外,因官僚作风而造成统计疏忽的情况也是有的。“隐口”现象会直接导致在籍户口减少。对此,明朝人多已论及。有人说:“余按古籍及后世之籍,户口代减,岂古之民多于后乎?盖上古据丁给田,故古之民无丁不报;后世论丁起役,故后之民无丁不瞒。然则非民之渐消,法使之也”。(嘉靖《增城县志》卷9)有人说:“顾令甲役民之制,丁赋三钱,以庸值计之,役五倍于周,而与事任力又不与焉。上但期于足用,不必计于隐口与否,下虽受重役之名,而实分输于数丁,上下固两得之矣。第此惟族姓繁夥者得以蒙浩荡之恩,而单门弱户分无所之,重役如故,至于以有身为患,不亦悲乎?”(《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2《福建二·户口》)还有人说:“抑或有司未稽其实,而奸胥蠹吏,佯为侥悻者地耳。旧制凡十岁一籍其民,大抵定田数而止,此弊政也。夫一邑之户始衰而终盛,一族之人始寡而终多,奈之何必因其旧也哉。是故豪家巨室,或百余人,或数十主,县官庸调,曾不得征其财帛。其一夫而田,田夫野人生子黄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钱,急于星火。此所以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也”。(万历《福州府志》卷26)可见“隐口”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其结果势必会造成载籍户口的减少。逃亡是赋役压迫的直接后果。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各级统治者都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使大量农民陷于极端的贫困化。明朝人说:“民贫以其产鬻于富家。富家得其产而遗其税于贫民之户。贫民惧逋而逃,官按户籍以取税,责及里长。里长无所偿则以逃。民之税摊之于存户。存户不能堪,又并以其产鬻而逃矣。前逃之税未了,而后逃之税又摊,其势必至于相驱而尽逃。不逃则亦相驱而尽盗也”。(嘉靖《增城县志》卷9)贫民“赋繁役重而力不能支,则其势不容于不逃;逃亡既多而赋役无所出,则官府不得不责之于见户。故一里之中,二户在逃,则八户代偿;八户之中,复逃二户,则六户赔纳;赔纳既多,则逃亡益众”。(《明经世文编》卷340《计处极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由此可见,赋役的增加和户口的减少是有内在联系的,可以说,重赋之下的逃亡也是明代华南载籍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四、载籍户口的价值
如上所述,明代华南载籍户口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政治腐败,赋役繁重而引起的黄册失真。由于政治腐败,纲纪废弛,贿赂公行,贪污成风,许多地方官把管理户口作为营私舞弊,渔肉人民,谋取暴利的手段,在编制户籍时勾结豪强,上下其手,随意改变黄册,隐瞒户口,把负担转嫁在普通百姓的头上。为了满足他们的腐朽生活,任意增加赋税,征发徭役,兼并土地,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迫使农民背井离乡,大量逃亡。被隐瞒或被迫逃亡的户口不在黄册之中,当然也就不在载籍户口之列。所以载籍户口所提供的户口数据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明代华南的实际户口比载籍户口要多。(注:目前有些学者在论述明代人口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见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既然如此,载籍户口还有没有价值呢?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
首先,载籍户口保存了较多的户口数据。明代华南文献不少,但户口资料却很有限。除了方志和某些地理书中的户口数据以外,只有个别人针对个别地方所发表的评论。这些评论虽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是一己之见,且往往不具体,不系统,不能进行定量分析。所以这些评论只能作为研究户口时的参考,而不能完全代替载籍户口,成为研究历史时期人口的唯一依据。明代华南的载籍户口虽不完整,但比较而言,本身是有一定系统性的。通志载一省户口,府志载一府户口,县志载一县户口,彼此之间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再说载籍户口数据较多,可以比较,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各地人口的变化。比如延平府及其所属各县的载籍户口中均有1442、1452、1462、1472、1482、1492、1502、1512、1522九个年份的户口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该府近百年间户口的分布和演变,不同年份可以比较,不同县份也可以比较。这是其他户口资料所不能代替的。此外,有些载籍户口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人口的民族结构、性别结构和职业结构。比如,《永乐大典》卷11907《广州府·户口》条载: 永乐元年,广州府“人户一十九万五千二百一十一,人丁男妇六十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四口”。同书卷5343《潮州府·户口》条载:永乐元年“人户八万六百九十一户,人丁男妇二十八万四千四百五十七口”。正德《琼台志》卷10载:永乐十年(1412)琼州府有户88606,口337479。 其中汉民71212户,296093口;黎人17394户, 41386口。正德七年(1512)年,琼州府有户54798,其中民户43174,军户3336,杂役户(包括官户、校尉力士户、医户、僧道户、水马站所户、弓铺祗禁户、鼋户、蛋户、窑户、各色匠户)7747,寄庄户541;有口250143,其中男子179524,成丁121147,不成丁58377,妇女70619。此类数据是其它资料中所没有的,对研究户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有人说,明代户口数中不包括妇女,(注:王其榘:《明初全国人口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有人说不包括军户、匠户等等。(注:王育民:《明代户口新探》,《历史地理》第9辑。)从有关资料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注: 葛剑雄:《明初全国户口总数并非丁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期。)
其次,载籍户口是明王朝实际掌握的户口,有一定的真实性。虽然说载籍户口中不包括隐口和逃户,不能反映当地户口的全貌,但载籍户口绝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随便编造出来的。前面说过,载籍户口是根据黄册整理的,而黄册既是明王朝的户口册,同时也是明王朝的赋役册,是明王朝征发赋役的依据。凡是编进黄册的丁男,都要服役,其他男人女人也要交纳“户口食盐税”及其他杂税,所以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口。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愿意多报户口而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赋役。尽管各级官吏在统计黄册的过程中因受官僚主义的影响可能出现一些差错,但差错肯定是少数。如果说这只是一种推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具体地看一看明代华南各地的载籍户口,把这些户口放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其他史料进行分析验证。通过这种做法,同样也可以证实载籍户口不是凭空伪造的,也有一定的真实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肯定明代华南的载籍户口确实是有史料价值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明代华南户口时,对明代华南的载籍户口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我们可以在掌握载籍户口的基础上结合隐口和逃亡情况推算明代华南各地的实际人口数量。但是,华南各地在各个时期隐口和逃亡的情况千差万别,文献中又缺乏应有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系统地列出明代华南各地的实际人口,显然是不可能的。与其在参数缺乏的情况下采用数理方法对载籍户口作主观上的修订,然后去分析所谓的“实际户口”,不如直接分析载籍户口。虽然载籍户口因“隐口”和“逃亡”而少于实际户口总数,但《大明律》对隐口和逃亡都有严格的限制,所以不可把隐口和逃亡的人数估计过高。应当说,载籍户口大体上可以反映明代华南户口的基本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