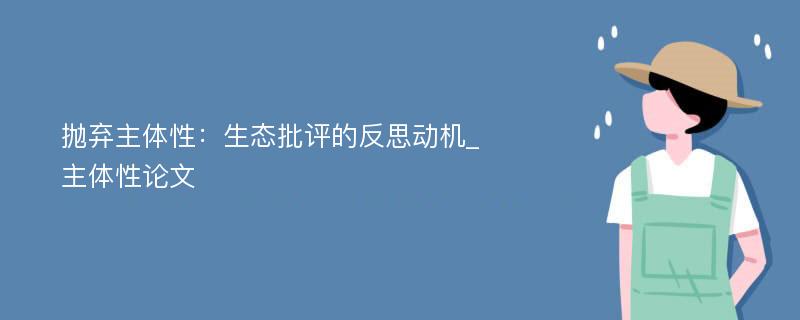
抛弃主体性——反思生态批评的动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动机论文,批评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注:本文摘自《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中的新方向》(Edited by Michael P.Branch,Rochelle Johnson,Daniel Patterson,and Scott Slovic,1998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of Idaho Press)一书,书中收录的所有文章都是从“文学与环境研究联合会”(ASLE,1995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召开)第一届会议中选出的,旨在“尽量广泛的呈现出代表生态批评领域最新观点的各种观点和主题”。生态批评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继女权主义批评和黑人批评之后、美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作品中的自然进行文化反思,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促使一种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新文明类型的出现。
1989年,谢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为文学批评家,我们要如何应对环境危机?”在她颇富影响力的早期论文《走向生态文学批评》(Toward An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中,格罗特费尔蒂说:“当其它社会运动,比如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都已经对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时,同时代的环境运动却没有做到达一点”[1]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格罗特费尔蒂试图通过提倡一种“研究人类与环境关系”[2]的生态批评“动员文学群落能够代表更广泛的生命群体”[3]。在格罗特费尔蒂以及很多追随她呼吁“生态批评”的人看来,“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不健康的、被误导的,因此正处于转折点或危机中。
这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它反映出一种常见的实体论宇宙观。很明显,通过将生态批评界定为对“人类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承认每一概念都作为一个彼此相关的名词,格罗特费尔蒂使得“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别变成真的。这种认为文化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分的观念在西方历史与认识论中可以找到对等物: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精神/肉体。人们意识到这种二元论导致了弊端——主体蔑视客体,文化反对自然,生态批评部分是对这一意识的回应。的确,正像很多其他生态批评家那样,格罗特费尔蒂敏锐的意识到二元论思维的危险,如她在其新近著作《生态批评主义读者》(The Ecocriticism Reader)的序言中所说:“一些学者……喜欢用‘生态的’取代‘环境的’作为他们的流派或者批评的前缀,因为‘环境的’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暗示着我们人类被非我族类的一切事物、被环境包围着。相反,‘生态的’则意味着彼此依赖的群体,结为一体的系统以及各组成部分的密切联系。”[4]因此,生态批评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发现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思维的途径。格罗特费尔蒂对生态批评的早期定义导致了“人类文化与环境”的二分体概念,这一事实正表明,生态批评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对二元论宇宙——被分成主体和客体的宇宙——的主观设定暗藏在我们用以谈论“环境危机”的每一个术语中。
通过比较生态批评与其它社会运动,格罗特费尔蒂主张将被解放了的主体性既作为目标又作为衡量公正的尺度。的确,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使得那些一度作为客体而被忽视的人群的主体地位获得承认,在这一点上它们是成功的。在这些“解放运动”中,主体性等同于获得发言权,即“在事务中发出声音”。按此逻辑,很多生态批评家已经致力于复员“自然的声音”并仔细聆听自然向我们讲述的。换句话说,人们希望自然的利益成为可以辨认的,正是怀着这一希望,“自然”正被带入“主体”范畴中。(注:在罗德里克·纳什(Nash,Roderick)的《自然的权利》(The Rights of Nature: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一书中这种哲学观念得到了最充分阐释。纳什认为将自然塑造为有“道德立场”的存在是那种“将权利扩展到被压迫的少数人身上的英美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人们决心通过将“自然”定义为主体来反对将其客体化,这种动机正是我准备在下文中仔细考察的。
人们总是希望人与自然能够重新连接或者统一起来,将自然看作“会说话的主体”的策略正是对这种的常见的整体主义希望的回应。但是,在准备承认“与自然建立连接”的部分整体主义幻想之际,我相信打着“会说话的主体”的旗号进行统一的努力无异于将一只方形螺丝塞进圆洞里面。在我看来,第一步失误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用来谈论整个问题时常用的那些词汇:通过承认诸如文化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类的二元,我们也承认了一个基本的实体论分裂,即中间空洞无物的两极性。在这篇文章中,我的意图就是设想我们可以迈出一直限制在文化/自然、或者主体/客体的实体论两极中的自然,而进入由实体间的关系形成的宇宙,其中的实体都是经常彼此调解和转化的。与其将其视作革命的尝试,像我在标题中使用的“抛弃”一词所意味的那样,不如把它当成批评意识的方向和价值的一种转变。抽象的纯粹在此毫无意义:虽然我们也会在关联中进行区分,但我们永远不会看见文化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出的清晰边界。同样,文学与其他种类的调解手段之间的界限也变得不那么清楚了。格罗特费尔蒂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之关系”的意图正是朝向这个方向的重要一步。即使如此,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用来定义关系中的两极的差异概念。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容易发现一些生态批评在有效杜绝这种两极性差异时,是如何采取了不同批评立场的。
正如格雷恩·拉夫(Love,Glen)所指出的,生态批评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提倡一种“自然导向的文学”“重新估价自然”,这种文学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必要纠正”[5]。在拉夫的宣言《重估自然:走向生态批评》(Revaluing Nature:Toward an Ecological Criticism)一文的标题中,“re-”前缀表明了人类在自然中的异化以及对自然的憎恶,这两种倾向都必须被生态批评工程克服。这两个互相交织的理论主题弥漫在很多生态批评中:自然一直被不公正的支配着,因此需要被解放,需要“被赋予声音”;不公正的支配来自异化的、病态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惟有重新连接人与自然才可以治愈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宣判——即认为仅关注人类文化不仅导致了对自然的不公正统治,而且也造成了人类社会自身的萎靡状态这种观点——表明迄今为止很多生态批评观点中潜藏着哲学整体论。虽然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联系的观念通常是拒绝二元论思维的,但问题在于它所期望的联合呈现在一种怀旧之情中:即主体只能在目前的异化与重新恢复到整体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意味着,主体客体之间的基本实体论分裂被当作了不可避免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与自然联系着的整体性之失落的追怀反映了一种最好被命名为现代性的姿态——即认为我们的世界与往昔截然不同,认为我们已经被从“自然状态”中异化出来了。
无论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失落的整体”是否被看作一种认识论假定——比如说,很多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就不会主张与在场的和谐——文化/自然或者主体/客体的两极都是使“环境危机”概念化的基本结构:文化做了有损自然的事情,自我利用“工具理性”压抑着他者。换言之,客体由于对主体没有价值而被虐待了,同样的推理方式可适用于女权主义批评色情文学。这种模式投射出以权利不平等为衡量标准而被意识到的危机,它相信清除客体化就会做到权利均衡,从而“解放”从前的“客体”。很多生态批评家力图通过重新恢复自然的主体性来实现此目的——也就是说,通过将所有自然事物从客体领域移入主体的理想领域中。这种观点认为所有重要的权利都伴随主体性而生,格罗特费尔蒂所指的那些社会运动的确获得了相对成功,因为它们为那些曾经被当作“客体”的隐形阶层争得了“主体地位”,比如妇女、少数种族、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等等。但即使如此,当那些被讨论的潜在主体——生态系统、迁徙的水鸟、地球——不能分享人类语言的时候,坚持把主体性当作有效的标准就困难重重了。对自然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的争论性描述很快就引发了关于谁可以真正理解自然的愿望的争论,而这个争论几乎没有解决的希望。在我看来,坚持将主体性作为有效标准正是被唐纳·哈罗威(Haraway,Donna)称作“简化主义”的一个例子,哈罗威将“简化主义”理解为“一种语言被强硬地当作众多变化和转化的标准时产生的‘普遍主义’”[6]。这样看来,挑战就在于用主体与客体或者文化与自然之外的范畴去设想人与其他实体的关系。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关系上,即使是集中在通过主体与客体的两极被理解的关系上,生态批评就已经开始重新理解整体了。
只要人们还把必要的生态运动看成是对遮蔽了主体性的自然的解放,批评家们就不得不理论化那些将“自然”容纳到人类政治学语言中的方法。为了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幽灵,生态批评家必须提出关于语言和主体性超越人类表达方式的定义。帕特里克·莫菲(Murphy,Patrick)已经根据从贝克哈汀那里得到的“女权主义对话”理论回应了这个问题,莫菲建议“从他者(other)中自然而然能够引申出‘另一个’(another)的观念,然后用‘另一个’去反思‘他者’或‘他性’。”[7]通过将这种彼此建构加在他性之上,“互相推动的生态进程——人与其他实体通过彼此相互影响而发展、变化和学习的过程——就成为可能了。”[8]“另一个”的概念与贝克哈汀的“时间性关联”概念有关,“‘时间性关联’是指在给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环境参数确定的时空中的社会/个体建构”[9],这意味着“‘他者’以其各种显现形式……参与着自我的形成”[10]。通过承认任何主体的基础都存在于活生生的经验语境中,通过尝试消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边界,个体作为“时间性关联”的概念就接近了生态批评所寻找的自我和他者、文化与自然的连接。莫菲对自我和他者参与彼此的形成这一观念所做的评价,与拉夫对“自然导向的文学”的评价存在着某些程度的相似——他们都把后者当作一种“必要的纠正”[11],当作把客体(自然)带入主体领域(人类领域)中的途径。
但是,当他者“参与”自我的形成进一步扩展到“建立在主体基础上的语言”这一层面时,问题又出现了:
正像‘他者’参与自我的形成一样,自我作为世界中的个体也以其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着‘他者’的形成。那么,与自我进入语言一样……‘他者’,以及任何实体,也都要进入语言,获得变成‘能够言说的主体’的可能。如此一来,‘他者’就成为被建构的,但建构者不是将要出现的会言说的主体自身,而是导致它出现的那个始作俑者 。”[12]
为了把“他者”塑造成会言说的主体,莫菲必须在各物种之间设置一个“通道”,此通道能够将他者的主体性输送到语言中。莫菲继续说道:“关键不在于替自然说话,而要使自然呈现给我们的意义变成以言说主体身份进行的话语描述,无论是通过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或者是通过没有明确主题的散文。”[13]对转化的信仰以及不误传“他者”意图的愿望,正是“替自然发言”与“使自然成为(发言主体)”的区别所在。在聆听曾经沉默的自然的声音的努力中发挥作用的力量,正是得到解放的主体性推动的解放运动所要实现的理想,格罗特费尔蒂使得生态批评模仿了这种解放运动:如果人们能够听到自然的声音,自然就可以在一切事务中发言了。
当莫菲公开声称自然不必象人类那样拥有意志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保持自然独立的真实性,莫菲问道,“当硒污染了地下水,导致动物畸形,降低了加利福尼亚农民持续耕种的能力时,我们能够读懂这些迹象吗?在阅读这些迹象并把它们整合进我们的文本时,我们是在让土地通过我们而言说抑或仅仅是我们在替它言说?”[14]我赞同莫菲的初衷,他是要把对环境危机以及导致危机的权利结构的思考当作一个批判性的道德问题,而非迷失在多重相对主义中的一些想法。但是我拒绝莫菲把言说主体的地位赋予自然的做法,因为它建立在“言说是获得权利的最佳途径”这个基础上。通过将“作为言说主体的自然的形成”建立在“出场”代理人身上,莫非希望将自然建立成—个被人类通过污染、城市化、人口膨胀等途径而压迫的主体。我当然赞同人类可以解释并理解污染的征象和环境恶化,并且这些解释是由情绪、道德观念以及对动物痛苦的同情心决定的。但是当评价“环境危机”的权威仅集中在一个纯粹的、沉默的、我们必须与之沟通的主体——自然——身上时,讨论已经倾斜到关于哪个“代理人”能够真正代表自然的利益这一话题上。我并非在怀疑非人类实体的道德可设想性,而是认为主体性作为决定价值、道德可设想性以及行动的模型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最后,“土地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就只剩下人们的争论所具有的分量;关于土地意味着什么的冲突性描述将会持续下去,继之而起的争论必然就是谁能真正理解这一意义。(注:如果时间和篇幅允许,我会引用生态批评家尝试为自然赋予声音的更多例证,特别是来自克里斯多佛·美尼兹(Manes,Christopher)和戴维·艾布拉姆(Abram,David)的例子,但我认为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明确了。我想再次强调,我并不想争论这些批评中潜藏的道德利害,而是想表明,既然大家很难在作为言说主体的自然究竟想表达什么这一点上达成—致,主体性理想作为有效的生态批评实践的基础就是不可靠的。所有这些都能够归结到关于代表权和真实性的老问题:我们如何知道自然是否真的被“正确”的表达了?我希望澄清的是,这个问题将我们的诸多关系——生态的、道德的以及美学的关系——徒劳地简化成了实体。)彼得·奎格雷曾经直接谈论过关于真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要将“自然”包括进当前关于语言和主体性的“合理化”概念中,就不得不把自然转化成“一个自由而不被妨害的个体”[15],一个有着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问题在于,不论多少被压迫的主体能够被从自然的客体领域中解放,主体与客体的两极性依然留下了中间有着巨大鸿沟的两个主要实体范畴。在此观点下,“主体”与“客体”或“社会”与“自然”就像是对宇宙中众多实体与关系的简单的令人震惊的同质性划分。
也许,主体性并不应该成为目的。我主张我们抛弃关于主体性以及对立概念客体性的话题,这两者是存在中高耸的极端。让我们设想多重的调解与关系,不是被标明在主体与客体这两大阵营中必属其一,而是由具体呈现、环境以及亲属关系展现出来。我以为,“自然导向的文学”与批评不能被当作赋予“自然”声音的途径,生态批评家应当把文学与批评仅仅理解为事物之间(人类也是事物,象其他一切存在一样)的一种特殊关系。通过提出这个本体论视角,我希望能够避免由“作为主体的自然的意愿究竟是什么”这一争议性话题引发的不断倒退。同时,我也希望发现一些方法,通过它们可以严肃的谈论人类如何评价与非人类实体的关系,即使是我们无法确定表明这些关系告诉了我们什么。换句话说,我认为成为人类语言中的主体不应作为道德可设想性的最高范畴。
布鲁诺·拉托尔(Latour,Bruno)所谓的现代性“净化工作”暗示着不通过主体与客体的清晰范畴而设想关系的困难。拉托尔将现代社会的核心劳动视为,根据事物如何适合于主体与客体或文化与自然的两极而将其进行分类和组织。拉托尔说,按照现代观点,不能适合这两类范畴其中之一的实体通常被当作“杂种或怪物”[16],即“两类纯粹形式的混合体”[17],它们被限定在经过净化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边境上。或者说,没有经过“净化”的实体只能通过它们既非彻底自然也非彻底文化的双重失败来定义。拉托尔认为,按照现代观点,主体与客体之间唯一可以被接受的关系是通过“媒介物”而存在的,比如观察或测量的工具,在观察时,它们允许主体独立于——明确的区别于——客体。这种“媒介物”“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联系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缺乏任何实体论地位”[18]。(注:拉托尔反复提到的例子是罗伯特·波义耳的真空泵,在自然科学史上它经常被当作用来发现气体的“真实”属性的纯粹工具。拉托尔声称,按照这种观点,“工具”在本体论上就另人怀疑的从属了它所指向的表面纯洁的“事实”;真空泵仅仅被当作科学家与自然真实之间的媒介物。)在拉托尔称之为“现代构造”的这种机制里,没有任何主客体之外的合法存在。
拉托尔建议我们密切注视存在于主客体纯粹极端之间的无人领域。在他称之为非现代性(与现代或后现代相反)的解释模式中,“(主体与客体或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分裂点——也即连接点——变成了出发点。解释不再是从纯粹形式前进到现象,而是从中心朝向极端。”[19]托尔建议我们应当设想“调解者”(mediator)而不是“媒介物”(intermediaries),“调解者是一个原发事件,它不仅创造了自己从中扮演调解角色的实体,而且创造了它所转化的东西。”[20]调解者不屈服于他者,即其他在本体上更有效的实体,反之,象所有他者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实体,存在于关系中并通过关系而存在。一旦人们不仅把调解者当作实体之间的关系属性,而且当作实体的建构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将本体的种类限制在二元中,”[21]比如文化与自然或者后主体与客体。由于调解是存在的属性,人们就不再过分高估抽象纯粹化的价值,抽象净化活动也就减少了可能性。没有什么是彻底自然或彻底文化的。每一事物都是调解者或者由其他事物转化而成,是一种不缺乏存在却由关联性构成的关系。
即使存在的纯粹状态不再有效,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进行区分并做出价值判断。只是,我们不必再考虑自然是否被文化过度改变,或者文化需要自然的影响,而是要思考什么样的调解活动正在进行,我们能够如何改变它们,以及它们如何有助于唐纳·哈罗威所说的那种事业,即造成“有限的自由、适宜、物质丰裕、从痛苦中体会到适度的意义以及有节制的幸福”[22]的事业。因此,文学批评家应当被看作复杂关系的解释者和参与者,他以自己在那些关系中的生存根基为出发点而言说,而不是站在一个想象中的“批评距离”上。从这一角度看,莫菲的问题——当我们写作或者谈论地下水污染以及动物畸形时,土地是否在“通过我们而言说”的问题——就显得有些误导了。关键不在于最后决定我们是否读懂了土地的意愿,而是要以格罗特费尔蒂所说的“巨大而复杂的全球体系”的参与者的身份发言,“在这个体系中,能量、物质以及观念都是彼此交织的。”[23]当我们阅读环境危机的迹象并把它们整合进我们自己的文本中时,我认为我们并没有使受伤的地球获得真正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我以为我们只是在表达以及投身于我们与土地、污染、动物、愤怒以及愿望的关系。正如我所理解的,这些关系是价值的基础,此外,我还希望有政治行动。
如此看来,格罗特费尔蒂呼吁研究“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通向那种我们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处境的重要的第一步。不错,我们应当研究关系,但我希望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不要首先就把存在归类到主体与客体的范畴中去。如果我们不仅把自身理解为需要被调解的对象而是看作调解者本身,那我们就不必担心造成一种纯粹却沉默的他者,因为我们会明白除了语言关系以外还存在着更多的关系。当我们的语言无法传达那所指之物的本质时,不用把它当作语言的失败,因为我们会知道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关系。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家们可以拒绝将文学作为对异化的人类灵魂的纯净丹药,这样做并不妨碍“对环境危机做出回应”。通过由各种活生生的联系构成的网络,文学(象很多其他事物一样)超越了艺术与学术之间的武断边界,生态批评家正是要坚持文学所体现出的这种超越的途径。“纯”文学将会随着主体与客体两极性的消失而蒸发,剩下的不是空洞,而是我们所能分享的存在的无限多样性与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