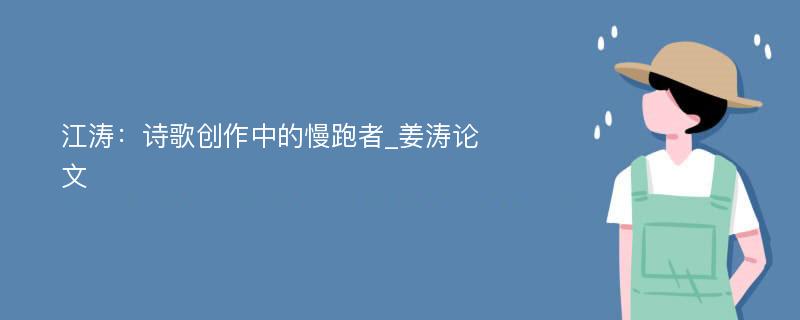
姜涛:诗歌写作的“慢跑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姜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缺乏目的,做起来却格外认真
白网球鞋底密封了洪水,沿筋腱向脚踝
输送足够的回力,一步步检讨大地
只有老套经验不足为凭,他决定尝试
新的路线,……——姜涛《慢跑者》(1999年)
在诗歌写作这条路上,姜涛自己就是一个“慢跑者”。他不算高产,也不唱高调,而且还常以他特有的自嘲来遮掩对诗歌的严肃、热情和与之相伴的苦闷。直到2005年,他的第一本诗集《鸟经》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①,而此时,这位貌似“新秀”的“70后”诗人其实已有十年以上的写作经历,这本诗集也已呈现出相当成熟的艺术面貌和明确的个人诗风。《鸟经》收录了姜涛自1995年到2003年间的56首作品,显示了他创作变化的轨迹与持续的创造力,被视为其诗歌写作的重要成果和风格转变的标志。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姜涛的诗歌写作确乎像是一场仍未完成的慢跑:他不求速度,不作姿态;“认真”,“检讨”,持之以恒;在耐力考验之外,还多有对“老套经验”的不满,以及对“新的路线”的尝试。
姜涛的诗歌风格也是“慢跑”型的。似乎是在有意抗拒雍容、沉稳、高贵、纯粹、激烈、高昂等诗歌美感的类型,他的“慢跑”于是大大有别于轻盈优雅的散步,或是果断急率的冲刺。他在语言和思维上故意制造的摩擦感造成了其诗歌节奏的相对滞缓,使他有时会表现得气喘吁吁、拖泥带水,有时又会“故意踉跄/甚至摔上一跤”,(《固执己见》——这既反映了他“讨巧不是一切的技巧”的写作观念,也暴露了他对于“某种尖锐的粗砺之美的向往”②,以及对于一种能够与“当下的思考、感受和生活,形成一种真实的摩擦的写作”的有意追求。——这一切构成了他的“慢跑”风格:在持续交替的腾空和蹬踏之间显示出力度、重量和耐性。
姜涛的诗歌呈现着一种综合、复杂、甚至矛盾、反复的特征,这也为阅读者和批评者提供了更丰富的话题和更大的解读空间。但惭愧的是,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遍览姜涛的诗作,也缺乏将他置于同代诗人当中进行比较并发现其独创性的积累与能力。因此,本文只能凭借并不周到的阅读来主观地、直感地讨论姜涛其诗其人,随意片面之处,只能请慢跑者本人和其他道旁观众多多原谅了。
从1995年创作组诗《厢白营》,到2005年出版诗集《鸟经》,姜涛的写作出现过几次转变。《厢白营》所代表的是其90年代“偏爱用粗大的重锤击打经验的外壳”的风格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尝试一种长长的、缠绕的句式,试图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结合进幻想、激情以及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创作了一系列体积较大的组诗。到了90年代末期,诗人开始有意识地“将对复杂性的偏好,控制在30行左右的空间里”,这让他“不得不充分考虑诗行的腾挪、转折,以及对短促瞬间的捕捉”。1998年的《三姊妹》、1999年的《编辑部的早春》和《慢跑者》都是这一努力的标志。而2000年的《情人节》则被他自己称作是向着“写得更松弛一些”的目标变化的开始:“在松散的诗节中”,他“开始公开谈论所谓的‘个人经验’,但又加入自我解嘲的成分,让诗中那个苦闷的自我,有一种虚构的面具效果。”随后三年中的作品,多数体现了这样一种“放松”的效果,因此,当2003年他自印的《鸟经》在圈中流传的时候,不少朋友将这种由“重”变“轻”视为姜涛诗歌风格的重要转变。冷霜就曾说过:“《鸟经》作为一个单本诗集,据有内在一致性的东西,同时也能明显标志了姜涛的新的写作阶段。给我最强烈印象的是,姜涛原先在一首诗、甚至一句诗里都要承担很重的能量,而后来他开始放轻了。……这些诗产生新的面貌、语调、句式上的轻盈,以及主题上的轻盈等,还有我们看到他对自己放松的方式,以及这与他原本一贯的诗歌气质之间形成的张力。”③
在姜涛诗歌写作的调整和转变引起广泛注意的同时,不容忽略的是这一变化背后的“不变”,或者说,是其转变前后写作风格的某种连续性。即如他自己所申明的:“其实,写得放松一些,并不意味着我也要追求‘轻逸’的品格,我的诗歌趣味,还是固执地倾向于浊重,‘举重若轻’才是我的理想。”在2006年的一次座谈中,姜涛这样表示:“就我个人的趣味而言,我觉得轻灵很好,但是不够细腻。我自己过去的诗写得太重了,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否就要解重呢?我发现在一些转变之后,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那种转变只是过渡,一种自觉放松的方式,但轻与重的问题其实在这里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一直说诗歌的戏剧化问题、综合的问题,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理想。其实很多东西要跟你的洞见联系在一起,诗歌获得真正的重量,不是单纯靠语言来解决的,不是仅仅结构放松就可以解决。……我的一个看法是,诗歌还是要有一种较劲的东西,一种力度,至少我个人觉得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诗学标准。诗歌应该有一种紧张感、一种对生活秩序的摩擦感,但具体怎么在写作中实现,我现在也很困惑。”④
无论从观念表述还是写作实践中都可以看出,姜涛并不是在进行一次顺序性的由“重”到“轻”的转变。也许应该说,姜涛的所谓转变是更倾向于在不轻易“解重”的情况下,将另一种品质——“轻”——加入到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姜涛的由“重”到“轻”不是在做减法,而是在做加法。他有意识地将“轻”与“重”两种品质同时——对峙地,并且尤要连带它们之间的张力地——内置到他的诗歌当中。因此,这种变化带来的不是单纯的放松感,有时反而是更复杂、更有张力的另一种“重”或是“更重”。这种“重”不同于他90年AI写作作的体积庞大、呼哧带喘,却构成了另一种质地更为复杂、更带有摩擦感的厚重风格。
笼统地以“轻”“重”来讨论一个诗人的风格也许有失精确,其中应该关涉到很多问题,比如冷霜谈及的语调、句式、主题,以及意象、结构、词语之间的关系等等。本文无意对这些方面一一涉及,只选择分析一个带有姜涛个人风格印记的特征:即其诗中大量出现的有关超逸的诗灵与沉重的肉身之间的纠葛,这里姑且称之为诗歌的“灵与肉”。在我看来,这对矛盾体在姜涛诗歌中的醒目存在,既与其诗歌风格之“轻/重”密切呼应,同时更是构成其“轻/重”风格的重要基础。
与作为文学主题之一的“灵与肉”不同,这里所说的“灵”与“肉”不是主题,也不仅指意象,它们更牵涉到诗歌的感觉方式、传达方式和美学效果。它们频繁出现在姜涛的诗作里,但彼此的关系却变化多端。“灵”与“肉”不见得长久相谐,也不一定随时冲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无所谓虚/实、高/下、主/从。就如同慢跑的步伐,总需由一次腾空与一次蹬踏来共同完成;“灵”的升腾与“肉”的滞重也往往就这样充满矛盾却又彼此依存地交织在一首诗里,共同结成一个复杂的整体。打个比方说,就像是姜涛在《另一个一生》中所写的那样:“屁股肿痛,脑袋里翻腾着思索”。
姜涛诗歌里大量出现的身体痕迹早就为评论者所注意。穆青曾认为,姜涛诗中所具有的“身体厚度和深度”,以及“它沉重的印痕和粗重的分泌物”,一起“构成了姜涛诗歌独具个性的阅读质感”;“人体上最沉重部位就屡屡现身在诗歌之中,几乎成为风格的标志。”⑤的确,粗略检视姜涛的诗就能发现诸如:“皮肤皱紧,眼袋含着阴影”(《内心的苇草》)、“梳着分头,牙齿乌黑”(《友情诗》)、“京味的下巴”(《另一个一生》)、胡须(《惺忪诗》)、眉毛(《我的巴格达》)、头发、嘴唇(《灭火》)。“一缕湿发,粘住多肉的大脑壳”、“黝黑的脸”(《梦中婚礼》)、“男人的喉结和胸沟”(《即景》),“膝盖和臂肘”(《生活秀》)、“女友的肚子”和“她身上的锁骨和假山”(《诗生活》)、“内衣里男人的脊背”(《外遇诗》)、“裸着”的“大汗腺”(《惺忪诗》)、“火热的精囊”(《另一个一生》)、“暴露的臀部”(《家庭计划》)、“裸身的男体”(《大河恋》)、“鲜嫩的脚趾”(《网上答疑》)等等,可谓从头到脚、面面俱到。甚至就连树木也“分不出性别,都长出粗大的喉结/和落叶的乳房”(《另一个一生》)。
这里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身体痕迹,意在让其特征和效果得以集中呈现。很显然,出现在姜涛诗中的这些形象多为粗重而笨拙的,既缺乏古典或浪漫意义上的美感,又不具备商业或娱乐意义上的性感。诗人写到身体的这些部分,并不带有对窥视者的迎合,也不是自恋式的暴露,更少有情欲的意味。事实上,这些身体痕迹在姜涛的诗中承担的角色,更多是美学风格意义上的。正因为它们既不美也不性感,反倒成全了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嘲笑了虚幻的美,消解了优雅与空灵,裹挟着具体生活中的苦闷气息,抗拒着智慧与玄思的过分炫耀。正是这些身体痕迹时时提醒着诗人:生活是真实的,肉身更是一个沉甸甸的存在。诗中这些身体痕迹,有的在无奈地发胖,有的甚至带着某种令人遗憾的缺陷,它们如同沉重的镣铐,使得总想腾空飞去的灵与思不得不时时返顾。诗人也由此不断地陷入自嘲、自诘甚至自反的境地。
当然,这种“灵”与“肉”应还不仅局限在字面意义上,更进一步说,它们的纠葛应还可以喻指诗歌中的“超验感”与“经验感”之间的复杂关系。我非常赞同姜涛本人的一个观点,即“‘经验感’的获得,不是因为写作者多么忠实于他自己,将他的城市、他的卧室、他的铺盖,一股脑地搬进他的诗里,而是他有能力,让那一些混乱的经验的柴禾,燃烧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经验’是诗歌中最隐晦的部分之一,指涉的是记忆、情感、知识的一种胶着状态,需要通过写作来艰苦揭示。正视它的‘晦涩’之处,就是要正视历史、生活的复杂性。”事实上,早有评论者认为:“在‘70后诗人’中,姜涛具有处理杂乱、琐屑、庞杂素材的罕见能力。”⑥应该说,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这几年的写作中,姜涛对于个人经验的处理尤为重视,他强调的是如何在混乱庞杂的经验感之中艰苦写作,以个人经验为基础,却腾挪自如,不陷入经验的泥淖之中。正如他在《诗生活》中所写的——
我几乎在所有能找到的东西上写诗
牙刷、雨具、屋顶的壁虎、床下的乒乓球
我甚至也在女友的肚子上写诗
当然,写的都是蠢话和废话
说大师的肚子也被浮云广播过
剩下的小辈,高矮胖瘦的
亦步亦趋,走过了90年代。
夜里失眠时,也会暗自琢磨
写过的东西都哪去了,变成印刷的楷体小鸟飞走了?
还是转化成持续的不平衡挤压在脑后
坚持自我教育吧:写过的才是经验过的;
而夏天的窗子四面开着,枝叶纷披着
一叶叶,反叛的也就是被教唆的
诗是从“所有能找到的东西上”产生的,而那些被称之为诗的“写过的东西”,即便是“蠢话和废话”,也都会插翅而飞,并不停留在“牙刷、雨具、屋顶的壁虎、床下的乒乓球”上。这或许就是“诗”与“生活”的关系,也是诗与经验的关系,同时还仍是某种意义上的“灵”与“肉”的关系。这种关系密切而又疏远,似乎随处可得却又神秘难测。一句“写过的才是经验过的”,准确地表露了姜涛的深思,就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内心的苇草》)。因为“诗”与“生活”虽然看似前者虚妄而后者真实,但事实却可能恰恰相反:那些未被“诗”捕捉和赋形的“经验”,永远无法脱离混沌、混乱的状态,只能听凭时间和记忆的过滤;而只有被“诗”照亮的那一部分“经验”,才能得以浮现,成为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
由此,姜涛在他的诗里建构了一系列这样复杂的、有意味的,甚至是古怪的关系:“轻”在加重着“重”,“重”在呼应着“轻”;“灵”在超度着“肉”,“肉”在诘问着“灵”;诗在照亮着生活,生活在蕴蓄着诗;……这些看似互不相容的因素被对峙着并置在一起,多少给人带来了陌生与震惊的效果。这让我想起姜涛的一句诗:“撩人的月色曾像一块牛皮癣,多少个世纪/都挥之不去”(《童话公寓》)。这里,“撩人的月色”与“牛皮癣”被古怪地放置在一起,诗人在看似不相干的地方发明了二者的关联,形成了阅读上的意外和摩擦。而这种奇特的效果不正是“轻”与“重”、“灵”与“肉”、“诗”与“生活”之关系的一种体现么?
由于多重具有内在张力的品质的共存,姜涛的诗歌风格呈现出一种类似“复调”的特征,而对戏剧化效果的追求,又进一步加强了其诗歌的对话性气质。诗人与诗中角色的对话甚至争辩,常常可以被理解为诗人内在双重自我的展现。他们在诗中不断变换着各种面具,使得原本倾向于自言自语的诗歌文体演变为多声部的交谈、诘问、反驳、争论的现场。在这样的文本中,很容易发现一种姜涛独有的自嘲与自恋、坚执与迟疑并存的诗歌写作姿态。
我当然知道把所有问题都“一分为二”地谈论,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方法,它有时甚至会出于还原复杂性的好心,却反而犯了简单化的毛病。但是左思右想我还是不得不继续拎出姜涛诗歌中可能存在的这种“二元”,来探究其复杂的诗歌美学效果的成因。也许应该说,是姜涛的诗歌自身所呈现的多元分裂和紧张,决定了我的谈论方式吧。
自嘲与自恋——这里所谓“自恋”并不包含任何贬损意义——几乎是姜涛诗歌的典型气质。尤其是在2000年后更多涉及个人经验的那个写作阶段,这种调子的出现就更加鲜明而且频繁。他常以自己的种种生活经历和经验作材料,施以一番不失严肃的自我解嘲。比如这首《固执己见》——
……当一个傻子被提拔成博士
出道后,他还要朝三暮四地奇妙
只有龙的形象沿袭不变
长嘴环眼,胡子像强盗
还能虚幻地消失,见不到首尾
在这个“被提拔成博士”的“傻子”身上,处处带有诗人自己的气息:他总是“被人看成是书生,一脸的梁山伯气”(《送别之诗》),与很多“也是苦出身”的“难兄难弟”一起,经历着“什么星移斗转,人世沧桑的/其实,什么都没变”的生活,“还彼此背诵对方的诗/白话格律,标点免费/精魂全在一口深呼的气里”(《富裕经验》)。姜涛的自嘲不全是诙谐的,他故作轻松的口吻还是泄露了内心沮丧的秘密。这说明了他的自嘲并不源于超脱,相反却是来自苦闷。当然,通过自嘲诗人并不能摆脱沮丧和苦闷,但或许能收获一种清醒和诚实的心安理得,并暂时性地取得某种与严酷生活之间的和解吧。
姜涛的自嘲是一种有节制的、矜持的自嘲,这一点又与他内心的自信与自恋相关。自嘲的人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自暴自弃,另一种则是善于清醒地自我审视。姜涛当然属于后者,在他自审的眼光里,流露出的常常是自信与笃定。这在《生活秀》一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其实,事物都会选择一个对立面
端详自己。下午无事
外出买酒,回家自我分析:
我的生活在镜子里看来平稳
已经渡过人称的危险期
抽屉里没有纸的风浪
与配偶的争吵也吵出了规律
还有个幻影在外面定期上班
定期约会,定期从银行卡里
向老家汇出记忆和眼泪
只有我知道,那不是我
至少不是此刻的我,一手把酒
一手敲打出键盘上的混蛋们
经常选择自己或自己的“对立面”进行端详和分析,表面上安于平稳、合乎规律,但内心却清晰而坚定地知道:“那不是我”。——这是姜涛诗歌中的自我形象的一个常态。他会同时表现出对生活表面的无奈让步,和对内心自我的顽强坚守,不停地徘徊在以自嘲寻求和解或以自恋坚持抗战的两种方案之间。然而现实往往是“无物之阵”,就像他最终沮丧地发现的那样:“生活早和对立面和解/早被一句儿戏催了冬眠”。于是,意外的和解又消化了抗战,而这个虽然沮丧但仍不失清醒的发现又反过来嘲笑了和解。或许可以这样说:姜涛在他的诗里不断地自嘲和自恋,但同时又随时设置“对立面”,以无法和解和无从抗战来抵消那一切的自嘲和自恋。这种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体现在对生活和自我的理解上,当属更高一层的认识。而这,应该既是姜涛的诗歌写作方式,又是他的基本人生态度。
因此,对待诗歌,姜涛一直也抱以一种坚执与迟疑并存的态度。正像他在《辩护之外》中所说的:“出于一种朴素的自我辩解的需要,我现在要说:自己真实的心态,不是依恋远山,而是想发明远山,是想重构一种写作的方法。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在语言的磨练之外,更需要对世界开放自己的身心。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清楚,写作停滞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没写那些不该写的。虽然该写什么,还是不知道。我甚至有点庆幸,自己能够停下来,好让沉闷的大脑里,能吹进一些空气,多一些回旋。毕竟,今后还是要写下去的,同样有时激越,有时沮丧,但希望自己不再为了一两首闷骚的好诗而忘乎所以了。我所希望的是这样一种诗歌,它能率性写出,但也饱含张力,并构筑视野。如果不能这样,放弃写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照此看来,姜涛的诗歌“慢跑”也许更要放慢脚步了。但让人相信而且期待的是,在这种放慢甚至停顿之后,一定有新路径、新风格出现。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①2003年,姜涛自印的同名诗集已在同行中获得了好评。
②《姜涛访谈录:有关诗歌写作的六个常见问题的回答》,西渡、郭骅编《先锋诗歌档案》,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176页。本文引文不注明出处者皆出自此文。
③④《生命场景中不经意的瞬间——解读姜涛的〈我的巴格达〉、〈古猿部落〉》,《中国诗人》,2007年第四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穆青:《诗歌的体态、体液和体味》,《先锋诗歌档案》第188-190页。
⑥敬文东:《没有钟点的旅行——也说“70后诗人”》,《偏移》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