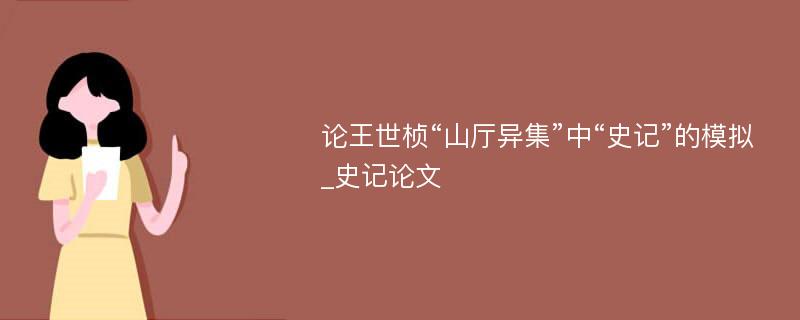
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别集论文,王世贞论文,弇山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世贞是明代的文史大家,八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多偏重于对其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其史学也受到广泛的注意。在瞿林东教授主编的《史学巨擘》〔1〕一书中,遴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家三十五人, 上起司马迁、班固,下迄翦伯赞、吴晗,而在明代史学家中,只选了王世贞一人,由此可见王世贞的史学地位愈来愈得到肯定。
王世贞的著述很多,其中不少是史学著作,除《弇山堂别集》外,还有《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名卿纪绩》、《明野史汇》等,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中亦有不少史学内容,万历年间董复表将其史学著作汇编为《弇州史料》前后二集。〔2〕在这些著作中, 最为王世贞重视且为明史研究之必备书的莫过于《弇山堂别集》。该书一百卷,笼统言之即为史料笔记,但仔细研究,其体例实自具特色。对此,明人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序中已有过说明,他说:“我以其才,为所欲为,纵横自放,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其于子长,以意师之,不可称龙门之大宗乎?”陈文烛提出王世贞以“意”师法司马迁,所以创立别集一体,《弇山堂别集》就是效法《史记》之作。笔者以为《弇山堂别集》不只是师司马迁之“意”,在“形”上亦步其后尘。下面看看他是如何“师意步尘”的。
一、史学之模拟
刘知几在《史通》中已经注意到史学模拟的问题,他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因为“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因之,他并未指斥模拟的本身,只是觉得模拟应该区别对待,他把模拟分为两类,一是“貌同而心异”,二是“貌异而心同”。〔3〕并认为前者是“模拟之下”,后者为“模拟之上”; 前者应当否定,而后者应当提倡。因此,模拟本身是毋须指责的,应该关注的是采取何种方式去进行模拟。
明嘉、万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一种文学上的反对八股时文,宣扬模拟古文的运动,他们宣扬“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4〕。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更具体谈了模拟的原因以及如何模拟,全文录之如后: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问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积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册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5〕
此乃王世贞模拟古人作文之思想与理论,是“文必西汉”的具体诠释。古代文史不分家,作文如此,修史亦不出此道。在史学上,他刻意模仿司马迁,从作史之志向、所采之史例到具体的成果,都反映了这一点。
从王世贞作史之志向看,他常有言论表示要师子长而著史,在《国史策》中,就有具体的表述,而且给自己找到了模拟的根据:
“愚故欲法司马氏,而窃意其变化于帝纪孔氏之文,训故《尚
书》、《家语》而节略之,以为不称。又生不遇左氏《传》,故其
叙春秋诸《世家》舛忽不详,好自发其意,故于《刺客》、《游侠
》、《货殖》、《伎幸》之伦,偏采而不忍斥,有能删节其凡例,
自羲皇而下迨于今,为一家之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愿为之执
鞭,而终其身也。”〔6〕
王世贞在这里指出《史记》乃效法《尚书》等节略之而成,同时表示了愿为国史而终身效法司马迁。似此作史志向,在给友人的信中又多次有所表示,他在给徐孺东的信中言:“仆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齐一代史事,以窃附于古作者之后。”〔7〕又言:“方仆盛壮时, 妄自意以为班史而后,纪传之体猥杂偏胜;左氏而后,编年之书繁简失次,亦欲整齐其事与辞,勒成二家,以追迹盲、腐。”〔8〕
在诸家古史中,王世贞认为只有班固能为史,其原因乃班氏继承和模拟了《史记》等诸家古史之结果:
“夫孟坚之为史也,非尽孟坚史也。后元而前,太史公共之矣
;始元而后,叔皮共之矣;志有十大家共之矣。夫志固无论,其它
若纪传,或繁而损,或略而益,或因而裁,或朴而润,微孟坚,畴
所折衷哉。帝纪之雍容有度,列传之整洁瞻显,彬彬乎太史公雁行
矣。”〔9〕
在这里王世贞以为班固《汉书》之所以成功,乃效法司马迁《史记》及其他史书的结果,是对以前的书稍作变化增删而成。而随后史书之失败也就在于未遵前人之体,未法前人之书。因之要使史书成功,非效法前人不可,非模拟古人不成。这是他模拟古人的理论根据。而王世贞的志向就是“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10〕。因之他要效法司马迁,成就当代国史。
二、何谓“别集”?
自《别集》问世以来,就受到非议。所谓“别集”, 当指文集〔11〕,其以史书而言别集,难怪要被人指责为不懂别集之含义〔12〕。其实王世贞名之“别集”,确实另有隐情。清人周中孚亦以为“是篇记述明一代君臣事迹,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他虽然指责别集一名,但亦不否认是另立一体。前面提到,陈文烛也以为王世贞之别集乃效法《史记》而自成一体,自具特色。
王世贞究竟为何以别集名史著,他在《弇山堂别集》自序中对“别集”一名加以解释,说:
“《弇山堂别集》者何?王子所自纂也。名之别集者
何?内之无当于经术政体,即雕虫之技亦弗与焉,故曰别集也。”
陈文烛则认为因“元美诗文有弇山堂正集,而此则国朝典故,比一代实录云。”〔13〕所谓“弇山堂正集”,即《弇州四部稿》〔14〕。故此书只能名之为别集了。
《四库全书》则以为是王世贞晚年知作史之难,故以别集为名以示谦抑:
“世贞承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
,故其所述俱确有可征,迥非诸家耳食传讹者比,且不敢自居笔削
,第用说部之体,烘聚条分,而以别集命名,深致谦抑之意,亦由
晚年境地益进,深知作史之难,故能敛晦如此。与当时略窥纪载便
奋然以史笔自居者,相去亦不啻霄壤。”〔15〕
笔者以为用“别集”还另有隐情,王世贞之志是法司马迁而作一部纪传体的明代史,但迟至暮年依然未见希望,只得退而求其次,编成《别集》,此书成于1590年前后,不久他即故去。陈继儒在《弇州史料叙》中谈及王世贞晚年于明代国史之心态时言:“偶及国史,辄停杯不御,为慨然感叹久之。”王世贞一生以国史自任,但终究未完成自己的心愿,那份于心不甘、壮志未酬的落寞感自不待言。既然编明代国史的心愿未成,只得退而求其次,做一部类似于纪传体而又非正式的纪传体史书,故名之曰“别集”,聊以自慰罢了!这大概是其以别集为名的真正内在原因吧。
对于《史记》体例上之模仿,王世贞在给友人况吉夫的信中表示过一种心态,他认为《史记》中的《游侠》、《刺客》、《货殖》之类使得《史记》“非正史也”,因为其“或借驳事以见机,或发己意以伸好”,故此完全模仿就有问题,“今欲仿之则累体,削之则非故,且《天官》、《礼乐》、《刑法》之类,后几百倍于昔矣,窃恐未可继也”〔16〕。王世贞对那些传不满意,想削之而稍作变通则有“非故”之忧,法之则又有“累体”之嫌,故此处于两难境地,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史记》之亦步亦趋至于何种程度。
《史记》之纪传体是以本纪志帝王,世家记诸侯,十表系时事,八书载制度,列传叙人物,而《弇山堂别集》主要有《皇明盛事述》五卷、《皇明异典述》十卷、《皇明奇事述》四卷、《史乘考误》十一卷。接后有诸表,共六十七表三十四卷,如《同姓诸王表》、《公侯伯表》、六部尚书、中书省等表及《卿贰表》。最后是诸考,共十二考三十六卷,如《亲征考》、《命将考》、《谥法考》、《赏赉考》、《诏令杂考》和《中官考》。此书之“述”、“表”、“考”三体〔17〕,就构成了陈文烛所言之“别集”体。从表面上看,除“表”一体为纪传体所有外,其他似与纪传体无关。其实不然,仓修良已注意到“考”对“志”的效法,并认为《弇山堂别集》是“编纂纪传体的一种素材”〔18〕。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各部份是如何效法纪传体的。
三、“三述”祖述“纪”意
所谓“三述”即《皇明盛事述》、《皇明异典述》、《皇明奇事述》,《四库全书》以为其“颇涉谈谐,亦非史体”〔19〕。其实王世贞设立此体,有其特别的意图。他在《皇明奇事述》序中,既对“三述”关系进行了阐述,又说明了他作“三述”的意旨:
“异典者,遘之自人主也;盛世者,遘之自天也。盛事之遘无
非媺已,异典之遘媺居十九,疵亦居一已,乃复
有遘之自人而不可言典,或人与事之巧相符者,或绝相悖者,为其
稍奇而不忍遗之,别录成卷,以备虞初、春明之一采,故不敢称稗
史也。”〔20〕在王世贞看来,所谓异典、盛事、奇事,或自“人主”,或自“天”,自然是关于明之军国大事,不应弃而不载。笔者以为从功能上王世贞是以之来奠定全书基调。刘知几以为“纪以包举大端”,本纪是记载帝王之事,统领全书格局。而林駧认为:“子长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秦始皇已并六国,事异于前,则始皇可纪也;项羽政由己出,且封汉王,则项羽可纪也;孝惠高后之时,政出房闺,君道不立,虽纪吕后亦可也。”〔21〕可见司马迁创立本纪一体时,亦并非只局限于帝王,只要是关于天下之事,即使非帝王亦可作纪。因此既然是关于“人主”和“天”之事,“三述”在功能上和全书的地位上乃是可比拟“本纪”的。
“三述”从形式上言,只是一条条的史料,似乎无甚关联,其实每一卷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以《皇明盛事述》〔22〕为例,它共五卷,卷一是记载宫廷与皇室的所谓盛事,如皇帝之功德,藩国之强盛,宗室之繁盛,勋臣国戚之事;卷二是记载官宦家庭中的所谓盛事,如官吏之封赠,几代同任高官,几代科第等等,卷一与卷二的两类家庭,构成了封建统治阶层的最上层,他们原本就是封建史家注意的对象,当然也是王世贞注目的中心。卷三偏重于某一地方之所谓盛事,如果一州一地有许多高官,当然可以说是盛事,如“崑山盛事”、“严州盛事”、“蒲州盛事”、“吴中盛事”等等;卷四偏重于记载个人获得的官职、封赠等等,封建士人最重高官重位,若一人能得多种官职,或历官长久,自然可以称为盛事,如“四入内阁”、“三总三边”、“四总河道”等等;卷五偏重年龄问题,既得高官厚禄,又得长寿,当然值得祝贺,即便不得高官厚禄,但得长寿,亦是令人羡慕的事,因而也成为王世贞注意的对象。我们总括各卷重心,可得如次的轨迹:宫廷与宗室之盛——家庭之盛——地方之盛——个人之盛。宫廷与宗室是封建国家的化身,家族与地方使家庭得以依存,人之官位与寿命可以说是修身之结果。这样很明显地体现了作者所关注的目标,正同封建社会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见,王世贞“述盛事”是独具匠心的。《皇明异典述》亦秉承同样的原则,以记载卓异之事,彰显明朝之功德。《皇明奇事述》之所谓奇事,则多是载有一种特征相同者,如同名、同爵、同官品、同姓、同谥等等诸种特征相同者,归纳为数条,如“嘉靖二真人”、“甲辰二会元”、“绍兴二首甲”、“蒲州二孤”、“全州二相”等等,亦有姓名相同一类的史料。王世贞所谓“异典”、“盛事”、“奇事”,正含有称颂当朝之意,这是其所用的春秋笔法。
汪荣祖指出:“国朝之国本植于帝室,求一姓之绵延”,而求一姓之绵延“有赖忠君爱国(国者,朝廷也),所彰之善,忠臣良将;所瘅之恶,乱臣贼子也。其归宿在于惩劝”〔23〕。王世贞的“三述”既是称颂明朝,同时又具劝惩之意。与王世贞同时代的归有光以为史家“扶翊纲常,警世励俗”应是常理,故国史之精神应有三点,“一曰显忠臣,二曰诛逆子,三曰树风声。”〔24〕《弇山堂别集》中的“三述”所担当的作用正是这三点。于此也可看出王世贞修国史那种强烈的责任心。而从功能上来说,“三述”正祖述了纪传体“纪”的用意。
四、诸表之模仿
《弇山堂别集》之表是对《史记》之表的模仿,自《史记》创立表后,即为纪传体史书之一例,但由于作表不易,后代史书多有略去者。在纪传体正史中列表的史书,《史记》以外,只有《汉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新元史》,一共九部史书,不足二十四史之半。但表之重要正如顾炎武所言:“年经月纬,一览了然,莫大于是。”〔25〕并以为作表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文字。浦起龙亦认为表“揆之史法,参以时宜,亲若宗房,贵如宰执,传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没,胥以表括之,亦严密得中之一道哉!”〔26〕赵翼则认为“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27〕诸多史家重视表,其重要性由兹可见一斑。
在《弇山堂别集》问世以前,郑晓《吾学编》中即已列四表,分别是:《同姓诸王表》、《异姓诸王表》、《直文渊阁诸臣表》、《两京典铨表》,前二表后即接同姓诸王传和异姓诸王传,采取表传结合的方式。王世贞显然参考了《吾学编》,但《弇山堂别集》中的表分得很细,前后一共六十七表,三十四卷,远非《吾学编》所能比拟的。先是《帝系》、《同姓诸王表》,下又分为《亲王》、《郡王》;《公侯伯表》下有《高帝功臣公侯伯表》、《永乐以后功臣伯表》、《恩泽公侯伯表》、《衍圣公爵系表》、《追封王公侯伯表》、《公孤表》;其他有《东宫三师表》、《公孤宫臣表》、《内阁辅臣年表》、《翰林诸学士表》、《六部尚书表》、《卿贰表》等。涉猎的范围从皇帝、王侯到大学士、六部尚书、卿贰,几乎囊括整个明代中上层统治者。
清初傅维鳞著的纪传体《明书》中的表,可以说是《弇山堂别集》之表的翻版。《明书》有《祖系故王表》、《同姓诸王表》、《公侯伯表》、《恩泽公侯伯表》、《圣贤世裔表》、《追封及赠王公侯伯子男表》、《辅臣部院正卿年表》、《柱国公孤表》、《学士祭酒表》、《卿贰表》、《先设后革诸官表》、《制科取士年表》等十二表,除《先设后革诸官表》、《祖系故王表》、《制科取士表》外,其它的几乎都是改编《弇山堂别集》诸表而成。王世贞修明代国史列表最完善,故此,其以后的明史书,只要列表,莫不受他的影响。《明史》诸表,有《诸王世表》、《功臣世表》、《外戚恩泽侯表》、《宰辅年表》、《七卿年表》,较之《弇山堂别集》要简略得多,而其参考了《弇山堂别集》也是显而易见的。
王锦贵将中国古代史书上的表分为七类:表国者,表部族者,表世系者,表官者,表人者,表地者,表事者。〔28〕这是根据表所记录的对象而分的,以此原则来分析《弇山堂别集》中之诸表,我们可以看到王世贞是以职官之大小,地位之高低来制作表的,可以称之为表世系者,表官者,表人者。从这些表中,我们可以了解明代爵位的变化,官职源流之沿革,因而其地位十分重要。
纵观全书,表的记载内容基本以明代为范围,唯有《衍圣公爵系表》例外。它是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明嘉靖年间一千多年的衍圣公封爵全都谱列出来,之所以打破有明一代之范围,王世贞在序中有如下的说明:“然孔子实成汤后,论者不知其所自起,余故因表衍圣公之爵系而备识之,明孔子非国家所得而封建也。”〔29〕明代对孔子的尊崇甚于往代,尤其是嘉靖年间,把孔子称为“至圣先师”,衍圣公之地位因而也显赫得多,故此,王世贞在史书中亦予以相应的重视。
从格式上说,《弇山堂别集》中的表与正史不同,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批评的,则是“多未依旁行斜上之体”,它未依表例,因之亦屡被人攻击〔30〕。但其价值则不容忽视。
五、“考”与“书志”的关系
《弇山堂别集》中有十二“考”,共三十六卷,是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除专门考辨史书之《史乘考误》外,还有《亲征考》、《巡幸考》、《亲王禄赐考》、《命将考》、《谥法考》、《赏赉考》、《赏功考》、《科试考》、《诏令杂考》、《兵制考》、《市马考》、《中官考》,一共十二类。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仓修良以章学诚之分析为根据,“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31〕。因而断言“考是记载典章制度,就是纪传体史书里的书志部分”。〔32〕“考”与“书志”之间的关系仓先生已作了充分的论证,但“考”是否就是纪传体中的书志部分,则还有详析的必要。
司马迁首创八书,班固变书为志,此后即成纪传史书之一体,历千年而不变。刘知几以为“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33〕。因此,志重点在于论述典章制度。王世贞虽然记载明代的制度,但是他只称“考”而不称“志”,其间必定另有原因,因之,将其完全等同于“志”似不太妥当。陈文烛以为《弇山堂别集》乃师法子长之意而作,“考”正可谓祖述“书志”之意而成。
在十二考中,《谥法考》、《科试考》、《兵制考》自然是典章制度,这毋需多言,《明史》中就有《礼志》、《选举志》和《兵志》,谥法是礼的极其重要的部分,而科试几可以与选举等同。《赏赉考》、《赏功考》谈明代有关赏赐制度及事例,在《明会典》中有类似的《给赐》、《赏格》,记载同样的内容。至于《中官考》、《诏令杂考》、《巡幸考》等则在书志中找不到相同的内容,但它们同样记载了许多典章制度方面的材料。即如《中官考》,先记载明代宦官制度的变化沿革,同时述说明代宦官专权误国之史实,十分详尽,远非一般的书志可比拟的。它既详细记载了制度的变化沿革有书志体的优势,同时,又详述了历史事实。可以说它兼有“志”和“宦官传”的功能。同时因其是按年月来记明代宦官之干政,具有编年体史的特色。因之,这些可以说是“考”自具的特点。
名之为“考”,还在于书中有真正的考据。并非只是一味地陈述史实,对于类似的问题,王世贞往往将其与前代相关史实进行对比。同时纠正明代有关书籍记载之错误,如《亲王禄赐考》,即参核《会典》,并纠正《会典》记载之错误。王世贞以为《会典》记明亲王、郡王禄赐时,俱引唐制为参考对象,但唐代之亲王、郡王与明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究其原因,“盖唐制王公以食邑为准,而有官则有禄,宋制食邑真食皆为虚,而以兼官制禄,与本朝之制异,不可强而引也”〔34〕。再如《之国之赏》,有如此考据之言:“按古之恩赐可考者,汉昭帝初,赐燕王旦……钱一千万”,考汉唐宋之恩赐后,其发议论曰:“汉与元之赐宗室如此,其去我朝何啻十倍也。”〔35〕
《弇山堂别集》中除有《史乘考误》专章考证明代的国史、野史、家乘之误外,在《考》部中,又随时加以考据。一则纠正史实,再则在考证之时进行评论。再以《中官考》为例,在述说明代宦官干政史实之际,详考相关的历史。如记宣德赐宦官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免死诏时言:“按太宗于光禄卿井泉张泌皆有之,则其时内臣所必有者,但不可考耳,此见范弘墓志,史所不载也。”〔36〕《中官考》中,常有“干政之始”、“封赐之始”这样的说明语,如记天顺元年王振恢复官爵,立祠赐额曰“旌忠”,作按语云:“按此内臣立祠之始也。成化中御马监太监刘永诚祠曰‘褒功’,弘治司礼监太监怀恩祠额曰‘显忠’。此二臣皆可纪者,自是而后繁且滥矣。”〔37〕又如记西厂之设云:“此立西厂之始也,虽与东厂侔,而势出其上矣。十三年革西厂,以御史戴缙言,仍复之。”〔38〕文中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既予考证又加议论。
《诏令杂考》原非书志一类所包含,但王世贞设立此体,实有深意焉。他在《诏令杂考》序中说明了作此之原因:“自高帝以后书檄之类不登诏令及不可以入史传者,录以备考。”〔39〕于是作《诏令杂考》四卷。似乎只是补遗性质。但是,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不仅保存了许多它书难见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诏令与书志的关系。唐代刘知几就提出应立一体以载诏令章表。他说:
“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
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
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以类区别,他皆仿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
。”〔40〕王世贞的《诏令杂考》虽未明确提出将诏令当作纪传体史之一例,但他的考是师法书志之意而成,恰在此部份收录了诏令,由兹可见,王世贞确实将其看作是书志的内容
其实在王世贞的著作中,也有名之为“志”的内容,《四部稿》中就有《北虏始末志》、《安南志》、《哈密志》、《三卫志》等,但这些名之为志的文章,只是将事件始末按年代先后予以记载,应属于纪事本末体一类的史料,与纪传体之志则基本上扯不上关系。
综上所述,“考”是师法子长纪传体“书志”而来,但又与“书志”有不同的特点,它不只是记载制度条文,同时,亦记录相应的史实。并进行相关的考证,它兼有“志”、“传”、“编年”诸体之特色,是纪传体的一种变体。如果按陈文烛的说法,王世贞独创了“别集”一体,那么,“考”可以说是“别集体”中最为成功的一例。1614年,王世贞的门人董复表编《弇州史料》时,特将“考”放在前集的最前面,由兹亦体现他对“考”之重视。
此外,在《弇山堂别集》中,每部分都有序,在每部分中,往往又分总序、分序、大序、小序,不一而足。而篇各有序,亦始自《史记》。
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总括《别集》中诸序,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曰说明编纂原则,统括全篇;二曰叙述渊源,明其沿革变化;三曰评论史实,表达观点。其中第二类是最多的,究其原因乃有关国家政制,“凡国家之典,始则若滥觞,继则滔滔焉,又继则汤汤焉”〔41〕。是故于序中明其变化因革就显得十分重要。
再则,在《弇州山人续稿》中有《史传》十卷,其中有“世家”四卷、“传”六卷,世家收录了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朱能、定兴王张辅和宜平王朱永,之所以将其列为世家,只不过他们有一王爵封号罢了。这是王世贞之模仿拘泥于形式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因为世家应“开国承家,世代相续”〔42〕,而明代的异姓王只有封号,既无封国,亦鲜少世代相续者,将其列入世家,实乃勉强。
六、总 评
明代文学上的复古,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因为由国初到末世,主张复古的议论层出不穷,因之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主流。〔43〕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古人,则鲜有人论及。其实古代文史原本一家,文学上的复古,势必也造成史学上的因循,因之而模拟古人。但史学很少谈复古的问题,因为明代文学上的复古主要是针对八股时文而起,而史学则无反动的对象,对史学而言,或是因循承袭,或是创新发展,这也许是史学很少谈复古原因之所在吧。王世贞是后七子的领袖,独掌文坛二十余年,在文坛上的模拟古人已成定论,而要修明代纪传体国史对司马迁的模仿自是当然。
中国传统史书中的三大体裁(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自创立以后历代因循,因之后人模拟是极其普遍的,具体要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刘知几并不反对模拟,但他主张“貌异而心同”,而反对“貌同而心异”。正如前面所提及,王世贞追求形式上的雷同,他觉得《史记》的《刺客》、《游侠》、《货殖》诸传不妥,删之觉得“非故”,仿之以为“累体”。《弇州山人续稿》的《史传》中特别设“世家”一体尤显无理,只就其名,不得其实,正是他模拟追求形式的体现。
《弇山堂别集》的模仿不像《弇州山人续稿》史传的模仿那样拘泥形式,“考”、“述”之设立是纪传体的一种变例。尤其是“述”,只是一种神似的东西,在“形”上没有任何纪的色彩,以故多为后人所忽视。“考”则是由纪传体的书志发展而来,体现了王世贞的创造性。但其表则显得过于细碎繁琐,而篇皆有序,前有总序,各部分有小序,亦太啰嗦。
总体而言,《弇山堂别集》在体例上由模仿而形成创造,它既非纪传体史书,也不同于一般的史料笔记,大概真可以称之为“别集体”吧。明清人一般将《别集》归于杂史类〔44〕。杂史一名最初见于《隋书·经籍志》,其言:“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觅,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45〕《四库全书总目》则将杂史定义为:“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46〕如果按此标准,把《别集》作杂史当然是合理的,但它是一种极力模仿《史记》的杂史。
王世贞对《别集》的评价甚是低调,他说:“是书行,异日有裨于国史者,十不能二;耆儒掌故取以考证,十不能三;宾幙酒次以资谈谑,参之十或可得四。其用如是而已。”〔47〕这显然同他作明代国史的愿望相差甚远,故只能名之曰“别集”,表现出他的某种遗憾。但陈文烛以为王世贞于明代国史似推而实任,对《别集》之评价他反王世贞之言而论之曰:“异日有裨于国史者最其大也,耆儒考证其次也,宾筵以资谈谑特其余耳。”〔48〕总体而言,王世贞之师法子长,是颇得其精髓的。可以说王世贞是善师司马迁者,变纪传体而为“别集体”。
注释:
〔1〕《史学巨擘》为《中华骄子丛书》中的一种, 其中收录了由张越编的《明史撰述的开创者王世贞》,北京:龙门书局1994年版,第104—108页。
〔2〕另有《袁王纲鉴合编》,现已公认并非王世贞所作。
〔3〕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八《内篇·模拟》。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283页。
〔4〕《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7381页。
〔5〕《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四《艺苑卮言一》。 《四库全书》第1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
〔6〕《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五《王弇州文集· 国史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7〕《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九○《书牍·徐孺东》, 第860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沈云龙选辑《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22种。
〔8〕《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二《书牍·徐生》,第8272页。
〔9〕《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四《汉书评林序》,第2322—2323页。
〔10〕《弇山堂别集》自序,第2—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16种。
〔11〕《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载:“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此乃别集之本意。
〔12〕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九,就指责其“盖不知诗文之当称别集也。”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4页。 徐朔方则以为古代文史不分,称别集乃重申此义也。《王世贞年谱》引论, 第484页。
〔13〕《弇山堂别集》陈文烛存,第7页。
〔14〕包遵彭亦似赞同此观点,见其《王世贞及其史学——为〈弇山堂别集〉影印而作》,见台北:文海出版社《弇山堂别集》。
〔15〕《四库全书》第409册《弇山堂别集》附提要,第2页。此处所附之提要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要详细很多。
〔16〕《弇州山人续稿》卷二○三《笞况吉夫》,第9121页。
〔17〕事实上述、考、表并非王世贞首创,郑晓《吾学编》中就有此种体例,其具体分:记(《大政记》、《逊国记》、《名臣记》、《逊国臣记》)、表(《同姓诸王表》、《异姓诸王表》、《直文渊阁诸臣表》、《两京典铨表》)、述(《地理述》、《三礼述》、《百官述》)和考(《四夷考》、《北虏考》),但除表外,《吾学编》之“考”与“述”和《弇山堂别集》中的并不相同,《吾学编》之“考”只有两篇,就相当于纪传体中的传;而“述”显然也就是志亦毋须多言;而《弇山堂别集》中之述、考则另有含义。王世贞称“述”、称“考”可能受到《吾学编》的影响,但并不拘泥于《吾学编》的范围,只不过借其名罢了。
〔18〕仓修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文献》1997年第2期。
〔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一《史部·杂史类》,第159页 。
〔20〕《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九《皇明奇事述序》,第2575—2576页。
〔21〕司马迁著,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2〕周中孚:《郑堂读书补逸》卷一○言:《盛事》为“弇州以明代官爵之制轻于前代,故公卿将相之位业亦少逊前代,因自洪武至万历,取其科甲功臣之盛者,汇为一编以纪之,凡三十九条,各标题目,而以类相从,亦唐人《卓异记》之类也。”。他以为不过是《卓异记》一类的东西罢了。
〔23〕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之《彰善瘅恶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页。
〔24〕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本《震川先生集》卷二《卓行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25〕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卷二七《作史不立表志》,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年版,第746页。
〔26〕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三《表历》,第70页。
〔27〕司马迁著,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一三,第340页。
〔28〕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36页。
〔29〕《弇山堂别集》卷三九《衍圣公爵系表》,第1735页。
〔30〕即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九引李绂《穆堂初稿》言,“同姓诸侯表,既不分世与年,徒列诸王国于前,而逐一纪其事于后,谓之传可也,何谓之表?高帝功臣表其谬亦然。永乐以后功臣,既称年表,仍用前法,功臣袭封薨除,各叙其年,不相联属,顾名思义,谓之年表可乎?”
〔31〕参见仓修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文献》1997年第2期。
〔32〕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编第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15页。
〔33〕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二《二体》,第34页。
〔34〕《弇山堂别集》卷六七《亲王禄赐考序》,第2865页。
〔35〕《弇山堂别集》卷六七《亲王禄赐考》,第2893,2899页。
〔36〕《弇山堂别集》卷九○,第3976页。
〔37〕《弇山堂别集》卷九○,第3984页。
〔38〕《弇山堂别集》卷九○,第3985页。
〔39〕《弇山堂别集》卷八五,第3691页。
〔40〕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二《载言》,第42—43页。
〔41〕《弇山堂别集》卷四四《赠公孤宫臣表》,第1945页。
〔42〕《史通通释》卷二《世家》,第52页。
〔43〕参见陈国球《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6页。
〔44〕《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杂史类,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称:“别史杂史颇难分析,今以官撰及原本正史重为整齐,关系一朝大政者入别史,私家记录中多碎事者入杂史。”因之他将《弇山堂别集》亦列入杂史类。见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45〕《隋书》卷三三《经籍志》。
〔46〕《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第145页,《四库全书》第2册。
〔47〕《弇山堂别集》序,第5—6页。
〔48〕《弇山堂别集》陈继儒序,第16页。
标签:史记论文; 弇山堂别集论文; 王世贞论文; 历史书籍论文; 读书论文; 司马迁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纪传体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