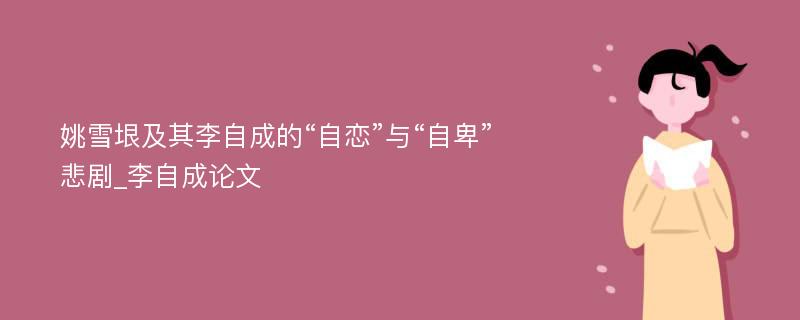
“自恋”与“自贱”的悲剧——论姚雪垠及其《李自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姚雪垠论文,李自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1)03-0133-06
一
《李自成》第一至第五卷终于全部出版了,作者姚雪垠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对姚雪垠其人其文进行“盖棺论定”,可谓正得其时。
我们还是先看一位评论家对《李自成》的评论。他首先肯定,小说“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写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生活的真正面貌,各个不同阶级、阶层代表人物的本质,从他们的生活到精神状态,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在《李自成》中,大的故事情节和小的艺术细节都很逼真,而实际出于虚构。情节和细节虽是虚构,但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是合情合理的,使读者能够信服”。作品所“探索的问题,不仅仅是艺术表现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即根本的问题是历史的具体条件,历史的典型环境,个人在其中所产生的思想、感情以及借以形成的性格”,[1]他甚至如此极力地推崇:“《李自成》是反映历史,但它是有计划、有目的创作的。它是封建社会后期一部百科全书。”[2]
为了强调姚雪垠的“开创性”贡献,这位评论家对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名著进行了比较。在他的眼里,“《三国演义》写了大起大落的故事,但没有写生活。《红楼梦》写了生活,但基本上局限于贾府圈子,朝廷大事和元妃的宫中生活不敢写,怕触文网。农村生活只写了乌进孝交租的事,没有正面写农村。刘姥姥同女婿所住的村庄,也就是巧姐避难的地方,没有具体描写。”中国的长篇小说名著不行,现代小说也不行,“有人说第二卷不如第一卷,茅盾同志对这种说法感到很惊奇。其实,也不奇怪,除因为第二卷某些方面尚需要在艺术上进行锤炼外,大概也因为新文学运动数十年来我国的长篇小说在故事进程上大多是单线发展。许多人看惯了这种单线结构,反而对《李自成》这样复杂的结构感到不习惯”,他甚至断言:“这种将历史场面铺得很开的写法,中国现代小说中没有”!没有办法,既然中国传统文学是这样地不争气,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技巧手法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又是如此地不行,我们只有再去向西方长篇小说寻找借鉴。但这位评论家又告诉我们,同样是描写普通下层民众起义的作品,西方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是沿着一个人写的,英雄与美女的情调太浓。奴隶决斗的场面写得很好,但斯巴达克斯离开军队,跑到情妇家里去住了很久,这一部分是败笔。艾芙姬妣这个妓女在小说中也显得比重太大,主要故事反而没有充分展开”。于是,只有“《李自成》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企图通过明末农民起义这条主线,写出一个历史时代的风貌,反映当时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不同地位和不同行业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百科全书’”[3]。
总之,中国传统长篇小说有着诸多缺陷,难以供人效法,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中,被人们视为主要成就所在的长篇小说,只有“单线发展”的一种结构模式,难以适应中国文学发展和多样化需要。他甚至认为:“五四以后,长篇历史小说几乎是空白!”[3]幸好,有姚雪垠的《李自成》来填补中国现代历史长篇小说的“空白”,才为中国几千年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模式!这位把《李自成》推崇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百科全书”的“评论家”是谁?如果不来个“脑筋急转弯”,大家恐怕很难回答出:这就是《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自己!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再重温一下有关长篇小说的基本知识。中国古典长篇的代表作《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虽然各有其描写对象的偏重,各体现着其壮美或柔美的美学特色,但都绝不是像姚雪垠所感觉到的那样单纯,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描写,都能够体现出大处见精神、细微处显真实等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功力,都能够从对人生的表现中体现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否则又何以被认为“名篇”?“红学”、“三国学”、“水浒学”等学科的建立和学术研究发展盛况,至今不衰,可以佐证!五四以来的长篇历史小说绝非如姚雪垠所说的是“空白”。30年代李劼人的“辛亥革命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作为“超长篇”的“大河小说”,就是标准的“将历史场面铺得很开的写法”的历史题材小说;于之大致同时的陕西作家李建候(即毛泽东曾提到过的著名开明士绅李鼎铭的侄子),30年代曾经以李自成题材写过《永昌演义》(“永昌”为李自成建“大顺国”的年号),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再说“结构”问题,茅盾的《子夜》虽然是以吴孙甫为中心人物,但其小说的“三条线、四个面”结构方式,是被学术界所公认的,而茅盾的大型长篇《蚀》三部曲,绝对就是姚雪垠当时尚未能“开辟”的多条矛盾线索并行发展的结构方式的体现。此外,巴金的《灭亡》、《新生》和“抗战三部曲”、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老舍的《四世同堂》等,也都绝不是“沿着一个人写的”结构。这些长篇小说早以“填补”了姚雪垠后来才“开辟”的结构方式“空白”,并且被人们所公认。姚雪垠自诩其《李自成》表现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代表人物的本质,从他们的生活到精神状态,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写出一个历史时代的风貌,反映当时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不同地位和不同行业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等特点,实际上正是他对以上作家技巧手法的模仿。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自诩为在文学、历史等诸多领域都是“专家”的姚老雪垠先生大脑中的基本知识一些“空白”!
二
姚雪垠宣称:“我有自己的一套关于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和长篇小说的美学思想”[4],并且运用这些“原则”和“美学思想”去指导自己的创作,在《李自成》中获得巨大成功。那么,我们就按照他的标准去检验他的创作究竟如何?
《李自成》的主题思想是对中国农民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用姚雪垠的话来说,就是:“写李自成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是全书的总主题”。主题的确立当然地决定着结构的安排,姚雪垠将小说的结构安排作了这样的比喻说明:“先确定一条中轴线,然后各种建筑群围绕中轴线星罗棋布,疏密得体,而每一个建筑群中又自成一个完整的布局”。他进一步说明:“我希望在小说中写出李自成领导农民革命战争的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写出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所以要集中力量写他的最后几年”[5]。在这里,我们对他的小说思想立意与结构安排表现之间的矛盾感到很难理解:既然是对中国“农民战争基本规律”的总结,那么,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的代表,李自成为什么起义,如何起义?就应该是小说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通过这些,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可惜,姚雪垠“不从李自成幼年写起,也不从他开始起义写起”,因为这样就“必然要花去很多笔墨写他的成长过程和前期革命活动。但是这和我希望在书中表现的主题思想关系不大。”[5]。姚雪垠在这里强调了“简练”,自以为突出了“重点”和“凸出”了主题,但实际上却游离了其“写出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的基本立意,偏离了主题。既然是希望通过农民阶级的代表李自成去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那么,李自成的“成长过程和前期革命活动”,就是一个“基本规律”的重要体现。对此,一位多次撰文颂扬《李自成》的学者也惋惜道:“没有从农民中塑造一个’官逼民反’的有力的典型,对《李自成》这样的书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疏忽和缺陷”,“特别是李自成起事,在他一生中是个飞跃”,“一二卷中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更浓的笔墨”[6]。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姚雪垠在小说构思上的一个严重失误,或者说,这体现着姚雪垠对“规律”的认识不清和思维的混乱。
更为严重的,还是其第五卷对小说结构“中轴线”的完全脱离,姚雪垠自己明确地表示:“第五卷就完全表现清兵入关及征服全中国的民族战争”。把《多尔衮率清兵南下》作为第五卷开始的单元,是因为“第五卷全部写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在清兵入关,打败和消灭李自成的战争中,矛盾的主要力量(历史运动的主人)是满清的摄政王多尔衮,而不是大顺国王李自成”[4]。如此一来,它与“写李自成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是全书的总主题”的关系又在哪里?过于自信和处于极度“自恋”状态的姚雪垠,在这里犯下了不该犯的严重错误。
这种错误,姚雪垠在小说第四卷中一犯再犯,他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历史进行研究,认识到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尽,明朝已亡,所以山海关大战的性质不再是李自成与明朝政府的战争,而是以满清贵族为核心并联合汉族和蒙古族封建势力所建立的清朝政权乘机南下,与汉族的各派武装进行的民族战争。”既然“山海关大战”是《李自成》第四卷中所描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既然是姚雪垠通过“对历史进行研究”努力而得出与众多历史学家不同的结论,他这里强调的“民族战争”性质,就不再是《李自成》这部小说本身的立意所在,更难以用作者自己所确立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这一主题来涵盖了。
或许,姚雪垠在此确实有另外想表达的想法?姚雪垠在这里给我们揭示着:“李自成的破北京,崇祯的亡国,吴三桂的反抗李自成和派人向清朝请兵,都是给多尔衮提供了向关内进兵的有利条件”。也许,这就是姚雪垠对历史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独特结论:“农民革命战争的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就是它必然地会引起外敌入侵的恶果,这岂不是历代反动专制暴君镇压农民起义革命的言论?更有甚者,他出于“对当时的统治思潮的叛逆行动”,竟然将汉奸洪承畴塑造成为一个大英雄,我们还是看他的原话:“我考虑到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从24岁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虽然前半生已经作了大官,但对中国历史并没有起重要作用,到降清后进入后半生,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在处理政治和军事问题上,表现得才华横溢,思路敏捷”[4],这里完全是一种汪精卫式的价值观,从一个进士而逐渐作到明朝的宰辅重臣,却对中国社会历史毫无贡献,只有叛变投敌之后倒可以大展才华。按照他给我们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中国知识分子下半生要想有所作为,就只有……当然我们不便将姚老雪垠先生设想为一种有意识的反动(虽然他老人家曾经多次对别人这样作过,甚至对老朋友臧克家也不例外),我们只好说这是他一种思想糊涂或者思维混乱的表现。
这种思维混乱使他在解说小说主题思想上又出现矛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突出一个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英雄主宰一切”[3]。也就是说,他创作的根本目的还不在表现历史规律和历史真实,“这跟宋朝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一样,他的画卷并没有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斗争,而我们则要为农民战争服务”[2]。到此我们才开始明白,他创作《李自成》的根本目的,还是“为政治斗争服务”。
姚雪垠一方面大谈历史,大谈史料考据并且对一些颇具造诣的历史学家挑刺指责(甚至包括对明清史专家吴晗),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历史知识修养或者说对其历史研究的正确与否,内心也有些惶然,在说了一番大话以后,他话锋转到文学,因为文学才具有个人性,好与歹很难有定论。“写小说不是写历史,要根据主题需要,对材料进行取舍”[3],“我的最终目的决不是像许多专业史学家一样要说明历史事件的本身,而是要回到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作家所努力追求的不是历史著作,而是艺术成果,即历史小说”[4],也就是说,姚雪垠创作的根本意图还是不在“写出李自成领导农民革命战争的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写出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而在于他试图“在长篇小说的美学追求或创作方法上,开辟我自己开辟的历史小说新道路”。这句话的表述使我们很难弄明白,既然是他“自己开辟”的“新道路”,为何还要由他自己再来重新“开辟”?姚老雪垠先生被“自恋”激情搅昏了理智,居然说出了这样的糊涂昏话!
姚雪垠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写历史小说的根本原则”,那么,姚雪垠的创作美学“根本原则”是如何产生的?天才看来确实与众人不同,姚雪垠这样告诉我们:“不是从别人借来的,也不是从五四新文学遗产中学来的,而是从我当时在文化修养方面所具备的综合条件自然形成的,尤其重要的条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从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家学习到的严肃认真的治史态度和方法,还有近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4],滑稽的是,他一方面强调这个“根本原则”绝对未受到任何外来的和别人的影响,纯粹是他自己头颅中“自然”而然地生成的;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其“根本原则”之所以产生的“尤其重要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即“思想方法”、“治史态度和方法”恰好正是“别人”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对古今中外名著指责甚多,但其《李自成》对前人和别人的技巧手法的模仿、乃至照搬之处亦不少。例如小说写李自成射箭,火星四溅后很大一块岩石飞落两尺外,箭也从岩石上跳回来的细节,第一卷中写敌人追赶李过,李过反而下马玩耍,迷惑对方等情节,都化自于《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李广故事;高夫人擂鼓助战的情节,是照搬《说岳全传》对梁红玉形象的描写;李自成带50骑兵先行,被官军发现,300骑兵追赶,到一个茅店铺被追赶上,李自成只留下几个人,浇灭灶火泼冷马粪,再把饲料大豆倒在路口,追兵马吃豆,领队军官查验灶台和马粪皆冷,疑对方已走远而罢。这实际化自于《三国演义·空城计》。虽然,姚雪垠曾经“常常批评这(《空城计》)故事虚构得不符合生活逻辑,经不起推敲”,“诸葛亮不至于如此行险,司马懿也不容易上当”,也表示“这种不合生活逻辑的情节,我决不学习。”[3]但他还是从中“搬”来一些情节和写作技巧。
此外,“近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恰好正是“五四新文学遗产中”的核心内容。我们知道,中国近代文学真正的开始,是由梁启超倡导的文学启蒙思想和王国维用西方文艺美学思想及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来导源的。真实的描写社会人生状貌,表现普通人生的情感,揭示社会的病根,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这正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而真实的描写,对细节真实的重视,采用性格塑造的技巧手法,和对人物心理描写的重视等,都是中国“近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者说是“五四新文学遗产”的基本特点。为了证明自己的“开创”价值,姚雪垠不仅仅是多次公然地贬低郭沫若,似乎也要无视鲁迅的存在和影响,40年代在重庆时还对人表达过对巴金的不以为然,连对他有过极大帮助的茅盾,也没有逃脱姚雪垠践踏,他在文章中指责茅盾曾经在《子夜》中的艺术努力未能成功……对古今中外著名作家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学遗产”的否定,把一部文学史说成是“空白”,以利于他自己在“自己开辟”的“新道路”上进行再“开辟”,从而把他自己放置于从“近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直接开始的“开宗立派”位置上,姚雪垠的“自恋”可谓发展到了极端。
三
姚雪垠企图将自己塑造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形象,他甚至说:“我当时是第一个摆脱多年来极左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4]。“我不仅反抗了一种流行多年的、占统治地位的、极左的创作思潮的压力,即所谓’二突出’的压力,而且还抵抗了恶意攻击和好心劝告”,“我在小说中表现的种种思想,和‘四人帮’鼓吹的那一套是针锋相对的”。而我们在其小说中看到的却是:《李自成》纯粹是“极左教条主义的思想”的派生物,是“三突出”创作模式的典型体现。按照姚雪垠60到90年代以来的行为言论表现,“第一个摆脱”说,真可以令人笑掉大牙!
姚雪垠主观上是想“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即“用浓笔刻划中心人物李自成,将他放在最激烈的矛盾旋涡中表现他的杰出的英雄性格和应变才能”[7],但因艺术功力不够而事与愿违,即使是肯定性文章,也认为:“有些同志反映,《李自成》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宫廷生活而不是义军军营生活部分;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不是农民义军内部矛盾部分;是知识分子部分而不是农民部分;而在农民部分中,写得精彩的是张献忠、罗汝才义军部分而不是李自成义军部分”。“作者着力刻画和歌颂的主人公李自成,在艺术上却难以令人满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较为明显:着墨虽多,却缺乏更多的艺术创新”,“为了理想忘了历史,为了或然性忽视必然性,把历史人物理想化现代化。李自成形象有时给人以不真、不象、不亲之感,关键就在此”[8]。回避历史原型中李自成与张献忠、罗汝才、贺一龙等“十三家”农民起义队伍的互相残杀、并且无视李自成杀害蔺养成、贺一龙、罗汝才等义军领袖和吞并其部队的事实,这就很难真正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应该注意的“经验教训”。《石匮书后集》卷63记载: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受重伤,“仅随数百人,奔河雒,欲赴李自成。自成有众50万,方自雄长,欲屈献忠,献忠不为下。自成怒,谋杀之。献忠乃昼夜东驰,与老回回诸贼合,入霍山,据险扼守”。另《明史》、《罪唯录》等都有类似记载。姚雪垠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将路线斗争觉悟、一分为二辩证法思想、阶级分析的方法、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以及群众路线等等全部堆砌在李自成身上,这恰好正是姚雪垠所要“反抗”的“三突出”创作模式的典型体现。更有甚者,在第一卷修改本(1978年)中,姚雪垠居然增加了李自成对张献忠宣讲“只要我的路子走得正”就是保障胜利的根本,“人马要多少会有多少”,这完全是“文革”关于“路线斗争”理论(文革中盛行的毛泽东的话是:“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的翻版!站在“正确路线”上、追随李自成的人,不仅性格就是脸谱都带着“正确路线”的特点,而站在“错误路线”上的人,例如张献忠身边的徐以显,就被描绘成“生得鹰鼻子鹞眼”,使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善良家伙”。
如果说在《李自成》的创作初始,姚雪垠还能够尊重历史而比较正确地描写高夫人,到了第二卷以及第一卷修改本(1978年出版),他将自己原定重点塑造的第二号人物(刘宗敏)替换为高夫人,虚构了潼关突围有高夫人统率军队的情节,通过正面、侧面去反复突出高夫人“处理全军各种大事”的才干和“有勇有智”,甚至借用刘宗敏之口要求义军“只要你们遇到敌人时不替咱李闯王和高夫人丢脸就行”。可以说,在姚雪垠笔下的高夫人地位,是随着中国高层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和“文革”的历程而被逐渐提高的。他说过:“高夫人在此之前的史料几乎是空白,我仅仅根据这一点点资料,塑造出高夫人这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小说人物”[3]。例如第二卷中高夫人对部下讲话“只有咱老八队为革命……”的口气,我们不难联想到“文革”中那个“旗手”的样子。姚雪垠这样描绘着:“高夫人虽然在全军中地位崇高,极有威望,对一切重大事情都很清楚,但是多年习惯,不参加正式的军事会议”,而在这次关系全军命运的会议上,高夫人开始起直接作用了。更有甚者,姚雪垠极力突出李自成死后高夫人在全军中的统帅作用,使之成为革命领袖兼丈夫死后继承其遗愿、继续革命的典型。列位看官,在这些描写和人物有关逻辑中,不是可以看到那个特殊“十年”的中国政治内容吗?这就是姚雪垠所自诩的“虚构的情节都能够令人信服,放在当时的历史生活中经得起推敲。这是‘历史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威力,也反映了我这个当代中国小说家在写历史人物时掌握的应有修养”。这种“修养”实际上就是迎合、投靠“四人帮”及其“极左的创作思潮”,正如其自谓“我的原意是:我们今天在历史小说中展开的风俗描写,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2]。
其他如第二卷中关于“刘宗敏审判吕维祺”一段情节,让一个铁匠出身、性格剽悍粗鲁、又不通文墨的大老粗“总哨”、“一个喷嚏吓死一只老虎”的赳赳武夫刘宗敏,对明代著名理学鸿儒吕维祺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批判孔孟之道等,可以作为明清时期“工、农、兵愤怒批判孔孟”的一个典型例证?牛金星是明朝的举人,“但他只是背叛明朝廷,并没有背叛本阶级”“是用地主阶级的思想改造农民军”(同前)的议论,把周皇后称呼为“总地主婆”,如此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文革”中评法批儒、评《水浒》等阴谋政治的留存。他甚至设置了几处李自成军队举行“诉苦会”的情节,将中共军队在20世纪40年代末才发明的革命教育方式,“提前”到明清时期!这或许就是姚雪垠所强调的:“不了解今天,不参加和不关心今天的政治斗争,就不能回头看清历史,就不能立足现实,就不能做到古为今用”[3]。姚老雪垠先生为迎合极左政治思潮而如此地任意篡改历史,又有何“历史科学”性可言?
四
在决定写这篇文章时,一位90岁高龄老教授、与姚雪垠在40年代有过往来的老作家曾经告诫我: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充分根据去说理。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尽量引用姚雪垠自己的原话,征引明确的事实。决不像姚雪垠那样随便给人上纲上线,尤其是随便用政治问题去否定论敌。
姚雪垠说:“我有自己的一套关于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和长篇小说的美学思想,包括的方面很多,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关系”[4],即“历史现实主义原则”。这就是说,在小说艺术性缺乏的地方他可以给我们说“历史科学”,而在其使用历史材料不“科学”的地方,他又可以来说“现实”,可谓“输赢都有糖吃”,也算聪明之至!
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他告诉我们:“《李自成》是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字数多,篇幅长”“可能要写到三百万至三百五十万字之间”“我这次写《李自成》是打的有准备仗,从第一卷到第五卷、尾声,重大的故事情节,主要人物的发展,我都心中有数”。大话说过头了,没有料到后来的变化,他又告诉我们:“近两三年来,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小说》上发表了一个较大的小说单元,题目是《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单元曾经修改过两次,几年前发表的若干万字作废了。我原计划将《李自成进北京》作为第五卷第一单元,发表之后,我改变了计划,将它作为第四卷最后一个单元,而第五卷就完全表现清兵入关及征服全中国的民族战争”。李自成方面、张献忠方面、崇祯方面,各是一个力量、一种势力“第一卷还没有多少矛盾,第三卷开始就多了”,“还有清朝在关外,在第三卷正式上场,这又是一种力量”。[4]这和他原来的创作立意已经大相径庭。
本来,文学创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艺术形象思维过程,作家在创作中根据人物性格的发展和生活自身的逻辑,同时也基于自己对生活感悟的进一步深化,从而不断地调整原先的构思,本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姚雪垠为了夸耀自己的“先觉”和才华,不愿、或不敢说实话,硬是不顾作品实际而极为勉强地把后来的创作变化纳入原有构思,这就突出了其“艺术思想体系”与小说实际表现的矛盾。还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多年极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文革”话语的绝对霸权制约,使姚雪垠在《李自成》的创作中表现了许多非文学因素和反历史的内容,这个责任首先不应该由姚雪垠来承担,但他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他可以忏悔(正如那些令人景仰的作家),也可以闭口不谈(大家也能够理解),如果一定要将污秽脓血说成是艳若桃花,这就难免使人厌憎。可以说,在姚雪垠极度“自恋”的背后,实际表现的是极度“自贱”。
姚雪垠颇为自豪的是《李自成》在篇幅上的“长”。而能够做到“长”的条件在于“我们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不需要等着稿费、等着米下锅,我可以精雕细刻,慢慢地一边构思一边写下去”。利用中国现行的“专职作家”体制,浪费国家的钱财和纸张,追求“超长篇”的宏篇巨制,以实现自己“成名”的私欲,其结果是给社会留下一大堆无人、也无时间去欣赏的废纸。即使有一两个闲得无聊的人耐着性子读完该书,最后却发现其中所表现的不过是作者极力追随“四人帮”极左思潮,着力体现“三突出”的“风派”内容。弥漫全书的只有虚假,既然“故事情节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虚构的”,其“历史科学”又何以立足?这种“矛盾文学”居然可以获奖,不是正反映着当时中国文学荒芜凋残的严重性?其实,姚雪垠的创作绝非偶然现象,它是新中国30年文学的那种“大事件”(题材决定论)、“英雄颂歌”、尤其是“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史诗性”(企图给读者指出什么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特点的典型体现。只不过姚雪垠在其创作历程中,更具有“为农民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乃至于为阴谋政治服务等“追风”的特点而已。就其实质而言,这是缺乏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和不敢对生活进行独特表现的“自贱”!这类文学的伪饰、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已经被当今人们所认识,这就是人们开始反思某些中国长篇获奖小说究竟有无实际价值的原因。“茅盾文学奖”的某些作品实际含金量如何,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了。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英雄史诗”,因为作者大多是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亲历者,出于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热情,作者们在“造神”运动中确实融汇着自己的真情实感,因而还具有一定的感染力(正如姚雪垠在1947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所表现的)[9],那么,姚雪垠则出于对“农民战争是历史动力”观念的图解,出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宣传,运用一些真真假假的历史材料去图解历史,又由于其受某些政治理念乃至于某个政治家思想的操纵,作品人物成为作者手中的玩偶,因而在历史层面既无“科学性”可言,在美学层面又因为“三突出”的公式化概念化而无艺术感染力。关于历史题材创作,我们还是认同鲁迅的说法,要么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式“很难组织”的“教授小说”,要么就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10],前者可以真正体现认识价值的“历史科学”性,后者则可以在艺术上尽情铺展以体现文学性。“立足现实”,将历史当作任人随意打扮的婢女来“古为今用”,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创作模式,应该得到彻底地清算!这就是我们通过对姚雪垠创作思想及其对《李自成》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姚雪垠已去,《李自成》却留存世间,虽然该书在各类图书馆尘封甚久,倍受冷落,但它毕竟曾经获得过中国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一段时间来曾经被误认为是“史诗性”作品,因此,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反思其“经验教训”以利于当今中国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收稿日期:2001-01-20
标签:李自成论文; 姚雪垠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描写方法论文; 农民论文; 高夫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