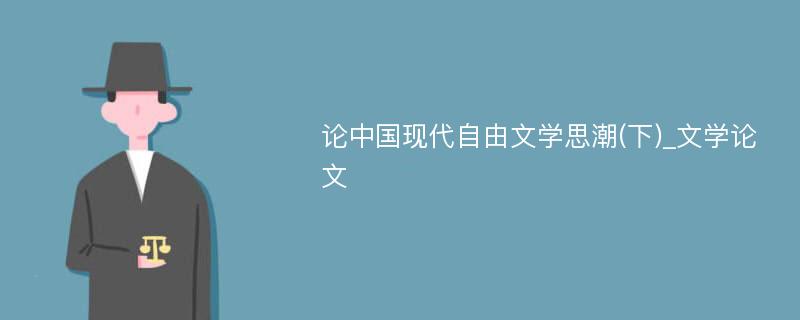
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定文学流派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必定会在它对主题的选择和处理中显示出来。以表现人性、描写人生为标榜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同时以重视道德的主题为标榜。道德和人性、人生本来有着内在的联系。深深影响过林语堂、朱光潜等人的美学家克罗齐曾说:“不论是什么诗,其基础都是人性,而正因为人性是在道德上实现的,任何诗的基础也就都是道德上实现的,任何诗的基础也就都是道德意识。”〔1〕中国现代,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时就说:“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2〕。他还曾这样说自己的文章:
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3〕
后来,朱光潜谈及梁实秋《文学的美》一文时指出,此文的论点,“可归纳到一个基本观念里去 ——‘文学的道德性’。其它艺术可以只是美,而在文学中美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道德性”〔4〕。但朱光潜本人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相同,他曾说:“审美经验是独立于道德的考虑的。”〔5〕
毛泽东在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6〕在一般的意义上,新道德,新文学,都并非不能通向自由主义。中国现代,作为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改造社会手段的革命路线与自由主义路线,它们的分歧,首先是从政治态度开始的。对道德的强调,则在这种分歧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当年,周作人曾驳斥封建卫道者对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的攻击,说:“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7〕。他这里所揭露的道德,是指旧道德。他认为郁达夫的小说不合旧道德,却完全合乎新道德。周作人此时从道德的角度谈问题,跟政治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强调道德,往往包含着淡化政治甚至反对政治的目的。林语堂说:“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应该说这话并不错,但它其它另有涵义。正是与这种涵义相联系,林语堂有针对性地说:“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一种多么难得的美德。”〔8〕而在创作中这时继续从人性为基础描写道德的主题或涉及道德问题,又表现出另一种复杂性。比如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小说,政治上起码可以“商榷”,道德上却无懈可击。因此,对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
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既然以人性论为基础,那它必定要坚持人的精神活动具有绝对个人的性质,文艺创作也具有绝对个人的性质。这是它的又一个基本点。林语堂说:“艺术也是精神的,所以个人的表现是一切创造形式的根本要素。这种个人的表现就是艺术家的个性,是艺术作品中唯一有意义的东西。”〔9〕周作人在《新青年》上有一篇《个性的文学》,虽不像《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那样出名,却告诉人们,既然新文化运动发见了人,作家同时也就发见了自己。对于欧洲自由主义运动来说,精神活动绝对个人的性质,文艺创作绝对个人的性质,既是事物的本来面貌,更是一种信仰,一种他们要为之争取的权利。霍布豪斯说,关于文艺,自由主义运动“为自我表现、为真实、为艺术家的灵魂”进行斗争。〔10〕而在中国现代,周作人和林语堂等人提出这个问题,则还结合着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本来不能没有这样的批判。在对传统的批判方面,当时有文学究竟应该“载道”还是“言志”的讨论。周作人说:
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指俞平伯——引者)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11〕
林语堂则认为,中国“经典的传统思想”,使得“‘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12〕。所以,他发出慨叹:“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传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13〕如果仅仅从理论上来谈“载道”和“言志”的关系,应该说后来朱光潜的认识,比较起来要深刻一些。朱光潜说:“如果释道为狭义的道德教训,载道就显然小看了文学。文学没有义务要变成劝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头讲章。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决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因此他认为,需要的是“文艺的‘道’与作者的‘志’融为一体”〔15〕。照朱光潜等人看来,这种融合是完全可能的。本来,他们强调作者的“志”,即强调文学创作的绝对个人性质,跟要求文学表现人性、描写人生,其间并不存在矛盾。后者是作家人格在创作上的要求,并使作家人格得到表现。
但由于中国现代的具体历史条件,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对现实的批判,跟它对传统的批判却并不全是一回事;尤其到了三十年代,两种批判甚至可以说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因为,现实不能为他们坚持文学创作具有绝对个人性质的观念的生长,提供合适的土壤。社会改造的迫切性以及政治在社会改造中的地位,各种政治势力通过其文艺政策向文艺提出的要求,都使得文艺空前政治化。特别是,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所造成的新的文学观念,更使这种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于是周作人写了下面的话:
……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哪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总之有两位,即是禅宗与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两个名称。文学无用,而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15〕
“新月派”则为了扶正他们所谓“倾倒了的”“价值的标准”,提出要维护“人生的尊严与健康”〔16〕。举着“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旗帜的胡秋原〔17〕,也要求“勿侵略文艺”〔18〕。这样,革命文艺运动,就成了他们批判的主要对象;而他们对现实的批判,也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的一种比较。
三
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以及整个文化思想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斗争的历史。这曾经被看作莫大的优点,看作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和文化运动得以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但现在又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以为它乃是人为的、多余的、错误的。而笔者现在只想强调一个本来大家都熟悉的事实,就是在这些斗争中,有许多次,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或其派别乃是其中的一方。从最初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二十年代同“现代评论派”,三十年代同“新月派”、“论语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与抗战无关”论,四十年代同“文艺自由”论等展开的论战,莫不是如此。下面两段话,并不能说明何以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现代具有较为长久的生命力,倒是透露了钟情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们何以特别要坚持自由主义。萧乾这段话写于1948年,即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胜负实际已成定局的日子:
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19〕
朱光潜这段话,同样写于1948年:
艺术底活动主要地是自由底活动。大哲学家如康德,大诗人如席洛,谈到艺术时,都特别着重它的自由性。这自由性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尊严。在服从自然限制而汲汲于饮食男女的营求时,人是自然的奴隶;在超脱自然限制而自生自发地创造艺术的意象境界时,人是自然的主宰,换句话说,他就是上帝。〔20〕
但说到生命力,那恐怕还得承认,在当时,在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两股潮流中,更强大的是前者。这是在既不受过去单纯批判自由主义的立场的限制,又并不试图重新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去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今天应该像这样来做判断,不是要追求所谓“超脱”和“公正”,而是为了从新的历史高度认识问题,为了结论的科学性。那么,当时革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又从何而来呢?这在根本上,当然是因为相比较而存在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前者真正深入了历史前进的潮流,认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未来。但倘要具体一点说,则问题还有其复杂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它自己的思想基础。而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运动在解释这一思想基础时,提出了一些不科学或不够科学的观点,以致使人感到,在有关文学的若干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上,革命文学有时甚至在自由主义文学面前“输理”。但是,让我们拿革命文学的杰出代表的文学观念来跟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念作一番比较,这样我们的糊涂看法就可以得到澄清。在革命文学的杰出代表中,笔者特别提出鲁迅。因为,上面所说革命文学运动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多次论战,发生在鲁迅生前的,他都发表了极为深刻的意见。而且瞿秋白曾经说过,“反自由主义”,乃是鲁迅带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宝贵的革命传统”之一。〔21〕同时,在革命文学运动中,鲁迅的文学观念,是最独特又真正具有代表性的。
鲁迅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文学观念第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鲁迅的观念中,文学这种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具有非常“现实”的品格;而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的观念中,它的基本品格,则是“自由”。鲁迅有一篇杂文写道:
林语堂先生以为“现代中国人尊其所不当尊,弃其所不当弃,……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黄帝子孙内行”。
但“咱们黄帝子孙”好像有两种:一种是“天生蛮性”的;一种是天生没有蛮性,或者已经消灭。
而“物质文明”也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吃肥甘,穿轻暖,住洋房的;一种却是吃树皮,穿破布,住草棚,——吃其所不当吃,穿其所不当穿,而且住其所不当住。
“咱们黄帝子孙”正如“蛮性”的难以都有一样,“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也并不全“内行”。〔22〕
在鲁迅看来,“黄帝子孙”分为两种,乃是文学必须面对的中国的现实中最根本的东西。并非人人都能像林语堂那样做“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的“内行”,更非人人都能像,林语堂那样做“最快乐的人”即“中等阶级的人”〔23〕。林语堂说:“我认为艺术之成为消遣或人类精神的单纯的游戏,是比较重要的。”〔24〕而鲁迅则认为,现在正是“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25〕,所以,“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26〕。他们要求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这种“现实”的品格跟精神活动应有的特征并不对立。相反,它有可能使精神活动的特征更加充分和突出,使文学变得气象万千。正如鲁迅所说:“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27〕。而鼓吹赋予精神活动一——即使像文学这样非常特殊的精神活动——“非现实”的品格,包括离开现实的“自由”的品格,未必就能使文学真正获得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相反,这时它倒可能失去基础,结果只剩下萎靡——途。要言之,如果根本否认文学属于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它在人们的观念里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实际上也就是它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品格的问题,不能不予以重视。尤其因为这个问题跟许多有关文学的重要问题相关。比如文学批评的问题。鲁迅对文学一向有明确的要求。他曾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8〕后来他评论叶紫的小说时说,这些作品,“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这又反映了他对革命文学的一种要求。他还谈到当时的杂文作者:“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29〕这“有益”固然需要解释,却也反映了鲁迅要求文学的一个基本点。所有这些,都是具体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则不同,梁实秋说:
文学批评不在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标准,而在于超出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建立一个普遍的文学标准,然后说明某一时代某一国土的文学品味对于这个标准是符合抑是叛异。
梁实秋同时“建立”起了这个“普遍的文学标准”。他说:“‘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唯一之标准。”而“‘人性’之所以是固定的普遍的,正以其有理性的纪律为基础”〔30〕。问题于是从具体变成了抽象,也从“现实”变成了“非现实”。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从胡适开始,就讲“容忍——容忍反对党”〔31〕;朱光潜也一再表示:“文艺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走。”〔32〕但是,在梁实秋这样的“文学标准”下,他们并不容忍鲁迅对文学的要求,并不容忍革命文学,这在三十年代的论战中表现得很清楚。而且,这个标准还说明,他们所谓的“自由”也是要受限制的,受“理性的纪律”的限制。梁实秋又进一步说:
文学并没有进步的趋势。一切的伟大的文学都是倾向一个公同的至善至美的中心,距中心较远的便是第二第三流的文学,最下乘的是和中心背道而驰的。文学批评的本身也是以至善至美的中心击中心,故其任务不在叙述文学批评全部的进步的历程,而在叙说各时代各国土的文学品味之距离中心的程度。〔33〕
文学究竟有没有进步的趋势?文学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应当怎样来描述?这些都是大问题。而对它们的不同回答,也反映着人们观念里文学作为人特殊的精神活动的品格的区别。鲁迅讲到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变化时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34〕。这就是历史,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历史。历史总是“现实”的,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历史也是“现实”的。鲁迅对它作了准确的描述,而它也是新文学发展中一种“进步的趋势”。这当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的。文学作品,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也有非意识形态的性质;或者说有意识形态的一面,也有非意识形态的一面。但文学思潮必定是意识形态的,在中国现代尤其是如此。现在要问:假使按梁实秋所说,把“各时代各国土的文学品味之距离中心的程度”当作文学历史的对象或内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历史又将被描述成什么样子呢?这样的描述的确是“自由”的,然而又是“非现实”的。
鲁迅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文学观念又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他们的观念里,文艺和政治有着不同的关系。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在其开始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潮,曾经提出政治自由在东方有“特殊重要性”〔35〕,此时它显然并不要求文学脱离政治。而笔者前面已经说到时,它后来反对文艺同政治的联系,固然仍有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的一面,要害却在于它认为革命文学运动要求文学成为阶级的事业,妨碍了“心的自由活动”〔36〕。周作人说:‘‘以思想杀人,这是我觉得最可恐怖的。”〔37〕林语堂说:“世间的强盗,真没有一个比劫夺我们的思想自由的人更大的了。”〔38〕这些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以文学必须是不受干预的文学、“自由”的文学这一点为核心,构筑起了他们的文学观念。陈源说:
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你们要民众舍弃了消忧忘愁的旧剧,来随了你们去“牺牲’,上法场,能不能有成功的希望?你们走的是不是死路?你们怎样会得到民众的赞助?〔39〕
梁实秋说:
过去的各种文学主义,乃是文艺范围以内的事,现在我们了解的文艺政策,乃是站在文艺范围以外而谋如何利用管文艺的一种企图。〔40〕
这段话里所说“站在文艺范围以外”的,无疑主要指政治;所谓“文艺政策”,也只能是政治权威制订的政策。
不能把鲁迅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简单化,不能认为只在把它同自由主义的观点简单对立起来就可以了事。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的观点非常独特,它表面的矛盾下面其实隐藏着极为深刻的东西,正是这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迅下面几段话要真正理解并不容易,他说: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41〕
如果说在这段话里,鲁迅讲的是文艺同革命的一致和跟处在相反方向的政治的冲突,那么,他在讲到“革命成功以后”的情形时又说: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42〕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仍旧认为:“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因此,革命文学,不仅同反革命的政治,而且同已经成功的革命政治,都是不一致的。除非“恭维革命颂扬革命”,而这“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它“已不是革命文学”〔43〕。仔细想一想,鲁迅产生这种观点并不奇怪,因为它跟鲁迅启蒙主义的“为人生”的观点有着内在的联系,内在的一致。启蒙主义的“为人生”,促使作家关注人生否定的方面;而杰出的和伟大的作家,必定还要更进一步,关注造成人生否定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的否定方面。也就是说,它观察和认识生活的角度,跟政治不尽相同;它们追求的历史内容,跟政治所要求的歌颂为主、写光明为主等也往往相悖。但鲁迅和自由主义仍有天渊之别。他的启蒙主义的“为人生”的观点,跟他认为文学乃是“改革社会的器械”〔44〕的观点,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现代,当政治越来越成为改革社会主要的、真正有力的器械的时候,始终不懈地探索着社会改革的道路的鲁迅,不可能提出或赞同文艺离开政治的自由主义主张。但他又不能不强烈地感觉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注视着当时革命文学运动在这方面包含着许多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同时注视着苏联这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在接触了苏联有关这方面的论争的材料之后,他认为,“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即党对文艺的指导应当“严”还是“宽”的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45〕。然而他仍旧坚持:“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46〕。简单说来,在鲁迅的观念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非常“现实”,又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因而解决起来须得十分慎重的关系。至于说解决的方向,当然决不会是自由主义的方面,但也不会就按政治的权威要求的方向。
鲁迅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文学观念再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他们的观念里,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也不相同。笔者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周作人、朱光潜等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重要观点,朱光潜下面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他的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应该是“不即不离”的观点的一种发挥:
我认为文学艺术是一种审美制造活动,它的创造者应当以一种超越一切优喜的纯粹审美的态度来观照社会人生,而不应直接卷入社会人生中的纷繁矛盾冲突之中。〔47〕
人生本来是现实的。无论世上是否真存在“超越一切优喜的纯粹审美的态度,总不能说“审美创造活动”的意义,是在用非现实的人生来代替现实的人生。而朱光潜还进一步认为,“美术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他说:
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现实界不可以造空中楼阁,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美尽善,理想界是有尽美尽善的。〔48〕
其实这里问题的根本,还在他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林语堂说过:“我想文化之极蜂没有什么,就是使人生达到水连天碧一切调和境地而已。”〔49〕本来在中国现代,几乎每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脑子里都有这个“人生”的问题。这是中国的现实,把它摆到他们面前的。但它到了这些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那里,变得离现实多么遥远!而下面我们就要看到,鲁迅的观点,跟他们的观点对比有多么鲜明!今天的研究者们对鲁迅的文艺思想有不少新的发现,然而,有一点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就是鲁迅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是他把对人生的描述,跟对人的灵魂的显示结合起来。鲁迅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曾经讲到陀思妥斯夫斯基是怎样在作品中“显示出灵魂的深”。他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50〕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正是鲁迅为自己的创作设定的目标;这方面他达到的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人可来比拟。而在讲到《阿Q正传》时,他明确地说他要通过这篇小说“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但是: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51〕
鲁迅的全部创作——不仅仅小说,也包括杂文、散文诗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这个特点。它决非只是“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是以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兴亡为出发点的。它也决不是和人生“不即不离”所谓“超脱现实”的东西。事实是,在鲁迅所描写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中,铭刻着历史,也铭刻着现实一——政治上以及思想文化上专制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换句话说,鲁迅通过对这样的魂灵的描写,即对中国的人生的描写,既深入了历史,也深入了现实。鲁迅所理想的人生,跟什么“水连天碧一切调和”也完全是两回事,而是“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能够“自己觉醒,都来开口”。所有这些,使得鲁迅观念里“为人生”的文学,成为一种既有鲜明的启蒙主义的特点,又必定要通向对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文学。而就像胡风所说的,正是在中国现代对社会实行革命改造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旧日的人生底衰亡及其在衰亡过程上的挣扎和苦痛。新的人生底生长及其在生长过程上的欢乐和艰辛,从这里,伟大的民族找到了永生的道路,也从这里,伟大的文艺找到了创造的源泉”〔52〕
注释:
〔1〕贝·克罗齐《美学的核心》。
〔2〕周作人《人的文学》。
〔3〕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4〕朱光潜《与梁实秋先生论“文学的美”》。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7〕周作人《<沉沦>》。
〔8〕〔9〕〔23〕〔24〕〔38〕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10〕霍布豪斯《自由主义》。
〔11〕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
〔12〕〔36〕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13〕林语堂《论幽默》。
〔14〕朱光潜《文学与人生》。
〔15〕周作人《<草木虫鱼>小引》。
〔16〕徐志摩《新月的态度》。
〔17〕参见古继学堂《胡秋原与中国现代文学》,《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18〕胡秋原《勿侵略文艺》。
〔19〕《大公报》社《自由主义的信念》(萧乾)。
〔20〕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
〔21〕瞿秋白《〈鲁讯杂感选集〉序言》。
〔22〕《集外集拾遗补编·两种“黄帝子孙”》。
〔25〕《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26〕《〈二心集〉序言》。
〔27〕《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
〔28〕《坟·论睁了眼看》。
〔29〕《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30〕〔33〕梁实秋《文学批评辩》。
〔31〕〔35〕胡适《自由主义》。
〔32〕朱光潜《谈趣味》。
〔34〕《且介亭发杂文·〈草鞋脚〉小引》。
〔37〕周作人《〈谈虎集〉后记》。
〔39〕陈源《民众的戏剧》。
〔40〕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
〔41〕〔42〕〔43〕《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44〕《县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45〕《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
〔46〕《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47〕《朱光潜谈鲁讯对他的批评》,《鲁讯研究月刊》1993年第8期。
〔48〕朱光潜《无言之美》。
〔49〕林语堂《今文八弊》。
〔50〕《集外集·〈穷人〉小引》。
〔51〕《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52〕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关键里面》。
标签:文学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林语堂论文; 朱光潜论文; 梁实秋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周作人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鲁迅论文; 文艺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