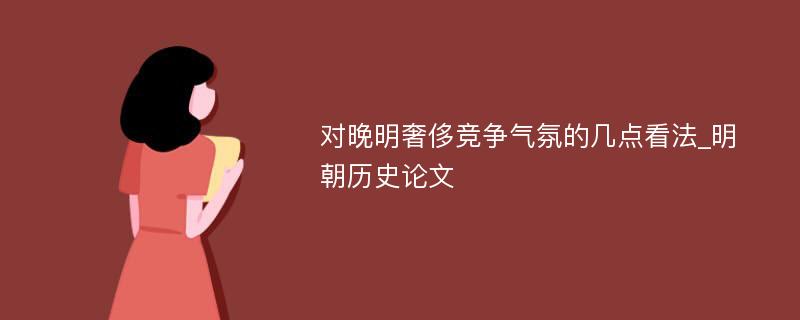
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气论文,看法论文,晚明竞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5-0139-11
晚明竞奢之风,目前已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在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从来没有讨论过: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这种竞奢风气,还有就是支撑这种竞奢风气的财富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明朝人从什么时候腰包里面有了钱,可以追求奢靡而花钱了?这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也就是晚明商品化生产发展的过程。因此,我感到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一是明朝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奢靡追求;二是为什么当全社会都发现这一社会问题而给予批评时,却丝毫不能改变其状况。本文拟就此略述陋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一条大家熟悉的材料是关于常熟谈晓的记述。
嘉靖年间,苏州的常熟有文社十杰,为首的一位名叫邵圭洁。圭洁字伯如,一字茂斋,号北虞。他在所撰《北虞集》中,有一篇为同乡一个名叫谭晓的农人所作的传文,不过他文章中传主名字却叫做谈参:
谈参者,吴人也,家故起农。参生有心算,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参薄其值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周为高塍,可备防泄,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之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鸟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复三倍。
参且纤啬惮费,平生无纨绮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饭,熟一卵,窍可容箸,籍而啖之,饭毕,封其窍,留之再饭,三饭乃尽。以故参之赀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然弗子,仅有女,女所适者某,睨共藏久之。一日参病亟,某请曰:“翁脱不讳,即谁嗣者?”参曰:“已有属矣,若将利之耶?”叱去之。参死,某乃谋戕其所属者,蔓而戕者几人,构为狱。官没参之产,某尽归其藏云。
论曰:昔马迁论货殖,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论巧拙哉!莫巧于参矣。参自奉不轻尽一卵,有余胡为哉?矧参无遗算矣,于身计懵如也,巧耶拙耶?千匦百匦,归一匦矣。谓千匦百匦者巧耶?余故论之,使效参者评焉。
时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引录了此文,并于其后写道:
此邵北虞圭洁所撰也。谈参实谭晓,常熟湖南人(行三,参者三也)。北虞系同邑,不欲显论之耳(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传》)。
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其中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谭晓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商品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了。这种商品化冲击到了中国最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由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那些认为土地低湿而不适耕作的人,便可以将土地出卖,去靠打鱼为生,所谓打鱼为生,其结果则只能是以贩鱼为生。而收购到这些土地继续经营农业的谭晓本人也只能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而且谭晓所经营的农业,又必须建立在他将这些田地收集起来以后,才能得以实行,否则那些低洼地、湿地,是无法为一户农家提供专门从事农作的条件的。
这里面的另一个信息,则是雇佣劳动。谭晓农业经营不可或缺的是雇佣劳动,他的田地之耕作,鱼豕之养殖,以至农闲时捕虫而售,无一不是商业行为。
凡佃人,每户课其纺织娘凡几枚,以小麦杆为笼盛之,携至苏城,每一笼可取钱一二百文。纺织娘即络纬也,觅之草间,不直一文,佃人本不苦纳(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传》)。
既然以每户为单位课收其所获昆虫,则所雇当为一家一户的雇工。那么,谭晓所能够使用的雇工又是什么人呢?在人口流动相对常态化的现代中国,富裕地区农业生产的雇工,往往是只有农业生产劳动技术的贫困地区农民。但是,在人口流动并未常态化的明朝中叶,会有什么人愿意到地主家成为雇工呢?
常熟当地的农民在将土地出售给谭晓这样的农业经营大户以后,或以捕鱼为业,或者去附近的城镇打工,成为城镇化以后的城镇农民工。谭晓所雇者,应该是部分出卖田地后的农户,以及当初就没有田地,或者仅有很少田地,而只能佃种地主田地的农户。
这与我们所熟悉的男耕女织式的中国自然经济相距又何其之远也!
郡守王叔杲曾记其事称:
谭晓者,邑之东里人也。家世业农,与兄照以力田俭啬起家。晓善心计,取利靡不至,遂以赀雄邑中。照持门户,晓总家计,兄弟于于如也,每饭必同几,晓不至则照不食(王叔杲:《王叔杲集》卷一七《常熟谭晓祠议》)。
这可以算得上是一户典型的传统农家了。谭晓殁后,其婿生员徐自成争其遗产,戕杀晓侄谭培,以行贿及出巨资筑城防倭,移罪家奴二人,叔杲为作祠议以证其事,终以杀徐平反其案,则已是谭晓殁去数年后的事情了。
在商品生产发展的时代,常熟一带当属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社会风气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迥然不同。王叔杲自靖江转任常熟郡守,对此感慨良多:
昨余之为靖江也,土瘠而民勤,地狭而务简。余既安于其陋,而土民亦安余之拙,以幸无戾于官谤,而过则不终无也。今由常熟较之,则疆域之广舒,盖不啻五倍之矣;户口之殷富,征输之浩繁,盖不啻十倍矣;狱情之微暧,交际之稠沓,又不啻百倍之矣。抱牍之胥,鱼贯而怀黠;持牒之卒,蚁集而匿情。余也手倦于批,目眩于盼,耳惑于杂听,舌战于游言,少或疏于诇察、怠于讥诃,而余之为过亦倍于靖江矣。一堕于过忽,已溢于舆人之口。而浸于监司之耳矣。是可以弗思乎?是可以弗思而补之乎?方其惑于来物而应于卒然,固不遑于思而亦莫知其为过也(《王叔杲集》卷一○《思补堂记》)。
这大约可以算得上是当时快节奏的地区特点了。当王叔杲之类谨行自律的官员们逐渐适应这种地区特色的时候,像谭晓这样的农业经营大户则早已能够适应商品化发展的变化,改变传统农作而转为经营化的农户,从而成为首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
与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的同时,也必然会有较多的农民沦为雇工,或者涌入城市,成为城市雇佣手工劳动者。
明人何良俊称:
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的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
何良俊说此番话时,尚在隆庆间,当时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而为官府差役,而为工商,而为无业游民,已占十之六七。其所称为乡官家人、为蚕食官府者,虽较前多之甚矣,就农民而言,仍为少数,多者转为工商、游食者也。
农民转而为工、为商、为游食,即当从农村而进入城市。但是这些进入城镇的农民,大多数并非转化为城镇的居民,他们往往仍然游离于城镇与乡村之间,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农工互动。我们所谓的农工互动,应当包括了生活于城乡之间的小商小贩。
又云嘉靖初,脚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数十群聚,阔边深网、青布衫裤,青布长手巾、靸鞋,人皆肥壮。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于行礼娶亲,俱有青布折,其人皆有行止。今虽极繁富市口,不过三五黧瘦之人,衣衫褴褛,无旧时景象(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这是时人所记嘉靖前后城市雇工的变化情景。但我以为,城市雇工群体的这种变化,其实乃是城市打工者从农民转变而为市民,从帮衬人家大事,转变而为城市手工作坊的雇工的变化,因此才会发生文中描写的情景。这也是商品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不过明朝的这种变化发生得比上述记述要早了一些。大约在天顺到成化间的一天,一位名叫叶盛的官员,路过翰林院官员钱原溥的宅第,被主人强留住宿在家里。他起初不知主人何意,待到第二天黎明起床时,一位熟人张士谦也来钱原溥处拜访,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这位相士端详了张先生许久,突然说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兄弟气力。”这位张先生听了,大笑说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来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这位张先生的家庭原来是一个官商之家。这种情况叶盛也是经历过了的,不过他也说不清楚其间究竟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据他的笔者记述,明初的洪武、永乐年间是没有诗文写作润笔的,到正统以后才渐有润笔的风气。其间一个变化发生在正统末年的“土木之变”以后,从事变前的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二三钱,一下子变成了非五钱一两不敢请了。此种情况直到成化以后,至于其中的原因,则“此莫可晓也”(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叶盛的记述仅至成化间而止,其后的发展情况,他就无从知晓了。到了正德时代,这种称为润笔的收入,不仅继续盛行,而且成为了上层士大夫们的重要收入来源。正德中曾任内阁大学士的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开始了罢政家居的生活。史书中记述说:
既罢政居家,请诗文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其风操如此(《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能以润笔资给日常生活开支,就给予文人士大夫们职业写作的可能。我常想,这是否为其后出现大批混迹于士大夫社会而谋食的“山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物质条件?于是人们得出一个结论:明中叶以后文人无不爱财。其实,此种爱财的风气,已从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蔓延至整个社会。一个官员的儿子因为出水痘,请小儿科医生来看病,先后请了几位医生,都说是大病,诊脉开药,索取极高的诊费。只有一位医生,医术极高,且与众不同,但因同行都在场,不能明言,只好找个机会,对官员说,孩子此病并无大碍,不需要花费许多钱,只需要吃些发散的药,安心休息即可。这位名医在当时被所有人视为另类,医生高价收费,乱开大处方,在当时已成风气,也成为他们索取高收入的手段(李乐:《见闻杂纪》卷二)。
我们为什么要首先谈到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呢?他们虽然不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却是社会风气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况且文化商品化,应该是物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在中国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商品生产对于文化的冲击,则表现为文化的商品化,也即今日所谓之文化产业化。将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发展,则必须由商品生产带动。归根结底,这一切便只能又回到商品生产这个根本性问题中来了。
我们过去所谓的中国式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是男耕女织的小型家庭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即使有交换,也是决然不可能支撑商品经济发展的。这种小农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既缺少抗风险能力,也极易恢复。以当时地处东南的江浙为例,按照明朝人的说法,东南财赋之乡的杭、嘉、湖诸府,在嘉靖以前,编审均徭,如库子、民皂、门厨之类,悉佥选乡民充役。结果翰充夕破,再到倭寇之患时,官使侵渔,公私俱尽,民不聊生。于是御史庞尚鹏首行一条鞭法,计值征银,而民力大纾。又议革去粮长,以里长收粮,彼此互管,贫富通融,十年一审。这样的结果,以中产之家应役,有一年之限,力均时暇,不至于破产,即使破产,亦可有救。此地方之大幸。其后岁久弊生,地方财政,渐为豪贵把持。
再以当时乌程县为例,知县罗用敬在任时,用“在图还图,在甲还甲”之说,民虽愤郁,慑于威刑,爱惜身家性命,且力未甚穷,只得隐忍。待到袁光宇知其县,仍因其旧,结果造成民间大困。“兴衰各异,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然无田者,有一半亩产而充至数分者,有户绝丁存,妄报分数,而亲族代当者。一佥解户,必至逃亡,系籍则百劫不免,漏落则安坐自如。凡势家之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田产系据膏腴,亩数为啻万倍,影射挪移,飞诡变幻,三十年来,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而一种奸猾又从中把持,或子女,或田产器具,乘机胁夺。……亦试度五十年来,能保闾里间,图图甲甲,尽如其旧哉?”(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四《揭帖》)如其所述,此时乡间的生活,随着朝廷政策的变化,起起落落,并非真正富裕起来。传统小农经济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总是在原地徘徊,不再能够前进一步。但与此同时,部分所谓“势家”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们则似乎因此成为了除去少数“势家”本体之外的一部分首先富裕起来的人。在他们占有了较多社会财富的前提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予这批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如虎添翼的机会。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这样一种特质:首先致富者总要伴随着权势的力量。
商品生产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还应该是手工业生产集中地和商品交换集散地的市镇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明代历史上有过十分明显的发展过程——江南市镇的形成与发展。在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江南市镇中原有传统政治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新型商品生产与交流市镇是同时发展起来的。时人张瀚曾经这样来描述明朝末年全国经济形势: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地,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鲜矣。今辇毂之下,四方之人咸鳞集焉(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般情况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首先会在远离政治中心而又相对经济发达地区得到发展,但是很快便由于消费需求而进入政治中心城市。紧随其后发展起来的,则应该是市镇周围的乡村,市镇的消费需求给这些地方农村较多发展的机会。其后复有交通便利之地,经商人转输,形成当时的商业网络。韩大成先生在他的名著《明代城市研究》一书中,专章记述了当时城镇的粮食贸易极为繁荣的景况,且其引据史料极为丰富,兹抄录于下:
如苏南的浙江等地,由于商业人口较多,商业性农业比较发展,所以,“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如江西的“赣(州)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吴会(今江苏苏州市)咸取给焉。两关转毂之舟,日络绎不绝。则俭岁亦橹声相同。”又苏州嘉定地区,“县不产米,仰食四方”,每当“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接也。中产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常熟出产的米,“每岁杭、越、徽、衢之贾皆问籴于邑”。嘉兴地区,“物产宜稻,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四”。石门“种梅豆……远方就市者众,亦称一熟。商人从北路夏镇、淮阳、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作油作饼,又或转贩于南路,商人豆船皆集包角堰,谓之小瓜洲”。又安庆地方盛产粮食,经长江大量远销各地。明末方都韩说,这里的粮食,“繇枞阳口达于江者,桐(城)居十之九,怀(宁)居十之六,潜(山)居十之三”。又庐州地区,其地“抱湖而吞江,水泽所及环匝千里,其民是工于农而务五谷,岁逢丰穰,则粒米狼戾转输他售者,车舟不绝焉”。大江之南的徽州、池州因工商业人口较多,所以,“大半取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贾从数千里转输[1]。
粮食贸易不同于手工业的产品,粮食的运销是典型的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过程。只是粮食可以通过相对方便的交通工具远途贩运,而城镇生活必需的蔬菜水果和肉类,除少数果品外,大多只能来自城镇的周边农村。这些物品交流只能是城镇中的商铺或者通过集市贸易方式来实现。明万历间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著有《宛署杂记》,详记各类食品价格,可为参据。
猪肉每斤价银二分,牛羊肉每斤价银一分五厘,大鹅一只价银二钱,鸡一只,价银三分四厘,鲜鱼一条五斤,价银一钱,糖果一斤,价银四分,栗子一斤,价银一分三厘。但是如远方贩运的荔枝,则一斤价银须四分八厘,较之京畿可产的猪、牛、羊、鸡要贵了许多(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五《杂费》)。
这是官府采办的物价,较之日常民间价格或许略高一点,但基本上可以反映当时物价情况。照此价格,一桌宴席下来,一二两银子是要的,那么当时一般家庭能够承担得起吗?
当时江南的粮价,一石大约是六钱左右白银,官方下兑,每石七钱,折兑每石六钱。万历时江南苏州府吴县的米价,丰年可以低到一两白银买四石米,但是荒年也可达到一两六七钱才能买一石米。一般丰年米价每石三四钱,歉年每石一两五六钱(崇祯:《吴县志》卷一一《祥异》)。按照这样的价格,一桌宴席就要花去农民几个月口粮。尽管江南物产丰富,物价或略低于京畿,但也只是蔬菜及鱼虾、鹅鸭之类价格稍低。不过明代在正常的年份,粮价相对稳定,南北应无大别,这也便成为明代民间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明朝万历间人顾起元曾经谈到南京的粮价:
金陵百年来,谷价虽翔贵至二两,或一两五六钱,然不逾数时,米价辄渐平。从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数百钱,而饥馑连岁,至啮木皮草根砂石以为粮者。则以仓庾之积贮犹富,而舟楫之搬运犹易也。惟仓庾不发,而湖广、江西亦荒,米客不时至,则谷价骤踊,而人情嗷嗷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议籴》)。
明中叶以后,已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
顾氏于此论及原因,一是仓庾富积,一是运售犹易。既有产量,且有流通之便,自然粮价不会居高不下。况且江南各地,商业活动亦复发达,足以补田粮之缺。
对此,明朝人说:“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江右荆、楚五岭之间,米贱田多,无人可耕,人亦不以田为贵,故其人虽无甚贫,亦无甚富,百物俱贱,无可化居转徙故也。闽中田赋亦轻,而米价稍为适中,故仕宦富室相竞畜田,贪官势族有畛隰遍于邻境者,至于连疆之产罗而取之,无主之业嘱而丐之,寺观香火之奉强而寇之,黄云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贫者日贫矣。”(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又说:“三吴赋税之重甲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人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其人亦生而辩晰,即穷巷下佣,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
所谓射利“无微不析”,也便是取利于田亩之外。这些获利,也就必然要有商品市场的依托,就如同明朝人所记,乡里贫民,将形状奇异的石块制成盆景出售取利。盆景是家庭装饰而用的文化产品,然其能够成为文化产品,则必有相应的社会需求。需求与市场活动促进了各种商品的生产,积少成多的社会财富也便由此而生。例如素称富庶的苏州,对于财富的追求早已成为地方风俗与传统。苏州城内分为吴县与长洲,一东一西,风俗不同,而勤勉致富的追求则无异。
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城中妇女,习刺绣,滨湖近山小民,最力啬耕渔之外,男妇并工细履辫麻织布织席采石造器营生,梓人、瓦工、垩工、石工,终年佣外境,谋早办官课。
湖中诸山,大概以橘柚等果品为生,多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生女未笄,教以育蚕。……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人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舟,又能泅水。其土贵,凡栽桔可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千,甚者至万钱。其民勤,虽蓄千金而樵汲树艺未之或废。其俗厚,民间无淫冶赌博之肆(今洞庭东山渐多,屡谨刑禁)。……其冠服朴雅,戴时制之冠,虽樵耕不去首。东洞庭女装,大略效南都,夏月行路,手执糊制纸团扇,遇人则掩面。凡婚丧务实而有体(崇祯:《吴县志》卷一○《风俗》)。
上述材料引据王鏊笔记,可知其时间尚早,风气尚属纯朴,但在洞庭东山,已有赌博之风,且屡禁不能止。顾炎武《肇域志·南直隶苏州》引文略同,其后复记称:“新郭、横塘,比户造酿,烧糟发客。横金、下保、水东人并为酿工,苏属州县以及南都皆用之。又习屠贩,每晨刳豕入市。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多开坊榨豆油。”[2]261又称:“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妪晨抱棉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恃此。”[2]310
以商补农,在当时大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仅是地狭人稠的江南一带,即如嘉靖间叶权所见岭南的广州,商业繁荣不仅可比苏、杭,其商业氛围较之江南更加平和、普遍。
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叶权:《博贤篇·游岭南记》)。
叶权记述此情此景之时,为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其时葡萄牙人已据澳门,广州开海市与之交易。“广东军饷资番舶”,“华夷交易,夷利货物,无他志,固不为害。”(叶权:《博贤篇·游岭南记》)可知自嘉靖后期,东南沿海各地,商业活动发展较快,成为城市生活中重要内容。商业活动必然带动相关需求,城市服务业也因此而得以发展。徐泓教授在其著名的论文《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中曾说:“除了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外,商业与服务业也是重要生业。”徐先生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服务业可算是晚明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特点,所以他引用了当时人陆楫的一段话:“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这里所谓不耕不杼者,并非指不劳而食的寄生群体,而是指那些通过服务或其他工作方式取得财富者。正是各种获利途径的增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社会财富的来源,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改变。因此,徐泓教授评论说:“一般乡里人民,由于经济情况改善,物力丰盈,有能力追求较高生活享受,使过去只有上层社会可以享用的,普及于下层社会。”[3]318-319正是财富的增加与“乡里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条件。明代的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变化。一些新兴起的市镇,成为当时商业巨镇,也因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如今天上海的朱家角,明时属松江府,史称:“朱家角镇,在五十保。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2]298
迄今为止,由于缺乏具体的生活费用指数,我们无法再现当时人民的日常生活消费情况。但是,有些材料记述,还是令我们感到不解,而有的史料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
长洲姚公木家贫,事父,惟与村民交互佣作,得米供父。父落魄,不事生业,而嗜酒眈诗。一日见你缓步庭中,作吟哦声,私谓妻曰:“汝舅无酒,故诗不就,汝亟温酒以进。”你常饮至夜分,必周旋伺候,未尝入室(张怡:《玉光剑气集》卷一四《孝友》)。
这只是一条关于孝道的记述,但是这位以孝称的姚某不过是与村民交互佣作,即可得米供父饮酒吟哦,而其父则可不事生业,如果这是当时佣工者正常生活,在比较富裕的苏州地区,一个人的佣工收入也必定可以养家了。
而同书所记湖广的情形,当时著名竟陵派领袖人物谭元春的家居生活,也不过如此:
谭解元元春,性孝友,伤其先人早逝,母日老,虽善游,时归定省。母弟五人,皆娴笔墨,互为师友。母兄弟妹,食必同席,人供一日。薄暮,取酒相对,谈学业世事,母喜出听,自制饼饵蔬醴佐之,酌啖辨闻以为乐(张怡:《玉光剑气集》卷一四《孝友》)。
所记姚、谭的生活,虽有贫富之别,却实在都是一种令人艳羡的天伦之乐事。
二
明朝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士大夫们最感优异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十分惬意。此时政治上已无明初那样的严酷,生活也已不似明初时的清贫,于是更多的文人士大夫们开始刊行个人的文集,并以此树立个人形象。
在这样的优裕生活中的士大夫们,渐渐发觉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社会生活风气已经隐然发生了变化。一位生活在南京并且亲身经历了这段变化的明朝官员顾起元,在其笔记中表述出了十分怀恋的心情: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咕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娼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者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红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不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
人们一般喜欢用“醇厚”二字形容过去,而用“浮华”二字形容现实,以凸显社会风气的变化。顾起元所谓的“醇厚”时代,虽然也有逐利、僭越与浮华,但不过百中之一二,如今这些现象已从百不一二见之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文中所述的变化涉及从士大夫到家庭中女性的所有社会人群。
此类社会风气变化,在当时人的笔记文集中,随处可见。明朝的士大夫们,在享受物质生活和宽松政治环境的同时,却又几乎都在批评这种变化,这实在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
我们不妨看看正统年间一位士大夫请客的情况。一般来说,他只需命一童子至各家邀请,不过是打个招呼:“请吃饭。”午时未到,客人们便已应邀而至。如果宾主共六至八人,则只用一张大八仙桌,准备的菜肴一般只有四大盘、四小菜,不设时果,饮酒时用两大杯,轮流传饮,桌上再放一大碗清水,用来洗涤酒杯,称作“汕碗”。午后席散,各自归去。这成为当时士大夫宴客的常规。可是十数年后,情况便逐渐发生变化了。这时候请客,要提前一日,用帖相请。帖宽一寸三四分,长五寸,上面写好姓名某拜,书写“某日午刻一饭”,虽然席间饭菜尚无大的变化,但已不能招呼即至了。再过十数年,请客始用折帖,一般三折,大约长五六寸,宽二寸,较前稍大了一些,写上“眷生某”或“侍生某”拜,吃饭时已经不能再用八仙桌待客,此时已设开席,一般二人一席,即后来所称“偶席”者也。客来亦有了规矩,不能待到午时才到,一般巳刻入席,至申刻方即散去。用时既久,席中的菜品果肴亦须丰富,不少于七八种方可。再至正德、嘉靖间,席间便多设乐,家常饭菜已不能设宴待客,而须专请厨师了。
如此看来,所谓嘉靖前民风的“醇厚”其实也在隐然变化之中。不过这时候,士大夫们还以清俭为雅士的本色,不愿让人感到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他们居家读书,门无杂客,只有士大夫们过访,方肯延见。可是他们家居的生活,却已十分奢侈。往往家中多畜少艾,穿着华丽,闭门居家赋诗作文与亲友共赏。每逢家中名花开放,便设宴请客,以古诗奇句、僻事奇人为酒令,嘲谑相错,追求风流雅兴,以自高其身。
这可以算得上是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情况。士大夫作为一个时代风气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这样的生活,既流行于士大夫之间,且为时人所艳羡。于是此种风气也便走出了士大夫的家门,渐至影响了整个社会。
南都服饰,在(隆)庆、(万)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靖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伙,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瓶,或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罗帽、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极矣。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屐、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即妇女之饰,不加丽焉(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巾履》)。
这里面讲到服饰的变化,但终究还是流行服饰。其后复有年轻秀才们争相效法,又别出心裁,更渐成为时装的追求,以表现个性,从而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曾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官员李乐也谈到了这种服饰的变化:
嘉靖辛丑、壬寅间,礼部奉旨严行各省,大禁民间云巾、云履,一时有司视为要务,不敢虚行故事,人知畏惮,未有犯者。不意嘉靖末年,以至隆(庆)、万(历)两朝,深衣大带,忠靖、进士等冠,唯意制用,而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状,朝廷亦曾设禁,士民全不知警(李乐:《见闻杂纪》卷二)。
如其所述,对于服饰的变异,官方是曾经有所管理的,但其目的应在于防止僭越的风气,而至嘉靖末年,风气已不同于前,即如严世蕃之类高官权贵,在家中与人谈议,已是当时的十大首富之一,足见商品生产发展之下,旧日等级已渐被财富取代,服装之风气,禁而不能止,则是必然之结果。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倒不是李乐的这些评论,而是他的亲身经历。他十五岁那年,大约是在嘉靖中后期左右的时间,他正在县学里面读书,是一名年轻的秀才。有一天,他跟着众秀才们一起去谒见嘉兴府的知府赵瀛。同去的一位富家子弟,姓曹,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衣着极为讲究修饰,与众秀才们同立于班中。知府赵瀛见到后问道:“生非娼优家子弟乎?何盛妆如此?”那位姓曹的富家秀才听到后,满面羞愧而感到无地自容。二十余年以后,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李乐已经为官多年了,他与学道一同去湖州巡视学校的时候,看到的情况则是“民生俱红丝束发,口脂面药,廉耻扫地,父兄方以为得计,而郡邑官亦未闻有正言黜阻者。”(李乐:《见闻杂纪》卷二)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李乐于是叹道:“噫,若遇赵公凝然在上,则人妖物怪安得可丑如是!”(李乐:《见闻杂纪》卷二)
其实,这位李大人的想法也未免显得有些天真了。既然穿着服饰的变化,已经从一名曹姓青年秀才变成了所有的学生们,而且当年的赵大人也已不复存在了,那么就不必感叹服饰变化了。甚至有些风气,正是此类大人物所倡导:
弘治、正德初,良家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髻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尤胜于妓,不能辨焉,风俗之衰也(谈迁:《枣林杂俎·女饰》)。
从个别到普遍,就是风气的作用。用强制手段控制社会风气的变化,只能起到一时的作用,并不能够长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风气的传播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发展。
也许如李乐之类的思想较为传统的官员士大夫们,很不习惯这种时尚的变化。但是,他们往往也并不拒绝生活品质的提高。官员们虽然受到品服的限制,但是他们的家人子弟,则可以充分追求华贵,而且将这种华贵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这一时期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首先便感受到了晚明人的这种风尚变化。而且有趣的是,利玛窦也注意到了明朝人用马尾织成的头巾和讲究的鞋子:
男女都穿拖到脚面的外衣。男人的袍子在胸前交叉起来,用扣子把里褶固定在左臂下面,外褶则固定在右臂下面。……男女的袖子都又肥又长,是威尼斯式的。……男人的帽子种类很多,制作精致,最好的是用马鬃织成的,然而冷天也戴毛织或丝织的帽子。和我们样式最不相同的,或许可以从中国人穿的鞋上看出来。男人的鞋是用布或绸做成的,上面绣的花甚至比我见到贵妇人穿的还要讲究。
当大臣或有学问的人出门拜客时,他穿上一件特制的拜客长袍,和他日常穿的长衫大不相同。甚至没有荣誉头衔的重要人物出门拜客时,也要穿特别设计的袍服,如果他穿平时的衣服,就会被人见怪(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一)。
利玛窦当然不知道其实明朝人的衣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所观察到的这些市井风情,都已经是经历了嘉(靖)、隆(庆)到万历变化后的情况。不过他的描述,印证了明朝人自己所描述的衣着的普遍的变化。
前面那位李乐这时候又记下了他家乡浙江桐乡的变化:“余乡二三百里内,自万历丁酉(二十五年)至丁未(三十五年),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染色大类妇人。”(李乐:《见闻杂纪》卷一○)他这里所说的若辈,既包括了地方富户,也包括了那些原本布衣蔬食的乡民。这显然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不过从上述材料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说法:“衣色大类女妆”、“口脂面药”、“即妇女之饰,不加丽焉”、“比贵妇人穿的还要讲究”、“且染色大类妇人”云云。
风气之变当然不仅于衣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比如饮酒的风气,大约从正统、天顺间便与明初大不相同了。
古人饮酒有节,多不至夜,所谓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乃天子燕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也。故长夜之饮,君子非之。京师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饮酒多至夜,盖散衙时才得赴席,势不容不夜饮也。若六科及诸闲散之职,皆是夜饮。吾乡会饮,往往至昏暮才散,此风亦近年后生辈起之(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
再如赌博的风气,亦起于正统以后,以昆山、太仓一带最为盛行。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大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俊,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灼,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
此时流行的小说,更是世风变化的写照,这大约也是从正统以后开始的。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读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读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骀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至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
而领导着这种社会风气变化潮流的,首先还是姑苏。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所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交往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2]263。
这显然是时代的风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在此种变化包括了从外在到内在的变化过程,我们已然显见其由俭而入奢的变化。
三
其实明朝中叶以后的人们,在谈到昔日风俗时,难免感叹一番,内容也无非是昔日如何淳朴节俭,今日如何奢靡。因知在从明初至中叶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由俭入奢的过程。
洪武、永乐两朝名臣解缙一份家书中,说尽了当时官员们生活的窘迫。
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皆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假象食之类,所费不赀(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四)。
永乐朝户部尚书夏原吉弟弟来京探亲,临去时原吉送给弟弟俸米二石。永乐帝得知后,感到太过寒酸,问原吉何故。原吉回答:“臣所遗俸,已寄之,无以为赠。”永乐帝过意不去,又特赐几匹好布(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四)。
大约明朝初年算得上是一个物质比较匮乏的时代,虽然国家可以兴大工、下西洋、迁都、出征,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不过国富民穷而已。不止于民穷,即如皇室、官员们,也不能算得富有。明仁宗时为太子,留守南京监国,经常因为手头过紧,不得不取给于城中富户伊氏。而像伊氏这样的富户,在当时实在少之又少(王琦:《寓圃杂记》卷二《金陵伊氏》)。那时候新科进士们看榜就宴,都是徒步而行,未见有乘车马者。直到宣德以后,进京赶考的举子,也只见有乘驴者。那时在京的御史住所,有的敝败不堪,仅避风日(金幼孜:《金文靖公集》卷一○《祭都御史胡元节母太夫人郭氏文》)。
官员尚且如此,民间生活更可想而知了。当时的官员邹缉曾说:“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处,人民饥荒,水旱相仍,至剥树皮、掘草根、簸稗子以为食。而官无储蓄,不能赈济。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穷财匮如此,而犹徭役不休,征敛不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邹庶子奏疏》)明代永乐一朝,是中国历史上蠲免赈济最多的时段,邹缉这里所说的北方各地,则显然是并无蠲免的去处。
这种情况大约到正统以后方才有所变化。当我们看到成化年间解职归乡的御史姚绶那种“粉窗翠幕,拥童奴,设香茗,弹丝吹竹,宴笑弥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姚御史绶》)的生活时,我们会深感这些乡官们就是社会奢靡风气的引导者和推动者。但是,其实这也不过是当时社会上层富人生活的写照。我们不妨看看隆(庆)、万(历)时的商人:
人亦有言:士固有志。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筴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召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百不足也(汪道昆:《大涵集》卷二《汪长君论最序》)。
我们看历史,皆知首先得以享受这种奢靡生活的人,只能是官员与商人。但是流风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到这个时候,人们却又要说:“士风俭薄,民风奢侈。”(万历:《榆次县志》卷一《风俗》)。不过此类说法,大都见到方志之中,这很能够说明民风趋奢成为一时之共见。这无非是地方修志者们认为,上层官员士绅与富商大贾的奢靡尽可理解,而民间的效法,则是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的衰颓之变。
天顺年间,一个老内官从江西回到京城,见到内府用官纸糊墙壁,不由落下泪来,因为他在江西看到了制纸的不易。据说洪武年间,国子监生员们用过的课本和写过仿书的纸张,要按月送到礼部去,仿书发送光禄寺包面,课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纸用。到永乐、宣德年间,年节烟火花炮还用旧纸制作,以后就不再这样制作了,成化以后,鞭炮均用新纸。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产量增多,旧纸供不应求,况且即使用新纸,生产出来的花炮也足以赚钱了。这似乎可以作为“民风奢侈”的佐证之一,但另外一些材料却告诉我们另一种情况:
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日之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可谓异矣。而书柬摺拍,亦不过一二寸耳。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郎瑛:《七修类稿》卷一七《义理类·刺纸》)
待到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年节时得到的贺卡,数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节,红帖积受,多至百千,今昔奢俭迥别。”(李乐:《见闻杂纪》卷轴)这显然又是自上而下的奢侈了。
我们其实并无必要考察晚明风气的来由。倘若一定要寻根问底的话,那也只能是商品生产的结果。正是因为商品生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所以昔日的商人会馆才会成为应试举子们的寓所,才会出现全民一致的弃本逐末。当这一切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时候,便无分贵贱老少男女了。
我们翻开晚明的文集、笔记或者方志,几乎随处可见关于社会竞奢风气的记述,而且记述下了社会风气从俭入奢的前后变化。
弘(治)、正(德)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民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价廉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故有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上座。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幺麽贱品,亦戴方头巾,莫知禁厉,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旧时便宜的羊肠葛、本色布因为没有销路而不再生产,这是典型的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是,里中子弟争相以价高而美丽者为衣,为裤袜,且倏忽变异,号为时样,则是追求时尚风气的结果。今日所谓追求时尚,其实是商家的行为,以此而促进商品的销售。年轻人永远是潮流的追逐者,晚明时代也是由青年们领导了时尚的潮流,并由青年人影响到整个社会。
吾乡先辈,岁时宴会,一席而宾至如归主四人共之,宾至如归多不能容,则主人座于宾之侧,以一瓷杯行酒,手自斟酌,互相传递。肴果取具临时,酒酷于市,惟其土风,不求丰腆,相与醉饱而别,以为常。庶民之家,终岁不宴客,有故则盂羹豆肉,相招一饭,人不以为简也。贵家钜族,非有大故不张筵,不设彩,不用歌舞,间有一焉用歌舞戏,则里中子弟皆往观之,谈说数日不能休。
今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偶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渎客,不敢以荐。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得之,以得者为豪雄(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既已称“今乡里之人”,显然已不限于里中的年轻子弟;既以夺他氏之歌舞“以得者为豪雄”,则里中年轻子弟们,已不仅仅于追逐潮流的行为:“今则里中子弟,以任侠为豪,其尤桀者,日与宾客奸人博塞酣歌,崇饮无忌,醉则入市攫人之金。有司者捕治之,则持刃而格斗也。”(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这里所说的通州,乃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省南通市,当时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而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万历《博平县志》卷四《风俗》)
这些方志中的记录,从宴饮说到服饰,再从服饰说到民歌时调,从上层社会说到下层社会,从市井说到乡里,竞奢风气似乎成为了当时城乡社会的普遍现象。
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崇祯《郓城县志》卷七《风俗》)。
这段记述将当时竞奢的风气与社会生活中的僭越行为结合了起来,而且谈及当时人在竞奢的同时,却不肯承担分内的赋役与社会的救助。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竞奢风气的背后,并未形成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而只是更突出地表现了拜金与对于享乐的追求。因此,晚明竞奢风气的积极作用也就很难显现出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较早关注晚明竞奢风气的学者是台湾徐泓教授和林丽月教授。他们首先提出:“嘉靖以后,社会风气侈靡,日甚一日。侈靡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尤其商品的贸迁质与量的增加,更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盛行,又影响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僭礼犯分之风流行,对‘贵贱、长幼、尊卑’均有差等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冲击甚大。尤其侈靡之风,刺激人们欲望,为求满足私欲,乃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恬不为怪,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3]318徐泓先生在这里既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也谈到了奢靡风气对于社会贪腐的推波助澜。我们感到,在晚明那个时代,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将整个社会推向了前途未卜的境地。
我们在诸多史料中看到的是万历以后社会风气的变化。顾炎武作《肇域志》记述扬州府事时,言称海门“民风蓝天称淳直,近则尚气而好攻讦,虽学校不免。”通州“其土田饶溢,民富而好义。又人文渤发,仕者多贵官显秩,盖风气固殊焉。然闤闠绣错,衣食服玩,日渐于纷华。”而如皋“土膏活而俗勤于稼。征科易集,讼稀简,在昔最为醇厚。自倭警以后,浸淫一变。富家巨族,竞以华侈相高。豪不逞者,辄诱良家子弟,纵樗蒲六博,荡其赀业,甚则为逋逃渊薮。迩或稍惩艾焉,但馀风未殄,长民者,其未可画诺而理也。”[2]350-351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将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化归结为倭寇之乱。
像嘉靖倭乱这样的事件,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东南财富之地在遭到这样动乱之后,也会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人们在追求社会生活安定的同时,对于过去富而不奢也极易产生反思,在兵燹之余,或许会更愿意去享受生活。我们或许应该讨论一下,嘉靖倭乱对于东南社会风气的影响。
那么,在晚明时代,面对这种奢靡之风,当时人又是如何评论的呢?晚明竞奢风气的意义不在于竞奢本身,而更在于对于社会奢侈风气的全新的论点,因为这才体现出了商品生产冲击下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象。
但是,奢靡并不代表真正的富有,而只是一种社会攀比的风气。在晚明时代,这种竞奢风气主要流行于南北两京及江浙一带。所以当时有人这样记述说:
各省虽富贵之家,惟布衣布服。两京、吴、越之地,以绮罗为常服。布者,富贵悠长,衣帛者,储无隔宿。所以贫多在市,富多在乡。饥寒生于大厦,饱暖处于草茅。此皆奢俭之效也(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卷一《商贾醒迷》)。
我们从当时材料中看到的,显然不是这样,这只是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奢靡追求的批评。况且奢靡风气会造成官员的贪腐,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所以当时御史赵文炳说:
未有小民奢侈而不困窘者,亦未有居官奢侈而能清介者。迩来繁华僭逾,风俗大坏。则去奢崇俭,诚救时急务。但大臣不行,何以表百官?京师不行,何以示天下?(《明神宗实录》卷二七六,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丙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因发生星变示异,礼科给事中张贞观上疏请申奢禁:
臣尝庄诵《大明会典》、《大诰》、续编及《大明令》诸书。太祖高皇帝奢靡之禁,盖亦甚严。我皇上即位以来,再三申饬。至十三年,因科臣言,命本部将题禁事宜通行内外。不数年间,颓靡如故。岂惟小民蠢愚而无知?抑亦有司奉行之不实。今天下水旱饥馑之灾,连州亘县。公私之藏,甚见匮诎,而闾巷竞奢,市肆斗巧,切云之冠,曳地之衣,雕鞍绣毂,纵横衢路。游手子弟,偶占一役,动致千金。婚嫁拟于公孙,宅舍埒乎卿士。惰游之民,转相仿效。北里之弦益繁,南亩之耒耜渐稀。淫渎无界,莫此为甚,京师四方之表,簪绅众庶之标。从风易向,不可不谨。诚有如科臣所言者:行父区区相鲁而家无衣帛之妾;平仲仅仅显君而口甘脱粟之饭。翼翼京邑,民极所归,赫赫师尹,具瞻攸属,诚不可不厚自准绳首先士庶,以副圣天子还淳崇俭之意(《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三,万历二十一年庚戌)。
有趣的是,一心追求奢靡的神宗皇帝并不在意海内的匮乏,他只注重官场的僭越风气,他在臣工奏折的批复中就曾这样说道:“近来士庶奢靡成风,僭分违制,依拟严行内外衙门访挈究治。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近闻在京庶官,概住大房,肩舆出入,昼夜会饮。辇毂之下,奢纵无忌如此。厂卫部院一并访缉参究。”(《明神宗实录》卷二六三,万历二十一年庚戌)
人们不断批评奢靡,但几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评奢靡成为一种不可少的程式,而并非一定要去改变这种现象。这也是晚明奢靡风气不可改变的原因。
收稿日期:2012-0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