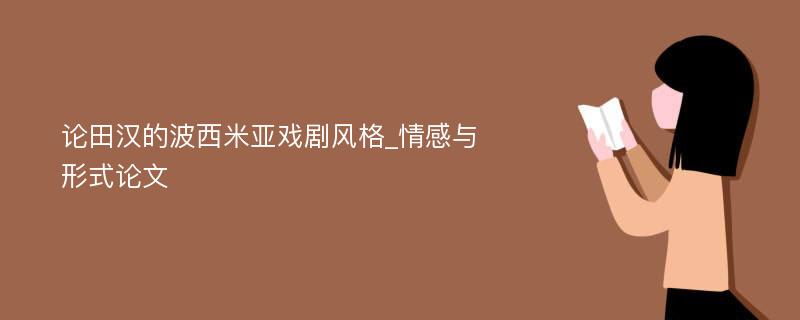
论田汉的波希米亚式戏剧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希米亚论文,戏剧论文,风格论文,田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田汉天生有一种喜好漂泊、向往流浪的浪漫心性。他9岁丧父,父亲田禹卿一直谋事在外,那番羁旅辛酸对于幼年的他显然并无体认的可能,但脱离末路家庭的复杂与死寂的那种洒脱还是给未谙世事的田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继父亲逝世,家道愈益败落,加之深明大义的母亲经年累月的教导,天南海北干大事业的舅父易梅园先生那种“春水何茫茫,一去不复悔”的潇洒风神的激励,田汉年少的心理早已抛撇了家的笼罩,外面风雨飘摇世界的精彩、神秘,哪怕是难免的苦厄,对他都是一种强烈的诱惑(注:参见《母亲的话》,《田汉文集》第15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这种诱惑几乎作用于他的一生,至少对他整个青年时代的事业选择和艺术倾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的记忆中,初次的离家丝毫没有分离的痛苦,反而心里“充满了小孩子的欢喜,充满了宗悫式的雄心,充满了诗人的想象”,(注:《从悲哀的国里来》,《田汉文集》第14卷。),他甚至愿意在某种积极的情感意义上理解“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这一古语,说是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一个人“尝过了些人生的滋味,你才真正了解它是何等黯然消魂的事”。他自己年纪稍大,尝过一些人生滋味后铩羽归来,得携未婚妻表妹同行,确实很少漂泊的伤感,所有的正是“黯然销魂”的体验:“这次旅行,虽是一种冒险,但实是我有生以来最甜蜜的旅行。我们都商量着将来的梦,对于故乡和亲人的留恋之情是很轻的”(注:《从悲哀的国里来》,《田汉文集》第14卷。)。
他对于故乡及故家的情愫如此地淡薄、疏远,要害更在于他宁愿将这种淡薄与疏远的情绪往一种经典美感的意义上作诗意的粘连,于是由此产生的感伤便蒙上了一层至少为他自己所极为欣赏的情调。家乡的诸多变化及故家的许多变故固然使他成了无家可归的畸零人,可他伤心的泪水却在英国诗人叶芝的诗句中结成了一串甘饴:“但我们一回到我们的‘银泥斯瑚理’时,才发现我们还是异乡人”(注:《从悲哀的国里来》,《田汉文集》第14卷。)。叶芝的《茵尼斯弗里岛湖畔》(Yeats: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诗中传达出的美丽的忧伤迅速使他在高雅的心理对应中得到了解脱。
田汉这种淡漠于故乡与故家,向往着外面世界的心性,还与他历来接受的文化素养大有关系。他从小就沉浸在《西厢记》、《倩女离魂》、《红拂传》、《五台会兄》等古典戏曲的艺术世界之中,其中或缠绵悱恻,或慷慨壮烈的故事都展现出现实之家以外的那一番海阔天空。田汉时年尚幼,于热烈美好的爱情还处于似懂非懂之间,但那种脱离家庭约束、摆脱家庭负累后的自由自在却深深地吸引着他,在他幼小的内心形成了某种积淀。后来阅读《红楼梦》,对宝玉反抗性的离家出走的同情便大大超过对宝黛之间恩爱缠绵感情的激赏。在外国作家中,他同那个时代的许多新文学建设者一样欣赏易卜生,并“尝自署为A Budding Ib-sen in China”(中国未来的易卜生)(注:《致郭沫若的信》,《田汉文集》第14卷。),但他并没有像胡适、鲁迅、冰心、王统照等人那样将易氏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甚至揭示社会“问题”的传统接受下来,而常常是被易卜生剧作中的“出走”和“孤寂”的情节所打动,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所谓“易卜生主义”的灵魂,但常播弄着易卜生式的“出走”与“孤寂”的冲动。他爱读歌德的《浮士德》,剧中主人公那种一刻不停地追逐新境界的流罪人心态每每给他以深深的感动;他热烈推崇王尔德,并不仅是因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艺术思想如何印合他的心机,更因为王尔德是颇为典型的波希米亚风格的文人,早在19世纪后期就公然着奇装异服举向日葵花在巴黎和伦敦的街头招摇过市,这种极力标榜异端的举动在田汉看来才是最具魅力的。
出于这种喜好漂泊、向往流浪的心性,田汉尝以“波希米亚”之风自况自许,称他的南国社“很浪漫地集合着许多所谓‘波希米亚青年’们”(注:《田汉戏曲集》第5集自序。);他的朋友们也这么认为,时隔半个世纪,夏衍犹在这样亲切地回顾着田汉的南国社:“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人”(注:《悼念田汉同志》,《田汉文集》第1卷。)。波希米亚本是指捷克西部的一个地方,那里经常受到异族的侵害,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便历史地处于正常的浪浪状态。后来人们在研究法国19世纪文学时,习惯于用这一地名称指代波特莱尔这类生活上豪放不羁、与常规宣战的文艺家(注:参见Cesar Grana:"Bohemian Versus Bourgeois:French Society and the French Mao of Lett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 Basic Books,1964.)。南国社也正集聚着不少具有这类倾向的青年,尽管不可能像波特莱尔特别是像一度旅居法国的王尔德那样走极端,可他们或作波特莱尔百年祭,或演出王尔德的戏剧,切身体验王尔德倡导的“人生艺术化”观念,由此赢得了“波希米亚人”、“无政府主义者”的称号。他们在明确意识中拒绝任何“家”的约束,常常为南国社及南国艺术学院的“无恒产”而备感自豪。他们发誓要成为“最有野性”的一群,正如田汉所说:“虽然当时的所谓‘意识’,就在我也还是很模糊的,不过在‘野’的精神一点,我却牢固把握住了”(注:《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汉文集》第14卷。)。作为一群充满着艺术梦幻的年轻人,他们天真而切实地以为拥有了艺术和才华便拥有一切,于是凭着这些既是无价的同时又是不值一钱的“财富”在江南的文化旷野上作艰苦恣睢的流浪,演出田汉那些常常是即席即景创作的剧本。田汉无疑是这群波希米亚式青年的核心及精神领袖,他深知“他们也喜欢我的味道”,这便是与波希米亚风格相通的“味道”;田汉“也为着使戏剧容易实现得真切,每每好写他们的个性”,这当然也就是波希米亚风的“个性”,包含着颠沛流离、坎坷孤寂、穷困落拓等精神内容。田汉清醒地总结道,因为充满着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们中间自自然然就酿成一种特殊的风格”(注:《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汉文集》第14卷。),这也就是田汉体戏剧的基本风格:演示波希米亚式漂泊、流浪的罗曼司。
二
以漂泊或流浪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古已有之,西班牙十六七世纪兴起的浪浪汉小说蔚为典范。但流浪汉小说作为城市文明初期的文化成果,表现的是下层平民冒险的经历与机智的品质,以讽刺社会及显示玩世不恭心态为旨趣,与田汉戏剧所展示的反映小布尔乔亚艺术家坎坷、落拓、颠沛、流离、穷困生活并抒写他们精神孤寂的波希米亚风格并无太多的联系。田汉体戏剧固然以人物的漂泊、流浪行为为表现对象,但更注重用燃烧似的心犀从这种漂泊、流浪中蒸发出浓烈的诗情,在美学价值感上对由此漂泊、流浪所产生的情绪充满认同的意愿。在典型的田汉体戏剧作品中,不仅人物的生存状态是漂泊或流浪的,人物的心理取向也是漂泊或流浪的;围绕着剧中人物展开的外部冲突固然以漂泊或流浪作载体,即使人物的内心冲突也是以心理的漂泊或心灵的流浪作结局;于是,田汉体戏剧的贯穿结构往往是由漂泊和流浪组织而成的。这便是田汉体戏剧的基本风格。
田汉一直以艺术家作自我期许,立志为艺术献身。他的作品塑造得最多也最好的人物形象便是艺术家。而他一开始所理解的艺术家在本质上就是波希米亚式的人物,用瞿秋白的话说,是“薄海民”:“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他写过一首《漂泊的舞蹈家》诗,诗中断言:“漂泊!是诗人的生活,是琴师的生活,/是歌女的生活,是舞蹈家的生活,/是一切艺术家的生活!”而且这种流浪和漂泊生活的自我感觉应是甜蜜的,是可以自娱的,虽像“暴风雨中的孤舟和沙漠中的旅客一般的飘摇而寂寞”,但更“像幽谷的黄莺给他自己的啼声陶醉了似的”那样凄美(注:《田汉戏曲集》第4集自序。)。在他的代表作《南归》、《古潭的声音》、《苏州夜话》中,主人公一直以流浪为生命形态,甚至只是以漂泊为业;他们的悲苦和甘甜皆得自于流浪的酸辛或漂泊的自由,这给他们的生命感兴带来了十分充实而又高度唯美的内容。
最初写那部“出世作”《环珴璘与蔷薇》时,田汉还不甚善于把握流浪酸辛的悲苦与自由漂泊的甘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他在自己的意识层能够充分理解它,但在剧作操作中他将这种关系作了割裂的处理——让柳翠从世俗化的意义上表述流浪之苦,于是对不知流落到天之哪一涯地之哪一角的张雪舫表示了这样的关切:“可怜他父亲母亲都死了,孤孤单单一身在外面跑,倒好象和我一样(说着不觉泪如雨下)”。接着让一个与他们并不相干的人物——李简斋的儿子李家骐表述漂泊的自由之于艺术家的意义。他讲述了法国一个著名小说《歌女与琴师》的故事,那故事里的两个主人公相爱了,“后来双双逃出巴黎,在世界各国流浪演奏他们的艺术。世界各国的人,受了他们俩的感化,都想望一种纯美的世界,所以世界上因此就没有战争了”。这种类似于痴人说梦的罗曼司当然连田汉自己也不能信服,所以他始终没有十分认同这一“出世作”。
到了他自己比较满意的第一部剧作《咖啡店之一夜》中,田汉则成功地克服了“出世作”在表现波希米亚风格方面的上述缺陷,将流浪酸辛的悲苦与自由飘泊的甘甜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将漂泊和流浪的意义落实在自由与欢爱之息壤的觅取上,而不再作《歌女与琴师》式的不着边际的理解。《咖啡店之一夜》中的白秋英是流落到城里来的乡下女子,她的艰难的流浪生活可以说是一种血和泪的控诉;但她为的是寻找爱情,争取自由,并终于换得了相对的自主自立,于是这番流浪的酸辛与甘甜在她身上得到了统一。这部剧中的其他人物,例如林泽奇,甚至包括那些多少有点无聊的饮客,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漂泊与流浪的生存状态乃至心灵状态,从中体味到意趣深长的苦涩与甜蜜。被称为冯先生的饮客甲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但却羡慕白秋英“可以独立生活”,拥有“领略不尽的人生”,而且也很羡慕俄国盲诗人可仑斯奇,羡慕他的到处漂泊——“他的生活真是一首哀歌;一个被放逐的盲诗人,怀着吉他在异国漂泊,不就是一首很动人的诗吗?”——他,其实也是作者田汉,从这首悲情的哀歌中品味出了感伤的甜蜜。
田汉对流浪的酸辛并非缺少体验,故而他在创作中对这种酸辛的表现一般都能达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堪称其代表作品的几部剧作,对主人公漂泊和流浪的惨状都有相当的渲染:《南归》中南归诗人的褴褛衣衫,《苏州夜话》中流浪画家的泣血之泪,《古潭的声音》中诗人的心力交瘁的陈述,无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些作品绝不是诉苦之作,正如田汉从不会在庸俗意义上理解漂泊与流浪,他深藏于内心中的波希米亚情结激励着他舍弃人生的安宁与平静,向高远荒漠处寻求精神的幽栖与情感的归宿。《咖啡店之一夜》中感伤青年林泽奇的话生动地表述了田汉的这一情结:“这种没有感情的生活,没有眼泪的人生,我完全厌倦了。”——为了寻找不俗的生活,为了反抗无聊的安宁与平静,富有波希米亚情调的诗人宁可期求眼泪,因而他们绝对不会拒绝漂泊与流浪。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向往漂泊、醉心流浪本乎一个具体的情感目标或情感寄托,比方说,为了寻找爱。在《雁语》一诗中,田汉确曾表述过这样的雁鸿之志:“散沙州,近在眼帘前”,“粘土带,远在青天外”;只因“听说‘散沙无情,粘土有爱’”,便决定了:“我不落眼帘前,宁落青天外!”“向有爱的地方,寻我的光明。向有爱的地方,寻我的宿地!”这似乎是甘愿作流浪者的最能说得过去的理由,但却不是田汉通过戏剧力图说明的旨趣,只有在《环珴璘与蔷薇》中,流浪与爱的关系才被表现得那么紧密,使爱成为漂泊的目的与“宿地”,成为流浪的原动力及全部意义的载体:秦信芳在失去柳翠之后便痛感到“自己的爱不能满足,世界上便没有一处满足的地方”,于是漂泊与流浪也面临着价值的否定。在以后田汉味日趋成熟的剧作中,爱的寻找至多只成了形式上的缘由或目的,漂泊和流浪本身倒成了富有质地的精神形态。《咖啡店之一夜》中的白秋英本是为了寻找爱流浪到城里,但在没找到爱之前及爱情之梦破灭之后,她那流浪女子的气质及无可归依的精神漂泊现象照样打动人们的心:这样的魅力并不因爱的不出现或者消失而流逝。很难想象《南归》中的流浪者在得到了春姑娘的爱情后就会安顿下来过安稳日子,正象我们很难断言假如《获虎之夜》中的黄大傻得到魏莲姑就不再在村头流落;倒是《乡愁》和《古潭的声音》给我们以这样的启发:得到了爱情的人仍然羡慕“万里一身孤”的流浪情境,即使将心爱的人藏于荒庐,交给老母,生性喜漂泊的诗人还是要天南海北地流浪。《苏州夜话》中的刘叔康则倾其生命的大半于颠沛流离中寻找救国之梦实现的契机。在这些田汉味表现得最为具足的作品中,漂泊和流浪本身就是充满美的诱惑力的精神形态,它们可以超越于包括爱在内的任何现实目的或情感依托,独自向那些带有波希米亚情结的诗人及准诗人施展自身的威力。
在波希米亚情结的策动下,田汉代表剧作中的主要人物或者以爱情的追求作幌帜,或者以梦境的追寻为口实,总是将漂泊和流浪当作自己的行为取向或内心意向,——幌帜与口实仅仅就是幌帜与口实而已,其原初内容的获得或是失去往往并不影响他们流浪的热忱和漂泊的兴致。在许多波希米亚式人物的心目中,漂泊和流浪已经被抽取了上述内涵而上升为带有某种本体意义的价值形态。如果说“在戏剧中,任何身体或内心活动的幻象都统称为‘动作’”(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第3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那么,田汉体戏剧中人物的贯穿动作往往就是漂泊或流浪,《南归》、《古潭的声音》、《苏州夜话》之类典型的田汉体作品自不必说,《湖上的悲剧》也还是呈现了漂泊与流浪的罗曼司:无论是杨梦梅漂流到西湖边荒废了的庭院,还是白薇扮着游魂时隐时现,他们都习惯于相对漂泊的生存状态。如果说对于杨梦梅,漂泊的理由仍然存在,即他想找寻失落了的爱,那么,白薇的隐匿漂流却早已失去了必要性,她的父亲已确认她已经死亡,不仅不会再逼迫她嫁人,甚至也不忍心造访她当年的住处。但白薇还是隐匿漂流着,因为那样的生活太适合于她,那是她的贯穿动作,她不可能安心于普通的家居生活的舒适,当杨梦梅出现便知道爱情无望之后,她宁愿选择死亡。可以设想,杨梦梅遭遇到这样的变故,绝不会心安理得地回到妻子儿女的温謦之中,他会一刻不停地漂泊,尽管爱的彼岸已永远失去。
当然,只有作家在较为自由的创作心态中才可能完好地表现漂泊、流浪的贯穿动作,如果处在于创作的因素牵制过多,就会影响这种田汉体风格的贯彻。著名剧作《名优之死》原是为纪念飘泊在南洋孤岛上的顾梦鹤而创作的,本来完全可以将人物的动作集中于漂泊和流浪方面。但由于又深陷于波特莱尔作品的规定情境,更受到著名须生刘鸿声事迹的掣肘,田汉失去了一贯的自由表现心性,故虽表现了艺术家的生活,但其中主要人物刘振声的贯穿动作已不是流浪,即使他事实上处于流浪状态,他的心也拒绝漂泊,一心耽溺于艺术之“家”,将吃饭的“玩艺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于是,从唯美主义艺术至上观念的宣扬方面观察,《名优之死》仍能代表着田汉创作的某种范型,但从戏剧人物动作的指向看,这部剧作已悖离了田汉体戏剧的基本风格,因而失去了充当田汉体戏剧代表作的资格。“一个动作,无论是出自本能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般都趋向于未来”(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第3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而刘振声的动作则趋向于过去,趋向于昔日的辉煌;他在厌倦流浪状态的同时真切地厌倦心灵漂泊,这实际上也就自拒于戏剧,自拒于戏剧的田汉体式。
三
田汉体戏剧既以漂泊和流浪意向为人物的贯穿动作,其总体结构也就必然围绕着漂泊和流浪的行为组构,因为戏剧的“总体结构”是“由动作组成的”,它就是“以戏剧动作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虑幻的历史”。(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第3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于是,在戏剧结构中突出流浪、漂泊的动因,是田汉体剧作十分独特的风格。
戏剧的结构往往是由人物贯穿动作所构成的戏剧冲突勾勒出来的。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一部戏往往通过故事情节冲突或人物性格差异等动作途径分析其冲突的基本形态。但在典型的田汉体剧作中,人们却很难循着一般的途径发现其中的冲突形态进而总结其基本结构。田汉体戏剧总是不精心营构紧张激烈的情节,大多带有抒情剧的意味,他后期的《丽人行》、《关汉卿》等写得情节曲折,气氛紧张,乃是一般意义上的好戏,而不是典型的田汉体戏剧。同时他的作品又绝少人物性格之间的尖锐对立,即使立场相对的人物其性格往往也是相近的,《咖啡店之一夜》中存心不良的李干卿在伤感、颓废的性格表现上就与正派善良的林泽奇十分接近。考虑到田汉剧作中人物的基本动作是漂泊和流浪,作为戏剧动作之集中表现形态的戏剧冲突也就充满着漂泊、流浪的动因,而田汉体戏剧的结构特征便由此凸显出来。
田汉体戏剧最典型的代表作当然应推《南归》。这部剧作不仅直接以流浪者的漂泊行径和感伤的心迹表白为主体结构,而且还通过春姑娘的爱情抉择,将以流浪的鼓励和漂泊的向往为核心的田汉式戏剧冲突表现得极其充分。流浪的诗人,那位辛先生固然是永远的漂泊者,在他的心灵中,回归温謦的庭院还是漂流向未知的远方组构成永难止息的矛盾运动,使得他常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北方的故乡及牧羊姑娘召唤着他,但随着牧羊姑娘的遗世,故乡的雪山森林都已无法挽留他;带着对南方的秀丽及春姑娘的思念,他又来到了南方这片熟悉的村落,可得知春姑娘另有追求者,便不愿作过多的逗留,甚至不想去了解真相,又捡起手杖背着吉它走向远方。他渴望爱情,故常动念回归温柔的巢穴,然而他更留恋于漂泊行吟的生活,即使他真的得到了牧羊姑娘或春姑娘,也不会满足于甜蜜安宁的家居生活,而注定要抛别爱人向远处流浪,正像田汉在《古潭的声音》里写到过的那样。《南归》截取了辛先生在故乡和在南方两度“失恋的生活情节,将他在流浪与留连的心灵冲突中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前者,从而完成了人物波希米亚性格的塑造,进而完成了戏剧自身鼓励流浪的波希米亚风格的营构。
在《南归》中,由春姑娘对爱情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向往漂泊的意绪,也很典型地揭示了田汉式戏剧冲突的特有内涵和特定风格。这种冲突明显存在于春姑娘面对流浪者与同村少年之间的不同情感投向。她当然更爱流浪的诗人,那理由似乎就是他喜欢流浪并实践着流浪;她不爱同村少年,唯一的理由也似乎就是他从无漂泊也不想漂泊:“就怨你是从小跟我一块儿长大的啊,就怨你始终不曾离开过我,要永远守着我啊”。继而她循循善诱地告诉他诗人与他的差异:“你瞧他,他跟你是多么不同:他来,我不知他打哪儿来;他去,我不知他上哪儿去,在我的心里他就跟神一样。不管是坐着,或是站着,他的眼睛总是望着遥远遥远的地方……”春姑娘不过是个纯洁可爱的村姑,但她在戏里像艺术家和人一样表现着鼓励流浪与向往漂泊的波希米亚气质,她甚至讨厌永远守着她的人,她分明觉得,最可爱的人就应该是个漂泊者。
田汉作品的戏剧冲突往往就像这样起源于对家居生活沉寂、安宁的厌烦,而让人物滋生起漂泊、流浪和飞翔的欲望。家居与流浪的矛盾、安宁与漂泊的对垒,是田汉体戏剧基本的冲突模式,其冲突的结果,总是漂泊、流浪的凄美与感伤征服了家居、安宁的俗气与无聊。《咖啡店之一夜》中,向往流浪或处于漂泊中的人物白秋英、林泽奇就演示着凄美与感伤,而为家困扰又享受着一份安宁的人物李干卿和饮客冯先生则主要体验着庸俗、无聊,尽管后者也染上了感伤的情调,但那番情调不过减弱了两股力量冲突的烈度,以使剧作更符合田汉风格而已。《颤栗》中私生子的体验也是如此:家居的日子使他得上了神经病,在郁闷烦燥中竟然举起杀母的屠刀;当他从神经病中惊吓醒来,便知道不该贪恋家的安宁,而一想到出走,流浪,他的整个心灵便完全复苏——“这几年来在天罗地网里面抓摸着冲撞着的灵魂,好象得了解放了,我的脑筋好象清醒得多了,我要离开你老人家,离开哥哥嫂嫂,离开这罪恶的家庭,一个人去建筑我自己”。这时,漂泊的生活深深诱惑着他,他简直就变成了一个诗人:“从今以后,我不是家里的人了,我是个自由人,我是个自然之子,我是个属于光明的未来的人啊!我的路是多么长呵!我的世界多么广大呵!”《生之意志》中因失恋铩羽而归的儿子体现着《颤栗》中的私生子还未及产生这种漂泊“自觉”之前的感受:他回到家里,渴望家能医治好“心的伤痕”;但家除了给他冷遇和不理解而外,再也不能帮助他什么,他只好离家漂流;本不相信他的老父最后还是吩咐仆人出去找回少爷,但从《颤栗》可知,如果他找回,更多的悲剧将会在漫漫的人生路上等候着他和他的家庭。这两部作品,从一正一反两个角度刻画了人物所面临的留与走、家居与流浪的冲突;《生之意志》可算是《颤栗》的序幕,展演着由流浪状态进入家居状态的尴尬及无奈,而《颤栗》能算作是《生之意志》的续幕,诗意地描述着由家居状态进入流浪状态的轻快与兴奋。
如果说上述作品主要展示了体现于人物生存状态及行为选择中有关家居与流浪的外在冲突,那么,更多的时候,田汉将这种冲突内心化,这样,既强化了他的戏剧作品消解外在冲突、趋向心理抒情剧的基本特征,也深化了剧中人物心灵冲突的层次,丰富了心灵冲突的内容。实际上,当田汉刻画人物内心中留与走、家居与流浪的冲突时,他自己分明沉浸在相同的心理矛盾境况之中,这时,剧中人往往就成了他的代言者,他心中时刻波动着的波希米亚情结必然将所有的人物心态引领到漂泊、流浪之境,从而构成田汉体戏剧的典型风格。
情形往往是如此,人只要处于漂泊和流浪的状态,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倦旅之心。但在田汉笔下,这倦旅之心只用作诉说感伤情怀的契机,而不会用来作为厌腻漂泊和流浪生活的口实。典型的田汉体戏剧《南归》即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好的分寸感。流浪诗人长期处于流浪之中,经常感叹旅途的寂寞,每每想求“暂时的安息”,但他知道自己的宿命就是流浪:“我是一个永远的流浪者”,甚至在少女的温爱中也“保不定”“没有不能不离开”的那一天,人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将养他的灵魂伤痛,“我又要向遥远无边的旅途流浪”,这时,虽然感到“我寂寞,我心伤”,可分明又十分留恋这样一种孤鸿独飞的寂寞与心伤。在这位辛先生的感伤的叹息中,在田汉的波希米亚情意结中,漂泊、流浪是精神解困的不二法门,是心灵滋养的灵丹妙药,是灵魂拯救的凌虚乐园,流流之途的寂寞、伤感与漂泊之境的永恒诱惑构成了他们基本的心灵冲突和心理波动,表现这种心灵冲突和心理波动就成了田汉体戏剧必具的内容和绚丽的风采。
只要田汉仍就沉浸在田汉体戏剧的营构之中,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再安定、幸福,也会莫名地滋生起漂泊和流浪的欲望,在漂泊和流浪的永恒诱惑之下心灵的无可安宁,成了田汉体戏剧中人物正常的心理状态,有时也就成了田汉体戏剧最内在的冲突结构。如果说《南归》中辛先生因为失恋的驱使,多少还存有不断流浪的现实依据,那么,《乡愁》中孙梅对流浪之孤寂及漂泊之境的向往则纯系一种精神要求。他的安宁生活很为流浪的朋友汪右文所羡慕,可孙梅以波希米亚式的心性对汪右文表白说:“你羡慕我们有家可归,我有时反羡慕这一种‘万里一身孤’的游泳生活呢”。“万里一身孤”,正是流浪诗人辛先生所感伤地诉说的流浪之苦,而到了孙梅那里则成了值得留恋和被向往的境界,这实际上也就是作家自己内心中波希米亚情结的质直表露。辛先生的昨天也许就是孙梅的今天,而辛先生的今天则是孙梅心仪的永恒。
在田汉体戏剧中,漂泊与流浪的确以某种永恒的魔力深深地蛊惑着青年艺术家们渴望动荡的心灵,这种蛊惑力之大乃是任何世俗化安宁幸福的吸引所无法抵御的。《古潭的声音》里那个漂泊的女子因为诗人的安排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归宿,然而她发誓要拒绝一切安排,对诗人的母亲如是说:“您知道我是一个漂泊惯了的女孩子,南边,北边,黄河,扬子江,哪里不曾留过我的痕迹,可是哪里也不曾留过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好象随时随刻望着那山外的山,水外的水,世界外的世界,她刚到这一个世界,心里早又做了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准备”。她的心是这样地渴望漂泊,“连艺术的宫殿她也是住不惯的,她没有一刻子能安,她又要飞了……”当她明白尘世间再也找不到更新更奇的“世界外的世界”时,她就选择了古潭,试图到真正的“另一个世界”去漂泊,并通过古潭将她漂泊的行径载入永恒:她和诗人都意识到了,“古潭”是漂泊者的“母胎”,也是漂泊者的坟墓。
漂泊与流浪之境的向往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罗曼司,但田汉体剧作中并没有简单地将此当作纯浪漫的表现对象,而是尽可能地深彻到人物心灵、性情乃至潜意识内部去寻找心理漂泊的精神基因,故如《古潭的声音》、《颤栗》便早跳脱了浪漫主义的窠臼而进入到包含象征主义气质的“新浪漫主义”境地。纵观田汉体戏剧中人物的心理体验,流浪趋向有时根源于现实的情势压迫,漂泊情结有时则来自于内心中莫名的躁动不安。而不论哪一方面,都体现着潜藏于作者心灵深处的波希米亚情结。这种情结时时策动着漂泊和流浪,心灵的活动就围绕着漂泊、流浪而兴起的种种内心冲突。《乡愁》一剧典型地表明,人们的漂泊和流浪欲望有时则是起源于对既定生活秩序的厌烦。这出戏本没有什么情节,构成本剧中戏剧冲突的便是主人公孙梅对安宁生活的不满:他是住在田园中向往都市的那一种人,“但是都会住久了,又令人想起田园”。心悬浮在田园与都市的双重引力之间,永无安定之日,这是无形的流浪,是心灵的漂泊,是人物内心冲突的隐秘状态,也是田汉戏剧冲突的一种内在形式。悬浮于田园与都市的双重引力之间的孙梅式的心绪,实际上也就是田汉自己的体验,是他久难平息的内心冲突的具现。他曾这样解剖自己:“我时常城里住得厌了,又下乡;乡里往得不安了,又上城。我总觉得我眼里的故乡,还不能慰藉我的乡愁。我觉得我在异乡异国受了侮辱、冷遇,感着人生的凄凉的时候,我所景慕、我所希求、我所恨不得立刻投到她怀里的那个故乡,似乎比这个要光明些,要温暖些,我光景是回错了!我的灵魂他又引我到所梦想的那个故乡去了。阿!梦里的故乡!”(注:《从悲哀的国里来》,《田汉文集》第14卷。)
生活在现实的地面,却不安于宁静的栖息,一心想让灵魂往“梦想的故乡”作漂流的飞升,这是《灵光》所展示的基本戏剧冲突。主人公顾梅俪对歌德的《浮士德》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她那不安于栖息的心灵感兴正与浮士德相通:“两个心儿,唉!在我胸中居住,人心相同道心分开;人心耽溺在欢乐之中,固执着这尘浊的世界;道心猛烈地超脱凡尘,想飞到了更高的灵之地带”。心灵中时时在感受着“两个心”的冲撞,灵魂悬置于“尘浊的世界”与“更高的灵之地带”之间,这便是她内心冲突的生动写照。顾梅俪的这种悬置于世俗沉溺与高洁之境向往之间的心理状态,也正是田汉所深刻体验并时常表述的“灵肉分离”之苦的再现。田汉将自己在《新罗曼主义及其他》一文中所阐示的“灵肉分离”感兴经常交付给笔下的人物,于是《湖上的悲剧》中杨梦梅痛感到“我的心在这个世界,而身子不妨在那一个世界”,结果身子与心在互相推诿,使得他难以适从;《咖啡店之一夜》中林泽奇觉得“我既不能恶魔式地冲破社会的束缚,爱我所要爱的人;也不能真正人道主义地去勉强爱我所不爱的人”,深陷于两难之境;《灵光》中的青年男女甚至徘徊在恋爱与结婚的矛盾选择之中,其结果乃是对徘徊状态的认同。既然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他们还是“舍不得这种裨史的(romantic)生活”,便相约彼此做“生香活色的腻友”。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抒情剧”,田汉体戏剧基本将戏剧冲突安排在人物的内心冲突的表现上,有时也外化到人物之间的矛盾中;但无论是内在冲突还是外在冲突,都传达着田汉自己所具有的波希米亚取向,将漂泊和流浪当作戏剧冲突的核心内容,在相当多的情形下,也当作解决这种冲突的必由之路。
四
田汉体戏剧的基本戏剧性也就表现在这种漂泊、流浪的波希米亚风格上。“所谓‘戏剧性’,就是那些强烈的,凝结成意志和行动的内心活动;也就是一个人从萌生一种感觉到发生激烈的欲望和行动所经历的内心过程,以及由于自己或别人的行动在心灵中所引起的影响……”(注:弗莱塔克:《论戏剧情节》,第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很明显,在体现着田汉戏剧最鲜明特征的剧作中,人物强烈的内心活动总是在漂泊和流浪的诱惑下次第展开,他们的意志和行动,他们的感觉、欲望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影响,都以漂泊、流浪为基本取向。戏剧性某种意义上乃是戏剧的根本特性,漂泊、流浪的波希米亚风格既然是田汉体戏剧的基本戏剧性,也就是田汉体戏剧最根本的特性,不是所有的田汉剧作都完成了田汉体的建构,像《名优之死》这样的作品,固然情节趋于完整,结构颇为合理,但缺少了漂泊的内容,冲突也不以流浪为主线展开,就真正缺少了田汉体的戏味,缺少了田汉式抒情的精彩。进行过“自己批判”,突现了方向转换以后的田汉剧作,大多往往抽取了漂泊、流浪的内容或线索,因而即使有良好的情节结构,就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生气,而一旦这种戏剧特性略有恢复,作品便又回复了诗质,回复了灵性。
对于田汉来说,方向转换原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所心仪的漂泊和流浪之境本来就没有充实的内容和实际的目标。如果说接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方向转换的实际内容和基本目标,那么,田汉的心灵漂泊早就光顾过这样的内容和目标。对于田汉早期笔下的许多人物来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正给他们展开了一个足资流浪的空间,那里能找到罗曼司的感兴,于是,《环珴璘与蔷薇》中鼓励恋人去流浪的柳翠这样告诉秦信芳:“你听着工场里工人疲劳的声音、欢乐的声音、痛楚的声音、耶许的声音、机器转动的声音和压迫人的声音,不也可以创造一种新音乐吗?”而在有些更富于波希米亚气质的人物看来,无产阶级的那种无产无“家”的生活反而有着一种说不清的魅力,于《薜亚萝之鬼》中的大姐竹君宣布:“我想从今日起把我们所有的财产都丢掉,去做她们的战友”。
不幸的是,田汉自己恰恰也是像竹君这样看待并处理自己的转向问题的:要转换方向,就必须离开自己熟悉的艺术之家,放弃原有的戏剧性。他没有从他最擅长表现的漂泊、流浪意识出发接受无产阶级观念,而是很彻底地将这种意识视作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对之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同时当然也就排斥了以此承载无产阶级观念的可能性。正与他素有的波希米亚风格相一致,田汉一旦动念“出走”,便欲将“家”抛得干干净净:即使认识到“‘坎坷、落拓、颠沛、流离、穷困’之境”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及至无产者同一的”境地(注:《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汉文集》第14卷。),他也没有动摇抛弃这种波希米亚情调的决心。他深刻地检讨南国社长期存在的“自称‘波希米亚人’,羡慕所谓Lavvie Bohemiene(波希米亚人的生活)”的倾向,表示:“我们要完全把感伤的、怀疑的、乃至彷徨的流浪者的态度取消,自觉我们对于时代的使命!”(注:《在南国社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田汉文集》第14卷。)可见,田汉转向的严重结果是将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定性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性的,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中,他否定了以前他创作时十分迷醉的富有孤寂情调的流浪和漂泊方式;但他又不可能认同“回归”家庭,于是便鼓吹投入到“集团的斗争”。他这样清算《颤栗》中人物的“出走”与流浪行径:“以私生子的关系在家里得不着遗产的,到外面去也就注定了他的命运,就是他将以无产者的关系受支配阶级的多层的残酷的剥削,他的路没有多么长,他的世界没有多么广大,他的未来没有什么光明,只除非他认识了他正确的路线,放弃他那种小资产者的自由主义,参加广大的阶级战,向支配势力开始拚死的斗争!”他总结道:“我们既然走上一条集团的斗争的路便不应再有一条孤立的逃避的路了。”(注:《田汉戏曲集》第5集自序。)
此后,他的戏剧创作便趋向于远离乃至放弃漂泊、流浪的田汉体特性。虽然田汉还不至于像曹禺那样习惯于将戏剧情节、戏剧冲突设计在“家”的范围之内,人物也常是不安于“家居”者,不过那些不安于“家居”的人物已不再漂泊、流浪,而常常是投身到社会革命、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之中,像《年夜饭》、《梅雨》等剧作所表现的那样;那时期他所创作的电影作品也是如此,包括被他称为“开始较明确地接触到社会矛盾”(注:《影事追怀录》,《田汉文集》第11卷。)的《母性之光》及《三个摩登女性》,还有剧作《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都致力于鼓励人物离开家庭,但不去作孤独的流浪,而是投入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值得一提的还有40年代的名剧《丽人行》,作者在剧中用力最多的便是鼓励小资产阶级女性梁若英走出家庭,抛弃“安定”。她昔日的丈夫章玉良告诫她:“‘安定’下来?能吗?……民族苦难一天没有解除,个人的安定是不会有的。”梁若英终于知道不能“回那个‘家’安分守己地吃那碗‘太平饭’”了,便毅然出走。即使有的人确已流离失所,田汉在创作时也不再让他们作漫游式的漂泊、流浪,而是像《洪水》所描写的,宁愿使得他们困守在屋顶之上,展演着人间的悲惨凄苦。
除《丽人行》而外,这些剧作不仅称不上现代文艺史上的优秀之作,即使在田汉的创作成果中也属于大可忽略不计的那类:虽然还是“田汉的”作品,构思中总离不了出走的情节;但出走了又不作具有伤感、孤寂的情绪内质的漂泊和流浪,因而流失了田汉体戏剧表现流浪情境的根本特性,消湮了田汉体戏剧抒发漂泊情感的固有魅力,从而消失了田汉体戏剧的灵魂,称不上“田汉体”戏剧。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到这阶段的创作以后,一向颇具自信的田汉常检讨自己“近期”的作品,说“惭愧的是我写那些东西都是在十分忙迫的时候,信笔写去,没有经过十分的推敲”(注:《回春之曲》自序,《田汉文集》第3卷。),并明确表示对近作的不满意:“因为我的剧本多是在非常的匆忙之中写成的,所以不满意的地方很多,本来无意刊行的”(注:《黎明之前》自序,《田汉文集》第4卷。)。这些话发表在1935年至1936年之间,多少可窥见作者当时失去了戏剧“感觉”及创作兴奋点的焦灼。
由上可知,田汉清算并告别波希米亚风格而净身进入革命戏剧创作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定,但他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谓不沉重。从30年代至50年代,他的戏剧创作基本上处在这种代价的偿付之中;其间当然有一些堪称杰作的作品,它们往往体现着田汉体戏剧构思继续作用的结果。
正如上文业已阐释的那样,波希米亚风格在田汉的创作心理乃至人生心理中已积淀为某种情结,即使他在主观意识上有意摆脱它,也不能保证它就能及时、彻底地退隐而去,不再作用于剧作的构思。事实上,只要有适当的机会,这种备受田汉自己清算及防范的漂泊、流浪倾向就会以美的诱惑、生命感兴及想象力调动等途径影响到作者的创作构思,从而也就会使作品呈现出田汉体戏剧的本味。反映国外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显然正是这样的机会。田汉就此草成了《风雨归舟》、《回春之曲》。特别是在写《回春之曲》时,他几乎是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早期创作的兴奋点:让高维汉抛别恋人,只身离开遥远的南洋,投身到祖国的疆场,旋又不幸负伤,神志不清,尽管有梅娘相伴,但还是一个人在战斗的记忆中孤独地漂泊。这一份浪漫,这一份热烈,比起田汉30年代的剧作来,显然更能动人心魄,更富有久违了的田汉味。由于在全剧的戏剧动作、戏剧冲突等构思中回复了漂泊、流浪的情结呈现,这部戏成了方向转换之后硕果仅存的田汉体作品。
田汉体风味并不突出的戏剧未必不是很优秀的作品,即使在田汉的创作中也是如此:《关汉卿》被公认为50年代戏剧创作的经典;同样的道理,像《南归》、《苏州夜话》这类田汉体风格特别典型的剧作未必称得上经典,甚至未必能算是精品,即使相对于田汉自己的作品而言。但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确认田汉体戏剧风格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可能是一种可靠的价值判断依据。一个作家赖以在文学史上站住脚跟的因素当有多种,至少不应将其作品所具有的经典性意义理解为唯一因素。人们的走出政治斗争决定论的陷阱以后,往往偏执地强调作家作品的经典性之于文学史的意义,而相对忽略了那种虽然未及营造富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却对某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作出了一定开辟性贡献并形成独特影响的文学现象。田汉在现代中国所具有的稳固的文学史地位,显然并不是通过其作品的经典性获得的,而是通过他独具的艺术风格即田汉体风味所体现的:这种包含着波希米亚情结的田汉体风格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极具魅力,即使田汉自己后期某些作品的成熟与成功,也难以取代它不可动摇的美学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