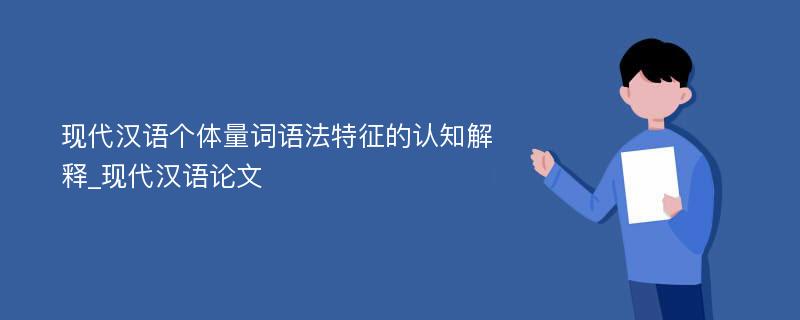
现代汉语个体量词语法特点的认知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词论文,现代汉语论文,认知论文,语法论文,个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认知语言学兴起,它认为语言结构通过人的思维认知方式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人的主观认知能力作为中介对语言结构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认知语言学在语义、语用等各个领域都提出了新概念、新见解。如原型范畴化、隐喻、象似性等,并用大量的语言事实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西方认知语言学已初具规模,而我国学者对自己母语的认知研究才刚刚起步。汉语是一种古老而复杂的语言,承载着绵延的中华文化,闪烁着汉族人智慧的思维和独特的认知方式。汉语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殊的组织规律正待人们去发掘。个体量词是汉语的特类,体现着汉族人对名词所指事物的认知方式。国外学者在其认知研究中虽对此有所涉及,但都是作为其认知语言学观点的佐证;有的虽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但范围和成果也是零星的。因此,笔者在已有的基础上尝试对汉语个体量词的词法特点作一初步的认知方面的考察。
一、个体量词的界定
大部分语法著作都没有给出“个体量词”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总是在“个体名词”与“个体量词”之间循环定义。我们认为,所谓个体量词是指计量对象为具体可感的,可以分别数出来的、在人的意识之中呈现为有界事物的量词,所以它的范围不仅包括大部分语法著作中所讲的“个体量词”,还包括所谓的“临时量词”和“准量词”。这两种量词的次类所计量的对象虽不是事物的个体,但人在认知过程中是把所称量的这部分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这一整体也是占据一定空间和时间的、可数的、有外形边界的个体有界事物,可视为“认知个体”,而与“真实个体”具有同样的认知效果。如“一池子水”,“水”虽然不是可数的事物,但“池子”一词的量化作用使之变成具体可感的有界事物,不是抽象的无色无味的客体“水”,而是“池子”大小所固定下来的水,人们头脑中就有了“一池子水”的形象,而且还会想象出“两池子水”“三池子水”的形象。又如“一世纪时间”,“时间”不是个体事物,而是抽象事物,这无庸置疑。但很明显,“一世纪时间”在人头脑中却是一个有明确起迄点的界限分明的可感事物。“世纪”一词使“时间”具体化了,可类推“两世纪时间”、“三世纪时间”,均具有个体事物的认知特点。所以“池子”、“世纪”之类的临时量词或准量词应视作个体量词。
这样,本文的“个体量词”其范围即包括一般语法书中所讲的“个体量词”、“临时量词”和“准量词”。
二、“凸显”、“有界”与数量限制
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注意程度有所不同,关注度高的事物在认知过程中被凸显出来,成为认知中的焦点映射到语言中,是句子语义的重心所在。负载新信息的句子成分易成为句子的焦点,汉语是语义重心后置的语言,句子的谓语部分,尤其是宾语、补语等往往体现着认知过程中的凸显对象。
在对量词语法特点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在三种句式中名词或名词短语前必有数量限制,我们试对此作一认知方面的解释。
第一种句式是“N1+V+了+数量+N2”,如“妈妈织了一件毛衣”,“弟弟的手划了一个口子”,“她已经写了三本书”,这种句式中的V是动作V,宾语是施事已完成了的,表结果的宾语。人们对此类句子进行认知时,受事宾语是关注度较高的新信息,是有界事物,自然需要利用数量词组的修饰限制而凸显出来。有界事物是指人根据自己身体的经验认识到个体事物占据一定的空间,可数,有外形边界,进而对认知过程中反映在人脑中的焦点事物也进行了有界与无界的分别(沈家煊1995)。“妈妈织了毛衣”“弟弟的手划了口子”不能成立是因为“毛衣、口子”是认知过程中渴望详细获得的信息,认知地位较高,所以被凸显出来。而这种凸显使得它在人脑中的形象更具体和鲜明,成为突出的有界事物,必然要求对此进行数量限制。
日本汉语学者古川裕也考察了汉语制约现象句(即存现句)和双宾句两种句式的一个共同的认知机制。古氏观察到现象句的宾语名词一般都是“数+量+名”词组而不是单个名词,且此名词不接受有定性修饰成分,如“那个、我的”之类,如“前面开过来一辆巴士”“对面走来一个人”。双宾语句的远宾语也是如此,如“蚊子叮了他一个大包”“她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前面开过来巴士”“对面走来人”,“蚊子叮了他大包”“她告诉大家秘密”均不能成立,是因为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时候,“活动”(包括“移动”)的东西较显眼,因此较容易被当作认知上的焦点而对它产生较强的反应。进而它又被感知为“有界”的东西,是一可数的个体,这样的认知特点要求语法结构为“有界”名词带上数量定语的标记。既然此时数量定语的作用是突出有界个体,那么就不必要求确切的限制量,所以存现宾语和远宾语的数量限制都是不确定的,而有定性的限制成分,如“那个、我的”之类自然与之不符,不被采用。从此推知,“他拿了一本书”之类表示不确定的普通宾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可由“凸显”及“有界”的认知观来做解释。沈阳(1995)在《数量词在名词短语移位结构中的作用与特点》一文中对数量词的作用作了详尽描写,我们认为除了可逆句式(如“十个人吃一锅饭”)是纯语义上的制约之外,其它各类移位结构中数量词的隐现机制均可由上述认知观点来阐释。沈的例句种类有:①泼了小李一身水─→*泼了小李水─→*泼了水 ②开小王一个玩笑─→*开小王玩笑 ③讨厌他一嘴黄牙─→*讨厌他黄牙─→*讨厌黄牙 ④偷了小李一辆自行车─→*偷了小李自行车─→*偷了自行车 ⑤a.我憋了一肚子气─→*我憋了气;b.憋了我一肚子气─→*憋了我气 ⑥他的腿瘸了─→*他瘸了一条腿─→?他瘸了腿 ⑦他跑丢了一只鞋─→?他跑丢了鞋(似也成立,重心是“丢”,事物是次重心,所以可用数量凸显,也可不用) ⑧那只鸟落树上了─→落树上一只鸟─→*落树上鸟 ⑨送小李一本书─→?送小李书 ⑩挂墙上一幅画─→?挂墙上画。
三、量名之间“的”字的隐现与距离性相似原则
典型的个体量词与名词中心语之间不能加“的”,如不能说“一个的苹果”,“两张的桌子”。然而个体量词系统内部的有些非原型成员却可以加上“的”修饰限制中心语名词,如“一脸的汗水”“一桌子的菜”“两国的人民”。从语言形式上来看,不带“的”的数量名结构中数量定语与名词中心语的距离要比带“的”的情况下数量定语与名词中心语的距离近。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成分之间的距离反映了所表达的概念的成分之间的距离”(Haiman 1983)。也就是说语言成分在意义上的联系越紧密,那么它们在表层形式上的联系也就越紧密。根据这种距离相似原则,最具原型性的个体量词与名词中心语的意义联系紧密于非原型性的个体量词,事实也是如此。原型性的个体量词与数词结合修饰名词时,表达的是造词的客观的数量情况,是名词事物不可缺少的性状特征之一,不会因人的主观认识而变化。而非原型性的个体量词与数词结合修饰名词时,就带上了一定的主观色彩。“一脸的汗水”“一桌子的菜”中的“一脸”、“一桌子”是“满脸”“满桌子”的意思,这种意思是主观意识所赋予的。这类个体量词体现的仍是名词的意思,而其后的名词与个体量词的关系是附着关系,并强调名词在附着对象上的范围之全、之广。一般来说,客观的性状与对性状的主观认识相比,前者与事物的概念距离较近,后者因主观因素的阻碍与事物的概念距离就远了一步。“两国的人民”之类中数量词“两国”本身就有自足的语义,可独立运用,与“一个”“一张”等典型的数量词相比,其与名词之间的粘着关系就十分松散,所以可以加“的”也是很正常的事。
四、数量之间插入形容词修饰成分的情况
现代汉语的个体量词必须先与数词结合,然后才能称量名词,数量结合十分紧密,数量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心语名词的其它修饰限制成分相并列。但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少数单音形容词可插入数量之间,如“一长条肥皂”“一大箱子书”“一薄片塑料”“一方块糖”,这固然与音节特点有关,双音及多音形容词未发现此种用法,其中也不乏认知原因。个体量词来源于事物的名词,且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与名词难舍难分。至现代汉语中,虽大部分个体量词已不再有名词的意义和用法,但却固定下来适用对象的性状类型。如“张”多用于可以铺张开来的、有延展平面的物体;“颗”多用于粒状的、个体较小的物体等。个体量词的这种特点使它具有了一种潜在的替名词划分小类的作用,在认知过程中,个体量词的出现和存在就会自然激活人脑中对某小类有具体性状特征的名词的信息。所以,人脑中个体量词与其适用对象是同一认知链条上密切相关的两个结点。单音形容词在语义上是指向中心语名词的,如“一小颗珠子”,“小”是“珠子”的属性,之所以可以放在个体量词“颗”之前,是因为个体量词本身已富于形象色彩。而“一大箱子书”之类是因为“箱子”具有名词类的原型特征,可受各种形容词修饰,这时的“大”在语义上也是指向“箱子”,而非“书”。
五、个体量词的重叠与重叠相似原则
个体量词重叠独立运用表遍指在现代汉语中十分普遍,重叠后的个体量词是语义自足的整体,也不必再粘着于数词和名词,独立表达所有个体的总和意义。个体量词能够重叠是其区别于名词的一大特点。除少数双音节的非原型性成员外,大部分个体量词皆可重叠。如“个个都是好样的”“句句都懂”。
个体量词单个出现时意义并不明确,本身也不能表现什么,只有加上数词才能表示个体的量。但重叠后功能大变,是所有个体的总和。如“他门门功课都挂了红灯”,若只用一个量词需加数词“一门功课”或“两门功课”,表示具体的量。若重叠一下用两个量词,就不需数词,而变为“门门功课”,功课的门数增加,意为所有的每门功课的总和。个体量词重叠以后概念义也增加,意为所有的每门功课的总和。个体量词重叠以后概念义也增加的情况可从认知的角度作出解释。
认知语言学中的重叠象似性机制是戴诰一(Tai 1992)基于对汉语的观察而首先明确提出的。戴将其定义为“语言表达形式的重叠(重复)对应于概念领域的重叠(重复)”,即是说表层形式的元素的量的增多代表着概念领域中相同内容的量的增多。个体量词形式上元素的增多正是与概念内容的增多相匹配的。
收稿日期:2001-02-16
标签:现代汉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