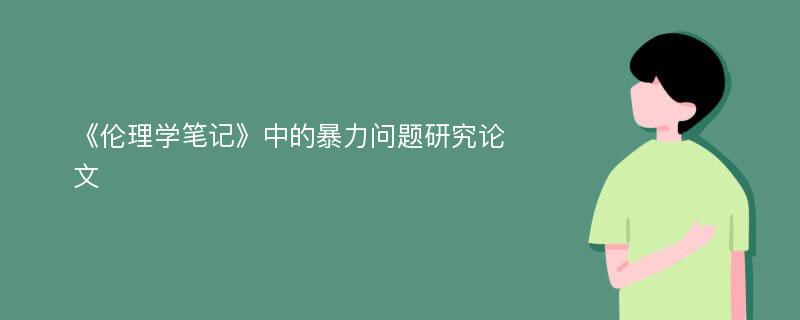
《伦理学笔记》中的暴力问题研究
崔昕昕
(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国外学者Gérard Wormser和Ronald E. Santoni对萨特《伦理学笔记》中的暴力问题展开了研究,不过他们都未对其进行细致阐释与分析,有的只是对其背景以及内容的简单勾勒。萨特的暴力是一种否定,它存在于某种被破坏的状态以及某种被摧毁的形式中,比如空的剑鞘和放到桌子上的剑。萨特指出了暴力的三种描述形式,却没有明确给出其本体论基础,不过根据萨特在本书中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暴力的本体论基础应该是自为同自在之间的关系。在萨特那里,暴力是对他者的要求,暴力需要他者承认其合法性,故此,他者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暴力与他者的关系是怎样的,这种关系是通过哪些形式展开的?进一步讲,萨特研究暴力问题的渊源在哪里?研究暴力问题是否有价值?
关键词: 萨特;《伦理学笔记》;暴力;他者
自从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萨特关于暴力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比如,德国学者Hannah Arendt在1970年《论暴力》(On Violence )论文中对萨特的暴力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是一种“新的自欺”[1];当然,也有为其辩护的,以色列学者Rivca Gordon在《回应汉娜·阿伦特对萨特暴力问题的批判》(A Response to Hannah Arendt 's Critique of Sartre 's Views on Violence )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阿伦特对萨特暴力的批判是无效的,萨特的暴力并非是自欺的,并非“暴力的新的传教士”[2]。美国学者Michael Fleming在《萨特论暴力:真的不那么暧昧吗?》(Sartre on Violence :Not So Ambivalent ?)中指出,“我认为,通过强调结构性暴力,我们有可能重新理解萨特是如何看待暴力的,从而证明萨特的工作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指南针,指引着我们在充斥着暴力的世界中定位自身。”[3]不过,学者们对萨特暴力问题的关注大多是从其《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 )、《辩证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抑或是从萨特为Fanon《天下可怜人》(Wretched of the Earth )作的序言来讨论的,很少关注萨特在《伦理学笔记》(Notebooks for an Ethics )中是如何论述暴力问题的。
法国哲学家Gérard Wormser在《建立现象学的伦理学?<伦理学笔记>中的暴力和伦理问题》(Ethique et Violence dans les "Cahiers pour une morale "de Sartre )[4]一文中,尽管分析了萨特在本书中研究暴力问题的起因,但未对其暴力内容进行细致的阐释,从而可以从整体上系统地勾勒萨特的暴力问题,并得出对暴力的看法。美国学者Ronald E. Santoni在《萨特论暴力——奇特的暧昧性》(Sartre on Violence :Curiously Ambivalent )一书中,谈及了萨特《伦理学笔记》中的暴力问题,他从对“droit”一词的分析开始,为我们对萨特《伦理学笔记》中暴力问题的研究做了指引。他指出萨特在这里坚定地将暴力定位为本体论上“与他者的关系类型”,并将其当作“在对他者的毁灭中肯定自身”的关系。暴力“指向他者的自由”[5]21,显然,Santoni指出了暴力问题有其本体论支撑,遗憾的是他也未曾对萨特在《伦理学笔记》中所论述的暴力问题做出相应的系统论述并给出自己的看法。那么,萨特在《伦理学笔记》中是如何系统分析暴力问题的,这正是本文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
何为暴力?萨特首先指出,“暴力”这个概念是从“力”的概念中衍生出来的。“通过按照事物的本质行事,力带来积极的影响。换句话说,这是积极行动的时刻或者人们依照它的积极性所思考的时刻的超越统一。”[6]170相反,暴力是一种否定,萨特以剑为例,我将剑放置到剑鞘中,正好滑入的剑,表现了我的一种力,这次操作符合剑和剑鞘的本性,所以说在这里不存在暴力。暴力存在于某种被破坏的状态中,某种被摧毁的形式中,比如空的剑鞘和放在桌子上的剑。暴力产生于力不足的地方,当使用力无法达致目的时,暴力就产生出来。比如,“如果我打开瓶子,这是力——如果我打断了它的脖子,那就是暴力。”[6]171
“哪里有部分正确的观点,哪里的暴力就是软弱。”[6]171因此,暴力暗指虚无主义,它是摧毁性的,可以通过一切手段来实施。“暴力的格言是‘目的证成手段’”,“暴力不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之一,而是通过无论什么手段而达成目的的蓄意选择。”[6]172换句话说,在暴力具有摧毁一切的特性上,它不是达成目的的“日常手段”,而是一种摧毁了任何手段的“手段”。或者说,人们一般不会通过暴力去达成手段,而当想通过任何手段达成目的的时候使用了暴力。暴力本身具有自己的证成,它通过自己声称有暴力的权利。暴力意味着每一个组织和立场都是毫无价值的。事物都是双面性的,一方面是障碍,一方面又是工具,暴力是把其当作了障碍。在暴力面前,宇宙也是一个障碍。暴力是自由的无条件的肯定。它肯定的是纯粹的虚无化自由,该自由假定人们可以摧毁世界。然而,“矛盾的是,世界永远是必要的,它作为被虚无的障碍。”[6]175这也正是萨特将暴力称之为“奇特的暧昧性”[6]176的一个方面的体现。萨特指出,暴力是“对他者的要求”[6]177,不过这里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暴力要求他者,我自己具有神圣的权利,我是自身甚至他者承认下的一种合法性的存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绝对的自由的运用;而另一方面他者也可以阻碍我。这就涉及到了暴力的本体论意义及其依据。
为了说明萨特的本体论依据,我们首先需要指出萨特对暴力的定义,“暴力是一个暧昧的概念。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它:利用其他人的事实性以及从外面来的客体来确定主体,使主体自身成为实现客体的一种无关紧要的手段。”[6]204关于暴力的本体论基础,萨特在《伦理学笔记》中并未明确给出,只是在论述过程中指出,暴力是把“世界的对象当作纯粹的密度来摧毁。”[6]176由此我们能够分析出暴力的本体论基础应该是自为同自在之间的关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区分了“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前者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后者是其所是。意识是一种自为存在,它不同于自在存在,又同自在存在处于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而自在存在同自为存在之间的区分是我们理解萨特暴力问题的基础。正如Ronald E. Santoni在《萨特论暴力——奇特的暧昧性》(Sartre on Violence :Curiously Ambivalent )中所说的那样,“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之间的关系的基本且普遍的区分以及在标志着我们同他者的本体论关系的冲突中,存有永恒的潜在暴力的分析,为之后出版的《伦理学笔记》铺平了道路。萨特在这里将暴力定位为本体论上‘与他者的关系类型’,并将其作为“在对他者的毁灭中肯定自身”的关系。暴力‘指向他者的自由’。”[5]21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萨特暴力问题的本体论依据来自于《存在与虚无》《伦理学笔记》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暴力展开研究的。这也就意味着,萨特在《伦理学笔记》中谈到的暴力并非没有本体论依据,是随性而写的。“从人出现的那一刻起,暴力就作为纯粹可能性显现在世界中。然而,为了清楚说明这一点,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描述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以便将暴力置于适当的本体论层面,而不是将其作为原罪或犯罪,而是作为与他者相关的类型。”[6]215
最后,课后辅导、布置作业也进行分层。作业的设计应该由课堂内容来指导,课堂讲到什么程度,作业就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对于A班学生,可以做思维层次高一些的习题,也需要拓展学生视野,曾加课外知识,提高数学趣味性。对B班学生,只需要解决基础问题,达到基本要求即可,可以适当放低难度,以免学生因为数学太难,而受到太大的挫折感。
二
对于萨特来讲,暴力是我们同他者的一种关系类型,在我们同他者本体论关系的冲突中,存有永恒的暴力可能性。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暴力的内涵、暴力的本体论基础、暴力的类型以及体现暴力可能性的形式,那么,暴力问题的渊源在哪里?此外,我们还需要追问萨特谈论暴力问题是否有价值?
“关于暴力的论述必须包括三个描述:第一,进攻性暴力;第二,防御性暴力(作为对非暴力行为的暴力防御);第三,反暴力。”[6]207强奸、父母对孩子的命令以及说谎等都是进攻性暴力。说谎也是另外一种暴力形式,在说谎中,也体现了暴力“奇特的暧昧性”的特征。“因此,在说谎时,我将自身置于他者的自由之中。因为我陈述了事实,所以就我所说的以及我把此事实归于我自身而言(即就我已自由地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行动而受到赞扬而言),我要求双重地被承认为自由的。”[6]195我将他者物化、客体化,要求他者承认我的自由,我利用了他者的自由,同时又否定他者的自由。
不久,竹韵悠悠醒来了,脸色惨白地对龙斌笑了笑,站起来走到电脑前,在百度搜索键上打下了杂志文章的标题,一搜索又令她气愤难当,不但这篇文章上了网,而且点击率,跟贴率极高。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大骂竹韵是骚货,是祸水,要将她拉出去斩立决,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竹韵突然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污水池里,淹得快要窒息了……
萨特以强奸以及父母对孩子的命令出发,来阐释暴力的“奇特的暧昧性”。强奸、父母对孩子的命令等暴力行为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是因为暴力具有自身的伦理学原则,它使自身合法化。甚至为了使其合法化,而否定了时间。以强奸为例,在强奸中,施暴者物化、否定他者的自由。对女孩儿的强奸是瞬时地、立即地拥有女孩儿的身体。但倘若要与女孩儿长期保持一段关系,就会破坏这种可能性。只有在瞬间中,显现与现实才是一回事。通过这种瞬间的永恒,男子将女孩儿固定在绝对中,也因此造成了自身的摧毁。所以,我们会说暴力对某些更糟糕的事情有信心。日常关系中的暴力则体现为父母直接命令孩子。在父母看来,这是一种绝对命令,小孩儿则是一种绝对禁止。在这个意义上,父亲认为孩子的自由是“较弱的自由”,自己可以进行压制,它要接受先验目的的贬低。萨特指出这种行为会体现以下两点:第一,父亲的自由压制孩子的自由,这里涉及到责任问题,也就是希望自己并不希望的事物,服从父亲的命令,责任是自由的异化。另外,单纯的父亲的暴力实际上并不能实施,这里还存在着孩子的共谋,即孩子的承认。孩子以一种不注视父亲的方式对自己的注视进行了放弃。第二,暴力并不单单停留在口头的、命令式的程度上,倘若孩子并没有顺从父亲的命令,父亲则会借助于力,这时候的力就不是力了,而演变成为一种暴力,由此,暴力关联善。在一种程度上,我们假设善已经实存,我们既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善规定着当下的秩序,这里的教育在于塑造既定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摧毁性的,孩子摧毁这种善就是暴力,对孩子的这种摧毁的组织其实也是暴力。另一种善则是后天培养的,但是孩子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善,需要借助于工具,这时他们可以借助父母对其进行认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所谓暴力其实是人对他者与世界谋求支配权的行动,而这一行动其实包含了一个基本前设:人具有裁决他者与事物在哪个层面上以及以哪种方式向人显现的权力。
祈祷、要求等是向他者请求的类型,拒绝、接受等是他者对其的回应。首先,“祈祷意味着接受。有一个事先承认的自由的操作与运作。”[6]216这就意味着在祈祷中,我服从于决定,同时悬搁其结果。他者处在绝对自由的处境中,我是在向他祈祷。一般来讲,祈祷表现为向他者祈祷,这个他者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上帝。在祈祷者的这一方,自己的自由被悬搁了,“我从一开始就接受自由等级制度。我自由的目的是次要的与无关紧要的。它们不能建立世界的秩序。我的自由只能接受这个秩序,要么通过屈服于主体的自由来维持秩序,要么就随便地扰乱它。”[6]217祈祷者是自欺的,这种自欺表现为服从,祈祷者请求获得自由,不过却是在虚无化自身的能力基础之上的。所以萨特将祈祷称之为“诗意的祈祷”:“其模糊性来自诗人没有决定如下事项:它是某种将要成为的事物还是一个实存,在任何情况下,祈祷者都知道他的欲望无论如何都不会找到一个地方……我同时还通过建立和承认一种自由的等级体系——这个自由体系将给予引入自由的存在,将存在引入实存——来摧毁作为自由意志之间的协议的人类秩序。祈祷的行为就像封建效忠,是由建立在世俗权力之上的等级的两种人所承认的。”[6]237这就意味着祈祷者幻想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向着一个全能者去祈祷,他向着“没有权利者的权利”去祈祷。萨特将祈祷称之为诗意的,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将自由之人重新放置到我们面前,而非将自由悬搁,我们需要他者的拒绝将我从想象的世界中拉回来。于是要求就产生了。
反暴力则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发生:第一,我拒绝与他者的关系。比如,将自身变成一块儿石头。第二,我拒绝时间,而接受暂时性,我在先地排斥每一种可能让我改变的手段。总而言之,“我肯定了我与我自身的同一性,我否认了成为真理,成为任何投射和变化。我是纯粹的存在,我的实存意味着与他者并肩站在一起,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拥有的是固执。”[6]214通过拒绝,我使自身从人类社区中退出。我通过摧毁同他者的关系,实现了这种反暴力。
关于暴力问题的渊源,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萨特以“主奴关系”为例谈论了要求的基础,要求的态度,要求同自由的关系。可见,主奴关系理论在萨特谈论暴力问题时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谈到主奴关系,我们不得不谈到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因为萨特的主奴关系理论是在批判、借鉴黑格尔主奴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耶夫在《黑格尔导读》中指出,“人类实在的‘出现’只有在并通过‘斗争’才能实现,这一斗争的高潮则是主奴关系。人类实在必然是植根于冲突或相互对立中的主人或奴隶的。”[7]12即无论主人还是奴隶都要求得到他者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主人的意志在奴隶那里得到彻底贯彻,奴隶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也绝不可能命令主人。主人在奴隶那里看不到另一个自我意识,他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自我意识。主人不直接面对世界,而是通过奴隶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奴隶直接和世界打交道。奴隶的权力不是来自对主人的命令(意志),而是来自对世界的改造,对物质的塑形。所以它的权力和主人无关。主人间接地依赖奴隶的劳动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主人依赖于奴隶。
萨特区分了防御性暴力与反暴力。“反暴力是对某些侵略行为或努力的反击,从而通过武力保证(国家的)安全,而防御性暴力则是针对非暴力过程的暴力求助。”[6]207我们先分析一下防御性暴力:比如在同他者讨论一个问题时,我不想与他讨论,突然间我中断了讨论,这里的暴力是通过拒绝发生的,它体现在对原有程序和进程的突然终结。而我实际上并没有告知他者,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观点。在这种防御性暴力中,“正像面对我的事实性那样(他的声音无法穿透这堵墙),我突然让他面对自己的事实性,我也突然让他面对作为一种事实的无力感,即意识的被给予的分离(虚无化的纯粹存在)。”[6]208显然,进攻性暴力的武力形式一般强于防御性暴力的武力形式。
1993年“国际人口行动”提出的“持续水—人口和可更新水的供给前景”报告认为人均水资源量少于1 700m3的国家为用水紧张国家。人均水资源量少于1 000m3为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量少于500m3为严重缺水国家。也有的认为:人均水资源量低于3 000m3为轻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低于2 000m3为中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 000m3为严重缺水。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m3为极度缺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 220m3,总体呈现轻度缺水。
萨特首先考察了要求的原初来源:究竟是普遍、无条件的义务还是在一个人对另一人的要求中诞生的?要求意味着绝对命令。命令无视处境,是绝对的。“因此,正是内在的通过处境来看,命令是不会得到修改的(即通过手段)。”[6]238命令相关实现它的手段与目的。在谈及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时,萨特批评了某种行事的本体论与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将人原初地封闭在自身的整体即世界中。人先天地具有目的,世界只是人去实现这些目的的无关紧要的手段。萨特指出,“人在朝向世界超越世界的过程中构建他自身,那么,目的与手段都变得难以分辨。”[6]241谈及目的,就会涉及价值、自由。目的是价值,因为目的欠缺我,我也欠缺它。同时它是我自身必须成为的东西。不过“它被返回到我的价值所萦绕,即被我的这一价值投射到存在所萦绕。”[6]248然而,萨特接着指出,“价值不是要成为的一种要求,也不是一种要成为的权利。它是一个不同的类型,即使它是对存在的一个宣称。”[7]249也就是说,我们追求的是目的而非价值,价值处在我目的的乐观的远处,我们看到的、实现的只是目的。萨特以主奴关系为例谈论了要求的基础,要求的态度,要求同自由的关系。自由诞生于要求的基础之上,要求的存在是那个被称之为“一”的存在。“要求首先作为他者的自由和我的自由的直接关系……要求不是我自由的结构,不是我投射的目的可以承担的形式,而是通过另一种形式而走向我……正是这种散居的单一形式,使我和他者一起显现,这种形式通过将我的意志制造为一个为他的对象,必然地构建了要求的基础,而他者是为我的一个对象。要求的原初形式是他者。”[6]261可见,要求必然涉及他者,要求意味着我与他者一同出现。然而,由于我们永远在异化,这种异化的自由好似责任,自身是非人格化的,“责任伦理就是奴隶的伦理”。要求者是自欺的,因为要求具有如下两个双重特性:“一是使我服从(在与被要求的目的相关联时,我是手段);二是拯救我免于被抛弃(目的在实存中支撑其自身,甚至反对我;我是优先的手段,我没有责任使其作为目的而存在,而只是在世界中意识到它),所以任何要求都没有踪迹可寻。”[6]250萨特认为要求是对服从的要求,在要求之中,具体的个人消失了,有的只是整体。它会让我们产生一个整体意愿,好像这种意愿是我们每个个人的意愿那样,个人在要求中被异化了,被蒙骗了,要求意味着不使用暴力,意味着对完善的“一”的绝对服从就可以达到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责任伦理学”。然而,这是无法实现的,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必须诉诸暴力才能解决问题。进一步讲,从暴力的三种形式可以看出,施暴者只追求从事物中寻求投合自身的意愿与形式的方面,只是单方面地欲求权力,尽管施暴者在否定他者自由的同时也肯定了他者的自由,但这只是一种必然且无为的结果。
三
我们已经看到,在萨特那里,暴力是“奇特的暧昧性”的,是与他者关系的一种类型。那么,暴力有几种类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由此种方式确立的暴力究竟是怎样的?
无论是进攻性暴力、防御性暴力抑或反暴力,其最终的结果都是摧毁性的,针对这一点,Ronald E. Santoni说,“暴力的最终图解是‘以暴制暴’”[5]27。任何形式的暴力展现出来的都是“双重否定”,是对人类现实的排斥与摧毁。暴力的产生源于人与人之间处境的不对称,正是这种不对称,产生了压迫。虽然萨特在一开始谈论暴力的时候并未谈及压迫,但这并不意味着压迫无关紧要,压迫实则是暴力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种形式。萨特在《伦理学笔记》中指出了压迫的五个本体论条件:“第一,压迫来自自由……第二,压迫来自多样的自由……第三,压迫只能通过另一种自由来实现一种自由,只有一种自由可以限制另一种自由。第四,压迫意味着奴隶和暴君都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的自由……第五,压迫者和受压迫者是共谋的。”[6]325那么,在压迫这一与他者的关系中,“产生出了作用于他者身上的不同种类主张:祈祷、呼吁、期望、提议、要求以及他者的回应:拒绝或同意。威胁。蔑视。”[6]215这些形式其实是为暴力服务的权利形式,是体现暴力的方式。
我们从萨特关于暴力的分析中,看到了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对萨特所产生的影响,正是在这种主奴关系理论的根基上,萨特才得以建立其暴力的理论。不过这绝不意味着萨特完全支持其理论,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萨特反驳道,“我描述了我与他者的关系。但是还有第三个要素:他者。我绝对不能单独面对君主。第一,领导者或君主,他的帮助者或直系的下属,通过相互承认在我眼前创造出一套无条件的自由(这是黑格尔忘记的一个层面,而且在这里不需要描述,除非说相互承认自由的理想从不会在建立在压迫之上的社会中缺席)。”[6]268简言之,萨特认为黑格尔在谈论主奴关系时,忘记了一个维度,即他者。因为我们无法独自地面对君主或者领导者,所以我们需要相互承认自由的理想,正是这种相互承认产生了无条件自由。萨特接着指出,“黑格尔的本体论乐观主义主张,我发现我的意识在“我=我”的形式下以及在他者那里不会改变。但是我已经证明,实际上通过逆转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行动的结果将会是纯粹的,并且仅仅是他者的统治。”[6]270所以这种黑格尔式的通过主奴关系所构建的整体性在萨特那里是无法实现的,即黑格尔忽视了他者的他性。在《伦理学笔记》中我们也看到了萨特在论述暴力时,指出了施暴者在施暴时是自欺的,他对被施暴者采取的行动是对其否定、物化,不过在摧毁他者自由的同时,相应地也证明了他者的自由。这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中是没有的。
承接上述分析,我们需要指出《存在与虚无》中的他者问题。因为萨特在《伦理学笔记》中指出黑格尔忘记了他者的维度,即忽视了我们同他者的“共在”,同时也忽视了他者的他性,这些理论实则源于《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对我与他者冲突关系的思考。萨特指出,“人的实在无法摆脱这两难处境:或者超越别人或被别人所超越。意识间关系的本质不是‘共在’,而是冲突……冲突是为他的存在的原始意义。”[8]524由于他者的注视,我发现了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通过他人的注视,我体验到自己是没于世界而被凝固的,是在危险之中、是无法挽回的”。[8]446他者的注视使我的世界去中心化,我发现自身被对象化,成为他者眼中的一个对象,这使我体验到了在我之外同我的世界相异的世界的存在,我自身也发生了异化,我的存在此刻变成为他的存在。然而,我不会满足于这种被对象化的局面,我也会注视他者,使他者的世界去中心化,使他成为为我的存在,简言之,就是超越他的超越。这时,我们就可以通过暴力来实现对他者的超越。
饱和输出灰度值随电子注量的变化规律,如图3所示,不同辐照偏置条件下器件的退化趋势相似,即随电子注量增加饱和输出灰度值不断减小,说明饱和输出灰度值对电离总剂量敏感。
关于萨特在《伦理学笔记》中对暴力问题的讨论同其《存在与虚无》中的与他者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分析,笔者比较同意Ronald E. Santoni在《萨特论暴力——奇特的暧昧性》(Sartre on Violenc e : Curiously Ambivalent )中所分析的,“尽管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并未使用‘暴力’一词来刻画我或他者尝试‘偷窃’,吸取,同化,或者收回我或他者的自由,显然,这些相互侵犯似乎是主张使用‘暴力’这一字眼,因为从词源上来看,‘暴力’一词来源于to violate (violare)——在这种情况下,侵犯自由且有意识的主体……暴力位于我的‘原初坠落’与我的原初‘为他者存在’的核心处,提议这一点这并不极端。然而,我下面想要强调一个限定点。前面对冲突的分析建基于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解释,但是之后他将这一工作指涉为‘转变前的本体论’,他认为‘转变是必要的,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在《存在与虚无》后半部分的脚注中,萨特告诉我们他之前的分析‘不排除拯救与救赎伦理学的可能性’,这一点‘仅仅通过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而稍后会讨论的激进的转变’就可以到来。”[5]19
四
在回答萨特谈论暴力问题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证明的是《伦理学笔记》一书是否有价值?萨特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曾在《存在与虚无》的末尾谈到将写一部关于现象学的大约500页的书,不过是要从伦理学角度来谈,这本书就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出版之后的四五年时间写成而生前却未发表的《伦理学笔记》。萨特使用“笔记”一词,是否意味着在萨特的《伦理学笔记》一书中没有成系统的体系,有的只是零散的想法,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学者Thomas C. Anderson在《萨特的两种伦理学》(Sartre ’s Two Ethics )中,指出“未出版的将近600页的《伦理学笔记》依然是最全面的来源,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萨特的第一种伦理学。”[9]《伦理学笔记》相较于《存在与虚无》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萨特对意识的分析,《伦理学笔记》中的意识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意向性,而是一种浸入式的,位于世界之中的意识。行动也是在世界之中的对物质世界的改变,而非仅停留于抽象的层面上。因此,萨特的《伦理学笔记》是对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尝试,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学轨迹。正如美国学者Sonia Kruks在《萨特的<伦理学笔记>:伦理学中失败的尝试还是新的轨迹?》(Sartre 's Cahiers pour une morale :Failed Attempt or New Trajectory in Ethics ?)中所说的那样,“对我们来说,《伦理学笔记》不仅仅是萨特的死胡同。它们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哲学和政治轨迹的开创性表达。”[10]
尼采曾经对建筑有过表述: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
暴力问题在《伦理学笔记》中又处于怎样的一种位置呢?研究暴力问题是延续《存在与虚无》中“为他”的分析。萨特想要做的是,让我们理解“从人出现的那一刻起,暴力就作为纯粹可能性显现在世界中。”[6]215它是我们与他者的一种关系类型,是揭露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种途径。我们通过分析暴力问题可以清晰地看到暴力是暧昧性的,施暴者在否定他者自由的同时,也肯定了他者的自由。萨特哲学研究专家David Pellauer在《伦理学笔记》的译者导言中,指出了萨特这本书的三大主题,分别是:历史问题、压迫与异化的区别以及自由的辩证法。其中第二个主题中的压迫就是暴力的一种类型,所以研究暴力问题对《伦理学笔记》一书的整体勾勒是十分必要的,它在整本书中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暴力问题既开启了萨特对历史的分析,又为自由辩证法的提出做了铺垫。
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基础较好,优势凸显,但核心区空间约束严重,扩展区小园区大产业模式相对薄弱,西部药谷尚在起步,产业链薄弱环节明显,整个产业链外向性欠缺。因此,促进产业空间整合,培育产业链各环节的核心竞争力,必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科研、技术、工艺、服务等方面的弱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高效持续发展。当然,因为无法获取全部企业的发展大数据,产业链内部如何有效实现功能互补和优势重组,还需要全面、深入地调研和进一步分析。
小结
让我们总结一下前面已经得到的结论。在萨特那里暴力是“奇特的暧昧性”的,暴力是与他者的一种关系类型。暴力是一种否定,它源于力又同力相区分。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的区别是暴力得以产生的本体论基础。暴力有三种展开形式:进攻性暴力,防御性暴力,以及反暴力。而祈祷、要求等是体现暴力的方式,同时也是对他者的要求,他者对其的回应是拒绝、接受等。萨特谈论暴力问题源于对黑格尔主奴关系理论的分析与发展,从而暴力这一同他者的关系类型,既有与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相同的地方,也有其不同。当然,萨特在《伦理学笔记》中谈及暴力,同《存在与虚无》中的我们同他者的“冲突”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冲突”的存在,才有分析暴力问题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萨特谈论暴力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在《伦理学笔记》中所谈论的暴力尽管内容冗杂,论点分散,但经过仔细分析、提炼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萨特在此向我们所展示的相关
思想:暴力是一种否定,但更准确地说,在笔者看来,它是片面的肯定。从暴力的形式,如强奸、父母对孩子的指令来看,其要求他者与事物只是以其自身意愿的形式呈现,这等于截断了他者与事物存在的其他向度向其显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J].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1970:20.
[2] Rivca Gordon.A Response to Hannah Arendt 's Critique of Sartre 's Views on Violence [J]. 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 2001(1):69-80.
[3] Michael Fleming.Sartre on Violence :Not So Ambivalent ?[J].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 2011(1):20-40.
[4] Gérard Wormser. 建立现象学的伦理学?《伦理学笔记》中的暴力和伦理问题[C].“萨特与当代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2005: 38-54.
[5] Ronald E. Santoni.Sartre on violence :curiously ambivalent [M].Philadelph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University Park, 2003:19-27.
[6] Jean-Paul Sartre.Notebooks for an Ethics [M]. David Pellauer,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70-325.
[7] Alexandre Kojève.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M]. trans. James H. Nichols J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12.
[8] [法]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7:446-524.
[9] Thomas C. Anderson:Sartre’s Two Ethics[M]. Chicago: Open Court, 1993:43.
[10] Sonia Kruks.Sartre 's Cahiers pour une morale :Failed Attempt or New Trajectory in Ethics ?[M].Durham,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86:184-194.
AnInvestigation on Violence in Satre ’s Notebooks for an Ethics
CUI Xin-xin
(College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China )
Abstract : Gérard Wormser and Ronald E. Santoni have studied the violence in Sartre's Notebooks for an Ethics , but they haven’t elaborated and analyzed it concretely. They just outlined of its background and content. Sartre's violence is a kind of negation, which exists in a state of damage and in some form of destruction, such as an empty scabbard and a sword placed on the table. Sartre pointed out three descriptions of violence, but did not explicitly give its ontological basis. However, according to Sartre's analysis in this book,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ontological basis of violence sh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itself and in-itself. For Sartre, violence is a demand on others, and violence requires the other to recognize its legitimacy. Therefore, the other is essential. The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olence and the other, and what form does the relationship take? Furthermore, where is the source of Sartre's investigation on violence? Is it worthwhile to study violence?
Key words :Sartre;Notebooks for an Ethics ; violence; other
收稿日期: 2019-03-25
作者简介: 崔昕昕(1991- ),女,河北省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法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9)02-001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