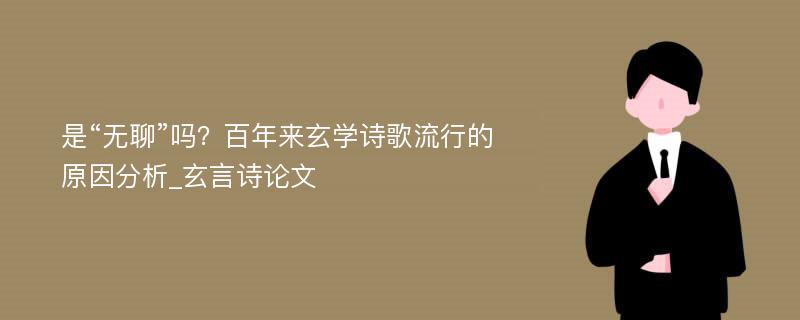
“淡乎寡味”吗?——玄言诗风行百年原因试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原因论文,淡乎寡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玄言诗在文学史上评价历来很低。人们往往认为,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序》),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种诗在西晋永嘉年间至晋宋之交的一百多年里竟然风靡了诗坛,成为当时诗界的主潮。怎么来理解这一现象?我以为其中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关键还在美学方面。因为任何一种文学所以能够流行主要取决于它所提供的美能否满足当时读者的审美需求。
一
玄言诗到底有没有诗味?应该怎样理解玄言诗的诗味?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应该如何看待诗歌美的问题,也是解开玄言诗风行之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钟嵘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玄言诗“淡乎寡味”,是没有多少诗意的,这可以说代表了南朝以后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然而晋人(主要指东晋,也包括西晋末。下同)却不这样看。我们只要从玄言诗风行一时的盛况及玄言诗代表作家孙绰、许询在当时文坛所享有的地位来看,就可以判定,晋人对于玄言诗不但不觉得“寡味”,相反倒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看来,这里的关键在人们对诗味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
我们先来看钟嵘所谓的“味”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味”论诗是钟嵘诗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味”《诗品序》谓: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我们再结合《诗品》全书对各家诗的品评看,就是指包孕在诗中的感情、形象、文采、风力以及赋比兴等因素。总之,都是指诗的感性特征。在钟嵘看来,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才算是有诗味的,才是“诗之至”,反之,就是“寡味”的。以此为标准,玄言诗显然不合要求,自然也就“寡味”。
晋人的看法与钟嵘不同。晋人没有就诗味作过直接的论述,我们只能通过晋人的审美观来寻绎他们对诗味的看法。我以为支配晋人审美趣味的是一种玄学美学观。这种美学观的核心是把“道”视为天地间的至美。这样,晋人的审美观也就具备了如下两个基本特征:
一、在形神关系上有重神轻形倾向。道家认为,“道”是隐蔽的,内在的,它恍恍惚惚,无形无迹,不可名状。“道”虽是万物之源,但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无法穷尽它。因此,在审美上,老子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命题。(《老子》41章)在他看来,大美是与“道”合一的,是难以用形迹来表现的,具体的音符或形象虽能反映“大音”、“大象”之一体,却不可能充分反映它的全体。而且按照王弼的看法,“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有形则有分,有分者,不温则凉,不炎则寒。”(《老子注》41章)这就意味着感性形态越是明确、具体,意义就越小,就越是不能体现内在的美。这样,在美的表现上,最佳选择就不是色彩鲜明而只能是素朴含蓄,平淡无味,这也就是老子说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35章)的意思。这个思想又进一步在魏晋玄学的有关命题中获得了支持。例如有无之辩中贵无论就认为宇宙万物以无为本,有生于无,却不能穷尽无,有虽然丰富多彩,却是短暂的、有限的,无才是永恒的、无限的。人们不应执滞于有,而应超越有,才能把握无。言意之辩中的言不尽意论也有类似看法:意涵是无限的,语言是有限的,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意,却不可能充分地达意,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入门的向导,对读者起某种暗示作用。人们应该得意忘言,也就是既通过言,又超越言,以此来把握意涵。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形神关系作了充分论证,从而为重神轻形的美学观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这就是说,在晋人看来,美首先是内在的,形迹之美是次要的,是为神服务的。既然形难以穷尽神,那么从美的表现角度说,就应以平淡无味为美;从美的欣赏角度看,则既要利用形迹,更要超越形迹才能直接感知、把握内在的美。这种倾向在当时审美活动中有明显的表现。如在人物品藻方面,晋人虽也比较赞赏人物的姿容美,但他们更看重的是人物内在的风神之美。《世说新语·品藻》载桓伊对卫玠与杜弘治的评价:“弘治肤清,卫虎奕奕神令”,意谓杜皮肤白皙,美在形貌,卫奕奕有神,美在精神,形神相较,神美高于形美。对此,谢尚说得更明确,指出杜根本不能与卫相提并论,“安得此!其间可容数人。”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一般人的观点,因此被认为是“知言”。绘画亦如此。晋人画风一般略于形迹,而以传神为鹄的。如卫协被认为是“不该备形似”,张墨、荀勗虽然“风范气韵极妙参神”,但“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谢赫《古画品录》)顾恺之则说:“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说明在顾的观念中“传神”是第一位的。他所以重视画眼睛,就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最能传神。至于四体的描画,是作大胆的夸张,抑或作必要的省略一视传神的需要而定,而不以外形的逼肖为准。这种“略其玄黄,取其俊逸”的审美观对玄言诗内容、风貌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在情理关系上有重理轻情的观念。晋人重玄理,重悟道,有很强的思辩能力。他们不仅著书立说,而且互相辩驳问难(清谈),风气所及以至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似乎谁如果不懂玄理,不会清谈就不够做名士的资格。可以这样说,就晋人对哲理兴趣的浓厚程度及哲学在社会上的影响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恐怕还很少有哪一个朝代能与之媲美。这一点似乎不必赘言。问题是晋人对情感的态度似乎比较复杂。一般认为晋人在实际生活中是多情,钟情,深于情的,这在《世说新语》中有很多材料可以加以证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当晋人把情与理放在一起作理性判断时,他们又觉得理重情轻。其实这种观念首先来源于老庄。老子虽未直接论述过情,但在他以道为本,清静寡欲,顺应自然的思想中包含着无情论的因子。庄子是明确的无情论者。他以追求绝对自由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主张人应保持主体独立性,应“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在他看来,人受外物刺激而动情是“物于物”的表现。人们只有解除情的束缚,“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大宗师》),淡泊宁静,“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德充符》),才能免除痛苦,获得解脱,此即所谓“悬解”(《大宗师》)。其次,在玄学讨论的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问题中也反映了这种观念。圣人无情论这里暂且不论。即使是圣人有情论者实际也持理重情轻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圣人既同于普通人,又超出普通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魏志·钟会传》注)这也就是说,倘若仅只具备五情,还不足以与普通人相区别,圣人之所以为圣,所以能超越众人,关键就在“神明茂”,亦即达到悟道的境界,具备了洞彻世事的大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应物而无累于物”,达于自由逍遥之境。这样看来,理仍然是高于情的。再则,两晋人士对名士风度的不同态度也能反映出重理观念的强化。作为对汉代儒家礼治的反拨,西晋前期(武、惠之时)士人普遍以纵情放达,蔑弃礼法为风尚。嵇康公然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阮籍也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士人多以饮酒、服药、裸裎为时髦。至东晋则风气转变,士人不再以放诞为高。人们所赞赏的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感情有所节制的优雅风度,像谢安那样当淝水激战时从容镇定地与人下棋,捷报传来虽内心狂喜却“意色举止,不异于常”;王献之当屋子失火,人们惊惶走避时,却“神色恬然”,从容不迫(《世说新语·雅量》),这种风度是受到时人称赞,得到高度评价的。在东晋士人的这种态度里,实际隐含着这样的观念:淡泊宁静,从容安详是境界高远,悟道的表现,“达节之人”就应是“能与道化推移而不以哀乐为心”(袁宏《后汉记》七)。相反,人若执着于情,为情所左右,则无异于为物所支配,是不够通达的表现。可见,在晋人看来,在情理关系上,美主要并不体现在感情的浓烈上,而在于一种了悟大道的智慧,这正可说明玄言诗以理为主,淡于情感的原因。
以上我们对晋人审美观作了初步梳理,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抽绎出他们审美趣味的特点。这就是以内在智慧(哲理)为美,以平淡无味为美,这也可以认为是晋人对诗的看法。如与钟嵘诗味观对照,他们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钟嵘之味重在感情形态,晋人之味重在理性内容(不意味完全排弃感性成份)。总之,玄言诗是这种审美观念的产物,而玄言诗一旦产生又进一步满足了晋人的这种审美需求。
二
玄言诗的诗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进一步来验证一下上文的结论。
既然审美趣味是相对的,那我们不妨调整一下阅读心态,尽可能地从晋人审美立场去阅读玄言诗。
从内容看,玄言诗实是一种哲理诗,它以老庄玄理为内容。因此人们常常把玄言诗称为押韵的哲学讲义,这种看法不免失于简单。玄言诗虽然以阐玄说理为主,然而它毕竟与哲学论文有所不同。如果说哲学论文是把哲理作为认识对象,以使人接受为目的的话,那么玄言诗则是在读者对哲理已有充分理解的前提下,进一步把哲理作为审美对象,以供人欣赏为目的。以鉴赏为主是玄言诗同一般哲学讲义间的最大区别。玄言诗的读者与作者往往是合一的,这些人大抵对玄学有相当修养,有些本身就是玄学家,他们对玄学命题不仅相当熟悉,而且还有较深入的研究。他们在哲学论文和清谈之外之所以还需要玄言诗,决不是为了到玄言诗中来弄明白玄理的涵义,而主要是想通过玄言诗来欣赏、体味哲理的美,“宅心辽廊,咀嚼妙一”(孙绰《答许询》之四(注:本文所引汉魏六朝诗均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版。)),以求得精神上的愉悦。因此,阅读玄言诗就主要不是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认识活动,而主要是一种以愉悦精神为目的的审美活动。换言之,晋人所以会对玄言诗表现出如此的兴趣,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玄言诗向人们提供了从审美角度去审视哲理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哲学论文所不能替代的。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这样说:玄言诗对中国诗史的贡献就在于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在传统诗歌的审美范围之外,又拓展出一片新领地——哲理。玄言诗在内容上也就随之产生了两个特点。
一、意蕴的深厚性。这是由玄言诗的题材、内容所决定的。相对于其它题材的诗歌,玄言诗既以哲理为内容,它的内涵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深度。哲理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深刻性,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倾注较多的注意力,通过反复的解读,逐渐开掘出蕴含其中的意义。例如: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孙绰《答许询》)
像这样的诗用简洁的文句表达一种祸福相依、得失互补的哲理,充满了一种相反相成的辩证精神。既是从生活中概括出来,又高出于一般的生活道理,而透着一种悟道的意味。简明含蓄,需要含咏咀嚼方能领略其中的佳妙。玄言诗中更多的是一些散见于诗中的格言、警句,如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如:
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王羲之《答许询》)言以忘得,交以淡成。《郭璞《赠温峤》)愠在有身,乐在忘生。(孙绰《答许询》)朴以凋残,实由英翦。捷径交轸,荒途莫践。(孙绰《赠谢安》)
或论人生态度,或述悟道方法,或从日常生活中体悟玄理,无不意味深长,富有意趣,耐得咀嚼,可堪玩味。这样看来,与其它种类的诗歌相比,玄言诗固然在形象、情感方面比较欠缺,然而在意蕴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方面却自有它不可否认的优势与魅力。玄言诗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意义可供不断开掘的可能性。读者在解读过程中投入的主观能动性虽较其它种类的诗歌为大,但只要他一旦有所领悟,往往就会产生一种悠然意远,余味无穷的审美体验,这也就增加了阅读的乐趣,产生一种智慧的欢乐。读玄言诗的感觉是与读某些“文憎过意”,了无余味的南朝诗(主要指咏物诗、宫体诗等)的感觉迥异其趣的。我想,这也许就是玄言诗最主要的魅力所在。
二、直观感悟性。尽管从所表现的思想来看玄言诗是理性的,但是这些哲理在诗中却不是抽象的,它总具有一定的感性色彩。这首先表现在玄言诗的主题上。玄言诗并不就是玄学思想的简单传声筒。不同于哲学论文对玄学论争,玄言诗中的玄理却是经过选择的,它对于某些距离现实较远,或过于抽象的问题,几乎没有或很少加以反映,从现存的玄言诗来看,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围绕着人生哲理而展开的。例如:
仰想虚舟说,俯叹世上宾。朝荣虽云乐,夕弊理自因。(庾蕴《兰亭诗》)
朝荣夕弊,盛极而衰,这是生活中极普通的现象,然而作者却从中引发出一种生命短暂,人生虚无的感叹,这就带有一种哲学的意味。这也是从《古诗十九首》以来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的看法。这种观念是根本性的,它决定了晋人在人生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
峩峩高门,鬼窥其庭。弈弈华轮,路险则倾。前辀摧轴,后鸾振铃。将队(引者按,疑当为“坠”)竞奔,诲在临颈。达人始悟,外身遗荣。(孙绰《答许询》)
这首诗用比兴手法阐述作者的生活态度。他感叹世道险恶,而人们多识不透这层道理,纷纷追名逐利,到头来反丧失了身家性命。诗人由此领悟,欲望(“身”、“荣”)才是一切危险的祸根。要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上确保安全,唯一的良方就是“外身遗荣”。这样,表面上似乎舍弃了功名利禄,实际上却是保全功名利禄的最好办法,“遗荣荣在,外身身全。”(《答许询》之三)所传达的同样也是老子的思想:清静寡欲,“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7章)如果说孙绰这种以退为进的人生态度还只是出于应对险恶环境的策略考虑的话,那么王羲之逍遥高蹈的风度则源于他更深层的哲学思考:
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緾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兰亭诗》)
面对运转不息的宇宙万化,自觉人力微弱,与其妄费心力,纠緾于名缰利索,不如随顺自然,委运乘化,逍遥酒脱地应对人生。玄言诗中还有不少直接表现诗人生活情趣的诗。他们徜徉于自然山水之中,从中领受到一份乐趣。“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人室鸣琴”(谢安《与王胡之》),潇洒脱俗,遗落世事,是一种充分艺术化的生活。“望岩怀逸许,临流想奇庄”(孙嗣《兰亭诗》),“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庾友《兰亭诗》),则又在自然美景中怀想古人,体悟玄理。可见,玄言诗固然以阐发玄理为主,但这玄理大抵是从生活感受中提升而来,是一种人生的感喟。与当时那种“校练名理”,辩析精密的哲学论文相比,玄言诗中的玄理就似乎带着更多的人情味和烟火气,而不是那种灰色的理论教条。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于哲学论文之外还需要玄言诗的又一个原因。其次,玄言诗的直观感悟性还表现在哲理的表述方式上。如上所述,玄言诗中的哲理是以读者的充分理解为前提的。因而,玄言诗对哲理的表述就不是论证式的,而只是一种感叹;不是抽象的思辩,而是始终结合着表象的思考;不是诉诸于读者的知性解析能力,而是作用于他们的直觉感悟能力。
鲜冰玉凝,遇阳则消。素雪珠丽,洁不崇朝。膏以朗煎,兰由芳凋。哲人悟之,和任不摽。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雪霄。(谢安《与王胡之》之一)
表现和光同尘的生活态度却用着一连串普通生活现象作比,通过表象来感悟人生哲理。还有些作品则用咏史的题材,通过对古人古事的吟咏来阐发哲理。
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二过。愿弘玄契,废疾高卧。(王胡之《答谢安》之七)
巢父、许由、伯夷、叔齐是历史上有名的避世的隐士,稷、契、太公则是入世的典范。按照一般的看法,出处对立,仕隐相斥,但作者却在对历史人物的追怀中表达了“各乘其道,两无二过”,出世、入世互不排弃,各有其道的看法,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儒玄合流,出处兼融,自然名教合一的思想。还有一部分诗则从山水景物中来体味哲理。
峩峩太行,凌虚抗势。天岭交气,窈然无际。澄流入神,玄谷应契。四象悟心,幽人来憇。(袁宏《从征行方头山》)
在对大自然的欣赏中获得了某种启示,含蓄地表达了蕴含在山水之乐中的意趣。所谓“山水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描画的尽管是自然景色,目的却在体味孕含其中的玄机妙理。玄言诗中大多数抒发人生感叹的诗都或多或少地浸染着一定的情感色彩,如王羲之《兰亭诗》:
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
慨叹时节如流,一往不返,生命如白驹之过隙,使人联想到他在《兰亭集序》里发出的“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样痛彻肺腑的悲叹。还有李充的《送许从》:
来若迅风欢,逝若归云征。离合理之常,聚散安足惊。
在送别中说理,表面上似乎平静达观,然而从友人来时的欢欣中也就不难推想到分别时的悲伤,哲理在这里成了一种对离情的慰藉和对痛苦的摆脱,实际上也不妨可以视为一种曲折的抒情。
从形式上看,玄言诗与其它种类诗相区别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平淡朴拙的风格。钟嵘评孙绰、许询诗曰:“弥善恬淡之词。”(《诗品》)其实不仅孙、许诗如此,整个玄言诗的风格就是如此。所谓平淡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藻饰,表现为质朴,少文采,具有一种朴素美;一是相对于繁复,表现为简约、含蓄,有一种言近旨远的审美效果。《世说新语·文学》载阮孚对郭璞的两句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大为激赏,赞曰:“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其实,如果仅就修辞技巧论,这两句诗不过只是白描很难说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它所以能予以“神超形越”的感觉,一方面取决于读者自身的哲学思考力,一方面则是由于诗句本身质朴、含蓄的风格,能在要言不烦中提供一种意象,给人某种暗示,从而使人展开联想,并最终领悟到一种运动不止、瞬息万变的哲理。这样,透过诗的表层意义也就可以进一步开掘出它的深层含意。我们在上文的例证所提到的一些玄言诗也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种风格。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绝大多数的玄言诗都采用四言体式。众所周知,建安以来五言诗逐渐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四言诗实际上已退居次要位置。玄言诗人为什么偏偏对四言体诗情有独钟呢?我以为这同玄言诗人对平淡朴拙风格的追求有关。四言诗在风格上一般比较质朴含蓄,庄重肃穆,钟嵘以为“文约意广”(《诗品序》),李白亦认为“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孟棨《本事诗》引)。四言诗的这种特点与玄言诗的内容非常合拍,也能较好地体现玄言诗人的美学崇尚。当然,还需要指出玄言诗的朴拙平淡风格并不意味着晋人缺乏审美能力与修辞技巧。我们从《世说新语》的有关记载中可以发现哲理美、自然美、人格美的意识在晋人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而在辞采的运用上,晋人也决不是无能之辈。史载孙绰、许询、郭璞、袁弘、殷仲文等玄言诗代表作家都是“雅有才藻”、“文藻粲丽”、“文章绝丽”(参《世说新语·文学》及注引),孙绰甚至以作《天台山赋》而自我陶醉,语人曰:“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世说新语·文学》)我们从孙、许现存的一些诗中也可以发现他们颇有一些讲究辞采之作,如“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孙绰《秋日》),“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许询残句),“舋舋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许询《农里诗》)以及江淹拟许询的八句:“丹葩曜芳蕤,绿竹阴闲敞”,“曲櫺激鲜飚,石室有幽响”(《杂体诗·许征君询自叙》),都能注意到声音、色彩之美。这些诗句在孙、许诗作中虽然不居正格,却足以说明玄言诗人并不缺乏辞采的能力。“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从历史的观点看,诗中重辞采的倾向是从建安开始的,而后越演越烈,至太康而登峰造极,人们在修辞方法上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技巧。这时摆在玄言诗人面前的是一笔既现成又丰富的遗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于玄言诗人来说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们偏偏改弦易辙,另辟蹊径,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这就说明,对于玄言诗人而言,藻饰词采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平淡朴拙风格乃是晋人自觉选择的结果。因为,如上所述,在晋人看来,平淡无味本身就是一种美。
以上我们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探寻了玄言诗的诗味。尽管这些特点从南朝人或者我们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是不足道的,然而它却符合晋人的审美趣味,因而在他们那里就觉得有味。我想,这大约就是玄言诗为什么会风行诗坛达百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了。
三
这里我们还想附带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玄言诗是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玄言诗也不例外。
从渊源看,玄言诗也可说是其来有自。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中已经有人注意到了。例如古直先生就以东汉仲长统的《述志诗》为例,指出,“清虚之俗,汉末已开其端”(《诗品笺》)。仲诗曰: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以素朴无华的语言表现率性任意的人生态度,同后来的玄言诗确实在某些方面已相当接近。但我认为倘若进一步追根溯源,玄言诗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老子》那里。一般认为《老子》是一部哲理散文,这当然大致不错,但同时还须指出的是《老子》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篇章在韵律、节奏等方面已经具备了诗的特征。如: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
○ ○
○
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
○ ○ ▲▲▲▲
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
▲ ●●●●
于朴。(《老子》28章)
句式整齐而错落,用韵紧密而多变(○为支部韵,“离”,歌部韵,歌,支通韵;▲为之部韵;●为侯部韵(注:说据江有诰《老子韵读》,见《江氏音学十书》,中国书店影印本。),低昂有节,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节奏感与音乐性,的确具备了诗的体貌特征,以此来传达哲理,可以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哲理诗。从某种意义上说,玄言诗就是直接从《老子》那里承袭发展而来的,或者不妨说,《老子》是玄言诗的滥觞。由此可见,在诗中阐说哲理起源甚早。中国诗歌虽然历来以抒情为正宗,但表现理趣也是诗歌的一项内容。《古诗十九首》是以“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著称的抒情诗,但诗中弥漫着的生命无常、人生苦短的感叹却带有哲学意味,而为当时及后世人所喜欢。《世说新语·文学》载王恭激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样的诗句,而此种感叹又差不多成为汉魏六朝诗的基本主题,表明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已成为当时诗歌的经常性内容。建安以来的诗坛仍以抒情诗为主,但也有一部分诗是以说理为特色的。例如曹操著名的乐府诗《龟虽寿》就是一篇以议论见长,阐说养身延年之理的诗,理性色彩颇为浓厚。这类诗虽然所论并不尽是哲理,然而却以理性思索为其特色,这在当时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在玄言诗以前,在诗中表达哲理比较突出的是正始诗人,其中以嵇康的成就为最高。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赠兄秀才入军》十四)
想像兄长的从军生活,表达自己对游心太玄,遗落世事生活的企慕,玄味十足。他更多的是那些在抒情的内容中插入的说理句子,如:“朱紫虽玄黄,太素贵无色。渊源体至道,色化同消息”(《五言诗》之二),“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四言赠兄秀才入军》之十六),“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遇过而悔,当不自得(《代秋胡诗》之五),这一类诗句与后来的玄言诗几无二致。这种在诗中说理的倾向,即便是在重情感、崇辞采的西晋初期也时有所见。例如傅玄有《论语诗》《周易诗》,直接用诗歌隐括儒经大义,其为折学之义疏的特征较之玄言诗有过之而无不及。陆机诗中也有若干这类作品:
太素卜令宅,希微启奥基。玄冲纂懿文,虚无承先师。(失题)
物情竞纷纭,至理自宜贯。达观傥不融,居然见真膺。(失题)
萧疏简淡,理入精微,同他缘情绮靡,重墨浓彩的风格大异其趣,而颇有几分玄言诗的味道。
由此看来,玄言诗在诗坛的崛起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积累准备。说理本是诗歌的要素之一,尽管它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哲理诗也不执诗坛之牛耳,但是到了东晋,由于受到时风的刺激,这一因子便发生变异,异乎寻常地膨胀起来,终于压倒情感、形象等因素,形成了统治诗坛的玄言诗。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粗略地探寻玄言诗的来龙去脉,还希望能从一个侧面来说明这样的观点:读者对哲理的爱好、欣赏是由来已久,且不会止息的,这正是玄言诗或者说是哲理诗存在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