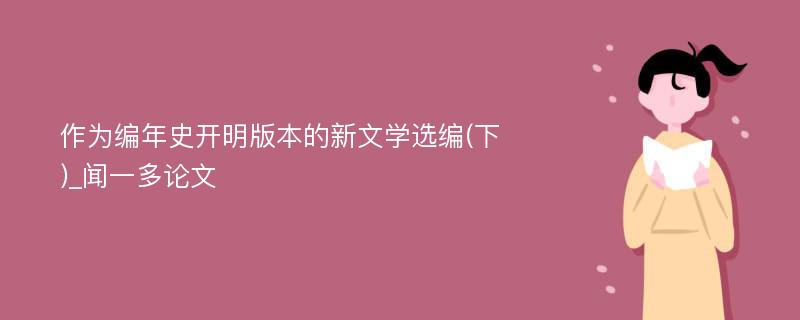
作为“纪程碑”的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明论文,新文学论文,选集论文,之二论文,纪程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样的描述,在已故作家序言中是有代表性的,体现了五十年代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共同理解。那就是,只有参加社会活动,与民众在一起,才能看到民族的力量,才能从个人主义的悲观失望、伤感颓废中挣脱出来,获得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立场转变。而作家从书斋走向民众成为斗士的过程,也就是汇入现实主义主流的过程。五十年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现实主义就是对现在有用”。
联系其他作家的序言,不难看出是在以集体主义话语对个人主义话语的批判中来完成对已故作家的形象塑造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等,这些在“五四”时期曾经起到积极作用的“主义”和思潮,随着阶级观念的出现,被界定为新时代阻碍作家进步的精神“负累”。比如,杨刚认为许地山早期受佛教影响,内容上表达了宗教的“命苦说”(比如《缀网劳蛛》),在风格上表现为“命定的浪漫主义”。到了写作《春桃》时期,“他的平民主义限制了他”,使他“不可能从阶级关系着眼”来塑造春桃。在丁易看来,“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这主调一直到他后几年的小说中还是浓厚的存在着。”“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特别是在‘五四’狂飙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革命有了正确的领导,社会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这种消极的自戕式的反抗,对于现实的反动政治无损于秋毫,而在客观上对于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却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老实说,达夫先生这些作品在这个时期,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了。”即便在他后期的小说中,在以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他过去作品中的主调——肉欲和色情的描写占了上风”。丁易认为,郁达夫虽然成了民族英雄,但是他还没有获得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达夫先生死了,他不能亲眼看到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投身于人民的行列中,把自己思想更发展更提高。”言下之意,如果郁达夫还健在的话,尚需进行思想改造。至于蒋光慈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封建文人才子佳人的趣味”在序文中批评得更重。
鲁迅是新文学中最光辉的形象,但在四五十年代之交,鲁迅也被塑造为自我改造的楷模。1949年10月19日茅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一文,认为鲁迅的思想发展曾经经过了“苦痛的自我批判的过程”,鲁迅的伟大就在于敢于自我批判。“在今天,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自我改造之时,鲁迅所经历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过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学习。我们是在新时代,政治上的领导和思想上的领导,都是鼓励我们自我改造的,这与鲁迅当年不同,我们比鲁迅幸运得多。要不虚负这幸运才好。”(注:茅盾:《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9日。)而“沿着鲁迅先生的道路走,新文学从茁长到壮大,成为今天灿烂的一片红霞,其中有过无数斗争的场面,牺牲的烈士鲜血,洒在大路上,使后来的人不致迷失方向。在新文学选集的第一辑里,都是已经去世的作家的作品,我们翻阅着,就使我们摸清了新文学的发展的道路。”(注: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认识鲁迅自我改造的道路,认识“已经去世的作家”自我改造的道路,是为了“不致迷失方向”,因而热情地希望作家们积极改造,少走弯路,省去可能出现的曲折与反复,飞跃前进。从而突出这样一个意念:作家们经过思想改造后就会写出思想纯洁和艺术成熟的无产阶级文学。
六、对旧作的“过滤”和“修改”
作家是以作品说话的。对一般读者来说,选集吸引他们的也是作品。选集中选编哪些作品,作品又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就至关重要。《老舍选集》收有《黑白李》、《上任》、《月牙儿》、《断魂枪》和《骆驼祥子》五个作品。他以“论篇数”、“论体裁”、“论时间”、“论技巧”、“论语言”、“论内容”、“论思想”七个排比句来“演绎”这五个作品之“好”。在这五个作品中,老舍认为《黑白李》在技巧上“不很成熟”,“因为它产生在我初学乍练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但是,选录它“是拿它来说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可见,老舍在选录作品时,虽说很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但为了显摆他的“革命”和进步,会把艺术上并不完满而思想性强的作品也编入选集。
李广田编选的《闻一多选集》,共选诗三十五首,文二十五篇。所选的诗,除了《奇迹》(写于1931年),《红烛》和《死水》两本诗集各选17首。所选的文,除早年写的《女神之地方色彩》、《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和《〈烙印〉序》外,其余的21篇都写于昆明时期。李广田在序言中谈到闻一多早期诗歌创作时,说《死水》中的现实成分比在《红烛》中增加了,可他还是从这两个诗集中选出了同样多的诗篇,表明他对这两部诗集是不偏不倚。从具体选目来看,《剑匣》、《死》、《艺术底忠臣》、《色彩》、《死水》等唯美主义诗篇,展现了闻一多创作的丰富性;为了凸现闻一多的“斗士”形象,李广田主要选了闻一多后期的文章。他在《〈闻一多选集〉序》中说:“闻先生是诗人,是学者,是民主斗士。要了解闻先生,须从全面了解。但这本书既是《新文学选集》之一种,也就只能选闻先生这些作品。从这样一个选本中,虽然不能看到闻先生的全部成就,但从此也可以看出闻先生的转变过程和发展方向。在文选中,较多地选取了后期的杂文,因为这些文字是富有战斗性的,是闻先生的一种斗争武器,是闻先生道路的终点,也就是最高点。没有这些文字,就不足以认识闻先生之所以为闻先生了。”在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中,杨刚编选的《许地山选集》、丁易编选的《郁达夫选集》、黄药眠编选的《蒋光慈选集》等都采用了这种编选方法,那就是在全面展示一个作家创作的整体面貌的同时,为了突出作家的“战士”形象对其后期创作有所侧重。丁玲更极端,在编选《胡也频选集》时,只选录了胡也频的后期代表作《到莫斯科去》与《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舍弃了他早期那些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的作品。
除了选目“过滤”外,还有一些作家或选编者修改了旧作。叶圣陶、老舍、曹禺等人修改了自己的作品。闻一多的作品则被修改。1954年,胡风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中,把曹禺修改《日出》一例,作为何其芳的“题材差别论”的“严重危害性”的例证之一,并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修改,如果说是照的理论批评家的意思,那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如果是作家自动修改的,那更足以说明:何其芳同志等底理论棍子把作家威吓到了怎样的地步。”(注:胡风:《胡风文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5页。)为此,曹禺撰写了《胡风先生在说谎》一文,指出胡风把“全中国的为工农兵的文艺”诬蔑为“不自由的,不民主的,完全被一种不受人民欢迎的理论所统治的东西”。表明自己“不是受了谁的理论的威吓才想起修改的,相反的,在修改的时候,我记得周扬同志和丁玲同志听说我要修改,曾经不止一次诚恳地劝我不要改动,还是把原来的面貌保存下来好,我没有考虑。那时我想,修改是我的事情,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就这样修改。修改以后,改稿曾由蒋天佐(注:“新文学选集”由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担任编辑任务,蒋天佐为编审处主任。)等同志看过,他们也是不同意这样修改,并问我可否仍照原作发稿,我仍然没有同意。这个修改本最后由于我坚持我个人的意见,就出版了。”(注:曹禺:《胡风先生在说谎》,《人民日报》1955年2月21日第3版。)可见曹禺是主动修改作品并坚持出版了修改本。
李广田修改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一事,很少被人提到。在开明版《闻一多选集》中,李广田删去了把中国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开明舆论”和“美国人民”的身上的内容,以及赞扬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现将这几段文字转录如下,删去的文字用黑体标出:
反动派故意挑拨美苏的矛盾,想利用这矛盾来打内战。任你们怎么样挑拨,怎么样离间,美苏不一定打呀!现在四外长会议已经圆满闭幕了。这不是说美苏间已没有矛盾,但是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我们的新闻被封锁着,不知道美苏的开明舆论如何抬头,我们也看不见广大的美国人民的那种新的力量,在日益增长。但是,事实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其次,反动派干得太不像样了,在四外长会议上才不要中国做二十一国和平会议的召集人,这就是做点颜色给你看看,这也说明美国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人民的忍耐和国际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无疑,李广田删改《最后一次的演讲》与毛泽东在1949年8月18 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有关。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认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的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在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当。”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闻一多作为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英雄形象来讴歌的,他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7页。)对照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闻一多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所表现的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没有认清美国殖民主义本质,具有“糊涂思想”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知识分子。李广田岂能不删改呢?也只有删改,才能在《〈闻一多选集〉序言》中把闻一多塑造为“学习《整风文件》”,追随共产党的斗士形象。
在“新文学选集”中,老舍对《老舍选集》中《骆驼祥子》大加删削,第10章和第24章,删的都是整章。在《曹禺选集》中,曹禺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都作了很大的改动,有些章节可说是重写。他们对作品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内容方面,在新文学史隶属于革命史的理念下,他们不得不按照阶级观念来重构历史图景,为了表现“革命者”和“敌人”的斗争过程,不仅要改变人物原来的身份,还要添加一些新的人物和情节发展的线索。
《日出》原本中,小东西的“父亲”是被“大铁桩子”“砸死”的打夯人。“小东西”无名无姓,她被妓院抓走后上吊自杀了。在修改本中,她叫傅连珍,父亲“被金八指示特务害死”后,引发了学生和工人的示威游行,以致“全市的工厂都在罢工”,“工人一直要求抗日,要赶走日本鬼子”。傅连珍在外出买东西时被人骗到妓院后,父亲的朋友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她。修改本新添了两个工人:田振洪和郭玉山,他们深入虎穴,到妓院救出了傅连珍。在原本中,方达生来自乡下,对现代都市生活陌生而不可解,他同情那些被金钱和权贵玩弄的弱者,愿意为他们做点事。在修改本中,方达生是一个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一个“救亡工作者”。他被国民党特务盯梢,不断变化住址,隐姓埋名。他“教教书,写写文章,还做应该做的事”,他的行动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革命者”相对应,修改本也点明了“敌人”,《日出》原本中,隐藏在幕后的金八身份并不明晰。修改本中金八是一个买办资本家,是日资“仁丰纱厂”的总经理。工人罢工使纱厂生产停滞,为镇压工厂罢工和学生游行,日军军部在码头上架起了机关枪,街上到处是日本陆战队的士兵。在修改本中,日本人还控制着国民党政府。原本中顾八奶奶的面首乔治,在修改本中做了“市长的伴郎”,日本领事闯进市长的婚礼,逼迫市长解决工人罢工问题,致使使礼无法照常举行。连乔治也哀叹:“在这种倒霉的国民党衙门做官,真麻烦。”
曹禺以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重新组织戏剧冲突,原本中复杂的人物和人性到了修改本中都类型化了:好的更好,坏的更坏。哪些人变得更革命,哪些人变得更反动,又都取决于他们的阶级属性。本着这样的原则,曹禺对《雷雨》的第四幕作了大刀阔斧地修改,它可以说是曹禺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极端例证。原本中,周朴园作为专制家长有他冷酷严厉的一面,也有亲情的一面。第四幕一开始,夜深人静,窗外瓢泼大雨;室内,疲惫不堪的周朴园寂寞极了,看到儿子周冲,不由得“面露喜色”,得知儿子不是找他时又有些“失望”。他叫住急于走开的周冲,“慈爱地”询问他怎么还不睡,吃药了没有,打球没有,是否快活,周冲冷漠的回答使他颇为伤感。修改本删去了这些剧情。原本中,周朴园回家三天都没见蘩漪。他白天处理矿上工潮,忙着会见各类客人,修改本人,周朴园白天忙于到“省里”开会;晚上在家里接见秘书长、乔参议。周朴园按照“英国顾问的意思”处理工潮,在得知鲁大海是自己的儿子后,还是建议张局长把他关起来,阶级仇恨淹没了骨肉亲情。按照用阶级情感取代人性人情的修改原则,《雷雨》中的其他人物也都被改写。原本中,周萍不顾蘩漪的请求和阻拦,决意带四凤离开;修改本中改为周萍哄骗蘩漪以后回来接她,把周冲叫来陪着四凤,自己准备悄悄溜走。倒是繁漪向四凤揭穿了周萍骗人的把戏。侍萍对周萍不再有母子之情,她坚信“不同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不一样”。蘩漪与四凤、侍萍等人从复杂的感情漩涡中超越出来,结成联盟,共同反抗恶贯满盈的周氏父子。
作家在修改旧作时,为了表现作为历史主人的工农兵形象,或删去那些有损工农兵形象的文字和情节,或干脆把它改换为具有反抗性的行为。《雷雨》修改本中,四凤怀孕三个月的细节不见了。原本中,同意复工的两位工人代表,签订后回到矿上,被开除的鲁大海到街上去拉人力车。修改本中改为工人代表被警察扣留,鲁大海准备去矿上继续作斗争。《骆驼样子》的第24章即最后一章里,祥子混迹于乞丐和送灵者的队伍里,他出卖了“革命者”阮明,变成了行尸走肉,彻底堕落了。在开明版《老舍选集》里,老舍把这一章全盘删去。出于同样的思考,老舍也删去了小说中下等人的一些“钱生钱”的手段。与祥子一起帮佣的高妈,得知祥子正在攒钱买车后,建议他放高利贷。祥子拉包月的方家,全家个人都有储金折子,方太太也建议样子到邮局立个折子。也许,劳动人民放高利贷、有存折的行为不符合五十年代对受压迫者、受剥削者的形象设定,这些叙述都被老舍删掉了。
作家对作品的修改,对艺术的破坏较大,不仅扭曲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带来了作品风格的异化,开明版《曹禺选集》就是明显的例证。曹禺的剧作往往写出一个人性格的多种层次,给观众复杂的情感冲击力,即便写一个人的“坏”,他也总是抱着怜悯的情怀。但是在开明版《曹禺选集》中,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重新组织剧情后,作品中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有曹禺在《〈曹禺选集〉序言》中所说的“憎恨”,那是感情上的“斩截”。曹禺为突出人物的阶级性导致了人物形象的简单化、平面化和类型化。修改后剧作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一)悲剧消失了。读者看不到《雷雨》原作中那震撼人心的结局:三个年轻的生命在一个晚上消失了,两个母亲一个疯了、一个傻了;《日出》原作中“小东西”自杀了,在修改本中“傅连珍”被救出了妓院。(二)诗意的抒情风格被放逐。修改本中删去了那些富有哲理的抒情文字,比如在四凤家周冲对“大海上驾着白船”的憧憬;陈白露看到窗户上的霜花所表现出来的纯真和诗意的细节在修改本中都看不到了。人物出场时关于精神状态的舞台提示词以及曹禺非常看重的《雷雨》的“序幕”与“尾声”,《日出》开始的七段“引言”,也都删去了。修改后的《雷雨》和《日出》,仅仅止于对人吃人、人剥削人的黑暗社会的表层的、简单的抨击和诅咒。
谈到五十年代现代作品出版时,王得后先生说:“从旧中国过来的现代文学作家,在新中国再版他们的作品,成为党的行为。党运用出版的手段重新审查他们的作品,赋予它以合法性,宣示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确立党的导向。作家对原作的修改,是接受党的领导,汇报思想改造状况的成绩单。”(注:王得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汇校和校记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的确如此。但是,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只是一个总的纲领,就某个具体作品的立意以及人物和情节的修改而言,作家也往往从权威评论家的批评中得到指点。至于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的修改与批评之间的复杂关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