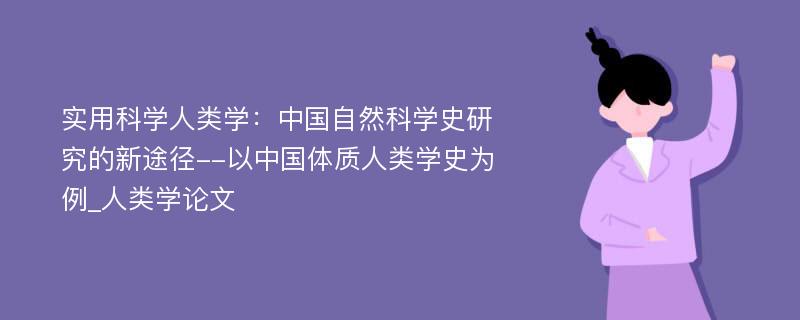
实践的科学人类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的新路径——以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为例论文,体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4)01-0022-10
最近五年来,笔者一直在吴新智院士指导下从事百年中国体质人类学(包含古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现代体质人类学)史研究。一方面希望从纯粹自然科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开展进行回顾与总结,找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希望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某门近现代自然科学,希望推进科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在数年研究基础上笔者新近出版了《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一书。
在序言中,吴新智先生认为拙著有两个创新:一是迄今出版的第一部专门致力于中国体质人类学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二是书中有几篇论文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行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可谓开国内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研究领域的先河。[1]对于吴先生的赞誉,笔者倍感诚惶诚恐,因为自知这项探索仅仅是一个开端,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任务亦很艰巨。
就目前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和科学人类学的学术实践而言,似唯有笔者是以双重身份(即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又作为一名体质人类学工作者)来开展一门自然学科发展史研究的学人。在数年研究过程中,笔者有意识将两个角度结合起来对中国体质人类学历程做考察,因而在方法论上有所思考。现结合笔者的学术实践,在拙著已有“心得”基础上进一步对其提炼,并系统论述如下。
本文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研究路数、国内现有科学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开展情况、笔者的实践人类学视域中的科学人类学方法论。重点落在第三部分上,前两部分仅作为一个背景而加以简要介绍。
一、内史与外史的研究
当下我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的主流路数,基本上走的是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的道路,即,按照一门自然科学本身的问题意识和发展逻辑来回顾和追述单一学科的发展历史与脉络。这种学术史研究思路认为,一门自然科学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问题意识向下发展,不大受自然科学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和情绪等影响。而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也坚持,自己的研究是力图屏蔽这类干扰因素的。但是后来学者们发现,世界上从没有一门自然学科生长在真空之中,都是特定历史场景下的产物,是应人类社会之需要和发展而产生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以及被理解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或“科学(技术)元勘”的STS等大体持有类似见解(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理解上的差异)。近些年来,国内也有一批学者(主要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自然科学史研究领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学术界习惯上称前者为“内史”,称后者为“外史”。所谓“内史”,是指把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科学内部,把科学史看做是科学知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所谓“外史”,是把科学看做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它与社会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诸如与经济、教育、政治、文化等的关系。[2]刘兵的解释更为详尽一些:“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内史论’(in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只应关注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逻辑展开、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而不考虑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默认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科学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指社会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外史论’(ex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应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学史时,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3]
笔者认为,不论是“内史”还是“外史”都自有其存在的道理,关键看科学史家的服务对象是谁。如果是写给纯粹自然科学工作者看的,能帮助他们找出学术上的问题和未来努力的方向,或改进研究方法,自然科学史的“内史”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大科学家写作的“内史”。如果是把自然科学史的写作看做供人文社会科学家阅读的,那么,“外史”的开展也是有必要的。当然,笔者不是说,自然科学家就没有人喜欢“外史”作品。“内史”和“外史”学术关注点不同而已。
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人类学是指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的、对某门自然科学发展历程或当下科学研究活动的考察与研究。如果按照内史和外史的二元论界分方法,科学人类学似应归之为外史部分。但在此需要声明,本文所主张的实践的科学人类学观并非单纯是一种外史研究路径,而是试图对两者有所包容和超越,追求“内”“外”互渗。涉及到“外史”研究部分,实践的科学人类学观不会按照现有“外史”研究路数,将各种社会因素分割为“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领域”。这类分割方法实际上沿袭了现有知识领域分类的陈旧认知模式。这样的划分是人为的,与事实并不吻合。是不同领域的知识群体为了生存而独霸一块空间的意志的反映。
二、科学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人类学在国内的开展状况
197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图尔(B.Latour)和沃尔佳(S.Woolgar)率先在全球开展了这项研究。他们当时进入了加利福尼亚一个神经-内分泌实验室里,观察“科学家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科学‘事实’的建构”,以此思考自然科学研究是否真的像自然科学家们所标榜的那样“理性与客观”。或者说,科学家们所研究的“事实”是否真的就是“客观事实”,还是一种人为及社会建构或选择的“事实”?[4]
“科学人类学”一语的英文通常写作:“Anthropology of Science”。当研究范围扩及到技术方面时,人们也使用“科学技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一说法。后者比前者包容的范围更加宽广,含有对人类工程技术领域的文化人类学考察等内涵。目前在我国这两个概念都有使用,多为自然科学史研究者、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和部分文化人类学家。
就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人类学”而言(笔者指的是选择某门近现代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人类学”),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除笔者从文化人类学出发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外,似尚未有人开展。也就是说,相关人员并没有选择某门具体学科作为考察对象。只有少数研究人员写了几篇文章来介绍西方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包括他们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等。比如,刘兵的《中国语境中的“科学人类学”之定义问题》[5]和《科学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的差异及启示》[6]、刘琣琣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7]和《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域》[8]、田松的《科学人类学:一个正在发展的学术领域》[9]、曾晓强的《拉图尔科学人类学的反身性问题》[10]等文章。余外,卢卫红选择回顾西方人类学的科学史研究为博士论文写作方向(《科学史研究中人类学进路的编史学考察》[11])。然而,上述学者并没有进入某门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内部,与科学家们“同事”并参与观察和访谈。也就是说,只是单纯地停留于引介西方的东西,并未就中国的诸自然科学学科做出实质性研究。退一步说,即便有人开展了所谓“科学人类学”研究(至少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信息而言,事实并未发现),也多半或可能是在某门自然科学的外围予以观察,且不是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开展的(他们缺乏必要的文化人类学学术训练),更谈不上严格而规范的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
不过,从“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概念出发,我国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展了此项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丁长青就发表《技术人类学抉要》[12]一文介绍西方关于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但真正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考察科学技术问题的学术实践,主要集中在广西民族大学,如,万辅彬、秦红增等人。这个方面目前已取得了一批成果。单篇论文有万辅彬的《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13]、《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与韦丹芳合著)[14]、《人类学——科学史研究的第五向度》[15]和秦红增的《人类学视野中的技术观》[16]等文章。另外,他们还出版了科技人类学专著,如秦红增的《桂北科技:科技下乡中的乡村社会研究》[17]。总起来说,他们选择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某门近现代中国自然科学,以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科技观念以及当下的科技实践为主,因而只能叫“科学技术人类学”或“技术人类学”,或者“民族民间科技人类学”,但不是上文所标榜的“科学人类学”。
需要说明,吴新智先生为了避免“科学人类学”这一提法引起误解,主张使用“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一概念:“197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图尔(Latour)和沃尔佳(Woolgar)开启了被称为Anthropology of Science或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翻译成‘科学人类学’或‘科学技术人类学’。中译‘科学人类学’一名可能被人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科学的人类学’,进而引申出一种误解,似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都是非科学或不科学的。而科学技术人类学一词或许可以避免这样的尴尬,所以笔者宁可使用后一中文译名。”[18]笔者与吴新智先生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三、实践的科学人类学观
笔者出身于文化人类学的训练,并获得了文化人类学的博士学位,然后进入中国体质人类学领域内,与中国体质人类学家共事,从师世界著名体质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在数年研究过程中,笔者努力以双重身份(文化人类学者和体质人类学者),既采用自然科学内史的视角,也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打量这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科学家们的具体研究工作(包括参加古人类学的野外考古工作)。一方面,笔者像一个严谨的自然科学家一样思考自己领域的纯学术问题,一方面又强调文化人类学所标榜的严格而规范的民族志田野方法。
因而在笔者看来,所谓“科学人类学”,是指即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学科史或学术史研究,也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某门自然科学之研究或某门自然科学发展的历程。就人类学这个包罗万象的学科而言,它只是从特定研究对象所圈定的一个研究视域或领域,就像宗教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或艺术人类学等随便一种称谓一样,不算是一门独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关于科学的人类学研究”。如果把科学人类学放在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或社会学等领域,也不应该算是一门分支学科,至多是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论而已,或一个研究的兴趣与问题域。
笔者以为,人类学大致可以分成两个分支学科:一是从生物性角度研究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自身,二是从文化角度研究人类的各种制造物。前者可称为体质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后者则可称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比较关注不同时空中人类生物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当然也对不同人群间基因交流感兴趣。它大致包含古人类学(又称化石人类学,通过化石记录来探索人类的演化轨迹和规律,在时间段上是指新时期以上的研究)、考古人类学(即新时期以来的古代历史时期的人骨研究)、人类遗传学(含分子人类学,主要从DNA角度而不是从形态测量角度开展的研究)、人类生长与发育学、灵长学等内容,与生物学、动物学、地学、解剖学、生理学、医学研究、公共卫生、历史学等有密切关系。而举凡器物、组织、制度、信仰、风俗、语言、神话、行为模式等均属于人类的制造物,只不过有的有形,有的无形,它们均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文化人类学主要包括旧石器考古学、一般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领域。当然,在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也存在一个交叉,即人类体质有时候不单纯是适应环境演化或自身遗传的结果,人类自身的各种制造物和由此形成的各种观念也反过来型塑人类的身体,并在某个时刻获得特定稳定遗传性状,并有可能以基因的方式往下遗传。注意:当下有人提出的“身体人类学”不能算作这个交叉范围,因为,“身体人类学”所关注的只不过是人类身体被当做一个文化创造物而已,不涉及生物性的基因等问题之研究,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笔者的这个主张与美国通行的四分支框架不一样。
中国体质人类学属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正如笔者上述所主张的那样,可以采取两种学科史研究路径:一种是目前为主流所接受的纯粹自然科学史研究,考察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生、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诸种问题,讨论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方向等等;另一种是有浓厚人文社会科学色彩的体质人类学史研究道路,侧重于考察中国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对于科学家个人来说所具有的生存意义。前者的阅读对象是中国的古人类学家和现代体质人类学家,或曰为科学家研究而写作;后者的阅读对象多为人文科学学者(当然,在最初本意上是为自然科学家而写作的,但部分自然科学家并不领情,认为是些“无稽之谈”或“谈资”,缺乏科学旨趣),目的在于反思和批判主流自然科学史研究的撰写方式和话语霸权地位。
笔者视中国体质人类学为布迪厄(P.Bourdieu)意义上的一个知识场域或科学场域。具体包括知识生产场域、知识传播或消费场域等。作为一个知识生产场域必须考虑投入知识生产的各类资本和投入,具体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生产期望、和生产机制等内涵。同样,作为一个知识消费场域,要充分考虑各种消费因素,尤其是消费对象的消费欲望或期盼。还要考虑知识生产场域与知识消费场域之间的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抑或更为复杂?
因而,笔者之考察中国体质人类学史,既想沿着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同时又把体质人类学史视做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部集体表象史,当然也把它看做是一般社会集体表象史,最后是特定知识生产场域的社会关系史。在这个知识场域里四个层面是相互渗透与贯通的。如果单纯着眼于后三个角度,这样的自然科学史完全可以看做是一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活动,即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去观察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属于美国人所讲的科学人类学研究。
笔者不大赞成STS等的研究路径,因为这种自然科学史研究视角同样遮蔽了许多问题。它一般较倾向于从社会宏观层面把握某门自然科学之发展历程,却不能沉下身子去,且钻到某个科学家的主观世界里去。比如,它看不到知识生产场域里的自然科学家的主体性,即,自然科学家有时会借助于社会结构来能动地表述自我和潜藏自我,从而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形下推动自然科学发展。在此种情形下,自然科学家并非消极地屈服于社会结构的压力,而是极富策略或富有智慧地在社会结构之下尽可能地实现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有时,自然科学家会把自己的研究行为看做一种对象征的追逐,由此获得对个体生存价值或意义的评估。笔者认为,一门自然科学按照自身的兴趣、问题意识和逻辑向前发展,和在特定社会场景下向前推进并不是彼此分离的,相反,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其存在的社会场景互相依附、互相表述。笔者的研究并非停留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层面,而是以探索两者间的互动为宗旨。这样做的目的是与现有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的主流现状与范式划清路线,并希望促进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向一个新的方向和领域发展,在解李约瑟难题上有所突破,消解“内史”与“外史”之间的隔阂。同时,也想改变迄今为止国内文化人类学界没有把自然科学学科史列入学术考察视野的局面。
但笔者又主张,纯粹的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和科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人类学史研究是不同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骨头,他天天盯着骨化石,测量也罢,做古DNA切片观察也罢,无非是想从标本中提取出足够量的信息(当然,他也会进入田野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来思考古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诸古人类标本之间的关联,最终归结到人类整体演化历史方面的探索,反映出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explain”关系。但科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人类学史研究则不同,科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人类学史主要关心人类学家与骨化石之间的互动,即把“人类学家与骨头的关系”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而且远不止于此。比如,人类学家之外的不同社会群体是如何解读标本和人类学家的成果的?包括媒体、一般社会大众、政治党派,甚至整个民族-国家对人类学成果的解读和使用,以及对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人类学家与非人类学家群体之间的观察和理解是否一致?人类学家和人类学之外的社会群体是什么关系?再者,要关注人类学家内部之间的人际关系:为什么这个标本只允许某个人研究,另外的人类学家则无权染指?甚至部分人类学者被迫离开研究单位而另寻出路?那么,在人类学知识生产场域里是否存在知识霸权?而知识霸权是如何形成的?他或他们又是如何通过学术资源配置而格定整个人类学领域的社会秩序的?等等,问题不一而足。所以,科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体质人类学史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不同于体质人类学研究,它除了使用“explain”外,还使用“interpret”技巧。当然,这里的“interpret”并不是要把笔者的理解强塞进过去的事件之中,而是试图深入探索历史的行动者之内心世界。否则,笔者的科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人类学史研究就蜕变成了笔者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投射,甚或可以说成了个人的“意淫”。笔者是坚决反对学术“意淫”的。对于纯粹的研究,对于科学家能够躲避开政治社会因素,或者能动地利用政治和社会环境来开展自然科学研究,科学人类学不可作过度诠释。在此种情况下,科学人类学家要学会细心地剥离。笔者在数年的研究过程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阅读(主要指人类学家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科研成果)、档案调查、科学家私人信件浏览、口述史访谈和“参与观察法”(即,有时深入到人类学家的田野地点和实验室中参与观察科研活动,留心观察他们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笔者把以上的理解暂且称为“实践的科学人类学”研究路径,并希望这样一套分析模式也能被迁移进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史研究里面。当然,也可适应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
为了让读者更详细地理解笔者的科学人类学的四维研究视角,下面具体通过研究实例来详加说明。从体质人类学的亚学科来说,主要取例于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现代体质人类学(以现生人群或民族为单位的生物研究)。
四、作为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一部集体表象史的中国古人类学史
如果把一部百年中国古人类学史看做中华民族的集体表象史的话,笔者首先思考的是:中国为什么需要古人类学?从传统中国向近现代中国转换以及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过程中,古人类学扮演了什么角色?即在现有国家知识生产体系里,古人类学被赋予了何种任务,要为国家生产出什么样的知识?国家与民族是如何支持其开展工作的?等等。
中国晚清以来遭遇西方列强入侵,使得中国有识之士思考:中国的衰败不仅是经济的滞后,也是社会制度、思想制度的落后。为了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问题,知识界一方面希望借助地质矿产业和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科学来发展民族国家经济,由此带动了古人类学的发展,至今古人类学被列为地质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需要进化论思想给予支撑,而以进化论为根本要旨的古人类学能够在接受其指导的情况下,也再生产出进化论知识,从而客观上满足了这份社会转型的需要。[19]
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至1980年代中后期结束,中国古人类学史(包括旧石器考古学史)上爆发了著名的人观之争,即关于“人猿区别”的论争。具体包括“生物人”与“社会人”之争、“曙石器”问题之争和“亦猿亦人”之争等三大学科事件。这些争论涉及古人类学学科内部纷争、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纷争,以及科学家和工农兵大众之间的纷争。尽管所持观点和结论并不一致,但各方均从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文章以及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的理论观点出发,视“劳动”为“人”“猿”相区分的根本机制,因而“劳动”成为一个学科三十余年的关键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性质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劳动”必须被强调到一个突显的位置。一方面,人类学家必须从人类化石标本上找出“劳动”的痕迹,生产出有关“劳动创造人类”的知识,以此教育人民:人不是由神创造的,培养大众的唯物主义观念;另一方面,科学家又不得不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而这两个过程又都是社会主义公民被制造和生产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深层次的“劳动创造人类”。但当代的“劳动创造人类”却是个观念的产物,意识的作为。特定时代场景赋予了中国古人类学以特定时代的任务,而特定时代的中国古人类学又不得不挂靠在特定时代场景之中以寻求学科发展的意义。这似乎是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既定逻辑”:没有独立出社会场景的纯粹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必须借助外在场景而获得自我表述,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自然科学也只不过是特定时代集体心智的一种投射而已。[20]
当理想的科学研究环境被扰动以致被紊乱的时候,科学家们如果不想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们就学会了利用现有的社会结构或场景来从事人类学研究。所以,表明面上看,在特定历史时期,比如社会主义中国时期,一些有作为的体质人类学家虽然喊了一些政治口号,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仍旧是合乎自然科学研究规范的。过往的科学社会学等的研究,只看到了“社会”的面相,却没有激活科学家个体的主体。在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主体死亡了。或者说,主体被科学社会学家流放到集体映像的荒原上去了。
不过,也有部分人类学家将自己演绎成了政治表述的工具或民族主义情绪的傀儡。所以,必须看到复杂的历史情形。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探索,我们就会发现,媒体、中国社会中的部分大众,甚至部分古人类学家(含旧石器考古学家),他们把北京猿人、元谋人等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乃至特定族群的祖先。[21]古人类学成了一种寻祖活动。事实上,中国考古学自20世纪诞生以来也大致是这条思路。
五、作为内史的中国古人类学史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百年中国古人类学纯粹是一部自然科学探索的历史,是为了探寻地球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而进行的一项旷日持久的科学活动,属于世界古人类学学科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视野里,元谋人、北京猿人等就不为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而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而是被当做全地球人类的祖先来对待,作为一个生物物种被研究。属于一种纯粹的没有国界和族群边界的自然科学行为。
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年,根据亚洲现生灵长类以及当时在亚洲大陆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的分布情况,西方一些学者坚持人类最初可能出现在古亚洲大陆(Pal-Asia)。德国生物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认为,亚洲猿类更接近人类,亚洲更可能是人类诞生的摇篮。美国人类学家奥斯朋(Henry Fairfield Osborn)于1923年提出了人类起源于“亚洲说”。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William Grabau)也主张到“蒙古和新疆的距今一千一百万年到三百万年的上新世地层里”寻找最初的人类。另外一些科学家则直接来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境内进行科学探寻。荷兰医生杜布瓦(Eugene Dubois)于1891年发现了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首先印证了海克尔的观点。1903年德国古生物家施罗塞(Max Schlosser)利用德国医生哈贝尔(K.A.Haberer)在北京搜集到化石标本,首次宣布了中国有发现古老人类化石的可能性的观点。再后来法国古生物学者桑志华(Father Emaile Licent)和德日进(Pierre Telhard de Chadin)也相继来到来中国寻找古人类化石和遗物,他们寻觅到了河套人化石。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J Gunnar Andersson)也被北洋政府农商部聘为矿政顾问,而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也于1919年来中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兼解剖系主任,他们连同中国学者翁文灏、丁文江等共同促进了北京猿人的考古发现。步达生和后来来华的德籍犹太(后入籍美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相继对北京猿人标本进行了系统研究,魏敦瑞提出了人类多元起源理论。[22]
195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中国境内又发现了多处古人类遗址和一系列化石标本(除北京猿人遗址外)。如,1951年发现的四川资阳人、1954年和1976年发现的山西丁村人、1956年发现的湖北长阳人、1958年发现的广东韶关马坝人、1958年发现的广西柳江人、1960年/1963年/1964年/1984年在云南丽江发现的木家桥人、1963年发现的陕西蓝田陈家窝人、1964年发现的陕西蓝田公王岭人、1965年发现的云南元谋人、1974年发现的界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和河北阳原县侯家窑村之间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1974年发现的辽宁金牛山人、1978年发现的陕西大荔人、1979年在贵州普定县穿洞发现的古人类脑颅、1980-1981年发现的安徽和县人、1982-1983年发现的安徽巢县人、1988年发现的河北涞水人、1989年发现的湖北郧县人、1993年发现的南京汤山人、2007年发现的河南许昌人、新近发现的广西崇左人。此外,还在云南元谋郭家包、山东沂源土门骑子鞍山、湖北郧县梅铺、郧西神雾岭白龙洞、建始高坪龙骨洞、河南南召杏花山脚、广西百色布兵么会洞、陕西洛南东河村农民处、淅川药店和药材仓库,发现过一些比较零星的直立人或可能属于直立人的化石。在湖北长阳、辽宁庙后山、贵州桐梓岩灰洞和盘县大洞发现过一些比较零星的早期智人或可能属于早期智人的化石。在黑龙江五常县学田村排水干渠底部、哈尔滨阎家岗(地表)、吉林安图明月镇石门山、辽宁喀左鸽子洞、沈阳庙后山东洞和建平、山西峙峪、曲沃朝阳西沟、陕西黄龙徐家坟山、长武(可能出自鸭儿沟)、甘肃泾川牛角沟、武山鸳鸯镇、山东新泰乌珠台、江苏丹徒将桥白龙岗莲花洞、浙江建德乌龟洞、福建清流沙芜狐狸洞、台湾左镇菜寮溪、广东封开河儿口峒中岩、广西来宾麒麟山、桂林广西师范学院附中校内宝积岩、荔浦、柳江土博甘前洞、柳州白莲洞、都安R5013号洞、田东定模洞、隆林祥播红岩山那来洞和隆林德峨一山洞等地、四川北川甘溪甘龙洞、宜木亚吧村、筠连镇州灯杆洞、奉节兴隆洞、云南昭通新田唐房过山洞、施甸姚关万依岗、宝山蒲缥塘子沟、昆明官渡区鸡街子山南坡洞、呈贡三线水龙潭山第一、第二和第三地点、宜良九乡风景区张口洞、蒙自红寨马鹿洞、西畴仙人洞、贵州的兴义猫猫洞、水城硝灰洞、六枝桃花山山洞、桐梓马鞍山山洞等地,发现比较零星的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或可能属于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化石。这些化石标本经历吴汝康、吴新智、周国兴、吕遵谔等中外著名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先后诞生了吴汝康的“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学说、“过渡时期”说和“镶嵌说”(Morphological mosaic),以及吴新智的“多地区进化说(Multiregional theory,or continuity theory)”(与美国学者Milford H.Wolpoff和澳洲学者Alan Thorne联合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和“河网状理论模式”。其中“多地区进化说”成为世界人类学学史上解释人类学起源与演化的两大著名学说之一。另外一种是“出自非洲说”,或曰“取代说”,或曰“夏娃说”(Out of Africa,or replacement theory,or Eve theory)[23]。
中国古人类学家,特别是吴新智院士等人提出的“多地区进化说”和“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等是完全建立在对古人类标本信息提取基础上的,而且是数代中外古人类学家努力的结果,看不到意识形态对其研究的侵染,尽管吴新智等经历了复杂的政治运动。
这样的学科史梳理,是纯粹的属于李约瑟研究的学术范式。
六、作为一部社会集体表象史的中国古人类学史和中国现代体质人类学史
“作为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一部集体表象史的中国古人类学史”实际上是从族群理论等所做的一种宏观视野的学术考察,而这里强调的“社会集体表象史”是从一般社会大众层面或类群意义上所作的解读,也包括大众的心态史研究,强调人群类别的意义。介于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微观的个体研究之间的一种“中观”观察,是一个过渡地带,因而也部分地含有“中华民族集体表象史”或“国家意志”在里面,同时也含有微观意义上的个体意志。
北京猿人遗址中的周口店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史前人类及文化博物馆。是中国古人类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假定把北京猿人遗址陈列室或博物馆看成一个“景物”。我们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的行动者都试图要借助这个景物来“言志”与“抒情”。
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需要该陈列室或博物馆承担起科普任务,突出“劳动创造人”的主题,普及“从猿到人”进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辨证方法知识,破除神灵或上帝造人的迷信说法,培养社会主义公民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告诉人民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参与和塑造了社会主义公民的国家行动。这样就赋予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陈列室或博物馆以“崇高”的政治任务。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陈列室或博物馆所负载的政治任务是有区别的:建国之初主要是培养群众的原始社会史知识观;文化大革命后期,过分突出政治内涵,强调毛泽东思想;而现在则主要针对青少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一个“政治博物馆”。但“科普”始终是它的主要职责,“从猿到人”的基本说法没有动摇。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周口店遗址及博物馆移交到它们手里后,主要想从事旅游开发,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放在市场经济的网络里来加以理解和使用。这是一个“商业博物馆”。
对于古人类学或古人类学家群体来说,他们也的确想开展科普活动,宣传进化论,普及“从猿到人”的人类学知识。结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愿望与整个新国家“劳动创造人”的期许相合拍。但是这个合拍不能被看成是古人类学家被迫或单方迎合新政权和新国家的投机行为,因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虽然在最初是因形势需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但后来他们自觉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原理与古人类学研究相互印证。更准确地说来,他们是试图从“劳动”机制上揭开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秘密。他们是真心地信奉“劳动”原理,是巧妙地利用形势和环境条件,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古人类学界再也不提这个原理了。这种不了了之,谁也无法说明“劳动”原理对不对。反正随着后毛泽东时代的到来,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主导观念上的调整,大家都选择了回避。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科普博物馆”,且带有一定专业性质的博物馆。退一步说,即使古人类学家出于主动迎合(因为,我不能排除个别古人类学家有迎合政治的心理和取向),那也不过是一种学科发展的策略,丝毫无损于该学科的国际形象,因为中国不同于西方。西方社会许多个人、团体机构或组织在资助科学事业时,大部分不附加条件(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科学资助是有各种各样目的的),由此保证自然科学在西方大部分演绎为一种纯粹自然科学。但在中国不同,在中国社会内部要想推动科学的发展,必须为社会及其场景承担一些科学之外的责任。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形下,中国的古人类学家即便在开展学术实践过程中,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赋予给它的政治或其他责任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借助某种外在条件来推动古人类学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人类学家的智慧。总之,比任何不作为要强得多。
对于古人类学家来说,不同的个体对这个陈列室或博物馆的理解或定位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同样都出于科学普及的目的,但究竟把该陈列室或博物馆办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博物馆还是单纯就停留在一个重要人类遗址博物馆的定位上,存在历史的争论。
第二,该陈列室或博物馆是具有更多的专业色彩好,还是更加通俗易懂点好?古人类学家们也有不同意见。过于专业化了就会被指责为成了“标本馆”,特别不适宜青少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今后能否让更多青少年看懂并参与,成了时下部分古人类学家所关心的事情。笔者认为,周口店很特殊,既有专业性,又有科普性,还具有文化保护价值,因而该博物馆必须考虑其多元需求。
第三,在布置展览内容时,陈列室或博物馆成为科学家们争夺的一个象征资本和知识场域,都想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以此显现自己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最后,能够定义陈列室和博物馆的科学家将陈列室或博物馆看成了一种抑制对方的一个工具。那么,从科学家个体角度讲,北京猿人遗址陈列室或博物馆就成了一个“言志或抒情博物馆”。
当然,周口店遗址陈列室或博物馆也许还有其他更丰富的文化内涵等待知识考古或挖掘。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时代的人们会用自己所在社会流行的“主题”去揣摩它、阐释它,赋予其新的历史含义。
从这番考察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古人类学是与国家、政治和社会难相分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国家、整个社会才关注和支持古人类学,古人类学由此获得了发展契机。我们看到,正是由国家推动的科普活动做得好,中国的工农兵大众在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中或提供线索,或直接报送人类化石标本和石器标本等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大量的古人类遗址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发现和被研究的。这是“中国特色的古人类学”发展方式。中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古人类学大国,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此。那种利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承担了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教育活动的历史事实而说中国古人类学受到了不应有的政治干扰、并走了一段弯路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失偏颇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别的哲学思想不能给中国古人类学研究以启发。
今日中国的许多古人类遗址和新时期以下的众多考古学遗址都有着跟北京古人类遗址相似的文化命运。“作为一部社会集体表象史”的学科史研究思路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当然对于博物馆人类学研究而言也有同等重要学术的价值。
七、作为一部人际关系史的中国古人类学史和中国现代体质人类学史研究
场域,是实践人类学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它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问题。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所谓“客观关系”可以包括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场域里充满了权力和资本,涉及到知识生产的资源配置与竞争,包括权力、学术权威以及象征意义的争夺。[24]不论是中国古人类学还是中国现代体质人类学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科学场域或知识场域。布迪厄本人也曾在《学术人》一书中提出过科学场域和知识场域概念。人际关系的研究是一种微观层面的观察。
作为知识生产场域既然要着眼于关系的考察,就要格外注重不同的科学家在这个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每个位置上的资源配置情况或资本占有等内容。要弄明白每个位置的获得是学术成就累积的结果,还是科学家本人的道德魅力,抑或学术场之外其他的权力安排的结果。这样的权力也许并不仅仅是政治威权,还包括经济等市场威权。在这个关系网络中,不同的科学家之间的具体关系也要思考。有些是小范围的学术共同体或流派,有些是师生关系网络,有些是利益关系网链,有些是老乡关系,有些是族群关系或校友关系,等等。这些不同的关系纵横在作为一个学科的大范围的场域中,往往会影响知识生产资源的配置、学术成果的发表、科学家名望的获得以及科学家个人权威的获得等。科学场域往往被各种既存在于科学场域之外的社会关系或场域给悄然置换。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生产的场域并不一定按照纯粹的科学逻辑进行运作,往往被非科学的各种逻辑给操纵。
具体到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体质人类学领域来说,如果不了解1950至1980年代时期杨钟健、裴文中、吴汝康、贾兰坡、周明镇以及古脊椎所时任书记孙继平等人的复杂人际关系,我们无法了解中国古人类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学术争论,无法了解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居然没有国家级的独立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如果我们不了解老一代学者与新一代学者之间的矛盾,我们就无法弄清楚上述学者在“文革”时期被批斗,无法了解一些青年人类学家被迫离开古脊椎所而到考古学研究所去,从而促进了历史时期古代人骨的研究成就。如果我们不了解吴定良与丁文江、竺可桢、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人的人际关系,甚至包括蒋介石、蔡元培、沙孟海等人,我们同样无法了解20世纪前半期中央研究院为什么要搞一个人类学研究所,无法了解解放前浙江大学的人类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如果我们不了解吴定良、马长寿和刘咸三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吴定良跟当时复旦大学生物系其他生物学家的关系,就无法搞明白为什么在复旦大学体质人类学只是委身于生物学下面,闹不清体质人类学与民族学在争夺学科生存空间时的历史情形。如果不了解吴定良与其学生邵象清(也是其秘书)和后来从苏联引进的接班人董悌忱之间关系,就不会明白文革时期吴定良被批斗以及最终被迫害致死的原因。
甚至在研究过程中往往要超越科学场域或知识场域,或者说需要进一步扩大科学场域或知识场域的范围,将与人类学家有关的各类社会人群都囊括在一起进行思考。比如,人类学家的家属、朋友等。1970年代后期,围绕着吴定良是否属于“被迫害致死”、是否该平反昭雪、给予家属以什么样的安慰和补偿待遇,甚至对吴定良的二次葬等诸多问题,在复旦大学校方(特别是吴定良生前有矛盾的领导)、吴定良家属及子女、上海市政府、吴定良的学生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吴定良的生前好友或科学家群体之间展开了复杂的“谈判”和“磋商”。这些都属于一部现代体质人类学史研究的范畴。因为体质人类学史不仅关心知识的生产、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也关心知识被生产出来以后知识如何在社会中发挥科学功能之外的价值和作用。由此全面理解知识生产与消费的系列运动。
这样的研究思路同样可适应于中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发展史的研究。如果我们不了解冰心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间的私人友谊,我们就恐怕不能洞察冰心女士的夫君——吴文藻——何以能在燕大顺利运作一个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也从而无法把握社会人类学燕京学派的由来及发展。而燕京学派在中国人类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可谓中国人类学的半壁江山。1950年代高等院系调整以后,燕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被整合到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和林耀华同时进入并继续共事。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了此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甚至延及到下一代人的学术实践中几近60年。如果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想彻底弄明白中国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史是不容易的。现有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史的研究皆回避了这些问题,因为人们对这方面讳莫如深。学科史家们担心,一旦在文本中呈现或披露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将会影响到自己的学术前程,乃至引来官司。这要求学科史家具备讲述历史真相的勇气。我们似乎已失去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知识场域观也许能帮助我们反思何谓良史?
八、小结与讨论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领域里的内史与外史的争论可以被本文提出的“实践的科学人类学”化解。
标榜自己是客观的、理性的、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表述和科学研究理念。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家在进行研究设计时也是抱着这种信念来开展工作的。他们否定被各种社会因素、个人情绪等干扰了自己的科学行为。但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学术实践不会停留在一个理想研究类型上,常常受到时代背景、各种社会因素和个人情绪等影响,致使其学术实践的轨迹与理想类型中的纯自然科学研究设计或模型相背离,亦即学术理念表述与实践的脱节,故无法做到绝对一致。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体质人类学家自始至终都想摆脱非科学因素的各种干扰或困扰,但却无法摈除。于是人类学家学会了利用现有结构或现实场景来能动地推进体质人类学研究与发展。因而,中国体质人类学始终游荡在两者之间来演绎自己的学科叙事。
从实践的科学人类学角度看,作为一个知识生产场域的中国体质人类学,若仅采用内史的观察,只能使其滞留于一种文本的理想研究,从而看不见复杂的关系网络。若仅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对其考察,恐怕难以进入自然科学史发展的内在脉络中体会科学追求的精神。
考察这样的学科发展历史不唯注重其知识生产的历史过程,也同时注重生产出来的知识如何发挥科学以及科学领域之外的社会效益,即知识传播与消费的过程,洞察种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正如古人类学可以被理解为考古学一样,笔者之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也可以被视为是一门知识考古学。但这样的知识考古学应该比福柯讲的知识考古学在理论思考上更深度一层,因为笔者所参考的布迪厄理论是后来在福柯研究基础上的一种推进。而布迪厄的实践人类学在研究设计上是缺乏历史变迁因素的,笔者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顾名思义是一种历史进程研究。因而,笔者希望在借鉴布迪厄智慧的时候,力争又有所突破和超越。
既然是场域就会有变动性。从一个场域转换到另一个场域,也就是中国体质人类学的进程。北京猿人遗址周口店博物馆的例子就是一个最佳说明。在具体的学科历史进程里,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学术问题和研究兴趣被延续下来进行讨论,有些问题只是特定时段和特定场景的兴趣,到了下一个场景时,讨论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在坚持与变化之间又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场域与场域的转换之际或交接地带,是场域的边缘或阈限。在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既有断裂,也有延续。这个场域“边缘”或“阈限”的研究是我过去所忽略的问题,今后有必要加强,因为科学范式转换的革命力量往往就诞生在模糊的“边缘”或“阈限”里边。
笔者自信,个人数年来所开展的“实践的科学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史研究,不论对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还是对于文化人类学界的科学人类学研究都具有方法论意义。笔者体会是:要想开展真正的科学人类学研究,那么,从事自然学科史研究的学者既必须具有扎实的所考察学科的专业知识,同时又具备严格、规范而长久的文化人类学知识训练。否则都是隔岸观火、隔皮猜瓜。可是目下从业人员在知识储备上“不是缺这就是缺那”,要么只能提出自然科学史研究领域的问题,要么只能提出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术问题。要知道,真正的科学人类学必然是兼有自然科学史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两个学科的学术意识,能够提出两个学科各自前沿的学术问题。中国的科学人类学仅仅是个开端,今后需要更多的学人加入。笔者的研究仅是一个尝试,存在的和未来将要面对的问题肯定很多,尚望专家们给予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