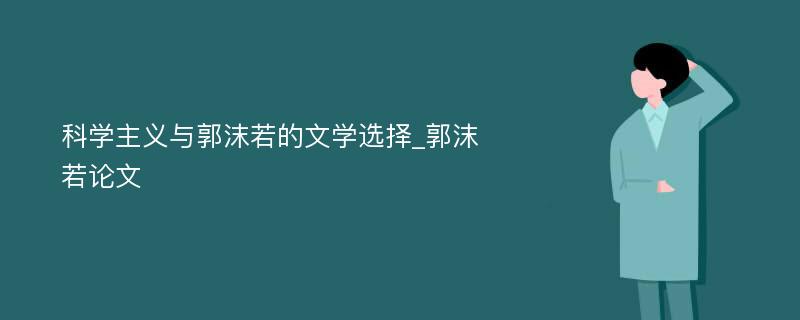
科学主义与郭沫若的文学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科学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论及“五四”文学思潮的动因时,一般为以下几点:一是晚清以来要求文学变革的动势蓄积,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及白话文的提倡等;二是以批判“儒术孔道”为中心的,打破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斗争;三是西方诸种哲学、美学、文学思潮的引进、吸收与激发。但笔者认为,还有一点重要的动因,迄今为止尚未被学界所关注,这就是作为“五四”精神标记的“科学主义”, 对“五四”文学思潮形成的推进与制约。 本文仅以1930年前郭沫若的文学选择为个案,来探索其间的学理逻辑关系。
一
1923年,胡适在论及“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的情况时写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科学,这位“赛先生”,与民主这位“德先生”一道取代了“至圣先师”孔子的地位,成为中国知识界新的偶像。当时,以胡适、吴稚晖、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激进派,竭尽全力地宣扬、传播科学。胡适侧重于把科学当成一种学术研究与拓展的方法,如假设、证验、演绎、归纳等,认为科学可以提高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评判的能力更进步,也就更切近真理。陈独秀对待科学与民主则更带有政治性、社会性的价值信仰态度,甚至渗入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的创造,也就必然地受到其影响和制约。
处在这样历史语境中的郭沫若,以他激进的政治倾向和爱国情操,对科学理所当然地抱着崇奉的心态。加上他在日本所学的又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医学专业,更使他时时以科学的规则规范自我,探索未知,解答课题,乃至影响到对文学性质的判断及文学主张的选择等。
1922年8月, 郭沫若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分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冲动性的人,在写诗冲动时像一匹奔马,冲动窒息时又像一只死了的河豚。他看到了“自己性格的偏颇,意志的薄弱”,便想借助于科学来纠正和锻炼,“我研究科学正想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渐渐坚强起去。我研究医学也更想对于人类社会直接尽我一点对于悲苦的人生之爱怜。”(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页。 )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不仅是疗救悲苦人生的实践性操作工具,而且也是锻炼自我意志力和训练理性思维能力的最佳方式。由此,科学的思维形式、思辨力度,科学的某些学科的术语及内容(尤其是医学),常渗入他的有关文学论文的内理,或作为参照的体系、比喻的意象等,出现在他的论证的逻辑进程中。
对于文学的本质,郭沫若从现代科学的时空论视角着眼,得出了一种异于现有文学理论的独特的结论。他写于1925年的《文学的本质》,开篇的文字就是:“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一种对象总要先把那夹杂不纯的附加物除掉,然后才能得到它的真确的,或者近于真确的,本来的性质。”基于科学的方法论,郭沫若认为,当时关于文学本质之争尚属于非纯净的层面,立足于小说、戏剧一方的,偏重客观,主张摹仿、无我;立足诗歌一方的,偏重主观,主张自我表现、绝对“主我”。这两种主张的极端对立,只有在“净化”之后,寻得如同化学“纯粹元素”、生物学“细胞”一样的文学的“原始细胞”才能得到调整。而这“文学的原始细胞”,它“所包含的是纯粹的情绪的世界”。郭沫若进而指出:“空间艺术的发生是后于时间艺术的”,诗属于时间艺术,在于它是情绪自身的表现;而小说、戏剧属于空间艺术,因为它是构成情绪的“素材再现”,增加了认识的分析及意志的综合等。所以诗先于小说、戏剧,它是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这样,“一切两绝端的主观说和客观说,唯美说和功利说,都可以沟通,可以统一了。”(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352页。)可以看出,论题及论辩的进展,均由缜密的科学方法导引,深蕴着思维逻辑推演的必然性。
对艺术创造过程的论析,郭沫若也多从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出发,他把艺术创造比喻成人的受精、怀胎、分娩。他认为:“艺术是从内部发生。它的受精是内部与外部的结合,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人的受精以至于分娩,在娘怀中总要住九个月以上。在这九个月中的胎儿的营养,自然要仰诸母体。”(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 )形象生动地说明艺术创造过程中,创造主体与所要表现客体之间的双向交流、相互融汇、孕育新质的特点。又如诗的创造,郭沫若认为,它不仅在于符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双声叠韵这些“外在律”,诗之精神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类似“音乐的精神”的异常微妙的、纯粹的“内在律”上,他明确地说明:“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这是我在心理学上求的一种解释”。他还进一步强调:“要研究诗的人恐怕当得从心理学方面,或者从人类学、考古学——不是我国的考据学方面着手,去研究它的发生史,然后才有光辉,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340页。)
即使是在论析艺术的审美性与功利性,即艺术的无目的性与有目的性,这一在当时学界争论激烈的矛盾命题时,郭沫若仍以自然科学的实例来解答。他指出,“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的争执,“不过是艺术的本身与效果上的问题。如一株大树,就树的本身来说并非为人们要造器具而生长的,但我们可以用来制造一切适用的器物。科学亦如此。如自然科学,纯粹科学的研究是在探讨客观的真理,人类即使不从而应用之,其所研究之真理仍然存在。”(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 正如科学寻求到真理首先具有客观的纯粹性一样,正如大树首先是为自身类的预定目的而生长的一样。至于而后用之盖房或造床的实用功利目的,则是后起的效果问题。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审美判断第三契机的深奥而玄妙的命题,在郭沫若引入科学的例证后,得到清晰浅显的解答,颇有举重若轻之感。
如果说上述事例是在学理的层面上表现出郭沫若对科学的理性遵从的话,那么,在另一向度,即在感性乃至潜意识的层面上,更能体现出他那崇奉科学的热烈程度。1920年2月, 田汉到博多湾首次探访郭沫若,而后,两人乘火车前往太宰府。郭沫若事后在给宗白华的信中是这样描绘当时的心境:“火车在青翠的田畴中急行。好像个勇猛忱毅的少年向着希望弥满的前途努力奋迈的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我’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在当时工业文明的代表——蒸汽机车的轰鸣声中,他与其声响节奏融化一体,情不自禁地吟诵起美国立体派诗人麦克司·威伯的《瞬间》一诗。科学,代表着希望;科学,充满了前途;科学与大自然、与生命个体亲密无间,完全“合而为一”了。这,就是郭沫若当时对科学痴迷的形貌。
诗歌为情感的外化与凝定。写于1920年6月的《笔立山头展望》 一诗更是郭沫若对科学和工业文明的一首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赞歌:“大都会的脉搏哟!/生的鼓动哟!/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若以20世纪末全人类共同奉行的环保意识来衡量的话,郭沫若几近于在赞美、歌颂“工业污染”。形形色色的打着、吹着、叫着、喷着、飞着、跳着的工业机械的运动,成了社会生命的脉搏;而笼罩蓝天的烟幕,竟让他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口来;轮船烟筒吐出的黑色浓烟,居然成了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成了世纪的名花,成了人类文明生身的母亲。现在看来,这是荒诞的,但这正是郭沫若当时真实的情感写照。当然,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对前人的作品作出苛刻的审美判断,但从中可以明晰地看出,郭沫若当时对科学在情感态度上的崇奉及价值判断上的认同。
二
上一部分,笔者以实证的方式论述了郭沫若对科学的崇奉与迷恋的情况;那么,这一趋向如何影响,即如何导引或制约了他当时的文学选择呢?以下笔者将以推理的方式来释解郭沫若缘何摒弃浪漫主义,而趋近于表现主义这一谜题。
笔者曾就创造社与浪漫主义关联的问题查阅过有关的资料,并做了累计。如:1922年8月,郭沫若的《创造》季刊《编辑余谈》;1923 年,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1923年,成仿吾的《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1926年,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1927年,郁达夫的《文学概说》;1928年,冯乃超的《冷静的头脑》……,这些文章均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持摒弃、批判,以至否定的态度。郭沫若甚至这样写道:“在欧洲的今日已经达到第四阶级与第三阶级的斗争时代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载1926年5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把浪漫主义文学推演为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政治上“反动”的文学形态,对其批判与否定已达到极限。就此否定的原因,孙玉石先生曾作过分析:“问题不在于怎样回顾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和自身命运的历程,而在于自我构建而又自我摧毁的这种艺术悲剧所根源的‘左’的思想和畸形思维的绵延,持续在诗歌和艺术领域里不断制造自身的萧条和毁灭。”(注:孙玉石:《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36页。 )笔者以为,问题恰恰在于不对中国所谓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历程作一次历史的回顾,而把答案仅仅断定为“左”的思想和畸形的思维所导致的。文艺上“左”的思想,可以成为郭沫若否定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动因之一,但更重要的事实是,郭沫若在1930年以前,就没有表示过他是以浪漫主义构建自我诗歌美学体系的。既未构建,何来“自我摧毁”呢?单一的政治倾向毕竟是外在动因,正如孙先生惯常所提倡的那样,作家的艺术选择更多的是出自艺术发展的内部规律,是为它所制约的。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摒弃浪漫主义呢?其内部规律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原因之一,在于他对科学主义的崇奉,从而对浪漫主义持否定态度。
1922年4月, 茅盾发表《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一文,内中一段话与本论题有关:“老实讲,中国现在提倡自然主义,还嫌早一些;照一般情形看来,中国现在还须得经过小小的浪漫主义的浪头,方配提倡自然主义,因为一大半的人还是甘受传统思想古典主义束缚呢。但是可惜时代太晚了些,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元素,绝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注:《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版,第187页。 )20年代初,由于科学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坛也盛行一种属于科学性质的“文学进化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各种文学流派成了此起彼伏、彼此取代的浪潮。按茅盾的意见,当时中国文坛应跳过浪漫主义这一阶段,原因是“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当年7月, 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看法。(注:《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版,第242页。)那么, 浪漫主义与科学主义有什么内在关联与矛盾呢?为什么科学方法盛行,浪漫主义就应该退隐而去呢?关键是要解答这种对立与矛盾究竟是什么?茅盾所说的“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元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这“别的元素”究竟是什么?
这就必须溯源至西方作为哲学、美学的浪漫主义思潮萌生的端点。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认可卢梭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而代表浪漫主义思潮诞生的理论著述,则是他发表于1750年的《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文中充溢着卢梭强烈的反封建的激情。他猛烈地抨击了18世纪法国封建专制社会的虚伪与腐朽,揭示了贵族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民众的贫困之上,但更重要的是,他把科学、艺术、文化和资产者的掠夺及上流社会的奢侈腐败、道德沦丧等联系在一起:“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注: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他第一次把科学技术与文化及其所促成的初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等,置于人类历史的审判台之上。的确,从20世纪末的视点来反观、反思,“人类的骄傲”、“野心”、“贪婪”等,已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隐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但同时也带来它的负面效应:人的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人与自然环境、自然本性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的泛化让人的价值与尊严沦落,技术思维的隘化使人的生存诗性丧失等……。这一异化的现状促发卢梭以始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的警觉与思索,他们提出经久不息的质疑,进行持之以恒的批判,亦即现在学术界所说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这就是人类思想史上浪漫主义思潮的渊源及其深层的本质内涵。因此,浪漫主义在本质基点上是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上述茅盾所指出的,浪漫主义文学里“绝对不适宜于今日”的“别的元素”,也就是其所内蕴的反科学主义的要质。弄清这一问题,郭沫若摒弃浪漫主义的原因也就可以释解了。
1936年,郭湛波先生出版了《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认为此前50年,中国思想界论战有以下五次:“孔教”与“文体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其中第二次、 第三次论战均涉及到科学主义问题。在“东西文化”论战中,胡适、吴雅晖、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方,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欢迎西洋文化;而另一方,则以梁漱溟、梁启超为代表,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的,西洋文化是物质的,应拥护中国文化,反对西洋文化。特别是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中国赴欧观察组成员目睹了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思想混乱,精神失落,这一切都使他震惊不已。但他更关心的是战祸及危机的根源,他也像卢梭一样把它归罪于“科学万能”论:“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的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注:《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梁启超此说, 极大地震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并引发了第三次,也是历次中最激烈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1923年2月, 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对科学万能的倾向提出质疑,要求重新审视精神的价值; 同年4月,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进行反驳,他称张君劢等为玄学鬼,意即沉溺于虚幻之境中,他主张只有科学精神才能对人生观的树立起积极的作用。
在这一历史语境中,郭沫若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1923年6月, 郭沫若发表了《论中德文化书——致宗白华兄》一文,在文中论述欧战的一段文字之后,特地加上注释:“此处有意反对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该书正尽力鼓吹科学文明破产。”亮出自己反梁、拥护科学的鲜明的立场。郭沫若分析道:“此次大战,欧洲人所受惨祸诚甚深剧。然而酿成大战的原因,科学自身并不能负何等罪责。科学的精神在追求普遍妥当的真理,……唯在资本制度之下而利用科学,则分配不均而争夺以起。”(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 第151页。)这一分析,几乎与丁文江如出一辙,不妨引录比较。 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中写道:“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注: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由此可见,郭沫若当时是坚定地站在主张科学主义的一方,态度十分鲜明。尤其有意思的是,1923年8月, 郭沫若写了《自然与艺术》一文,有两段文字,最初发表时为:“但是到了近代,文艺又成了科学的奴隶了。自然派的末流,他们的目的只在替科学家提供几个异常的材料。”收入《文艺论集》时,把“科学”与“科学家”二词改成“市侩”与“变态心理学家”。(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这虽然只是小小的更动, 但从中也透露出郭沫若对科学崇尚的态度。
在《论中德文化书》的末段,郭沫若再次强调:“我国自佛教思想传来以后,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要救我们几千年来贪懒好闲的沉痼,以及目前利欲薰蒸的混沌,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把接受西方的科学作为唤醒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的前提,其倾向性尤为明晰。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对于“东西文化”的对立矛盾,所持的态度不像胡适和梁漱溟那样走极端性。他认为中国古代精神和希腊文明两相契合,都是一种“活静”,是一种动的群力合作的平衡状态,即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祈求静的日神式的表现。两者都包含科学的内涵,中国古代像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始作八卦;像《诗经》中天文学知识之丰富;像《墨子》中的伦理学、物理学之萌芽;像邹衍的归纳法,惠施的学说等等,都“具有纯粹科学的面目”。现在,世人均把希腊文明当作近代科学之母,那么,我们也“不能忘情于我国的传统”,所以“科学文明不当加以蔑视”。(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58页。)
总之,在1923年中国思想界的“科学与人生观”这场论战中,郭沫若是以鲜明的态度支持科学的,具有明确的科学主义倾向。如前所述,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萌生,其本质要义是反对科学主义的,是反对科学技术所促生的工业文明,是“现代性”的自我批判。这一本质要义也就是茅盾一再指出的浪漫主义内含的“不适宜于今日”的“元素”之所在。因此,作为科学主义的崇奉者的郭沫若,当然不会去选择在“文学进化论”流程中已属于“过去”,属于历史流逝中的反科学主义的浪漫主义美学及文学思潮。
三
那么,郭沫若当时的文学选择是什么呢?学术界已有人提出:趋近于表现主义。笔者以为,这一命题是正确的。综观1926年以前郭沫若的文学主张,他明确地表示肯定,“共感”的艺术流派唯有“表现派”这一家。1923年8月,在《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一文中, 他批评道:19世纪的文艺是“受动”的文艺,像自然派、象征派、印象派、未来派,都是“摹仿”的文艺,都还没达到“创造”的阶段(笔者提请注意,浪漫派连提及的资格都没有)。他呼吁:“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能符合这一美学创造要求的,当时看来只有表现主义流派了,所以郭沫若激动地“共感”道:“德意志的新兴艺术表现派哟!我对于你们的将来寄以无穷的希望。”(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在1932年所写的《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回忆20 年代初创作《棠棣之花》等诗剧的情况,他表白说:除了受歌德影响之外,“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妥勒尔的《转变》,凯惹尔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赏的作品。”(注: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这说明表现主义流派在当时郭沫若的文学选择中是占据着较重要的地位的。
那么,郭沫若当时在文学创作上为什么要选择表现主义流派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表现派重视心灵、崇尚主观的倾向与郭沫若关于文艺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按鲁迅所译的日本片山孤村的《表现主义》一文,表现派的状况比较复杂,“但要而言之,隐约地推崇着心灵,精神,自我,主观,内界等,是全体一致的。”(注:鲁迅:《壁下译丛》,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41页。)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回忆做诗剧所受表现派的影响时,还有一段话:“那一派的人有的是崇拜歌德的,特别是把歌德‘由内而外’的一句话做为了标语。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译过了之后的我,更感觉着了骨肉般的亲热。”(注: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表现派从主观的“内界”,表现自我的心灵,这与郭沫若主张文学的本质是“情绪的世界”,是“内心的要求”,遥相合拍。郭沫若在《文艺的生产过程》中还引用表现主义理论家朗慈白曷教授的一段话:“艺术是现,不是再现”,他认为“这句简明的论断,把艺术的精神概括无遗了。”(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可以看出当时郭沫若对表现主义认同的程度,所以他才会对它感到“骨肉般的亲热”。
第二,表现派强调“动”的精神与郭沫若当时的反叛意识、创造情绪相一致。片山孤村指出,表现派第二个要质是:“将他们所要表现的精神(心灵,灵魂,万有的本体,核心),解释为运动,跃进,突进和冲动。‘精神’是地中的火一样的,一有罅隙,便要爆发。一爆发,便将地壳粉碎,走石,喷泥。”(注:鲁迅:《壁下译丛》,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46页。)在《论中德文化书》中,郭沫若就一再强调要把中国古代传统中“动的文化精神恢复转来,以谋积极的人生之圆满。”(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动”就是要拯救我们这衰老僵滞的民族精神,创造一个“再生的时代”。郭沫若写于1923年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精神不许我们退撄。我们要如暴风一样唤号,我们要如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迸射出全部的灵魂,提呈出全部的生命。”(注: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27日。)连文词几乎都和片山孤村的描述一致。片山孤村认为,表现派在哲学上受到“尼采和伯格森的影响,则将现实解作运动,发生,生生化化,也见於想要将这表现出来的努力上。”(注:鲁迅:《壁下译丛》,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42页。)郭沫若在1920年致宗白华信中也已谈到对伯格森的认同:“《创化论》我早已读完了。我看柏格森的思想,很有些是从歌德脱胎而来的。凡为艺术家的人,我看最容易倾向到他那‘生之哲学’方面去。”(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柏格森关于“生命冲动”,“意识绵延”,在创造进化的运动中所产生的神秘的力量,都和郭沫若“神会”式、“直觉”式的艺术观念合拍,这就使他和表现派在精神内质上自然地相互沟通,彼此融汇。
第三,表现派对丑陋现实的抗争行为与郭沫若当时改革现状的强烈要求相一致。若按美学倾向来说,表现主义也是对科学、科技理性及其所促成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持警惕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它接近于浪漫主义。但两者之间又有所不同,如果说浪漫主义在批判中呈示为一种柔性的,向后看的忆恋的话;那么,表现主义在批判中则呈示为一种刚性的,向前寻索的突进。因为表现主义要求最大限度地肯定生命本体,勇于与一切压抑生命的逆向力量相抗衡。片山孤村说:“表现主义却是对於现实的争斗,现实的克服,压服,解体,变形,改造。”(注:鲁迅:《壁下译丛》,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47页。)在这一向度上,如果科学主义能给予支撑的话,它也会接纳之。例如,惠特曼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美洲这个“新大陆”的赞美,以及对感性的“带电的肉体”的生命的讴歌,都说明它对科学主义不是绝对排斥的。像郭沫若类似惠特曼诗风的《天狗》、《凤凰涅槃》、《匪徒颂》等,也都充溢着表现主义的精神及气势。更重要的,“表现派是开首就提倡非战论,平和主义,国际主义的,则内中有许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注:鲁迅:《壁下译丛》,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42页。)表现派的大多数成员介入了反对“一战”的实际斗争,研究“从战争唤起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且其中一部分成员还是社会主义者,同情无产阶级,这一政治倾向更使郭沫若感到与表现主义的“亲和”。因为当时郭沫若已朦朦胧胧地感应到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召唤:“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注:《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在这样的政治性、社会性价值取向的导引之下,趋近于表现主义自然是当时郭沫若最理想的文学选择了。
标签:郭沫若论文; 科学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郭沫若全集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