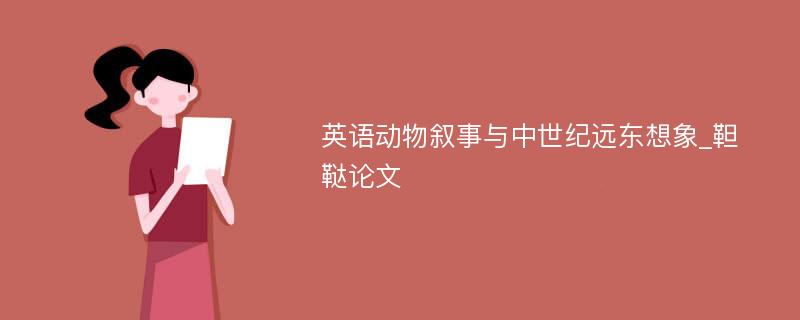
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与远东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东论文,动物论文,纪英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远东”主要指今天的太平洋西岸、北冰洋以南和澳大利亚以北地区,也是今天地理学中的东亚地区。①它和“近东”、“中东”合在一起统称为“东方”。这是殖民时代开始之前欧洲人以欧洲文化体系为中心进行划分的结果。西吉斯指出,在马可·波罗之前,拉丁基督教国家把从君士坦丁堡到世俗乐园的范围看作是东方,它里面充满了奇特和恐怖之物(Higgins 3)。13世纪到14世纪,英国本土陆续出现了几位在作品中书写或记录远东的作家:巴特洛迈乌斯·安戈里克斯(Bartholomaeus/Bartholomew Anglicus,1203-1272)、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1200-1259)、约翰·曼德维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14世纪)和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在借鉴欧洲大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动物叙事和远东想象结合起来,以此定位他们的文化身份,构建起中世纪英国人想象的远东世界。 拉丁文作品中的动物记述和远东构建:《物之属性》和《编年史》 中世纪英国人对远东的书写首先来自安戈里克斯的百科全书和帕里斯的编年史。他们在英国率先谈及对远东的看法,具体涉及印度和中国。安戈里克斯出生在英格兰,曾在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神学,后在巴黎大学讲授神学,是方济会百科全书作家。约在1230年,他用拉丁文撰写了《物之属性》(De Proprietatibus Rerum),许多人认为这是中世纪第一本重要的百科全书,用以教授方济会修士和供普通读者阅读。全书分为19卷,主要涉及天文、宇宙学、医药和动物学等知识,地域涉及欧洲国家,又包含东方国家,尤其细述了对印度的看法。安戈里克斯指出,印度有金山,是全世界最辽阔、最富有和最美好的地方。他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一致。库尔克和罗特蒙特指出,除了从前希腊人的记述之外,罗马人对同印度贸易的描述构成了欧洲人对印度印象的基础,即印度是一个富庶的地方(122)。事实上,古罗马著名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采用数据说明印度(Indiae)幅员辽阔,“它的部落和城市不计其数”(Pliny 381)。他指出,恒河边上居住着不同的印度人部落,人们以不同部落拥有的步兵、骑兵和大象的数目说明其富有程度,比如巨大且富有的巴特那市的国王拥有6万步兵,3万头马和9千头大象,“从中你就可以想象他的财富了”(Pliny 389—391)。他指出印度的山民挖掘大量金矿和银矿(Pliny 395),商人甚至找到捷径,“为获得财富的欲望把印度拉近了”(Pliny 415)。显然,安戈里克斯在叙述上和他保持了一致性。 在安戈里克斯的描述中,印度有大型野兽和猎狗,当地居民体型高大,有八指头人和狗头人。印度东部男性没有嘴巴,身着苔藓,不吃不喝,只闻花香和木苹果的香味(Anglicus 94—95;Gray 189)。他描述的印度人和笔下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芬兰人稍显不同,他侧重描写后者的性格、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技术。老普林尼指出,“印度有体形最大的动物:比如印度狗比任何狗都体形大”(Pliny 519)。安戈里克斯和老普林尼的描述具有互文关系。他还指出,印度有一种混合型动物叫蝎尾兽,即人头狮身蝎尾的曼提柯尔(Manticore)。这种动物据说会用甜美的歌声诱惑人,然后将人吃掉。中世纪英语骑士文学《亚历山大国王》(Kyng Alisaunder)同样描述了亚历山大的士兵被曼提柯尔吞噬的情景。可见,狮鹫和蝎尾兽这些充满异域或神话色彩的动物成为印度的象征。 安戈里克斯在文中不断指出他参考了老普林尼的著作,用“正如普林尼说的那样”,“普林尼听说过这些奇景”(Anglicus 94—95)这样的话语说明信息的来源。事实上,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克利特亚斯(Ctesias)在《印度》(Indika)中就记载了印度北部的风土人情,其中包括狗头人、独脚人和蝎尾兽。虽然中世纪西欧人对狗头人的描述主要参照了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但最早的记录应该来自克利特亚斯。老普林尼也在《自然史》中提到了克利特亚斯。索尔特认为,从亚历山大的骑士文学中可以看出印度的自然世界充满敌意和威胁感,印度的动物似乎比其他国家的动物体型大,更为凶猛(Salter 135)。弗里德曼指出,这种再现传统可以追溯到克利特亚斯,他所描述的印度是恐怖的动物和畸形的种族居住的地方,自然规律并不适用于这片土地(Friedman 5)。 显然,安戈里克斯对远东的看法继承了欧洲大陆叙述传统,通过个人阅读、转述和编撰,再现了他想象中的远东。罗斯-里德尔指出,在古典文学和中世纪欧洲奇观记述中,印度通常被描成是一个充满奇观和怪物的地方,而印度人通常被描述成奇怪、可怕的动物,半人半兽,举止奇异,有时甚至挑衅西方人(Rossi-Reder 53)。这种偏见也许和印度历史发展有关。公元前1500年,来自俄罗斯草原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到达印度。据印度最古老的吠陀经典《梨俱吠陀》记载,雅利安人身材高大,眼睛为蓝色,肤色白皙,而当地土著人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没有鼻子,被称作“达萨”,即奴隶(斯塔夫里阿诺斯79—80),他们是雅利安人的敌人。肤色成为区分自由的雅利安人和臣服的土著人的标志(库尔克罗特蒙特48)。雅利安人因此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历史上,雅利安人曾经摧毁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国家,有着辉煌的历史。不管是克利特亚斯、老普林尼还是安戈里克斯,他们从欧洲白种人的视角出发来描述印度,自然和雅利安人容易产生认同感,肤色较深的土著印度人就成为文化他者的代表,以怪物的形象出现。这恐怕更能说明欧洲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在丑化印度人的基础上强化自我优越感。 帕里斯出生在英格兰,是圣安尔伯斯修道院的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插图画家。他秉承此修道院编撰编年史的传统,以编年史家罗格的《历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为基础,用拉丁语撰写了《编年史》(Chronica Majora),时间跨度集中在1236年到1259年之间。期间,大批皇室和上流社会来访者给他提供了重要历史信息,温切斯特大主教罗切斯送给他一本有关东方奇迹的书。他在《编年史》中率先向英国人介绍了来自远东的鞑靼人(tartars),并在所绘地图中标注出了鞑靼人所在区域。②13世纪中期,来自远东的鞑靼人攻打俄罗斯和匈牙利,引起拉丁基督教国家的恐慌,使西欧人闻风丧胆,心存恐惧,遂把他们和“地狱”(tartarus)一词联系起来。莱兹指出,鞑靼人不仅征服了东亚,还征服了欧洲许多国家。1259年,这个王国有着从黄河到多瑙河的广袤疆域,这引起西欧人的恐慌(Letts 25)。 帕里斯沿用了欧洲大陆作家命名鞑靼人的做法。在他的笔下,鞑靼人是来自地狱的人,是撒旦一样的人。他以“撒旦”、“魔鬼”和“怪物”等词语来描述鞑靼人,说明他们与上帝和人类对立。中世纪西欧文化强调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狱的二元对立。这些来自远东的异教徒自然被看作是来自地狱的魔鬼,成为典型的文化他者。他们身穿牛皮,配备铁制武器,“像蝗虫一样布满地面”,“比狮子或熊还野蛮”(Gray 75—76)。他又用“蝗虫”、“狮子”和“熊”的比较来说明鞑靼人低贱、无知和野蛮,持有蔑视和恐惧态度。刘迪南指出,帕里斯对鞑靼人的描述与13至14世纪西欧人游记中的蒙古人形象吻合,即他们是陌生可怕、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形成一种互文关系(17)。在欧洲动物论和文化构建中,狮子是力量和王权的象征,但帕里斯却凸显鞑靼人身上的兽性。这说明以鞑靼人为代表的远东文化和以基督教占据主导位置的欧洲文明对立存在,鞑靼人作为没有宗教律法的异教徒存在。李勇指出,帕里斯对鞑靼人的描述并非他的个人想象,而是当时西欧人的普遍想象。他们的恐惧来自鞑靼人血腥行为的传闻和对鞑靼人缺乏了解。因此,西欧人对中国的认识从早期的巨人形象演变为鞑靼恶魔形象,展现了他们的恐惧心理和文化构建的需要(123—160)。显然,不确定感引发恐惧感和好奇感,在妖魔化鞑靼人的过程中确定了西欧人的文明体系。 安戈里克斯和帕里斯扮演着研究者和编撰者的双重角色,在百科全书和编年史编撰中把动物叙事和文化想象结合起来,采用转述和整理的方式进行。这符合中世纪学者表述思想采用的文学形式。他们既继承了欧洲大陆叙事传统,又表现出对未知人群和未知世界的想象,彰显出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因此,他们笔下的印度人和鞑靼人身上呈现出怪物特点和动物性并不为奇。20世纪,西方人仍用这种词语来描述蒙古人。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中西交流史》中称成吉思汗为“嗜血的怪物”、“破坏力极强的野兽”。他指出,蒙古人征战欧洲的时候,法国和德国都“害怕这些蒙古魔鬼”(Soothill 49—50)。这些含有基督教色彩的词语说明远东文化是和以基督教占据主导位置的西欧文明对立的存在,是典型的文化他者。正如赛义德所言,东方不仅紧邻欧洲,而且是欧洲最大、最富有、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最深远和最反复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东方以截然不同的形象、观点、性格和经验帮助欧洲(或西方)界定自我(Said 2—3)。 虚构游记中的远东和动物:《约翰·曼德维尔游记》 约翰·曼德维尔用盎格鲁-诺曼语撰写了《约翰·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研究发现,曼德维尔受欧洲传教士伯郎嘉宾、鄂多立克和托钵士鲁不鲁乞书写的东方见闻的影响,其作品融合了游记、历史作品、百科全书、书信、文学作品和科学论述等不同素材。显然,他是一位做了大量研究的编撰者(Higgins 9—10;Moseley 19—22)。虽然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此作是编撰、抄袭、想象、拼贴而成,但《约翰·曼德维尔游记》现存的三百本手抄本足以说明它比当时风靡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更受西欧人青睐。这本游记以旅行空间的变化可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去圣地耶路撒冷的旅行见闻,第二部分主要讲述在远东的所见所闻,涉及印度、印度洋群岛国家和中国等,作者带着困惑和主观臆断展现了沿途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而动物叙述成为理解文化差异的中介。 曼德维尔对印度人的牛头神崇拜基本出于印象。他写道,关于偶像崇拜,印度人说牛是最神圣的动物,他们的上帝乃半人半牛,原因是人类是上帝创造的最美最好的创造物,而牛是最为神圣的创造物。看管牛的人用金器盛牛粪和尿后交给高级教士,高级教士转交给国王。国王把牛尿和牛粪抹在脸上和胸口,希望他有牛的美德并得到牛的祝福。随后,大臣、王子和仆人会如法炮制。他写道:“在那块土地上,他们的偶像,他们错误的神,有着半人半牛的样子”(Mandeville 124)。在印度教文化中,牛的地位颇高,被看做神祇膜拜,三大神湿婆的坐骑南迪就是一头瘤牛。曼德维尔的看法体现了他的本土意识和文化优越感。原文中大约用了五个“他们说”来表述这种信息来源。他以观光者的视角如实再现,但对半人半牛的神祇做出了他的评价,即“错误虚假的(faulse)”。这是两种不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个人主观臆断。 曼德维尔也描写了印度的狗头人(Cynocephales)。有关狗头圣徒的想法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从希腊文翻译为古英语的文学文本《东方见闻》(Wonders of the East)和《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的信》(The Letter of Alexander to Aristotle)中都提到过这种狗头人。事实上,老普林尼引用麦加斯梯尼说明印度有“八指头人”,“还有一种人是狗头人,身着野兽皮,讲话就是吠叫,靠狩猎和豢养家禽生活,指甲是他们的武器”(Pliny 521)。他对印度其他不同部落的人进行罗列描述,认为他们很奇怪(Pliny 519—527)。这些人具有人和动物的双重特点,他们像人一样用武器狩猎,但像动物一样吃生食和人肉。里奥纳伦指出,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狗头人在中世纪欧洲以他者形象存在。他们的差异为中世纪西方社会构建文化身份提供了二元对立的必要陪衬物。同时,他们和人的相似性使他们成为基督教文化企图压制的恐惧、焦虑、幻想和欲望的客体(Lionarons 170)。作为文化他者,狗头人身上展现的是分类危机感。这和基督教文化对狗的看法有一定的关系。罗斯-里德尔指出,这种带有偏见的描述产生一种奇观感,甚至恐怖感和厌恶感。狗头人非人非兽,属于中间人。这种做法是降低人格,甚至非人化的过程(Rossi-Reder 58)。里奥纳伦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形象,狗头人在西方人想象东方的过程中尤其流行。这种观念使中世纪西欧人把异教徒和其他宗教异议者看作狗,而把宗教他者和狗的关系和异教徒、食人族与狗头人等同起来只有一步之遥(Lionarons 171—173)。因此,在曼德维尔的描述中,狗头人的双重性实际上是东西方信仰和文化冲突的外化,也是英国人对异质文化持轻视态度的表现,进一步说明英国人以彰显印度人的怪物特质彰显自己的主体性,通过创造物种差异凸显英国人作为有信仰的文明人的优越感。 在曼德维尔笔下,印度尼西亚各个岛屿上的人充满怪物特质。他列举了十五种不同的人,例如,“独眼人”、“无头人”、“平脸人”、“雌雄同体人”、“八指头人”和“独脚人”等,用“邪恶”、“可怕”、“丑陋”、“像四足动物”等词语进行评价。这些人既不是人,亦不是动物,呈现出怪物特征,处于物种分类的模糊状态。萨里斯伯里指出,《约翰·曼德维尔游记》的流行程度表现了中世纪人对怪物的关注(Salisbury 149)。莱兹认为,曼德维尔笔下描述的大部分怪物借鉴了老普林尼、索利努斯和依西多禄的记述(Letts 63)。科恩在《怪物理论:解读文化》中指出,怪物指涉的意义超过自身,它是一种移位,是分类危机感的表现,而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催生了怪物的再现,这和宏观层面展现文化的相异性是一致的(Cohen 4—8)。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对于远东的看法大多来自个体想象、个别旅行者的游记和自然主义者的记述。他们对远东地理的不确定感和未知感引发了恐惧感、好奇心和窥视欲。这种复杂的情感在确定投射物和对客体认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在曼德维尔笔下,居住在拉莫里(即今天的印尼苏门答腊岛)、印度和蒙古的人不但贩卖人口,还喜好吃人肉,成为食人族(Mandeville 127,134,158,175)。因此,远东人成为文学景观,曼德维尔成为文化或文学观光者。在“看”与“被看”、“想象”与“被想象”、“书写”与“被书写”之间,曼德维尔表现出把远东文化看作是文化他者的思维定势。这些被怪物化的人和食人族成为曼德维尔认识自我本体地位和建构自我文化心理的他者,是他的动物帝国主义意识实践的对象。 需要注意的是,曼德维尔在写到中国的时候表现出艳羡之情,态度明显宽容。西吉斯指出,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没有哪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占据了那么多的文本叙述空间。通过说明鞑靼人的祖先是诺亚的儿子哈姆,曼德维尔填补了《圣经》中的空缺,把鞑靼人带入到基督教历史之中(Higgins 157)。曼德维尔认为广东比巴黎繁华,那里有各种不同的鸟,有白色大雁,像英国的天鹅,头顶有红色圆点;广东人喜用蛇招待贵宾;富人喝马、骆驼、驴和其他动物的奶。他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并和威尼斯进行比较,居住在杭州的和尚通过摇铃组织动物用镀金的银器吃食物。曼德维尔在文中还不断彰显中国的繁荣和辉煌,用“高贵”、“富有”、“伟大”、“卓越”描述中国,认为没有人比鞑靼的可汗更伟大、更富有和更强大。可汗的城池中有天鹅、鹤、苍鹭、鸳鸯和其他鸟类,城外有鹿、兔和麆鹿等。不管可汗何时想狩猎或驯鹰,他都可用猎鹰捕杀野禽,指挥猎犬追杀鹿而不必离开房子。通过对不同动物的描写,曼德维尔说明中国皇室过着贵族生活,和当时的欧洲贵族相似,既猎鹿,又驯鹰。这些动物成为皇权的象征,强化了他们的贵族身份。中国皇宫的工艺品、赠品、陪葬品以不同的动物或动物造型为主,显示出这些动物的特殊社会交际价值和文化意义。他对孔雀工艺品的赞美表现出对中国人智慧的肯定和对处于政治霸权地位的中国的艳羡。曼德维尔借用中国人的话语指出,中国人在科学和技艺方面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因此中国人自认为用“两只眼”看世界,基督徒用“一只眼”看世界。洛克里指出,“曼德维尔这种表述方式借自雅克·德·维特里,后者认为独眼巨人把有两只眼的动物看作奇观,但曼德维尔在认识上的本土化把欧洲人描述为独眼人,把中国文化和知识的广博用两只眼睛来估算”(Lochrie 597)。显然,他间接性地把欧洲人和独眼巨人等同,把中国人和有两只眼睛的动物等同,暗含着东方是奇观的意味。为了表示尊重,可汗的同族赠送给皇帝盛装的白马、狮子、豹子及其它走兽、鸟、鱼和爬行动物,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有生命的创造物都应该尊重皇帝并服从于皇帝。皇帝派遣专人看管矛隼、猎鹰、兰纳隼、雀鹰和夜莺等不同鸟类,还豢养一千头大象(Mandeville 152—153)。可汗死后,陪葬品有母驴和小驴、配备马鞍的马以及身上摆满许多金银珠宝的马。这样做的目的是皇帝还可以继续喝奶和骑马(Mandeville 159)。 曼德维尔通过对不同动物的描述来证明可汗的威严、权力和高贵。这与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一脉相承,展示了中国皇宫的富丽堂皇。姜智芹指出,曼德维尔幻想的富庶玫丽的中国是一个世俗天堂,而此时的英格兰非常需要物质化的异域形象来获得一种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启示。曼德维尔笔下的中国形象旨在颠覆基督教对人性中世俗欲望的压抑和泯灭(118)。究其原因,这和中国在西欧形成的政治影响有关,而中国成为英国人想象中的文化乌托邦的代表人物。这种态度在曼德维尔再现不同地域的天葬风俗时同样表现出来。他认为坎菲罗斯岛和安德曼群岛上的这种风俗是“邪恶的风俗”,而这些人是“邪恶而残忍的人”(Mandeville 134)。但是,在描写西藏的天葬风俗的时候,他认为里伯斯(即西藏)是个美丽的地方,属于可汗,盛产玉米和酒,那里的人为了“给予父亲荣耀”而举行天葬(Mandeville 186)。 曼德维尔笔下的动物叙事是不同文化空间的外在表征。这些描述既是印象式的,又带有英国人“看”远东人的好奇和偏见,甚至夹杂着恐惧感。他既突出人和动物之间物种差异的模糊性,又以不同的动物来证明人的社会地位。在他的叙述中,远东体现出野蛮性、模糊性和怪物特质,但又是高度文明和发达的地方。他既寻找文化的共性,又企图扩大文化的差异性。他的描述回应了西欧人对远东的文化想象,而此书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证明这符合西欧人对远东人的刻板看法,即远东是荒谬、非正常、异域和非理性的代名词,又是文化乌托邦所在。 骑士文学中的远东和动物叙事:“扈从的故事”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大部分故事背景设置在欧洲大陆,但“扈从的故事”(The Squire's Tale)却设在远东,即鞑靼人的土地上(land of Tartarye)。林奇指出,学界研究表明,乔叟对东方和蒙古比较了解(Lynch 531)。滨口惠子认为,“在书写鞑靼世界的时候,他(乔叟)可能受益于中世纪晚期的东方主义者,诸如马可·波罗、曼德维尔、蒙古传教士、伯郎嘉宾和鲁不鲁乞”(Hamaguchi 50)。故事中,鞑靼国王成吉思汗(Cambyuskan)庆祝生日,一位骑士代表阿拉伯及印度之王给成吉思汗献礼,礼物是一匹黄铜骏马、一面魔镜、一枚魔戒和一把利剑。国王把戒指给了公主卡娜斯,魔戒能够助她听懂鸟语。卡娜斯听到一只雌性游隼在哀鸣,问及原因,这只游隼讲述了她被雄性游隼抛弃的痛苦经历。在王子坎巴鲁斯的调解下,雄性游隼悔过自新,重新回到了雌性游隼的身边。这则故事充满远东文化元素,铜马和游隼具有很深的文化含意。 故事中,骑士指出,不管什么天气,铜马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带国王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还可以像鹰一样飞翔。大家对马的来源表示猜测。费勒指出,不同的猜测说明,成吉思汗宫廷贵族担心骑士会带来致命问题,表现出想对来自异域的东西进行解释和驯服的冲动(Fyler 6)。扈从对远东的想象使他认为这匹铜马不仅具有魔幻色彩,同时具有破坏力。我们知道,当时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给西欧人造成了政治威胁,使他们心存畏惧感,又有好奇感。故事中提到的特洛伊马潜在表明了扈从对异教徒蒙古人的恐惧。他既强调成吉思汗宫廷的异教色彩和贵族气息(比如吃天鹅和鹭),又通过对铜马来源的猜测说明英国人对蒙古人的想象。他不仅渲染远东的富庶,说明蒙古人处于政治和文化霸权地位,而且说明成吉思汗宫廷充满魔幻色彩。对于时常服务比武大赛的扈从来说,阿拉伯和印度不过是向蒙古帝国称臣的国度。而成吉思汗对充满魔幻色彩的铜马表现出的兴趣是其征服世界、跨越不同物理疆界的雄心的表现;但铜马突然消失匿迹,这表明扈从在文字表述层面上抑制了驰骋欧洲的蒙古人的征服历程,他在心理上对来自远东的异教徒进行想象的时候充满文化排斥感。 三只鸟作为故事主角有利于扈从理解爱情的含义。他不仅凸显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而且展示了英国人对蒙古人的婚姻观的看法。卡娜斯手戴魔戒,“自然就能完全理解/任何哪一种鸟叫声中的含义,/而且连回答也用鸟语;/所以她立刻懂得那游隼的意思,/出于同情,为她难过得要死”(Chaucer 432—436行)。这其实涉及三种关系:英国年轻贵族(扈从)与蒙古公主(卡娜斯)、人(卡娜斯)与鸟(游隼)的关系、男性(雄性游隼)与女性(雌性游隼)的关系。扈从对远东的想象由雌性游隼和蒙古公主卡娜斯之间的对话构成。这是一个女性化的悲惨世界,悲剧由雄性游隼的背叛引起。卡娜斯安慰雌性游隼,后者“抄着游隼的语言这样开了口”,就这样,“一个在讲自己的苦难,/另一个却哭得泪人一般;/后来那只雌性游隼劝她不要哭,/一面叹气把她受的苦倾诉”(Chaucer 495—498行)。雌性游隼频繁使用的词语有“贞操”、“名誉”、“爱情”、“意志”、“忠诚”、“背叛”。她们之间的对话是讲述者/作者—听众/读者的对话,是语言和情感的互动。克瑞恩指出,卡娜斯和命运悲惨的游隼之间产生同情,这说明扈从把女性和动物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此紧密,以至于鸟比卡娜斯更能生动地说明女性的地位(Crane 67)。这牵扯到物种与性别的问题:鸟-人,异域游隼-蒙古公主。雌性游隼向蒙古公主卡娜斯倾诉自己被背叛的爱情故事,说明了外部世界的诱惑和危险。 卡娜斯和雌性游隼之间的身份认同成为这个故事的焦点。滨口惠子指出,被抛弃的雌性游隼对卡娜斯产生了影响。她可能警告卡娜斯要注意外面世界的危险而不要离开鞑靼宫廷。她的哥哥从中协调,使雄性游隼回到雌性游隼身边,这可能使卡娜斯选择宁可嫁给她的同父异母哥哥,也不愿离开鞑靼宫廷(Hamaguchi 57—58)。雄性游隼最后回到雌性游隼身边,原文说他们属于同一类(Chaucer 608行,619行)。这可能暗指卡娜斯和哥哥之间的婚姻。学界一直在争论这个故事的乱伦主题(Hamaguchi 47—52),即蒙古族同父异母兄妹之间的婚姻问题。中世纪时期,西欧人对蒙古人婚姻的印象是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儿子可以娶死去的父亲的妻子,哥哥可以和同父异母姐妹结婚。这个故事隐含了扈从/乔叟对文化他者的想象。这个文化他者体现的是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界限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说明了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关联性和可转换性,而又潜在地表明了他们无法接受的远东婚姻观,即婚姻乱伦的问题。 《坎特伯雷故事》中,扈从、商人和平民讲述故事的主题顺序是:女性背叛婚姻(商人讲述)——女性被抛弃(扈从讲述)——女性坚守爱情(平民地主讲述)。这种顺序符合乔叟对女性、爱情和婚姻主题挖掘所持的态度。扈从通过语言重构远东形象,而平民地主控制任何有关远东的话语讲述,转向讲述发生在法国布列塔尼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爱情故事。可见,平民地主其实是阻止扈从继续谈论远东,目的是停止谈论和乱伦有关的话题。皮尔索指出,扈从没有把故事讲完,因为这个故事逐渐演变为一个可怕的东方萨迦,扈从已无法掌控它(Pearsall 90)。可以看出,这则以“卡娜斯公主-坎巴鲁斯王子”和“雌性游隼-雄性游隼”为代表的充满异域色彩的故事潜在地展示了一个充满欲望的异域世界。扈从在尝试性的构建和想象中,把远东世界和野蛮、欲望、异教、神秘、异域风情和乱伦联系起来。事实上,卡娜斯的故事在奥维德的《女杰书简》(Epistulae Heroidum)和中世纪英国诗人高厄的《情人的坦白》(Confessio Amantis)之“卡娜斯和麦克莱尔的故事”中都已出现,是关于卡娜斯和同父异母哥哥乱伦而孕并最终自杀的故事。这两则故事未明确指出故事发生地点,但扈从/乔叟把故事发生的场景设在了位于远东的鞑靼王国。可见,扈从/乔叟以此表明他们对远东所持的矛盾心态:他们认为远东神秘富庶,充满魔幻色彩,但对蒙古人的婚姻风俗持有偏见,以含沙射影的方式谴责蒙古人的婚恋观,凸显了鞑靼人的他者性。 在《坎特伯雷故事》中,“修士的故事”、“律师的故事”和“修女院院长的故事”发生在中东或近东,再现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扈从的故事”不含宗教色彩,反倒充满异域色彩,表现出乔叟对远东的文化想象。乔叟通常采用动物意象来表征人性,进行说教,但“扈从的故事”中铜马的消失是对远东文化的排斥,而雌性游隼的故事更表现了乔叟对发生在远东的爱情和婚姻的偏见,以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书写说明了英国人对曾经驰骋欧洲的鞑靼人的想象和重构。 13世纪到14世纪,英国文坛处于多语种进行文本生产的时期。安戈里克斯、帕里斯、曼德维尔和乔叟书写了他们对远东的想象。他们不像中世纪英国寓言作家玛丽和奥托一样借助动物讽刺社会,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借鉴了欧洲大陆各类文献,在记载、转述、改编、想象和重写的过程中,呈现出偏好选择,延续了西欧人坚守的意象体系和文化翻译策略,和欧洲大陆的远东叙事传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可见,远东想象和文化翻译使英国人定位自身文化身份,有助于他们融入欧洲大陆文化圈。通过他们的动物叙事,远东呈现出双重性特点,既是富庶的文明之地,又是怪物充斥的野蛮世界;既是文化乌托邦的代表,又是文化他者的代名词。 ①关于东亚地区名称的变化和指涉范围,参见庞希云:《东南亚文学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7-ll。 ②中世纪欧洲人通过地图展示物理空间发展历史和空间身份。在“T-O”地图中,耶路撒冷位于地图中心,说明了基督教的扩张活动和范围,但十字军东征和商贸的发展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帕里斯绘制了两张“巴勒斯坦地图”,以图片方式展示了东行路线图。东方位于地图上方,鞑靼人位于地图最东北端突出的区域。See Alfred Hiatt,"Mapping the Ends of Empire," Postcolonial Approaches to the European Middle Ages:Translating Cultures,ed.Ananya Jahanara Kabir and Deanne Williams(Cambridge:Cambridge UP,2005)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