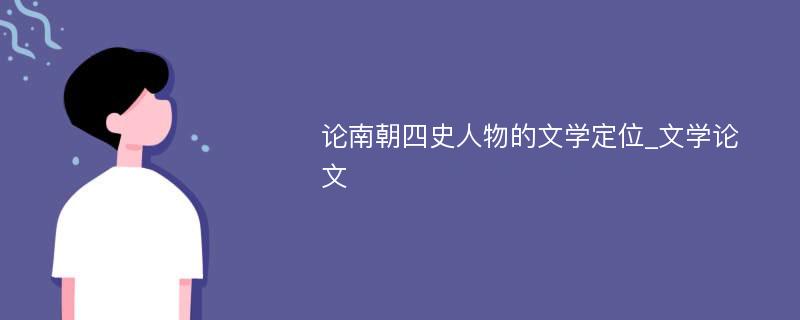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传人论文,文学论文,四史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常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中云:“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故据唐宋人之言以评论汉魏,每不及六朝人所为的;据近人之言以评论六朝,亦不如唐宋人所见较确。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1] 罗氏所言未必完全正确,但他指出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历史上文学的认识也会发生各种变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其时人对于文学现象的认识与评价。这确是很好的意见。纵观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文学发展的阶段性、连贯性及其所呈现出的放射状扩延趋势还是较为明显的。从刘宋时起,帝王宗室、高门士族对文义的爱好和赏会充斥于史书的记载中。他们对文学的崇尚和提倡,承继了魏晋文学的创作实践,结束了东晋百年间玄学哲理的笼罩,同时也奠定了各重要文体的创作基础。由于四史俱为纪传体,因而作家作品论成为史书反映文学发展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
一
在南朝四史中,史臣加以强调的文人与今天文学史所肯定的虽然有相同之处,但还是存在着很多不同。一些经典作家如谢灵运、谢朓以及梁代众多文人集团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无论是南朝四史还是今天的文学史都给予了很多的关注,然而还有一些在四史记载中声誉甚高文名甚盛的文人,他们的创作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已经难寻影踪。也就是说,文人作家的经典化存在着两种逆向发展趋势:有一些文人在当时文坛并无盛名,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学标准的变化却逐步为人注意、受到重视;而也有一些文人在当时的文坛声名卓著,却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消失于历史的背后,成为文学史上寂寞的一族。这种变化说明文人作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处于一种被动的被接受的地位,文学标准的变化影响着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同时也体现出史臣作为同时代人,他们对这些文人的评定与后人的判断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差异。因此,历史人物的文学定位存在着一个动态发展的变化过程。然而,史臣对文人作家的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后人的感性认识和价值判断,如果我们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进行观照,就不能忽视史臣在这些文人基本定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一定的导向作用。
现以陶渊明为例,对史书中文学人物的成相过程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我们知道,沈约作为南朝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史书的撰作还是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在沈约的《宋书》中,陶渊明被列于《隐逸传》中,这说明在刘宋乃至南齐时期陶氏主要是被作为一名隐逸的征士来看待的,人重其德胜于重其文。同期文士颜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也只是称誉陶氏的隐逸之德,赞赏他高洁超脱的情操。如其序文所云:
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纤绚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
又诔文曰:
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全宋文》卷三八)
可见,在与陶渊明交往密切的颜延之看来[2],陶氏主要是一位隐居者,因而对他的文学成就并未言及。即使如此,《宋书》史臣还是收入了陶渊明的主要作品,如《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书》和《命子诗》。据内容观之,史臣选录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说明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毋宁说是为了证明他归隐山林、乐于农事的心情。这与引录谢灵运的《山居赋》的目的和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但尽管如此,在一篇不长的传记中连引4篇诗文,这仍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陶氏的诗文恰当地表现了其高尚的情怀。陶渊明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其德行延及其文学。据现有史料的掌握来看,陶氏的文学成就正式受到重视是从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亲自整理陶渊明的文集并作序写传开始,从此世人才对陶氏有了一个全新的评价。萧统先从隐逸之德论述陶氏,然后评价其诗文成就: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进。故加搜校,粗为区目……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陶渊明集序》,《全梁文》卷二○)
他认为陶氏不仅是一位道德高士,同时也是一位与众相异、卓尔不群的文士。陶氏文章独超众类,读后令人感觉心高气爽,有助于反对和抵制其时世重享乐、日渐颓靡的社会风气。萧统另撰有《陶渊明传》,对陶氏的隐逸之德特加阐述。从对征士的介绍到对陶氏文学作品的评价与重视,显示出文学观的发展变化,萧统可谓是给予陶渊明以文学定位的第一人。陶氏在文学史上地位之确定,大体就由后人崇其德而重其文,进而至唐代出现效仿其文学风格的田园诗派之后才形成巨大的影响。
如陶氏这种由隐向显者的实例还有鲍照。《宋书》中沈约附鲍氏的传记于《刘义庆传》中,并载其长文《河清颂》,虽然与史书的体例有所不合,但也显示出沈约对鲍照遒丽文风的重视。在四史中有关时人对鲍照文风的评价和关注的记载较少,惟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鲍氏文风的继承者归于一类,言其“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显示出对鲍氏文风的注意。综而论之,如陶、鲍这样的文人,他们的文名在当时还是比较寂寞的,对其诗风的重视和学习是在唐朝以后。
以上为由隐到显的一种发展方向,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如傅亮、刘孝绰这样在史书的记载中时誉很高、文名甚著的作家,其声名却消歇于六朝之后的评论中,这是由显到隐趋向的代表。《宋书》中对傅亮的文名多有记述,如《傅亮传》中言:“时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又《蔡廓传》中云:“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如此等等,可见在刘宋初期,傅亮虽然不能与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的地位相比,然而就教令文以及表奏等文体的创作来讲,他在当时的成就还是很显著的。《颜延之传》中云:“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与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傅亮对颜延之的作品不仅具有品评资格,并且他的评判深为时人所认同。观傅亮现存作品如《感物赋》、《为宋至洛阳谒五陵表》等,深具情文之美乃是实情。尤其是应用文,的确文质彬彬,声情并茂,其中有5篇被崇尚“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强调“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萧统载入《文选》。梁代以文笔著称的文士任昉更是奉傅亮为楷模(注:《南史·任昉传》中云:“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可见,傅亮的文章作为应用文的典范代表在南朝时期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清代许梿赞其《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以深婉之思,写悲凉之态,低回百折,直令人一读一击节也。”“不甚砍削,然曲折有劲气。六朝章奏,季友不愧专门。”(《六朝文絜》卷五》)可谓推崇备至。《宋书》选载了傅亮的3篇诗文:《感物赋》、《演慎论》与《奉迎大驾于道路赋诗》,以示重视,并体现出傅亮作为刘宋重臣在废立少帝之前的忧惧。由此可见,在宋齐之际乃至梁代,傅亮的文作受到了时人的充分重视。同样的情况还有刘宋名士袁淑,“文冠当时”(《宋书》卷五一《临川王刘义庆传》);刘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何承天,也是久负盛名,《宋书·谢晦传》中收录了他代谢晦所写的3篇自理奏表,自陈忠情,有理有据,殷殷之意可见,颇令人感动[3]。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论刘宋作家:“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飚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可见,刘宋文坛确实是人才济济。但是在今天的文学史中,除“元嘉三大家”之外这些文人的龙章凤彩已经难觅影踪。因此,南朝人对其时作家的认可与今天文学史的观照结果有很大的不同。不但刘宋时代的作家如此,齐梁时代一些著名文士也逐渐消歇于历史的折合中。如吴郡张氏一族,人才辈出,文名甚盛。其中张永、张畅、张率、张充等无不是当时文坛才秀。再如彭城刘氏,族中70余人并能属文,尤以刘孝绰为盛。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其文名在当时决不亚于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焉,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的那种盛况,在梁代文坛自有一席之地。但是今天的文学史中,这些文士的文名俱已消歇,即使如刘孝绰之俊才高秀,后人对他的注意也只是视之为帮助萧统编撰《文选》的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这种变化显示出今天的文学史对南朝作家的认同与南朝史书中史臣的记载对其时文人的认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与后人评判南朝文学的价值标准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
这两种方向的延伸向我们喻示了文学史的面貌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如傅亮等在史书记载中久负盛名、时誉很高的作家为什么渐渐销声匿迹,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与判断很大程度上受着前人评论的作用与影响。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经历了唐宋以来1000多年的选择与评定之后所形成的结果。南北朝之后,唐代文学批判地继承了六朝文学的发展成果,注重诗歌创作,遵循情感、意境、音律相统一的文学原则,倡导创造一种感动人心的审美境界。唐中期的古文运动亦以反对六朝骈俪文为主旨,而傅亮、刘孝绰、张率、徐勉、张缵等南朝文人俱善属文而非吟诗,所作均骈偶成章而与古文形式相悖,如《梁书》中所录刘孝绰的《答湘东王书》、张率的《舞马赋》、徐勉的《报伏挺书》等俱为当时美文。因此,他们身后的寂寞就是由于后人重视诗歌而又反对骈俪的双重因素造成的。在史臣的笔下我们读到的是由这些文士所组成的非常活跃的文坛。这些文人各领风骚的实际创作以及时人对他们作品的认可与摹拟,确定了他们在其时的文学地位。我们尊重千百年来文学经典化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同的认识。史臣通过他们所记载的内容构成了历史上文学原初的相状。
二
南朝四史中文学面貌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做纵向观,则文学人物的数量逐步增加,同时史臣所用的笔墨也就更加繁富和仔细,而且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史臣对史传人物的基本定位主要表现在传记的处理与布置、文人的文学素养和文学活动的表述以及借鉴与吸收时人评论等方面。
(一)史臣对于传记的处理与布置
四史史臣对历史人物的传记布局有一定准则,体现出他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一些看法。早在《史记》当中即有类似实例,如司马迁特设《司马相如传》并大加选录其《子虚赋》和《上林赋》以及《难蜀父老》等文章,就是为了表现司马相如的作品风格及其讽谏方式。同样,《宋书》中沈约特设《谢灵运传》与《颜延之传》,也是因其文才卓著而另眼相待。南朝四史中,史臣对文士的记载从少到多、由简到繁,存在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趋势,而且有些传记还体现着史臣的某种判断。如《宋书·谢晦传》就是一个独特的史例。谢晦出身于陈郡谢氏,乃是晋末宋初的名士。他与傅亮、徐羡之同为刘裕临终所托的顾命大臣,在元嘉三年的政变中以逆反罪名而被宋文帝刘义隆诛杀。在《宋书》的结构安排中,史臣不仅列谢晦专传,还选录了5篇重要作品,显示出非常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史臣对元嘉之变的认识态度。同样,沈约《宋书》对鲍照传记的安排也不排除主观因素在里面,其初衷缘于对鲍照文学才华的赏爱。另外,南朝史书中《文学传》的设立给予文学人物以更大程度的集中和关注,这一体例创式正是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新尝试。史臣对史传人物的传记处理依据时代的需要而发生着变化,也就愈发体现出史臣在传记处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二)史臣对史传人物的文学素养和文学成就的表现
四史史臣对史传人物文学素养的表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直观表现,如《宋书·江湛传》云其“爱好文义”,谓谢灵运“江左莫逮”,等等。史臣通过这样的基本介绍来表现史传人物的文人修养,展现其精神面貌。其次是选取史传人物的文学作品以显示其文学才华,如《宋书》选录谢灵运的《撰征赋》、《山居赋》,《南齐书》选录刘祥的连珠15首,《梁书》中选取张融《海赋》、张缵《南征赋》以及刘峻的《辩命论》,等等。再次是借鉴与引录时人的意见,宋文帝的知赏意见就被《宋书》史臣多次引用,如《宋书·苏宝生传》云:“苏宝生,有文义之美……为太祖所知。”《梁书》史臣言刘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他们以这样的时论来印证史传人物的文学地位,有时还加入更为具体的评论。如《梁书·文学传·何逊》:“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世谓之‘何刘’。世祖著论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最后是加入史臣自己的评价,体现史臣本人的价值取舍。如《南齐书·陆厥传》云:“少有风暨,好属文,五言诗甚新变。”反映了萧子显对诗体变化的关注。再如姚察父子赞扬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梁书》卷三○《裴子野传》),指责江总“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陈书》卷二七《江总传》),又谓王筠“为文能压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美”(《梁书》卷三三《王筠传》),“(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均体’”(《梁书》卷四九《文学传·吴筠》),等等,从而可以看出史臣的褒贬态度和明显的文学批评倾向,而他们的这种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成为今天的文学史对文人作家做出肯定与否定的依据和理由。史臣的意见所形成的这种导向和判断作用对于文人的文学史定位有着直接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南朝四史中有关重要作家的传记表述加以对比,那么就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由简到繁、从少到多、从宏观到具体的变化趋势。《宋书》记述方式较为传统,对史传人物文学地位的评定尤其注重时人的议论。如谓谢灵运作品时人无论贵贱莫不竞写乃至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史臣以刘宋时人这样的直接反映来传达谢氏的文学影响和文学地位。又《颜延之传》云:“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并称颜、谢焉。”可见,《宋书》注重外在的、宏观的时论评价。《南齐书》与《宋书》类似,如谓谢朓“文章清丽”、以文才之著而深为萧子隆赏爱,并借用沈约“二百年来无此诗”的评价来加以印证。不过,相对《宋书》来讲,《南齐书》已经开始注意对作家文学风格的表述,体现出一种进步。发展到梁代,史书对文人作家的记载不仅在数量上骤增,而且史臣对历史人物的文学活动也更加注意,描述也更为详细和具体。如:
(柳)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旧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元长(王融)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萧衍)所美。当时咸共称传。(《梁书》卷二一《柳恽传》)
(张率)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适值任昉在焉,约乃谓昉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
(率)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率又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梁书》卷三三《张率传》)
天监初,(刘孝绰)起家著作佐郎,为归沐诗以赠任昉,昉报章曰:“彼美洛阳子,投我怀秋作。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贬,辖司专疾恶。九折多美疹,匪报庶良药。子其崇锋颖,春耕励秋获。”其为名流所重如此……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
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度支尚书琅邪王筠,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并高才硕学,(江)总时年少有名,缵等雅相推重,为忘年友会。之遴尝酬总诗,其略曰:“上位居崇礼,寺署邻栖息。忌闻晓驱唱,每畏晨光赤色。高谈意未穷,晤对赏无极。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曷用销鄙吝,枉趾觏颜色。下上数千载,扬榷吐胸臆。”其为通人所钦挹如此。(《陈书》卷二七《江总传》)
从所引材料可见,《梁书》史臣对于文士文学素养的描述方式较之《宋书》、《南齐书》已有很大发展,不再局限于简略概要的点评,而是注意文学活动中文士的表现,尤其注重以诗文的形式来显示文士的才华和时人的推崇,叙述更为具体,文士形象也更加丰满生动。这是史传人物文学定位方式的一种改善和进步,也是文学兴盛对史学冲击和影响的结果。史臣通过对史传人物进行多方面的安排与表述,体现出他们在文学定位中所起到的导向作用。史臣材料的选择与价值的取向,影响着后人的总体判断,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史传人物的文学地位。一些史传人物的作品成为经典,为后人所传诵,而也有一些人一度显赫,却在历史的折合中成了附庸。所以,对于文学人物的观照及其文学地位的审视,史臣的表述与评价是我们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标签:文学论文; 宋书论文; 南朝论文; 谢灵运论文; 陶渊明论文; 南齐书论文; 陈书论文; 刘孝绰论文; 诗歌论文; 史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