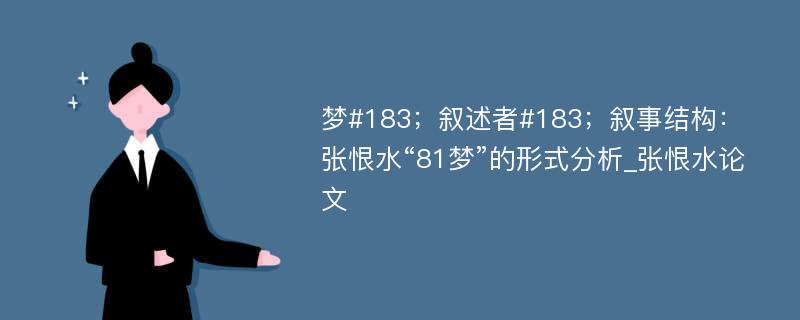
梦#183;叙述者#183;叙事结构——对张恨水《八十一梦》的形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叙述者论文,形式论文,结构论文,张恨水论文,八十一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名家论评
张恨水在回忆自己的写作生涯时曾自述:“事过境迁,《八十一梦》,无可足称。倒是我写的那种手法,自信是另创一格。”〔1〕在我看来,“无可足称”实属自谦,“另创一格”倒是道出了作者在文本创造过程中形式意识的自觉。《八十一梦》也许不是张恨水最好的作品,但在形式上却是最具个性、最富有探索精神的。
一、梦的形式与功能
张恨水曾认为小说有两个境界,一个是叙述人生,一个是幻想人生,而他自己“总是取径于叙述人生的。”〔2〕这就是说他的作品大都是直逼人生的。但在《八十一梦》中,作者却一反旧的叙述方式,不直叙人生,而是将笔伸向“我”的心灵潜域,通篇写“我”的梦中神游。他巧妙地将“叙述人生”融化在“幻想人生”中,使现实与梦幻相互渗透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创造了一个神奇的梦幻文本。
在中国文学史上,写梦是早已有之,如“临川四梦”、“南柯一梦”、“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等。但这些梦要么是传达神的旨意,要么是预示吉凶祸福,要么只是构成人神相约的氛围,缺乏人的主体性,梦往往只是一种迷信的仪式。与之相比,张恨水则以现代精神融注于梦,以梦经纬作品,梦成为文本存在的基本形式,具有独特的文体功能与意味。
首先,梦的形式使文本具有寓言功能。“寓言十九托之于梦”,这是中国文人对梦与寓言关系的理解与阐释,一个梦即是一个意蕴深邃的寓言。张恨水对此体悟颇深,他在文本创造过程中有意追求意义的寓言效果。《八十一梦》中每一个梦都是一个精致的寓言,在其显在的故事后无不隐匿着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譬如第5 梦“号外号外”的显层情节写“我”在抗战胜利的“号外声中”的所见所闻,既写房东与“我”讨价时的变色龙姿态;也写了王老板在抗战胜利的号外声中决计舍弃患难与共的朋友、回南京自谋发迹的心理;还写了命馆算命先生标榜自己早已算出日本必败之日期,所以希望不知何去何从的同胞速来命馆问津。作者通过不同阶层人士在抗战胜利号外声中的言行表现这些显层情节,寓示了更深层的人生内涵,诸如患难与共却不能欢乐同享、“天下事,无论好坏,一切都是富人的机会,一切都是穷人的厄运”、人与人之间永不能沟通等。抗日战争只是中华民族苦难史上的一页,但作品所表现的却远非这历史瞬间国民的人生状态,外在情节构成一种寓言载体,它的寓义指向若干世纪以来国民的劣根性,让人反思近代以来民族大众的深层症结。再如,第72梦以孙悟空终于败在通天大仙的巨掌底下这一外在情节,寓示了乌烟瘴气的重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实。《八十一梦》作为一种“寓言”存在,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其一,它是通体寓言。在一般文体中,寓言只是局部的存在,只是文本的特殊构件,旨在深化某一主题,所以往往可以单独剥离开来独立成篇,而《八十一梦》则是由不同梦整合而为的一个通体寓言。它的每一梦都是一个单独的寓言,这些单个寓言,尽管结构方式、内在关系不同,但其寓指方向是一致的,寓义是相似的。《八十一梦》即是由这些单个梦有机整合生成的一个人生与历史的大寓言。其二,它是现代人编排的现代寓言。叙述者“我”是从现代意识出发,在现代意义的基础上编码的。即使那些古人如子路、墨子、钟馗等也是作为现代符码编进寓言中的,他们不再只是以古人的眼光审视现代世界,他们身上有叙述者的现代精神的投影。叙述者尽管努力做到较客观地叙梦,但现代观念已汩汩地融入到文本的血脉中。其三,在《八十一梦》中,每个人都是作为寓言人物出现的。猪八戒、孙悟空、通天大仙、廉颇、西门庆等各有寓义,他们是作为特定的寓言符码被编排到文本中的,他们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们进入《八十一梦》语境之前孤立存在时所含之义。这些寓言人物被“我”巧妙地编排在一起时,构成一种新的结构关系,使文本具有深远的寓意。其四,它具有召唤审美接受者参与虚构与想象的功能。《八十一梦》中的每一梦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似无缝隙,但在梦与梦之间,尤其是在文本潜在的结构中则存在着大量的艺术空白,为接受者提供了审美接受、参与的多重可能性,它召唤接受者走向文本,以自己的想象与虚构填充这些空白处,参与到叙述创造中来。其五,它具有特殊的劝喻讽刺的审美教化功能。
其次,梦的形式为叙述者提供了较自由的叙述空间。大多数小说的叙述者似乎永远是带着镣铐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一方面叙述对象质的规定性限制了叙述者的自由;另一方面作者的人生观、审美观内在地制约着叙述者;另外直线型的语言在原生态的生活、非语言经验面前的无能进一步陷叙述者于不自由的苦恼中。然而,在《八十一梦》中,叙述者一直生活在梦幻中,他叙述的是离奇古怪的梦,梦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解救了叙述者,为叙述者提供了自由运作的用武之地:其一,梦境的非逻辑性,消解了生活原生态对“我”的制约,“我”不必按日常生活的外在逻辑构思、叙述,而是完全从自己的目的出发,超越时空的限制,自由组构材料。其二,由于梦是一种无意识、潜意识的心理现象,所以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可以违背隐含作者显在的意图,超越隐含作者的限制。其三,梦的荒诞性使叙述者某种意义上能不受语言逻辑的规范,以跳跃的荒诞的梦幻语言叙事。其四,梦的荒诞性还可以使叙述者较少地顾及接受者的欣赏习惯,以荒诞的形式喜笑怒骂。
再其次,梦的形式具有模糊叙事时空的功能。作为无意识、潜意识的心理现象,梦是反物理时空的。在《八十一梦》中,叙述者穿梭于离奇古怪的梦境,有意模糊叙事时空,使我们很难感觉到那种统一的物理时空观。譬如在第10梦《狗头国一瞥》中,“狗头国”的时空存在形式是模糊的:“这地方是大海洋中的几个小岛”;国旗是黑的,上面镶有三个黄色古钱图案;“狗头国”的人嗜糖成癖;狗头国人皮肤是黑色的,额头和下巴突出,有些象狗,眼珠是黄的,有自己的土语;衣服多为黄色西装革履;等级森严,阶级压迫严重。显然,这“狗头国”没有时空标志,它坐落何方不明确;它处在进化发展的什么阶段,属什么年代,这一切皆是模糊的。再譬如第15梦《退回去了廿年》中,叙述者“我”忽地退回去20年,生活在已成为历史的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阴历正月。“我”徜徉于历史的时空,做起飞黄腾达的美梦,得意之时却被死去的祖父、父亲及国文先生训斥与痛打。整个梦境时空交错、更迭,似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八十一梦》时空模糊性的文体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为叙述者“我”的幻想提供了最大的自由限度,他或者穿行于天南地北,或者造访天上人间,过去、现在与未来在他看来已没有实在意义,他似乎生活在自己独特的心理时空中,使整个文体充满着一种神奇的浪漫情调;另一方面它深化了作品的寓言功能,使作品超越了固定时空的限制、获得更深厚更宽广的寓意。
二、叙述者个性及其文体功能
在《八十一梦》中,叙述者通过对特定叙述话语的操作,虚构了一个独特的梦幻文本。与作者其它作品的叙述者相比,《八十一梦》的叙述者具有与自己创造并生存其间的文本语境相适应的独特个性与文体功能。
戏剧化的叙述者。在《八十一梦》中,叙述者直接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出现在故事中,人格化、戏剧化为一位实实在在的人物,变得与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生动。“我”作为戏剧化的叙述者,其个性与功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我”是故事的讲述者,具有叙述职能。每一个梦都是“我”的一次精神漫游,“到了次日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抽笔展纸,把梦里的事情默写出来。”〔3〕没有“我”的讲述, 也就没有整个梦幻文本。其次,“我”是作品中的一位介入式的人物。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叙述者大都是出场但不介入的叙述者,叙述者很少人物化;在张恨水其它作品中也没有完全介入式的叙述者。但在《八十一梦》中,有时“我”完成参与到故事流中,与作品人物进行直接对话,“我”作为一个角色既推动着叙述语流的发展,又丰富了作品的人物画廊;有时,“我”则是一位介入故事中的观察者或见证人,譬如在第10梦《狗人国一瞥》中,“我”与朋友一起来到狗头国,“我”参与到故事中,但只是一位旁观者,观察着自己的朋友怎样与狗头国人做生意及狗头国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狗头国奇异的习俗,狗头国人相互倾轧引起“我”的好奇。“我”只是不时发问,以推动叙述语流。“我”介入到故事中,充当一位观察者、见证人,为提示梦中寓意取开泉引水的作用。再次,“我”与被叙述人物间有一种情感与道德上的距离。《八十一梦》是叙述者以梦的方式对当时种种民族败类进行的批判,体现了叙述者对现实的认识与道德倾向,正如艾特玛托夫所言:“幻想对我来说,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识和注释现实的方式。”《八十一梦》作为对现实的一种认识、注释,即使是较客观地叙述故事,但对投机商人、贪官污吏、空谈家、发国难财者等也有一种强烈的讽刺倾向,批判的精神已化入叙述的血脉中,“我”在情感与道德上与作品中人物间保持着一种批判否定的距离。
可靠的叙述者,所谓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与隐含作者的道德价值观、审美观相同、能够代替隐含作者发言的叙述者。里蒙·凯南认为“可靠的叙述者的标志是他对故事所作的描述评论总是被读者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描写。”〔5〕按这一原则界定, 《八十一梦》的叙述者“我”是一位可靠的叙述者。作者曾在《〈八十一梦〉前记》中谈到自己创作这本小说的原因:“只因为那个时期重庆的一片乌烟瘴气,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将军’们,压在人们头上无恶不作的豪门,不顾死活只知道抢钱的贪官污吏,在官僚资本豢养下的囤积居奇、跑‘滇缅路线’发‘国难财’的商人,无耻下作的文化特务,地主型的房东,大大小小的‘裙带官’,‘拳头也是外国的好’的美国生活崇拜者……这些家伙,集结在重庆,隐身‘抗战’的旗帜下,进行五颜六色的卑鄙、恶毒的勾当。”“愤怒的火焰燃烧着我,我就写。一个、两个……,我最初准备把所看到的都写出来,无知、丑恶的人和丑恶的形象太多了,是写不完的。我所写的,只是比较典型一点的。”作者谈到的这一原因即是其审美创作的意图,它包含着作者的道德、价值观与审美观,且在文本创造过程中自然地转化为隐含作者的理想,构成隐含作者审美建构的全部驱力。然而,正如查特曼所分析的“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不同,他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没有声音,没有直接进行交流的工具。它是通过作品的整体设计,借助所有的声音,依靠它为了让我们理解而选用的一切手段,无声地指导着我们。”〔6〕隐含作者无法直接地在作品中发出声音,他通过文本的整体氛围、语境等无声地控制着文本的意识流向。具体地说,他通过叙述者来实现自己的意图。那么,《八十一梦》的叙述者是否忠实于隐含作者呢?他在道德观、审美观上是否认同于隐含作者呢?隐含作者的意图是否被叙述者完成呢?对诸类问题稍有警觉的读者便不难发现,《八十一梦》的叙述者否神游天堂,或听命于钟馗帐下,或去狗头国一瞥;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叙述使命,隐含作者似乎一直在他体内私语,无形地控制着他的活动。如在“号外号外”梦境中,叙述者“我”对抗战胜利这一历史转折关头投机者的利己心态进行了冷嘲热讽;在“生财有道”中,“我”经由几位亲戚朋友的言行揭示了国统区污浊的环境;在“忠实分子”里,“我”以连珠炮似的发问,对道貌岸然的“忠实分子”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我是孙悟空”里,叙述者化身为孙悟空,勇战妖魔,虽未获胜,但意志弥坚。叙述者“我”或直陈其事,或冷眼旁观、冷嘲热讽,或沉入故事底处,或笑遨故事边缘,但创作旨意始终未变。“我”所建构的梦幻世界,虽是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但“我”却始终拿着一把正义的尺子衡量着是是非非,“我”所具有的对邪恶的批判精神始终回荡在梦幻天际。每一个梦都是“我”借物联想、借物抒情,对正义的张扬。弗洛伊德曾指出:“精神活动是与当时的印象与当时的某种足以产生一种重大愿望的诱发性的场合相关联的。从那里回溯到早年经历的事情(通常是儿时的事情)从中实现这一愿望;这种精神活动现在创造了一种未来的情景,代表着愿望的实现。它这样创造出来的就是一种白日梦,或称幻想,这种白日梦或幻想带着诱发它的场合和往事的原来踪迹。”〔7〕正如弗洛依德所说的, 《八十一梦》中的叙述者“我”往往是在某物的诱发下,产生一种对那不公道世界的批判愿望,在这一愿望驱使下,浮想联翩,神游大千世界的。如在《在钟馗帐下》、《狗头国一瞥》里,“我”都是在某种诱发物的刺激下,唤起对早年某种经验的回忆,从而产生一种愿望,在作品中实现这一愿望的。我们不难发现,叙述者“我”的愿望,正是隐含作者的愿望。“我”始终在维护着隐含作者的审美意图,隐含作者的道德价值观就是“我”的价值观。“我”在文本创造过程中对故事所作的描述与评价体现了隐含作者的愿望,从而被读者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描述。“我”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相当短,“我”完全充当了一位可靠的叙述者。
叙述者的可靠性在《八十一梦》这一特殊语境中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利于艺术地传达作者的创作意图,张扬作者的正气,有利于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诠释;其消极性在于少含蓄,词锋太露,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品的讽刺性。所以,确切地说,《八十一梦》不属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只能被称之为谴责小说。
干预型的叙述者。《八十一梦》的叙述者,如前所论,是一位戏剧化的、可信的叙述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干预型的叙述者。 叙述者“我”的干预可以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指点干预,旨在解释说明叙述方式。这种指点干预在文本中的体现,一是叙述者精心设计的“楔子”,其功能是多重的。首先,它交代了梦的来源,“我寄居北平,曾得了一次作梦的怪病”、“或一日记下二三梦,或一日记一梦,或两三日记一梦,不知不觉写了一大卷纸。点点次数,共是八十一梦”,后来被鼠啮只剩下十一梦。无疑,“楔子”旨在提示叙述人与“八十一梦”的关系,揭示文本的虚构性,它是叙述者实施的一种叙述策略。其次,它揭示了“八十一梦”的现实意义,“再回想梦中的生离死别,未尝不是真事所反映的,又着实增加许多伤感,多少可以渗透一点人生意味”,这就是说梦中情景完全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梦中情景尽管离奇古怪,但每一梦都是作者“一个愿望的履行”〔8〕,是作者反抗现实这一愿望的物化形式。再其次, 它解释了文本的结构特征:“好在所记的八十一梦是梦梦自告段落,纵然失落了中间许多篇,与各个梦里的故事无碍。”这既是对叙述方式的指点,同时也为读者阅读文本提供了一把钥匙。总之,“楔子”是叙述者“我”对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的全面指点,是“我”有意为之的一种叙述策略,也可以说是叙述者为召唤读者特意设置的一个叙述圈套,是对读者阅读行为、阅读心理实施的一种先入为主的控制。指点干预在文本中的另一体现是每一梦的“标题”,如“退回去了二十年”“天堂之游”、“忠实分子”“我是孙悟空”等标题即是叙述者“我”对梦中情景的概括说明,是对文本内容的指示,而且标题本身渗透了叙述者的一种道德价值取向与情感倾向。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梦中情境内容与标题含义是相矛盾的,从而赋予标题一种反讽的特征,于是标题不只具有指点干预的功能,而且它体现了叙述者对文本的一种道德上情感上的参与、一种价值评判,具有评论干预的特性。指点干预的第三个表现是在梦的结尾,叙述者“我”跳出叙事语流,对叙事情节加以指点,宣告梦的结束,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诠释。譬如,第15梦《退回去了廿年》写到“我”父亲与肖先生等正举手打“我”、“我”周身冷汗直冒、昏然躺下时,叙述者却不顾情节的发展,突兀地站出来道破上述一切原是一个梦:“哈哈!当然没有这回事,读者先生,你别为我担忧!”,“我”宣告了上述情节纯属虚构,子虚乌有,叙述嘎然而止。再譬如第36梦《天堂之游》写“我”正欲凭猪八戒介绍寄宿“天堂银行”,却见两位旧友留在桌上的打油诗,看毕汗下如雨。正当读者急切地想知道叙事的发展结局时,叙述者却跳出梦境写道:“你想,我还恋着如此天堂吗?”以此结束全文。叙述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写作,自觉地引出读者“你”,向读者暗示了“我”的态度,从而控制了文本的诠释权。
毋庸讳言,《八十一梦》的指点干预主要脱胎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未脱尽传统章回小说的痕迹。但它已具有自己新的品质,譬如它的每一梦自成段落,并非高潮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且叙述干预者“我”是一位戏剧化的叙述者,不同于传统章回小说中全知全能式的叙述干预者,“我”的视域受到限制,干预方式往往是内在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八十一梦》的指点干预是传统章回小说的开头、结尾程式的现代转型,具有现代小说的品性。
《八十一梦》叙述者干预的另一类型是评论干预。评论干预的目的主要是叙述者对文本内容进行道德评判。在《八十一梦》中评论干预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我”的心理活动方式。当“我”看到听到某种情景时,总是在心里进行分析、取舍。如第8梦《生财有道》中, 当“我”帮亲戚邓进才搬运药箱后,对这位投机者、发国难财者感慨万分:“我想,我怎么会不对呢?就替你省了三分邮票。但我累得周身臭汗,实在喘不过气来答他的话。”心理活动、心理分析是“我”评判事物的一种主要方式。第二种是疑问句方式。在叙述语流中,“我”对梦中人、事处处置疑,总是以疑问句形式向当事人请教原委。“我”的疑问一方面起到了推动叙述进程的作用,构成叙述话语演绎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它传达了“我”对现实、对人生的认识与态度,包含着“我”对特定时期生命形式的价值取舍与道德评判。第三种评论干预方式是议论式。议论或出于“我”之口,如在第5 梦《号外号外》中,“我”于“外号声中”听到见到种种怪事后,直接发议论:“阔的朋友,到了四川以后,更阔;而穷的朋友呢?到了四川,也就更穷了。这样看起来,贫富始终是个南北极。现在要回南京,看这情形,还是那样?”。“我”的议论是“我”对文本意向的直接干预。议论有时出于人物之口,如第5梦是“我”借大街上某人之口道出“天下事, 无论好坏,一切都是富人的机会,一切都是穷人的厄运。”以此对整个梦境作质的定位。再如第10梦《狗头国一瞥》借狗头国人之口,“我”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态度:“外国的耳光是比本国的耳光要值钱一百倍。一耳光下,百病消除。”这种议论往往能取到一种反讽的修辞效果。在《八十一梦》中,议论的方式尽管不同,但都是内在的,是叙述话语的有机部分,是一种戏剧化的议论,这是《八十一梦》中议论的一大特征。第四种评论干预方式是人物脸谱化。在《八十一梦》中,人物大都缺乏个性、缺乏性格史,他们往往只是一种抽象的符码,如万士通、魏法才、马知耻等,他们的性格是先验的,不变的,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作为“类”出现的,他们身上有叙述者过于直接的道德渗透,体现了叙述者对文本的一种干预与控制。
总之,干预是叙述者“我”控制叙述流程,控制读者对文本诠释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尽管“我”的干预意识过分强烈,干预方式太明显,缺乏艺术的含蓄,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本的艺术性;但“我”的干预总的来说是内在的,是叙述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戏剧化干预的尝试,所以,相对于张恨水其它作品,《八十一梦》的干预方式更富于现代意味,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三、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与小说文本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八十一梦》的叙事结构由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构成。
表层结构指的是作品的外在构架。在《八十一梦》中,它是由“楔子”“正文”与“尾声”三部分构成。“楔子”与“尾声”是叙述者对“正文”的指点干预,交待“正文”的来龙去脉、叙述方式与意义,它是叙述者策略行为的体现,是结构的次要构件。“正文”由十几个梦构成,属结构的次要构件。这十几个梦彼此独立成篇,各自叙述着自己的故事,正如作者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所指出的“各梦自成一段落,互不相涉,免了做社会小说那种硬性熔化许多故事于一炉的办法。”每一梦都是一个精彩的短篇小说。这一组构方式,既体现了梦本身的特点,又有利于反映广阔复杂的现实生活。生活的原生态是线性故事所无法表现的,张恨水对此深有体悟,所以他努力“把现实世界的各部分加以改变、替换、缩小、扩大,由此造成一个自己的整体,以表达他自己的意图。”〔9〕《八十一梦》中每一梦都有自己特殊的功能意义, 揭示了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类人的本质。十几个梦连缀在一起构成一个立体式的结构,以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八十一梦》的深层叙事结构是由叙述者“我”的梦中神游即“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构成的。“我”作为作品中的人物贯穿十几个梦中,使彼此独立的“梦”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我”的情绪贯穿始终,单个的梦有如平原上的孤丘无法构成一种气势、一种风景线,作品表层结构的诸功能也必将因缺乏内在关系而被消解。英国作家毛姆曾断言亨利·詹姆斯是现代小说叙述模式革新的一位先驱者,因为“他通过一个在小说中担任部分角色的观察者的感受来讲述他的故事。这是一个绝好的窍门,来为他的小说取得所企求的生动效果。”〔10〕如果以此作为界定作品的一条准则,那么张恨水在创作《八十一梦》时,显然是在有意识地追求叙述方式、叙事结构的现代意味。整个作品的视点基本上固定在“我”的身上,“我”在作品中角色化、戏剧化,参与到故事中来。但“我”始终不是故事的中心人物,而是故事的观察者、见证人,是作品中各种关系的纽带。“我”作为叙事结构的核心,其文本功能首先在于揭示了梦境的深层内蕴,控制了文本意向;其次是取穿针引线作用,将不同的生活画面串连起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再次,由于整个叙述视点是“我”,整个叙述流是“我”的梦中神游,所以外在世界都是由“我”的心灵折射出来的,是一种情绪化了的世界,对读者无疑有一种强烈的审美召唤力。
综上所论,《八十一梦》的叙事结构由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构成。表层结构虽未脱尽古典章回小说的痕迹,但其深层结构无疑是现代的,充满现代精神。在作者精心构思、策划下,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相互融合,构成一种有机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文本意义的生成取着决定性的作用。
注释:
〔1〕〔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收入《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3〕《八十一梦·楔子》
〔4〕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前言》收入《苏联文学》,1986.5
〔5〕〔6〕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
〔7〕〔8〕弗洛依德《创作家与白日梦》
〔9〕莱辛《汉堡剧评》第34篇。
〔10〕毛姆《论小说写作》,见《世界文学》,1981年第3期。
标签:张恨水论文; 寓言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八十一梦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