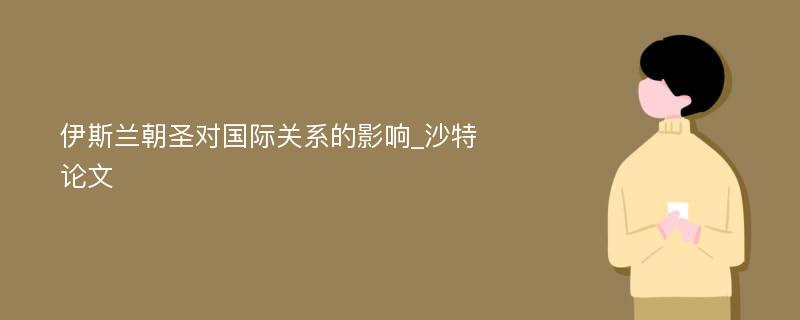
伊斯兰朝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4-0069-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一、研究缘起
为什么要在国际关系视野下研究伊斯兰教朝觐?这是因为冷战结束以来,宗教的全球复兴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与现象,国际关系中主权的让渡与人权因素的强化、次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宗教对于参与国际关系的合法性的谋求等共同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和趋势。对于前两者,国际社会多抱以超然的态度来面对,而对于宗教,其形象也从单一的“冲突根源”开始拓展至同时拥有“动荡根源”与“和平使者”的双重角色。①宗教朝觐(朝圣)对于世界性宗教而言是一个维系教徒信仰与情感的纽带,世界性宗教本身就是最先实现全球化②的领域,因此,宗教朝觐(朝圣)对于古代与现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且错综复杂的。③
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朝觐”和“朝圣”在英文中皆为pilgrimage,泛指各种宗教的朝觐或朝圣活动。就三大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而言,前往宗教圣地的朝觐(朝圣)活动是宗教功课,其中以伊斯兰教最为严格。就天主教而言,《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及其门徒主要活动的地方,如耶路撒冷和罗马便是朝觐之地,而梵蒂冈本身更是朝觐的圣地;伊斯兰教在《古兰经》中明确规定前往麦加朝觐是有经济能力的教徒一生必须完成的五项功课之一,对于朝觐日期、服饰、饮食、仪式等都有着细致的规定;伊斯兰教什叶派除了与逊尼派一样前往麦加朝觐之外,还将诸多圣徒殉道的地方奉为朝觐圣地,主要分布在什叶派密集的伊朗和伊拉克;佛教分支较多,藏传佛教尤为崇拜宗教领袖,其出生、死亡及主要活动的地方皆可成为信徒朝觐之地。在中国,“朝觐”一词在多数情况下特指伊斯兰教穆斯林前往麦加的朝觐活动,英文为Hajj或Hadj,来自于阿拉伯语音译。
由于宗教朝觐活动本身具有跨国性和信仰上的全球性等特点,因此其对于现行国际体系有着多重作用:第一,正面的维护作用,如梵蒂冈支持天主教徒前往以色列朝圣而促进了梵以关系的发展,韩国支持基督徒和穆斯林分别前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朝觐而促进了与西方和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关系;第二,负面的维护作用,如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地成为世界藏传佛教信徒的朝觐圣地,这些信徒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所在国政府与社会以支持西藏建立主权国家;第三,超越现行国际体系,如伊斯兰教。由于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政治化倾向和全球扩张性,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斯兰国际体系在中东地区开始重构,坐拥两大圣地的沙特阿拉伯试图构建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而拥有什叶派圣地的伊朗则试图在全世界构建其主导的什叶派网络。④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在很多问题上依靠伊斯兰原则而非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使全世界穆斯林朝觐信徒对于宗教、国家乃至对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认同感都产生了冲击。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2011年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10年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都促成了伊斯兰势力在中东国家的兴起并走向掌握政权。这些与中东伊斯兰复兴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斯兰教越来越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信仰伊斯兰”也在全球不断扩张。“信仰伊斯兰”,即伊斯兰教的信仰版图遍布世界各大洲,包含伊斯兰国家信徒(大聚居)、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省区信徒(小聚居)和非伊斯兰国家其他地区的个体信徒(散居和杂居),他们之间以伊斯兰信仰为共同纽带,伊斯兰国家构成了伊斯兰国际体系的核心。“信仰伊斯兰”版图的不断扩张与国际事务中的体系转型、全球治理、战争与和平等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重合之处,完整地集中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议题。全世界穆斯林在具体宗教教义、政治信念以及其他领域的认识千差万别,但对于伊斯兰教的基石“五功”和“六信”本身没有疑义。伊斯兰宗教朝觐不仅是伊斯兰教“五功”中最为壮观的全球最大的跨国宗教运动,也是在世界性宗教中唯一被最基本的宗教经典明确列为宗教功课的活动。可见,在国际关系视野下研究信仰版图不断全球扩张的伊斯兰教的朝觐活动,对于进一步认识伊斯兰教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参与大有裨益。
二、伊斯兰朝觐与圣城所在地沙特
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典便是《古兰经》,《古兰经》在若干章节中多次提到“朝觐”问题,如《黄牛章》、《仪姆兰的家属章》、《筵席章》、《忏悔章》等,而最为集中的则是《朝觐章》。这些章节的经文涉及朝觐的时间、地点、仪式、禁忌、食物、献祭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规定的时间与地点,第一,时间方面,“新月是人事和朝觐的计时”、“朝觐的月份,是几个可知的月份”;第二,地点方面,“真主以克尔白——禁寺——为众人的纲维”、“赛法和麦尔维,确是真主的标识。举行大朝或小朝的人,无妨游此两山”⑤。因此,从信仰伊斯兰的角度来看,朝觐活动是真主通过穆圣而降世的《古兰经》中的明确话语,即朝觐是神的意志,任何真正的穆斯林都不可否认此项功课的存在,朝觐是真主对穆斯林的一种制度(institution)安排。
通过制度主义来观察和分析朝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制度可以是一种通过制裁等手段来引导行为的规则(rule),是一个已被制度化的规范(norm)”,“制度可以是通过系列规则等手段而被引导的行为(behavior)体系,它是有组织的行动(activity)”⑥。从这个角度来看,真主为朝觐制定了规则和制度化的规范,朝觐作为每年规定时间与地点的宗教功课具有相当大规模的跨地区组织性,而在朝觐过程中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行为也会获得制裁手段,如《古兰经》中记载:“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不信道的人(无损于真主),因为真主确是无求于全世界的。”“谁能朝觐,并没完成,那么,他是非信士,因为真主说:‘不信道的人(无损于真主),因为真主确是无求于全世界的。’”⑦有能力而不履行朝觐功课,便实际上被剥夺了穆斯林的身份,这对于虔诚的穆斯林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惩戒和制裁。由于《古兰经》只是模糊提及“能”朝觐的穆斯林,而这实际上承认了“不能”朝觐的穆斯林的存在,同时穆斯林有朝觐的义务且不可否认此义务,因此教法学家为真主设计的朝觐基本制度进行了制度完善而非修正,即穆斯林具备朝觐资格的所需条件为:信奉伊斯兰教、成年、理智健全者、自由民、有能力朝觐者,而其中所谓有能力者,即指身体健康、路途平安、拥有川资和骑乘物。⑧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许多穆斯林无法完成朝觐功课与坚持伊斯兰信仰之间的矛盾。教法学家严格按照《古兰经》原典来予以判定,实际上仍然是真主的制度设计。
《古兰经》与圣训共同构成了伊斯兰教朝觐基本制度的合法性文件,《古兰经》便是朝觐基本制度不可修正的永恒保障。真主是朝觐基本制度的设计者,穆斯林是实践者;由于神-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真主为穆斯林所设计的朝觐制度具有正式性和单向性的特点,即朝觐制度的规范传递是真主向穆斯林的单向传递过程,而不可能有逆向的修正过程,穆斯林只有遵守朝觐制度的义务而无修改或废除该制度的权力。虽然朝觐作为伊斯兰教的一项基本制度而存在,但是具体的朝觐组织、圣地保护等活动需要拥有圣地的国家和政权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完成,这基于穆斯林分布全球的基本事实,被控制的边界限制了穆斯林向麦加的自由流动,穆斯林必须向所在国表达政治上的忠诚。因此,具体的朝觐管理最初并不存在,历史上管理圣地的当局和穆斯林所在的其他国家政府共同构成朝觐管理制度的设计者。
自第三沙特王国成立迄今,伊斯兰圣地麦加一直处于沙特王室与政府的有效治理之下。因此,土耳其1926年废除哈里发制度之后,沙特因其独特地位而自封为“伊斯兰盟主”,从而在朝觐管理制度中处于核心位置。沙特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了朝觐部,而且还对麦加禁寺、克尔白等处斥巨资予以修缮,制定了针对本国穆斯林、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和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的不同的朝觐政策,其核心是本国穆斯林要将机会多留给外国穆斯林,如1999年开始,沙特穆斯林只允许五年朝觐一次;而对于伊斯兰国家穆斯林朝觐,则实行名额分配;对于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原则上没有名额限制。沙特对于穆斯林的区分契合了其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中所处的地位。
(一)沙特与外国政府之间在朝觐管理制度上的对接因对象国而异
第一类,与伊斯兰国家之间容易通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方式达成一致,即正式合作机制下的朝觐管理制度对接。这来自于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国家中的核心地位,各国政府对于朝觐问题的重视首先具有宗教上的属性。1962年成立的伊斯兰世界联盟在协调各国朝觐政策,促进伊斯兰国家在各领域合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伊斯兰国家内部也存在多种类型,从地域上可分为中东国家、中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从政权性质上,可分为神权共和国、政教联盟君主国、世俗共和国等,其中那些威权领袖长期统治的世俗共和国对于伊斯兰势力往往呈打压态势,如土库曼斯坦严格限制朝觐活动,甚至取消某些年度本国公民的朝觐活动。土库曼官方对于清真寺和穆斯林控制非常严密,政府筛选朝觐名单,2010年仅派出188名朝觐者,远远低于沙特按照千分之一比例给予土库曼的4500名朝觐配额。⑨某些伊斯兰国家与沙特之间的不友好关系也会影响到本国公民的朝觐活动,如2004年12月,卡扎菲被指与沙特王储的暗杀案有关,这恰好发生在当年朝觐开始之前不久,费萨尔亲王予以谴责之后,仍然表示“沙特政府承诺仅将我们的反应限制在目前举措范围内……尽管发生了令人愤怒的事情……这是为了兄弟般的利比亚人民,尤其是在麦加朝觐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不希望任何事对利比亚朝觐者构成障碍”⑩。
第二类,与非伊斯兰国家间的制度对接程度不一,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欧美和韩国等国家由于在政治上奉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宗教上支持信仰自由,因此并不从制度层面干预本国穆斯林公民的朝觐,往往也没有政府所设置的朝觐管理部门或制定的朝觐法规等,朝觐只是限定在公民个人信仰范畴中予以对待。正因如此,这些国家的穆斯林朝觐往往通过沙特授权的非官方的朝觐旅行社组织本国穆斯林每年的朝觐活动。但在具体技术层面,这些国家的某些政府部门会消极应对穆斯林朝觐问题,如2010年,17名北弗吉尼亚州的穆斯林因海关和边检部门扣押了加利福尼亚一家朝觐旅行社通过UPS寄还的带有朝觐签证的护照,而错过了直飞沙特的飞机,弗吉尼亚穆斯林协会主席拉菲·乌丁·艾哈迈德(Rafi Uddin Ahmed)指出:“有人评论说,如果那些包裹上注明是‘约翰·史密斯’的话,那么还会被扣留么?”(11)这反映了“9·11”后美国“恐伊症”对国内穆斯林的某种不信任。而在其他非伊斯兰国家,如中国,则对于朝觐有着官方主导的管理制度。总而言之,伊斯兰教朝觐基本制度与各国朝觐管理制度共同构成了伊斯兰教总的朝觐制度。
(二)沙特以圣地为核心构建伊斯兰体系
伊斯兰教朝觐活动皆以麦加为目标,在穆斯林的世界观里,麦加乃世界的中心。在当代,沙特以朝觐圣地积极构建以其为核心的伊斯兰国际体系。朝觐对于沙特构建伊斯兰国际体系具有重大意义。20世纪七十年代埃以媾和意味着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彻底失败,极度西方化的伊朗在1979年走向神权共和国意味着伊斯兰原则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修正。神权共和国本身就是伊斯兰原则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糅合:首先,这受基督教在冷战中向国际关系“回归”的影响,对于伊斯兰教世界整体而言,伊斯兰教并未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中有所描述,因而其从未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被放逐;其次,中东不成功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困境或成功的现代化所带来的腐败与堕落导致传统伊斯兰价值观的复兴。伊朗以霍梅尼主义为核心思想向全世界的革命输出,意图建立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共同体,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便属其中;沙特则推行反纳赛尔主义和反霍梅尼主义原则,以伊斯兰会议组织为主要框架试图打造国际伊斯兰阵营;冷战结束后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全世界构建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网络。以上三者共同构成了伊斯兰国际体系,这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主权属于真主——这来自神圣的《古兰经》。(12)沙特作为温和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希望通过坐拥两大朝觐圣地的优势,在伊斯兰国际体系中获取领导地位,因为“千余年来,朝觐圣地的制度,对于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联系各种不同的教派,发生了最有效的纽带作用”(13)。
(三)朝觐业收入对“伊斯兰盟主”沙特国家独立地位的维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其大国外交的顺利开展
沙特因为地貌多为沙漠,在石油发现之前,几乎是不毛之地,正因如此,英国才默许沙特王室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也才容许了沙特王室推翻麦加贵族的行径。沙特才能顺利作为一战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并在中东较早获得了主权国家地位。因为坐拥两大伊斯兰圣地以及朝觐基本制度的存在,朝觐业成为沙特王国在石油大规模开采之前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为沙特的国家生存、伊斯兰哈里发制度的消亡以及日后伊斯兰国际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当今时代,朝觐业及其相关产业和工程建设仍然是沙特的一笔可观的收入。由于沙特朝觐业的消费群体来自全世界,因而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沙特,朝觐者数量锐减,这对沙特的国家生存构成致命威胁。1932年,沙特所欠债务达21.9万英镑,国王伊本·沙特说:“如果任何一个人现在就给我100万英镑,我将欢迎他在我的国家里得到他所要的一切特权。”(14)美国乘势进入沙特,美沙自三十年代开始了延续迄今的盟友关系。
(四)沙特以朝觐功课为契机促进伊斯兰教义的革新,这为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改革奠定基础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大大落后于西方,除了殖民主义的入侵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宗教的僵化导致对科技的排斥。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翻译运动”一直延续到15世纪欧洲海外活动的扩张这段时期内,伊斯兰世界在技术上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伊斯兰世界的衰落和欧洲的崛起都不是偶然的事件,面对技术和科学的态度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实际上与宗教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联。“16世纪以后所产生的宗派的勃兴,也是科学停滞、进步枯竭的一部分主要原因”,“如果有创造出科学技术需要的充分的经济繁荣,伊斯兰各国的宗教狂热主义就不能取得对科学的胜利”,“1580年,由泰基尔丁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伊斯兰最后的天文台遭到破坏这一事实,显示了宗派对科学的胜利”(15)。沙特遵循的正统的逊尼派瓦哈比教派被视为最符合先知穆罕默德思想,作为圣地的守护者以及完成朝觐功课的主导者,沙特王室和掌管教权的谢赫家族通过广播伊斯兰经文、汽车运送朝觐者等方式改革了伊斯兰教义,使之与现代科技发展相结合,其独特地位为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契机与合法性来源。在科技的发展带来交通的便利,朝觐的时间和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时,朝觐人数得以激增。
(五)朝觐为沙特改善与各国关系提供了契机
由于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沙特与各国的关系中存在很多潜在的冲突。首先,与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什叶派国家的关系上,朝觐往往成为一个沟通宗教与政治的平台。由于伊斯兰国家遵循的具体教派有所不同,而沙特是一个逊尼派国家,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往往受到歧视和限制,这又会在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和以伊朗、伊拉克为代表的什叶派国家之间引发冲突,增加海湾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复杂性。沙特充分利用朝觐的时机,召开伊斯兰世界联盟会议来加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沟通。不仅如此,朝觐也成为海合会国家改善与伊朗关系的最好时机,2007年12月,沙特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28年,首次邀请伊朗总统前往麦加朝觐,“内贾德的朝觐之旅可谓虔诚。在前往麦加的途中,他一直捧读《古兰经》,在抵达沙特城市麦地那准备中转时,也是手不离经,并诵读《古兰经》里的诗篇”,“内贾德这次朝觐之旅可算是伊朗与海湾六国关系大跃进的象征”(16)。在与新的谋求独立的穆斯林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关系上,朝觐也成为双边关系的关键,如科索沃问题。科索沃2008年宣布换发“科索沃共和国”护照,“对那些直飞沙特的科索沃朝觐者,沙特当时虽未承认科索沃,但将科索沃新护照视为有效的旅行证明文件”(17),在此推进下,尽管沙特并非最早承认科索沃的伊斯兰国家,但它是伊斯兰世界最早与科索沃建交的国家,双方于2009年8月7日建交。其次,与拥有数量可观穆斯林的非伊斯兰国家,朝觐成为发展双边政治关系的突破口。如新中国成立之后,沙特仍然与中国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实质关系,甚至敌视。周恩来总理利用万隆会议的舞台亲自与费萨尔亲王商谈中国大陆穆斯林朝觐事宜,1955年中国大陆顺利派出了首个朝觐团赴麦加,1992年中沙建交之前,双边最为常规化的人员往来便是每年(除1965~1978年外)的朝觐活动;不仅如此,首个朝觐团还访问了埃及等伊斯兰国家。“新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是促成中埃建交的一个重要因素”,纳赛尔在中埃建交公报发布后第一个口头告诉的人便是朝觐团团长达浦生大阿訇。(18)
三、伊斯兰教朝觐对国际关系具体领域的影响
古代的国家与现代的主权国家有着根本区别,由于当时陆海交通的落后及工具的受限,跨国关系往往集中在某一地区,跨地区的国家交往并不频繁且深度有限,当时的国际关系往往是地区内部的国家间关系。随着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发端于欧洲的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得以向全世界扩散。国际关系从传统的政治与军事关系慢慢向经济、文化,甚至环境、气候、节能减排等共同议题发展,这些可以看做是国际关系的具体领域。朝觐及其相关事件对于国际关系具体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朝觐活动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冲击:第一,由于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是为欧洲量身打造的,其主权与民族的原则来自于对基督宗教的“放逐”。由于宗教战争给君主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和震撼,宗教在欧洲被视为混乱、无序和战争的导火索,当宗教问题在欧洲业已解决之时,宗教便实质上从欧洲国家的内政以及国家间政治中放逐了。当宗教问题获得了解决而不再成为问题时,欧洲国家又在神圣的宗教去政治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的神圣原则,即民族国家的独立实体地位、国家间互不干涉内政、国家的主权不可随意剥夺。朝觐虽然自立教之初便已有之,但在欧洲走向全球时代之前对于欧洲并无明显影响。在当今伊斯兰全球复兴时代,朝觐作为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与其他宗教的复兴一道,首先共同构成了对“去宗教化”的现代国际体系的挑战;第二,由于非国家或超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即全球或地区性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传教运动等对主权国家的地位形成挑战。朝觐涉及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联盟、穆斯林个人所构建的伊斯兰国家网络和全球穆斯林网络。西方国家在中东的霸权尤其是美国失衡的中东政策造成了许多伊斯兰国家政府和民众的不满,以伊斯兰信仰为纽带的全球性跨国朝觐活动实际上成为抗议西方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集中性表现。
其次,朝觐对于世界走向整体在交通上的促进作用。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经历了数百年,其中欧洲国家发挥的重要作用,新航路的开辟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基督新教伦理在这种殖民主义扩张中发挥了精神层面动力的作用。(19)欧洲的全球交通网络的建构实际上继承了穆斯林的许多早已有之线路和技术。自有朝觐之日起,朝觐便很少中断,世界不同地方的穆斯林千方百计地以不同方式前往麦加。在古代,从北非到东南亚的穆斯林通过陆路与海路的方式抵达麦加朝觐,这种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商业动机的伊斯兰教自觉行为事实上保持了东亚与中东地区交往通道的畅通,如中国郑和船队第4次出访开始,访问许多阿拉伯城市,其中包括圣地麦加,这与其穆斯林身份以及祖上多次赴麦加朝觐有着巨大关联,从某种意义上,郑和的西亚北非之行实际上是一次朝觐之旅。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通过朝觐聚集在麦加,麦加成为多元文化和商业往来的平台,朝觐在沟通东西方通道以及维护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媒介作用。由于奥斯曼帝国阻隔了东方与欧洲的陆路通道,结束了穆斯林统治之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利用阿拉伯人留下的航海技术迅速走向了探索并连接世界的道路。
再次,朝觐与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朝觐者来自世界各地,因各国卫生条件不同和审查宽严度的差异,朝觐者极其容易引发公共卫生疾病或危害。受新型疾病感染的朝觐者归国后极有可能在国内传播该疾病,造成公共危害。20世纪以前,由于伊斯兰教传播范围有限,交通相对落后,朝觐人数不多且主要是中东地区穆斯林,即便如此,不同区域穆斯林所带来的卫生问题在当时便引起了重视,早在9世纪,古斯塔·伊本·卢加(Qustā Ibn Lūqā)医生便注意到朝觐所引发的疾病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机制设计。(20)20世纪,伊斯兰教开始向欧美国家、东北亚国家传播,伊斯兰教在欧洲和美国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韩国与日本等单一民族的非伊斯兰国家也有了一定数目的本国穆斯林。朝觐穆斯林来源更加广泛、人数不断增多,朝觐期间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仅对沙特的卫生管理水平产生挑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26年制定的《国际卫生公约》中就包含了应用于朝觐的特别条款。(21)沙特红新月会在朝觐卫生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红新月会在麦加设立了14座大医院和80个医疗站,为患病朝觐者提供及时的救治。21世纪以来爆发了数次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沙特朝觐部宣布暂停副朝签证的发放;2009年甲型H1N1流感泛滥之际,沙特与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地区分支机构对于当年的朝觐人员健康要求有了新的规定。
最后,朝觐圣地沙特允许美国驻军的行为引发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反西方行为。虽然美国插手世界事务引发了诸多不满,但来自宗教上的反对情绪主要因为其海湾战争后驻军沙特的行为。由于沙特拥有两座朝觐圣城,沙特国王甚至改头衔为“两圣地仆人”,因此沙特被整个地视为伊斯兰圣地。“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允许美国军队——其中不乏基督教徒和女兵——进驻沙特领土,这对沙特本国穆斯林乃至世界穆斯林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必然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22)。尽管沙特王室通过谢赫家族发布了“法特瓦”,但并未能获得全世界穆斯林的一致认可,而且因为逊尼派的特性,即“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中,法特瓦是一种由被认可的权威或合法的学者,就伊斯兰法或实践的某一点所发布的,没有约束力的意见或解释”(23)。换言之,“法特瓦”对穆斯林个人并未有实际约束力。因此,本·拉登反美主义坚持认为美国与沙特共同玷污了伊斯兰圣地,九十年代开始了依靠暴力的反美活动,其宗教恐怖主义也彻底改变了21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格局。“9·11”事件后,美沙关系历经严峻考验,沙特也不得不顺应伊斯兰世界的呼声,力主美国撤军。
四、朝觐与中国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讯息与人口的全球流动越来越频繁,这对于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而言增添了许多新的挑战,伊斯兰宗教朝觐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年度性跨国运动,其国家、民族、教派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程度使得麦加成为多元宗教与政治思潮的汇聚之地。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其中回族、维吾尔族等10个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人口达2200多万人。因此,中国需要朝觐功课的群体十分庞大。中国并非伊斯兰国家,因此原则上沙特并不限制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人数,但中国穆斯林每年能够完成朝觐功课的人数大大低于沙特为伊斯兰国家确定的千分之一的比例,1955~1964年,中国大陆朝觐人数总和仅为132人次,近年来每年通过各种手段完成朝觐的穆斯林超过一万人。(24)
首先,正因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利用朝觐机会向各国穆斯林输出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许多国家政府对此保持警惕态度,如基地组织、东突等向中国朝觐穆斯林灌输分裂主义思想。由于中国国内政治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政治,因此,为了维护国家边疆安全,中国政府只允许各相关部委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导朝觐事务,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非官方主导的朝觐行为,并为此发布了相关的行政法规。
1995年1月28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安部、外交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中国民航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自费朝觐若干规定的通知》,其核心定位在于“朝觐是一项大规模的涉外宗教活动,政策性很强,国务院明确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主管,国家七部门协调配合工作,并委托中国伊协组织实施,其他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形式组织正副朝觐或变相朝觐活动”。《通知》确定了每年朝觐名额为2000人,由各省市进行筛选,并组建“中国朝觐总团”,对于护照颁发、费用收取、不允许零散朝觐等都作了详细规定。2004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宗教事务条例》,其中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公民前往国外朝觐,由伊斯兰教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组织。”第六章第四十三条规定:“擅自组织信教公民到国外朝觐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2005年6月3日,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关于严禁旅行社组织出国零散朝觐活动的规定》,将朝觐定位为“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宗教活动,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我国的国际形象”,《规定》的核心在于打击游离于官方之外的零散朝觐和相关旅行社。
不难看出,中国官方对于朝觐认知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朝觐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过多的涵义,如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国家形象等,实际上将朝觐的功能异化。不仅如此,在朝觐人员的选拔中,也存在穆斯林散居地区名额用不完,聚居区名额远远不够的问题,朝觐指标甚至成为某种黑市商品;朝觐收费所涉及的权力腐败问题。这些造成了许多穆斯林与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官方组织的朝觐排队遥遥无期,尤其是许多年纪较长的穆斯林实际上已失去朝觐的可能;另一方面,私人朝觐活动被不断打压,组织者面临严厉制裁。
其次,宗教朝觐活动是非政治性的活动,其参加者是穆斯林个人而非主权国家,因此,许多不被承认的国家和政权利用其穆斯林朝觐活动开展泛宗教活动,而台湾方面的朝觐活动对于在国际社会宣示台湾的主体性拓宽了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台湾穆斯林的宗教朝觐活动得到台当局的大力支持,并将朝觐视为国民外交活动的组成部分。以2011年“中华民国百年”宗教朝觐为例,其中的“台湾”与“中华民国”元素就较为明显,而这在国际社会其他政治或非政治性组织或活动中很难展现。朝觐团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朝觐团成员穿着统一的背心,背心上印有台湾岛地图和覆盖其上的“中华民国国旗”,朝觐团在沙特公开高举“中华民国国旗”;(2)基于中国台湾方面的不懈努力及其与沙特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此次朝觐团全部得以住在圣城麦加而非以往的吉达,所下榻的旅馆距麦加禁寺不远(25);(3)朝觐团展开针对沙特官方的外交活动,如部分成员拜会沙特朝觐部东南亚国家领朝委员会副主席,就中国台湾朝觐团行程、交通、正朝营地规划等进行协商,不仅如此,部分团员还拜访了沙特朝觐部正副部长、世界伊盟秘书长等高级官员,并有中国台湾朝觐团员受阿卜杜拉国王邀请前往王宫参加国宴(26);(4)朝觐团积极与圣地华侨展开交流,如得到旅居麦地那的华侨领袖阿哈迈德家族的款待,该家族已多年接待中国台湾朝觐人员;(5)朝觐团展开宗教教育交流,如两位团员前往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拜会其校长,就发展学生交流项目交换意见。
除了中国台湾驻沙代表处外交人员的鼎力协助之外,台湾朝觐团的顺利成行也得到政府的资助并在回国后得到礼遇。“中华民国朝觐团多年来受政府公费补助,因此朝觐之旅除了团员完成自身的宗教功课之外,更肩负国民外交的责任,具体来说就是前往沙国相关政府单位与民间机构的拜会”(27)。中国台湾朝觐团完成朝觐功课后,“副总统”萧万长予以亲切接见,大力称赞伊斯兰教对“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均有重要贡献”,“企盼台湾穆斯林能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促进我国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更深厚的合作关系”(28)。
虽然从当前国际关系中宗教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泛滥来看待中国政府的朝觐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长远看,如何从朝觐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视角中受益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而言十分重要。
第一,从宗教的视角来观察朝觐。穆斯林完成朝觐,既是功课,也是义务,对于穆斯林而言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大事,而对于非信徒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在大部分普通信徒眼里,朝觐就是朝觐,没有过多的其他涵义。即便穆斯林利用朝觐参加政治活动或违法活动,其首先违反的是伊斯兰教法,因为朝觐期间不允许有任何政治活动,违反此教法,自然会有教法予以有效处置。“让宗教回到宗教”是必须之道。
第二,从超国家宗教信仰与主权国家的正确关系的视角来观察朝觐。在伊斯兰教朝觐问题上,中国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考虑,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限制国内穆斯林的朝觐权力。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流动频繁,依靠单纯的管制并不能完全根除个人零散朝觐。穆斯林宗教信仰及其外在表现形式——朝觐,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并非对立关系,朝觐中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与政治意图和极端民族主义有关,而与宗教无关。在中国,宗教并不可能对政治有干预,因此穆斯林的朝觐只是宗教信仰问题,而非政治和国家信仰问题。
第三,要将朝觐看作私人性的公共外交活动,并准确定位国家形象。目前的朝觐管理制度,中国政府完全将朝觐看做是展示国家形象的橱窗,因此大力选拔符合政府标准的人,认为若不如此,国家形象便会受损,这种思路远远落后于信息化时代的认知。中国穆斯林的形象,既在走出国门,如朝觐的时候展示,也在外国人进来后日常接触的时候得以展现。任何经过官方塑造的、对外展示的形象在当今时代往往适得其反。最为重要的是改善民族地区民生,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信教群众的整体素质,这才能培育出较好的国家形象。
①参见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序》,载徐以骅主编的“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系列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也有学者认为三大宗教向五大洲的扩散过程并非现代意义的“全球化”过程。
③如十字军为夺取圣地耶路撒冷而采取的东征行动,与伊斯兰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军事冲突,这导致了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关系的恶化,也为两教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阴影;又如1967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人在夺取耶路撒冷尤其是圣殿遗迹——哭墙之后的亲吻和祷告,实际上以宗教朝圣的方式向全世界传递了自己对于耶路撒冷归属的认识。
④钮松:“三种国际体系在中东并行交错”,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9日。
⑤参见《古兰经》相关章节。马坚译:《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Jan-Erik Lane,Svante Ersson,The New Institution Politics:Performance and Outcomes,New York,NY:Routledge,2000,p.23.
⑦《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
⑧http://www.norislam.com/islamlaw/fd.asp?id=407.
⑨Nazik Ataeva,"Turkmenistan Stage-Manages Muslim Pilgrimage:Government Decides Who Can Perform Hajj on the Basis of Rigorous Loyalty Check," RCA,Issue 634,November 10,2010.http://iwpr.net/report-news/turkmenistan-stage-manages-muslim-pilgrimage.
⑩叶平凡、刘广聚、涂龙德:“利比亚密谋杀王储沙特利比亚关系急转直下”,载《北京青年报》,2004年12月24日。
(11)Tara Bahrampour,"Travel Delay for Mecca-bound N.Va.Muslims,"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9,2010.
(12)钮松:《三种国际体系在中东并行交错》。
(13)[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9页。
(14)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版。
(15)[叙]艾哈迈德·优素福·哈桑、[英]唐纳德·希尔著,梁波、傅颖达译:《伊斯兰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16)范新红:“内贾德受邀朝觐麦加伊朗与海湾六国关系大跃进”,载《青年参考》,2007年12月21日。
(17)钮松:“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大国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1期,第39页。
(18)敏俊卿:“新中国穆斯林第一次朝觐的前前后后”,载《中国民族报》,2009年9月15日。
(19)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NY:Routledge,2001.
(20)Gerrit Bos,Qusta Ibn Luqa's Medical Regime for the Pilgrims to Mecca,Leiden:Brill,1992.
(21)Stephen Allen,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22)陈敏华:《美国、中东国家和中东激进组织对石油利益和经济公平的不同解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6期。
(23)Deana Heath,Chandana Mathur,Commun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South Asia and Its Diaspora,New York,NY:Taylor & Francis,2011,p.200.
(24)马晓霖:“中国穆斯林朝觐者们鲜为人知历史”,载《环球》,2009年12月7日。
(25)朱云清:“中华民国百年朝觐纪行”,载《中国回教》,2012年1月15日第333期,第10页。
(26)同上,第14页。
(27)于嘉明:“伊历1432年朝觐纪实与感言”,载《中国回教》,2012年1月15日第333期,第16页。
(28)“伊历1432年中华民国朝觐团晋见萧副总统万长先生纪要”,载《中国回教》,2012年1月15日第333期,第7页。
标签:沙特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韩国穆斯林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古兰经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麦加朝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