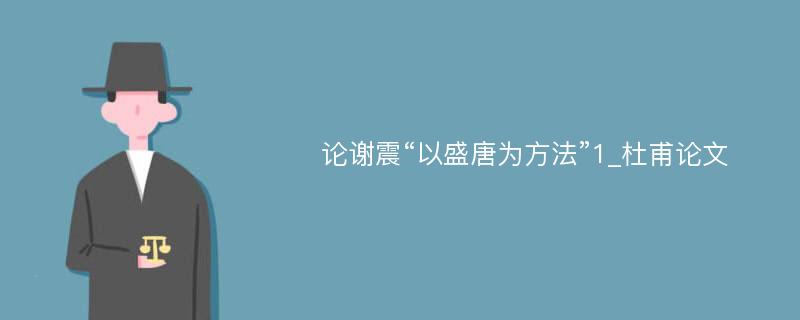
再论谢榛“以盛唐为法”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再论谢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谢榛“以盛唐为法”,主要是师法李杜的较为活泛的说法。其内涵:(一)“夺盛唐律髓”。在这方面,侧重师法杜甫。(二)偶言以“兴”为诗。在这方面,偏向师法李白。(三)追求“格高气畅”。这是盛唐特定的时代风格。谢榛打出复古的旗号,旨在矫正时弊,试与李杜等“盛唐诸公 ”比肩并立,独自成家而已。
关键词 盛唐 声韵 兴 格高气畅 独自成家
一
“盛唐”二字,是从唐诗分期中拈出的,后来也用以划分唐代历史。
对有唐一代诗歌流衍盛衰史,首先着手明确分期的,是南宋的严羽,其《沧浪诗话·诗体二》专“以时而论”诗体,把整个唐代诗歌标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五种,即将其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从严羽自己对唐诗五体的简要注释看,肃宗至德至代宗大历,德宗建中至宪宗元和,计有25年未包括在五个阶段之内,知其对唐诗分期只是“论其大概耳”(《沧浪诗话·诗评》)。而严羽在对唐诗划分五个阶段的同时,也流露了将盛唐与晚唐之间的大历体、元和体混而为一的倾向。所以不久,生当宋、元之交的方回,就在他编选的《瀛奎律髓》卷十评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一诗时,将“大历”、“元和”合为“中唐”,虽略而不言“初唐”,实际上,已把严羽的五阶段改造为“四唐”。时至元杨士宏选编《唐音》,“正音则诗以体分,而以初唐、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四库全书·唐音提要》)其《序》已明言初、盛、中、晚之四唐。只是如王士祯所说:“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杨士宏《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迨明初高棅裒辑《唐诗品汇》,“即因其例而稍变之”(《四库全书·唐音提要》)。“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唐诗品汇·凡例》)并对“四唐”诗歌声律兴象、文词理致之品格高下,作了较为扼要精到的阐述,使唐诗分期臻于严整而系统化。尔后,尽管人们在“四唐”起讫上时有出入,宗法上也各有侧重,但大都未越出高棅的指划。
谢榛论诗,虽远绍严羽,但在涉及唐诗的分期问题时,他罕于言及大历、元和,只言初、盛、中、晚之“四唐”,可知其所标举之“盛唐”,乃是直接承袭了高棅之说。
二
谢榛倡言“以盛唐为法”,有时也提及“初唐”。在《诗家直说》中,“初唐”计出现5次,其中4次是受推重的,即:
七言近体,起自初唐应制,句法严整,或实字叠用,虚写单使,自无敷演之病。(见笔者《诗家直说笺注》卷四,齐鲁书社1987年5 月版,以下引文凡出此书者,书名从略,只列卷次)
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卷三)
予以奇古为骨,平和为体,兼以初唐、盛唐诸家,合而为一,高其格调,充其气魄,则不失正宗矣。(卷四)
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学者能集众长,合而为一……(卷三)
以上四段引文告诉我们,有3次就是谢榛在说到“盛唐”时, 才把“初唐”带出来的。由此进一步联系《诗家直说》中提到的“初唐”的代表作家,谢榛除对沈佺期、杜审言、宋之问评价较高外, 对王绩、王勃、骆宾王、上官婉儿、陈子昂等都没有多大热情,可以说他并不是真那么看重“初唐”的。而对“盛唐”,他在《诗家直说》中直接提到20次,还有使用频率很高的“唐”一词,也主要指“盛唐”而言。谢榛使用了“极”、“最”等最高级的词汇赞誉“盛唐”,把“盛唐”奉为光辉的楷模。这足以说明,他倾心力倡的只是“盛唐”。“作者当以盛唐为法”(卷一),才是他的真正取向。
从时间上看,谢榛所谓的“盛唐”,当指唐玄宗开元初年(713)至代宗大历初年(766),这与高棅是一致的。 他论及的“盛唐”诗人,除李白、杜甫两位大家外,著名的尚有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岑参、高适、李颀、贾至等。对李白、杜甫,他一再相提并举,颂扬倍至,如:“太白、子美,行皆大步”(卷三);“诗乃模写情景之具,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当知神龙变化之妙:小则入乎微罅,大则腾乎太宇。此惟李、杜二老知之”(卷四);“奇正参伍,李、杜是也”(卷二)等等。其于“太白少陵两诗豪”(《江南李秀才过敝庐,因言及诗法,赋此长歌,用答来意》,见笔者《谢榛诗集校注》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而对其他诗人,皆有褒有贬。如:对王维的诗,一方面称许“爽健自别”(卷二)、“旷阔有气”(卷四),一方面又指摘“声律未妥”(卷四)、“韵短调促,无抑扬之妙”(卷三)。对孟浩然则曰:“浩然五言古诗、近体,清新高妙,不下李、杜;但七言长篇,语平气缓,若曲涧流泉而无风卷江河之势。”(卷二)这样看来,谢榛乐道的“盛唐诸公”实质上主要指李白、杜甫二人。因此,我们又可肯定,谢榛的“以盛唐为法”,主要是师法李白、杜甫的较为活泛的说法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谢榛宗主“盛唐”,但并不就匍匐于“盛唐”脚下,唯唯讷讷,马首是瞻。他清醒地看到:“虽盛唐名家,亦有罅隙可议,所谓瑜不掩暇是也。”(卷二)因而,他不仅对王维、孟浩然等人,即使是衷心敬仰的李白、杜甫,也时有微词,不为贤者讳。如:对杜甫的诗,《诗家直说》批评其“文不逮意”(卷二)、“非诗家正法”(卷二)、“为韵所拘”(卷四)、“为韵不雅”(卷二)、“对起,颇似简板”(卷三)、结句“似无归宿”(卷二)、用字“着力”(卷二)等,计十余处。对李白的诗,也指出其“两联意颇相似”、“兴到而成,失于点检”(卷三)之处。这是颇具胆识和眼光的。而且,虽然他囿于严羽格以代降思想的支配,对“盛唐”之后的诗存有偏见,贬抑过于苛刻;但他并不坚持“贞元而后,方可复瓿”(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他对“中唐”的韩愈、刘禹锡、刘长卿、李贺、白居易、贾岛、韦应物、顾况、钱起、严维、李绅、皎然、王建、张籍、司空曙、戴叔伦等,对晚唐的李商隐、许浑、杜牧、于濆、胡曾、李群玉、卢弼、崔涂、陈陶、孟迟、包佶等,对宋代的林逋、苏轼、陈师道、葛天民、戴石屏等,都有程度不同的肯定。他认为,后人亦有“气骨不减盛唐”(卷一)、“得盛唐气骨”(卷三)、“气象雄浑、大类盛唐”(卷二)者。这就暗伏了他“以盛唐为法”的可行性。
三
按最粗的线条,谢榛将诗体分为古体和近体两大类。基于此,谢榛明确地指出:“凡作古体、近体,其法各有异同。”(卷三)这就从体式上对古体诗之法、近体诗之法,作了区分。
关于古体诗,谢榛主张应以汉、魏以前为法。具体说就是:“四言古诗,当法《三百篇》,不可作秦、汉以下语”(卷一),因为“《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卷一);骚体,当法《离骚》,因为《离骚》“高古浑然”(卷一),“汉、魏以来,作者缤纷,无出屈、宋之外”(卷一);五言古诗和乐府,当法汉、魏,以汉为主,因为“汉、魏古诗,气象浑厚”(卷一),而“诗以汉、魏并言,魏不违汉也”(卷一)。但是,谢榛对古体之法,多为旁及,即使正面涉及,也是点到为止。因为无论从其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创作看,他一心专注的是近体诗。
关于近体诗,虽直承齐梁体,远孕于汉、魏,但其五言律、绝,是在初唐形成和定型化,至盛唐才臻于极致的;七言律、绝,兴起虽稍晚于前者,初唐时尚未完备、圆熟,但进入盛唐,经过精心锤炼,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足可与五言律、绝争艳斗奇。谢榛专尚近体,当他巡检我国诗歌的流变兴衰,发现盛唐近体诗耸峙的丰碑,于是惊喜和振奋之情引发了“以盛唐为法”的极大内驱力。
严密的格律规范是近体诗的标志。近体诗各品类对字数、句数的要求是容易做到的,而对仗、平仄、押韵等限制就难于把握了。对仗涉及到词语、句子的结构方式,也关涉到平仄。平仄,属于声律,押韵归之韵律,二者合起来就是声韵。可以说,声韵是近体诗最基本、最主要的构律要素。谢榛的“以唐为法”的大旗,就是在论及声韵问题时举起的。
综观谢榛有关诗法的言论,他断然否定类同于棋谱、牌谱的“风骚句法”(卷二)、宋人“十三”格(卷一)、“杨仲宏律诗三十四格”(卷二)等等,提倡“活法”,鼓吹“摆脱常格,瓊出不测之语”(卷二),唯独于近体诗的声韵循规蹈矩,恪守不二。他自诩“草茅贱子,至愚极陋,但以声律之学请益,因折衷四方议论,以为正式”(卷三)。又谓“予著《诗说》,犹孙武子作《兵法》,虽不自用神奇,以平列国,能使习之者勘乱策勋,不无补于世也”(卷四)。其宗旨即在于“夺盛唐律髓”(卷四),排荡“中唐”、“晚唐”,特别是“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于起句,借用傍韵,牵强成章”(卷一)的出格越轨行为。这固然不免守旧之嫌,但详察中、晚唐乃至宋、元之诗再也难与“盛唐”把臂比肩的事实,又觉得这对于维护近体诗体式的纯正而不落傍门邪径,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具体说,谢榛所要“夺盛唐律髓”就是:
其一,“求声调”(卷三)。这被他列为学诗“三要”之一(卷三)。此所谓“声调”,即“平仄四声而有清浊抑扬”之妙(卷三)。他认为“句分平仄,字关抑扬,近体之法备矣”(卷三)。要求写诗必须做到“平仄以成句,抑扬以合调”(卷三),特别应注意“凡字异而意同者……审而用之,勿专于义意而忽于声律也”(卷三)。并再三批评王昌龄《长信秋词》、刘禹锡《再过玄都观》、杜牧《开元寺水阁》等诗“无抑扬之妙”(卷三)。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说过:“心灵里没有音乐,决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谢榛极力倡导的,正是一种“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卷一)的圆转流活、响亮高昂的音乐美。盛唐是南乐北曲、中外音乐大融合、大交流的时代,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浓厚的音乐气氛,不仅风流皇帝唐玄宗及达官显宦嗜好音律,众多诗人也精晓音律。流风所及,诗歌亦显示了强烈的音乐性,甚至大量的诗歌,“可以协丝簧,谐音节……入弦歌”(卷一)。谢榛所求之“声调”,就是这种盛唐之音。
其二,“工于押韵”(卷四)。其标准就是“用韵妥帖”(卷三),不“为韵所牵”(卷一),“但搜字以补其缺”(卷三)。这就要求:(1)“透悟”,象盛唐诗人那样,于“押字不苟处, 能造奇语于众妙之中”(卷三)。(2)“择韵审义”(卷三),用宽韵、平易韵, 忌粗俗、艰险韵(卷一、卷四),反对古韵(卷一)、进退格(卷一),和上句同韵(卷二)等。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二:“何无忌与人论诗云:‘欲作佳诗,必先寻佳韵,未有佳诗而无佳韵者也……’可见工诗者未有不留意于韵。”在这方面谢榛所追求的,仍然是近体诗“句法浏亮,可以咏歌”(卷二)的音乐美。
其三,“律诗重在对偶”(卷一)。谢榛要求对偶应做到“精确”(卷二)、“自然”(卷二)、合乎“格律”(卷三),反对“简板”(卷二、卷三)、“粗直”(卷四)等。如上所述,对偶虽关涉到平仄,但他很少言及。他具体探讨的,主要是结构安排(卷一、卷二)、用字虚实(卷一)、颜色浓淡(卷一)诸问题。这些具体对偶问题,盛唐已有“定法”,为了维护盛唐的正宗地位,即使诗圣杜甫稍有超越,也被视为大疵,如“排律结句,不宜对偶。若杜子美‘江湖多白鸟,天地有青蝇’,似无归宿”(卷二);“子美起对固多切者,宜在中而不宜在首,此近体之定法也”(卷三)等等。其态度之认真,由此可见。
对于近体诗的声律,谢榛虽说过:“工于声调,盛唐以来,李、杜二公而已。”(卷三)但在这点上,他更推崇、更侧重师法的,是杜甫,而不是李白。因为李白天资豪纵,不屑于雕章琢句,更喜欢乐府歌行、古体等较为自由奔放的形式,最卓越的贡献是七言古。虽然他的五言、七言绝句,也是“字字神境,篇篇神物”(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代表着这一体式的最高成就;但对于作为近体诗最基本形式的律诗,他写得极少,今所存990余首诗中,仅有五律60余首、七律10余首。 而集大成者的杜甫,唐代流行的各种诗体,几乎都在他手里得到了发展。就近体诗而论,绝句诚然不及李白,但他对绝句的境界开拓和表现形式创新所作的巨大贡献,功不可没。至于律诗,则是在杜甫手中成熟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他在用字、造句、对仗、声调、谋篇、运笔诸方面都使律诗的美学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据统计,杜甫现存的1400余首诗中,律诗就将近900首。如此这般,谢榛力倡“夺盛唐律髓”, 自然会更注目于杜甫了。这正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说:“学诗当以子美为法,有规矩,故可学。”杜甫娴于声律,自言“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八),谢榛所谓“子美可法”(卷三)者,此即一主要方面。谢榛时而于杜甫诗中寻痕觅瑕,固然反映了他拘囿于“盛唐”既成的模式,反对新变的守旧保守性,同时也表现了他师法杜甫的热情和认真态度,期望过高,求之弥深,些微差失就不肯放过了。但是,由于其态度十分诚恳,这指摘“固无害于杜之大也”(汪师韩《诗家纂闻》)。
四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谢榛“子美可法,太白不易法”(卷三)之议,就是因为杜甫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胸中有道节制心潮的闸门,感情擅长抑扬顿挫于近体诗(特别是律诗)的谨严法度之中,成为后世轨范,有法可循。而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赵翼《瓯北诗话》卷一),是不易法的。
不易法不等于不可法。为确保宗主“盛唐”,入门须正,路头不偏,象南宋严羽大不满“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和“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沧浪诗话·诗辩》)那样,谢榛也指斥“晚唐格卑”(卷一)、“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卷一)等,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超越宋人和晚唐,直薄“盛唐”,以“兴”为诗的问题。他说:
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欢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无穷。欢喜诗,兴中得者虽佳,但宜乎短章;悲感诗,兴中得者更佳,至于千言反覆,愈长愈健。熟读李、杜全集,方知无处无时而非兴也。(卷三)
这段话:(1)极力强调了“兴”的重要性;(2)指明李白、杜甫的诗“无处无时而非兴”,值得效法。但是,细加辨析,李白之“兴”与杜甫之“兴”,并不完全相同。阙名《静居绪言》曾比较说:“太白诗寄兴物外,故意在言外;子美之诗兴在目前,故意在言内。”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考《诗家直说》中诸言“兴”条目,只有上引一条笼统地提到杜甫,而大部分,或明或暗关涉到的只是李白。如:
太白夜宿荀媪家,闻比邻春臼之声,以起兴,遂得“邻女夜春寒”之句。(卷二)
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卷一)
可见,在近体诗的声韵方面,谢榛是侧重于师法杜甫的;而在“兴”的问题上,则又偏向于师法李白了。
虽然,有两次谢榛是把“兴”纯粹视为一种修辞手段论及的,但他热心倡导的,却是另一种含义的“兴”。
这“兴”,不同于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的“兴寄”说。(《陈伯玉文集》卷一)“兴寄”的含义是比兴寄托,即以比兴手法,抒发情感,寄托政治抱负。其重点放在寄托上,而不是比兴手法的本身。这对于泛滥于齐、梁诗坛至初唐仍然流行的“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隋书》卷六六)的靡艳之音,无疑是一剂良药。
这“兴”也不同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提出的“兴趣”说。从严羽“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论述中,可知“兴趣”乃指诗中形象的空灵、蕴藉。其主旨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趣”上。这对于宋代诗坛,特别是江西派崇尚议论,流于浅白直露,缺乏蕴藉之旨的流弊,是狠命的一击。
这“兴”,更不同于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之“序”和“评语”中三次提到的“兴象”。对“兴象”的理解,目前还很不统一,但概而言之,诸解说都是把“兴象”视为诗歌形象或艺术境界的美感特征的。据《河岳英灵集序》“挈瓶肤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乎异端,妄为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等语,知“兴象”乃是针对齐、梁绮靡诗风及其余波而标举的审美概念,这也是对盛唐诗风美学特征的概括。
谢榛所倡之“兴”,强调了三个方面:
(1)触物起兴。如:“触其心思”,“因所见而得句”(卷四);“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非沉思苦索而得之”(卷二)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谢榛的举证虽涉及到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这些所触之物,但他主要论及的却是“阅书醒心”之“书”(卷四)。杜甫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袁守定《占毕丛谈》亦记曰:“吴立夫谓胸中无三万卷书,眼中无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纵文亦儿女语。”可见,书也是引发感兴和天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过分看重了这点,就会使人疏离自然和社会,颠倒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
(2)兴的偶然性。如:“作诗有相因之法, 出于偶然”(卷四);“心中本无些子意思,率皆出于偶然”(卷四)等等。这就是说,兴并不是诗人呼之即来的,往往是无意间突然涌上心头,“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陆机《文赋》),神秘莫测。
(3)兴的随意性。如“走笔诗成,兴也”(卷三); “漫然成篇”(卷一);“意随笔生,不假布置”(卷一)等等。这正是指兴之来时,浮想联翩,思如泉涌,万般境象,纷至沓来,诗人笔起龙蛇,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景。
由以上三点可以判定,谢榛所说之“兴”,就是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二中说的“观物有感焉,则有兴”之“兴”,也就是常说的“感兴”,即诗人在外物激发下产生的感情昂奋、兴致勃勃、想象飞腾、顿然开悟的状态。正因为此,在谢榛那里,感兴和天机是相通的,他探讨的“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卷二),应归于感兴范畴。这又可以看出,谢榛力主诗法盛唐(特别是李白)之“兴”,宗旨乃是要求诗应有感而发,出乎天然,信从自然,顺流直下,水到渠成,浑然无迹;反对以力构,刓精竭虑,凿空强作。
翁方纲《石州诗话》卷一:“盛唐诸公之妙,自在气体醇厚,兴象超远。然但讲格调,则必以临摹字句为主,无惑乎一为李、何,再为王、李矣。”而谢榛于师法盛唐声韵同时,又提出了“兴”的问题,正是他高出李梦阳、何景明和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一筹之处。
五
“格高气畅”,也是谢榛“以盛唐为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诗家直说》卷一曰:
格高气畅,自是盛唐家数。
明确辨识盛唐“家数”,从严羽开始,他反复申说:“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沧浪诗话·诗法》)“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辩》‘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答吴景仙书》)很明显,谢榛在这方面直接承袭了严羽之说,其于“盛唐”“格高气畅”的概括,实乃严羽所谓:“盛唐之诗……雄浑悲壮”;“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如此诠释,我们亦可从谢榛对前人诗作的品评中取得实证,诸如:
韩退之称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为佳句,未若“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气象雄浑,大类盛唐。(卷二)
许用晦《金陵怀古》,含联简板对尔,颈联当赠远游者,似有戒慎意。若删其两联,则气象雄浑,不下太白绝句。(卷二)
“格高气畅”是谢榛在提到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四所载梅尧臣《续金针诗格》“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一段话时特意说出的。从以上引文看,《续金针诗格》所谓“含蓄”,仅指论诗如商度隐语、穿凿附会、字字句句必有寄托而言。这是宋人的习气,如此论诗,且定为“诗格”,会葬送诗的意象风神的,所以谢榛要针锋相对地标举“盛唐家数”的“格高气畅”,并说:“太白曰:‘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迄今脍炙人口,谓有含蓄,则凿矣。”(卷一)而对于真正的含蓄美,谢榛是予以肯定的。但是,谢榛在论及“含蓄”时,多将其归之于“唐调”,如“意婉味长,不减唐调”(卷一);“清丽有味,颇类唐调”(卷二)等等,不言“盛唐”。可见,谢榛以为“盛唐”所独擅者,乃“格高气畅”。
按谢榛及高棅的界定,盛唐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开元、天宝之际,政治的格外清明,经济的空前繁荣,思想文化的自由开放,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以及对外扩张的不断胜利等等,给社会注入了勃勃生机。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唐帝国虽受到沉重的打击,开始走下坡路,但由盛而衰,元气初伤,希望的火星并没有熄灭,人们仍切盼着恢复“开元之治”,重振声威。面对这种时代风貌,诗人们无不昂扬奋发,兴会无前,痛快淋漓地抒写着自己的情怀。因而,浩气流注,境界宏阔,气象浑厚,风神飞动,蕴蓄着一泻千里之势,回响着青春健美的旋律,焕发着欣欣向荣的风采,就成了盛唐诗歌最突出的特色。谢榛提倡师法“格高气畅”的“盛唐家数”,大旨即在于追求这种时代风格。
谢榛崇尚盛唐之诗的时代风格,并不忽视个人风格的差异和多样性。他指出“盛唐诸公”虽浸沉在同一时代的氛围之中,但由于“诗人养气,各有主焉”,他们的风格同中又有异,“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卷三)。“盛唐”那种“格高气畅”的时代风格,正体现在这多姿多态的个性风格之中,并不是孤立、抽象地存在着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谢榛虽曾多次论及“文随世变”(卷一)的问题,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能坚持这一认识。对于盛唐之诗“格高气畅”的时代风格,他仅仅是从直接体悟中把握住了,却缺乏对这一风格赖以生存的时代进行探讨;更不知当时过境迁,“盛唐”一去永不复返时,那种时代风格也就不会再现了。而他处在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的明代中后期,要求诗整体上超越时代,展现盛唐风貌,简直近乎痴人说梦。笔者认为,时代风格几乎是无法师承的,更不能复制。
六
审视历史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古代诗歌正是沿着复古——排古——复古——排古……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怪圈前进的。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只有排古才是革新、创新,而复古就等于守旧、倒退。其实,大多数复古也都称得上是一种革新、创新的,这是因为:(1)除个别情况外,每次复古,总要给诗坛带来一些新鲜的因素,绝不仅仅是历史的重演。复古不是复旧。(2)复古派的出现,都有现实的依据, 针对性很强。复古,只是打出的旗号,意在借助于古代典范的影响,号召与流俗抗争,革除时弊,确保诗歌循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以免误入歧途,流荡莫返。(3)有目共睹,彪炳于文学史的陈子昂、李白、韩愈、 欧阳修、严羽等人的复古主张及其实践,对诗歌发展的推动力,是远在排古者之上的。基于这些认识,我们也不同意先哲和时贤常常武断地将谢榛和“前、后七子”一同打入复旧派,横加指责。“前、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卷二八六)的大旗,向弥漫诗坛的“台阁体”和“理气诗”发起冲击,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声势赫赫,前后持续百余年。其末流乃至自身,固然多可指摘处,但其历史功绩,即使后来持严厉批判态度的公安三袁,也不得不承认:“自宋、元以来,诗文芜烂,鄙俚杂沓。本朝诸君子出而矫之,文准秦、汉,诗则盛唐,人始知有古法。”(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见《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三《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 月版)何况跻身其间而倍受排挤的谢榛,并不真心复古呢?他树起李白、杜甫及“盛唐诸公”等历代受人敬仰的楷模,只是要试与比肩并立,独自成家而已。如此,岂可以复旧论之?尽管他认识并不全部正确,主张并不都切实可行,实践也不是一无偏差的。
注释:
〔1〕笔者《论谢榛“以盛唐为法”》, 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三十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