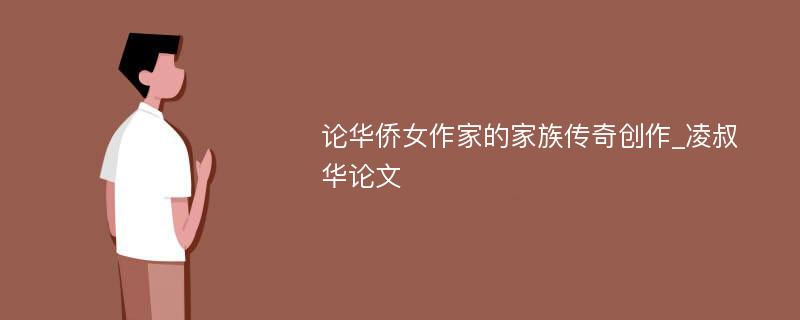
论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家族传奇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海外华人论文,家族论文,传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915(2016)04-0083-07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16.04.013 一、个体视点下的家庭状态 (一)大家庭中的个体孤独 家族传奇书写围绕的核心是家庭。由于《古韵》与《饥饿的女儿》是以作者亲身经历为蓝本的自传体小说,家庭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作者笔下的生活场域与文化场域。凌叔华以小十的眼睛看她经历的家庭琐事,虹影则以六六的视角体验家族成员的命运。在两位作家的笔下,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使得“我”的所见所感显得尤为真实,也从“我”的心理活动中呈现出自我形象。 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侧重主观性、内向性,倾重描述个人经历,同时也侧重抛弃一切幻想去反映生活,甚至包括理解生活的全部悲剧意义的现实主义的观点——这种总倾向的最突出的成就是中国的自传文学。”[1]这段引文揭示了中国自传体文学的特点,即作者深入挖掘内心感受与体验的同时又密切关注外在的世界,试图在内心与外部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用以完整地表现生活。 在《古韵》中,“小十”是凌叔华为自己塑造的人物,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小十天真无邪,善良聪慧,以孩子的眼睛去看大家庭中的人物和故事。然而,养尊处优的生活也并非意味着幸福,作为母亲的第四个女儿、家族中的第十个孩子,小十从父母那儿分到的关注非常有限,从异母的兄弟姐妹那儿也不能得到寻常人家的手足之情。很多时候,她是孤独的,甚至只有当哥哥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小十才觉得自己“有用”,个人的价值在孤独中浮现出来,形成一种矛盾。同时,大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消解,亲情的纽带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的独立存在。自我意识的体现集中在小十的孤独感与疏离感上,在《中秋节》一文中,火辣辣的太阳、红得耀眼的柱子、又甜又苦的菊花香味、慵懒地打着呼噜的猫儿……时隔多年,凌叔华依然能无比清晰地回忆起那时的画面,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一样都不缺,可见当时的场景让她深切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那些物件成为自我孤独感的载体,因而就像是嵌在脑海里的图画一样,成为自我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凌叔华书写家族传奇中童年自我意识的萌发,与她一贯擅长的人物心理刻画密不可分。她笔下很少出现情节性较强的故事,总是以人情世故、琐碎生活和细腻的心理活动来表现女性的苦闷与命运。凌叔华不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但她是出色的画家,她能够用文字“画”出自我,“画”出某些难以捉摸的情绪。 虹影在《饥饿的女儿》开篇写道: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贫民区长大的私生女,家中的第六个孩子,“六六”的生活同样是孤独的、不被关注的。她充当着“边缘人”的角色,身处在为温饱而挣扎的家庭里,说出口的爱、陪伴与理解犹如奢侈品,是六六极少体验过的。出生于生活极度艰难的大饥荒年代,使本来就挨饿的家庭雪上加霜,六六甚至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原罪。从少女走向成年,中间交织着叛逆与反抗、孤独与困惑,六六试图通过逃离家庭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她始终与家庭保持着一段距离,在无人的角落里兀自舔舐伤口。家人的奇怪态度让她感到疑惑,这种疑惑不仅是对个人身份的探寻,也是对自身命运不确定性的表现。人总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个体的身份就如同一个人的根,能够回答是谁、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六六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不同身份,私生女的真相通过她自己一点点地挖掘而显现。当个人的历史已经真相大白,对于到哪里去的问题,也就能够回答得坚定而有底气了。她借着梦想的微光对命运作了安排,她不愿平庸地埋没一生,而要逃出这片狭隘的天地。六六的“自我”是与家庭、南岸居民乃至政治事件对立的存在,正是在与后者的对抗性关系中,她弄清了自己的身份,明确了自己的未来。 不同于凌叔华,虹影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她在文章开头便吊足读者的胃口,带领读者慢慢寻找使她“背脊发凉的目光”。她曾经表示:“写出秘密的文本才是有魅力的文本。”[2]因此六六的所见所闻与虹影的现实生活重合度极大。虹影笔端的自我意识,既是对个人身份的强烈好奇,亦是勇敢坚决的逃离——如此渴望被爱,却被所有人辜负,那就选择离开,生活是她自己的,不是“他们随时随地可穿越的领地”。 从凌叔华到虹影,两位女作家在自传中都渲染了自身的孤独与疏离,这使得她们观察家庭状态的视点更加冷静与含蓄,同时更加清晰地呈现了她们的自我意识。虽然自我意识显露的方式不同,但是在她们的自传体小说中,“自我”都是与外在的“他者”对立的。凌叔华笔下的“自我”,是在现代新思想新观念作用下的自我发现和平等意识,对抗的是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封建家庭内部关系、矛盾以及由于年龄、性别和性格带来的孤独。虹影笔下的“自我”,则是处于被社会和家庭忽视的“边缘人”,以其坚韧和独立,对抗的是狂热的历史和天灾人祸悲剧下沉浮不定的家庭命运和家庭成员的个人命运,以及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 (二)家庭框架下的女性困境 凌叔华生活在大家庭,她笔下除了贵族阶级,也有普通人。限于童年经历,她所描写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家族中的人。在《古韵》中,家庭框架下最突出的个体并非是掌握着权威的男性,而是在父权体制下生存的女性。 《穿红衣服的人》一章末尾,讲到美丽的媳妇谋杀婆婆的事情: 当爸跟五妈说那个女人确实漂亮时,五妈讲了什么,伤了爸的自尊。爸把一杯热茶全泼到五妈的新衣服上。五妈是个性子刚烈的女人,当晚就吞了鸦片。全家都吓坏了,好在一位神医救了她的命。不过,妈相信这是爸想再续一房的原因之一。[3] 从这段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中,凌叔华向读者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大家庭中,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他享有最大的权力,包括对妻妾的处置权。五妈的失宠就在于她挑战了家长的权威,这种稳固的权威非但不会动摇,女性反而会因挑战家长权威而被惩罚。即使是性子刚烈的五妈,她能选择的反抗方式只有自杀,乃至最后出家为尼,这是女性表达不满与抗争的方式。五妈在全书中着墨不多,但是从对她的描写中可以窥见大家族中妻妾的地位是不固定的,失宠或受宠完全取决于是否顺从于家长、取得男性的欢心。 大家族中妻妾间的等级秩序取决于女性手中掌握了多少男性资源,受家长宠爱的妻妾和生了儿子(男性继承人)的妻妾往往拥有更高地位。母凭子贵,即使是女儿有才华有出息,地位也比不上一个平庸的儿子。温柔和顺的母亲朱兰,有才华有主见,唯独没有反抗,她相信命运的安排,默默承受不平和不公。但是,在女儿小十心里,已有反抗的种子发芽。在《叔祖》一章中,《镜花缘》的故事给她带来了幻想和希望,她期待自己能像男孩子一样参加科举出人头地,弥补母亲无子之苦。这是小十渴望性别平等的意识萌芽,也是以温和折中的方式面对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不过,这种反抗是具有妥协性的,小十并没有争取男女的真正平等,而是企图扮演男孩的角色来获得安慰,这是小女孩不成熟的表现。 才华横溢、温柔美丽的义母对艺术有着极佳的品位,但即使是这样的大家闺秀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也不过是扮演贤妻的角色,过着精致而空虚的生活。她喜欢带小十去放风筝,而那些做成蝴蝶、鸟儿或者美人形态的风筝就如同女性的命运,被父权社会所控制、牵引,没有自由。中国传统闺阁女性对放风筝的感情颇深,想必是风筝能飞得高而远,虽是执线人手中的傀儡,亦可代足不出户的她们舒展苦闷心情。民国初期的高官夫人依旧无法摆脱家庭角色的固定模式,许多具有知识的女性也并未走出新的道路,像千百年来的封建时代的女性一样,她们囿于狭小的场域中,依附于丈夫,默默耗尽韶华。 凌叔华笔下婉顺的女性群体,表面上是符合父权社会所要求的温良恭俭的,这表明凌叔华本身也是一位接受父权社会规则与约束的女性作家。可贵的是,对被封建家长制压抑的女性的细微的描写恰恰表达了她对父权社会的反叛与抗争。[4] 在虹影笔下,母亲着墨最多,其形象是在生活重压下艰难前行的粗野暴躁的女性。她的一生都被家庭压制得喘不过气来,年轻时逃婚,结婚后放弃刻骨铭心的婚外爱情,在家庭的责任面前,无路可逃。母亲代表了社会底层的一类女性,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因为看重家庭的责任与女性的义务,一生都奉献于家庭。在家庭的框架下,整体的利益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因此自我牺牲不可避免,个人的悲剧也由此而生。 母亲代表了一代女性的困境,而六六则体现了下一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在那各自挣扎、各求生存的家庭里,没人注意到六六的双重饥饿和个人欲望。不过,她并未在困境中坐以待毙,而是选择直面、摆脱与逃离。她毫不避讳地诉说自己身体的秘密: 最奇异的是我感到自己的乳房,顽强地鼓胀起来。的确,就是从这一天起,我的乳房成熟了,变得饱满而富有弹性。[5] 身体叙事是女性意识的一大体现,在传统的男性话语中,女性的身体是通过男性的视角去描述的,性爱的体验亦出自男性笔端,读者只能知道男性社会中对男女之事的感受与认知。而在女性文学中,女作家从女性的角度去感受身体的原始欲望,去感知男性的身体,使得女性处于主导地位,从而打破了男性社会的话语权,颠覆了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男性叙事。在虹影笔下,在性爱中掌握主动权的是女性,六六赤裸裸地揭示身体的秘密,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的欲望。六六从历史老师身上得到了欲望的满足,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抵抗精神的孤独、逃避世俗的庸常,甚至是寻找缺失的父爱。在性中掌握主动权的一方,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六六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对家庭的反抗,让她仿佛瞬间成熟,拥有了离开家庭的勇气与能力。 然而就像书中最后一章呈现的,六六的流浪时光充斥着放纵、欲望和烟酒,但是这并没能让她脱离内心的困境,她依旧迷茫,依旧对渴望的东西求而不得,依旧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定位,这就是家庭的缺失给她带来的无法弥补的伤痛。 从凌叔华到虹影,她们看到的家庭对女性生活的影响由压制转为缺失。20世纪初期封建家长制还未被打破时,凌叔华感受到身为女性在大家族中的焦虑不安,她们是男权社会的附庸品,是精致的花瓶。然而破茧而出的力量已经在积蓄,新女性走出家庭踏入社会渐成风气,男女平等的思想也初露端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封建家长制早已荡然无存,女性却并没有完全摆脱家庭限制。母亲依旧被逼婚,依旧为了家庭而放弃爱情;六六因为缺失家庭之爱陷入生命的困境。虽然女性走向了社会,但她们并没有获得来自家庭的有力支撑,不得不只身面对困难。母亲那一代人选择了屈服与承受,六六那一代人选择了反叛与逃离。在人人自危的历史背景下,家庭原本承载的温馨之意淡去,在女性生命中是缺位的。总之,20世纪从初期至七八十年代的大半个世纪,女性依旧在家庭的困境中挣扎。 凌叔华与虹影的个体呈现与女性意识都与家庭状态密不可分,而家庭状态又与民族、国家和历史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而言,家庭是国家的一个缩影。它的矛盾和命运,也是整个国家的矛盾和命运。传统文化消亡、现代文明涌入,凌叔华对两种文化有都着难以取舍的心态,于是她以美好含蓄的笔调赞扬了以家庭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精致优雅,同时又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和思想去鞭挞文化中流传千年的糟粕——封建家长制的腐朽残酷。这种态度与有识之士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是一致的,依托传统走改良之路还是彻底摈弃传统走革命之路是充满矛盾难以抉择的。虹影的家庭充满饥饿,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更缺乏手足之爱,当时的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横扫整个国家的大饥荒饿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文革和政治狂热又使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多是自保与钻营。畸形的家庭折射出畸形的社会,虹影揭露了种种丑恶与人性的黑暗,通过冷漠的家庭看到了同样的社会。家庭中的清醒者也是这个国家少数清醒者的象征,他们冷眼观察家庭关系,也审视国家的政治环境。 二、家族环境呈现的中国想象 (一)家居陈设中的东方特色 《古韵》中,凌叔华选取的是具有浓厚东方古典气息的场景。在描写父亲审问犯人时,鉴于目标读者对东方法庭的一无所知,因此有必要详细地描绘公堂的场景。凌叔华以小十之口说出了对旧式法庭的高度认同与自豪感,认为这是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犯人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旧中国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人治,这与西方相对完善的法制来说完全是古老而落后的。但是凌叔华通过自己的描写,将这种带有人治色彩的法庭表现得有声有色,甚至是公正威严的,与西方世界固有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差异。认知上的距离能产生神秘感与传奇性,这就使这本小说具备了强大的吸引力。 在描写家具陈设时,凌叔华选取了屏风、青铜香炉、盆花、古琴以及最好的红漆桌案等物件进行详细描写,这些是中国传统文人书房必备的陈设,雅致的家具和昂贵讲究的用料体现了屋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文化品性,因此这类物品就成为文人雅趣的典型意象。凌叔华将这样的场景描绘出来,意图将西方读者带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场域之中,这就使其中发生的故事具有异国情调,即东方美的韵味,“古韵”这一书名的意味便在于此。 相比之下,《饥饿的女儿》没有丝毫精致典雅的文化气息,它展现的是赤裸裸的地狱。在虹影写作的年代,西方对中国古老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了共同、固定的印象,却对新中国建立后普通人的生活知之甚少。在历史的激荡起伏之中,虹影向西方人描绘了底层民众的状况。 虹影构建的生活空间几乎都展示了丑陋的一面。拥挤不堪、破旧潮湿的六号院子如同一间囚室,睡着六个孩子的小阁楼白天得拆掉床板用于吃饭,南岸贫民聚居地的垃圾堆散发着臭味,阴暗的防空洞弥漫着腐烂的气息,公共厕所的肮脏不堪,女孩嘴里吐出的蛔虫……令人作呕的画面成为六六逃离的理由之一。 不像凌叔华所处的大宅子,有着精美讲究的陈设,虹影童年时的狭小家中几乎没有家具。她以冷静的笔调营造了一个底层贫困家庭的真实生活空间,充满庸俗自私的市井气息。其小说中令人震惊的细节描写与大多数读者的认知产生了距离,从而达到了审丑的效果。 (二)日常化叙事投射出的文化背景 家庭的日常化叙事,是跨文化叙事的一种手段,日常生活的描写往往将异国读者带入作者自身文化氛围下的现实情境中。凌叔华和虹影都采用了这种叙事手段,在看似真实中达到传奇的效果。 在凌叔华那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不仅仅停留在对家具陈设的描写上,家中人物不起眼的三言两语往往也是文化的表征。宽厚善良的保镖马涛对砍头一事的评论是,“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句屡屡出现在传统戏文中的台词代表了中国普通民众对生命的态度。凌叔华在信中写道,她的自传是关于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他们的思想是由代代相传的古老格言和谚语控制着,他们说不清什么才是道德的,但他们知道什么是做人所必需的”。[6]146熟语的运用,一方面具备了东方特色,一方面揭示了中国普通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看似淡漠中达到超脱的心境,是普通人所共同信奉的生活哲学。这种生活哲学存在两面性:它既可以被称赞为不羁于物的超脱,也可以被批评为思想的封闭性与麻木性。缺乏教育的普通百姓遵循着千百年来的古老经验与处世方式,他们不去思考事件的原因,也不会想到如何作出改变,他们只知道祖先是这么做的,其他人是这么做的,心里就平衡了。中国文化的惯性与惰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家中花匠老周和李大伯对养花种花的热爱与精通,可见老北京人的生活情趣。文中插入了李大伯描述的慈禧太后对花的品位和鉴赏力,使文章读来颇具传奇性,也体现出这位宫廷花匠经验的丰富与手艺的高超。辜鸿铭先生夸奖老周是一位天才,是潜在的了不起的政治家。的确,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常常提炼于生活之中,“治大国如烹小鲜”即是。人们善于从具体的实践中抽象出高深的道理,将不同领域的智慧融会贯通。 在凌叔华的笔下,她对消逝中的传统文化的留恋与热爱俯仰皆拾。然而,期望成为新女性的她对于禁锢女性的制度,又表达了不满与反抗。她身上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凌叔华,却对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理念持不同看法。在《古韵》的《老师和同学》一章中,她借语文老师张先生之口道出自己的观点:传统文化不可全盘否定,它蕴含着西方无法企及的智慧。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得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的异国情调不在于文化和传统,而在于深深融入进家庭生活和人物命运的地域和历史。长江与船是贯穿小说的一个重要意象,也是虹影一生走不出的文化象征。虹影在后来的访谈中也提到,无论她去到哪里,她依旧是长江的女儿。长江之于她,就像是缺失的父爱与母爱,陪伴她走过孤独的青春,她把这种情感寄托在六六这一角色中。江上的船就如她漂泊的一生,在水中起伏航行,却始终逃不出江水的怀抱。长久以来长江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在虹影的小说中,长江与船成为文化意象,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悲剧与家庭的命运,孕育生命也终结生命,既象征着逃离又象征着回归,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身处异国他乡的虹影的精神安慰,是她与故土的情感联系。 虹影想要真实而生动地向世界呈现她的亲身经历,具有特色的地域元素是形成神秘感和传奇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六六和家人的对话中,方言的运用最为突出。“啷个”“啥子”是典型的重庆方言,在母亲、大姐的话语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一方面可以刻画出两位女性的敢爱敢恨的暴躁脾气;另一方面也仿佛将读者带进了民风耿直倔强的山城。小说中讲述了重庆地区的一些鬼怪传闻,在神秘诡异的氛围中,读者仿佛在探险,深入古老而遥远的地域,刺激而惊悚。这具有蜀地文化特色的元素使虹影的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虹影用大量篇幅来展现大饥荒中如同草芥一般逝去的生命。例如文革武斗的惨烈,人性的阴暗、残忍、愚昧跃然纸上。六六一家的人物命运都与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密不可分。虽然六六并不关心政治,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种种悲剧却无法与残酷的历史环境分离。 总之,经历了极端政治狂热的遥远国度、充满秘密和故事的家庭、出身贫民的旅居英国的华人女作家,这些东方元素足以调动西方读者的好奇心。 凌叔华和虹影笔下的中国想象成为远在异乡的她们与故国之间的一条纽带,遥远的土地给漂泊的她们以精神上的支撑与慰藉。她们早年最熟悉的家庭自然地成为中国想象的载体,传统文化、历史政治和地域因素都通过自传式的回忆,倾注在家族传奇的书写上。只是,不同的出身和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书写模式。贵族出身的凌叔华在记录她的见闻,并不多写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西方人对中国古老高雅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感兴趣,她也恰好拥有写作的素材与资源,于是她适度美化了那些记忆片段与家庭生活场景,给西方读者营造出典雅的中国文化氛围。贫民出身的虹影既写内心感受也写社会见闻,她将两者结合起来,展现给西方一个相对陌生的新中国。她适当丑化了自己早年家庭生活中的情境与场景,融入意识形态的描写,造成令人震惊的审丑效果,成为西方读者眼中的另一种“异国情调”。凌叔华与虹影分别根据自身经历与西方的兴趣构建了中国的美与丑,形成历史变迁中的中国想象的两面性。 三、家族传奇书写的文本结构 (一)生活的横断面:《古韵》中的散文性 五四以来的女作家,限于女性生活空间,大多选择以散文笔调来描述她们熟悉的事物和抒发细腻的情感体验,作品往往具备散文性的特征。凌叔华也不例外,她的《古韵》截取了生活中幽远明净的场景,与家居陈设的典雅有致形成统一的审美风格。 凌叔华笔下的景致,色彩明丽,层次清晰,《一堂绘画课》、《秋日天津》等篇章中景色的呈现比比皆是。这得益于她的另一身份——画家。在画家的眼中,浑然一体的自然景色能分解成斑斓的色彩和明暗浓淡各异的层次,诉诸文字之后,读者能体会出“文中有画”的美感。国画讲究的情景交融、意在笔先、虚实相生都在这些文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这些散文性的描写,看似与家庭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它们是小十心境与情绪的产物,是对家庭生活环境的抒写,起到了烘托氛围的作用。同时,景致也是凌叔华创造的“中国想象”的一部分,悠远明净的意境构建起文化审美的场域。 《古韵》由英文写成,古老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对西方读者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然而有些文化典故却是他们完全陌生的,因此凌叔华在书中许多地方插入了对中国文化、文学和历史的介绍,在文中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停顿。例如对清末广州城的经济、贸易和四大家族的介绍,是为了让读者明白清末贵族家庭的生活景象;对兰花品种和形态的介绍,展现的是传统文化的艺术和贵族阶层的审美情趣。这些停顿打破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形成了从容不迫的古典风格,使得小说更具散文性与文化性,也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 由于写作时已经离童年有一段时间,凌叔华实际上是在回忆的片断中寻找那些闪光的亮片,并将之拼接在一起,形成了“生活中的横断面”结构。这个结构是静态的、并不连贯的,像是跳跃式的记忆片段,因此小说的故事性相对淡化,散文性却愈发突出。小女孩的视角使她过滤了记忆中那些不愉快或无关紧要的东西,留下的是充满诗意的天真烂漫的画面,回忆里的情感和对美的体验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醇香。凌叔华的文字很少见到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用含蓄内敛的温婉风格刻画女性的内心。鲁迅这样评价道:“凌叔华的小说,却发样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7]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古文明的精致优雅,温婉顺从的贵族女性以及她们丰富而含蓄的情感,是一个新鲜而充满美感的世界,无怪乎《古韵》在异国受到欢迎。 (二)多重时空转换:《饥饿的女儿》的戏剧性 在《饥饿的女儿》中,虹影构建了多重时空,这些时空自由切换,使家庭命运与历史、政治环境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戏剧结构特征。 故事的主体时间和空间发生在重庆南岸的贫民窟,在六六的十八岁生日前后。虹影从开篇就设置了一种悬念,那个跟踪她多年的目光到底是谁,父母为何将她与哥哥姐姐区别对待,而她的家庭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在团团疑云中,六六开始寻找个人与家庭的秘密。大姐回家的几天,六六敏感地认定大姐知道许多往事,因此在她的坚持下,大姐说出了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叙述者从六六切换到大姐,时间也倒转回到1943年的严冬,为了将那时的政治气氛与人物心理刻画出来,虹影选择了冷静的第三人称叙事,通过大姐的口吻描述能够过滤掉六六对母亲的情感偏见,将现实和过去区分开来,形成丰富的结构和层次感。 关于文革中重庆两个造反派别武斗的历史,其实是由历史老师说出的,因此叙述人称又切换到第三人称。事件发生的空间也不限于南岸的野猫溪一带,而是整个城市的两江三岸。那时六六还年幼,自然无法明白其中的恩怨,然而借着历史老师的视角去看待,就得出了超出十八岁少女思考范畴的成熟观点。历史的悲剧与恐怖在平静的叙述下更加凸显,使得小说脱离了纯粹的个人和家庭,而上升到对历史的关照。 不仅是叙述人称的变化,而且即使是第一人称,也存在不同时空的叙事。文中的“我”,既是现实的经历者,又是回忆的讲述者。六六经常会在家庭琐事中插入自己的回忆,通过倒叙、插叙的手法让读者全方位地体会她的孤独与精神饥饿,全方位地呈现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甚至是邻里关系。这种在不同时空中的自如切换增加了自传体小说的层次,使文本具备了文学性和吸引力。 虹影所擅长的“讲故事”,不仅表现在故事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上,还体现在结构上。多重时空的转换、叙述视角的切换进一步加深了文本的戏剧性。戏剧讲究冲突,《饥饿的女儿》隐含了大量的冲突元素。六六自我身份认知的冲突,与不理解自己的家人的冲突,与陷入政治狂热中的邻居、老师、同学所代表的社会的冲突,还有欲望和现实之间的冲突。种种矛盾在时空、人称的转化中被赋予动态的叠加效果,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凌叔华的日常化叙事营造的散文化效果是相对平静舒缓的节奏,就像一条小溪潺潺流淌,这种文风与旧传统对女性的要求是一致的,以婉顺柔和为佳。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凌叔华试图展示古老文明的优雅从容,小说结构上也呼应着文风。而虹影的多重时空转换的叙事营造出了相对激烈紧张的戏剧化效果,恰如表面平静的海面暗流涌动,与畸形的社会氛围、残酷的政治背景和悲惨的人物命运遥相呼应。总之,两位女作家根据自身小说的主题和意图,各自选择了恰当的结构,为小说增添了亮色。 女作家写作自传体小说时,常被批评为“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她们构建的叙事空间离不开自我经历和家庭记忆,使得女性自传体文学的整体空间囿于她们所熟悉的生活琐事。然而,对家族记忆的传奇式书写恰恰是海外华人女作家自我身份认同的建立。她们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中产生了迷茫与疏离,需要重新找回自我身份。另一方面,家族是历史长河中民族和国家的缩影,以小见大,海外华人女作家通过家族传奇建立起了自我和故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了遥远神秘的东方国度作为依托,她们在陌生的文化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也找到了获得西方认可的捷径。 凌叔华写《古韵》的初衷是用以排解自己苦闷与不安情绪,是暂时脱离家庭矛盾的一种安慰,最终成为她逃离战火纷飞的中国后在西方文化界立足并获得认可的“赌注”[7]。凌叔华所心心念念的童年,正是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走向衰亡,现代化思想和文化的兴起之时,她用不断回顾往昔的方式将自己的身份认同确定下来,并在文化上获得了来自遥远故国的支撑。正如魏淑凌在书中写到的:“她们的童年故事提供了一种暂时的解脱,一种关于‘原籍’的想象,一种回归的依托,还创造出一个永恒的瞬间。在这一瞬间,她们可以把自己视为一个勇敢的、真正的英雄。”[8]63 虹影说她得了一种只有弱者才有的逃离病,于是她逃离南岸,逃离重庆,最后逃离中国。然而她在逃离中又在回归,从她回到北京居住、原谅母亲、与自己的出身达成和解来看,她也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且在这曾经让她饱受创伤的土地上找到了自我。虹影小说里充斥着漂泊感,这种与逃离相依相伴的感受通过写作获得了安慰。随着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日益密切,世界另一端的生活方式已经不那么陌生。因此,她不再写典型的东方文化,不写那些西方人印象中美丽的中国元素,而是写自我和内心,写传统断裂后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写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里普通人的悲剧,那些是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人眼中陌生的景象。其文本中的脏乱丑恶与《古韵》中的精致优雅形成鲜明的反差。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殊途同归,都在向西方人展示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凌叔华展示的是消逝的古文明造就的异国情调;虹影展示的是历史大背景下渺小的个人命运。 从凌叔华到虹影,她们期望获得西方认可这一点从未改变。然而时代不同,两者的书写重点也有变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危亡、传统消逝时,也是西方世界战乱动荡之期,家国与文化的概念更能引起西方的共鸣。帕特里夏·劳伦斯认为,凌叔华和伍尔芙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同是处于战争期间的女性和作家的身份,是文化上的交流,而非帝国主义姿态下的不平等[6]380。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西方的局势趋于平稳,新中国刚刚向世界重开大门,在西方人眼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又陌生,这个历史背景下的普通人的内心、女性的意识成为更普遍的主题。凌叔华和虹影,都利用了西方对东方的好奇心,利用了文化差异而获得成功。她们站在文化的一方去观察另一方,其文化交融的视角与思考方式,也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标签:凌叔华论文; 虹影论文; 六六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饥饿的女儿论文; 古韵论文; 家庭论文; 自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