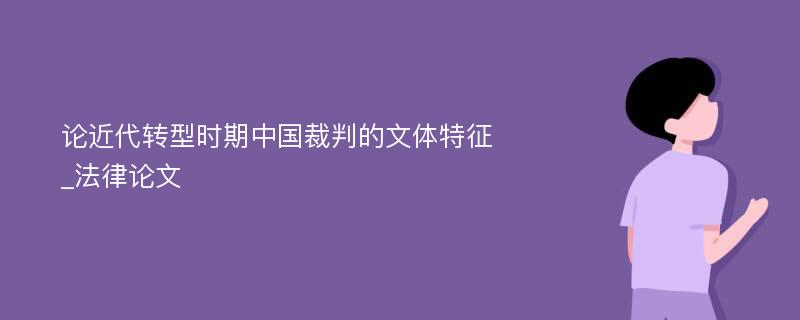
论中国判词近代转型期的语体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体论文,判词论文,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清末戊戌变法和修律运动,近代(1840-1949)判词在中西法文化碰撞中出现了重大转型,受异质文化的渗透和冲击,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突破,从判词的篇章结构到语言的运用都不同于传统的判词。不论是结构模式还是语汇的专业化均出现新的突破,判决理由吸收西语的逻辑繁复之表达,增强了说理的逻辑效果,改变了古代判词重道德修辞轻法律修辞的语体特色。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判词语体中程式化及逻辑化问题加以探讨。
一、近代判词语体研究综述
有关我国判词研究,目前学界多集中于古代判词,比如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刘愫贞《判词语体论》、赵静《修辞视域的古代判词研究》三部著作,分别从法史角度、语体角度、修辞角度加以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均以古代判词为研究对象,没有涉及近代判词。另外,诸多论文也多是围绕古代判词从不同角度分析论证的,如贺卫方《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王志强《〈名公书判清明集〉法律思想初探》和《南宋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取向》,郭成伟的《唐律与〈龙筋凤髓判〉体现的中国传统法律语言特色》,苗怀明的《中国古代判词的文学化进程及其文学品格》、《中国古代判词的发展轨迹及其文化蕴涵》、《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品格》,田荔枝的《从〈折狱新语〉看判词语言风格的变化》,陈宝琳的《中国古代判词的发展演变和特点分析》等等。
而对于近代判词,研究者较少,从笔者目前所搜集资料看,相关论述主要见于以下文献:
何勤华在点校本《华洋诉讼判决录》前言中,对直隶高等厅有关华洋诉讼的判词作了总体评价,并纠正了一些传统认识:“当时的判决书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以及文章风格的。对控诉人的控诉理由,法院都是严格依据证据、法律、法理,层层分析,详细辩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长的判决书竟长达28页,共22000多字,而最短的才十几行字。这种依照案件的内容来制作判决书的精神,对我们目前的司法审判工作,仍具有参考的价值。”①
李启成在点校本《各省审判厅判牍》序言中有一部分相关论述,指出了近代判词在社会转型期新旧兼备的特色:“发现各级审判厅推事们制作的诸多判词,向读者展示了清末社会在司法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势话语体系:那些从异域移植而来的新法学名词……占据了说理的中心舞台。正是以此类法学新名词为核心,形成了一套新的强势话语体系。”②论述颇为精到。
俞江在点校本《塔景亭案牍》导读中对清末民初(大致在1908年至1914年之间,即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年之间)地方审判资料——江苏省句容县县衙判词,根据审理对象作了分类,并指出:“判词所处理的对象也极为复杂,民事诉讼尽管是判词处理的主要对象,但不能把县衙的判词一概视为今天意义上的民事判决书。”③
张德美的著作《从公堂走向法庭——清末民初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一书,也有部分章节涉及近代判词问题,主要是清末民初的判词,提出:“证据调查为判决提供了事实基础,而适用法律是判决的核心问题。清末民初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使判决样式发生了变化,判决的精神也从古代的执法原情发展为依法裁判。”④
还有部分论文,如李贵连、李启成的《司法判决书与中国近代法研究》,周祝一的《中国判词近现代发展概况》,何勤华的《(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王春丽、余钊飞的《1928-1937年上海档案馆若干刑案判词研究》,邓雯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湖南邵阳地方刑事判决书探微》,王长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之裁判文风》等等。
台湾学者对此进行的研究颇为突出,如黄源盛在其相关论著中多次涉及近代判词的风格、制判人员的素质等等,其著作《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1912-1928)》对民国初年大理院判词作了高度评价:“1912-1918最亮丽的是什么?是大理院的裁判文书,都用毛笔字写的。不仅仅内容好,书记官的毛笔字都可以当作艺术品来欣赏。我后来跟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照过,国民政府的裁判书差太远了。甚至台湾早期的裁判书也跟不上大理院的裁判书。”⑤
二、近代判词语体发展分阶
近代判词语体发展的典型阶段为清末时期和民国时期。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我国近代判词语体呈“双轨”现象发展: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判词,另一方面是革命根据地的判词,后者较前者不仅目的、性质完全不同,而且语言更为通俗易懂,但仍沿袭传统格式。
(一)清末判词语体
20世纪的晚清法律改革,中国传统法律和法制逐渐被扬弃,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借鉴西方的司法独立,审级制度上实行四级三审制,在审判制度上采用资产阶级的辩护制度、陪审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原则以及第二、第三审判决的合议制度,并建立了由大理院执行的“复判”制度等。立法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民刑不分,逐渐与现代西方司法接轨。
受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影响,翻译、引进西方两大法系实体法、程序法著作之后,以大陆法系国家判词为蓝本,制定了包括判词在内的法律文书的新格式。清末宣统年间由奕劻、沈家本编纂的《考试法官必要》借鉴日本、德国司法文书制作经验,启动现代法律文书格式,对刑民判决书的格式作了统一的规定,主要项目与现代判词十分相似,在制作格式上与古代判词迥异。
然而,这些判词格式在清末并未启用,而是由民国政府根据实践需要逐步完善后得以实施。因为尽管晚清法律规定比较完备,但由于当时中国传统司法的惰性,人才、资金的缺乏,民众观念的落后,在实际的改革中,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清末民初的司法体系呈现出的是一种新旧交替的局面,即上诉审和终审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受理,而初级审判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因此,清末初级审判的判词不论是司法官有权作出判决的“审语”,还是其无权作出判决而制作的供上司参考的“看语”,在内容上,虽然也包括了事实、分析和裁判结果三部分,但是在结构上却没有明确的分野,需要读者自己去发现和分析,表现出对古代判词的传承意识,在法律体系新旧交替的语境下保留了古代判词的特点,只有在专门审判机构针对上诉审和终审所作的判决中传递出判词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信息。
另外,晚清一些思想开明的有志之士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为判词语体的演进开拓了新的语文环境。黄遵宪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出发,将它们与人的智识联系起来,强调通过变革文体以利民众,把语言文字当成了开启民智的工具。推进文言通俗化,改变中国文体,借以普及文化,提高大众文化素质,促使全民族的觉醒和崛起,成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声。梁启超倡导的报章“新文体”,浅白、生动、平易晓畅,突破了文坛的种种定则,极大地解放了文言文体的束缚,它吸收了文言和白话各自的优点,影响和改变了一代文风。在语言运用方面出现了两种情形:面向民众,白话文成为宣传政治的手段,而在上层仍使用文言,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认为文言高雅而白话低俗。白话与文言的发展是与历史时代的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因此,晚清的白话文文体更倾向于半文半白,这种语言风格同样在判词中有所体现。此期判词主要见于《各省审判厅判牍》⑥、《塔景亭案牍》⑦。
(二)民国时期的判词语体
1.民国元年至1927年的判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判词格式沿袭清末法制改革时期推出的新格式,并作了改进。引入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的文书格式,形成“主文—事实—理由”三段论式结构。
清末变法修律,西方法文化的输入,以西方的法言法语被系统地引进为标志,且随着法学教育的展开,从“中华民国”元年起,判词已不同于过去,大量的语体词——法律专业术语出现在判词中,结构模式稳定成型,语体风格上以散体为主,语言平实精炼、叙事明晰、论证充分、说服力强。
从写作技艺看,民国时期的判词颇有造诣,可以说是中国判词语体史上继唐宋以后又一次质的飞跃,这在《大理院判决录》⑧中有突出体现。大理院的判词结构与布局大体上有一定章法,依规定分为主文、事实与理由三部分,判决主文一般需引用法条文句,或按事实内容而为准驳,大多是简易的文言,并不难懂,只是事实及理由部分的措辞往往因个人文字素养而有不同,但法律术语多,且因当时未加标点因而断句相对困难。此期判词语体对后世判词的断案的“个性化”和说理的“论文化”均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直至1949年以后,这些语体特点仍为我国台湾地区继承和发展。
此期判词主要见于“法理精醇、文笔雅洁”的《现行律令判牍成案汇览》⑨、《最新司法判词》⑩、民初大理院汇编的《大理院判决录》、直隶高等审判厅编印的《华洋诉讼判决录》(11)、天虚我生《司法案牍菁华》、谢森等《民刑事裁判大全》(12)等判牍汇编。
2.1927年国共合作分裂后的判词
主要分为国统区判词与革命根据地的判词两支。
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法要求裁判书记载受裁判人之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所,记载检察官或自诉人并代理人、辩护人之姓名。而且,判词笔录之正本,应由书记官依原本制作之,盖用法院之印,并附记证明与原本无异字样。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颁发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判词和书状的格式内容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没有形成程式专书。
革命根据地的判词在结构上基本沿袭“主文—事实—理由”的模式,但判词语体风格与国统区截然不同,逐步走上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为新中国现代判词语体奠定了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的语言差别并非是汉语本质上的分化,汉语仍然是人们共同的交际用语。两个地区并未出现大量的专用词语和特殊句式;书面语的差别只是语体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并非处处都是分明的——事实上,国统区也有白话,而革命根据地的判词有用半文不白的语言风格,从判词实例可以证明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共两党审判机构的判词,语体上可谓文白兼有,古雅不失简明,通俗亦显雅致,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三、近代判词语体: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自晚清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欺辱下,迸发了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法律改革作为此种宏大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也具备社会转型的新旧兼具等特点。在法律体系新旧交替的语境下,清末判词一方面表现出对古代判词的传承意识,像《塔景亭案牍》中体现司法行政合一、制作主体为县官的判词还依旧存在,这些判词更多地继承了古代判词的语体特色,重道德说教、伦理化程度较高而且情感化语言颇多。另一方面,中西法文化碰撞为判词语体的重大转型提供了契机,在异质文化的渗透和冲击下,判词的结构模式、法律修辞意识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同时吸收西语的逻辑繁复之表达,增强了说理的逻辑效果,这在清末判词的代表性专辑《各省审判厅判牍》中就已初现端倪,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新的结构、新的话语风格。
(一)判词篇章的程式化
程式化是判词体现其法律权威的必然结果,是法制进化的必然过程。程式化判词,有助于约束制判者思维状态,有助于展示法律推理的逻辑性。可以说,古代判词向近代判词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判词的程式化。
判词程式化在古代判词中虽有些微体现,(如《折狱新语》(13)中的开篇词“审得”等)但仅限于部分词语的习惯性用法,其粗略与简单尚不足以说明实质性的程式化。到了近代,判词的篇章结构已划分为几个特定的组成部分,且每一部分都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化语言(或词语或句子或句群、段落),体现出制判者的严谨理性。在人类的语言实践中,人们总是力图使其所归属的文化或行业内的某种语言标准化,从而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减少交易成本,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吉本斯指出:“在法律中,读写能力的标准化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一种语词形式被认为是充分地满足了某个特定的法律目标,例如某个特定的语言在法庭上被认为是创立了一项有约束力的承诺,它便成为在后来的允诺中再次使用该语词表达的一个充分理由。事实上它起到了一种先例的作用。一旦法律行为通过书面文字确立下来,它们便可得到商讨,相关要素可以得到复制。在法律中,这促进了格式文书(Form Books)的发展,它们提供被人试用过并得到检验的语词形式,法律学者们可以将它们汇编在一起形成操作性文件。……它也可能会适时导致制作整个操作性法律文件的标准方式的产生……它也可能会导致一项法律功能得以实现所必须经历的那些步骤的标准化,亦即会导致标准法律语体的产生。因此,连贯和保守是法律书面语的典型特征。”(14)很显然,经过历代法律人的共同努力,判词语言不断地被标准化。事实上,判词语言按照一种经验主义的做法被固定下来,文本越来越程式化、标准化,形成了法官们必须遵循的行文格式。这些格式既是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标准化和格式化的努力。
判词程式化主要反映在语篇程式化与语句程式化两方面。
语篇程式化。具体表现为判词文本有明确的固定段落标示并使用提示语如“主文”、“事实”、“理由”等结构全篇,使判词展开模板化。一般而言,判词展开程序为:主文、事实及理由,语篇段落分类固定。结构模式如下(注:当时行文采用竖排版):
“右列上告人……本院判决如左……主文……事实……理由……”
表明判词语篇有固定的模式,裁判思路逻辑严谨。在这一总体模式下每一部分又有相应的下位层次构成。
如前文所述,清末宣统年间由奕劻、沈家本编纂的《考试法官必要》对刑事、民事判决书的结构内容作了统一的规定,主要项目与现代判词十分相似。晚清法部所颁布的通行于全国各级审检厅的章程《直隶省各级审判检察厅暂行章程》第二章审判通则中第六节公判第四十六条规定(15):
判词之定式,除记载厅名并表明年、月、日,由公判各官署押盖印章外,其余条款如下:
刑事
一、罪犯之姓名、籍贯、年龄、住居、职业;
二、犯罪之事实;
三、证明犯罪之理由;
四、援据法律某条;
五、援据法律之理由;
以上系有罪判决之款式。其无罪之判决,但须声明放免之理由。
民事
六、诉讼人之姓名、籍贯、年龄、住所、职业;
七、呈诉事实;
八、证明理由之缘由;
九、判断之理由。
清末判词的代表性专辑《各省审判厅判牍》中所收录的判词(见后附实例一),基本上都明确分为案件事实、判决理由和判决主文三部分,每部分相应的提示语分别为“诉讼事实”“判决理由”“判决主文”,虽然总括这每部分的用语可能微有差别,如“判决理由”一项,有时称为“证明理曲之缘由”,有时称为“援据法律某条及理由’’等等,但由于其明确的段落划分和用语提示,和古代判词的结构相比,其结构的明晰性不可同日而语。此种结构的变化,其意义不仅在于结构自身,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判词所服务对象的变化、制判者司法观念的转变。《各省审判厅判牍》中的判词虽然并不尽如上例所示依照明晰结构安排判词内容,但其多数判词已经开始注意判词语篇的模式化问题。因此,可以说《各省审判厅判牍》新旧交杂,以新取胜,是古代判词语体向近代判词语体过渡时期的新动向,它向世人传递出一种新的信息:判决修辞开始注意行文的理性。
然而,判词语篇程式化的真正实施出现在民国初年。此期的判词呈现出全新的语篇模式,其首部、正文、尾部均有相应固定的构成部分,每一部分提示用词一一固定,避免了《各省审判厅判牍》中同义提示语多种选择的情况,更简省了古代判词中的收尾提示语“此判”二字,而是以一种全新、定型的模式化语篇出现,跨出了向现代意义上的判词语体规范转化的重要一步。民初大理院汇编的《大理院判决录》、直隶高等审判厅编印的《华洋诉讼判决录》、天虚我生《司法案牍菁华》、谢森等《民刑事裁判大全》等判牍汇编,均可以看到民、刑判决书等各类判词模式趋于成熟定型。
在语篇模式化的基础上,语句的程式性也是判词程式化的一个方面。主要表现在贯穿于判词语篇的习惯性或固定性词语。其中包括宣判提示语、陈述提示语、证据提示语、论理提示语等等,这些词语形式固定、所指明确,程式性明显,是最能代表判词语体特点的语体词,是判词区别于其他语体最直接的体现。
如“本院判决如左”、“主文”等便是宣判提示语。民国时期的判词不论是国统区还是革命根据地的判词,均有这种固定的判决提示用语,尽管案件结果因个案有别,但需要借助这种语言加以表述。陈述提示语包括程序提示和案情提示。其用语庄重典雅、要言不烦。如:“右上诉人……因……案件,不服……第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案经……侦查起诉……”;案情提示语则如“缘……”、“因……遂……致……”以示下文是对法院所采信案件事实的叙述;证据提示语多用“经……”、“据……”、“讯据……”、“核……”;理由则用“讯据、经查、采信、无可采”等说明判决依据及理由。主文部分用“维持……”、“撤销……”、“判决……”等语陈述判决结果。判词对当事人陈述的表述在词语程式性上亦有所体现,或间接概括或间接转述,或直接转述,或直接引用,从而在述清案件来龙去脉的同时对构成事实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行为人、手段、情节、后果诸要素予以交代。通过语言建立其间的内在联系,使案情成为一个具有逻辑性的、完整的、有着自身特性的案件事实,也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等程式性极高的语体词有客观依据。
判词程式化对判决修辞选择的限制呈递进关系,程式化程度愈高,修辞选择的范围愈狭窄,程式化实质上是对思维的限定,让制作者在一个预先制定好的思维模框中展开叙述、议论、说明,也可以说是确定了话语基调,所选修辞一定是和这种基调保持一致的,否则就会发生有违语体的修辞现象。
中国的判词从唐代的骈判发展到后来的散判,再由结构不明晰的散判发展到此种三段式的散判,不仅意味着判词所表达的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之间逻辑关系的强化,而且使得判词本身更易懂,更容易阅读和传播。判词的功能也必然产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满足上司检阅和存档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说服当事人以及因此判决而受影响的人们,甚至于普通民众。同时,这又反过来会影响制作判词的法官,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判词在内容上更有说服力、在形式上更通俗易懂,这种双向互动有助于提高判词的整体水平。
(二)判决理由的逻辑性
判词的程式化实际是其内容逻辑性的外化。近代判词在行文结构定型的同时,析理语言增强,体现出明确的裁判逻辑程式,正如有学者所言“判决首先是法律适用活动的一种结果,而法律皆以规范的形态存在,因而判决论证是一种规范论证。规范作为一种应然命题,它是对人类行为进行要求、禁止和允许的一般性规定。所以规范论证不是对真相或真理的证明,而是对规范或人类个别行为是否正确或妥当提出合理的依据。是故裁判者欲证明一个法律判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则‘必须至少引入一条普遍性的规范’,而‘法律判断必须至少能从一条普遍性规范连同其他规定中逻辑地推导出来’,并且‘必须尽可能多地展开逻辑推导步骤,直至无人质疑:相关陈述的确适用于系争案件’”(16)。重视判决理由的法律论证成为现代判词规范的重要标志之一。
古代中国自秦以后中央集权日益加强,君权至尊,逐级而下严密地统治着百官群吏,民众位处最底层,上下的关系不仅是职务、权威的大小,甚至还在道德、智能上,也推定其有高下之分,同时信奉“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因此在判词制作中,对阐述法律理由并不重视。“在重大案件的报告里,臣下虽有‘管见’可做建议,但无不以在‘圣聪’、‘宪虑’的洞察之中,自然无用哓哓上渎,只要将案情叙述明白,以供上宪、圣主的决定便行了。至于皇帝最后的判决,因为无虑他人批评,除非有意使它成为一个新例垂诸后世,必须阐明其意图之外,大多极为简略,不屑对案情、法理等多加解释。”(17)另外,古代中国没有健全的法律教育和律师制度,“司法者在审判之时既无人能加以监督,所作判决无须详申理由,判决之后又很少能加以批评,其心智不免流于疏懒,其判决不免失诸简陋”(18)。
因此,我国古代判词语体多缺乏法律修辞特点。如西周时期的《亻朕匜铭》(19),文字简洁平实,说理性不强。汉代判词注重在实践中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突出以儒学经典断案析理。唐宋时期是古代判词的繁荣阶段,判词语言富于变化,感性成分突出,即使在宋代判词以及古代判词成熟阶段的明清时期,出现众多重视事实与情理分析,并有引律为判之判词,但是古代判词论证的方式仍是夹叙夹议,长于言情理,拙于论法理,事实叙述和证据分析多一并进行,且均随法官意愿和制判风格变化,短则数十言,长则上百言,有的推己及人,循循善诱;有的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往往成为辞章华丽、对仗工整的道德修辞,缺乏逻辑推理的严谨理性和严格的制度性要求,可谓道德修辞胜于法律修辞。
然而,说理语言是判词的灵魂,是衡量判词质量的重要标准。西方国家从16世纪到18世纪确立了判词要说明理由的做法,判决必须说明理由现在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原则。而在近现代诉讼制度中,判词已成为各国诉讼法的重要内容,称判决理由为公平的精髓,法院不只是作判决,还必须解释其判决,解释的目的是说明判决的正确理由何在,英美法系的法官通过判词来创造法律,大陆法系的法官则通过判词来阐发法律的精神。近代中国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末修律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法律继受欧陆法律(主要是德国法),是中华法系亘古未有的巨变,传统国家制定法逐步遭到扬弃,而代之以源自与中国差异极大的欧陆社会文化下的法律”(20),采用了主文、事实、理由的判决模式,这种判决模式的优点在于,每一部分都相对独立,从不同层面共同为判决的形成提供理据,每一部分均可充分展开,如判决理由中既包括事实认定的理由即证据分析,也包括对性质、情节和处理方式的分析,便于法官展开针对事实部分的心证过程,同时一并辩驳控方或辩方在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不同看法。于是,判词语体在说理文字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清末民初的判决书,逐步摆脱了以往行政公文的色彩,认定事实、援引法律成为判决书的必备要件,更能够体现司法机关的权威性。”(21)逻辑论证增强,析理语言法律专业化凸显,这使得中国迈向现代司法制度的步伐较之清末更快,中国传统的情理型判决也进一步转向现代西方法规范型判决。
1907年《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首次明确判决须说明理由,1911年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规定判决如不附理由,“以违法论”,明确确立了判决理由的法律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判决应叙述理由,如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23条之规定,有罪判词之理由应分别情形记载下列事项:1.认定犯罪事实所凭之证据及其认定之理由;2.对于被告有利之证据不采纳者,其理由;3.科刑时就刑法第五十七条或第五十八条规定事项所审酌之情形;4.刑罚有加重、减轻或免除者,其理由;5.易以训诫或缓刑者,其理由;6.谕知保安处分者,其理由;7.适用之法律。
北洋政府时期对判词的制作和理由进一步重视,其颁行的《刑事诉讼条例》对判决书的制作、内容、送达等都作了详细要求。判词理由阐述已开始走出道德说教的传统模式(尽管有时还存在),开始引用法律、判例以及习惯来增强说理,尤其是法律在说理语言中开始占有突出地位。如果说《各省审判厅判牍》中所选判牍法律修辞尚不很明显,那么《大理院判决录》、《华洋诉讼判决录》则呈现出以法言法语为主导、逻辑性语句为手段的析理局面。
1.表示逻辑关系的词语
从实体内容看,近代判词多数重视锤炼事实,突出要点(以民商事判决书而言,围绕双方争议的焦点调查取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在理由部分对当事人双方的请求、答辩及所持理由逐一分析、论证,用事实的叙述、证据的分析和理由的论证来支撑和阐释此前载明的判决。从这些判词来看,当时的一些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官们亦具有从事实证据出发,充分论理,赢得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的司法理念。纵观近代判词语体,其理由论证中出现了诸多表示语义逻辑关系的词语,比如“先……次……再次……”,“如果……则……”之类以及表示思路展开层次性的“(一)”、“1.”、“(1)”、“其一”、“其二”,“甲”、“乙”、“丙”之类标题序号和观点性标题,有助于论理逻辑轨迹形成和析理思路的明晰。以《大理院判决录》(见后附例二)和《华洋诉讼判决录》(见后附例三)尤为典型。
大理院的判词虽然因制判者个人文字素养不同,于事实及理由部分的措辞风格有所变化,但语篇结构章法固定,行文理性严谨,结构模式、判决理由的类型及长度都与日本和当今的台湾地区有接近之处,正如黄源盛所言:“民初法院体制继受欧陆,类似法国的分区设院,法院受理案件限于一定地域,其所管辖不易扩充。以当时交通之阻滞,区划之辽阔,加以司法人才之缺乏,国家财政之困难,欲求裁判品质优良,谈何容易?不过,或许是时事因缘,据民国十一年间的调查所得,大理院当时共有推事四十三人,这些人员中,四十人曾留学于日本,二人曾留学于欧美,只有一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法律人士。……据此以观之,大理院的司法人员出身与能力迥异于当时的下级法院,可以说是人才荟萃。而外国法律对民初法制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判词的制作与文体深受外国影响,其中尤以日本为最。”(22)由此可见制判者个人的职业素养也是制约判词修辞选择的重要因素。
论及《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的判词,何勤华认为“当时的判决书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以及文章风格的。对控诉人的控诉理由,法院都是严格依据证据、法律、法理,层层分析,详细辩明,有话则长,无话则短”(23)。其中最长的判词《日商加藤确治与索松瑞等因违约涉讼一案判决书》竟长达28页,共22000多字,而最短的民事判决书《张星桥与道胜银行因债务纠葛一案判决书》全文仅510字。依案件内容需要确定判词篇幅,且不论篇幅长短,其结构模式均规范一致,即采用主文—事实—理由三段论模式,偶有省略事实项者,多为关涉程序问题;同时有固定的模式化用语。
2.引据类语句
从《大理院判决录》和《华洋诉讼判决录》来看,当时在处理民刑事纠纷时,适用的原则很丰富,法律渊源大体有法律、判例、习惯几种。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革时期,新的法律关系大量出现,但立法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虽然北洋政府规定仍适用清末现行法律,但在许多领域,法院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没有法律可依,从而不得不求助于习惯。主要有商事活动中通行的惯例、民间的借贷习惯,质、契约出现纠纷时的责任分担习惯,民事诉讼适用当事人主义——凡当事人已有协议须遵守协议的习惯,审案中法官劝争息讼的习惯等。《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直隶高等法院在受理案件时,除适用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各种诉讼法律、法规之外,还适用1914-1919年这一段时间内大理院、司法部发布的一些司法解释、命令和判例。
依法律、判例、习惯论案析理增强了判词的说理效果。同时,为了明确所依法律、惯例、习惯等,在判决书理由部分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查……”、“据……”、“就……”、“按……”、“依……”等之类句式,且出现频率很高,用特有的句式表明判案论理讲究依据,注意证据的来源和证明效力的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地区法院的判词中,理由同样是判词的主干,在判词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其内容一般都是结合事实和证据来阐明被告构成主文的罪名以及是否应减轻或加重的情节,然后根据该罪名及犯罪情节注明所应适用的法律条文。如王恩荣杀人案之理由:“……尤足见该被告于下手刺杀时,实有致死之决心,该被告应负杀人罪责毫无可疑,乃尤以并无杀死王德奎意思为其诿卸之论,殊无可采。依上论结,应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第二款判决如主文。”在认定事实方面,法院在起诉方举证和被告辩驳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写明庭审所查明的基本涉案事实。在判决理由方面,包括认定事实的理由和适用法律的理由,分别对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论证,主要是法官对证据的分析与阐述。对判决主文进行论证,是关于如何得出结论的逻辑阐述。不论是有罪的判决,还是无罪的判决,都写明了理由,通过理由将事实与主文有机联系在一起。
综上,中国判词发展到近代在语体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清末民初成为判词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是民国以后某些典型判词在结构及说理上甚至远远超过了当代判词。正如199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法律咨询委员会主任王怀安所言,当代的司法文书写作“不如旧中国的某些司法文书中,重视证据的剖析和论证”(24)。由上观之,近代典型判词文本在格式化与逻辑性上的突破,确有诸多值得今人借鉴之处。
附:
例一,《各省审判厅判牍》中杭州高等审判厅审理的“立继嫌隙案”判词:
立继嫌隙 杭州高等审判厅案(25)
诉讼事实:缘浦德年即三明,隶籍海宁,其堂叔崇云,即永生,所生二子,长德勤,次德全,均身故无子,应以伊子祥汉承继,方符同父周亲之例。乃德勤妻浦费氏不允,自于宣统二年冬,领养周叙财之次子云生为子,后来彼此涉讼。
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经海宁州以德年与浦费氏既有嫌隙,且有向浦费氏家滋闹阻殓情事,断令族中协议,为浦费氏另择贤爱,不许德年之子祥汉承继。德年不服,于五月初二日,上诉到厅。经调取卷宗,传集人证,遵章片请检察官莅庭,集讯三次。谕:据族长顺才等开呈德氏、祥氏两派名单;又据该族长等请求,并为德全之妻朱氏立继;又据浦费氏请求,以德华之子入继为嗣。经传德华到堂面讯,据供情愿等语。案经再三研究,已无遁饰。
援据法律之理由:查律载:无子立继,应继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则于昭穆相当之内,择贤、择爱,听从其便,立以为嗣等语。此案浦德年与浦费氏既情不相能,且屡次涉讼,揆之律意,自不能再许其子祥汉承继,致多纷扰。除德年外,与德勤昭穆相当者,有德富、德才、德华,皆各有二子,而浦费氏请求德华之子为嗣,德华亦极情愿,于择贤择爱之意,尤为符合。该族长等请求并为德全之妻浦朱氏立后,尚近情理,惟主张以德(华)[年]次子祥汉承继浦朱氏,近于调停,非正当办法,自应以德华次子祥林承继德勤兼祧德全为是,合行判决。
判决主文:判得浦德华之子祥林令其承祧德勤、德全两房为后,所有一切产业归祥林承受,德勤之妻浦费氏所领周姓之子作为义子,将来亦许酌给财产,但不得即以为后,德年不得希图财产,任意混争。族中如有再行耸使涉讼情事,由浦朱氏另行起诉,按律惩办,上诉费用由败诉之浦德年负担。俟判决确定后执行。此判。
例二,大理院所判“李鸿山等掏摸财物分别处罚、缘赦除免上诉案”判词:
大理院刑事判决(26)
元年上字第二十三号
判决
上告人:李鸿山(山东泰安县人,年二十七岁,无职业,住奉天小南关)。
吕仲海(山东福山县人,年二十九岁,无职业,住奉天小南关)。
选定辩护人:曹汝霖。
上告人李鸿山等,对于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奉天高等审判厅,就被告人李鸿山等掏摸财物分别处罚、缘赦除免一案、所为第二审之判决,声明上告,经本院审理特为判决如左:
主文
原判撤销,并撤销第一审对于李鸿山、吕仲海、诸永德、王成志之判决全部。
李鸿山、吕仲海窃盗之所为,褚永德收受赃物之所为,王成志诈欺取财之所为,均予免诉。
事实
李鸿山、吕仲海纠约行窃,于前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奉天大北门内盛京书局门首,由吕仲海向张星浦衣兜内掏得白布包一个,计大钱票五张、小钱票二张,价共二百五十元,遂交李鸿山。因窃取时为褚永德所见,许允分赃。随至东菜行王成志钱摊,李持钱票考讯价额,兑投现钱。王成志知其来历不明,百元之钱票伪称二十五元,以八十五元四角作为中贴换得大钱票二张、小钱票二张。李鸿山等随将现洋及剩余钱票作大小股瓜分。嗣经事主报,由警局获案。
理由
查本案诉讼记录,第一审审判衙门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用现行律将李鸿山、吕仲海、褚永德、王成志四名分别科罪,并援大赦令准予除免。乃李鸿山一名竟自认为有罪,而以科刑太重为词,声明控告,与诉讼法例被告人仅得为自己利益上诉之原则,显相抵触,本系无可准许。而奉天高等审判厅不予驳回,转对于已经及未经控告之被告各人,更自为本案之判决,其违法一也;审理此案之际,又未传集被告公开审讯,其违法二也;原判并于登载“暂行新刑律”大总统赦令之政府公报到达后,犹引现行律认定犯罪事实,并宣告罪刑,其违法三也;既援赦令除免,复据督令宣告缓释,是认督令有取消赦令之效力,其违法四也。乃李鸿山复行上告,然又不主张此等审判之违法为理由,而仍以科刑太重为词,亦系无可准许。惟选定辩护人曹汝霖列叙上开四种违法情形,作为追加上告谕旨,自可认为正当。至吕仲海并未控告,是第一审判决早经确定,于理不能有上告权,惟其上告迫于第二审违法之判决,若不许声明不服,未免失其平衡,故认其有防御权,与李鸿山之合法上告一并受理。而对其论旨与追加论旨之说明,亦与李鸿山同。
本庭审理此案,认为与本庭从前判例有歧异之见解,持依据《法院编制法》第三十七条、第八十条之规定,对于本案评议以决定之。按:不告不理,为现今诉讼法例之通则,然使过于拘泥毫无变通,甚非国利民便之道。现在诉讼法规未备,本院审判案件自不能不折中至当,自定条理。凡共同被告人中,有一人经上告审,认为原审判衙门对于该上告人之判决,限于适用法律错误或公诉不应受理之两条件,不能不撤销时,则凡未上告之共同被告人,亦受利益之影响,对于各该被告人之判决部分当然可以一并撤销。至撤销原判、维持第一审判决时,对于第一审判决之确定部分亦同。本案原判衙门对于王成志、褚永德二人因李鸿山一人之控告而重予审判。于登载《暂行新刑津》大总统赦令之政府公报到达后,犹引用旧律,认定犯罪事实,并至宣告罪刑,而后援赦令除免,洵不免引律错误。本院对于王成志等二人,自可根据此理更为判决。据以上理由本院认为原判应将全部撤销,自应维持第一审判决之效力。惟第一审判决又于登载《暂行新刑津》大总统赦令之政府公报到达后,仍用旧律认定被告人等之犯罪事实、并误予宣告罪刑,亦不免引律错误,应并将全部撤销,由本院自为判决。查新刑律与大总统放令之效力,既系同日发生,自应依据撤销《暂行新刑律》,先决定有无犯罪事实。李鸿山、吕仲海之所为,适与该律第三百六十七条相当,褚永德之所为适与该律第三百九十七条相当,王成志之所为适与该律第三百八十二条相当。惟事犯均在三月初十日以前,应仍查明大赦令及关于新刑律赦令条款;均予除免,宣告免诉,特为判决如右。
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大理院刑庭审判长推事 姚震
推事 林行规
推事 潘昌煦
推事 张孝移
大理院书记官 汪乐宝
例三,《华洋诉讼判决录》中“张星桥与道胜银行债务纠葛案”判决书(27):
判 决
控诉人张星桥,年三十八岁,天津人,业商。
周赵氏,未到案。
被控诉人 道胜银行
代理人 郭定森律师
上述控诉人为债务涉讼一案,不服天津地方审判厅本年三月三十日第一审之判决,声明控诉。本厅审理,判决如下。
主 文
本案控诉驳回。
诉讼费用归控诉人负担。
本案为缺席判决之周赵氏得于公示送达七日期满后二十日内,依式向本厅声明窒碍。
事 实
缘张星桥所开之瑞生银号倒闭后,结欠道胜银行川换本利银六千二百二十四两三钱。张星桥借得刘姓及周赵氏家等地契四张交该行作押,日久未偿。道胜银行诉经天津地方审判厅,判令张星桥照数清偿。如张星桥不为清偿或偿不足额时,即将周文禄、周永发(即周赵氏翁父)、刘玉书房地契变价作抵。张星桥声明控诉,周赵氏对于变卖地契部分亦声明控诉到厅。
理 由
张星桥对于原判债额数日并无异议,惟以请求道胜银行将利息让免为控诉理由。查债权人肯否让免利息,乃系两造协议问题,不得请求法庭减免。本案控诉认为无理由,应予驳回。并照章令理曲之张星桥负担讼费。其周赵氏因水灾屡传不到,例得于公示送达七日期满后二十日内依式来厅声明窒碍,藉维缺席当事人之利益。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一庭
审判长推事 胡凤起
推事 李兆泰
推事 张德滋
书记官 郭振铨
注释:
①直隶高等审判厅书记室编辑,何勤华点校:《华洋诉讼判决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11~12页。
②汪庆祺编,李启成点校:《各省审判厅判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注释(1)。
③俞江:《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0页。
④张德美:《从公堂走向法庭——清末民初诉讼制度改革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⑤黄源盛:《历史视野下的“六法全书”》,载燕山大讲堂,http://view.news.qq.com/ysdjt.htm.
⑥此书由汪庆祺搜集清末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的各种判牍,择其精华编成。从编者所撰的“凡例”可知,此书编纂时间为1911年冬到1912年春,后于1912年印行出版。李启成点校:《各省审判厅判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⑦许文濬:《塔景亭案牍》十卷,民国间刊本。该书前有许文濬的“自序”一,后有俞龙的“跋”一。正文共分十卷。其中,卷一为“呈文”,卷二为“通告”,卷三为“指令”,卷四至卷十均为“庭判”。是难得一见的纵跨清末和民初两个时代的县知事案牍资料。
⑧该书由大理院书记厅编辑,华盛印书局民国二年(1912)六月二十日初刊。
⑨该书由孙鑫源编,上海文明书局1915年版。收录中央平政院、大理院及京外各级法庭的判牍525篇,可见民国时判词制作之大概。
⑩《民初司法判决书汇集》,共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发行。
(11)该书由直隶高等审判厅书记室编辑,何勤华点校:《华洋诉讼判决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12)该书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2年出版,1934年三版。全书分为民事和刑事两部分。民事包括:民事第一审、民事第二审、民事第三审、民事抗告和民事再审等内容。刑事包括:刑事第一审、刑事第二审、刑事第三审、刑事抗告和刑事再审、刑事简易程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其他、刑事覆判和刑事特别法等内容。书后附有民事裁判书用语注意事项和强制执行公文程序等内容。作者认为,虽然民刑诉讼因案情不同,其裁判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这是针对实体法而言的。如果从程序法看,民刑案裁判的程式及引用法律之条文,或完全相同,或大同小异,自有其不变的内容。基于此,本书将民刑事两大裁判资料合并一处。
(13)该书是明末李清(字映碧,1602~1683)在宁波府推官任内审理各类民刑案件的结案判词专集,分为婚姻、承袭、产业、诈伪、淫奸、贼情、钱粮、失误、冤犯十类,分别成10卷210篇。
(14)[美]约翰.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程朝阳、毛风凡、秦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15)汪庆祺编,李启成点校:《各省审判厅判牍》,第297-298页。
(16)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司法论证理论导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34页。
(17)黄源盛:《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1912~1928)》,(台湾)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2000年4月初稿,第85~86页。
(18)黄源盛:《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1912~1928)》,第86页。
(19)此为1975年12月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一件西周晚期青铜器上所刻的铭文,学界一般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判词。铭文共157个字,记录了三千多年前西周恭王时期一个叫牧牛的人起诉其上司之后,法官伯扬父处理该纠纷时所作的判决。
(20)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21)张德美:《从公堂走向法庭——清末民初诉讼制度改革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22)黄源盛:《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1912~1928)》,(台湾)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第115~116页。
(23)何勤华:《〈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
(24)宁致远:《办好法律文书推动写作研究》一文引语,《法律文书与行政文书》1995年第2期。
(25)汪庆祺编,李启成点校:《各省审判厅判牍》,第132页。
(26)选自大理院书记厅编辑:《大理院判决录》民国二年(1912)二月份,华盛印书局民国二年(1912)六月二十日初刊。
(27)直隶高等审判厅书记室编辑,何勤华点校:《华洋诉讼判决录》,第225~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