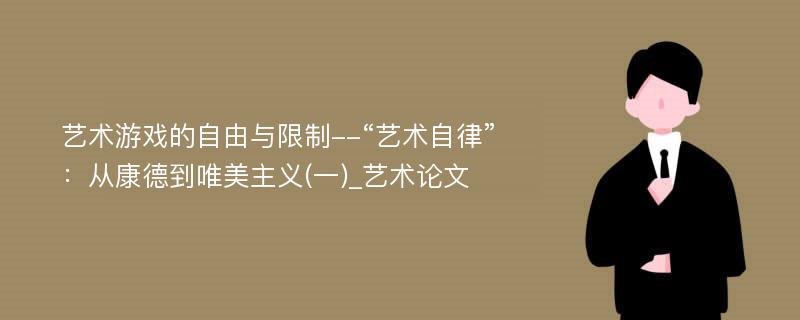
艺术游戏的自由与限度——“艺术自律”:从康德到唯美主义(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艺术论文,限度论文,唯美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6-0127-08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看来,唯美主义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它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义断然隔绝了艺术与现实、道德和人性的天然联系;奥斯卡·王尔德甚至声称生活模仿艺术,艺术除了为生活提供“美的范例”外没有任何义务。这表明,唯美主义正在以不光彩的角色参与去人性化艺术的形成。但为之辩护的奥尔特加-加塞特则认为,艺术的去人性化与唯美主义的关系不大,它是艺术自律观念与破坏性的反传统观念相互诱导的结果[1]46;唯美主义鼓励艺术自律,还不足以创立艺术的反人文原则,真正地去人性化艺术出现在“注定要反叛”的先锋派之后。加塞特提及先锋派,显然是在转移人们的视线。诸多证据表明,唯美主义不仅强调艺术自律,而且具有鲜明的反传统观念——取缔文艺复兴以来文学关注现实与人性的传统,任意僭越人文边界,就连唯美主义阵营内部的沃尔特·佩特都忧心忡忡。更为关键的是,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观念与康德美学确立的艺术自律概念一脉相承[2]32,甚至能获得席勒与黑格尔美学的支撑。这是否意味着康德乃至于整个德国古典美学都不能摆脱与“去人性艺术”的干系?艺术自律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本身是否包含着天然的反传统因子?“去人性化艺术”是否是艺术自律观念的必然结果?这些问题将引领我们重新回到德国古典美学的语境中,通过细读的方式重新认识艺术自律在不同美学话语系统中的内涵,从而确认它与唯美主义的真实关系。此外,我们还需要在辨识美的本质与艺术自由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讨论艺术自律可能的问题。 一、艺术自律概念的反思性确立 诚如阿多诺所言:艺术的自治权是“通过艰苦斗争从社会中夺取并社会性地确立的”[3]238。这个论断透露的显著信息是,艺术自律观念的确立乃是一次尖锐的历史文化事件。它不仅意味着艺术道路上的诸多绳索已被斩断,而且表征着艺术内部权力次序的更迭——原本被贬斥的绘画、文学与雕塑等艺术,获得了自足发展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艺术家的地位获得提升,局部社会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种鲜明的历史场景中,夏尔·巴托提出“美的艺术”概念便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由此,1750年成了后世美学家津津乐道的年份——不仅因为鲍姆嘉通开创了美学学科,而且因为巴托牧师“让艺术获得了特权”[4],并“为艺术世界内部结构的分析创造了条件”[5]54-55。这种状况也证明了另一事实:在历史提供适当时机之前,艺术自主性的获得过程充满了艰辛。 决定艺术自律概念确立的另一个因素,是启蒙运动的历史语境。启蒙是关乎人之主体性的文化重构事件,有关艺术自主性的探讨都与之密切相关,诸如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夏夫兹博里、库柏、阿什利等人的艺术自律阐述,其实都是启蒙的小片段叙事。康德对艺术自由与自律的关注缘于同样的原因,但与同时代人点到为止的风格不同,他对艺术自律概念的论证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将之视为自身美学体系的重要构成和启蒙话语系统不可或缺的支柱。这也是学界将艺术自律概念的确立归功于康德的主要原因。不过吊诡的是,康德从未强调过纯粹的艺术自律;相反,由于启蒙语境和启蒙目的的制约,他在确立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充满反思和犹疑,从而导致艺术自律成为一种有着苛刻条件限制的存在。 康德界定艺术的首要标准是“自由”。如果某种产品不是在自由状态下生产的,即便贴上了艺术的标签也是徒有虚名。真正的艺术只能“以愉快的情感作为直接的目的”,“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通过自由生产来“表现事物的美”,从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6]182-189。自由而愉快的情感目的和游戏,自由呈现美的功能,诸如此类的自由表征,让艺术与非艺术变得泾渭分明,艺术自律的概念也呼之欲出。但康德对艺术自律的思考并非只停留在自由层面,他还着重考察了艺术的“自由度”问题。快适艺术便因自由度较低而失去了自律性。它提供的愉悦只是伴随“单纯感觉的表象”,“以享受为目的”而不承担自我表现的后果[6]184;这种表面自由的愉悦有着令人不安的事实:它仅是“在感觉中使感官感到喜欢的东西”,受控于“利害”与“刺激”[6]91。很难说,这种艺术是以表现美为己任的。因此,尽管快适艺术直接以情感的愉悦为目的,有着自由游戏的核心本质,但它在服务于“享乐”“利害”和“刺激”等方面否定了自身,包括自律性,甚至艺术性。 康德以自由为标准界定艺术,并排斥快适的艺术,并非是出于美学逻辑上的谨慎,而是意在指出:何种性质而非何种类型的艺术才有资格拥有自治权。一首出于消遣目的的诗或音乐,一尊哗众取宠的雕像,一幅刺激感官的春宫画,一支宣泄情绪的舞蹈,尽管都属于巴托提出的美的艺术类型,但它们都因服务于“享受目的”或“感觉刺激”而失去了自律的可能。快适艺术的“劣根性”也使之容易受到资本操控。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18世纪的艺术已经“体制化了,成为一个与教会和宫廷生活截然有别的专门行动领域”[7]。但这个领域并非是艺术和艺术家完全自主建构的,而是在资本和货币系统的邀约下形成的。快适艺术以资本市场的趣味为导向,以商品身份在娱乐市场寻求消费对象,因而表面上自由生产和流通,实则处于被操控的状态。因此说,快适艺术无论是在自身掌控方面还是在给人的愉悦贡献方面,都是他律性的。 相比之下,美的艺术却要倔强得多。这缘于美的艺术含有不屈的内核,它能突破层层阻力去彰显艺术的自主权。这个内核即“艺术中必须是自由的且唯一能够赋予作品以生命的精神”[6]183。所谓精神,实际上是艺术家的审美品性在其作品中的涌动或抛头露面,它“在审美的意义上是指(天才)心灵中激发生气的原则……是使心灵诸力合目的地进入焕发状态、进入游戏的东西,这游戏是自持的,甚至为了自持目的而强化着心灵诸力”[6]192。显然,精神在作品中的呈现并非是为了彰显艺术家的个性和情趣,而是为了赋予艺术以生命,保障艺术游戏的自由与自律。当然,为了这一目的,精神需要完成以下几件事。 其一,精神需要突破艺术中的强制成分,使之为我所用。艺术中的强制成分主要是指艺术创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诗艺中的韵律知识,绘画中的光学,音乐中的转调技能等,它们在艺术中所起的作用是机械的,也是艺术家不能回避的强制。精神需要与它们合作,否则自身“根本不会赋形,甚至会完全枯萎”[6]183。但这种合作实际上是转化和突破的过程,精神的审美品性需要调动想象力和理解力,使得艺术的强制元素合目的地为审美表象的呈现出力。这个过程中的理解力几乎完全服从于想象力的需要,以满足精神赋形的需要。 其二,精神需要突破艺术美的依附性。在康德看来,只有纯形式的或自然的美是自由的,它们具有非感受性、非认识性和非概念性,不是对善的愉悦,而只是“想象力在自由中为自身维持着愉悦的心意”[6]153,因而总是带给人无利害的自由愉悦[6]95。艺术美则不同,它因艺术总是“从属于一个特殊目的概念”而需要以对象的概念来完善[6]114,因而是一种有条件的依附美。这决定了艺术美感总是“伴随着作为认识的那些表象”[6]184,并“直接或间接地与各种道德观念结合”[6]203。艺术自律的最大威胁因素正在于此,一旦艺术家被观念所左右,理解力便能单枪匹马地毁灭艺术于无形。幸运的是,精神的存在规避了这种可能。精神能够使想象力处在亢奋状态,此刻它的表象能够引起万千思绪而又没有任何确定的概念或观念来理解它的全部,这种表象即审美理念,是与没有表象依托的理性理念相对的感性理念[6]192。精神调动审美理念将“概念作了无限制的审美扩展……并使智性理念焕发,从而能够在想象表象中领会和说明更多的东西”[6]193。在此,康德特别强调了精神的审美意图。如果不是处在审美的情境中,想象力“将受到理解力的强制和受到适合知性概念的限制”;精神只有在审美想象这种“转瞬即逝的游戏”中抓住结合着概念的表象,才能表达艺术家心中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作普遍传达。因此,此刻精神需要与审美判断力联手介入到想象力与理解力的调和中,以便使“在其自由中与理解力的合规律性适合”,这就是为什么说:“美的艺术需要想象力、知性、精神和鉴赏力。”[6]197也只有艺术家的这四种心灵能力通力合作,艺术的依附性才可能被克服,才能以自持的游戏姿态维持艺术的自律。 其三,精神需要实现艺术表现美的形式。由于艺术的概念依附性,它的美并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在于它模仿自然时能够达到的“骗人”程度,即“艺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是艺术而在我们看来它又像自然时,才能被称为美的”[6]185。这意味着艺术必须全力以赴地模仿自然,承担这一任务的依然是精神统辖着的想象力。在精神激发生气的原则下,想象力的创造性被完全激活,它能够从“自然提供给它的材料中仿佛创造出另一个自然”[6]192。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发现适宜于观念表达的审美形式。在康德看来,美的形式是一切美的艺术的根基,即“所有美的艺术,本质的东西都居于为观看和判断而存在的形式中,那里愉悦同时滋养和调整着精神达到理念”[6]203。例如造型艺术,它使人愉悦的是素描,素描中使人愉悦的“只是通过其形式而使人喜欢的东西”。康德据此断言:美的艺术“大部分受制于美的形式要求,即使在魅力被允许的地方,它们也只有通过美的形式才变得高贵起来”[6]110。康德如此重视形式,乃是因为形式的自然性、自由性和审美象征性。形式背后聚集的是与某些概念相关的想象力表象,而这些表象提供的东西远远大于概念阐释的东西。这样,形式提供的就是审美理念:“它向内心展示了亲缘表象组成的看不到边际的远景领域。”[6]193在审美理念的支撑下,艺术甚至能够“优美地描写自然中将会是丑的或讨厌的事物”,除了“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6]190。因此,当艺术以美的形式展示了自然事物的美与丑,精神自身也就实现了自由。 至此,康德完成了艺术缘何自律以及如何自律的阐述。这个过程的鲜明特征是,康德从始至终将艺术自律的可能与艺术家的精神捆绑在一起。拥有精神才能的艺术家被康德视为天才,这一独特称谓除了表达其审美创造的自然含义外,还有着美学之外的意味。精神在艺术中必须是自由的,这意味着艺术家也必须是自由的。自由是启蒙时代颇具魔力的关键词,它与理性一道构成了人之主体性的概括,并作为一种召唤回响在时代的旋律中。艺术家的自由表面上以艺术自由为目的,而实际上却是人之自主权的一种彰显,一种自由精神的传达。康德对美的艺术设立的检测标准也印证着这一点:以合乎自身目的性的艺术游戏并非是承载着自足的惬意任意游荡,相反,它自动地“促进着心灵诸力的陶冶,并将之作社会性的传达”[6]184-185。言外之意,美的艺术尽管是自律的,但不能逃避滋养社会心灵的义务。这也是美的人属性质决定的,“美只适用于人类”[6]95,人们对于美的热衷只是为了“自我加强和自我再生”[6]106。这种自我的加强和再生,实际上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提升。美的艺术无论多么自由自律,都需要面向人类提升生命的需求。这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真正的艺术不是要阻止生命,而是要激发生命、释放生命、美化生命;要将存在置入澄明之中,并把这种澄明作为提高生命本身来贯彻到底[8]。如果离开康德的艺术启蒙宏愿,那就很难理解他对艺术自律的人文规约。进一步地,如果因为唯美主义师承了康德的艺术自律观念而将康德与去人性化艺术扯上关系,那也是无稽之谈。 二、席勒:美的形式的限度 康德反思性地确立了艺术自律的概念,在其追随者中引发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天才、精神、形式等概念随之走红,充斥在互不通约的美学话语间。然而在现实中,艺术自由口号下的艺术实践似乎更在意“美的形式”,其中被席勒归类为“哀歌”的诗就是这种情况。诗曾被康德称为“完全充分的”的形式:能够表现不可言传的思想,审美地提升自身到达“众理念的高度”;能让心灵自由自主地舒展和加强,能超越感性透视自然图式;它以随意产生的幻影做游戏,却“能被理解力合目的地用于它的事务”[6]204。这些溢美之词表明,诗的形式彻底取得了康德的信任,它似乎永远是自由的。但席勒悲伤地发现,以自然和理想为感伤对象的哀歌并非如此。哀歌诗人只是利用诗的形式表达着厌恶的经验和绝望的现实,眺望着遥不可及的理想与无限,寻求着已然被破坏的天性。这类作品只是迎合感觉,不能占据我们的心灵,如果长久地沉溺于此,性格中的活跃力量必然被夺取。显然,哀歌利用了美的形式,却被感觉操控,既无益于心灵陶冶,也谈不上自由自律。席勒将这种状况称为“美的滥用和想象力的越界”,认为它们已经“损害了生活”,声称“精确检查美的形式运用”已经迫在眉睫。 根据席勒的考察,美的滥用是感伤时代最普遍的特征,不仅哀歌如此,牧歌也存在这种状况。牧歌的特点是“拥有美和鼓舞人心的结构”,诗人可以根据自然法则和田园风光的描写表现理想,能够“摈弃虚伪生活的一切污点”;但牧歌除了抚慰心情外没有丝毫精神价值,“它们只能给予有病态的心灵以治疗,而不能给予健康的心灵以食物”[9]316。如果根据席勒检测“美的滥用”标准:能否将人的感性力量和精神力量引向和谐,牧歌使用美的形式依然是一种滥用和越界。但席勒承认牧歌的治愈价值:它能够以积极的宁静介入到心灵诸力的平衡中,不像理想型哀歌那样“把人带回到世外桃源”,而是在充实中“伴随有无限力量的感觉”,将人“引导到极乐世界”[9]319-320。席勒的矛盾在此鲜明地表现出来:牧歌是美而自由的,对于平衡心灵的力量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它在精神提升方面的匮乏致使其进入了“美的滥用”范围。换句话说,牧歌并未因自身的自由自律而获得肯定。这与其说是对康德艺术自律概念的反对,毋宁说是对他的重要补充:艺术能够做到“陶冶心灵诸力并做社会性传达”这一点还不够,它还需要提升人的精神。 在席勒看来,既然美的属性在于人的世界,那么自然美就不是一种高级的美。诸如人体和人的形象这类自然性的“构造的美”,其性质是“理性概念的感性表现”,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是美的。自然赋予人体的美,并不比其他自然产品更优越,而且处于不能自持的损耗中。因此,人们只能“通过自由和道德精神的建构”去维护或加强自然赋予的美。这样,真正的美必然包含三种要素:自由驾驭的美、自然提供的结构美、心灵提供的游戏美[10]181-183。人属的美也是一种不确定的运动美,“可能偶然地进入主体,如同它可能从主体身上消失一样”[10]169。这是因为真正的美需要将感性和道德感结合以“超越任何自然条件”,剔除纯粹自然性的本能和欲望因素。否则,美“既不能够,也不值得当作人性的表现”;古希腊人的美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性由精神(道德感)完美的指引着,人性与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0]172-173。言外之意,美的本源不在自然,而是在于人性的道德结构中。道德感不仅决定了人属的美的生成,而且决定了它是否驻留在主体中。据此我们可以推断,精神的核心内涵即道德感,它的外延则是推动心灵游戏美的自由意志。 对于美的独特理解也就决定了席勒对于艺术自律的态度:不是以美的生成和精神提升为己任的任何艺术,都没有资格获得自治权,即使它是精致而唯美的哀歌,抑或优美而自由的牧歌。换句话说,审美趣味不是艺术自律的理由,因为它诉诸感觉而不是精神的提升。如果人的心灵被感觉所掌控,艺术面临的窘境就不仅是美之形式的滥用,它还将导致庸俗和鄙陋艺术的泛滥。所谓庸俗,就是“将全部兴趣集中在感觉上而不是诉诸精神的事物”上;鄙陋则是“卑贱和丑陋的结合”,是悬置道德律令后的本能满足。它们的危害性远远超出美的滥用,不仅会将艺术受众抛给感觉的幻影,而且激励欲望、本能等非美因素攻击人性中的善。席勒将庸俗和鄙陋艺术的出现归咎于艺术家而不是现实题材——它们鲜明地表征着艺术家道德精神的匮乏,抑或说其精神和尊严的双重丧失,因为只有“通过道德力量统治本能,精神才是自由的,而精神自由在现象中的表现就叫作尊严”[10]217。在艺术家的精神丧失了自主性的情况下,他的作品又何谈是自由自律的?因此,席勒不无愤怒地指出:“放任精致的审美文化是极端危险的,这将直接使我们把自己完全抛给美感,直接让我们把审美趣味提升到意志的立法者地位。”[10]253 说到底,没有艺术家的道德意志和美的人格,艺术的自由就成了一种任意的僭越;艺术作品没有精神的规约,它的自律目的就没有任何价值。席勒正是基于这一点,为我们推荐了一种自由且美的形式:嬉戏的讽刺诗。这种形式来自于诗人的优美性格,“只能由一颗优美的心来完成”;或者说这种性格内在地“包涵着一切的伟大形式”,嬉戏的讽刺只是从优美性格中自由流溢而出的形式;它在每个进程点上都潜藏着无限的力量,“永远是自由的”;凭借这一点,诗人能够以个人力量来维持题材的审美性质,能够始终如一、舒适自在地畅游在崇高的艺术境界中[9]292-293。所以,嬉戏的讽刺诗不必取悦于人,便自动向人的心灵呈现优美的精神,表现人的尊严。在这种高度自由的形式之外,还有一种叫作凄厉的讽刺诗的形式。这种形式出自“高尚的灵魂”,但诗人总是“被题材支持”着,“必须纵身一跳才能进入”崇高境界。这决定了崇高性格必须“通过紧张的努力”和“力量的衔接”才能达到伟大和突破限制,因而凄厉的讽刺诗形式只能维持断断续续的自由。尽管如此,它依然能够通过诗人的崇高性格实现自由,能够“通过审美的方式”恢复被激情破坏的心灵自由[9]293。这就是说,喜剧和悲剧的讽刺形式都是自律的,但取决于诗人心灵的优美或崇高。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席勒将道德精神视为艺术自律的唯一保障,与其说有着充分的依据,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席勒看来,能够表现人性圆整之美的素朴艺术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人们已经进入理性膨胀的感伤时代,感性不仅与理性分离,而且想象力、审美趣味乃至于整个艺术都受到理性的操控。艺术家的感受不再是素朴诗人那种自动结合着理性能力和善的游戏,艺术家的思想也不是素朴诗人那种充实着自然与人性的游戏。在感伤时代,艺术家的想象力被迫“需要和理性观念结合起来”,痛苦地摇摆于二者之间,素朴艺术的愉悦和静谧被感伤艺术的焦虑骚动所代替;如果诗人只是从既定艺术中寻求灵感,那么已经受控的艺术将使人的感性和谐处于停滞状态。在复归人性圆整和善的和谐的期冀中,艺术家除了“表现为道德的统一体”外,别无选择[11]102。 尽管席勒以充分的理由论证了艺术自律的道德前提,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对艺术自由给予了比康德还要严格的限制。这不禁让我们担心阿多诺的忧虑会重现:“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利用非自治性元素,即与社会纠缠不清的东西,是因为这些元素在作为社会内容的同时也总是属于艺术自身的。尽管如此,艺术通过艰苦斗争从社会中夺取并社会性地确立的自治权,仍然可能退回到非自治的状态;与累积不变的东西相比,每一种新事物都是脆弱的,随时可能回归原初的状态。”[3]283 三、黑格尔:解放“精神”的艺术 席勒关于艺术本质的诸多观点都受到了黑格尔的赞美,但相对于席勒来说,黑格尔对于艺术自律的态度更为自信。他在美学讲座开篇不久即指出: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作为有用的工具去实现艺术领域以外的自有独立意义的目的”,而是在于“它自身的目的性”,即“用感性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理,去表现……和解了的矛盾”[12]82。艺术的这种内在目的性,决定了它不是为任何文化目的服务的工具,也不是任由外在因素操控命运沉浮的玩偶,而是充分拥有自治权的一种存在。对此,朱光潜可谓一语中的:黑格尔的这一观念就是为艺术而艺术论[13]69。事实也表明,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论的确与黑格尔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后文关于佩特的讨论中会得到充分揭示。这里需要理解的是:缘何受到理念制约的艺术还是自律的?显现真理和表现矛盾的目的是否意味着艺术并未摆脱工具化的命运?艺术仅仅作为真理的面具存在吗?在黑格尔美学中,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 在黑格尔看来,艺术和理念是一组本质相关的概念。艺术美意义上的理念并非指哲学逻辑中的绝对,而是“符合理念本质而显现为具体形象的现实,这个理念即理想(Ideal)”[12]105。简单地说,“理想”就是艺术,是理念显现自身的活动和方式。这表明,艺术与理念具有同一性,它不是外在于理念的存在,而只是理念本身的形象化和现实化。从这个角度说,艺术即理念,只不过是一种具体的理念,因而谈不上受到理念的制约,自然也不是理念的工具和面具。不过,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即理念如何显现自身以及以何种方式显现自身,也不是取决于外在条件,如艺术家的技巧、天赋等,而是完全自主的,即艺术理念“已经包含了它采取什么方式显现自身的原则,它本身就是将自己显现为自由形象的过程”[12]106。这种被称为理想的理念是自律的,因而艺术也是自律的。 艺术自律不仅体现在目的和显示方式上,而且表现在它表现美和真的自主性上。在黑格尔的概念中,美就是理念本身,不过它是“一种确定形式的理念,即理想”[12]145。这与对艺术的描述如出一辙:美和艺术都是理念显现自身为自由形象的方式。这也决定了美与真的关系。当理念通过客观实在呈现于意识,并且其概念与它的外在现象直接统一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2]151。这意味着美的理念自动呈现真,艺术表现美的理念时必然显现真理。尽管如此,黑格尔依然澄清了一个事实:艺术只是美的理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否显现真和美取决于美的理念。象征型阶段的艺术就因理念没有美的理想而呈现出“失真”、“离奇而不完美”的形象外观[11]107;古典型艺术是美的理念扬弃自身缺陷后观照完美理想的阶段,艺术的形象和意义直接统一,因而既美且真[12]109。所以黑格尔说:“形式的缺陷总是缘自内容的缺陷。……艺术作品的表现愈完美,其内容就愈真实,思想就愈深刻。”[12]105当美的理念自身有缺陷时,即便被用作艺术创作的内容,也不可能有美的形式,更不会恰当地显现真理。当美的理念逐渐克服了矛盾,扬弃了自身的片面性,它自然就会显现出美和真。 美的理念不仅决定了艺术表现真与美,而且决定了其发展和终结。当美的理念依据自我确证的原则上升运动时,各种特殊的艺术类型出现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只是理念的“差异面”:其一,它们是美的理念自己分化出来的;其二,它们是美的理念或理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发展。因此,从象征型艺术建筑到古典型艺术雕刻,再到浪漫型艺术的诗歌与音乐,都是美的理念的自我分化、自我确证的过程。理念分化的动力是自身通过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来完成的,它表现为生命或精神的生动过程。从象征型艺术到浪漫型艺术的每一次飞跃,都是理念扬弃片面性的结果。即便古典型艺术已经将美的理想表现的几近完美,但理念依然发现了自己的缺陷——具体的感性形象无法表现普遍的、无限的自由本质。于是理念它开始寻求在心灵内完成自我表现的方式——诗歌与音乐,以削弱对感官形象的依赖。这样,浪漫型艺术承担了破坏理念与现实统一的任务,“在较高阶段上回到了象征型艺术所没有克服的理念与现实的差异和对立”[12]111。 黑格尔将艺术走向内心生活、在心灵中完成统一的状况称为“艺术超越了艺术本身”。这种超越同时也意味着艺术正在走向溃散和终结。这不仅是因为美的理念需要扬弃片面性,而且因为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理性不断膨胀。理性膨胀导致“直觉经验和感性变成了与意识无关的东西,理性的人……将自我抛给了隐匿的客观必然性。”[14]309对于失去感性观照的人来说,艺术显现的真理也就失去了意识的依托,这无异于逼迫美的理念逃离。由此黑格尔慨叹道:“希腊与中世纪晚期的黄金艺术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实证的艺术家因为感染了周围盛行的思考之风,养成了喜欢思考判断艺术的习惯……艺术对于现代人来说已成为过去,因为它已经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或者说已经转移到我们观念世界里去了。”[12]24-25尽管艺术的终结是理性膨胀的结果,但艺术的终结还是由理念自身决定的——它扬弃了艺术不能自由显现它的片面性。 综上来看,艺术自律的根本在于理念。它不仅决定了艺术的目的和表现美与真的程度,而且决定了艺术的源起、发展和终结。问题出现了:艺术既然是自律自为的,全然是外在于人的理念游戏,那么艺术家的作用何在?艺术对于人的价值是什么?理念游戏是否意味着艺术的去人性化?纵观整个黑格尔美学,我们会发现他对这些问题不以为然。 与康德类似,黑格尔对艺术家做了非世俗性处理。黑格尔承认,情感灌注能力能够让艺术家在材料处理中“体现他的自我,即作为主体的内在特性”;但这种情感能力只是意蕴获得外化的条件,艺术家只有通过创造性想象“在心中将绝对理念转化为现实形象”,即完全作为艺术目的的手段,将美的理念“转化为作品”,他才能“充分表现他自己”[12]366。所谓想象力的创造性,其实质是将视听记忆表象的关系发现出来,让“外在现实转化为内在的精神性存在”,并且让“精神性的东西在观念中取得外在事物的形式”[15]256。也就是说,艺术家就是理念显现为形象的手段,想象中必须消除任何世俗性因素:“必须凭借想象力将精神的主体性和肉体形状中的任何偶然因素过滤,不带主体的任何癖好、情感、私欲以及各种激动情绪和突发的机灵巧智。”[15]373由此可见,艺术家只能具有理念的自我而不能拥抱世俗。黑格尔的解释是:艺术家的能力并非是“凭借(世俗)自我之力发展出来的,而是天然地直接存在于他身上”[12]367。这意味着艺术家与艺术具有同一性,甚至一体化。 艺术家与艺术的一体化让艺术的人文价值变得可疑起来,因为艺术受众很可能被绝对理念裹挟到自身的运动中。不过黑格尔一直强调:艺术“也是为人而存在的”[15]255。例如,建筑的意义在于“它对人的关系”[15]260;绘画在浪漫型阶段需要涉及具体化的内心生活,而这种生活“需要贯穿到人作为个别的主体所能感兴趣的且能从中获得满足的一切事物里去”[16]61;促使绘画到达高峰的“正是精神灌注给生命的亲切情感和极致苦乐所构成的深刻意蕴”[16]21;雕刻形式“是精神的实际生活,即人的形象及其被精神灌注生气的客观有机体”[15]259。总之艺术必须“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艺术活动的产品”[15]266。黑格尔的逻辑是,人本身就是绝对精神自我确证的产物。人性、道德、情感等内容都是精神自我分化的“差异面”。以此而论,理念的艺术游戏不仅不存在“去人性化”,而且是提升人性和道德精神的必要途径:它“并非是单纯提供愉悦、效用的游戏,而是要将心灵从有限的内容和形式中解放出来,要让真理之花绽放在感性存在中”[16]573;它通过提供审美观照来让“对象保持自由和无限,没有加以占有的欲望,没有将之视为满足有限需要和意图而加以利用的工具”[12]155-156。人在艺术审美中悬置了意志和欲念,实现了解放和自由。 如此人文的艺术沉思,很难让人把黑格尔放在去人性化艺术观念的开端位置。但也需要指出:黑格尔依然继承了康德与席勒的形而上思路,自律的艺术中总是含有一枚令人禁忌的内核,它需要人的崇拜和臣服。此外,艺术观照中实现的自由毕竟是观念上的自由,对于实践的人来说,解放价值微乎其微。尤其是黑格尔以艺术自律的名义宣布了艺术的终结,这是否说明,黑格尔已然发现了艺术的人文价值正在溃散?那么,艺术的剩余物还有什么? 四、戈蒂耶与“去人性化艺术”的开端 在黑格尔去世的1831年,法国的泰奥菲尔·戈蒂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青年。他是浪漫主义的狂热分子,已经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诗集。他也是雨果的忠实粉丝和学生,《克伦威尔·序》(1827)和《欧那尼·序》(1830)中宣扬的艺术至上观念,一直在他心里激荡着回声。戈蒂耶还身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德国古典美学倡导的艺术自律观念正在他周围聚集。当然,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被视为这一观念的首要倡导者,只是出于对雨果的崇拜和对时代艺术的敏感才写下了《阿贝杜斯·序言》(1832):“赋诗……旨在求美”;“东西一旦变得有用,就不再是美的了”;“一旦进入实际生活,诗歌就成了散文,自由就变成了奴役”;“艺术……决不为任何目的服务”[17]16。此后,戈蒂耶又在《莫班小姐·序言》(1835)中重申了艺术的无功利、无目的性和旨在求美等主张,并重点阐述了艺术超越道德的观点。他认为,伟大作品从没有服务于道德的先例;相反,道德经常会成为讥讽和侮辱的对象[18]。艺术没有道德义务,这是艺术的无目的性律令所规定的。显然,戈蒂耶这些宣言成了德国艺术自律观念的法国回声。 艺术自律观念在法国有个响亮的名称:为艺术而艺术(L' art pour l'art)。有证据表明,这个口号式短语只是法国人对康德艺术观念的概括;它从德国传播至法国的中介则是斯达尔夫人、雅曼·贡斯当和维克多·库赞[19]。在戈蒂耶倡导这一观念的最初,法国人对为艺术而艺术并不熟知。因此,有批评家在1833年指出:“为艺术而艺术理论并非是公开而完整的法则,它只是借助一些令人迷惑的序言隐蔽地流传着。”[20]371在随后由尼扎尔主动挑起的为艺术而艺术论争中,戈蒂耶、雨果等人的名字经常盘旋于批评家唇齿间,成为臧否对象。但是吊诡的是,直到1847年,戈蒂耶才首次使用“为艺术而艺术”谈论艺术之美:“为艺术而艺术所代表的是那种除了美本身与其他事物毫无关系的作品。它并非像它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从外在的观念中解脱出来,拒绝提出任何理论信条,拒绝直接的实用性,为了美而形式。”[20]376应该说,戈蒂耶关于艺术自律的观点全部浓缩于此:“为了美而形式。” “为了美而形式”几乎是所有唯美主义者的口号,但却露出了“艺术去人性化”观念的最初端倪。在戈蒂耶那里,美的形式并非康德所言的,是一种适合于内容和思想表达的形式,也不是席勒所说的优美性格溢出的伟大形式,更非黑格尔意义上的美的理念自我决定的形式,而是去除了剔除了任何现实性因素,从时间中逃逸而出的永恒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是与现实绝交的形象,如《莫班小姐》中唯美浪荡子达尔波尔(D' Albert)的独白: 我生存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不理解我周围的社会。基督不是为我而生的……我叛逆的躯体拒不承认灵魂的主宰,我的肉体拒不压制情欲。……在我眼里,形式的完整就是美德。……使我产生快感的三件东西是——黄金、大理石、猩红;灿烂辉煌、扎实坚固、色彩鲜艳。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用它们建筑我的全部空中楼阁。……我喜欢用手指触摸我亲眼目睹的东西,而且喜欢把外形的轮廓捉摸到它们最难捉摸的隐微曲折之处……这就是我一贯的性格。我是用雕刻家的眼睛,而不是用情人的眼睛来观看一个女人的。我一生最感兴趣的是酒瓶的形式,而不是装在瓶里面的内容。 当然,作为诗人,戈蒂耶的形式更多地还是指向技巧,但这种技巧需要过滤掉情感。戈蒂耶借达尔波尔之口宣称:“诗中的感情……那是无关宏旨的东西。绚丽辉煌的词句,音韵和节奏——这些才是诗。”[21]341形式律令规定了艺术家的任务就是雕刻形式。戈蒂耶认为“诗人”一词的本意即为制作者之意,制作不好的东西都无法存在[23]34。诗这种文体在他看来就如“闪光而坚硬的材料”[23]36,如果不对它精心琢磨,美的作品就无从谈起。因此,戈蒂耶断言:“对形式反复雕琢才能产生出佳作。”[17]203戈蒂耶甚至从这种形式雕琢论中引出一种颓废风格论: 颓废风格……是旧有文明衰败之际,裹挟它的邪恶荣耀使其艺术达到成熟创作的极限点——这种风格精细复杂且充满隐微曲折,需要通过研究探索才能不断推进言语的边界。它借助于所有词汇技术,从所有调色板中着色,并在所有键盘上获取音符,奋力呈现思想中不可表现、形式轮廓中模糊而难以把握的东西,凝神谛听以传译出神经管能症的幽微密语,腐朽激情的临终表白,以及正在走向疯狂强迫症的幻觉。颓废风格是词语世界的最后努力,它要求表现任何事物,并达到绝境的极限[24]19。 至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以戈蒂耶为代表的法国唯美主义,最终撕毁了艺术的人文承诺,以艺术自律之名走上了形式主义的不归路。这与其说是对德国古典艺术观念的继承,毋宁说是一次令人不安的策反。艺术的去人性化观念正是随着这种形式主义逐渐蔓延的,它跨越英吉利海峡抵达大不列颠,那里有一大批文人墨客翘首企盼它的到来。斯温伯恩、道生、佩特、王尔德等将会相继登场,一场轰轰烈烈的唯美主义运动将在英国展开。而在法国本土,魏尔伦、兰波等象征派诗人正结合着唯美主义汇集成一股颓废主义思潮;具有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双料身份的于斯曼在1884年推出小说《逆流》,以惊世骇俗而又颓唐浪荡的德艾辛特(De Esseintes)形象将“去人性化艺术”观念推向顶峰。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是艺术自律观念的必然结果还是艺术发展史上的一次插曲?艺术的主要力量真的集中在它的绝对自主性上吗?(待续)标签:艺术论文; 康德论文; 唯美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康德资本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美学论文; 人性论文; 席勒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