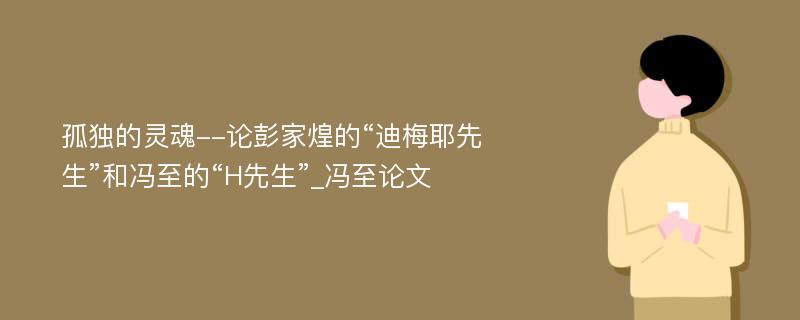
孤寞的魂灵——论彭家煌的《Dismeryer先生》和冯至的《H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魂灵论文,论彭家煌论文,Dismeryer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07X(2006)01-0026-04
彭家煌和冯至是两位有着不同艺术理想和创作风格的作家。彭家煌素以铺叙深切丰厚的血肉人生见长,长期卖文为生的经验非但没有减弱出自其艺术追求本身的感染力,反而无形中增强了这种力量。初见反响的短篇小说《Dismeryer先生》交错于政治、哲学、文化等层面,体现了“真正有教养的现代人的意识”[1]。无独有偶,同在1926年发表的冯至的《H先生》也把现代人作为诠释的向度,时以抒情新诗见称的冯至同样没有放弃时代赋予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品质在《H先生》上的实践,使得看上去相似的两部作品更多了些精神上的联系。尤为重要的是,两篇小说突破了以往写下层妇女的人道主义惯用笔法,大胆直写异域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为新文学题材的开拓和思想的深化提供了可贵的探索,从而也为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尝试增加了厚重的砝码。
两篇小说都以德国人为主人公,都存在“想象”和“现实”两个圈子(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又都于想象与现实之间逆反的张力中求得性格的建塑和悲剧的升华。《Dismeryer先生》写了一个失业的德国年轻人酸楚的遭遇,Dismeryer先生变卖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财产,却终于难以生存下去,自尊和自强的性格也使他杳然不知所终。同样有着争强好胜性格的H先生是冯至作品中比较独特的一个典型,不同于伍子胥等传统中国文化形象,H先生提供了一个“西方”想象,他拼命地教书,拼命地挣钱,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悲惨地死去。在两篇小说里,对于他者的想象是主要的结构形式。《Dismeryer先生》里P的妻是“想象”功能的主要承担者,由“对普通一般外国人的观察所得来的一种异样的可怕”,到“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先验判断,近代历史形成的不正常的弱势国民心理已严重扭曲了一般人所有的心态和别择,以致P的妻有这样汪洋恣肆的愤辞:
难道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受够洋鬼子的糟蹋吗?他们是野兽,南京路、汉口、广州,哪处他们不横暴地作践我们!我们的血是猪血,我们的命是狗命,哪一次奈何他们过!我们为什么还要饲养这种残忍的野兽啊?我真是越讲越恨呀!
情感的民族隔阂妨碍了人心的交流,阻断了常人之为人的所有路径,一切都是那么阴惨凄惶,恰如战争的阴霾覆盖下的世界。《H先生》“想象”的设势更为自觉,小说中除着力提及德国人O.博士的“很骄傲”、“日耳曼民族的性格”外,关于H先生的死还很有一番剖白:
只要说起德国人来,在我们的脑子里便现出一个又高又大、康健的身体,仿佛与“死”永不发生姻缘;就是“死”来拜访他们,也要经过了三揖三让而后敢逼近他们身旁。这样骤然的死,似乎只许在中国的乡间……一个医学最发达的国度里的又高又大的人而能在一两日内死去,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轻于相信的。
这里,民族想象在所谓“政治神话”的诱发下遮蔽了哪怕被信为自然规律的生死,它至少致使民族的自馁感和奴性心理的滋生。有意味的是,两篇作品中“想象”的发生契机还略有不同,《Dismeryer先生》倾向于政治冲突下民众普遍的仇恨情绪,而《H先生》与科学、种族的瓜葛要多些。不管怎样,人类异化、人性缺失是它们竭力认识到的人格症候,从而在解构“政治神话”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建筑着现代的“人文神话”。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倡扬人的文学的主张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方思潮的冲击固然是打破羁绊、激发潜能的源头,积弱积贫的苦难社会现实却总会首先变成人性的炼狱,最早的一批作家看取生活的视角或有不同,情感冷热甚至迥殊,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迷惘于老大帝国的运命及其子民的挣扎与悲哀,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所谓反封建小说是对历史的纵的证辩,而《沉沦》这类反帝的小说则是现实的横的逼视,其意义可以千差万别,根本上毋庸置疑的一点当是国人健全人格的跂望和焦虑。《Dismeryer先生》和《H先生》的出现不仅仅只是题材变化或角度调整的问题,毋宁说是认识生活和思想视野的转变,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参照,人性之路并不是一个沉滞阴晦的畏途,狂人的令人颤栗的遭际和《沉沦》里“他”的神经质的忧郁所带来的沉重即使不为Dismeryer先生和H先生经历的惨伤所减轻,至少也在半殖民地中国苦难读者的心灵上求得一种慰藉。实在地说,《Dismeryer先生》和《H先生》所代表的倾向还够不上新文学思潮发展上独立阶段的标识,但它们确实充分地指示了人的文学的可能性,拓展了文学发展的空间。
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还要得益于两部小说的“现实”圈子,与简洁的背景似的“想象”圈子相反,“现实”的圈子有如荡在水中央的涟漪,渐行渐远,悠然归于寂灭。Dismeryer先生是个二十多岁来华已经两年的德国人,战争使他失掉了摩托车制造厂的工作,生活的困窘又逐渐勒迫他到了绝境,以至四个铜子的价格就变卖了皮带,八成新的皮鞋也只要四毛钱,随后不得已只好寄食于P夫妇家,但同样生活于水平线下的P夫妇亦无可奈何,夫妇俩一次提早的闩门晚餐因妻子捻灭了油灯而最终破碎了Dismeryer先生的幻梦,“这穷无依归的Dismeryer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小说虽以疑问收束,还是未能把Dismeryer先生也许倒毙的运命从人们脑中赶开,正像大多数中国赴法勤工俭学者一样,“抱着他们伟大的希望在异域的坟墓里长眠”。更少传奇色彩的H先生悲剧色彩似更浓。五十多岁的H先生在中国已呆了十二三年了,他不辞辛苦,情愿一天担任七八点钟课而不觉累,甚至还想做家庭教师,不幸也是战争使他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经济生活一跌不起;加之北京教育界的欠薪,使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地坏了下去,最终染上白喉,同死神握了手。相比之下,作为“想象”的圈子被撞得粉碎,而“现实”的圈子赢得了一切。H先生和Dismeryer先生共同的向死的悲惨结局并不是偶然的——正如他们都是德国人一样并不是偶然的——强国公民在弱国并没有享受相应的优越待遇,反而愈受苛酷,怅惘之下不能不使人思索人类的普遍性境遇。小说中“想象”的圈子和“现实”的圈子错综而成的“愉快的悲哀”的潜叙事无形中加大了思索的力度。其中“愉快”是“想象”视角的情绪伴生物,基于民族怨恨的复仇心理,带有丑陋的性分,因而或多或少地置于被排摈的状态里,《Dismeryer先生》里P的妻所说的“起码货”,《H先生》中听差因赏钱而发生的不信任感都是。而“悲哀”是“现实”场景的内化,是作为载体的主导情绪,如《Dismeryer先生》的“异端落魄者的悲哀”,《H先生》末尾虽云“并不悲哀”,但接下来的故乡老父母“只为望着”的丰富而无奈的遐思,反把悲哀推得更远。总起来说,“愉快”和“悲哀”两者互为辅车,“愉快”为表,“悲哀”作里,以悲哀主导愉快。作为看取世界的独特视角,“愉快的悲哀”的磁场有效地吸附了人性观照的散佚和失落。
对人性的揄扬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心,推究起来这种揄扬也只是在现代后期的空气下才得以普泛化,人间的意义和资源也才得以重新整合,值得注意的是,一面是人的无限进取性的展露,一面却是人的孤独感的逐渐强化,而且文明程度愈高,主体间情感愈强,人的孤独的心态也愈膨胀,这就是浮士德意义上的发展的悲剧。中国文学是在辛亥革命后涌起的鸳蝴小说里明显赋以这种色调的,尤其是苏曼殊的小说,哀哀情诉之下尽有着孤惨的影子,虽然思想道德仍是旧的。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作家更以奋具此种文艺伦理而大可以被视为解构性、潮流性的审美观念,《Dismeryer先生》和《H先生》就是这特别的作品,说它特别,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所提供的象征寓意,这在《Dismeryer先生》中表现得更为显明。Dismeryer先生虽会说本地话,但他的德国人的身份已足够使他不能融入于群体的生存了,即使不强加任何政治意识。这里有武士的勒索欺诈,有P的妻的不怀好意的臆测,更有娘姨的斥辱和可笑的防范,只这些倒也罢了,可怕的还是失业使他断绝了生活来源,无以为命,这从他壁上挂着的袒胸赤背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图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被理解、苦闷自励的委屈可见一斑。周围冷冰冰的力量在男妇买走皮带和皮鞋不无得意的反语中达到极顶。比照经常在街头作漫漫长夜的巡行者,“我”的同情和善良好象无边无际的海洋中的一叶方舟,给身陷绝境的Dismeryer先生带来了无穷的希冀和热望,而结果却是饮鸩止渴,Dismeryer先生更深地堕于孤寂的阱中,直至湮没。其中第一个有意义的场景是考英文,试看下面的描写:
Dismeryer接着书,全部灵魂浸在书面上几个字,看了半天然后展开念起来,一字一顿,长的字便一音组一顿,一页一页慢慢地读下去,头上的热汗涔涔地流,嘴唇发颤,但是他的神情是很镇静的。P已验明他的程度,无须再读下去,便要他停止。他没有听见,精神贯注地仍然读着,似在和强敌决斗,拼命地决斗,全生命都在这孤注一掷了。
且不说“考”本身是对霸权想象的颠覆,是对由政治、历史、种族造成的人格不平等的快意报复,就是考英文这一细节也意味着错位悖谬,如果是考德文,Dismeryer先生不就可以大显身手,衣食无忧了吗?其萧索的心境怕也不会再有了吧?但无论P怎样的扼腕,怎样对“考”所含有的即使些微的专断与残酷充满不安与自责,而痛感“他应该生活,不是应该被污辱的”,事实是都没法被改变,Dismeryer先生还得继续从前的生活,而且很明显境况只能更坏下去,他在P夫妇生活里的失败是必然的,打击当然也会更大。就食于P家在Dismeryer先生可谓万不得已,在P夫妇却是力不从心,不难猜测他们只能在难堪的情景中终止,Dismeryer先生孤寂的生活终于没法改变。自然这中间也有文化观念的不同造成的隔阂,如P的妻深怕过于牵累了自己,以为与其自己挨饿,不如不作假慈悲,但她又不敢说直话开销Dismeryer先生,只想客客气气地招待,使他自己怀惭而退,而Dismeryer先生毫不体会这样的情形,觉得有时带些食品就已足够联络感情了。小说中Dismeryer先生七处善意的微笑似乎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然则微笑面对世人与生活,现实还是在他孤独的心境里毫不留情地涂抹着,直至把一切都没入黑暗。
与Dismeryer先生相比,H先生人生的况味要厚重些,在其卑微琐屑的生活背后矗立着不可言喻的孤独,哪怕只是一类人的生活状态,而作为生命它却要真实得多。起始部分倒叙场景里就有深广地喟叹:“在这广大的人的城中,谁会注意到呢,一个万里外的异乡人孤寞地病死在旅馆内,没有家族,没有朋友。”H先生的死倒不能说明对“孤独”意义的异议,反而是对“孤独”的伤悼,说它是对于戕害的愤激亦无不可。H先生平平常常,甚至似乎有些低能,他拼命挣钱,却拿不到自己应得的报酬;他揽下很多功课,但自己知识贫乏,毫无趣味;他脾气很怪,但对学生倒还和气,此外诸如听差们恨他,嫌他吝啬,不知有赏钱,对学生的Appointment冷漠,本国人看不起他等等,不能不使我们感到这是个再凡俗不过的人了,某种意义上这会带给我们的审美心理不小的挑战,不过这样的个性形式毕竟只能给寂寞增加怅然之感,并不能动摇其后坚固的东西。这个高高的、庄严的、有着军人姿态的外国人,“微微的笑纹里隐藏着寂寞”,能够体会到平常人体会不到的文句。看似厉害的背后总是淡然的和蔼,他能对欠薪四五千元的当时北京的教育界说些什么呢?!与骄傲的本国人合不来,沉重的生活又难得使他有廉价的乐观去对中国学生作表演,虽然这也与民族性格有关。他只是拼命的生活,绝不敷衍迁就,连走路的姿势也不肯放纵,正常人的喜怒哀乐与决不姑息的作风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孤独却也因此获得了源泉和动力。孤独体验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情感基点,且不论鲁迅的《孤独者》,《阿Q正传》就以其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而饱含有知识分子特有的孤独的人生观,郁达夫、冰心、叶绍钧等庶几近之。除了社会与生活造成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失衡外,相近的精神资源如尼采、易卜生、裴彖飞等高倡反叛的声音,差不多也成就了相似的文化心理,在冯至那里还要特别加上一位,这就是里尔克。在给朋友的信里,冯至写道:
我从Rilke的诗里懂得了一点寂寞同忍耐,从尼采的文里懂得了一点寂寞同忍耐,从Van Gogh的画里懂得的也是一点寂寞同忍耐……
他的一篇散文《好花开放在最寂寞的园里》连题目也打上了“寂寞”的烙印,文中称述“尼采、屈原,是我们人类最孤寂的人中的两个,他们的作品却永久在人类的高峰之上,绝非普通一般人所可仰及”,并且非常自信地认为“没有一个诗人的生活不是孤独的,没有一个诗人的面前不是寂寞的”。里尔克深刻的寂寞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冯至的创作,这充分体现在他对凡俗之上的寂寞的美的追求,这追求又是纤尘不染、明净澄澈的。剧作《鲛人》里“女”这样呛呼:
我的性格是孤独的,不大喜欢同许多人在一起,可怜的鲛人呀,我不能爱你了,你不能是爱我的人了,我不耐烦再看这样子的俗人,魔鬼化身。
对爱情的净界洁土似的追求正突出了孤独的价值。H先生也是这样一种意义的追寻者,他诅咒北京教育界的欠薪,不能容忍战争所加给他的灾难,本国人的强悍也是他不能接受的,但他又能怎样呢?在连听差也不理他的情况下,他只有辛辛苦苦的活着,远离嚣杂烦闷的现实,躲进孤独的真空中,难怪他的精神要一天比一天地坏下去,在对待“损失”和“苦恼”的问题上,冯至提出一种湮灭希望的策略,“如果你借给人家钱,最好的是不要希望他偿还”,冯至称之为“秋天的,第二番没有力量开放着的花”,H先生完全做到了这样,但死还是捉住了他,几乎无事的悲剧里包含了孤独的代价[2]。
冯至的作品较多理想色彩,人间的爱是其重要内容。《乌鸦——寄给M弟》中如此礼赞母亲:“母亲是神圣的,比世上的一切的感化都伟大”,“母亲在我们心中燃的灵火永不熄灭”,《H先生》里亦有这样一副笔墨,作品的后两部分浓墨重彩地属意于此:“别离了的多年的万里外的游子一旦归来,那一双白发老人该如何欢喜!”“只看他(H先生)的额上有些光似的,大半那里承受了双亲的吻了!”最后一段运用了传统的对照手法:
我似乎看到那在他的故乡的老父母,早就该永息了,而尚未永息,只为望着他们那远在天涯,留在东方的孤独的儿子……
看似陷于更大的孤独,实际上是投下一服疗剂而稍稍远离不安与痛苦。相反,《Dismeryer先生》连同情都没入无奈和危险之中,小说结尾P夫妇脑子里时时萦纡着的问题未尝不是人类的孤独问题,这也是彭家煌小说创作的特色所在,几乎每个故事都是悲剧,而这悲剧终是人类相互间理解的困境的结果,有名的《怂恿》、《陈四爹的牛》不必说了,短期内重版五次的《皮克的情书》仿佛以喜剧结尾,但那肥皂泡似的希望该是多么不堪一击。《节妇》里阿银荒唐的生存实在是人生怪圈的缩影。被施蛰存称赞为“描写的手腕已经达到圆熟的地步了”的小说《美的戏剧》更为别裁,美与丑在秋茄子那里得到了统一,不过可悲的倒还是那自我挖掘孤独的西西弗斯式境地[3]。再来观照《Dismeryer先生》和《H先生》,可以说,作品扑散出的爱与深深的孤独就成为了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
作为有着不同创作原则的两位作家,冯至和彭家煌都不无寂寞的情怀。冯至译《画家VAN GOGH与弟书》中确认“新的艺术家多半是更大的思想家”,《赛因河畔的无名少女》则盛赞“百年才开一次的奇花”,在所译《Rilke通信》里则有着创作“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向着内心走去”的主张,孤独之美在冯至是有其伟大的内在动因的。被鲁迅称之为“是我们这边的”作家的彭家煌一生困厄,以吃饭为严重追求的作家反以多吃冰淇淋患上致命的胃病,最终死在上面,但“如果友人穷了,他甚至可以当了自己的被来周济你[3],却从不曾向友人作过什么困难的请求的”。正是这样的反差,也才容得人沉思他独特的、不能不有的孤独心境[4]。因此,曾七次修改的《Dismeryer先生》和深得作家情调的《H先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