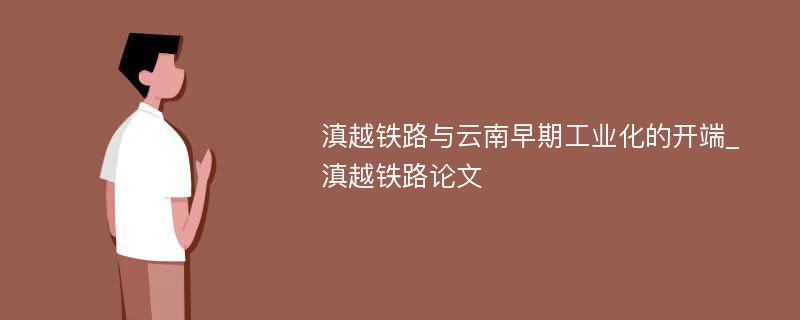
滇越铁路与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铁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585(2000)05-0073-06
一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所形成与内地交往的困难,近代云南与全国不同,其出现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并不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在1880年的中法战争之后。1883年的中法战争及之后中法两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云南的经济渗透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云南在自然与矿藏资源上的优势及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形势——即农矿业并行发展,锡矿逐渐取代昔日铜矿的地位并仍处于上升的发展势头——也必然成为其关注的对象。锡矿早在17世纪,尤其是西方工业化起步以后,就已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在英国“锡产量的增加虽然无法与煤炭产量的增加相比,但在17世纪以后,这种增长仍然是显著的”。如1638年为120万镑,到1687年已达327万镑,发展速度为273%,“这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从英国进口锡”,可见锡矿资源对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云南的锡矿要进一步扩大出口量,提供现代化的交通手段显然至为关键,这当然也同时成为对其它资源进行开采掠夺的前提,正如法国驻越南总督都墨所言:“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由于各行省,(修建)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由此可见西方殖民者在云南建立现代交通条件的初衷,然这一举措也的确在客观上造成了云南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机,并由此而拉开了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序幕。
美国现代化理论主创人之一罗兹曼在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论题时就曾经讨论过关于何谓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可以“用非生命动力资源与生命动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指的乃是人力)资源之比率来界定现代化的程度”。由于现代化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所以在其发展进程中“这种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也越高。”而这一对现代化内涵的简略归结,也清楚地标示出了工业化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一种更为直接的表述方式是“所谓工业化,从总体上来说就是非生物动力工业替代生物动力工业的过程,也就是机器工业替代手工工业的过程”。而以蒸汽为动力的火车这一现代运输手段的启用,显然就可以被视为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点了,因为它意味着由于铁路运力的诞生将突破人力和畜力的生理极限而在一种新的能级上把社会经济结构推向一个更高的运行水平,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云南地区在20世纪初出现这种在生产力手段上的跳跃式发展,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考察,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有如马敏所指出的:“正是‘西力东渐’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真正推动力和逻辑起点”。同时朱英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在许多领域中明显出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转化,实际上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这种转化与清政府实施的新政策与改革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近代西方的殖民侵略;晚清政府行为和体制出现新的转化;以及维新运动等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均成为这一事件发生的相关因素。也说明我们对云南早期工业化起步的这一时间界定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条件和得以成立的理论依据,它与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正是这种由殖民侵略引发的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步方式,使它具有了不同于常规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启动的特点:
首先,从早期工业化的动因来看,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商品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为稳固竞争中的霸权地位和实现进一步扩张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棉织品是国际市场销量最大而且最有利可图的商品,海外贸易的拓展也使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但要保持其优势地位,如何使产品质高价廉便成为竞争的关节点,这就促成了当时在纺织业的生产手段上寻求解决的基本动因。所以,西方早期工业化的萌发是源于一种内生的因素。而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步则以西方列强的殖民野心为直接动因,是由外生因素促成的。1880年以后,云南的交通阻滞显然是当时英法帝国主义者从东南亚通过云南地区对中国实施所谓“扬子江计划”的瓶颈,交通遂成为殖民者首要考虑解决的问题。随着《马关条约》签定给予日本投资办厂的权利之后,几经周折中法双方议修滇越铁路的计划也逐步趋于成熟,光绪27(1901)年滇越铁路法国公司成立,即开始动工,1909年部分区段营运,1910年全线建成通车。这就贯通了云南通过越南直抵出海口最便捷的途径,由于运输时间的节约而导致空间距离的缩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洋货的倾销和原料的出口,仅短短几年进出口贸易额便成倍增长。马克思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趋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马克思接着又说:“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从初始动因来看,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本性促成了殖民地经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转机。
其次,从早期工业化发生的部门时序和其扩散能力来看,西方早期工业化的产生首先发生在前工业产业的部门之中,即工场手工业的棉纺业。棉纺机的使用使生产率水平大幅度提高,从而带动了净棉、梳棉、漂白、织布、染整等各道深加工工序也发生了由机器替代手工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并扩散到其他相关的部门和产业,使国民经济发展由此而跨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之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工业化的特点是它具有一种强扩散效应,即它是以纺织行业的轻工业生产的需求为导向而促发了对产前的农业、矿业,产中的相关行业和部门,产后的交通设施、运输手段、仓储保管、市场销售等的要求而形成一种连动的生产力性质的结构性转变,从而在整体上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确立。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它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正由于此,它也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日本学者十时严周在描述日本早期工业化发生的部门时序时则又有所不同,他认为日本“工业化过渡的起始点当在江户时代幕府以及西南雄藩引进西洋军事工业时期。安政四年(1857),幕府在长崎设立浦溶铁厂,随后我国最早的6马力蒸汽锤开始起动。它的马力虽小,却标志着使用蒸汽机并拥有一系列工业机械体系的正规工厂的出现。以此作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具有深远意义。因为该工厂的工作母机能够生产出其它工作母机,而这些新机器又能在其他地方制造出新型号的工作母机。如此不断更新换代。它意味着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已植根于我国”。由此可以认为日本早期工业化的起步是从机械工业即重工业开始的,但如果它没有后期军转民用运行模式的调整,其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扩散的能级水平将比西方常规模式要低,因为它不仅缺乏来自市场最终需求的刺激,而且由于重工业所具有的投资大、成本高、周期长等特点,也将使其掉入后发展现代化国家(如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教训)资本积累不足恶性循环的陷阱之中,从而在整体上延缓其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云南早期工业化发生的部门却是以铁路运力作为起始点的,因为以蒸汽为动力的承载力的生产力性质的变革,对以陆路及人、畜力运输为条件的云南来说,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重大解放,而且冲破了长期以来运力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而跃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能级水平,在短期内推动了工矿、农业和商业的大幅度增长。当然,以铁路运力作为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点,其部门扩散的能级水平将受到更大的限制,因为某一设定的运力能力在短时期内是很难发生变更的,尤其云南在当时处于自给自足状况下其资本积累的极度有限,要想在短时期内增加投入就更难了。但尽管如此,铁路运力在当时的起用已对云南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二
滇越铁路建成对近代云南社会经济进程的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滇越铁路的创设开启了人们的现代交通意识,为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交通条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人才、管理等知识的培养和积累。滇越铁路云南段的兴修是采取中法双方合资的形式,即中国方面出土地、劳动力、及负责之后的保养、维护和修理;法国方面出资金、技术和相应的技术管理人员。80年为期,在此之前铁路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均属法方;在此之后中国方面可与法方商议收回地段铁路及铁路一切产权。当然,其产权的收回也是有条件的,殖民者所提供的现代化手段和设施绝不会是不要代价的。然而,也正是在修筑滇越铁路及其之后运行的过程中,在有关方面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也学到了关于现代交通建设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大量知识,并开启了时代建立自己的现代交通设施的思路和具体实践,而云南地区现代交通体系的建设亦由此而肇始。如当时在全国路矿运动的推动下,针对英国意欲修筑滇缅铁路以夺取滇西交通要道的活动,云南人民成立了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决定自筹资金来修筑铁路。并首于1912年筹议,1914年动工,在滇越铁路的基础上延展了碧临屏铁路。其中个碧铁路完工于1921年,这就使个旧的大锡能从产地直接起运通过滇越线输往国外,不仅减轻了人力和缩短了运输时间,而且降低了产品的运输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增加矿业资本的积累速度提供了条件。
第二,缩短了云南对外交往的时空距离,使经济效益短期内成倍增长,首次实现了由经济的渐变性发展向突变性增长的飞跃。滇越铁路通车前,云南进出口商品走滇南线从蛮耗下水算起用舢板经红河水运至越南海防港其净行程都要半个月左右,回程逆流而上则需时约一个月,而这已是云南最近的出口线路了。到内地北京、上海等地,则一般要先经贵州、湖南到汉口,约需时40日,然后再转其它地方。加之货物运输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这不能不受到人、畜生理条件的限制而制约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个旧至碧色寨(两地与蛮耗同属临安府)只要6、7个小时,而碧色寨到海防港也只需2日左右。如果从昆明上火车,6、7天就可到达香港,9天就可到上海。这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来说,其贸易量几乎不受什么限制。这就在短期内促成了云南经济的成倍增长,云南1908年以前其对外贸易年均出口额为1200万关两左右,但到1912年便已达2200多万关两。其中蒙自关占总额的87%,约2000万关两,比1908年以前年均1000万关两左右的水平增长了近一倍。在1914年~1917年间由于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蒙自关进出口货值总额下降到1500万左右的水平,但其中出口额却呈上升趋势,到1917年已近1300万关两,并从1910年到1920年间出现贸易的持续出超,这在全国来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到1927年,全省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到3000多万关两的水平。而从进出口主要货物的结构来考察,此间各业的发展速度也迅速加快,参看下表:
1927年云南前五位进出口货物价值、结构比较 单位:海关两
名别
进口名别 出口
货值
占总额%
货值 占总额%
总额19834261
100 总额11960469 100
棉纱
9128093 49.1 锡 8162100 70.0
棉布
3921550 21.3
针丝
2016130 17.3
煤油 612271
3.3
皮革
768360 6.5
棉花 551060
3 猪鬃 132767
1.1
人造靛541014
2.5
主要金属品
104052 0.8
资料来源:《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第578~584页。
契波拉认为:“贸易是供给与需求的体现,贸易特征的更深刻的变化可以反映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1910年以后的十几年间,云南对外贸易无论是从增量或是从结构上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从发展规模和各产业的地位来看,到1927年云南进出口贸易规模比1908年的1200多万关两已增长了1.5倍强,达到了3000多万关两,从中可以看到由于滇越铁路现代化运力的提供所明显出现的倍增效果。进口商品前五位中的棉纱、棉花和人造靛均属纺织用原料,价值总额为1000多万关两,为1908年以前约300多万关两规模的3倍强。从前五位商品类别的地位来看,到1927年云南进出口贸易与1908年以前相比大宗贸易的前一、二位没发生变化,说明锡矿业及纺织业的主产业地位没变,并且由于上述产量的成倍增长,其地位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其后的某些商品在排序上却发生了变化,如进口方面1908年以前的前三位中就没有煤油,但1927年它已排到第三位,而且进口额达392万关两之多,说明民间消费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仅照明一项已从原来依赖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为限制条件的消费状况发展为更多地依赖洋油照明的现状:出口方面前五位中的皮革、猪鬃和金属品行业的发展,则明显是受到国外市场需求的引导而在最近发展起来的,而这一点又与全国同一时期出口产品结构顺序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其次从进出口商品的绝对额及种类变化则反映出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既有原部门的进一步深化,亦有新兴行业的拓展。如出口产品中大锡与前期相比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所占比重基本未变,仍维持在75%左右的水平,但绝对数已从1908年的400多万关两增长为800多万关两,产量则由原来的近4000吨增加到8000多吨,表明该部门的投资规模已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增加。此外,出口商品中经丝1927年的贸易绝对额约为200多万关两,比1908年以前的40多万关两增长了近5倍,而此时在云南为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区域内的丝织业资本已有所发展,不象前一时期的黄丝出口,主要是做川丝的转手贸易。如原属商业资本的富春恒商号就于1918年兼营开设了第一家解丝厂,“至一九二四年共设十八个厂,年产解丝约五千箱,工人共六千余人”。该商号的“资本积累曾一度达300多万元大洋”。至于皮革、猪鬃及金属品三项价值价值总额为100万关两,则基本是基于区域内资源、手工业及商业资本的积累在1910年之后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再从进口商品的发展变化看,1910年以后,纺织行业发展更为迅速,在1908年以前纺织行业年均投入棉花和棉纱的资本额(即棉花、棉纱的进口贸易额)为300多万关两,但到1927年其投入额已达1000多万关两。前期纺织业进口原料的规模约为锡矿出口规模的75%,而现在已达该业出口规模的125%左右,可见纺织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矿业的发展。而从理论上讲,这也是正常情况下符合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上述各进出口商品规模的扩大及种类的变化均说明云南在滇越铁路通车之后其经济的发展水平与1908年以前相比已超越了渐变性的运动轨迹而获得了突变性的增长,实现了云南地区近代向工业化过渡的一次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第三,滇越铁路现代运力技术的移植和使用,在推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要素也由此而导入,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原有经济形态的解体,从而开启了云南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滇越铁路的建成通车,使现代技术设备的引进成为可能,并由此而出现了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化。现有资料表明,云南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生产企业除1888年官商合办企业中唐炯购置机器,聘用日本技师首次在东川采用机器炼铜外(但以失败而告终),一般均出现于1909年之后(该年滇越铁路已分段营运)。而其企业有些在此之前就已创办,原因是1905年“晚清新政”的实施,为民间企业的创办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但机器的使用由于运输问题仍受到限制。随着滇越铁路的建成通车,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企业也随之产生,如昆明耀龙电灯公司的石龙坝发电厂,其全部机械设备于1911年由该路运入,1912年投产营运,装机容量为450千瓦;并于1923年建立第二座发电厂,装机容量为850千瓦。该电厂也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发电厂之一。并于1914至1926年间相继成立了蒙自大光、开远通明、河口汉光等电灯公司,其规模虽小,发电量都只有几十千瓦,但却标示着我省的电力工业已从无到有,并逐步发展。矿业中现代机械设备的使用则起于个旧锡务公司,该企业于1909年改组后,向德商礼和洋行订购机器设备,于1913年建成投产,至此云南锡业中才开始出现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另外还有1911年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的宝华锑矿公司,其时该厂股本及负债总额约35万多元,亦向德商禅臣洋行订购机器设备开设炼厂并投入运营。该二厂也是矿产业中最早使用机械设备并投产运行的企业。此外,1909之后逐渐开始采用机器生产的行业还有轻工业中的皮革、猪鬃加工业、面粉业、印刷业;1910年以后创办的广同昌铜铁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启隆机器厂、振亚机械厂等制造业;以及炼油、玻璃、造纸的化工业等,到1930年前后,使用机器生产的电力、工矿业厂数已有二、三十家,其中工业(狭义)资本约为44万多元,基本集中于昆明,这一现代工业成分的增加,也进一步强化了昆明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因而,有研究认为:“近代云南的统一市场”是随着“滇越铁路的全线修通”,昆明作为“全滇商业中心的出现”而“最后形成”的。从理论上讲,区域市场中心的形成意味着昆明已具备了“交通便利,为各路之交汇点;贸易腹地广大,为货物集散中心;金融、通讯等商业机构健全,生产、消费均居全省之首”。而这就意味着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出现了一种质的飞跃,这同时也就为新生产力的移植提供了资金、市场、劳动力等必要的物质前提。而上述由于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而导致的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张,以及新生产手段的植入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更,均在有形和无形之中产生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的解构作用,其作用力“越靠近铁路的受到震动越大”。譬如沿线的农村“由于田主们受到外国商品的刺激”,其消费的需求日渐膨胀,加之“利润的引诱,多想兼营运输、山场……等,所以他们急切需要货币,而庄园剥削受永佃权的限制,不能任意加租”,便促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这样庄园便被破坏了,其破坏的程度,则与铁路的距离成反比。昆明、宜良、路南、开远……等县最剧”,使“为数不少的人口投入商业城市,其中不仅有弃农就商的地主,也有失去土地的农民,昆明、宜良、开远、碧色寨、河口等地也就这样日益繁荣起来了”,所以,毛泽东在论述关于殖民侵略对我国传统经济的作用时也指出:“它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尽管近代滇越铁路的修建及后期营运都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它对云南早期工业化起步与发生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渡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滇越铁路的建成对云南地区来说,犹如在一个封闭体中导入了一条与外部联接的强劲脉流,沟通并加速了云南与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交往与对流,带来了资本、技术和人才,开拓了云南的市场,冲击了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基础——自然经济,也使滇中及滇南一带在1910年之后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商品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在我们前引的有关当时已具有现代生产力性质的矿业、电力、轻工业等企业也几乎全部都分布在这一区域内,可见滇越铁路的建成对云南地区经济发展与促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它对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发生与进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早期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甚至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走向衰落和破产,云南亦然。但究其原因,并不在于现代交通本身,而主要在于旧政府的政治腐败,不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本和群众力量来推进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保护,必要的急需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各种赔款、用于战争等,使社会经济难于发展。近代云南社会的发展历程给我们予启示,亦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教训。根据云南自然地理条件的实际,作为一种历史借鉴,深入研究交通与云南工业的关系应是云南经济史的一项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