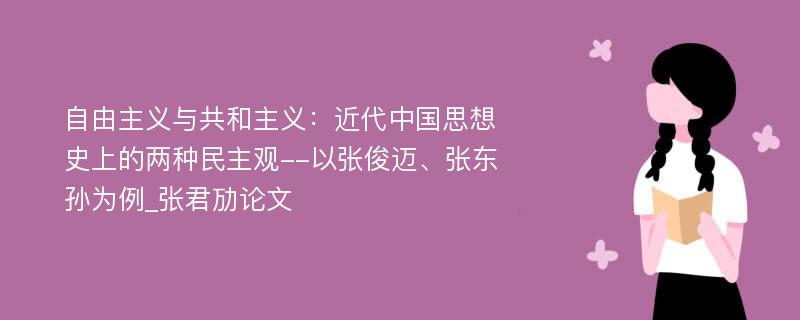
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两种民主观——以张君劢与张东荪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共和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民主做共和主义式和自由主义式的区分,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西方民主思想所做的一个规范性阐释。按照他的观点,自由主义认为,社会只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交换的系统,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可避免,民主只是按照不同利益来进行权力分配的问题。因此,政治最终表现为类似于市场交易的权力交换行为;共和主义则认为,国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民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应当表现为一种道德上的自我理解,而公民们的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构成了社会作为政治总体性的中介。因此,社会自我组织的自治是共和主义民主实现的重要前提(注: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载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284页。)。这两种民主传统对于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主权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自由主义民主认为,由于国家与社会在现代出现了分离,政治不能随意侵入私人领域。因此,私人的权利保障成为国家的主要任务,而民主则体现在通过代议制、投票等程序来获得政治的正当性;共和主义民主则强调共同体的政治特征,对公民美德有很高的要求,认为只有培养公民的美德、让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才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善。和自由主义不同的是,共和主义将社会看作是政治性的,是伦理的延伸,道德与政治无法分离;在主权问题上,共和主义认为,正当性在于普遍意志的实现,但是,它不同意自由主义的代议制,认为主权是无法被代表的。
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一方面直接汲取了大量的西方政治思想的资源,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接受绝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史华慈对严复的分析表明,严复在吸收西方思想资源时受制于其儒学背景(注:参见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林同奇《误读与歧见之间——评黄克武对史华兹严复研究的质疑》,《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而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发现,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有极其明显的“路径依赖”,对于西方思想的接受实际是自身传统的不同脉络被重新激发的过程(注:这方面可以张灏对梁启超的研究为代表,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一
作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的党魁,张君劢不仅在第三势力的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他的民主宪政思想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毕生宣扬其宪政理想,而且身体力行,参与制定了民国的几部宪法,从而被称为民国的“宪法之父”。
张君劢本人在叙述其政治思想时,说“哲学喜欢德国的,政治喜欢英国的”。在张君劢看来,英国政治思想传统包括了代议制、个人主义以及改良的精神(注:张君劢:《政治典范》译序,载赖斯几《政治典范》,张士林(张君劢)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5页。),民主所包含的要点无外乎:“一、统治权属于全体的分子。二、各分子之意思表示靠投票。三、投票不能求全体人民之一致,只可以多数取决”(注:张君劢:《立国之道》,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101页。)。
张君劢认为,民众参与政治虽然要通过民主投票的程序,但是,现在只能通过代议制度来实行。在他看来,“绝对的直接民主”需要知识精英的不断努力,提升暗弱国民的素质,才可能最终实现。张君劢明显是精英主义的政治思路,他认为政治秩序的关键在于代议制和宪政。他在分析拉斯基的思想时,指出:
惟赖氏(现译拉斯基)之意在严防政府之擅权,故于国体政体之分别则否认之。昔人有言曰,主权之所在曰国体,主权之行使曰政体,而赖氏则曰国家何在,不可见焉,吾人每日所接触者,独政府而已。政治学中之问题,非国家主权之问题,而政府行为之问题也……然则政府之良否,不在政府自身,反在于监督之国民矣。于是个人之智识与个人之权利乃为政治学中第一问题。(注:张君劢:《政治典范》译序,载赖斯几《政治典范》,第27页。)
显然,张君劢同意拉斯基关于政治的关键问题在于政体而非国体的观点。他说:“鸦片战争后,欧洲国家踏进我们国土,我们最初认识的是船坚炮利,最后乃知道近代国家的基础在立宪政治,在民主政治,在以人权为基础的政治。”(注: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七年(1948)版,第2页。)
那么,张君劢是如何建构他的人权理论的呢?按照何信全的分析,张君劢在知识与伦理两个层面都接受了康德的观点。他以康德的“以人为目的”作为伦理层面的根基,因此,人权成为其民主思想的最终理据(注: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在张君劢看来,个人自由固然重要,但需要权力来保障政治秩序。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同时要面对政治秩序与个人权利保障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政治秩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维护,另一方面,没有宪政约束的国家权力又容易侵蚀个人的权利。因此,张君劢试图调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这一矛盾。这种思路并非是张君劢所独有的。黄克武就认为,在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一条调适个人与群体关系问题的思想脉络,梁启超就是这样处理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问题的(注: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4年第70号。)。作为梁启超的学生,张君劢明显也有这种调适思想。这一点在《立国之道》中有非常清晰的表述:
根据以上两项,我们获得政治制度之纯粹意义:一、国家行政贵乎统一与敏捷,尤须有继续性,故权力为不可缺之要素;二、一国之健全与否,视其各分子能否自由发展。(注:张君劢:《立国之道》,第146页。)
但是,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集中却是有着内在张力的,张君劢由此提出的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主要关切的问题就是权力与自由的关系。张君劢将政府的权力与个人自由酌情安排在互为补充的位置上,他用心物二元观来解决这个冲突。他认为,“权力是计划,是系统,是轨道,自由是意志,是机动,是精神”,“没有系统与轨道,将无以端其方向,结果不免于乱;若无动机与精神,将无以促其向上,结果不免于死亡”(注:同上书,第366页。)。在这点上,他和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存有差异。自洛克以降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强调自然法所赐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防止国家侵犯私人之领域乃是英国自由主义之首要目的。但是,张君劢本人是康德主义者,而且他还用儒家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作为另一思想资源,他没有为个人权利寻求天赋的自然法根基,而是以超验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作为人权之基础。
虽然张君劢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有所修正,但是他的这一思考路径,明显又是遵循着自由主义民主的逻辑。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作为个人权利的伦理依据,从而依靠限制权力来保障个人权利,而人民又通过代议制和民主投票来实现政治的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张君劢在安排个人、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要将个人自由、社会普遍的福祉及国家秩序调和起来。他在《立国之道》中谈到:
一国之中最不可少者有二:甲曰政府之权力;乙曰国民之自由发展。介乎此二者之间尚有社会公道问题,其所关涉的以经济为多。(注:同上书,第142页。)
在张君劢看来,个人与国家形成政治秩序的两极,而社会只是一个经济系统,一方面个人要在其中进行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国家要利用权力调节贫富差别。这一预设显然是将个人与国家对立起来,忽视了社会组织的政治性格。张君劢在构造他的宪政方案时,一直都没有很好地考虑社会自治的政治力量。他始终认为,依靠少数政治精英作为主角的党派政治,就能够形成有效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政制度。他在《立国之道》里讲道:
一国政治上的运用,有时是靠少数人,而不能件件请教于议会或多数人。少数人之责任,如此重大,所以一国以内,要有少数人时刻把一国政治问题精心思索,权衡厉害,仿佛剥竹笋一样,要剥到最后一层而后已。(注:张君劢:《立国之道》,第353页。)
而这正如江勇振所描述的那样,张君劢建构出一种“有道德、有知识的秀异分子鞠躬尽瘁于上,而自由解放的国民如众星拱月一般勤奋不懈于下,上下和谐不已的政治哲学”(注:江勇振:《我对君劢先生政治思想的点滴认识》,载郑大华编《两栖奇才——名人笔下的张君劢张君劢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87页。)。这种精英主义政治理论很明显地认为,精英分子是改造政治秩序的主体,而国民则是被改造、被启蒙的对象,国民自己是无法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来参与到对整个政治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去的。这种只强调精英和国家之间政治互动的观念一直支配着张君劢,虽然他也非常注意社会公道,但却始终认为,公平之类的问题必须在国家权力架构下完成,个人与社会的福利必须依靠国家来保护。
因此在多个层面上,张君劢都显现出与自由主义民主观念近似的取向。比如,他将个人权利看做民主政治的基础,强调靠精英的党派政治来建立宪政制度,以此约束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的权利。在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关系上,张君劢基本上将国家与社会以及个人领域做了一个分割,使得政治、经济及个人道德产生了深度的分离。他进而认为,在政治制度运行过程中,只有党派互相监督和利益的妥协,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这也是张君劢在民国之后多次立宪过程中表现非常活跃,而且最终参加了1946年“国大”的原因之一。
二
张东荪和张君劢相识于1907年,从反清、倒袁直到组织国社党,两人的政治取向基本一致,被世人并称“二张”。1946年两人失和,这里面固然有当时社民党内部激烈的人事矛盾以及其他因素,但是,两人在民主和宪政观念上存在分歧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张东荪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且和梁启超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段时期里,他和梁启超等人的政治立场比较一致,都追求英国的宪政主义模式和政党政治来整合社会和国家。当时他在《庸言》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表现出宪政主义的立场。但是,1913年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后,张东荪的观点有所改变,他试图以社会的对抗力来约束国家权力。他说:
立国制治,在国民之自由,非特在普泛之自由,尤在间接得致其影响于政治之自由……欲社会之力,足以威迫其政府,则必有社会威迫之道,而不为政府所夺,其道即国民之政治上自由是也。(注:东荪:《制治根本论》,《甲寅》第1卷5号,1915年5月10日。)
很显然,他所叙述的政治自由是参与性的“积极自由”,强调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对抗性,市民可以利用社会力量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以此来分散国家的权力和保障自身的权利。其后张东荪所提出的“联邦论”和“自治论”也都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五四运动”时期,张东荪开始主张缩小国家领域,扩张市民秩序。按照韩国学者吴炳守的分析,这一时期的张东荪接受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确立了“伦理的市民论”与“普遍的市民意识”的观念(注:吴炳守:《民初张东荪国家建设构想的形成》,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在后来张东荪主持的《解放与改造》和《时事新报》上,他提倡由个人组成自由平等的自律共同体,试图将文化和社会改造运动结合起来。
应该说,20年代的张东荪意识到,宪政运动的失败在于没有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来支撑,从而主张依靠社会的自治和联合参与国家建设。他在后期的著作,特别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特别强调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个概念。他认为,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会直接导致政治性的不平等。因此,平等从来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而且还应该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是以经济平等为出发点,但其指向却是政治的平等,目标最终是民主主义(注:参见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
他在1932年《再生》创刊号上明确提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原则和精神。这一思想在《思想与社会》中有了详细的表述,他认为:
近代把民主政治化为民主主义,使其除政治外包括各方面,例如生活与思想态度亦在其内。于是民主主义便是一种文化,而不仅是一个制度而已。既是一个文化则又可说是一种精神。只要精神是合乎民主,则纵使其外表的形式有种种不同,亦绝不要紧,反之,我们纵使有民主政治之制度,而无其精神亦是徒劳。(注:张东荪:《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张东荪在这里将民主不仅理解为一套制度,而且上升为一种精神,这无疑和自由主义对民主所持的工具性认识有所区别。他特别声明,他所阐述的民主乃是一种精神(Spirit),而非作为制度上的“政府学”。他注意到当时西方一些学者对民主所做的阐释。比如,他提到了当时的一些欧美学者如杜威等人,都将民主视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和精神(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1946)版,第145页。)。在民主问题上,杜威认为:
民主的政治与政府方面只是一种手段,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好的手段,用以实现遍及于宽广的人类关系领域及人格发展方面的目的。正如我们常说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的和个人的,尽管我们可能并未领会这一提法所蕴涵的全部意义。(注:杜威:《人的问题》,载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孙有中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张东荪的思想与杜威的看法基本一致,对民主的界定并未停留在制度程序上,而是认为民主应是一种理想的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我们总括来说,民主主义同时是个政治制度,同时是社会组织,同时是个教育精神,同时是个生活态度,同时是个思维方法,同时是个前途的理想,同时是个切身的习惯。这样则民主主义就等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之全体。(注:张东荪:《思想与社会》,第192页。)
张东荪将民主主义看做是一种渗透在各个领域里的文化。他认为,民主主义是中国未来的文化希望,是一种可以整合哲学、经济、政治诸领域的整全性方案。他明确提出,《思想与社会》一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以哲学为代表的理论知识与有社会性的实际生活之关系究竟如何”(注:同上书,第3页。)。他试图为中国建构出一套彻底的方案,用社会文化来打通哲学和政治。在张东荪看来,科学、理性都是与道德分不开的。因此,政治生活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群体来说,都是道德性的生活。
张东荪针对反对派认为普通人智识水平不高,因而不能实现民主的观点反驳道,“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给人民以实习的机会”(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147页。)。因此,民主实践可以促使民众提高参与政治的能力以及智识水平,而教育主要是立足于养成受教育者的独立判断力,使得公民们能够在政治生活中自由讨论。这种强调实践和教育培养民主习惯和能力的看法与杜威是不谋而合的。杜威也认为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藩篱应该打破,应该充分信任民众接受教育的能力。也就是说,社会应该是平等的,而平等的内涵不仅仅是政府所赋予民众的相同的权利,而是无论社会个体地位如何,他的存在就已经确立了个体的自足性和不可宰制性。只有每个人发展自己的独创精神和适应能力,他们才不会落到少数人宰制的局面,才能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到公共的生活中去。
在谈到如何介入政治时,张东荪认为儒家传统的律己精神可资利用,可以用道德热情来追寻作为一种文化的民主主义价值。因此,他认为,中国民主之建立,必须托命于“士”,因为士有两种长处:一是理性主义,二是道德主义。他们可以承担西方公民社会中的“公民”角色,依靠“公民美德”(Civic Virtue)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并且通过教育来培养市民的理智能力,最终普及民主主义。
总体来看,张东荪并不认为中国应该向一个政治与伦理分化的方向发展,他延续了儒家传统对政治秩序的看法,认为社会不仅是伦理性的,而且还是政治性的。但不同的是,他将儒家的“道统”置换成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将平等看做是政治秩序的价值基础,从而建立了一套卢梭式的“总意”架构。而由于他没有将道德与政治分离开来,因而强调道德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强调只有通过教育,让个体肯定民主主义的价值,那么,民主才最终可以有所实现。这种看法与共和主义民主的观念架构颇为相似。当然,张东荪一直都致力于对儒家政治传统的转化,我们似乎可以将他视作儒家式的共和主义者。
三
考察这两人的民主观,我们尽管可以拿西方民主观作为一个比较的基准,但是,正如前面所言,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他们两人绝非规范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他们各自利用了儒家传统的很多资源,这样的“民主”建构方式显然都是儒家式的。
从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脉络中,我们基本上可以梳理出两条民主观的脉络,一条是以严复为代表的密尔式的自由主义民主观,强调“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将自由看做基本的价值,而民主则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来保证个人权利(注:参见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另一条则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民主观,强调政治与道德不可分离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性(注: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五四运动”之后,这两种民主观念在中国进一步深化,张君劢与张东荪无疑可作为典型代表。张君劢以自由意志作为道德之根基,从而推导出人权作为民主哲学上的理据,并以此作为整个宪政架构的基础。虽然他同时也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力的二元平衡,但是他基本上认为保障权利为其根本,权力的运作只在于保证行政的效率和社会公道问题的解决。张东荪与张君劢则有所不同,他受卢梭影响,强调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正当性的重要性,他将之称作新的“道统”;他也不同意宪政主义者将政治制度与伦理分离的取向,而是认为民主需要道德来推动,假如忽视道德的培养,民主自然无法实现,这自然和自由主义者将政治与道德分别看做是独立的“公域”和“私域”不大一样。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张君劢构造的政治制度最终是精英主义取向的议会政治,而张东荪却最终强调民主主义的平等理念,因此,张东荪最终的国民理想是平等主义。在这点上,张东荪和梁启超是一致的(注:同上书,第153页。)。这样一种平等的关怀使得他不同意张君劢试图通过上层政治来进行分权限权的宪政主张,反而将其视作是反民主的。
在1946年“国大”召开之际,由于共产党不参加此次“国大”,张东荪认为,这样一场国大显然只不过是国民党控制下的政治分赃游戏而已,各民主党派根本无法有效制约国民党的权力滥用,这样的民主当然是“假民主”。而且他认为,国民党作为代表豪门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政党,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意愿,在这样的“国大”框架下所进行的宪政实验最终只是“宫廷政治”的另一次重演而已。
而对于张君劢而言,1946年的“国大”只是另一次的党派斗争妥协的时机。他认为,利用党派之间的斗争和妥协,可以依靠精英建立起一套宪政制度,然后再靠这套权力分散的制度和民众权利的觉醒来监督政府的权力,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民主。宪政的建立固然可作期待,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政治实践过程如何实现的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宪政主义和权利理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传统,实际上无法应对政治实践过程的残酷与血腥,其中庸和渐进的政治性格只能使自身被逼压到社会的边缘,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宪政主义屡次失败的根源所在。
标签:张君劢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张东荪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梁启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