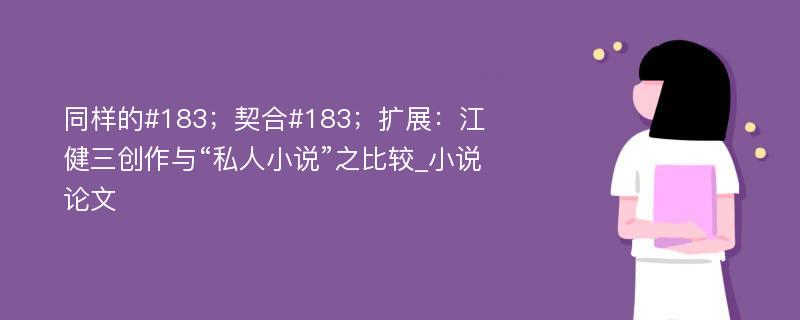
相同#183;契合#183;延伸——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与“私小说”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大政时期,一种在自然主义文学的土壤中萌芽,依据个人的琐细生活为素材,以吐露自我心绪为主的“自我小说”,在日本广为流行,这就是所谓的“私小说”。“私小说”将作者个体通过作品“自白于世”,其宗旨是表现“自我”。“私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可追溯到日本古代平安朝时期的女性日记文学,其纤巧的风格,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较强的写实性,可以说是代表了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方向。大政末年,“私小说”一度统治日本文坛,为许多作家和读者所钟爱,究其原因,除了它能深刻地揭示人生的体验,强调人物心理层次的分解外,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日本社会结构的民族性格。这种叙述生命体验和披沥心境相结合的文学形式在日本一度“称雄一世”,至今仍是日本纯文学的主体。我们说,任何一种思潮、流派、现象,如要持续、绵延,决不能仅仅停留于对传统或“意象”的简单显现,它重要的是要在继承和借鉴中有所扬弃,以寻求传统的、民族的与现代的、世界的契合点,从而以崭新的现代形式来适合现代人的意趣与爱好。“私小说”的流向就遵循了这一发展规律。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历来被公认为是现代流文学的中坚作家,其实在他的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印有“私小说”痕迹。他在1994年12月7日斯得哥尔摩皇家文学院发表演讲时说:“我在文学上最其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①]“本人是在通过写作来驱赶恶魔,在自己创造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所共通的东西。”[②]1963年对大江来说是个极不平凡的时期,大儿子大江光出生,头盖骨先天性残疾,给大江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夏天,大江到广岛参加原子弹爆炸后的调查。“这两件事给大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强烈的震撼”。“随着残疾儿的诞生,我经历了从未感到过的震撼,我觉得无论自己曾受过的教育还是人际关系,抑或迄今所写的小说都无法支撑起自己,我努力重新站立起来,即尝试着进行工作疗法,就这样,开始了《个人的体验》的创作。”[③]《个人的体验》正是作者在这种苦闷之中创作的一部以亲身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别致的内心世界:我面对残疾儿子,异常痛苦,完全抛弃他,良心将不得安宁;正视、接纳他,则缺乏足够的信心与勇气,于是,我选择了让他“自然消亡”这条路,暗示医生用糖水代替牛奶。后来,我经过了“地狱”般的磨难,“炼狱”里的考验,终于能面对残疾儿这一事实,勇敢地承担起残疾儿父亲这一角色。可见,大江表现的是“身边琐事”,通过眼前的现实,披露其隐秘的内涵。大江沿袭“私小说”这种“自我暴露”、“自我忏悔”的套路,无疑表达了最民族性的日本灵魂的嬗变,其深层含义就是对个性的张扬,自我价值肯定的追求。这种典型的“诉说其内心世界的自白和岛国生活的精神体验”与其说大江在实践“私小说”不如说他在探寻日本民族心理文化的支点。
一、主题意向的表达
大江并未让自己的创作深陷于“私小说”的窠臼之中,他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开拓、超越了“私小说”这种形式。在主题意向的表达上,传统的“私小说”多描写由贫困、疾病、酗酒、恋爱所引起的烦恼和痛苦,其终极是“我”、是“个人”,其视野从未超出过“个人”、“我”这个圈子。而大江在作品中也描写情感的纠葛,命运的暴戾,但他能从这些琐事中带出一个全社会、全人类关注的问题;他能在个人的体验中隐含着对人类自身的忧患;他能从表面的、个体的不幸中,探摸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而最终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并将“微小的、局部的、个体的东西放大,升腾为人对社会的一种现象的、情感的价值判断形态。”从而将这些个别的、特殊的现象向遥远的、普通的地平线开拓,以期达到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度哲理性的探讨与概括。
大江笔下年轻的一代,是精神、信仰失落的一代,他们焦灼不安,惶急困惑,孤独与失落、迷惘与痛苦环绕着他们,他们不能做一些对自己、社会、人类有意义的事,从而也就无法实现人生的价值。他们整日醉生梦死,用发泄自己的情欲来确立自我的存在。《我们时代》中的南靖、赖子、康二;《性的人》中的丁夫妇,爵士歌手等,他们都在用荒诞的性行为来与社会对抗,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荒诞的、毫无动机的行为和毫无原因和目的的冲突”。大江在这里是把性行为作为一种展示人类弱点和缺陷的手段来对社会和人生哲理进行思考。战后日本经济畸型发展所造成的空前繁荣后面隐含着危机,传统道德、理性、信仰的丧失,使人们对生存制度产生了深深怀疑,感到人活在这个世界是痛苦的、孤独的。再加上战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断完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将人又拖入到大机器工业革命的旋涡之中,人与物的对立、冲突愈演愈烈,人进入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陌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产生惊恐不安和忧患,人们弥漫在冷酷无情和苦闷之中,周围充斥着肮脏、丑恶和混乱,人的命运被强大的异己社会所左右,人们的精神世界已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江这种对人的精神危机的反思与焦虑,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的揭示,在传统的“私小说”里根本找不到的。
从本世纪以来,核战争的威胁,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大江借描述“个人的不幸和苦恼进而严肃地探究人类共同生存的问题。这无疑是他的过人之处,他在随笔《广岛札记》里描写了广岛人在遭受原子弹侵袭后的惨状:美丽的少女还未体味人生的真谛便匆匆地离开人间;年轻的母亲虽然幸免于难,却染上白血症,病魔将与她终生为伴。大江一次次地向人们提出,在核武器威胁着世界的今天,人类应如何超越文化的差异而生存下来。大江写道:“广岛似乎是整个人类的一块最为裸露的伤疤,那里在萌生着人类康复的希望和腐蚀的危险两种幼芽。”[④]核战争的威胁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而且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摧残也令人发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国家纷纷进行核试验,拥有核武器,大江把这比作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欺凌。一个核实验场的建成,将会造成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这已不是一个国家、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人类需要反思自身,以人文来引导科学。大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呼吁: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这是一个多么愚味、可悲的行为,因这将造成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思理性的限度;实践的两重性;反思人的精神支点、未来归宿等都融进了大江的文学世界里,形成了一种20世纪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是对近代意识的一种超越与反拨,它对当今的人们起着一种警世作用。
大江正是用这些貌似“私小说”的“告白式”描写来揭示当今全球所关注的课题——人类精神危机、核问题、残疾人如何生存的问题。这些课题具有鲜明的普遍性,能使人们超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从而产生共鸣。在《个人的体验》里,作者娓娓地描述了作为残疾儿父亲的内心世界,深入地探讨了残疾者如何生存、残疾者父母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襟怀。在《新人呵,醒来吧》小说集中,大江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残疾儿父母如何艰难启发、教育残疾儿直到把儿子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父亲虽在国外旅行心里时刻惦记着在家的残疾儿,“为了超越自己和残疾儿关系转折期的危机”而努力工作,父亲试图在译书、写诗中来摆脱这种危机。母亲忍辱负重,一面承受着残疾儿子的“扫蹚腿”,一面为开发儿子的音乐才能而不倦地努力。大江在《天降怪物》中谴责了一位作曲家对自己残疾儿坐视不救的反人道作法。大江在作品里让这种丧失人性的人最终在地球上消失。《洪水淹没我的灵魂》里,大江对那些视残疾儿为怪物,不敢正视现实的人给予了嘲笑、鞭笞。大江认为他们这些人是心理、人格不健全的弱智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畸型儿。大江首先在思想意识上揭示他们的“残疾”,然后在作品结局里将他们引入生理的“残疾”圈。可见大江对残疾者人格的尊重,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在表现人类困境中的不安,探寻人性复苏方面,大江显然与传统“私小说”作家不一样。“私小说”在描写上没有“可释性”,它是一种“直白式”、“披露型”的描写;如在描写“性”时,直接为个人的情感服务,因而注满了感情的因素。通过肉欲的描写,直接暴露自己的“丑恶”。田山花袋的《棉被》中把时雄对女弟子的畸型爱欲作了淋漓尽致的渲染。虽然“私小说”展示爱欲与世俗的约束以及个性与旧习俗之间的冲突,但本质上仍未超出个人的局限,都是表现内部情感的失调,原始情欲与世俗社会的冲突;都是以追求自我的绝对自由为终极。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自我内部的自由,以自我的真诚告白于天下,这种一昧沉浸在个人的内部世界,必将导致其作品只揭示非本质的个别问题,纠缠在婚姻家庭之中而未能迈出这狭小的“家族”圈子,就更谈不上对社会、人类问题的思考与总结。大江的创作却不然,虽然他也在作品中大量抖露原始情欲的燥动,但这决不仅仅是表现纯个人的情感,而是揭示人类自然共性的客观存在,因而它是人类普遍情感的物质载体。正如美国当代哲学家苏珊·朗格所说:“文艺不表现纯个人的感情,文艺要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即人类共性的情感,只有表现人类的普遍情感,才是艺术创作的任务与目的。”[⑤]如在《我们的时代》中,作者将日本青年的精神世界扩展到以“性”为中心的整个思维、行为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生命和迷惘浓缩凝聚,呈现着当今人类困境中令人窘迫的画面。”虽然在其中,大江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南靖与赖子之间的性关系、性行为,但作者显然赋予这些“性行为”的是一种符号,积淀其上的是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精神需求等。所以,这种符号我们姑且将它看作是一种揭示人的价值伦理观念、审视人的内心世界的文化现象。大江将性的描写远离了人的情感,通过它来探究人的生存本质。用现代符号美学、现代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大江作品中对性欲、性关系、性行为的描写,更多的是一种符号的组合,这种符号的组合有两层含义:一是符号本身的含义,它感性的组合形式是词、词组、句子组成的符号系统,它是由感觉器官接受的表示成分,它是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式的依据是纯粹的文学惯例和准则。在《性的人》中,以丁为首的一帮年青人,他们无聊地生活着,他们驱车旅游,他们在远离城市的乡间别墅里酗酒、喧闹、放纵情欲。这些都是生活的表面现象。而作者的宗旨是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是符号美学理论所要阐述的第二层——象征层,它是一种被表示的成份,这是一股暗流,它才是作品的“精髓”所在。伟大的作家总是要透过这符号现象来把握这“精髓”。因此,一部文学作品重要的不是揭示感性的艺术表象,而是那种在表象遮饰下深潜的“真象”。这种“真象”具体在大江的作品里,就是对人性作更深层的开掘,以表现现代日本人精神与灵魂的嬗变,揭露人类竞争背后潜藏着诡诈的趋向,以此将“人性的力量与弱点;人性的荣耀与悲哀;人性的沉浮与变异”统统坦露于世。大江在《羊》里,将这一“真象”表现得最为充分。从符号表层性叙述来看,《羊》反映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象绵羊一样驯服、软弱的人,纵然在遭到欺凌、侮辱时仍不能激起反抗。在这里,“我”是个被否定的对象,“我卑微、胆小、缺乏自尊和民族意识”,而“教员”是位启蒙他人,拯救他人的“耶酥”。然而在这符号表层叙述含义的背后,作者意要揭示的是人性中的阴暗、肮脏的一面,以牺牲他人的名节来成全自己的崇高,这是一种对他人实行心理虐待从而显示自己完美的阴暗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表现。大江对所谓:“正义化身的冷澈质疑”是其他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大江预示性、形象化地挖掘人性的深层,将人性中最卑下、最阴暗、最原始的底层抖露,表现了作者的创作贯彻始终的是对理性的追求。
二、形式技巧的选择
大江作为日本现代派代表作家,他对文学观念的更新、作品主题的表现以及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上的更新,都与日本战前传统文学作家不一样,大江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突破摒弃了那种追求肤浅的外在冲突,缺乏对人的内部精神领域开掘的传统写法,而刻意表现战后社会政治、经济变动中转换了的当代意识,展示了战后的人际关系和人物的心态变化。”[⑥]他用“带有现代意识的全新的艺术形式,以荒诞的隐晦、离奇的暗喻、混乱的抽象、象征的烘托来深刻地反映现代日本人对社会的厌恶、绝望感。”因而他的小说具有反传统的色彩。如同样写人物的心理世界,“私小说”多以个人的彷徨、苦闷为结构中心,他们将个人与社会对立,展现的是社会对个人欲望的摧残,在他们心灵深处,多为内部情感的失控,原始的情感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岛崎藤村在《春》里描写了“我”和一批青年由对社会、人生、艺术的热爱跌落到黑暗专制制度的深渊,作者真实、细致地描写了这些青年人最终离家出走或自杀前的心理状况。在《新生》中,岸本与前来料理家务的侄女发生了暧昧关系,致使侄女怀孕,岸本害怕自己同侄女的违背道德的行为败露,曾一度想轻生,作者用心理描写勾划了岸本胆小、自私、利己主义的思想特征。田山花袋的《棉被》展现了时雄对女弟子的爱欲,作者充分地展现了时雄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雄的欲望澎胀着,他那生机盎然的原始生命力在强大的世俗社会面前遭到了压抑与毁灭。“私小说”作家们描写的是人物内心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目的是对人类行为方式与现实关系作社会的、心理的分析,从而间接地达到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大江在继承“私小说”心理描写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开拓,他更多的是表现人物心理内部的矛盾冲突,他力主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他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内字宙,应该是文学描写的对象,无论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还是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的精神远比他外在现实深远、宽广得多,因此,文学的反映功能是通过人的心理过滤和折射面表现出来,通过人物的意识活动、内省经验的表达来达到间接地感知社会现实。大江虽然象“私小说”作家那样竭力捕捉人物心理的每一层细微波折,但他能从这波折皱纹中传递时代的信息,通过对人物深层意识的揭示来确立人物主体岌岌可危的地位;并通过人物的内省精神或人物在某种情境下的内心体验来把握现实的真实。这种仰仗人物的深层意识,往往容易导致人物的情绪化,人物性格的模糊、浮泛和解体,使人物更多地成为作者一种深层批判意识的载体。《死者的奢侈》就是通过深层意识投射到尸体来反映战后日本的混乱,人们价值观的错位与失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和隔模感。
另外,“私小说”作家在表现某个主题时,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和描写发生在身边的琐事,将个体与群体分开,人与社会隔离,以暴露自我为宗旨,从不重视虚构、想象,因而缺少创造性,而大江却不然,他势衷于在“虚构与现实相重叠的世界”中驰骋,难怪瑞典皇家学院称他的作品是:“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把生活与想象浓缩成今日人类困境令人惊悚的形式。”[⑦]大江这种借助虚构与幻想的表现手法,既深深地烙印着东方传统的泛神论式的自然观和日本式“部落”的传统观念的印迹,又带有浓郁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文学色彩。大江在他的作品里大量地导入日本传统文学中的想象力(玄虚)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幽玄),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真实”。大江是位熟谙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作家,他在自己作品里借(玄虚)和(幽玄)来伸张自己对政治的关注,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患。在《洪水淹没我的灵魂》中,作者将反核思想融入虚构的神话世界里,在这神话世界里,大江揭示了当权者的残忍,反映了年青一代的沮丧与失落,同时具体阐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江用这种非现实性的虚构,融现实、神话为一体,以此来揭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大江有意采用隐喻性或象征性的情感意向,目的是有意抹去现实的具体针对性,或者模糊社会背景、超越具体时空界限,造成现实与幻想交融的情景,导致小说的艺术世界与客观现实的疏离,从而达到在“破碎的意象堆积”的上面重建某种理想或形式的整合。《万延元年足球队》这部被称为现代传奇小说,作者就是将小说的背景置于虚构的森林、山村,这个森林、山村是作为主人公归宿的领地而设置的,密三郎夫妇由于生了一个残疾儿子,双双陷入绝望的境地;鹰四则因为生活无目的,空虚、无聊而出走美国。他们对现实生活厌倦、惶惑,倍感个人的孤独,于是决定去寻找一块心灵的“绿洲”,在这块“绿洲”里,他们寻根访祖,想从祖先那里得到一帖仙丹妙药,来医治自己的“绝症”。作者通过一幅幅离奇怪状图画的镶拼,组成人类关注的主题;即人类怎样从不自由走向自由。正如大江所说:“我的文学特征在于虚构渲染现实,不是藉现实进而令虚构成为真实。二者泾渭分明,却又随意叠加,我只是想基于自己的想象力,描写相去甚远的两类事物,并将这种小说家的心境传导予读者。”[⑧]
以上笔者从大江作品在主题意向的表达和形式技巧的选择上比较了与“私小说”的异同,从而论证了作为现代派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创作上仍与传统的“私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说明“私小说”这种文学传统不会衰竭,因为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它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开始呈现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靠拢的趋势,它那“暴露式”、“告白式”个性特征,正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主脉相一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注重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深入挖掘人的潜意识领域,着重自我的心理体验和直觉性的感悟。“私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同时转向描写自己,转向内心世界,证明“私小说”与世界文学同步;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们把文学创作的焦点盯在表现个人对周围世界的复杂现象的模糊情感与感觉,从而使作品陷入了“与外界隔绝的自我表现的狭小范围。”这种以自我存在为本体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和“私小说”的唯情绪主义的认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其共同的特征都是人为夸大人的感觉、欲望、情绪和本能。今天,在我们迈向21世纪时,由于传播媒介的科学化和电脑的普及化,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毫无防护地互相接触、侵入、穿透。在文学形式多样化的时代里,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界限将被打破,“私小说”多样化也势在必然。
注释:
① ④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第331页;第69页。
② ③《世界文学》95.1期 第292页;第293页。
⑤R·巴特《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第18页。
⑥孛德纯《战后日本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第198页。
⑦《南京社会科学》,1995.2期 第70—71页。
⑧《外国文学评论》,1995.1期 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