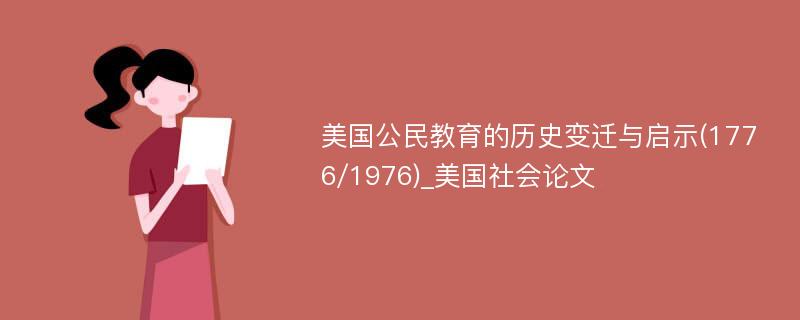
美国公民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启示(1776-197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美国公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1.011 美国是高度重视公民教育的国家,认为公民教育关乎国家存亡。阿尔蒙德曾断言:“没有公民就没有共和,没有教育就没有公民。没有学校,公民不过徒有其名。”①这是对公民教育的经典概括,但并非原创。早在美国建国之初,托马斯·杰弗逊就已经认识到,民主公民的知识、技能和行为在人们身上不会自然产生,必须通过有意识的教导才能实现。200多年以来,“民主公民”(Democratic Citizenship)教育一直备受重视,被当成是美国公共教育的理性基础。美国以公民教育之名,却行政治教育之实,其公民教育的成效有目共睹。美国公民对本国、本民族的归属感普遍较强,对美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也普遍较高,政治参与意识强烈,且美国对他国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渗透也“卓有成效”。本文试图对美国建国以来200年间的公民教育发展历程做一梳理,探讨其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历史变迁,揭示公民教育发展演化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1776-1861年:美国公民教育的萌芽期 殖民地时期美国的教育基本上是欧洲教育的翻版,公民教育也不例外。但在独立战争以后,美国便开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公民教育模式。从独立建国到南北内战,美国处于一个力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影响,建立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体系的特殊历史时期。与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相适应,美国公民教育以摆脱殖民色彩、构建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培养民族精神为核心内容。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合众国的创建者们认为,这场革命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或社会上的,因而在他们看来,新的国家所需要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作为达到学术卓越、个人自我完满的途径或为工作而做的准备。他们更多是把教育作为自由、公众意愿、公共利益的奉献这类目标的实现路径,而不是为了自我提高或职业准备。历史或政治类教科书也以渲染民族凝聚力的价值、对国家和自由的热爱为主要功能,民族认同和“美国主义”成为美国公民教育重要的价值导向。教育过几代清教徒的《新英格兰识字课本》中讲解字母W的句子,从“大海中的鲸,也服从上帝的声音!”变成了“伟大的华盛顿英勇,他的国家得以拯救”②。华盛顿饱受溢美之词,几乎成为了朝拜的对象。另一本1797年的教科书中评价他是“在世界舞台上出现过的最无可挑剔的、最完美的、最接近上帝的人物形象”③。在建国后的半个世纪里,学校公民教育最有影响力的载体是拼写书和阅读书,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是“让孩子忠于国家和民族”“爱国感情和对上帝的虔敬不分先后”以及“爱国主义作为美德的基石必须被视为最崇高的社会美德”④。 历史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开国元勋们的特别重视。杰斐逊在1779年提议弗吉尼亚州立法设立公立学校时谈到,“从本法看来,没有什么比给予人民保卫其终极自由的武器更重要,更合乎法律了。为此,人们首先要有阅读能力,由此可以接受完整的教育,主要是历史教育。通过学习历史,人们能更好地决断未来。历史还能教会人们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经验。历史能使人明断是非、提高素养,历史能使人了解在各种伪装下所深藏的野心,了解了历史,才能提出更好的观点”⑤。作为美国民主传统的奠基人和建国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家,杰斐逊为美国的公民教育构建了理论与实践基础。美国前联邦教育部长威廉·J·贝内特(William J.Bennett)曾就美国教育改革问题指出,“杰斐逊曾列出他所处时代的良好公民教育的内容:写作、计算和地理知识,还有‘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能力’。这种强调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学习知识、技能相结合的教育思想仍然是或应该是当今美国教育的基础”⑥。 除了历史,对有关政府知识的传授也成为公民教育的另一项基本任务,但这基本局限于高等教育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生们才是最需要学习有关政府知识的人,因为他们最有希望成为理性的公民领袖,投身公共服务之中。华盛顿在1796年最后一次给议会的咨文中指出,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对年青一代进行关于政府的科学的教育。在一个共和国家,还有哪一门课程是同等重要的呢?又有什么比制订计划将这些知识教授给国家未来的守护者们更迫切呢”⑦?杰斐逊正是在华盛顿这一观点的鼓舞下,于1818年创立了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他明确指出此举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公务员、立法者和法官,因为公共事业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都仰仗这些人。 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公民教育很少教授政治知识,也未明显尝试培养学生的政治参与技巧。这一任务在客观上是由初期的政党以及城镇聚会、教会、咖啡屋和小酒馆来完成的。在这些地方,人们聚在一起谈论政治、交流观点。正如当时《联邦主义者报》备受追捧所体现的那样,报纸在散布真实或偏颇的政治知识方面可能比学校做得更多。 总之,从建国初期到美国内战这一段时间,公民教育的核心理念直接源于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的美国《联邦宪法》。这两份文献奠定了两百多年间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成为美国公民教育的启蒙宝典。“美国人在确立美国革命的意义和自由政府的本质的同时,也为美国公民教育的演进确立了一个理性的方向,以后的美国公民教育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朝前发展的。”⑧这一阶段,美国公民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构建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培养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就是“美国化”,即培养美国人对美国文化和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忠诚感,使之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员,从而造就具有国家和民族意识、公民意识的共和国的健全公民,而不是原宗主国的臣民。 二、1861-1914年:美国公民教育的成长期 19世纪后半叶,美国在政治上通过南北战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在经济上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而跃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进入“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美国迎来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成长期。经济成就和“西进运动”推动了教育界对“美式价值观”的宣扬和歌颂,而大批新移民的涌入也给美国公民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 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公民教育所灌输的价值观相较于共和国的头一百年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在自由平等、爱国主义、乐善好施的基督教道德这些华丽灿烂的价值观之外,又加上了中产阶级尤其是新英格兰中产阶级的道德诉求,包括勤劳、诚实、正直、个人努力、对合法权威的服从等。路斯·埃尔森对数以百计的教科书进行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与许多现代学校用书不同,十九世纪的教科书刻意回避在当时太具争议性的话题,同时在基本的信仰问题上坚定而刻板地持守着传统。价值判断是惯用的手段:对国家的爱,对上帝的爱,对父母的责任,培养一系列良好习惯如节俭,诚实,苦干,以积累财产,还有就是要确保进步,让美国更完善。整个国家内部的任何巨变也不能偏离这些基本价值观。从教学法方面看,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学校书籍经历极大变化,但价值观的持续性却丝毫不受影响。不论是南北战争还是19世纪90年代都未出现基本价值观的分水岭。”⑨ 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充斥着对美国及其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观的颂扬,但多以情感渲染为主,缺乏理性的知识分析。正如埃尔森所说:“所有的书都同意,美国从政治上表达的是如福音般的自由,一种拟人化的自由,派以使徒,献以颂歌,置于神一样的荣耀中,却很少为其下定义。在这些书中寻找自由权的意义是个阴郁的难题。儿童读者们可以确定,自由是荣耀的,是‘美国’的,是应予尊重的,而且值得他给予头等忠诚。但这个孩子要是能从这些书中找出自由是什么,则会令人震惊。”⑩ 杰斐逊主义者班戈洛夫认为,19世纪的教科书绝大多数都是倾向于联邦主义和保守派的。“虽然这些书籍的作者们自认为是自由的守护者,但把他们形容成传统的守护者却更为准确。对于社会问题,这些书从来都很保守。美国一直与自由的形象联系着,但这自由应该定义为1783年从大不列颠分离时确立的那种自由。在这一阶段,美国公民教育开始有意识地渲染所谓的“美国精神”。但在教育实践中,这种对“美国精神”的宣扬,更倚重的是对学生情感上的影响,而不是建立在对政治知识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 直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在公民教育领域普遍流行的观念开始形成,即在教科书和课程中应增加更为严谨的所谓“学者型知识”。由哈佛校长伊利亚特带领的国家教育协会10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Ten)(11)是这种观念的主要代表。他们的主要构想是,历史教学不再只是为了培养好公民和爱国感情,而是要教会学生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12)。10人委员会的学术倾向主导了此后20年间公民教育的教学思想和课程构成。在历史课方面,强调的是用第一手资料来培养学生的历史感,训练他们查寻历史资料,权衡证据并得出结论。为了让青少年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学者们希望将前一个世纪浮夸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历史彻底“撕掉”。比如,1899年,美国历史协会一个7人委员会力促用第一手资料来补充教科书;1909年创刊的《历史教师杂志》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亨利·约翰逊都主张在实验室或工作间环境下的历史问题“解决”和有理有据的判断。 另一方面,移民问题开始成为公民教育的新挑战。在很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看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们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巨大威胁,他们威胁到民主政治社区的认同感,威胁到宪章制度的稳定,威胁到政府权威的行使。保守主义者甚至把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居住区、街头犯罪、工厂中的恶性罢工、地方政府的腐败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蔓延等,都归罪于移民。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会在1907年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新移民”问题,引发了名曰“美国化运动”的公民教育活动。在各地教会、企业界和教育机构的支持下,这场运动很快遍及全国。在不同地区,运动的形式和规模各有差异,但在内容上,基本上都是通过创办夜校和培训班的形式,为移民设立历史、文学、法律、数学、政治和公民学等课程,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帮助他们归化为“真正的”美国公民,为美国的发展作贡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各地都成立了帮助外来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社会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纽约市教育联盟”(New York Education Alliance)、“费城希伯莱裔教育协会”(Philadelphia Hebrew Education Association)、“青年基督教协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和“外来移民北美公民联盟”(Im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 Citizens Union)等。为了协助各地的“美国化运动”,美国移民局印制了《公民教育大纲》和公民培训班毕业证书,待移民结业时一并颁发毕业证书和公民资格证书。为促进移民归化事业,美国还专门建立了“全国美国化委员会”(National Americanization Movement Committee),并将1915年7月4日定为“全国美国化运动日”(National Americanization Movement Day)。为了扩大声势,激起全国公民和外来移民的热情,该委员会要求各地的所有居民参加这次活动,各地的居民和社会机构都必须悬挂美国国旗;同时,该委员会又与全国62家铁路公司和数百家商贸公司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它们在全国各地张贴了5万多份海报,宣传庆典活动(13)。 总而言之,虽然作为美国社会根基的基本价值并未发生激进变革,但在半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迅速转型,造成了公民教育的两个重大改变。首先,之前强调的对一个广阔而自由的国家的爱变成了对一个伟大而强大的民族充满激情的献身。证实命运的理想,赢得西方的理想,海外扩张的理想,使得美国将自身当成世界上更高层次的国家,满载着带领世上其余国家的使命,并因此应该,甚至是要求对“我的国家,无论对错”绝对忠诚。所有的这一切给公民教育造成了一个日益显得民族主义的刺耳腔调。其次,大规模移民引发了公民教育的第二个改变,即移民的“美国化”。无论是移民机构、爱国主义组织、本土主义协会还是公民教育教科书,都一边倒地宣扬移民“美国化”的观念,这对于美国社会的整合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1914-1945年:美国公民教育的勃发期 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均免遭战火的侵袭,反而紧抓历史机遇,实现了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这也为公民教育理论范畴和实践形式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础。1916年始,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陆续发布《中等教育中的社会科》(Social Studies in Secondary Education)、《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等报告,提出美国公民教育应由民主观念引导,要注重公民的社会参与,把社会科课程作为学校公民教育的主要载体,并将胜任公民职责作为中等教育的七大目标之一。该系列报告对美国公民教育影响深远,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公民教育开始的标志。 在美国,社会科(Social Studies)是一门根植于社会科学基本概念与原理的课程,但并不等同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而是自有其独特的内涵与目标。《中等教育中的社会科》将社会科的范畴定义为“凡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组织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皆是,因为人是社会团体的成员”(14)。“社会科”一词涵括的科目不仅有《历史》《公民学和政府》,还有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直接与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而发生关联的那一部分内容。至于目标设置,“社会科要随时谨记的目标是培育好的公民……即使一个人效忠他的国家;一个国家要和睦,其成员必须了解国家的理想,尊敬、效忠国家,就像一个家要和睦,其成员必须团结、自重及忠于家庭”(15)。相比之前的公民教育,它“降低了与政治的关联,而重视社会经济和实际的私人问题。公民参与的技巧也成为教育目的的一部分。社会科在培养目标上要求更高也更为广泛,既包括培养学生对美国社会的忠诚,也要求培养学生参加地区社会的积极态度,以及适当的职业观、处理个人及社会问题的能力。民主的校园生活成为迈向民主社会生活的缩影”(16)。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对美国公民教育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使公民意识成为社会科的根本教育目标,在教学上倾向于将抽象的学术素材让位于活生生的问题,将公民教育中对政治的考量让位于社会、经济及实际的个人问题。总而言之就是实现了从“宪章问题到追求良好公民意识的转变”(17)。正是缘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社会科由此成为美国学校的核心课程,美国公民教育也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当然,公民教育的革命性转变也伴随着传统保守力量的阻碍。一战后,由一些保守的公民和爱国组织发起的、以“反外国、反太平洋、反移民、反改革”为口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偏激的爱国主义运动,对新的公民教育的开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The American Legion)在20年代多次发起运动,要求议会和各州立法机构制定法规,在公民教育中加入“向国旗致礼、宣誓效忠以及军训”的内容,借此将国民精神团结在美国国旗周围,并且要赞颂作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美德和成就,而不允许有任何贬损之语。 进入30年代,为应对资本主义经济萧条而产生的社会改良主义,也自然对公民教育产生了影响。美国历史学会社会研究委员会受卡耐基基金会资助,于1932年到1937年间出版了17卷书籍。这些书所表达的主导论调可以在《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1934)》中窥其一斑:“个人主义和经济与政府的自由放任时代正在结束,一种要求社会规划和政府调控的新集体主义正处于新兴阶段。富足之中的掠夺、收入的不平等、失业率的上升、自然资源的浪费、犯罪和暴力事件的增多、公共福利让位于个人利益以及对原材料的国际争夺,正是这种要求提出的社会背景。为此,即便不需要设置特别的课程,青少年们也应该被灌输以经济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相互依赖的思想,以取代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同时,继续促进个人和文化方面的个人主义和自由。”(18)抱有类似观点的还包括乔治·S.考斯等“社会重建主义者”。1934年,作为《教育前线》的主编,考斯签署了将美国历史学会的《结论和建议》作为这份新杂志指导政策的决定。 “社会重建主义者”对公民教育增强其“社会性”的呼声引发了众多专业组织的积极响应,但同时也招致了诸多甚至是尖锐的批评。如国家教育协会下属的教育政策委员会,通过对教育与民主关系的阐述,来反对“社会重建主义者”的观点。1937年,该委员会出版了查尔斯·A.伯德(Charles A.Beard)的《教育在美国民主中的独特功能》一书,强调了民主意识是教育的中心主题。威廉·G.卡尔1938年执笔的《美国民主中教育的目的》中,确立了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分别是:社会公平(公民要对人类状况的差异保持敏感)、社会活动(公民会采取行动以改变令人不满的状况)、社会理解(公民能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关键决断(公民对政治宣传要有防御力)、宽容(公民要尊重意见分歧)、节约(公民要对国家资源有所考虑)、世界公民意识(公民是世界社区的合作成员)、遵守法律(公民应尊重法律)、经济能力(公民对经济有认识和运用能力)、政治公民意识(公民要接受其公民义务)、献身民主(公民能以毫不动摇的忠诚为民主理想而行动)(19)。 显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官方意志的公民教育机构及其成员们,更着眼于让公民教育贴近社会现实,更为“实用”,而尽力避免他们眼中“激进的重建主义”或“反动的激进主义”这样的极端思想,“最终回归到民主的基本理想,回归到能让学生们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却不参与有争议的话题”(20)。 30年代法西斯势力在国际政治中的崛起以及1939年二战的爆发,推动了爱国和民主再度成为学校公民教育的主旋律。美国不仅要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与法西斯国家作战,而且扮演着二战中“世界民主的堡垒”角色。公民教育不仅要激发民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他们在前线和后方支持作战,而且要以“民主”为武器、在意识形态领域防止法西斯思想的侵蚀,并与之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四、1945-1976年:美国公民教育的回落与反弹期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并开始了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冷战”。在“冷战”初期,美国教育的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倾向日趋明显,教育同国家安全、科技发展同综合国力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阶段的美国公民教育受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更加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对抗性,而公民教育的理论、方法途径等方面则被极大地忽视了。为“冷战”和国家利益服务,成了制定教育政策的根本依据。正如梅逊在论述“学校作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时所指出的,“鉴于这种情况,按照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来制定教育标准的趋势增强了。因此,一个刚入学的聪明儿童,越来越不被看做是一个未来的诗人、画家、音乐家、文学家、评论家、宗教领袖、哲学家、小说家,甚或是政治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技师、工程师——一个工艺技术王国里的预言家和牧师。人们把生产和创造看成是制造大机器和创造新技术”(21)。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新科技革命的影响,美国公民教育的理念、政策、内容等均发生了变化,公民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抵制共产主义的武器。在“赤色恐惧”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治气氛中,公民教科书开始刻意夸大苏联的威胁。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在其第32册年刊中发表了它下属的公民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on Educating for Citizenship)提交的报告,宣称苏联共产主义威胁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自由民主信念,呼吁公立学校加强公民教育。该报告指出:“美国公民经常用他最大的力量去努力实现本国历史上的观念。现在,当共产主义者的霸业威胁到各方面的安全时,公民对这种旧有的观念有一个新的赞赏——把这种观念作为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的一种永不动摇的基石。这种旧有的观念,就是指美国人民最多地依赖于公立学校这种途径来确保所有儿童能够继承美国的传统。所以现在,公民们要求学校进行公民教育、培养合格的公民比过去更为迫切。”(22) 公民教育委员会认为,苏联共产主义在政治上威胁到西方的民主自由,最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威胁着西方“自由世界”人们的道德和精神观念以及宗教和伦理标准,所以学校应当加强公民教育,传授公民知识,培养学生的公民态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同他人合作来促进社会福利的技能。显然,这种直接将公民教育开展的目的定位为“解决政治对抗或威胁”是偏激的,是冷战时期的特殊政治产物。 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学生校园暴力骚乱的愈演愈烈,美国政府和社会开始对公民教育进行反思。特别是在理论界,公民教育愈来愈成为争论的焦点。伊利诺伊大学的克拉伦斯·凯利尔认为,公民教育的历史就是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的稳步胜利,而学校对国家的这种胜利负有部分责任。凯利尔认为学校不应该教育学生对政府或宪法的忠诚,他对学校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持悲观态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马文·拉泽森认为,既然公民教育不允许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存在合法的根本性差异,因此,除非国家本身发生变革,公民教育的变革绝无可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迈克尔·B.卡茨指出,历史的本质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学校总是站在上层阶级那边,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并非心甘情愿的下层阶级。因此,卡茨认为学校教育应该保持价值中立,只教授基本的学习技能。他同样对公民教育持悲观态度。 相比之下,著名公民教育家沃森认为,政治的“多元”仍是公民教育可取的目标,而且学校应该尽力在每一代公民中生成民主政治意识。他赞同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所说的,共和国的福祉确实有赖于受过教育的公民。一个真正的公民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赋予所有人民行使权力的力量,以完成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公民的职责。沃森还认为,公民教育应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社会、政府和公民的性质,在过去200年里已经发生巨变。所以不应满足于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的公民教育课程。像杰斐逊提议的那种简单的历史教育,或者华盛顿提议的公民政府要素的教育,都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对道德、精神或政治美德的说教式呼吁是不够的,对特定经济或意识形态平台的党派灌输也是不恰当的;教科书的编写也不应交给在社会或政治上保守的作家。当然,学校的确有责任竭尽所能教导现代民主公民所需的价值观、知识以及参与技能。这些任务不应像革命时期一样留给政党、报纸、部长或者咖啡馆,也不应像现在常常发生的那样交给现代企业、工人领袖、电视评论员或者特殊利益辩护人。学校仍然要承担主要的公民教育责任,以服务于社会公共福利。 最终,这场论战的结果就是,学校公民教育应该更加科学化和社会化,特别是公民教育的教学法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两种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方式方法最具代表性,分别是“社会科学学科内容方法”(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Content Approach)和“反思性探究/批判思维方法”(Reflective Inquiry/Critical Thinking Approach)。其中,前者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所谓的“新社会科”(New Social Studies)时代达到鼎盛,这种教学方法侧重于社会科学学科基本结构和方法的教学,通过传授若干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使学生成为良好的公民。在学界有很大影响力的“新社会研究”运动,主张公民教育要采取社会科学的新模式,包括认知分析、对有组织的知识的系统掌握、概念分析、询问型学习、探索法。简而言之,就是强调公民教育工作者像社会科学家一样思考。第二种方式是利用批判的和反思质疑的方法对社会重点问题和争论进行分析和评价,培养学生辨析、决策的技能,以促进“参与式公民”(Participatory Citizenship)的养成。 对于这两种公民教育方法的优劣和所面临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民主社会公民教育的任务正处于极富挑战性和持久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民主社会致力于促进公民行使自由,这就要求必须重视价值多元性的存在,如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和知性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无论是民主的社会,还是非民主的社会,都应该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和公民意见的一致性。这样在政治自由及多样性的目标和社会一致性共识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在如何进行民主社会公民教育的问题中引起了冲突和论争。”(23)总而言之,在这两种处于竞争态势的公民教育方法中如何进行抉择,就是在面对公民发展的难题中如何保持合理基础知识与反思质疑能力及批判精神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这两种公民教育的方法,也代表了美国70年代公民教育的两个主要理论流派及其教育观念。两大理论流派在美国公民教育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影响了70年代至今美国公民教育的发展。系统传授公民知识、技能与培养批判、质疑精神,正是在此时开始成为美国公民教育的两个主要目标和内容。随着公民教育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自70年代后,美国把公民教育课程教学作为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载体在全国普及。这标志着美国公民教育开始从低谷反弹。 五、评价与启示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说过:“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24)通过以上对美国公民教育200年历史发展的梳理可以看到,美国公民教育的历史几乎与其国家的历史相重合。这表明,美国的政治家、政府和社会历来都重视公民教育这一有着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教育实践活动,对其可谓常抓不懈。并且在对待公民教育的态度上也一贯旗帜鲜明,正如美国教育家卡扎米亚斯所说,“即使在具有民主传统和声称民主之冠的国家,也必然要进行政治灌输和禁止异说,这是很实际的问题”(25)。 纵观美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历程,尽管每个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主题内容、基本特征等都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很大差异,但在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观上却保持了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公民教育的根本目标上,始终表现为倡导资本主义优越性、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培养对美利坚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教授民主社会政治参与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在公民教育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上,始终逾越不了资本主义关于人性解放、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观念。正是基于这些核心的教育目标及价值观传递,使得公民教育在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上发挥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美国公民教育历史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保持一致。公民教育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社会及政治文化的变化,及时在内容、方法上进行调整、更新,不断在实践中对自身的理论缺陷和偏差做出修正,进而较好地实现了公民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使得民众对“美国梦”、国家精神及政治体制的认同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 思想政治教育(在美国表现为公民教育)是人类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根本上来说,都是为解决民众的“政治认同”或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受社会发展条件制约,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时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乃至教育模式不尽相同。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积极挖掘、配置、利用各种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极力增强和巩固本国民众对本国政治体制的认同。在与美国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政治制度背景下,开展政治认同及其教育的国别与比较研究,坚持“洋为中用、去伪存真、经科学扬弃后为我所用”的原则,有利于揭示和认识政治认同产生与政治认同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丰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营养,有利于批判地吸收借鉴外国政治认同教育的有益经验,提升我们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自觉自信,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认同教育。 ①Gabriel A.Almond,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35. ②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历程》,谢廷光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83页。 ③滕大春:《美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④Ruth Miller Elson.Guardians of Tradition:American Schoolbook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4,p.282. ⑤R.Freeman Butts.The Revival of Civic Learning:A Rationale for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Chicago: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1980,p.55. ⑥朱旭东:《杰斐逊教育思想的现代性阐释》,载《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9年第6期,第76页。 ⑦R.Freeman Butts.The Revival of Civic Learning:A Rationale for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p.56. ⑧高峰:《美国政治社会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⑨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⑩W.F.康内尔:《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张法琨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11)19世纪后期,中等教育存在的各种显形或隐性的问题引起了关心教育的开明人士的注意,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校长伊利亚特。他们决定对公共中等教育进行实证调查,从现状入手,力图对中等教育进行一次大的改革,于是,“十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Ten)应运而生,这个委员会的宗旨为“调节和协调中等学校和大学的关系”。 (12)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朱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7页。 (13)Edward G.Hartmann.The Mowment to Americanize the lmmigrant.New York:A.M.S,1967,p.118. (14)M.R.Nelson.The Social Studies in Secondary Education:A Reprint of the Seminal 1916 Report with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http://eric.ed.gov/?id=ED374072,2013-10-29。 (15)Commiss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The Social Studies in Secondary Education.http://www.jstor.org/stable/1824486,2014-12-15。 (16)富兰克·布朗:《美国的公民教育》,陈光辉等译,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67页。 (17)丹尼尔·坦纳、劳雷尔·坦纳:《学校课程史》,崔允漷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18)R.Freeman Butts.The Revival of Civic Learning:A Rationale for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p.68. (19)Educational Policies Commission.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in American Democracy.Chicago: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1938,p.108. (20)R.Freeman Butts.The Revival of Civic Learning:A Rationale for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1980,p.129. (21)罗伯特·梅逊:《西方当代教育理论》,陆有铨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22)R.Feeeman Butts.The Civic Mission in Education Reform:Perspectives for the Public and the Profession.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9,p.194. (23)S.H.Engle,Anna S.Ochoa.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88,p.28. (24)杰里尔·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345页。 (25)A.J.Ryder.Twentieth-Century America:From Bismarck to Brand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p.69.标签: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史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公民教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移民论文; 经济学论文;
